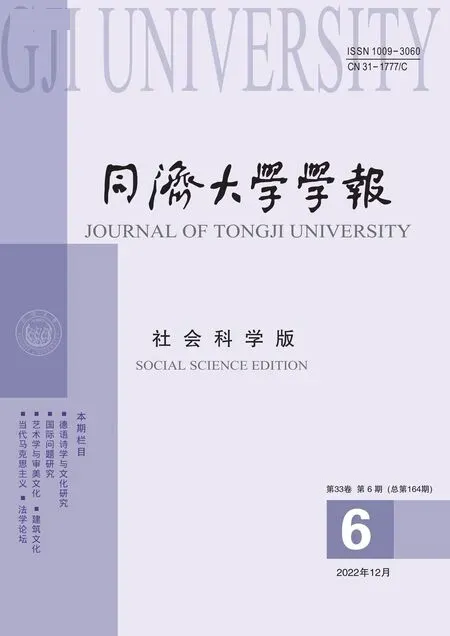话语生产、视觉建构与再媒介化
——当代中国短视频文化的乡村叙事实践
2022-02-11柴冬冬
柴冬冬
(杭州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 杭州 311121)
20世纪以来,在中国剧烈的历史变迁中,乡村、土地、农民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走向,成为革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心(1)韩文淑:《新世纪中国乡村叙事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页。。在此背景之下,书写“乡土中国”成为现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绕不过去的一个母题,乡村(2)本文将“乡村”视为一个与“城市”相对应的概念,不仅指代发生在乡村范围内所有人、事、物的活动,还是一个包容文化、历史、社会、政治、地理等内涵的综合性符号。开始在不同的层面被频繁叙述,逐步构建出了一种世界文化史上独特的“乡村叙事”景观。进入数字文化时代,以短视频为代表的自媒体文化凭借其独特的视觉修辞和文艺消费潜能开始频繁介入到对乡村的叙述活动中(主要表征形态为乡村类短视频),使传统乡村文化的存在样态、审美品质、传播方式、社会功能都发生了转变。由此,一种新的乡村叙事范式开始出场。厘清这一范式的内在生产逻辑,将助力把握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及其文化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所涌现出的新特点与新问题,对乡村文化振兴也具有一定意义。
一、 短视频文化与乡村叙事的嬗变
乡村成为中国文艺的叙述内容并非一个现代事件,而是古已有之。从春秋时代的《诗经》开始,就有对乡村风貌、乡村生产和生活场景的描述,如《风》中的《硕鼠》《桑柔》《民劳》等。魏晋以来,中国诗歌逐渐形成田园叙事传统,大量文人热衷于乡村意象的创造,创作出了大量乡村题材作品,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王维的《田园乐》、白居易的《观刈麦》、翁卷的《乡村四月》、陆龟蒙的《五歌·放牛》、张耒的《田家》、杨万里的《悯农》等。它们或是描绘乡村生活场景,或是表现农业生产的快乐与艰苦。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并从诗词领域扩大到小说、戏剧、绘画艺术,它们构成了古人对乡村的认知、想象与再现,开辟了中国古典文艺生产的重要领域。然而,这与现代性意义上的乡村叙事并不相同。因为古代文艺对乡村所展开的叙述是以有限的乡村风景、乡民生活与农业生产为对象的叙述活动,是一种偶发性的叙述。不仅如此,因受制于创作群体、传播范围与传播媒介,其影响是十分微弱的,也并未与整个社会的转型与发展紧密绑定在一起,更不带有“乡土中国”的底色。这种叙述活动虽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联,但并未体现一种基于乡土的传统文化传承性。由于彼时乡土中国还未暴露在世界面前,我们很难从中看到乡村所蕴含的更为丰富和复杂的文化、伦理与社会内涵。
乡村开始展现出更为深刻的艺术性和社会意义,并成长为一种叙事性话语,是伴随着中国的现代性(化)进程而展开的。自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自身的社会结构和发展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大众的社会心理、情感体验、思想范式也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被重塑,这使得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思想谱系逐渐式微,新的现代性思想体系开始在中国的文化知识和社会意识生产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启蒙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全球化与多样化等思潮纷纷提出自己的历史叙事、社会规划与自我构建思想,(3)吴海清:《乡土世界的现代性想象:中国现当代文学乡土叙事思想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由此出现了东方与西方、世界与中国、传统与现代、工业与农业、个体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等诸多新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也成为新的社会构建的基本问题域。乡村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进入文艺叙述者的视野中被频繁讲述,它被表征为与城市文化、工业文化等现代性文化不同的文化。
从内容上看,这种叙述活动主要围绕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费孝通等政治家或思想家从理论层面将乡村世界纳入中国整体的现代性社会设计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或启发了文艺创作;二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陈忠实等作家以风格多样的文艺创作实践对现代性进程中的乡土中国进行描述与反思,形成了与理论层面的呼应。这是一种能够以自觉的状态、以规模化甚至规范化的形式去叙述乡村的社会结构、历史前景、生活状况、生命体验、经济发展、伦理体制、器物与民俗文化,并展现其对乡村世界的理解与规划的叙述活动。由于这些叙述与中国的社会革命与改革紧密绑定在一起,且包裹着一层艺术的外衣,其对转型期的中国反思自身的乡土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方向产生了积极影响。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所着力阐释的“乡村叙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这种叙述活动是一种审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重要“方法”。以今天的视野来看,中国现当代文艺所开辟的乡村叙事无疑已经成了一种重要的文艺生产和接受传统,且至今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属性上看,乡村叙事是以“乡村”为核心元素展开的。我们知道,乡村在传统意义上指向的是在行政区划中与城市相区别的、以农业作为经济基础并组建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具有独特自然景观的综合性文化地理空间。与乡村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乡土”。“土”在字面意义上指的是土地、土壤,它是物质性的,同时也具有社会文化层面的内涵。费孝通认为,土是乡下人的命根,种地是乡下人最普通的谋生方法,是在数量上占着最高位的神。(4)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页。土在带给乡下人生产和居住之条件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还孕育出了中国乡村独特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配的观念体系,并成长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根基。如果说乡村是一个有复杂意味的范畴,那么乡土则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视为乡村的特质,它指向的是乡村社会的内在运作逻辑及其对乡民的社会经验与历史命运的形塑。也正因此,乡村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生态学、经济学内涵,并延伸出了乡村文化、乡村社会、乡村审美、乡村伦理、乡村经济等意蕴,这构成了乡村被不断叙述的基础。
从形态上看,乡村叙事作为一种叙述活动,依然呈现为不同的叙事文,具有一般叙事所具有的属性和特征。叙事在当代叙事理论中往往被区分为“叙述话语”和“所述故事”两个层次,分别用来指涉表达层和内容层。(5)热拉尔·热奈特、里蒙-凯南、米克·巴尔等学者提出了“三分法”之说,其中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将叙事区分为故事(被叙述的内容)、叙述技巧(用于叙述故事的口头或笔头的话语)、叙述行为(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过程)等三个层面,其影响也最为广泛。不过,这种三分法也曾一度在研究中引发了混乱。因此,为了避免陷入混乱,本文采取更为普遍的二分法,同时也认为叙述和对话语(文本)的讨论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乡村成为一种叙事(叙事文)不仅依赖于乡村本身所具有的叙事性,还在于它必然包含了所述故事和叙述话语两个基本层次。这意味着,乡村叙事应当是叙述者在特定的时空语境下以乡村及乡村所指涉的人、事、物、情、景及其他相关性层面为“生产资料”,按一定的叙述方式(话语)将其联缀成叙事文,再将其传达给读者(听众、观众)的一系列事件。它既表达特定的乡村故事,又包含了讲述乡村故事的行为本身,同时二者又作为一个整体表征了整个乡村叙述活动。但在中国语境下乡村叙事一开始就与社会变革绑定在一起,由其激发并不断壮大。因此,乡村叙事的文本不是普通的叙事文,对它的分析不能脱离社会变革的话语框架。
华莱士·马丁曾指出,叙事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只要有故事的地方,就会有叙事。(6)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尽管乡村叙事萌发于文学叙事活动,但我们对它的理解绝不能陷入文学叙事的牢笼。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并在短时间内成为乡村文艺生产与接受的主导媒介。从80年代的《新星》《雪野》 到90年代的“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 再到 2000 年以来的《希望的田野》《当家的女人》《三连襟》《农民代表》,以及 2010年之后的《女人当官》《老农民》《平凡的世界》《黄土高天》《大江大河》《山海情》等,这些乡村影视作品所展开的乡村叙事与文学的乡村叙事虽存在着媒介差异,但却产生了重要的互动。它们在文本层面依然注重戏剧化呈现,其创作主体也多是专业的艺术家或艺术机构,其内涵也旨在揭示变革进程中中国乡村社会的演进、伦理的流变、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的成长。
然而,短视频这一新的视觉文化形态对乡村叙事的介入却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这突出体现在:其叙事方式从艺术化的客体性描绘变成了日常化的自我性展演。在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头部短视频平台上,乡村类短视频的内容发布涵盖了乡村日常生活所涉及的不同方面,如:“李子柒”对清泉山野、手工劳作、锄地播种、丰收采摘等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的展示;“乡村食叔”对各类乡村美食的展示;“张同学”对具有怀旧特色的北方农民日常生活的展示;“巧妇九妹”对各类广西乡村农产品的展示;“胡闹闹”对乡村劳动场景的展示;“苗家阿美”对苗族乡村特色文化习俗与美食的展示;等等。这些短视频融合了技能分享、幽默搞怪、公共热点、公益教育、广告创意等主题,表达出的是一种宁静祥和、趣味多样、风景优美、绿色健康的乡村(田园)生活新范式。尽管短视频制作者的叙述活动依然有着特定的脚本,但由于自媒体平台赋予其极大的自主性,且叙述主体多不是专业的艺术从业者,作品本身其实并不需要复杂的艺术加工,只要具备一定的特点和主题就可以进行拍摄,这使其难以像普通影像文本一样承担纯艺术性叙事,而是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日常生活性展演。在这里,乡民既是故事的直接创作者和叙述者,也是直接演绎者。他们的形象是多元化和去等级化的,从返乡青年、留守老年到劳作的女人、拼搏的男人,再到致富能手、能工巧匠、乡味大厨,这里没有等级化的人物群像,有的只是平民当下的微观生活;受到短视频媒介属性的限制,大时段、大跨度的触及社会深层结构和文化隐喻的叙事方式,在这里也少了用武之地,叙事也可以不用再主动构建启蒙、改革、反思、成长等带有宏大意识形态的内容,强烈的戏剧冲突也可以不用出场。
叙事方式变化的背后其实隐含的是乡村叙事从精英范式到大众范式的转型问题。从主体上看,乡村叙事的主体由艺术家变成了普通的乡民,尽管乡民也有着对乡村社会文化问题的关注,但由于固有的知识结构与社会阶层局限,其更为根本的出发点是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感悟与思考。他们制作短视频除了分享自己的日常、进行娱乐消遣之外,还存在着重要的商业变现诉求,而要变现就得与互联网时代大众文化的消费逻辑相媾和。而从接受者来看,他们观看乡村短视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重温乡愁情感,缓解城市生活的焦虑,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虚拟的空间中得到慰藉。因此他们更为注重短视频的消遣性,而非严肃的艺术说教。这种双向合力造成了乡村叙事最终成为大众娱乐文本。但需要指出的是,大众化并不是意味着其叙事功能的弱化。比如,文艺界曾对乡村题材影视剧的过度娱乐化倾向发出强烈批判,认为其消解了这一题材该有的反思性。但实践却表明,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依然可以窥见“中国农村发生了怎样的巨大变化,农民生活的步伐和都市节奏有怎样的联系,农村当下问题汇聚在哪些层面等等”(7)周星:《文化概念变异视野中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概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第4期,第64-66页。。如孟繁华所指出的:“乡村叙事一直存在着一个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乡村文化将在嬗变中坚守。”(8)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94-100页。可以说,只要内在文化结构不变,乡村叙事就依然可以持续起作用,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其在新语境下的生产逻辑,即具体动能、策略与效果,以此来保障它的属性。
二、 话语生产:短视频文化的乡村叙事动力
短视频文化的乡村叙事并不是偶然性事件,而是持续性的社会文化现象。据抖音平台于2022年2月发布的《乡村数据报告》显示:2021—2022年抖音中乡村相关视频增加了3438万条,获赞超35亿次;有78万人发布了“乡村游”主题视频,视频累计播放63亿次;全国网友累计打卡122万个村庄;“我的乡村生活”话题获得1043亿的播放量。(9)光明网:《乡村数据报告:生活和美食类短视频最受欢迎》,https://m.gmw.cn/baijia/2022-02/14/35516782.html,2022年2月14日。短视频不仅带火了乡村旅游,更带动了乡村的创业,使一大批乡村特产、民俗文化、特色器物得到展示和推广,使乡村文化迎来了新发展。时至今日,短视频乡村影像的数量、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传统的电影、电视媒介,开始成为我们体验乡村文化、审视乡村社会问题、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方式。
那么,为何乡村会成为短视频文化持续叙述的对象呢?短视频文化不断进行乡村影像生产的意义何在呢?如果将答案归结为乡村本身所展现的魅力和乡民主体性的彰显则未免过于简单。想要挖出深层动因,我们还需要剖析其背后的生产逻辑。麦克卢汉说,“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10)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4页;第92页。,媒介具有一种可以把人的经验转换成新形式的能力(1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4页;第92页。。作为新兴的视觉媒介,短视频对乡村图景的生产所传递出的是一系列互联网视觉观看语境下的乡村叙事景观,而这种新的叙事形式之所以会出现,正是由于短视频对当代文化生产主体之乡村经验的转换。但由于短视频作为自媒体所开放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生产场域,它在叙述事件、展现场景的过程中还受到产业、技术、审美、消费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短视频对文化主体乡村经验的转换也不是自律性的。这也就意味着,即便短视频赋予了乡民前所未有的表达其乡村经验的权利,但这种表达作为一种文化表征所产生的意义却不一定由其主体所限定,也不仅仅由短视频所表征的乡村表象所确定,而是由乡村叙事所构建出来的整体表征实践所决定的。
霍尔认为,这种表征实践要凸显哪个层面的意义其实是由表征过程的参与者进行争夺的结果,它是通过话语的方式进行的,是一种争夺话语控制权的斗争。(12)斯图尔特·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汪凯、刘晓红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39页。在话语中争夺意义控制权的斗争引起的最相关的效果或结果就是,它赋予符号(物)以意识形态性(13)V.N. Volosinov, Marxism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eminar Press, 1973, p.23.,实现对物的编码和意义的塑造。话语作为一系列陈述方式,它为表征有关某一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而各种社会实践的意义也是在话语范围内被建构的。(14)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4-65页。当然,在另一个层面上,“话语是被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受制于社会层次上的阶级和其他关系,受制于诸如法律或教育等特殊机构所特有的关系,受制于分类系统,受制于各种规范和各种习俗”(15)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60页。。按照这个逻辑,短视频所进行的乡村叙事实践在其生产、演进等动态的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意义,其实也是不同话语生产的结果。一方面,各类话语为短视频提供不同的乡村素材,并提供相应的秩序、规则、方法;另一方面,短视频和乡村作为社会结构为不同的话语秩序提供了展演的场所,它们之间的斗争赋予了乡村类短视频以不同的意义。
文化话语的生产是短视频展开乡村叙事的基本动力。短视频表征的是新的互联网文化范式,融流行性、时尚性、社交性、消费性于一身。它既具有大众性,又具有亚文化性;既呈现精英性,又呈现草根性,是一种新的文化话语。而它与乡村的融合,在促进乡村文化在展示、生产、消费等层面革新的同时,实际彰显出的是自己在乡村文化和互联网文化两个层面的话语优势。如李子柒短视频通过构建田园化与诗意化的乡村,对大量的乡俗、乡味、乡物进行了展示,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的乡村文化产品,展现出了其话语的独特特征——故事丰富、形式新颖、趣味多样、生产简单、传播迅速、受众广泛。它在作者和观者层面都有着比传统乡村叙事文本更多的文化资本,并有着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转化的优势。对平台来说,鼓励和扶持乡村类短视频创作有利于攫取流量,实现商业变现;对企业来说,乡村类短视频的火爆可以助力相关农产品或农村文创产品的销售;对普通乡民来说,创作乡村类短视频有助于展示与传播自己的特色文化,凸显文化主体性,亦可以通过产业化运营获取商业资本;而对主流媒体来说,发布乡村类短视频有助于宣传新时代的美丽乡村形象,助力乡村振兴。
更深层地看,文化话语生产的内部还涉及审美话语的生产,审美话语作为文化话语一部分为文化话语提供保障。乡村类短视频的火爆实质凸显的是:乡土审美成为当代文化生产、消费的新范式,传统的中国乡土审美经验借助短视频实现了其在互联网时代的新书写。历史地看,自工业革命以来,乡土审美是与都市审美逐步分裂甚至走向对立的。雷蒙·威廉斯在其著作《城市与乡村》中对这两种审美范式曾有过形象描述:城市代表着智力、时尚、交流与知识,但又掺杂着世俗、喧闹与人情冷暖;而乡村则被视为落后、愚昧且受制于传统的地方,但它却又象征着和谐、宁静与美德。(16)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页。尽管这种界定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审美经验建构,但对于正处于现代性开展期的中国来说,其依然是存在的。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下,城镇化进程也如火如荼,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在传统的乡土中国社会逐渐确立,并在自由主义思潮和城市大众媒介的裹挟下不断嵌入中国社会发展的肌理中。无论是在知识话语层面还是在文艺实践层面,城市与乡村日益朝着威廉斯所界定的两极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乡村的文化主体难以如实、合理地表达其审美追求。尽管存在一些有一定影响的乡村文艺作品,但在都市文化的包围下也难免被划入猎奇、低俗、审丑等“土味”审美的范畴,难以获得自身的审美主体性。而随着短视频的兴起,乡村底层群体获得了更多可以表达自身审美品味的机会,并借由短视频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和商业价值,获得了大量陷于现代性工业文化焦虑的城市受众的认同和向往,乡村的审美观念、审美品味开始成为一种可以和都市品味相抗衡的审美资本。于是,不仅大量的乡村文化主体竞相参与,就连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城市文化主体也积极投入到乡村类短视频的创作和传播中,乡村审美形态、审美方式和审美经验迎来了新的范式转换。
商业话语的生产建立在文化(审美)话语基础之上,是短视频展开乡村叙事的基本保障。它意指短视频对乡村的叙述来源于资本,依赖于资本,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话语。从传播上看,乡村类短视频在传播过程中所依赖的各大播放平台都是有商业属性的。从生产上看,由于乡土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娱乐要素,并融入了大众文化的生产进程(如东北乡土文化就是其中的典型),其商业属性是难以避免的。相较于乡村影视剧、乡村小品等传统乡土大众文化,短视频语境下的乡土娱乐既有意境悠远的乡景展示、富有传统意味的乡俗展示,又有琐碎纷繁的乡村百态、功能众多的身体实践,同时还夹杂着恶搞、戏谑、调侃等元素(如“土味老爹”“土味挖掘机”等),这是一种现代消费文化影响下的奇观生产和快感消费,是一种杂合文化的狂欢,乡村文化在此更多展现出的是一种以商业为目标的娱乐消费符号属性。
当然,最为根本的是权力话语的生产,它同时对商业和文化两种话语展开制约。权力话语指向的是政治层面,即:短视频对乡村的叙述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也不是一个产业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在文化层面,它涉及的是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话语权之争。历史地看,现代以来的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是主导性的,这导致乡村文化即便凭借短视频等自媒体获得了一定的主体性实践,但它在根本上仍然受到城市文化的形塑和剥夺,是按照城市文化的需要而生产的(当下绝大部分乡村短视频的消费群体由城市人构成)。因此,乡村文化从根本上说是被压制、被塑造的。而在产业层面,其涉及的是平台(文化主体)为争夺乡村短视频的资本控制权而展开的行动。乡村也好,短视频也罢,都是一种获取商业利益的媒介,对从事相关创作的账号来说,谁能持续获得流量,谁就能获得资本的青睐,谁就能掌握文化领导权。此外,在“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精准扶贫”等国家话语的推动下,非盈利性的主流媒体平台也积极通过短视频进行乡村叙事,并嵌入到商业平台领域,如快手的“幸福乡村”战略、今日头条的“三农合伙人”战略就是主流话语与商业话语合力对乡村短视频展开的收编。
值得注意的是,短视频本身也具有话语性,具有权力属性,它与上述主要话语(文化的、审美的、商业的、权力的)是相互嵌入的。霍尔认为,“表象既通过展现而运作,也通过未展现而运作”(17)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88页。,恰恰是未展现的内容具有权力色彩。“物要进入话语领域,就必须经过话语的洗礼。”(18)党西民:《视觉文化的权力运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1页。乡村要进入短视频的视觉秩序之内,首先要顺从短视频本身的视觉编码规则,在此过程中,文化、审美、商业、政治等话语开始进入,它们对乡村进行归类、渲染、遗弃,决定哪种东西才能成为可见之物,并在色彩、景别、景深、剪辑、音响等层面对其进行加工,使其具有文化性和审美性,以符合大众的消费需求。这是短视频所展现出的一种功能性权力。福柯说:“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19)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页。创作者生产乡村类短视频的同时,又不断因文本实践和社会实践改变自身,把自身不断融入作品的再生产进程中去;而乡村类短视频一旦进入观看进程就会构建出一个观看主体的位置,召唤出符合自身的观看群体,使观者习惯它的表达,然后采取暗示、鼓励等方式,不断激起观者的兴趣,最终实现连续性生产。与传统的表征活动一样,在这场意义的构建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依赖于信息所包含的符号价值。(20)斯图尔特·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汪凯、刘晓红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35-437页。应该说,各种话语正是看到了乡村和短视频结合后所产生的符号价值才持续介入的。
三、 乡村性的视觉建构:短视频文化的乡村叙事策略
从媒介角度看,短视频对乡村的叙述依然是一个视觉文化事件,它从属于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所构建出的视觉文化叙事机制,而正是有了大众对此的接受,它才得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大众对乡村短视频不是一般的观看行为,而是带着一定的乡愁情感,通过数字界面对作为图像(景观)的乡村展开了一种虚拟性观看。乡村尽管在这里是一种源于乡民的纪实性影像实践,但它并非完全真实,而是经过系列的视觉编码才被展示的。也就是说,乡村依然是被视觉构建出来的。它的生产资料并非作为物质实体的乡村,而是乡村之为乡村的“乡村性”,是作为表征的“乡村”,它通过形象和想象进入到短视频所构建的视觉文化叙事中。因此,如果说话语的生产描绘的是叙事动机,那么乡村性的视觉建构则是维系话语特性的主要策略。因为只有使乡村性通过短视频被观看(消费)了,其经验被习得了,话语所施展的权力才能真正实现。
新的视觉乡村的出场及其成为观者的一种日常性视觉生活是乡村短视频进行视觉建构的第一个层面。“任何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主体,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生产着自己的视觉经验,这些经验最终转化为某种主体性的‘文化建构’。”(21)周宪:《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36页。短视频是一种典型的数字界面图像生产机制,它通过拼贴、戏仿、恶搞等后现代文化思维对传统视觉修辞(画面造型、剪辑与声画结合等)和内容叙事进行创新,以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增强用户黏性,观者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触屏”这一数字界面与创作者所创作的世界展开沟通,这是一种全新的日常性视觉体验,其过程是循环性的。而事实上,从用户分布情况来看,广大乡村地区已然成为乡村短视频生产和传播的沃土,短视频开始与乡民的生产和生活流程紧密绑定,成了乡村社会进行视觉建构的新范式。
短视频对乡土情感的视觉形塑与生产是第二个层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都市化取得了极大进展,城市与乡村互动性逐渐加强,但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并没有消逝,守乡、怀乡、回乡、以乡为根仍是多数中国人固有且难以割舍的情感。特别是对在城市打拼的乡民而言,这更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短视频正是建立在对这一意识的激活之上的。如“张同学”以各种生活段子来展现北方乡村青年日常的一天,“手工耿”以“安保巡逻机甲”“美梦枕头”等创意发明来展示充满乡村趣味的手工技艺,“李子柒”以“桃林游记”“春节年货”“萝卜的一生”等来构建带有诗意和隐居色彩的田园生活,凡此种种,使得原本陌生的、落后的、衰败的乡村被赋予了质朴、平淡、创意、趣味、优美、宁静等新的形象,在快速、繁忙的城市生活模式面前,这种全新的乡土生活世界无疑成了一种新的精神家园。但正如米歇尔所言,“形象向来是媒介的主要通行货币”(22)W.J.T.米歇尔:《图像何求?形象的生命与爱》,陈永国、高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4页。,只有将乡愁以诸多不同的视觉形象创造和显现出来,才能满足网络时代的多元化观看欲望。因此,情感在这里只能被把握成图像进行展演,而观者则通过观看、评论等方式参与到这场虚拟的情感狂欢中。
“展示乡土”视觉伦理的出场及生产是第三个层面。短视频虽带有草根传媒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功能,但同时也是个性化、消费化和娱乐化的,它所构建的是一个混杂的、信息更迭极度频繁的视觉狂欢场域,其观看方式是散视的、消遣的、加速的,刷屏、好玩、好看等展示逻辑才是其正义。当乡村进入这一视觉场域,它在传统文艺作品中所获得的启蒙、批判、审美等正面价值则极容易被消解。比如在“万能子墨”所发布的短视频中,乡村手艺是被嵌入乡村情侣生活趣事之中的,其中不乏对经典电影、流行段子的恶搞、戏仿。尽管其制作的工具有实用价值,但却是以娱乐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事实上,观者也是带着感性的、娱乐的而非仰视的、敬畏的心态刷屏的。抖音博主“华农兄弟”以分享养殖竹鼠获得了三百多万粉丝,他们发布的很多视频是带有养殖行业介绍和知识普及属性的,但网友对此并不关心,相反,他们的评论充满着调侃、戏谑:“竹鼠:莫挨老子?老子没感冒,没中暑、没打架,没不听话,能下崽”,“欢迎来到华农毙熟山庄”,等等。如果说在电视剧、电影等传统的视觉叙事中,对乡村的观看还存在一定社会常态的伦理节制和理性,那么在短视频中,这些是被完全解构的,对乡村的观看则完全是个人观看欲望的彻底释放。它以“博取观者的眼球与点击为首选,以快感激发与欲望释解为主要目的”(23)张伟:《从“非礼勿视”到“视觉狂欢”——图像时代的视觉伦理及其文化表征》,《兰州学刊》,2017年第1期,第111-118页。,全面的展示才是正途。
当然,不管是哪个层面的建构,其都是在视觉体制的影响下完成的。视觉体制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性概念,是个体、视觉机构、政府、市场发生互动关系的场所。(24)周宪:《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326页。它表征了视觉文化场内生产什么样的形象,采取什么样的制度,生成什么样的视觉经验,构建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对于短视频来说,它的视觉体制是与乡村文化发生交互作用后共同生成的。一方面,当代中国的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互联网消费、数字技术等的构建下呈现出了以主动的形象生产来构建视觉秩序进而获取资本(文化的、经济的、象征的)的新特点,其表征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已与印刷文化和电子图像时代有着质的差别。另一方面,短视频凭借其技术、文化与资本特性正逐步展开新的社会的视觉建构与视觉的社会建构进程。尽管二者依然存在着被文化、技术、资本规训和褫夺的态势,对文化主体的异化也在所难免,但二者的交互的确构建出了一个复杂的“乡村—城市—互联网”文化结构、多元视觉主体及乡村形象发生互渗、互动的场域。目前看来,以乡村经验为表征的视觉狂欢是这一体制的核心旨归,而重复生产这种体制则是乡村短视频得以生长的最终策略。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种视觉体制是建立在数字技术所搭建的虚拟观看基础之上的,恰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讨论的“洞穴隐喻”,观者所看到的形象、所感知到的情感,并不是直接的经验,而是虚假的、受束缚的,这也昭示了乡村性的视觉建构必然有其消极性。
四、 媒介乡村:短视频文化的乡村叙事效果
当观者观看乡村短视频时,很少会注意到短视频的播放媒介或设备,甚至是图像本身,视觉重心往往是其传递的内容,而正是这些内容让观者理解了图像所传达的意义,同时又使观者将观看经验转换成其他形式,这是一种再媒介化过程。不过,这一过程还与总体的视觉效果相关联。因为尽管观看乡村短视频是一种私人化行为,但它的展示却是公共性的,“关注”“点赞”“分享”才是其生存逻辑。通过这些行动,视觉主体在群体和社会层面发生交往实践。换言之,视频一旦被创作和发布,就要进入到不同的群体的观看场域中,并与这些群体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产生关联,单一个体所获得的意义其实并非视频展演的终点,群体所获得的意义及其所传达出的意义才是叙事的归宿。在文化生产层面,我们可以将这个链条称为“媒介乡村”,指乡村以及短视频对乡村的叙述具有媒介功能。
媒介乡村是在符号与视觉的双重合力下完成的。短视频语境下的乡村是高度符号化的,如打谷机、红薯藤、水井、镰刀、菜地、山坡等都是乡村特有的实物,通过将它们放置在一种展示的语境下,这些实物成了符号,并传达出特殊的意义,如:打谷机表征的是劳作和丰收,菜地表征的是绿色无公害的乡食。对不同符号的编织将构建出不同的乡村图景,从而传达出特殊的如怀旧、诗意、恬淡的乡愁情感。不仅如此,符号还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如柿子饼象征着时令,虾片象征着小时候的味道。观者通过观看这些符号,询唤出属于自己的或被建构出来的乡土记忆,再通过评论互动,获得情感的共鸣。(25)简贵灯、周佳琪:《制造乡愁:乡村短视频中“拟态家园”的空间转场与符号建构》,《当代电视》,2021年第12期,第22-28页。但不论是观念性符号还是物质性符号,都是化约成视觉映像的,其采取的是“景观生产方式”,即德波所说的“一种表象的肯定和将全部社会生活认同为纯粹表象的肯定”(26)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第16页。。它们具有被展现的图景性特点,景象使乡村符号为观者所接受,景象制造各种欲望,欲望决定生产(27)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第16页。。
媒介乡村在隐在与显在两个层面起作用。平台和创作者用乡村短视频获取商业价值、文化价值,社会文化部门用它传递价值观,观众用它获得实用、技能、娱乐等信息,这条价值链是显在的,由短视频的公共性所决定。但正如德波所认为的,现代工业所造就的景观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景观展现为某种不容争辩和不可接近的事物。“原则上它所要求的态度是被动的接受,实际上它已通过表象的垄断,通过无需应答的炫示实现了。”(28)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这意味着人们对景观的顺从是无意识的,景观是隐性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这仅仅是德波对景观发展初级阶段的判断,而以今天的视野看,现代数字媒介下的景观密度其实是更高的。乡村短视频作为新的数字媒介依旧编织在这一逻辑之下,其本质依然是视觉意识形态的蔓延。
从社会功能来看,媒介乡村既昭示了一种新的乡村文化生产逻辑,也推动新的乡村文化治理逻辑的出场。工业社会以来,乡村文化是作为城市文化的对立面存在的,乡村文化始终处于一种被改造、被形塑、被启蒙的状态,特别是面对市场化、产业化的大潮,乡村文化更是陷入了无序的状态。这直接导致了乡村文化治理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的出场。那么,在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数字文化时代,乡村文化依然处于这种状态吗?我们不能否认,在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快速的社会结构变迁驱动下,当代中国的乡村文化的确存在着被消散的趋势,但短视频作为城市工业文化的产物,它对乡村的符号化生产已然证明了两种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共存的。至少在视觉和产业的驱动下,短视频文化促进了当代人对乡村文化的再梳理、再发现。同时,其也证明了,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乡村文化有它的时尚性与审美性。从这个角度看,乡村短视频的流行标志了一种新的数字化乡村文化生产范式的出场,但它不是传统乡村文化的简单复现,而是与技术、消费、娱乐、时尚等城市文化形态结合,是乡村文化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存在样态。
由此看来,当我们在这一前提之下再去思考乡村文化治理问题时,一些新的思路便会显现。首先,乡村短视频的高度自由性、参与性呼唤一种互动式的乡村文化治理范式。从生产、传播到消费,乡村短视频依靠视觉的公共性创造了一个多元主体平等对话的交互空间,乡民由之前的被引导到当前自发地表达文化诉求,进而参与到乡村文化的生产与创新中,由此促进了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这给目前群众和社会参与不足的乡村文化治理窘境带来了活力。其次,乡村短视频在内容、传播、消费等层面的多元复合性召唤着以关系为本的乡村文化治理实践。乡村短视频是多元话语争夺的场域,特别是在资本和媒介的作用下,它对乡村的展现是动态塑造而非静止的,只有将其置于关系语境下才能厘清其本质。再次,乡村短视频的差异性彰显了在地化对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乡村短视频以乡民主体的多样性和乡村文化的丰富性为支撑,以展示在地化的乡村为基本逻辑,以对乡村一整套社会关系、文化形式、价值关系和情感结构的形象化生产为基本内容,这给当前“千村一面”的乡村文化治理格局提供了新思路。最后,乡村短视频的景观性表明视觉文化是乡村文化发展的新范式。一方面,乡村文化借助短视频实现了向新的数字视觉消费业态的转换,并塑造出了新的线上乡村文化市场;另一方面,短视频凭借视觉修辞优势,给缺乏共同体意识、认同意识,甚至逐步走向迷失、焦虑、疏离的乡民搭建了一个基于视觉的对话桥梁,为新的文化共同体乃至城乡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感官前提。
五、 结 语
任何媒介对乡村的叙述都有其特定的动机与方法,但由于乡村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先天性关联使得其叙事效果及影响超过了普通的媒介叙事活动。中国语境下以不同媒介所展开的乡村叙事深深嵌入社会情境之中,与总体的文化环境、技术环境、生活方式、制度环境、产业环境存在复杂的纠葛。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艺生产实践中,乡村叙事虽在不同的时空中承担着重要的思想启蒙、意识形态宣传、文化建设、政治构建等功能,但由于其叙述主体并非乡民,这使得乡村叙事的能量没有被完全释放,乡村也并没有在整体性意义上被发现。此既提示我们必须将短视频的乡村叙事放在系统论意义上进行考量,又表明乡村叙事归根到底是乡村甚至社会问题的暴露场,这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相关问题的路径。乡村是落后和衰败的表征吗?乡村一定是城市的对立者吗?乡村文化是孤立、静止的存在吗?乡村文化仅仅停留在乡村吗?当我们系统地审视短视频文化对乡村的叙述后就会发现,这些都是值得商榷和深思的问题。总之,回到与城市相关联但又相区别的乡村本身,重视其在新的数字语境下的文化与经济潜能,重视乡村文化生产作为一种视觉表征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场中寻找解决乡村问题的方法,才是我们在新时代振兴乡村所应秉持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