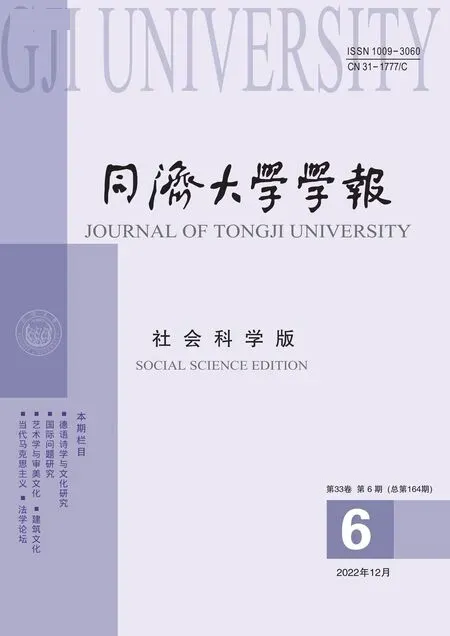走出戏剧幻象的戏剧小说
——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对戏剧的呈现与反思
2022-02-11任卫东
任卫东
(北京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 北京 100089)
对普通读者而言,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以下简称《学习时代》)或许没有达到《少年维特的烦恼》那种家喻户晓的程度,但是,就德语文学史上的地位来说,《学习时代》丝毫不逊于《少年维特的烦恼》。《学习时代》不仅是德语文学中修养小说——“最高贵的、与史诗相比最能深刻把握小说本质的一种特殊形式小说”(1)Karl Morgenstern, Über das Wesen des Bildungsromans, inländisches Museum,1820, Bd. I, H. 2, S. 46-61; H. 3, S. 13-27, hier H. 2, S. 61.——的“典范与原型”(2)Hans Heinrich Borcherdt, Bildungsroman, in: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2. Auflage, Bd. 1, De Gruyter, 1958, S. 177.,而且获得了同时代浪漫文学理论家施莱格尔的盛赞:“法国大革命、费希特的《知识学》和歌德的《麦斯特》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趋势。”(3)Friedrich Schlegel, ”Athenäumsfragment 216 (1789)“, in: Charakteristiken und Kritiken I, 1796—1801, hrsg. von Hans Eichner, München u.a., 1967, S. 198.施莱格尔用这三件事物阐明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800年前后)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学习时代》就代表着德语文学的发展倾向,即“囊括了古人和现代人的全部诗,并且包含了永恒进步的萌芽”(4)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此处引用对译文有改动。。
《学习时代》是歌德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如果从其最终出版时间1796年10月来看,这部小说距离1774年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有20年的间隔,但实际上,歌德从1777年就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写作。1785年11月,他在给冯·施泰因夫人的信中写道,他已经写完了六卷。这六卷就是直到1910年才被发现的《威廉·麦斯特的戏剧使命》(以下简称《戏剧使命》)。(5)Vgl. Goethe-Handbuch, Bd. 3, hrsg. von Bernd Witte und Peter Schmidt, Verlag J. B. Metzler, 1997, S. 114.也就是说,在《学习时代》出版了一个多世纪之后,世人才知道《戏剧使命》的存在。1785年,歌德去意大利旅行,写作就中断了。直到1793年,歌德重新开始改写这部作品,并确定小说标题为《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戏剧使命》的六卷被改成了《学习时代》的前四卷。
《学习时代》主要讲述了市民商人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威廉在追寻自己戏剧梦想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人与事,最后在塔社成员们的引导和帮助下,放弃戏剧梦,进入社会,成为一名实干的人。戏剧不仅在小说中占据非常大的篇幅,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小说前半部分的主要表现对象和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把《学习时代》称为一部戏剧小说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它不仅描写了主人公威廉追逐自己戏剧梦想的过程,而且再现了近现代德国戏剧的发展状况,展示出一幅18世纪德语戏剧的全景图。同时,小说的更加精妙之处在于,歌德借助威廉进入剧团、体验戏剧生活、最终离开剧团的经历,展示了自身对戏剧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不断变化的认知过程。
一、 戏剧使命和戏剧理念
童年时,木偶剧触发了威廉对戏剧的喜爱,长大后他一直追逐自己的戏剧梦想,但这不仅仅是他的个人兴趣爱好,而是如他在小说一开始就明确表达的:他所追求的崇高目标是成为未来民族戏剧的创造者,他对于德意志戏剧的强烈使命感,也是“很多人极度渴望的”(6)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386; S. 658-659.。所以说,威廉的追求,“并不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约束力的个人梦想,因为民族戏剧的理念,是市民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7)Klaus-Detlef Müller, ”Wilhelm Meisters Weg in ein tätiges Leben. Jarno als Mentor“, Goethe-Jahrbuch 2016, hrsg. von Frieder von Ammon, Jochen Golz und Edith Zehn, Göttingen, 2017, S. 58.。威廉代表的正是17、18世纪以来德国市民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和迫切使命感:借助民族戏剧树立德意志民族意识。
当时的德国虽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然而,德意志民族意识已经开始萌芽。这一过程首先出现在文化领域而非政治领域,而且,“真正开始提出民族性主张的是市民阶层”(8)王建:《德国近代戏剧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页。。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他们越来越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由于德国市民阶层在政治上没有可以发挥影响的空间,所以只能通过文化领域来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于贵族和市民的不平等以及市民阶层无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这一事实,威廉有非常明确的看法,他说:“如果说贵族通过展现自己就表现出了他的一切,那么市民通过他个人却什么也展现不出来,而且他也不应该展现出来什么。贵族可以而且应该表现;而市民只应该存在……贵族应该行动,产生影响,市民应该努力工作、实干。”(9)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386; S. 658-659.由此看来,市民阶层只能在文学领域提出民族性的要求。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剧院是形成政治公共领域的文学预演,是公共对话的练习场。(10)Jürgen 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1971, S. 44.因此,建立德意志人的戏剧舞台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政治行为。1767年,汉堡建立了一座民族剧院,这是德国最早的、自下而上由市民发起建立的公共剧院。(11)参见佐尔坦·伊姆雷:《欧洲的“民族国家剧院”:观念与实践》,赵晗译,《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22页。莱辛受邀担任戏剧顾问,并为之撰写了104篇剧评,也就是著名的《汉堡剧评》,但剧院还是在一年之后失败了。1782年,在于1777年正式成立的曼海姆民族剧院上演了席勒的《强盗》,引起了巨大轰动。1791年,魏玛宫廷剧院成立,后改名为“民族剧院”。在歌德和席勒的积极推动下,该剧院书写了德语戏剧的辉煌。
德国市民阶层知识分子和作家创立德国民族戏剧的道路是从模仿外国开始的。启蒙初期的哥特舍德以法国古典主义宫廷戏剧为样板,整顿德国戏剧舞台,想建立正统的德语戏剧。之后,莱辛批判了法国戏剧僵化机械的弊端,转而推崇英国戏剧,开启了18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的莎士比亚热。这些情况在小说中都有反映:威廉跟着剧团在伯爵的府邸为亲王演出,那位以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弟弟(亨利希亲王)为原型创作的亲王,就只喜欢法国戏剧,尤其是高乃依、莫里哀和拉辛的戏剧。威廉为了取悦亲王,还当面向亲王赞美法国戏剧。雅尔诺等一些贵族则对英国戏剧非常感兴趣。在雅尔诺的强烈推荐下,威廉接触到了莎士比亚的剧作,读了几本后“就被强烈地影响了,以至于他不能继续往下读了。他的整个心灵陷入了震荡中”(12)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552; S. 552-553; S. 662.。威廉接触莎士比亚的经历,不仅具有文学史的典型性,而且再现了歌德本人的莎士比亚体验。22岁的歌德在赫尔德影响下初次接触莎士比亚戏剧,受到了同样的震撼:“他的著作我读完第一页,就被他终生折服;读完他的第一个剧本,我仿佛像一个天生的盲人,瞬息间,有一只神奇的手给我送来了光明。”(13)歌德:《纪念莎士比亚命名日》,《歌德论文学艺术》,范大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页;第17页。歌德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看到了五彩斑斓的生活和人类历史:“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一个美丽的西洋镜,世界的历史拴在一根看不见的线上从我们面前滚滚而过。”(14)歌德:《纪念莎士比亚命名日》,《歌德论文学艺术》,范大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页;第17页。威廉也感觉到,他生命中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对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他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从一个个有个性的人物身上看到普遍的规律,使得他更好地认识自己,看清生活。威廉的戏剧使命感被激发出来:“我在莎士比亚世界中看到的这几眼,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能激励我,在现实世界中更快地前进,使自己投入到这降临世间的命运洪流中去,有朝一日,如果我有幸能从真正的自然之海中汲取几杯,我要把这甘露从舞台上赠与我祖国的焦渴的观众们。”(15)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552; S. 552-553; S. 662.
小说第四、五卷的主要内容是威廉竭尽全力把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搬上了舞台,并亲自扮演哈姆莱特。在这个过程中,威廉与赛罗兄妹对《哈姆莱特》剧中人物和戏剧结构作出了非常详细的分析,这对于当时德国观众理解和接受《哈姆莱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筹备演出过程中,威廉与赛罗就剧本是否要修改及删减等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威廉坚持要完整地上演《哈姆莱特》,赛罗则认为,包括《哈姆莱特》在内的许多剧目已经超过了剧团全体演员的人数,超出了“布景和舞台技术的能力”,而“用删减的剧本也能达到跟用完整剧本同样的效果”(16)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552; S. 552-553; S. 662.。最终,威廉做出让步,对剧中人物和情节都做出了删减和修改。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对莎士比亚戏剧接受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赛罗所说的“布景和舞台技术”问题的确是现实中曾长时间阻碍莎士比亚戏剧在德国上演的原因。后来,在德国18世纪上演的《哈姆莱特》基本上都做了删减,歌德在魏玛上演的《哈姆莱特》以及莎士比亚的其他戏剧亦如此。歌德在《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为这种做法作出了解释:“多年来,在德国流行一种偏见,认为莎士比亚在德国舞台上必须逐字逐句一点不错地演出,即使演员和观众会因此感到窒息也应如此。”但是,歌德指出,这种尝试从来没有成功过。所以,莎士比亚的剧本若是在德国上演,必须进行改编。如果坚守莎士比亚剧本一字不能改动的意见,“那么几年之内莎士比亚就会从德国舞台上完全被排挤出去”(17)歌德:《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歌德论文学艺术》,范大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9页。。
二、 戏剧实践与剧团经营
小说前五卷表面上是写威廉追逐戏剧梦想的过程,实际上却是威廉对最真实的戏剧演员生活和剧团经营状况的观察和经历。不过这一点被视作小说的缺陷而受到了席勒委婉的批评。席勒认为,小说中关于剧团事务和经营的描写过于详细繁杂了,与整本书所要表现的自由、宽广的精神境界不够协调。(18)席勒1795年6月15日写给歌德的信,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张荣昌、张玉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60页。尽管歌德听从了席勒的建议,对这一部分进行了大幅压缩,但仍然能让读者从小说中对当时德语戏剧的实际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威廉深度接触并参与过的剧团有两个:第一个是由他出资、梅林纳创建的剧团,第二个是他在剧团遭遇抢劫后所投奔的赛罗的剧团。威廉自己的剧团,包括他的情人玛丽安娜所在的剧团,都是典型的流动剧团。17世纪,在英国流动剧团和意大利流动剧团的影响下,德国也出现了流动剧团。流动剧团与宫廷戏剧及学校剧团是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戏剧演出形式。顾名思义,流动剧团没有固定的演出地点和场所,而是在各地游走,寻找演出机会。流动剧团的经理不仅负责招聘演员、管理剧团日常事务、决定演出剧目,还要与演出地的市政府官员商谈以求获得演出许可,这是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到了18世纪,宫廷戏剧由于偏爱意大利歌剧,学校戏剧也受其业余性的局限,二者影响逐渐减弱,而日渐成熟的流动剧团则成为“德国戏剧的主导力量”。(19)王建:《德国近代戏剧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6页。王建教授在其著作《德国近代戏剧的兴起》中对于从巴洛克到启蒙运动时期德语戏剧的发展有着非常详细的呈现和论述。而且,由于启蒙运动以来德国兴起的戏剧热潮,不少像威廉这样出身优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被流动剧团的演员生活所吸引,投身演员生涯,对德国戏剧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流动剧团的生存状况非常艰难。小说中,梅林纳在第一次见到威廉时,就坦诚地说明了之前剧团的艰难处境:“剧团经理会去拜倒在每个市参议员脚下恳求,只为能趁博览会期间的四个星期,在一个地方多赚几个铜板。……要是他想让收入和支出基本持平,那观众就会觉得票价太贵了,剧场就会空了,所以,为了避免彻底破产,就必须赔着钱、忍受着痛苦演出。”(20)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406; S. 406; S. 538; S. 414.怀抱梦想投奔流动剧团、渴望摆脱市民狭隘生活的年轻人,为了谋生不得不辗转各地,并且常常忍饥挨饿,“即便付出如此的辛劳,他们的经济收入依旧得不到保证,不得不仰赖各个演出地的特许和观众的认可,如果没有演出的机会,或者得不到观众的承认,很可能拿不到任何薪酬,戏班往往要抵押资产度日,甚至陷于破产的境地”(21)王建:《德国近代戏剧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58-359页。。小说中,梅林纳一开始所在的剧团和玛丽安娜的剧团都破产了。梅林纳怂恿威廉出钱赎买的舞台道具和服装就是由前剧团经理卖掉的。
在这种经营模式和演出环境所带来的压力之下,剧团为了招徕观众完全不注重剧本的质量和表演艺术,而是一味迎合与讨好观众。因此,演员地位低下,流动剧团与杂耍班子没什么差别。正如梅林纳所说:“世界上还有任何一块面包,比演员挣得的那块面包更可怜、更不可靠、更辛苦的吗?几乎跟上门乞讨差不多了……真的,演员最好长一层像狗熊那样的皮,才能跟猴子和狗一起,被人用链子牵着、被鞭子抽打着,随着风笛的节奏在孩子们和下层人面前跳舞。”(22)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406; S. 406; S. 538; S. 414.
演员地位低下,不仅表现在他们的生活困窘之上,更体现在他们所遭到的歧视和排斥上。在贵族眼中,演员们,尤其是女演员,只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工具。这一点,在小说第三卷剧团在伯爵府邸演出的情节中体现得非常清楚:雨夜到达伯爵府邸的演员们,只能住在废弃的房屋中,吃着残羹剩饭。从一开始,年轻军官们就打起了女演员们的主意,把她们当做自己的玩物,经常彻夜饮酒作乐。伯爵对书呆子以及伯爵夫人对菲琳娜的所谓宠爱,就如同人对宠物那样,只是因为他们会察言观色、“摇尾乞怜”。伯爵饭后会把演员找到面前谈话,这在演员看来是莫大的荣耀,“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同一时间,主人也让猎人和仆人把狗和马匹牵到院子里来遛”(23)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406; S. 406; S. 538; S. 414.。
对演员的蔑视不只是贵族的特权,相反地,其更多体现在市民阶层身上。演员们生活漂泊不定,因而生活方式不受市民准则约束,而且因生活所迫,常常会用特殊的方式为自己寻找生活的保障。女演员们会委身于某个有钱人,充当地下情人。比如,威廉的初恋情人玛丽安娜早已被富有的商人诺尔贝格包养。因而,威廉眼中纯真痴情的玛丽安娜在当地居民的闲话里和维尔纳眼中就是一个“善于诱惑人的姑娘”,“就是为了骗……钱”(24)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406; S. 406; S. 538; S. 414.。男演员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第二卷里,威廉遇到的那个杂耍班子的走索艺人纳尔齐斯就曾毫不避讳地告诉威廉,他要夜间去拜访女士,凭借他的身体和才能“他收到了几位女士的口信,她们迫切要求进一步认识他,他担心,他要做的这类访问,在午夜前是不可能结束的”(25)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457; S. 405; S. 408; S. 553; S. 606; S. 721.。
这种现象在演员当中是非常普遍和司空见惯的,但却与市民道德相违背。所以,市民阶层尽量避免跟演员扯上关系。这一点在梅林纳夫妇的爱情遭遇中表现得很充分:第一卷里,威廉在一次商务旅行中凑巧遇到债务人家的女儿与一位演员(也就是梅林纳)私奔了,这对女孩儿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威廉从自身的经历出发非常同情那一对年轻人,想从中斡旋,促成二人的婚事。然而,令他震惊的是,一方面梅林纳坚决不愿意再当演员,而“更愿意接受一种普通市民的差事,随便什么都行,只要能得到”(26)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457; S. 405; S. 408; S. 553; S. 606; S. 721.;另一方面,女孩的父母虽然同意了婚事,但他们坚决拒绝帮助梅林纳找一份市民差事,“他们不愿意再见到这个品行不良的孩子,他们家是一个有声望的家庭,甚至跟一位教区牧师是亲戚,他们不愿意让这个来路不明的人因为与女儿结婚而永远留在本地”(27)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457; S. 405; S. 408; S. 553; S. 606; S. 721.。对于市民阶层的人而言,与演员有瓜葛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
小说中梅林纳夫妇的遭遇其实是威廉与玛丽安娜关系的一面镜子或者预警,只不过威廉自己没有意识到。小说的叙述者从一开始就暗示了威廉与玛丽安娜的不匹配关系。不仅是威廉与玛丽安娜作为恋人身份存在着巨大差异,小说中也多次暗示或明示威廉与其他演员的不同,雅尔诺更是直截了当地问威廉:“您是怎么进入这个剧团的?您不该属于它,您所受的教育也与之不合。”(28)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457; S. 405; S. 408; S. 553; S. 606; S. 721.由此可见,演员群体的社会地位得不到承认,他们不仅受到贵族的歧视,而且也被市民社会排斥在外。
关于第二个剧团,也就是威廉投奔的赛罗的剧团,虽然小说中没有明确说明,但能看出是常驻剧团的状态。赛罗自己是非常出色的演员,同时也是剧院的经理。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歌德同时代著名的剧院经理、演员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施罗德(Friedrich Ludwig Schröder,1744—1816)。施罗德的母亲和继父都是演员,特别是他的继父阿克曼是当时德国一个著名流动剧团的经理。他曾把莱辛的《萨拉·萨姆逊小姐》搬上舞台,并且努力地在汉堡经营自己的剧院。小说中,赛罗的剧团有固定的演出地点,赛罗本人是剧团的灵魂,他不仅是天生的好演员,具有极高的天赋,而且有很好的文学领悟力,赞同并支持威廉把《哈姆莱特》搬上舞台。赛罗不仅自己拥有丰富的表演经验和表演技巧,而且对其他演员的表演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他认识到威廉的价值,同时也直言不讳地责怪威廉,给他“推荐了一些没用的人……梅林纳先生和他那些人,很难被观众接受”(29)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457; S. 405; S. 408; S. 553; S. 606; S. 721.。
赛罗对剧团的要求和面临的问题就是17、18世纪常驻剧团的困境:常驻剧团虽然免去了奔波流浪之苦,但是,常年在一个固定地点演出,由于观众数量有限,其对于演出剧目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历史上,在哥特舍德对德语戏剧进行改革之后,剧团演出提高了对剧本文学性的要求,把传统的小丑角色赶出了戏剧舞台。但是,注重文学性的剧目无法满足观众寻求消遣娱乐的要求,因而剧团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要想方设法招徕观众。因此,虽然赛罗的剧团演出《哈姆莱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作为剧院经理,赛罗想的是如何吸引观众,更多地赚钱以维持剧院的正常经营。他知道梅林纳在表演方面毫无可取之处,甚至都不让后者演客串角色。但是,当梅林纳向他提议上演歌剧以便赚到更多的钱时,赛罗立刻认识到梅林纳是个能帮他经营好剧团的人。虽然他清楚地知道这种所谓的歌剧只是“一种混合的演出,既不是真正的歌剧,也不是真正的戏剧,必然会使人们对特定的某种真正艺术品所剩不多的品味彻底丧失殆尽”(30)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457; S. 405; S. 408; S. 553; S. 606; S. 721.,会把观众的爱好引入歧途。这显然与威廉追求的戏剧艺术理想以及希望通过戏剧培养、教育观众的理想大相径庭。但是,迫于生存压力,赛罗决定甩开碍手碍脚的威廉,与梅林纳联手,这也加速了威廉最终离开剧团、走出戏剧的步伐。
在《学习时代》中,歌德以一种非常现实的目光观察着德意志的戏剧世界。他关注剧团的经营方式,反思戏剧在娱乐和教育之间不得已的摇摆,也批评了戏剧产业在迎合观众的谄媚中艺术性丢失的现象。结合歌德本人在古典阶段对通俗文化的态度来看,威廉退出剧团是必然之举,剧团生涯让威廉意识到艺术屈从于社会权力关系、经济结构以及民众意识的现实。通过对剧团生活的细致观察,歌德呈现了艺术作为“营生”的困境,也体现了威廉最终走向务实人生的必要性。无论是流动剧团还是常驻剧团,在当时的演出环境中,最终都会向现实妥协——换言之,现实无法为真正的、绝对的艺术提供健康土壤。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意识到,威廉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并非意味着不得已的放弃。如果说剧院是一种间接影响社会的方式,那么在塔社引导下的威廉则走向了一种直接参与社会改良的路径。从这个角度来看,歌德在《学习时代》中对戏剧部分的繁冗描写有特殊的必要性——只有看清剧团及其背后的社会景深,我们才能理解1800年前后修养与艺术以及社会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 对戏剧教育功能的反思
1800年,施莱格尔在评论《学习时代》时说:“这部完整不可分割的作品同时也是两个部分,是一部双重作品……这部作品是分两次写成,写于两个不同的创作时间,产生于两个念头。第一个不过是写一部艺术家小说的念头。但是作品为小说体裁的发展趋势所震惊,于是忽然间愈写愈大,超出了作品的初衷,再加上生活艺术的教育学说,于是生活艺术变成了整部小说的精髓。”(31)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施莱格尔说这段话时并不知道有《戏剧使命》的存在,也并不了解歌德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但他敏锐地观察到了歌德的思想变化。
比较《戏剧使命》和《学习时代》,研究歌德对此的改写过程能够清楚地看到歌德对戏剧思考的变化:《戏剧使命》讲的是市民生活与戏剧艺术生活的冲突,主题是威廉以创建德意志戏剧为使命离开家,进入剧团,努力成长为德国的“莎士比亚”。而《学习时代》讲述了威廉逐渐认识到他的戏剧追求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因而离开剧团,进入现实生活,成为一个实干的人。因此,从《戏剧使命》到《学习时代》不仅是主人公威廉的成长和修养经历,也是作家歌德对社会、政治和艺术,尤其是戏剧艺术的认识逐渐变化成熟的过程。
小说中,威廉的理想是“成为公众人物,在一个更大的圈子里被人接受、发挥作用”(32)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659; S. 659; S. 448.,为此,他认为必须对自己进行全面的教育。但是,他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市民阶层的人,“我的出身没有给我和谐的天性,现在,我对训练自己这种和谐的天性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渴望”(33)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659; S. 659; S. 448.。与贵族不同的是,市民阶层的这种教育只有在戏剧舞台上才能实现,而且威廉坚信,“戏剧对所有阶层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就连国家也能从中获得很多益处”(34)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659; S. 659; S. 448.。
这里可以看到,威廉对于戏剧对人的教育和培养功能的认识是与德国自启蒙运动以来强调戏剧塑造人和德意志民族的功能一脉相承的。尤其是席勒,他认为社会的改善和政治转型必要的前提条件是不断对人进行完善,通过平衡人的理性和感性从而塑造出“完整人”。然而,在充斥着“粗野”“懒散”和“上层与下层分裂”的社会中,恢复人的“整体性”只能通过审美教育、通过“更高的艺术”(höhere Kunst)来恢复被破坏了的人的完整性。(35)参见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席勒经典美学文论》,范大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95-374页。在第五封和第六封信中,席勒集中讨论了人的整体性丧失和如何通过艺术恢复人的整体性问题。早在1784年的一次题为《好的常设剧院究竟能起什么作用》的演讲中,席勒就明确把戏剧舞台定义为一种道德机构,认为其起着教育人和教育民族的作用,因而是最重要的国家机构。比起其他任何公开的国家机构,戏剧舞台更是“一所实际生活经验的学校,一座通向公民生活的路标,一把打开人类心灵大门的万无一失的钥匙”(36)席勒:《好的常设剧院究竟能够起什么作用》,《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页,译文有改动;第15页。。席勒认为,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戏剧更适合对人的教育,它以最高贵的娱乐方式把对人的理性和感性塑造结合起来,它比宗教和法律对人的作用更大。一个好的常设剧院对民族精神会产生巨大影响。他以古希腊为例来说明戏剧与民族凝聚力之间的关系:戏剧“漫游于人类知识的整个领域,详细探究生活的一切情况,并且照彻心灵的一切角落;因为它把一切等级和阶级联合在自身之中,并且能够达到理智和心灵的康庄大道。……如果到了有一个民族剧院的那一天,那么我们也就会成为一个民族”(37)席勒:《好的常设剧院究竟能够起什么作用》,《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页,译文有改动;第15页。。
小说中,威廉投身戏剧时所怀的理想是:完善自身、创立民族戏剧、塑造民族精神——这与席勒的思想竟然不谋而合。然而,进入戏剧世界之后,威廉所经历的人与事不仅让他自己也让读者清楚地认识到,那只是他的幻想。他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演员,但并没有哪个能通过戏剧表演变得高尚完美。曾深深吸引过他的菲琳娜是一个非常聪明、善于观察和模仿的演员。她揣摩贵族的各种礼仪,并且通过模仿让自己变得行为得体、举止优雅。但是,模仿并没有让她成为一个高贵的人,她只是利用自己的这种能力和优势为自己寻求利益最大化。赛罗和他的妹妹奥莱丽都是非常出色的演员,但也并没有通过戏剧变成更杰出、更完整的人:赛罗的表演技巧只能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匠人和商人,他只想通过演戏多挣钱,让自己随心所欲地生活。而奥莱丽把演戏当作毫无节制地宣泄自己个人情感的方式。其余的绝大多数演员,就连最基本的专业素养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是完整的人。他们不懂文学,从来不尝试理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根本不会谈论一出戏的文学价值,而只是关心能挣多少钱。
威廉投身戏剧一方面是想通过戏剧完成自身修养,另一方面,他还想通过戏剧教育和培养观众。然而,他的这种“学究式理想”不仅遭到赛罗和梅林纳的嘲笑,而且奥莱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威廉,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威廉最后决定离开舞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观众的绝望。小说中威廉放弃通过戏剧教育观众的幻想,实际上表现了18世纪德语戏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席勒将戏剧视为教育观众、塑造民族性的最好途径;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为剧院培养出来观众之前,剧院很难培养它的观众”(38)席勒:《论当代德国戏剧》,《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页,译文有改动。。
威廉最初是带着儿时的梦想接触并投身戏剧的,他对戏剧、戏剧生活、演员的职业以及戏剧教育功能的认识,更多是他的想象或者幻想。就像梅林纳第一次见到威廉时说:“一看您就没当过演员。”(39)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405; S. 687.奥莱丽也戏称他为“极乐鸟”(40)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405; S. 687.,整日飘浮在空中,根本不了解真实的生活。剧团的经历是他一次次失望的过程,也是他认清现实的过程。同时,通过威廉的经历,歌德对于戏剧这个美的假象王国,这种审美游戏是否真的能够起到教育和塑造人、培养民族性的作用,提出了质疑和新的思考。
德国古典主义认为,艺术和人的审美教育对于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学习时代》中的威廉试图从戏剧艺术中认识现实生活的尝试却失败了。这显然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古典艺术崇拜和审美崇拜相悖,这是否暗含着对古典审美教育和审美生活态度的批评?(41)Vgl. Hermann August Korff, ”Individuum und Gemeinschaft: Wilhelm Meister“, in: Am Beispiel Wilhelm Meister, hrsg. von Klaus L. Berghahn und Beate Pinkerneil, Athenäum Verlag, 1980, S. 97f; S. 98.席勒虽然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反复强调,人只有通过艺术才能走向自由,而“理想的艺术必须脱开现实”(42)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席勒经典美学文论》,范大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09页。,但是,他关注的最终目的是社会政治问题,艺术与审美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好途径。所以,古典主义不是唯美主义(43)Vgl. Hermann August Korff, ”Individuum und Gemeinschaft: Wilhelm Meister“, in: Am Beispiel Wilhelm Meister, hrsg. von Klaus L. Berghahn und Beate Pinkerneil, Athenäum Verlag, 1980, S. 97f; S. 98.,美和艺术指向的是现实生活。
歌德在《学习时代》中对艺术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关联性给予了更多的思考和强调。《学习时代》的成书史呈现了歌德从狂飙突进到古典时期的观念变化:《戏剧使命》将艺术与生活对立起来,威廉投身戏剧是为了逃避庸常的市民生活;而在《学习时代》中,歌德则意识到了艺术的局限性,但他仍然让主人公在戏剧艺术中认识生活,就像雅尔诺点醒威廉时所说的那句话,他所经历的“不是剧团,而是人世”(44)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811; S. 798.。歌德虽然让威廉最终离开戏剧,走进真实的现实社会,但并没有否定艺术的作用,而是通过阿贝肯定了艺术在人成长中的意义:“我们遇到的一切,都会留下痕迹,一切都会不知不觉地有助于我们的修养。”(45)Johann Wolfgang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rsg. von Wilhelm Voßkamp und Herbert Jaumann, in: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9,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2, S. 811; S. 798.歌德给威廉设计的道路是“从艺术的外行和审美的梦想,进入务实的生活实践”(46)Karl Vi⊇tor, ”Das Problem der Bildung“, in: Am Beispiel Wilhelm Meister, hrsg. von Klaus L. Berghahn und Beate Pinkerneil, Athenäum Verlag, 1980, S. 109.,但艺术修养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如席勒所说,威廉“从一个空洞的、不明确的理想步入一种明确的、积极的生活,却并没有丧失理想化的力量”(47)《歌德席勒文学书简》,张荣昌、张玉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44-145页。。威廉的这种转变体现出歌德希望在艺术与生活之间达成和解的倾向。
从文学与社会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学习时代》呈现了1800年前后的社会现实意识对文学艺术空间的渗透。被席勒寄予厚望的戏剧舞台作为一种对政治发声的艺术空间在小说中被宣告放弃,乌托邦式的剧团梦想被真实的社会共同体所替代。从剧团走向塔社是市民从间接的、隐藏的政治影射走向直接的、积极的政治行为的跃进。《学习时代》以一种非政治的、艺术的方式呈现了一个市民青年的成长历程,但同时,它又为市民作为政治个体的合法性提供了所有必要的说明。小说体现了歌德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做出的回应,也反向体现了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政治理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