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露》:女子抗婚之歌
2022-02-10刘毓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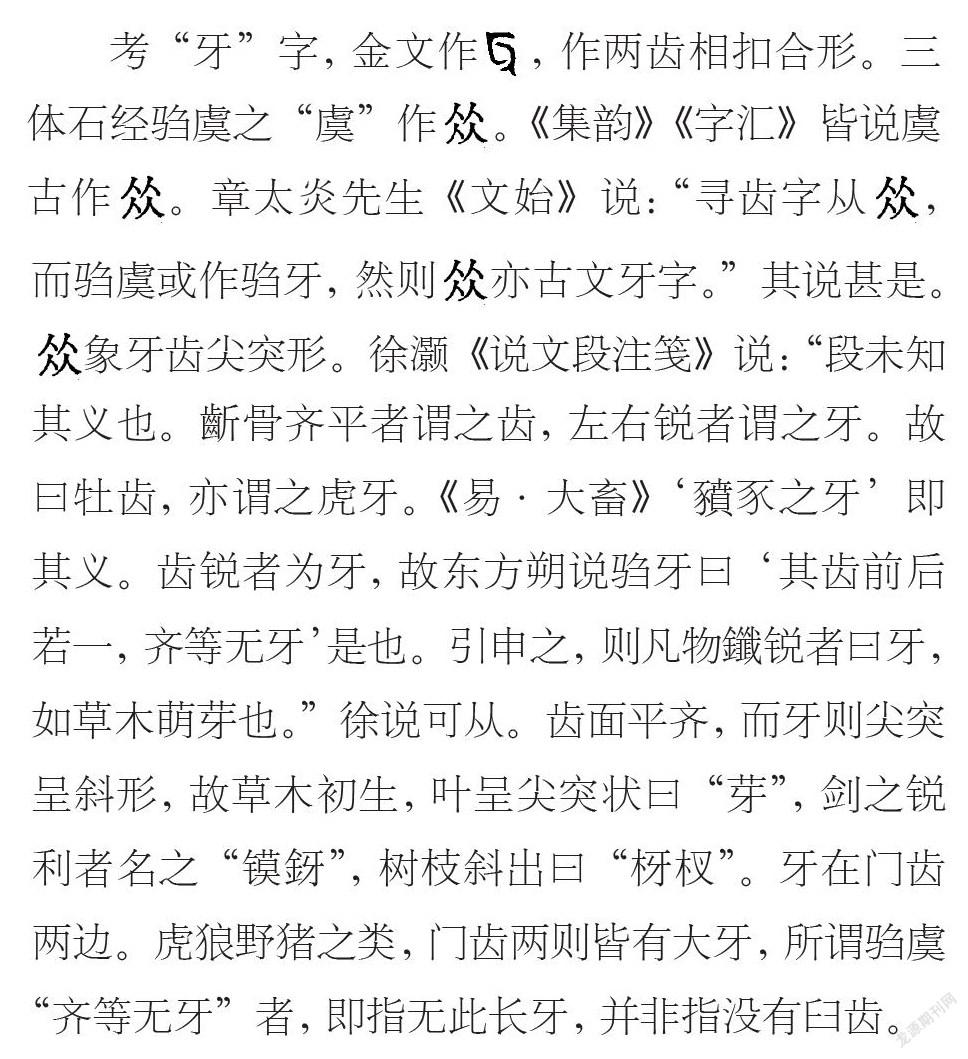
关键词:行露 行路 雀角 鼠牙 谁谓 何以 诗旨
在民国以降的各种《诗经》选本中,《行露》多半被选入。原因是它对不合理婚姻的反抗之声与妇女解放运动发生了呼应,人们从中听到了中国古代妇女为追求幸福而发出的呐喊。全诗共三章。原文是: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这首诗从章法看,便有点特殊。第一章仅三句,第二、三章却长达六句。第一章写因露水影响了走路,二、三章却写拒绝逼婚之事。前后内容不相连贯。故《诗总闻》说:“首章或上下中间,或两句三句,必有所阙。不尔,亦必阙一句,盖文势未能入雀、鼠之辞。”王柏《诗疑》亦云:“《行露》首章与二章意全不贯,句法体格亦异。每窃疑之。后见刘向《列女传》“谓召南申人之女许嫁于邦,夫家礼不备而欲娶之,女子不可,讼之于理,遂作二章,而无前一章也。乃知前章乱入无疑。”今世学者孙作云又把《诗经》中有可能是错简的篇子放在一起做了考证,认为此篇是两篇诗的误合。但据《韩诗外传》前言“《行露》之人许嫁矣”,后引《诗》“虽速我讼,亦不尔从”的情况,说明汉初经师所传“虽速我讼”就属《行露》篇的内容,并非误合。再则,这篇诗出现在《诗经》开头的“二南”中,是古人学习的重点篇目,因此读书人大多默记能诵,错简的可能微乎其微。虽然今人对这种形式难以理解,恐怕只能怪我们对古代缺少了解,千万不可轻易指斥古人错了。这里需要讨论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是“行露”还是“行路”
诗题作“行露”,显然是根据《毛诗》本的首句而定的。《毛诗》用字每多假借,这是古人早就指出的,因此不必固执。诗言“厌浥行露”,《毛传》根据“行露”二字解释“厌浥”说:“湿意也。”《广雅·释诂》:“湆浥,湿也”。说者以为鲁、韩作“湆浥”。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谓“‘厌浥’,露浓之貌”。钱澄之《田间诗学》以为:“厌,足也。浥,湿也。厌浥,犹云湿透是也。”罗典《凝园读诗管见》以为:“厌读去声,谓恶之耳。浥,沾濡之意。”山本章夫《诗经新注》以为:“厌,压;浥,湿。厌浥谓径草为露所垫濡也。”不难看出都是顺着《毛传》的思路,就“露”字上发挥的。但如果我们把“行露”读作“行路”,情况便会大变了。
《焦氏易林》卷三《大壮之姤》云:“婚礼不明,男女失常。《行路》有言,出争我讼。”这显然是演义《行露》诗义的。但字作“行路”,就说明当时《诗经》传本有作“行路”者。清代学者以为焦氏学《齐诗》,是《齐诗》有作“行路”者。巴黎斯坦因藏敦煌《诗经》残卷、伦敦伯希和藏敦煌《诗经》残卷,“行露”皆作“行路”。“行”是行走,“路”是道路。这里指的是在道路上行走。
返回来再看“厌浥”,就不可能是形容露珠了,当是形容行走状态的。厌、浥双声,韩、鲁二作“湆浥”,王先谦说:“‘湆浥’二字,声转义同,故叠文为训。”在上古汉语中,双声字往往是由叠字音变来的。窃疑“厌浥”“湆浥”当是“厌厌”的音变,犹“旅旅”之转为“庐旅”(《公刘》“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是语语”,马瑞辰据上下文以为“庐、旅古通用,本或作旅旅,后譌为上庐下旅”),“涟涟”之变为“流涟”(《诗·氓》“泣涕涟涟”,《后汉书·翟酺传》作“涕泣流连”,《晋书·江统传》作“悲泣流涟”)。《秦风小戎》“厌厌良人”传:“厌厌,安静也。”《小雅湛露》传:“厌厌,安也。”所谓“安静”“安”,皆有徐缓、平和义。《黄帝内经素问》卷五:“平肺脉来,厌厌聂聂,如落榆荚,曰肺平。”唐王冰注:“浮薄而虚者也。”“浮薄而虚”是指其濡弱平缓无力。《难经》卷二说:“气来厌厌聂聂,如循榆叶,曰平。”王九思等集注引吕广曰:“其脉之来,如春风吹榆叶,濡弱而调,故曰平脉也。”所谓“濡弱而调”,是指柔弱缓和。此指脉象言,若言人,则此为病弱态。如《世说新语·品藻》:“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厌厌”即形容微弱状。欧阳修《送张屯田归洛歌》:“季秋九月予丧妇,十月厌厌成病躯。”具可证。此處当是形容柔弱之躯的行路状态,是女子自喻。这样与下两句“岂不夙夜?谓行多露”也一脉相贯了。朱熹释此句说:“我岂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尔。”这个解释应当是正确的。“谓”借为“畏”。正是因为身躯柔弱,故才有畏露之思。
由此而言,诗第一句的“露”当作“路”,第三句的“露”才指的是露水。
关于“雀角”“鼠牙”的问题
在表面上看,麻雀没有头角,一望可知;而老鼠啃箱咬柜,似是有牙的。把“雀无角”“鼠无牙”列在一个平面上论,显然不合适。于是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在老鼠有牙的基础上来解释“雀无角”的问题;一种是以“雀无角”的常识为基础,来推定老鼠没有牙的问题。
认定老鼠有牙者,则认为“雀无角”的“角”,并不是指头角,当是指麻雀的嘴。于是在就“角”如何与嘴联系的问题上进行研究。此一说产生于宋代。宋段昌武《毛诗集解》云:“东汉注云:角谓觜。盖方言则然也。”宋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六“角”字一则说:“《董仲舒传》:‘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师古曰:‘谓牛无上齿则有角,其余无角者则有上齿。’仁杰按:颜注本出《淮南书》所云‘戴角者无上齿’,此非通论也。其他羊鹿之属,岂皆无上齿乎?按《行露》诗‘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盖古谓咮为角也。兽有齿而鸟有咮,鸟有翼而兽四足,故曰‘予之齿者去其角,傅之翼者两其足’。互文以见鸟与兽不相兼耳。”明以后此说益盛,如徐光启《诗经六帖讲意》、姚旅《露书》、胡绍曾《诗经胡传》、王夫之《诗经稗疏》、萧昙《经史管窥》、俞樾《群经平议》、闻一多《诗经新义》、于省吾《诗经新证》等,皆从音韵训诂角度,详加考证,以为角即噣,角字应读为咮或嘱,角、咮、嘱三字古音并属侯部,可相通假。
另一种意见,是由“雀无角”来推定“鼠无牙”。“雀无角”人皆知之,至于“鼠无牙”,人便多疑了。如《孙公谈圃》即引“曾有人捕一䑕与王荆公辨,荆公语塞”故事,以说明鼠实有牙。于是清儒段玉裁注《说文》,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证。其云:
“牙,壮齿也。”“壮”,各本讹作“牡”。今本《篇》《韵》皆讹,惟石刻《九经字㨾》不误,而马氏版本妄改之。士部曰:“壮,大也。”壮齿者,齿之大者也。统言之皆偁齿、偁牙,析言之则前当脣者偁齿,后在辅车者偁牙。牙较大于齿,非有牝牡也。《释名》:“牙,樝牙也。随形言之也。”辅车或曰牙车,牙所载也。《诗》:“谁谓雀无角”,“谁谓鼠无牙”,谓雀本无角,鼠本无牙,而穿屋穿墙似有角牙者。然鼠齿不大,故谓无牙也。东方朔说驺牙曰:“其齿前后若一,齐等无牙。”此为齿小牙大之明证。
段玉裁此说影响甚大,清儒如胡承珙、陈奂、多隆阿、龙起涛、马其昶以及日本学者竹添光鸿等,皆从段玉裁说。但段玉裁说实有武断之嫌。其误有二,第一,改“牡齿”为“壮齿”,没有考虑到许慎“牡齿”说的真正意义。“牡”本指雄性动物,雄性动物生殖器突出,“牡齿”当指锐突的牙齿。故“牙”有雄性的意思,如公猪又称牙猪,公狗又称牙狗,男孩又称牙子或伢子。宋沈括《梦溪笔谈·辩证一》说:“牙璋,判合之器也,当于合处为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军旅,则其牝宜在军中,即虎符之法也。”此皆可证《说文》不误。其次,以“壮齿”为齿之大者,意其所指为口中臼齿。今之《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权威工具书,都接受了段氏“壮齿”之说,径释牙为臼齿。但据现代生物学研究得知,老鼠实有臼齿,其口中共十六颗牙齿,四颗当口者为门牙,两边上下各三颗臼齿。因此段玉裁的说法不能成立。
关于“谁谓”“何以”的问题
“雀无角”“鼠无牙”既是实情,新的问题便又产生。无论是角还是牙,都不是穿屋、穿墙的工具。即如日本安井衡《毛诗辑疏》所说:“凡有角者皆走兽,我未闻牛羊麋鹿之属有穿屋者。”因此“何以穿我屋”“何以穿我墉”的质问,便不能成立。
也就是说,依雀有角、鼠有牙之说,“谁谓”之问便不可理解。如《谷风》言“谁谓荼苦”,是因为荼实苦,《何广》言“谁谓河广”,是因为河实宽,诗人的反问,旨在表示己之看法与众不同。因此只有在“雀无角”“鼠无牙”成为事实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提出“谁谓”的问题来,以表示事实有意外,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如果说雀本有角,鼠本有牙,那就不会有“无角”“无牙”之说产生,何来“谁谓”之问?难道是为辟谣而发?其之不通如同说“谁说鱼不会游泳”“谁说羊不会吃草”一样,事情本不存在,反诘自是多余。如果依“雀无角”“鼠无牙”的解释,那么“何以”之问便不靠谱了。解释这种矛盾的方法,现在只有合理的破读了。
我认为“谁谓”当读作“虽谓”。“虽”繁体作“雖”,与谁、唯皆从“隹”得声,例得相通。《易·丰》“虽旬无咎”,汉帛书本“虽”作“唯”。《淮南子·道应训》“谁知言之谓者乎”,《列子·说符》“谁”作“唯”。《左传·成公八年》:“唯或思或纵也。”《释文》:“唯,本或作虽。”《墨子·非儒》“用谁急,遗行,远矣”,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即读“谁”为“虽”。其实谁、雖、维、惟等字,其初文都只书作“隹”,是后来人根据用意才加了意符,变成了形声字。这在金文和甲骨文中看得很清楚。而“何以”则当读作“可以”。
在金文中,“何”多作“可”。文献中也常通用。《左传·襄公十年》“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释文》曰:“何,或作可。”《昭公八年》“若何吊也”,《释文》曰:“何,本或作可。”石鼓文“其鱼隹可”“可以橐之”,后人皆读“可”为“何”。
试着这样一读,文理便非常畅通了。角、牙都是锐利之物,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虽说麻雀没有锐利的角,但可以穿破屋檐;老鼠虽没有尖锐的牙,但可以穿透厚墙。以此来喻男子虽没有“家”——没有大夫那样的权势,但足以撺掇弱者吃官司。在这个比喻中便可以看出,这里的“家”是有特殊意味的。但《毛传》没有解释,郑玄以为是“家室之道”,朱熹以为“家谓以媒聘,求为室家之礼也”。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以为“‘家’即室家之家,夫妇合则成家”。牟庭震《诗问》以为“无家”指“无妻室也”。这些解释都觉得勉强。恩师姚奠中先生以为此“家”当是“大夫有家”之“家”。《尚书·洪范》“其害于家”疏:“王肃云:大夫称家。言秉权之臣必灭家,复害其国也。”《周礼·称官·方士》“方士掌都家”郑注:“家,大夫之采地。”《论语·季氏》:“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何晏注:“孔安国曰:国,诸侯也;家,卿大夫也。”《史记·魏世家》:“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庄子·骈拇》:“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皆以家属大夫。朝鲜李瀷《诗经疾书》亦云:“此诗之要在一‘家’字,其无家而速狱,如无角、牙而能穿也。”这个解释是很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家与诗中的角、牙是同一个重量级上的事物,它在这里象征着权势。诗中的逼婚者虽没有大夫那么样的权势,但他足以把一个反抗者送入牢狱。
关于诗旨问题
关于《行露》的诗旨,汉时已有歧说。《毛诗》家以为其事言召伯听讼,其旨言文王之化。故《毛诗序》首句说:“《行露》,召伯听讼也。”继则言:“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郑玄解释说:“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当文王与纣之时。”把时间推定在文王之时,以明此所言为文王之化,因“贞信之教兴”,故有了贞女拒强暴之男的守贞行为。据郑玄所言,讼起的主要原因是:“媒妁之言不和,六礼之来强委之”,即男女双方没有谈好,男方便强逼其成亲,也即孔颖达所说的:“男女贤与不肖,各有其耦,女所不从,男子强来。”这个解释应该说是从情理推出的,较合于一般人的理解。如果把所谓“贞信之教興”的经学诠释语言删除,这便是女子反抗强暴婚姻的声音了。
《韩诗》家则把此诗之旨落实到了“婚礼”上。《韩诗外传》卷一说:“传曰: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故举而传之,扬而歌之,以绝无道之求,防污道之行乎。《诗》曰:‘虽速我讼,亦不尔从。’”这里所引的“传”虽不知为何传,但可以肯定是韩婴前的《诗传》。刘向《列女传·贞顺传》说得更具体了。他说:“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嫁于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与其人言,以为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轻礼违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于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礼不备足也。君子以为得妇道之仪,故举而扬之,传而法之,以绝无礼之求,防淫欲之行焉。又曰:‘虽速我讼,亦不汝从。’此之谓也。”这可以说是一则诗本事。这对于诗篇的传播应该是很有帮助的,但可信度很值得怀疑,这可能是汉儒为传播守礼的思想编出的解经故事,故后人多不从此说。
代表《齐诗》说的《林易》,其《大壮之姤》说:“婚礼不明,男女失常。《行路》(露)有言,出争我讼。”也以为此诗是有关婚礼之讼的。
《毛诗》家重在教化,故所言“贞信之教兴”,旨在社会风气之变;《三家诗》(或以刘向代表《鲁诗》说,如此,则鲁、韩说相同)重在守礼,故所言“一礼不备”,旨在婚礼制度的坚守。虽同为经学诠释,而意义指向则不同,但可注意者有二:第一,他们各有经师传说做根据,传说或有变异,则非无根;第二,都是在为社会秩序的稳定考虑的,故而后世经学家从不同角度做了合理的修正与发挥。如朱熹说:“南国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乱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礼自守,而不为强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诗以绝其人。”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此篇玩‘室家不足’一语,当是女既许嫁,而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因不肯往,以致争讼。盖亦适有此事而传其诗,以见此女子之贤。不必执泥,谓被文王之化也。”
宋以后随着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需要和经师旧说约束的解除,新说便丛出不穷。或以为美大夫断讼者,如伪申培《诗说》曰:“强委禽而不受,至于兴讼,大夫以礼断之,而国史美之。”或以为拒野人强婚者,如伪子贡《诗传》说:“野人强昏不得而讼,女氏终拒之,赋《行露》。”或以为嫠妇执节者,如朱谋玮《诗故》说:“(《行露》)嫠妇执节不贰之词也。”或以为女子虚设之词,如姜文灿《诗经正解》说:“通诗大意,谓我之守身防礼,不敢踰越。假令犹有强暴不谅,横以相加,虽雀角鼠牙疑似难辨,而我必白之,不妄从也。甚言以自固,非贞曾待断于召伯也。”或以为女子父母之言,如李诒经《诗经蠹简》说:“《行露》,此即守礼拒婚以致速讼之女子,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盖诗人托为女子父母之言,非出自女子之口也。”或以为失怙女子之作,如方苞《朱子诗义补正》说:“盖此诗既女子所自作,则失怙恃,且无兄弟之依可知矣。……不知设诈以求偶,即此已不足为人夫,此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决也。”或以为贞女遭谤者,如罗典《凝园读诗管见》说:“其时以未嫁之女子,贞而被谤,即得出而诉之召伯。召伯听之亦疑,执夸者与女子相质,而讼遂理。”或以为召公为文王遭谮所赋者,如胡文英《诗经逢源》说:“文王忠于殷,小入谮而囚之羑里,召公赋此以抒情焉。”或以为跛男告美女者,如牟庭《诗切》说:“申氏女好,而酆氏之子盖跛行蹩躠者也。申为媒妁所欺,而不肯嫁。酆人讼之于理,理官察其实曾许婚,而惜以好女配非其偶,故作是诗,判其狱而遣之。”或以为强而为妾之女词者,如于鬯《香草校书》“行露篇谁谓女无家”条曰:“玩此诗之意,盖此强暴之男欲强此女为妾,而女不愿,以至于讼。”或以为贫士却婚以远嫌者,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说:“《行露》,贫士却昏以远嫌也。”又说:“大抵三代盛时,贤人君子守正不阿,而食贫自甘,不敢妄冀非礼。当时必有势家巨族,以女强妻贫士。或前已许字于人,中复自悔,另图别嫁者。士既以礼自守,岂肯违制相从?则不免有速讼相迫之事,故作此诗以见志。”或以为女抗拒不亲迎者,如王先謙《诗三家义集疏》说:“礼不备而欲迎之者,夫不亲迎也。女不肯往,以不亲迎为轻礼违制也。”或以为戒民无讼者,如王闓运《诗传补》说:“方伯巡行,戒民无讼,以靖民志。”或以为召人化召公之德者,如日本伊藤善韶《诗解》说:“言召人化召公之德,妇人非正礼仪,不从非理之娶。”或以为诗人代言者,如山本章夫《诗经新注》说:“《行露》南国之女以礼自守,不为强暴所污,诗人代述其志。”或以为诸侯去纣归周者之作,如朝鲜沈大允《诗经集传辨正》说:“诸侯有去纣而归周者,遭纣之谴,怒而不改其志,托于女子之自守而风之也。”这些几乎都是在依违于旧说之间而揣摩出的新见,从经学的角度讲,这是允许的,因为这可以体现经学意义的无限伸张性,并大大扩展了经典的伦理内涵。
但从史学的角度考虑,毕竟有个求实的问题。从诗篇的内容分析,这是一篇女子抗婚诗,但至于是父母之词,还是诗人代言,确难认定,不过这不碍于诗意的理解。《毛诗》“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之说与《三家诗》“许嫁”而“礼不备”说,求之经文,都是相吻合的。因为只有以婚约为依据,才有可能发生“速我狱”之事;也只有“礼不备”而强行婚娶,才能形成“强暴之男侵陵贞女”的事实,也才有“亦不女从”的表态。齐、韩、鲁、毛四家,只是就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而立说,应当是有历史传说依据的。孔颖达曾举《左传·昭公元年》“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黒又使强委禽焉”一事,以说明逼婚的可能行。林义光《诗经通解》又结合上古礼俗考证此篇,以为暴男侵贞女与周之立法有关。其云:“按强暴之男侵陵贞女,而反能致女于讼狱,此必证以古时嫁娶之法,而其义(古嫁娶之法)始明。盖古人惧民之不嫁不娶而流为淫泆,是以严为嫁娶之法。《墨子》云: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节用》上篇)。嫁娶之年,男自冠以至三十,女自笄以至二十。(《文十二年榖梁传》注引谯周曰:‘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则速,后是则晚。凡人嫁娶,或以贤淑,或以方类,岂但年数而已?若必差十年乃为夫妇,是废贤淑方类,苟比年数而已。礼何为然哉?则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说嫁娶之限,盖不得复过此尔。’)期尽之岁,以仲春冰泮为限,故《周礼》媒氏于每岁仲春,伺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会读如会计之会,谓稽核也)。贫不能备礼者,许其杀礼行,故曰奔者不禁。奔者,不聘之谓也。《荀子》亦云:‘霜降逆女,冰泮杀止。’(《大略》篇)若限满而不嫁娶者,则以为不用令而罚之。立法如此,故亦有无家之男伺得无夫之女,致之讼狱因以得妻者。而召伯听讼,则此等暴男不得售其奸,故其诗云尔也。”此也可备一说,但最合理的解释,恐怕还是不能抛弃“许嫁”说。
结合四家《诗》说,参以前人研究,此诗当与周代婚俗有关,即如林义光所说,是仲春二月“会男女”之令为背景的。《周礼·媒氏》记载,为了繁衍人口,政府出了男女婚配的强制性措施,即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是一个极限。并于仲春之用“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奔者不禁”,反映的是婚姻的自由状态;“不用令者罚之”,反映的是当时男女婚配的强行法规。在这种背景下,或有强暴之男强使女家许婚者,但又礼数不备,遭到女方拒绝,故有了借势告女方于官的事情发生。这首诗所反映的便是女子对这种强婚行为的反抗。
诗与经的双重解读
这是一篇女子抗婚之歌。从内容分析,当是男女双方有了婚约,但婚礼之事并没有商量妥当,即如《毛诗》所言“媒妁之言不和,六礼之来强委之”,或因礼数不到,即如《韩诗》所言“一物不具,一礼不备”,男家要强行婚娶,遭到了女家的拒绝,于是便借官府的势力给女方施压。诗篇很巧妙地用雀角、鼠牙带出了这位男子的非正当行为。麻雀虽然没有坚确的锐角,但可以穿破屋檐;老鼠虽然没有尖锐的牙,但可以穿透厚墙。同样,这男子没有大夫那样的“家”——权势,但可以把自己送入官府。说明这位男子采用了不正当手段,非君子之行。
需要說明的是关于这个“家”的问题。古时大夫不但有相当的产业——家,而且在法律上也有超出平民的特权。《周礼·小司冠》云:“凡命夫(大夫)命妇(大夫妻),不躬(亲自)坐狱讼。”《左传·昭公元年》记郑大夫子南、子晳为争美女发生纠纷,子南因自卫而伤了子晳,可是子产却说:“直钧(各有理由),幼贱有罪(年少而位下者有罪),罪在楚也(子南之名。因子南年少而贱,子晳为大族,故云)。”大夫之间,可以依权势大小决定曲直。若大夫与平民争讼,胜者自然是大夫了。大夫有家可以凭着家势送平民入狱,在平民之间,则可以以行贿取得讼争的胜利。《左传·襄公十年》传云:“政以贿成”,《国语·晋语》云:“梗阳人有狱,将不胜,请纳贿于魏献子,献子将许之。”由此测之,《行露》中的男子,当也是以行贿的手段,召女家吃官司的。所以诗篇用无角无牙的雀鼠来比喻男子,表示了对这种反常规、不合理现象的极大愤慨。
诗篇通过奇妙之喻和女子的态度,展示出了双方不同的品格。“强暴之男”强横无理,不讲礼义,如鼠、雀之辈,品行龌龊,干的是穿墙、破屋的勾当。“贞女”则不屈于势,不苟于行,即使在高压下,也能保持坚贞的品格。诗篇表现出了对不规行为的鄙视和不为强势所屈的堂堂正气,我们从诗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反抗强暴的烈女子,更是一个民族坚守正义、不屈强暴的堂堂风貌。诗中咏及的雀角鼠牙,因其构思之奇,遂成为文学史的一种意象,不断地呈现于诗人的笔下。如明周瑛《送丘大尹知黟县》诗:“黟中风俗近如何,雀角鼠牙知不多。君到山城无别事,棠阴满地听弦歌。”即以雀角鼠牙喻无赖子。
前人从艺术角度分析此诗,颇有妙论。今择数则于下,以供参考。
戴君恩《读风臆评》:“先鸣其守,为下张本。气象从容,不突不急。下文正意只‘虽速我狱’二语便了,却先反振谁谓雀无角四语,遂觉精神耸动,笔力遒整。乃知文章家唯反则不板,唯反则不死。”
又说:“首章如游鱼衔钩而出渊,二三如翰鸟披云而下坠。”
牛运震《诗志》:“章首似截去一句,别格冷韵。得力在疉两行露字,婉绝峭绝。隐语抝调,三句中多少曲折。(二章)陡接‘谁谓’,咄咄逼人。雀说有角,奇!末二句说得豪门富户,真不值一盼矣。足令狂子败兴。(三章)雀鼠,骂得痛快而风流;‘室家不足’,说得冰冷;‘亦不女从’,拒得激烈。”
又说:“平空撰共两造对簿之辞,奇甚!《孔疏》所谓诗人假事而为之辞,甚得诗旨。定以为女子所自作,失之。”
龙起涛《毛诗补正》引旧评:“‘谁谓’‘何以’四字,皆从必无而忽有之事反覆驳诘。‘虽’字一转,折出下句,倍觉森峭。”
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起势陡峭,岂不句一折,笔情婉妙。后二章反振四句,然后折落,如鹰隼翔空,披云下坠。”
从《毛序》到汉《三家诗》,基本上认定此诗的主题与抗婚相关,虽然对于具体事件的阐述不尽相同,但在观念形态中则是相一致的。这就确定了经师们对此诗伦理道德意义认识的一致性。其作为经的意义,大略言之有二:
第一是女子之“贞”。欧阳修《诗本义》以“女能守正不可犯”,季本《诗说解颐》言“女子能持择配之正,不为强暴所陵”,“守正”“持择配之正”,都是《诗序》所谓的“贞女”的诠释,也是对诗篇中“亦不女从”行为的体悟。而《三家诗》“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轻礼违制,不可以行”的阐释,以及后儒所谓“贞女守礼”(郝经:《毛诗原解》)、“自述其守礼远嫌之志”(陆化熙:《诗通》)、“守礼拒婚”(李诒经:《诗经蠹简》)、“以礼自守”(丁若镛:《诗经讲义》)之说,更是对“贞”的具体诠释。这里所反映出的是这个民族对于道义的坚守。作为女子,她所坚守的是不被强暴所污;作为一个普通人,则有一个如何保持品格纯正的问题。古人每以贞女比贞臣,也正是在“坚守”上立说的。一个以功利为第一原则的人,是谈不上坚守的,也是不知道义为何物的。
第二是对强暴的反抗。“守贞”是自己不去做,而“抗暴”则是要抗拒别人强迫自己做。诗中的女子,在“速狱”“速讼”的威逼之下,仍能坚守原则,表现出“亦不女从”的决绝态度,大有“舍生取义”的气概,这也正是民族文化中一再所倡导和弘扬的精神。
再则,《毛诗序》所谓的“召伯听讼”,以及后儒对“召伯听讼”意义的发挥,也大大拓展了此诗的经典内涵,代表着国人清官、清政的意识。如王十朋《召公》诗说:“䑕牙雀角岂能欺,召伯聪明听不疑。南国政成公已去,甘棠长结后人思。”这反映出的是中国人向善心理与政治清明的理想追求。同时也是历史峡谷的永恒呼唤:文王何在?召伯何在?提醒秉政者对自己的政绩与行为进行反思。
作者:刘毓庆,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