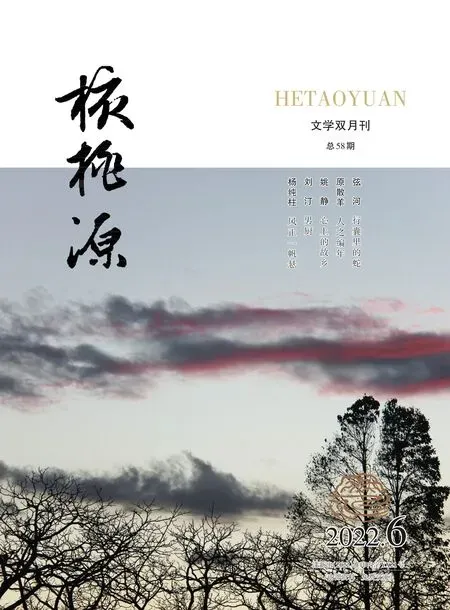心上的故乡
2022-02-10姚静
姚 静
每个人心上都有一个故乡,她不仅仅是一方熟谙的山水,她更多时候是一处精神皈依之地。作为精神皈依之地的故乡不再是一个具象的地理位置,她甚至不在地球之上,只驻我们心上,惟有心灵才能感知到她的牵绊,她的存在。
——题记
对我而言,故乡是这样一个所在,年少时拼命逃离,人到中年却频频回首。其实啊,我回首眺望的是最初离家时那个圆满丰润的少年,不带伤痕、不着尘埃,即便流泪,泪光里闪烁的也都是希望和期盼。
每个人离开故乡的第一步都是一个簇新的脚印,柱仗而归,只为寻找那一个簇新的初始。
我的藉贯和故乡是不一致的。
父亲的故乡在昭通。我一岁多的时候随父母回去过一次。我蹒跚学步的双脚晴蜓点水般在那一块土地上站了站,没有留下一丝儿关于昭通的记忆。因为父亲在昭通已无直系亲属,后来再也没有回去过。那一块土地永远复归陌生。
母亲的故乡在昆明。外公在世的时候,倒随母亲回去过几次,逛过西山龙门,赶过花街,对村里的大水井、秋千架也有些许印象,但终究是匆匆一瞥,对那个位于西山脚下的彝族小村庄始终隔膜得很。
我的父亲母亲参加工作以后,就远离了他们的故乡,四处兜兜转转,辗转滇东、滇南至滇西,最后在大理州剑川县生下了我。
长大后我时常需要填一些表,其中藉贯一栏,我有时候填上父亲的故乡“昭通”,有时候填上母亲的故乡“昆明”,不论昭通还是昆明,于我都是全然陌生的地方。后来单位整理个人档案,要求藉贯必须明确一致,我思索良久,其实我最想在藉贯一栏里填上的是“剑川”,可是所谓藉贯指的是祖父及以上祖先的长久居住地,剑川显然不是我家祖上的居住地。
剑川是我的故乡,我生于斯,长于斯,我熟悉她的山水风光、人情风俗,如同熟悉自己掌间的纹路。这一份日积月累的熟谙,无论离多远,无论隔多久,一句乡音,一截衣袂,都会瞬间唤醒记忆。
一个人无论走得有多远,心的指向永远朝着故乡。你离故乡有多远,心离故乡就有多近,随着年纪的增长,故地旧园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心上梦里。
当你在道“晚安”已过,说“早上好”太早的时刻醒来,除了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就无事可做。故乡,关于故乡的种种,在这样的时刻都会袭上心头。
大佛殿是我的出生地。她是一个彝族小山寨,位于剑川县西北方老君山脚下。老君山号称“滇山之祖”,传说太上老君曾在此炼丹,它的山势之雄奇,林壑之优美,自不用多言。
我第一次张开眼睛,看见的是大佛殿的山水;我第一次蹒跚学步,脚踩的是大佛殿的土地。大佛殿是我人生的源起之处。
“大佛殿”听上去像是一座寺庙,这个地名确实源起于寺庙。老君山上有一座小庙,供奉着一尊大佛,大佛殿因此得名。
我没有见过那个隐于深山的小庙。小时候时常看见附近村寨的一些老人(妇女居多),他们三三两两相约着,带着米面等吃食步行到老君山上烧香朝拜。为表虔诚,他们中有些人是从数十公里外走着来的,以求今生平安,来世顺遂。那个隐于深山的小庙让我觉得神秘可畏,对络绎不绝去烧香朝拜的人们,总是不解。小时候我不知道人总要有一点念想才能活下去。今生的遭遇,是前世的果;今生的修为,是来世的因。没办法说服自己时,迷茫的心总要找一个出口。这也是那个小庙香火不断的原由。
成年后,方明白三生轮回的说法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安慰,让人活得不至于太绝望罢了,真假间留下一丝儿念想,把诸多的不甘寄托给下辈子。人生的大幕落下,是否尚存一缕芳魂?循着旧日踪迹而去?能如此也算一种圆满,在走过万水千山之后。
再长久的人生终有掩卷的一刻,纵有万般不舍也要打出“剧终”两个字。如此一想,离合悲欢便少了一点锥心的疼。人生际遇不同,不羡慕别人,也不哀怜自己,脚下该走的路一步不少,心里该熬过的思念,一分不少。
谁不是走在朝拜的路上?
据说大佛殿彝族的先辈是从丽江宁蒗游牧而来,他们爱上了老君山脚下这一方山水,就留下来。他们像一把种子,撒落在老君山脚下的山谷间,生根、发芽、长叶、抽枝,慢慢繁衍出一个村寨来。
虽然经历了辗转迁徙,他们却一直延袭着本民族传统的祭祀、嫁娶、丧葬等习俗,成为一个具有浓厚彝家特色的村寨。
对于大佛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入侵者。我的父母是林业工人。当时林业局在大佛殿有两个伐木点:三工队和四工队,四工队就驻扎在大佛殿,三工队还要往上走,几乎进入老君山腹地。
我家在四工队,和大佛殿相邻而居,看得见寨子里的袅袅炊烟,听得到寨子里的鸡鸣狗吠。
每天林业工人们抬着轰鸣的油锯和锋利的斧头上山去,他们砍倒一棵棵树木,修掉树枝,堆放在一起,然后装到一辆辆绿色的解放牌汽车上,运到山外去。
绿色的林涛哗哗起伏,带着松脂的清香四处翻滚,大佛殿周围的山岭上仿佛有着砍伐不尽的树木。
我不知道父亲手里的油锯放倒过多少棵参天大树?只知道家门前那一条林区公路上运送木材的解放牌汽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那时候林业局时不时会来一场“大会战”,以此激励工人们的工作热情。大会战时工队上插满彩旗,高音喇叭里放着振奋人心的歌曲。在油锯和刀斧声里,工人们喊着“顺山倒”的号子,一个个山头被剃光。
小时候我不知道这么多的木材运到山外去做什么?后来读了郭小川的诗《祝酒歌》才知道:“广厦亿万间,等这儿的木材做门楣;铁路千万条,等这儿的枕木铺钢轨”,大佛殿的木材,林业工人的辛苦,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
林业工人很辛苦,工资却不多,须精打细算才能顾住一家人的温饱。林场工队又多在深山老林里,生活艰苦不便。羊岑是离大佛殿最近的乡镇,也在十多公里之外。羊岑每逢星期四赶街,人们采买购物都集中在这一天。为方便日常生活,工队职工家家户户都自己开挖了一块菜地,还养了鸡猪鸭鹅,尽力争取菜蔬自给自足。
在那个物质困窘的年代,大佛殿的腊肉成了我的温馨记忆之一。大佛殿属高寒山区,腌制出来的腊肉色泽靓,味道香。放学回家,一踏进院门,如果闻到一股腊肉喷香的味儿便欢呼雀跃:今天吃肉!母亲习惯用一个圆鼓鼓的锣锅煮腊肉,放在一个燃着炭火的炉子上,咕咚冒着热气,肉香四溢。腊肉汤时常用来煮大白豆,或者干板菜,或者干蔓茎片。大白豆、干板菜、干蔓茎片都是当地的特产,也是我一直爱吃的菜。我的胃也忘不掉故乡的味道。
父亲和大多数林业工人一样,有喝酒抽烟的习惯。他们的工作太苦太累,何以解乏?惟有烟酒吧。一群工人围着一张饭桌划拳赌酒是当时最常见的娱乐方式,他们大呼小叫,喧声震天,直到月亮升起,星星满天才散去。
我的人生和大佛殿重叠的时光并不长,我四五岁的时候,便随父母搬迁到大佛殿外五六里处的一个白族村寨——旧栗坪。林业局在旧栗坪有一个道班,专门养护运输木材的林区公路。
我在旧栗坪上了小学。
相比之下,我在旧栗坪生活的时间更长,可大佛殿是我的出生地,她对我便有了非凡的意义。她是我记忆洄溯的终点,在她之前,我没有来处。
出生在这里,或者出生在别处,我无法选择,却感激冥冥中安排一切的诸神,让大佛殿连绵的青山,起伏的绿林,潺潺的小溪,漫坡的野花,漆黑的垛木房,着长裙的彝家女,成为我关于世界最初的印象。
旧栗坪与大佛殿相隔不远,两个村寨的人也都互相熟识。我们时常到大佛殿找蘑菇,采蕨菜,看电影。那时候,林业局有一个放映队,轮流着到各个林场和工队放电影。因为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同一个片子在旧栗坪道班放过了,我们还是会追随着放映队,到大佛殿四工队再看一遍。
电影散场后,和邻居、和附近的村民一起打着手电筒,举着火把往家走,一边讨论着电影里的情节。现在回想起来不觉得辛苦,只觉得那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大佛殿滋养了我。我关于世界最初的记忆在那里伫足、停留、徘徊、依恋、缠绵。在别人眼里,她不过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只因为我的第一声啼哭在她的山谷中响起,我的第一个脚印落在她的泥地上。我的潜意识里美化了她,她成了一个无可替代的山寨。
每一个人的出生地都是无可替代的,哪怕再也回不去,却永远是心头最柔软的地方。
四季可以轮回,人生却无再次。当我重返大佛殿,已年过五旬,再也回不到呀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儿时。
人到中年方明白,离乡背井的奔赴不过是为了去遇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在历经千百场聚散后,只要最重要的那一个人还在身边,那么千百场聚散都可以挥手笑别。一旦最重要的那一个人离你而去,余生便成了一场漫长无期的告别,岁岁年年、日日夜夜、分分秒秒你都在依依不舍。思念一点点吞没你。这时候,蚕食,是极形象的一个词;凌迟,是血淋淋的一件事。而你却要不动声色地面对。人生如戏,却由不得自己去编排,许多的偶然、意外、猝不及防让人生变得千疮百孔。
大佛殿是我的疗伤之地。
衣锦还乡是得意人的炫耀;梦回旧园是断肠人的抚慰。故乡无言地接纳着每一个回归的游子。
当眼前的日子过得不尽如人意,就回故乡去。
我们的车子沿剑兰公路前行,过了红旗林业局机关所在地,就偏离剑兰公路,穿过一个叫作“金坪”的村子,岔上通往大佛殿的公路。
到大佛殿的公路还是原来那一条林区公路,从前林业局为运送木材修建的。路线一点没变,每一个弯拐,每一道短坡还和记忆中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从前坑洼不平的泥土路面变成了水泥路面,光滑平坦。公路一直在山坳里穿行,几乎没有陡坡,也没有急弯,车轮贴着水泥路面刷刷前行。近乡情怯,看着车窗外熟悉的景色,我不由得心跳加速。车子驶上一段平缓的短坡,一侧是溪涧,雨季里会涨水,平时几乎干涸。另一侧有一道低凹的山箐。我记得春天山箐里会开满蓝色的灰背杜鹃花,蓝莹莹的一片,像一块蓝纱巾遗落在那里。接着车子进入一条山谷。山谷拐弯处,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叫作“瓦窑”。曾有人在这里修窑烧瓦。现在瓦窑早就没了踪影,那块平地全部变作了庄稼地,中间立着一幢用来看守庄稼的土墙房,孤伶伶的。车子驶上一个长坡,爬通长坡,就看到大河了。“大河”是从老君山上流下来的一条河,它流经大佛殿、旧栗坪、金坪、羊岑等村寨,林场的人都叫它“大河”。大河河水清亮、充沛,哗哗不绝。夏天,我们时常到大河里洗澡、戏耍。架在大河上的原来是一座木桥,由数根粗大的木头并排而成,上面铺着碎石和泥土,透过缝隙,看得到桥下白哗哗的河水。现在木桥的位置上有了一座水泥桥。
从前交通不便,人们时常步行回家。这座桥边是一个休憩地。走乏了的人们,御下背负的东西,到大河边洗洗手,掬一捧水喝,再坐到光滑的石头上歇一口气,抽一支烟。河水哗哗,像和人们问候打招呼。
山未变,路未改,我却从稚子到了中年。山水是否记得我?我曾沿着这条公路到山外求学,一次次往返,从小学走到中学,从中学走到大学,直至一去不返。三十年的时光已过,为什么我还看见儿时的自己在这条公路上走着,走着……
人有记忆是幸,抑或不幸?有人羡慕金鱼,只有三秒的记忆缅怀过往,再痛再疼也不过三秒。可是曾经的欢愉,曾经的痛楚,都消失干净了,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过了大河,旧栗坪就到了。
我们在道班旧址停了车。道班的职工住房早已踪迹全无,被夷为平地,变成一大块平坦的庄稼地。曾经家园的位置我还是找得到的。那条小河还在,父亲亲手种下的蔷薇篱笆也还在,只是那道蔷薇篱笆内我们家的位置上盖起了一幢土墙房。看那幢房子的式样应该是从旧栗坪迁来的人家。故园旧貌留在我的记忆中,只能回想。我在小河边,看到了一棵垂柳,它粗壮发黑的树干分出两个粗大的枝丫,又被迎头砍去,两截断口处有新枝长出,举着鲜绿的柳叶。我认出了这棵柳树,它是我儿时种下的。我不知道柳树还记不记得我?我不再是那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了。好想伸手去摸一摸这棵柳树,只苦于隔着小河和蔷薇刺丛。
我默默和老柳树告别,想来花草树木荣枯盛败也会疼会痛,只不过它们的表述无声罢了。
不远处便是旧栗坪,这个小山村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房子多了,从山脚一直绵延到公路两边来,貌似人口增多了,也热闹多了。
我对着荡然无存的家园感叹一番,又接着赶路。再往上走五六里路便到大佛殿了。
在阔别三十年后,我回到了大佛殿。
三十年,近一半人生的岁月。我不知道关于大佛殿的记忆有没有错漏?我还能不能找到童年时的蛛丝马迹?
记忆是过去从前的存储器。如果记忆也会有错漏,这一生如何留存?转念一想,何曾要留存什么?人的一生不过自己觉得精彩罢了,在别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冗长乏味的故事。有无都没甚关系。许多名人传记在书店里都被束之高阁,何况草芥小民的一生?不过一沙粒而已,来不扰人,去不可惜,独独疼了自己的心。
在大佛殿我几乎没有熟识的人了,心情还是激动,与这一方山水,终是一场重逢。
是不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便止步不前?开始慢慢洄溯一生,在内心深处一点一点向出生地靠拢,即便身在异乡,心却回到了出生地。
公路两旁的树木越发苍翠茂密了,针叶的松树、阔叶的栗木和低矮的灌木长满了山坡和沟谷。山水依旧,春天会开满杜鹃花,夏天会长出野蘑菇……她们似乎都还在等着那一个穿着塑料凉鞋前来戏耍的女孩。与山川河流相比,人的一生不过是白驹过隙的一瞬间。
山还是那一座山,坝子还是那一方坝子,每一个远游的人回来,依然找得到方向。
大佛殿的山水丛林在我眼前,也在我心里。这是一块隐秘之地。她的独特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才能感受。
与那些险要高山,惊心大川相比,大佛殿就一荒村野寨,它的风光不过是小景小物。在长久的岁月里无人问津。只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记得她,因为熟谙,所以走了心。
我相信还有许多人也牵挂着大佛殿。曾经在这里抛洒过汗水的林业工人们,他们或因工作变动离开,或是退休回了老家。他们奔赴另一个地方,需要一点一点去熟识,去相处,去和诸多的不适应和解。而大佛殿是真正的故土,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会在心上梦里牵绕。
前方远远地出现了一道高大的寨门:公路两边各筑一个亭子,上面饰有彝族风格的图案。一条走廊把两个亭子连接起来。走廊中央装饰着一个牛头。牛头下方是“大佛殿”三个金色大字。
原来的大佛殿没有寨门。寨门的修建凸显了她彝族山寨的气息。
站在寨门前,我有点恍惚:大佛殿还是记忆中的模样,却又不是记忆中的模样。是记忆撒了谎?还是大佛殿变化太多?雄峻的老君山脚下,道道山梁环绕的小山村,给人的感觉不再是寂寥荒凉。一幢幢装饰着彝族元素图案的民房散落在山坳里,一幅安居乐业的温暖静谧。
曾经的大佛殿是让人一见之下便想落泪的,她穷苦,偏远,荒凉。黯淡漆黑的垛木房,圆木相扣成墙,木片履顶做瓦。怕大风把覆顶的木片吹了去,木片上压上一个个大石块。火塘里终年不熄的烟火把整个屋子熏成漆黑,连檐下的蛛网,灰尘都是黑的。洋芋,苦荞是这里主要的作物。洋芋挖回来后晾干,像小山一样堆在墙角,用一块大大的竹篾圈起来。这里的山水是一幅出离红尘的美景,身处其间的人,却要时时处处为一日三餐挣扎苦拚。
那年月,在这里生活是需要有一颗佛心的,视贫苦为素朴,落后为常态,永远不要和外界的繁华富庶作对比,挡住令人心动的诱惑,方能淡然,安然。
日复日,年复年,日子过得宁静却清苦。
我偏爱大佛殿,也就爱着她的僻远和荒寂,不过是因为我出生在这里,如同一条鱼,在这里孵化,然后启程游向外界。“出生地”让她具有了别样的意义。我心里有爱,才觉得这里的风清凉,水甘甜。记忆是一层纱,给这个原本荒僻的小山村披上了虚幻的美,随着年岁的增长,在我心上她如殿堂般神圣起来。
故乡的山水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她的美,她的亲,有着无可比拟的力量。
我记忆中的大佛殿是三十年前的模样,比我年长的人记得她四十年前、五十年前的模样,她被原始森林覆盖的时候,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是谁?有一个词叫“史前”,遥远到没有记载,无法探寻。
大佛殿的史前是什么样子?轻风知道,绿水知道,自然万物比人睿智,它们不言。
仿佛转瞬之间,半生已过。游子归来,故乡已不是旧时模样。
一条卵石铺成的路曲折绕进寨子。
清明前后,正是山村最美的时节。沿路李花雪白,桃花艳红,还有几树海棠花也鲜艳的开着。我睁大眼睛,搜寻着一丝半缕童年的痕迹。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行,我便是从这里起步,无论走多远、多久,这里始终是我目光回望的终点。没有大佛殿,我生于何处?来自哪里?
我们把车停在大佛殿小学背后的一块空地上。
大佛殿小学校舍整齐干净,校园中央竖着一面五星红旗。孩子们放学回家去了,校园里静悄悄的。
大佛殿也有了导航信号,我们跟着导航找到了开心彝栈。
到开心彝栈去要跨过一座小桥。我在小桥上停留了一会儿,桥下水声哗然奔流着的就是大河,它源起老君山,流经大佛殿,流经旧栗坪,伴随了我整个童年、少年时代。我站在桥上屏息聆听大河哗然的水声。
开心彝栈的大门上用彝文写着一幅对联,我不知其意,只是感觉彝家气息更浓郁了。进了大门,迎接我们的是开心彝栈主人杨禄森的妈妈。我一见老人,只觉面熟。小时候,我一定是见过她的,只不过那时候她还年轻,是个风姿绰约的妇人吧?穿长裙的彝家女子走在弯弯山道上,我时常与她们迎面相遇。
我们订好房间,安置好行李,便到寨子里四处转转。
古老的水磨还在,温暖的火塘还在,只是整个山寨给人的感觉却是不同了。老旧的垛木房不见了,家家户户住的都是清一色的瓦房,土黄色的墙壁上绘着红黑相间的彝族风格图案,院落宽敞整饬。
两条小溪一左一右穿过寨子。卵石小路沿着潺潺的溪流铺伸。路旁溪边海棠花、李花、桃花,东一棵西一棵盛开着,摇曳多姿。
寨子里还有另外几家客栈和农家乐,装饰都很有特点。想来经常有游客到这里来游玩休憩吧。寨子边上,有一个民族文化广场,立着太阳柱,是人们举行活动的场地。火把节时,寨子里的人会穿上彝族盛装在这里围着火把唱歌跳舞。
寨子一侧的山上有一个观景台。踩着一台台阶梯爬上去,可以看到大佛殿的全景:一块块翻耕好的土地等待着播种;牛、马、羊群在草甸上悠然地吃草。白的李子花,红的桃花,粉的海棠花,零零落落点缀其间。在观景台上转个身就可以远眺老君山的雄姿,它巍然肃立的苍天白云之下,想起太上老君在山里炼丹的传说,不由感慨自然的神奇与恒久。
时光在这里流淌缓慢,你可以捕捉到太阳一点点西斜的痕迹。
一朵云飘过来又飘走了,一阵风吹起来又停下了。房檐下的阴影由短变长。然后月亮升起来,挂在山尖,清辉泻地。
我们回到客栈。主人杨禄森也回来了。他邀请我们到堂屋火塘边喝茶。围火塘坐着的还有寨子里的几个邻居。我们聊起了四工队、三工队,还有几个熟人。
故乡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地方,不止是山水风土,人情习俗,还有这方土地上承载着的故人旧事。一个个故人,一件件旧事串起的记忆让故乡胜过了所有的地方。故乡成了一个收藏过往的所在。哪怕她山高水远,哪怕她贫穷枯槁,我们回望的目光永远温存。
夜渐深,我们便洗漱休息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很难安静下来,心里总是充斥着各种挥之不去的杂念,它们叨扰着我,让我无法专注地去做一件事,甚至无法专注地去看一朵云。一深思凝想,那些杂念就遁迹无踪;不去想它们,却又纷涌上心头。这就是浮躁吧,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在大佛殿的这个夜晚,我忽然安静下来,只想专心地睡一觉。大佛殿的夜晚万籁俱寂,偶尔有风从窗外扫过,像一声轻轻落下的呓语。
这是一块佛性的土地。没有晨钟暮鼓,没有经卷诗文,但人们脸上写着安然与宁静,写着通透与放下。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幸福的,从稚气童子到耄耋老人,年年岁岁,看朝露初敛,夕阳落山,一生缓慢平和,心里静谧得没有一丝儿情绪。折磨世人的是妄念与执着,而妄念与执着有着另一个名字叫希望与追求,令人疲于奔命。能安然于简静生活的人,是值得羡慕的。
这个夜晚,我在大佛殿梦到了大佛殿,她红白紫粉的杜鹃花、辽阔的高山草甸、还有沿着山溪分布的九十九个龙潭……我在梦里与大佛殿对话,我回来了,你远行的游子。在你的怀里,我无须戴着面具去讨人喜欢,让所有的瑕疵一览无余,用本真的面目去面对天地、山水、树木和花草。
我终于放下。
山高月小的夜晚,不惊不扰的梦境,时光不急不缓地走着,将又一个黎明送来。
我起了个大早,迎着天边的晨曦,顺着卵石铺的村道,去寻找我记忆中的家园——四工队。
我一步步走进记忆深处。
记忆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它能带我们重游旧地,重返从前。记忆有时候也是靠不住的,有了情感的加持,它会美化或丑化过往。当我们觉得记忆也无法真切再现昨日的时候,人生便有了一种虚幻之感。
岁月久远,许多细节遗失了,想象或许给记忆增添了一点点无缘由的装饰,却不影响四工队从我的脑海里清晰浮现。一条小河哗哗流过四工队驻地。一条小路跨河而过,延伸到篮球场上。篮球场边有序排列着几幢平房,有刷了白石灰的土墙瓦房,也有盖着油毛毡的木板棚。房屋周围是一道道木栅栏,圈起一块块菜地。篮球场上有两个木头做的篮球架,还立着两根放广场电影时用来挂银幕的木桩……它们一一从记忆中走出来,依稀模糊却是一生不忘。
我很快找到了四工队的方向。那一条经过四工队门前通往三工队的林区公路还在,只是年久失修,铺路面的碎石变得七零八落,凸凹不平,但仍然清楚地看得出那是一条公路的模样。我顺着公路向前走去。
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在哪里拐了弯?当年只是沿着这条林区公路一直往外走,走到不能再走的地方,大佛殿已抛在身后,我有了一种全然不同于父辈的生活。
一条小河出现在路边,水量枯乏,听不到哗然的水流声。小河那面就是四工队原址,如今全部变作了庄稼地,用一道木栅栏圈起来。一株青绿的柳树下有一幢民房,想来是这块土地现在的主人了。
什么叫沧海桑田?这就是了。四工队早已烟消云散,它像一个青春的故事,有始无终。隔世经年的重逢里泛着欣喜和忧伤,喜的是山水依旧,忧的是物是人非。我鼻子发酸,忽然间想要流泪。
三十年后回归的我已然是客,故园旧居不在,却终究与这一方山水难舍难离。我很难淡定从容。隔在我和大佛殿之间的岁月,远如山海,屡屡的回望里,她一直是最能抚慰我心的地方。
我自问:如果当初不曾远走,是不是就少了那些历劫般的遭遇?
每一个人从故乡出发时,内心都是茫然的,因为根本不知道将走向哪里?命运的结局早已定下,却一无所知地往前走。走着走着,添了第一道伤痕;走着走着,添了第二道伤痕……早知道最后是不可收拾的境地,何不留在故乡终老?徒经一番颠沛流离。
于我,故乡有着别样的意义,圆润光洁,毫发无损的我永远留在了故乡的土地上。
我是凡俗之人,做不到离尘清欢,所以常惹烦恼悲伤,白发早生。
无欲则刚,世间无欲者成了罕物。我们恋山恋水,恋华服恋美食,只有在碰壁受挫,万般失落时才会想起故乡,这时候故乡是一个逃逸之地。像病痛者求一贴止痛的药膏,故乡温柔地抚慰着我们。
所有的烦忧皆从贪欲而起,可面对红尘诱惑又怎么做到心如止水?所以我羡慕大佛殿守在火塘边,点起一只兰花烟的老妇。她把日月星辰全部藏在那一只自制的烟卷里了,一口一口慢慢品咂,让一生无惊无扰地过去。饱读诗书的人,也不见得比她活得通透。四季轮回,荣枯有序,这其间心能简静安然,便是悟了之人。
人总是患得患失,难有心满意足的时候,我们永远做不到毫无牵绊的出离,厌世却又恋世。这尘寰间可有满意之人?一生不闻悲声,所见皆是欢喜。
当所有的努力无益,便妥协成随遇而安。
我站在这条废弃了的林区公路边,凭空消失了的四工队——我的故园旧居。
许多悲伤来得突兀莫名,我们在吃饱穿暖的日子里悲痛欲绝。
我慢慢走回寨子。
大佛殿的山野上李子花是最多的,星星点点的素白,繁密地开了一树又一树。溪边桥头,村口地边,散着淡淡清苦的气息。其间夹杂着几树粉艳的桃花或海棠花。“桃红李白”四个字便是这一季大佛殿的速写。
柳枝泛青,桃杏绽红,光阴又老去了一段。
棉絮般的云彩在湛蓝的天空飘游,太阳温煦地照着青山,绿水,照着初长成的小小青梅。鸟儿轻盈地飞上天空,我听不到它向上振翅的喘息。
曾经大佛殿的贫瘠于我是疼痛,荒寂于我是酸楚,一直希望她能好起来。如今在党和政府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政策下,她终于从贫苦中走出来,另展新颜。家家户户都住上了大瓦房,村内道路硬化,铺了碎石甬道,沿路有太阳能路灯,还栽种了一排排海棠花。两条山溪穿寨而过,潺潺有声。Wifi 信号全覆盖,她不再是偏隅一角。2017年大佛殿被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大佛殿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我心里淡淡感伤,为一去不返的童年时光,却也欣慰,眼前的大佛殿一天天时尚起来,富足起来。一切都在往前走。
在不相干的人眼里,大佛殿依然是一个素朴的小山村,她的诗意与浪漫是我赋予她的。她的山林、草甸、花海、苍松、冷杉,还有沿着山溪汇聚成的一个个“龙潭”,在我眼中都无与伦比。
你的故乡或许是一个小镇,或许是一座喧闹的城市,或许是一个小山村,但她给你的感觉一定不是别人眼中的模样。因为是故乡,这座城,这个镇,这个小山村就有了温度,即便是路边一株缺失养分的植物,在你眼里都温暖可亲。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故乡。
如果你想从这篇文章中读到点什么?或者学到点什么?那么注定你要失望了。这许多个方块字堆砌起来的只是一大段关于我对故乡的感受,它千头万绪,深入肺腑,我却做不到把这一感受形象生动地表述出来。每一个人关于故乡都有不同的记忆,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我的欢悦说不出来,我的疼痛更难以出口。无论我写下多少文字,欢悦和疼痛仍在我心里。我站在回忆的路口,无法与他人共情。可是我又希望有人读到这篇文章,从我杂乱的叙述里认识到一个叫“大佛殿”的山寨,由这个山寨想到自己的出生地,我从哪里开始?将在哪里终结?
终究不能长久地留下来。吃过午饭,我们就离开大佛殿了。
一旦远离,我又要频频回首。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我放弃了许多所爱所恋,学会内心荒芜地活着。大佛殿只能留在心上。
和所有人的故乡一样,大佛殿不再是一个地名,她是我的精神皈依之地,她的山风,她的清溪,无一不是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