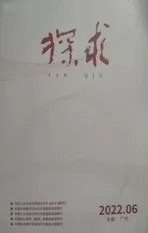金花诞的文化渊源与社会功能考察
2022-02-09蒋艳萍
□蒋艳萍
金花夫人,又称金花娘娘、惠福夫人,是广东和海外粤籍华侨华人普遍信仰的颇有特色的掌管生育的地域性神祇。金花夫人原属广州地方俗神,拜金花夫人逐渐由求子功能演变出可以保佑一切与生育相关事务的功能。金花夫人信仰具有极大的亲民性和务实性,在其麾下配祀有十二奶娘或十八奶娘、二十奶娘,分工细致,从投胎、怀胎、定男女、保胎直到分娩、养育,甚至吃喝、梳洗、行走、去病等,生育上面大大小小的事都能找到相应的奶娘祈福。在明清时期,广府地区民间普遍供祀金花夫人,香火很盛,逢其诞日(农历四月十七日)更会举行隆重的诞庆活动,四乡信徒必到庙中祭拜。金花庙亦会举行斋醮、演戏酬神等活动。至今广州仍保留“金花街”“惠福路”等与金花夫人信仰有关的街道命名,可见其影响之大。随着在广州民间的影响渐大,金花夫人信仰逐步扩展到广府文化辐射区域,如珠海、肇庆、河源、连州、吴川、香港、澳门等地。随着粤籍华侨华人的移动,金花夫人信仰也被带到了海外,迄今粤港澳各地、东南亚地区依然保存多处金花庙,供奉金花夫人和十二奶娘,或将其并祀于其他庙宇。近代还存在女子组织“金花会”,成为女性的自救自助会。
本文拟对金花夫人信仰的文化渊源及金花诞的社会功能予以考察,探讨金花夫人信仰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金花夫人信仰的文化渊源探寻
金花夫人的故事大约产生于宋元时期,最初的故事形态简洁,其身份为女巫形象,其信仰被官方视为陋习败俗,几番抵制,但民间对其信奉热度不减,地方士大夫于是对其故事不断添加儒家文化元素,使其从文化上、政治上归附于正统。道教也将金花夫人纳入信仰体系,将其与其他道教神灵并祀于宫观,并赋予其道教女仙的身份。几经起伏,金花夫人信仰终于获得从民间到庙堂的推重,在明清时期得到充分发展。
(一)儒家的规训纯化
目前最早的金花传说记载出自明代张诩于弘治十八年(1505)所撰的《南海杂咏》卷二《祠庙·金花小娘祠》诗序:“(金花小娘祠)在仙湖之西,相传郡有金氏女,少为巫,姿极丽,时人称为金花小娘。后殁于仙湖,数日尸不坏,且有异香,乡人神之,为立祠。”[1](P80)张诩《南海杂咏》为阅读《南海志》之后赋诗而成,据学者考证,张诩所读《南海志》应是元大德版本,故金花夫人传说应在《南海志》成书的大德八年(1304)之前就已在民间流传,才会引起地方士大夫关注,被载入地方志书[2]。诗序中关于金姓女子死后尸身不坏、体有异香的传说可能是金花夫人的最早记载,言说简略,对其具体职能也没做交代。对此美丽的传说,作为理学家的张诩的态度却是矛盾的,所写咏诗情景兼融,让人们沉浸于仙湖美景中追忆金花小娘的美丽容貌:“玉颜当日睹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无心还片片,晚风吹落万人家。”但序言按语形成奇异的反差,“予按金花虽有贞节显异,然失身巫觋,不能守人道之常,祠而祀之已非矣。其后巫觋假之以惑世,诬民滋甚。广之愚夫愚妇翕然从之,使在位有狄梁公者出焉,吾知是祠之在所去也必矣。他如北郭外崔府君庙讹为东岳行祠,其陋习败俗尤甚。予特举此例其余云尔。”[1](P80-81)序言中先道出金花小娘的美丽传说,接着以按语的形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以迂腐的道学姿态批评金花夫人失身巫觋,惑世愚民,后人立祠而祭祀之,实乃陋习败俗。张诩对金花小娘的矛盾态度,也正反映出金花夫人身份的复杂以及官方与民间对其不同的态度。广东人爱拜神,乡间供奉的神灵林林总总,令正统的封建士大夫十分不满,他们将没有获得官方认可的大小庙宇一概称为淫祠。金花夫人少时为巫却被立祠建庙,还被世人“翕然从之”,这在明代道学家看来就是“淫祠”,应予以规范,甚至取缔。明嘉靖初年(1521)广东提学魏校为推行儒家教化,以广州府为中心大规模捣毁淫祠,其中就包括金花夫人庙。其后,粤人奉金花神像于珠江南岸石鳌村(地近今海珠桥西边滨江西路一段),后来又在仙湖街原址复建起金花庙。然而此修复的金花庙乾隆年间又毁于内阁学士翁方纲之手,于是石鳌村金花庙便成为当时唯一的祭拜金花夫人之所。
虽屡遭官方打压,明代以来岭南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封建正统的教化运动并没有撼动广东乡民对金花夫人的崇拜。金花古庙后又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从重修碑记中可以看出,金花夫人的身份也逐渐被官方认可,并不断提纯,被赋予越来越显耀的位置。
清初梁佩兰《金花庙前新筑地基碑记》云:“按郡志,神为郡人金氏女,旧有灵应祠,在仙湖西,祈子往往有应。成化初,抚军陈公濂为之重建,称金花普主惠福夫人。张东所先生为之题诗,盖其由来古矣。今吾粤无问城市、乡落,在在有庙,祝祷者皆以嗣续为事,犹泰山之有碧霞元君。以粤女而为粤神,犹莆田之有英烈天妃,虽威灵所及,有远近大小之殊,其有功于人一也。”[3]709此则碑记将金花夫人提到和泰山碧霞元君、莆田天妃相提并论的地位,而且指出“吾粤之地”不管城市还是乡村,都“在在有庙”,可见当时信仰之盛。
清代冯成修《重建金花古庙碑记》中视金花夫人为“天南大母”:“岭南仙城,我粤一大都会也。去城里许,则曰珠海……兀峙于珠海畔者,则惠福夫人古庙也。夫人生而灵异,谈祸福,多奇中。常以育婴保赤为念,都人德之,没则祀焉。没而英灵较著,粤之获石麟、怀玉燕、沐神赐者,所在皆遍。即或梦冀熊羆,嗣迟兰茁,一再祷之,无不有祈立应也。岂南为生育之乡,造物特异之,以为天南大母欤?抑珠江之秀,独毓夫人,故明珠皆在其掌中欤?何昭报之不爽也!粤之人出入祝之,饮食祀之,扶老携幼,虔俎豆,无虚日。而于麦秋,夫人设帨佳辰,称祝尤为极盛。其迎牲赞币者,远近舣舟,指莫胜屈云。盖夫人以子子粤人,粤人以母母夫人者,数千百年于兹矣。”[4](P711)将金花夫人视为粤人的母亲神,可见其地位之尊。就这样,金花夫人在乡绅、官吏的共同合力改造下,一步步从出身巫觋的身份中解脱出来,变成粤人普遍信仰的母亲神,金花庙也从淫祠的尴尬处境走向正统的礼仪祠祭行列。
金花夫人的身份在儒家正统的规训下,逐步去其野蛮鄙陋之性,成为被万人仰慕的尊贵、端庄、贞洁的惠福夫人、天南大母。其“处女+天母”的身份也符合封建正统对诞育天下而不失赤子之身的创世母神的想象。
(二)道教的吸纳升华
除了儒家系统对金花夫人的规训改造,在道教系统,金花的巫女身份也得到了升华,被纳入到女仙的行列,甚至被视为道教最尊贵的女神——西王母之妹。
道教与民间信仰紧密联系,对巫觋文化也是宽容的,巫女与神女、仙女的身份转换也很常见。当儒家正统将金花信仰斥为鄙陋之习从而摧毁金花庙时,道教系统给予了其实际的容身之所,无处安身的金花像大多被安置在道教宫观,与其他道教神灵一起供人膜拜,直至今日,粤港澳乃至东南亚地区都可见金花夫人附祀于其他道教宫观的现象。
最早将金花夫人与仙联系在一起的记载,我们目前仍只能从明代张诩《南海杂咏》中寻找证据。《南海杂咏》卷五“仙湖”诗云:“仙湖之水长东流,仙湖之仙麻姑俦。湖仙本是西王妹,一谪尘寰几千岁。依神为觋不嫁人,笙歌长游玉洞春。一朝灵骨蜕湖水,披拂异香闻十里。玉颜花貌俨如生,怪底惊杀五羊城。湖傍特起金花庙,灵祝昭昭人不晓。只今湖上多白莲,白莲花开疑水仙。”诗序言:仙湖“在城中,因金花得名,今白莲池,其故址也。”“药洲”诗云:“洲上风吹百乐香,洲前流水一溪长。金花显迹平湖出,刘鋹归朝九曜荒。白雪黄芽非世药,填离取坎却真方。紫阳未出玄关闭,谁把参同扣魏阳。”诗序言:药洲“在城西。伪刘聚方士炼丹之地,今濂泉书院即其地也。”[1](P104)
从这两首诗及序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金花夫人在诗人笔下本为西王母的妹妹,是和麻姑一样的女仙,被谪人间托生为女巫,自然不会与人间男子结为夫妻,因其落水而蜕,被认为是湖仙或水仙,其实只是重返仙籍,故而体有异香,容貌如生。其显迹之地在药洲,因她而名为仙湖,这里虽为诗人的文学想象,但也包含着世人对金花夫人的美好想象,而且采用了六朝时期盛行的神女谪降人间的表达方式,也是民间流传的神女下凡故事原型在文人笔下的再一次复活,亦是民众集体无意识的表达。
之所以会被附会为西王母之妹,与广府人对西王母的职能想象有关。据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广州多有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两送子者,两催生者,两治痘疹者,凡六位。盖西王母弟子,若飞琼、董双成、萼绿华之流者也。相传西王母为人注寿注福注禄,诸弟子亦以保婴为事,故人民事之惟恐后。……是则开辟以来,有天地即有西王母,而道家以为西王母者,金母也。木公生之,金母成之。人类之所以不绝于天地间者,以有金母之成之也。金母者天下之大母,故曰王母。居于西,以成物为事,故曰西王母云。壁上多绘画保婴之事,名子孙堂,人民生子女者,多契神以为父母,西王母与六夫人像,悉以红纸书契名帖其下,其神某,则取其上一字以为契名,婚嫁日,乃遣巫以酒食除之。”[5](P214)西王母是道教最尊重的女神,能救助危难、传授兵法,西王母又被认为是金母,与木公共生天地,故金母为天下之大母。广府民间将西王母保婴促生方面的神力进行了进一步发挥,将西王母与六夫人奉为妇人生育、孩子成长的保护神。金花被附会为金母之妹妹,既然金母为天下之大母,其妹为“天南之大母”,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教系统吸纳金花夫人还体现在将其并祀于道教宫观,特别是在被儒家正统思想排斥在外、大量金花庙被当做淫祠摧毁之际,道教系统对其张开了怀抱,很多金花像都被安置并祀于道教宫观中,与其他道教神灵一起被信众们朝拜。其中最有名的是明代广州著名道观五仙观对金花夫人的收编并祀。罗燚英在《明清时期五仙道观与金花信仰揆析》一文中对此问题有深入研究。她认为,明清时期金花夫人附祀五仙观,既有信仰地理因素的作用,更有道教女仙信仰传统的考量。五仙观兼祀金花夫人,应在嘉靖初年至天启五年之间,或与嘉靖初广东提学魏校推行大规模捣毁淫祠的政策有关。五仙观收编民间祠神金花夫人,更进一步促使其由世俗性的女巫转变为宗教性的女仙[6]。
二、金花诞的主要社会功能
从地方志书和文人笔记中可以看出,明清时期,金花诞是广东地区民间颇为隆重的节日,四乡信徒必到庙中祭拜。金花庙亦会举行斋醮、演戏酬神等活动庆祝。金花诞也是广府女子走出家庭与好友聚会的日子,很多志同道合的女子在诞会时结为“金花会”,缔结深厚的友谊。
(一)祈福求子功能
民间传闻在金花庙求子非常灵验,金花诞日,一大早各乡村民接踵而来,争先恐后涌入庙中,善男信女们轮流跪拜,有祈求生男育女者,有祈求生育平安者,甚为虔诚。妇女们到金花庙除了祭拜主神金花夫人祈子保婴、家宅平安之外,往往还要按顺序在二十位奶娘(或十二奶娘)神前各插一炷香,周而复始,直至将手中的香全部插完,看最后一炷插在哪位奶娘面前。如果这最后一炷香插在手抱孩子的奶娘前面的神龛,便预兆得子,就要把红绳系在奶娘怀抱的童子身上,好让奶娘手里的婴孩投胎到自己腹中。如果最后一炷香面前的奶娘是空手的,也就是姑婆(即不婚嫁的女子),就无需再求,等来年再拜金花求子。庙堂中挂有大灯笼,四周悬挂着红白两色彩带或花朵,供求子者采摘。求男者摘白花,求女者摘红花。人们一边参拜一边祈祷,口中念叨:“祈子金华,多得白花,三年两朵,离离成果。”[5]215
番禺人洪瑞元(字景清,号瑶圃,乾隆三十年举人,官山东盐大使)在《赛金花庙神歌》一诗中记录了金花诞的盛况以及妇女拜金花的过程:“河南庙鼓何渊渊,黄梅雨过闻扣舷。潮乘瓜蔓舟并集,水边人影相延沿。入门香气散如雾,左右环侍皆婵娟。玉座煌煌俨冠帔,丹荔黄蕉纷几筵。阶前堂上舄交错,四体投地膜拜虔。巫擂花腔代神语,歆尔旨酒丰牲牷。报尔征兰协吉梦,花红花白随归船。……求嗣人人祷辄应,西京岁岁祀甘泉。燕啄王孙亦已尽,肯为一祷释其愆。神福粤人使震育,仙湖灵迹传当年。那禁流俗不祠祷,宜肃典礼明祀湮。不然男女纷杂沓,姜源简狄开其端。举国若狂竟何事,谁职造物生化权。为作此歌告守土,无使礼法胥沦旃。”[7](P418)诗中写到了金花诞时的热闹场景,也提到了拜金花的过程。首先交代了金花庙里面的陈设:神像穿着凤冠霞帔,庄严肃穆,面前几案上摆着时令水果。接着描述了信女们四体投地虔诚跪拜在神像之下,不断祈祷。担任神巫的人暂时成为金花夫人的化身,以花腔代神发言,接受各种祭品。然后以郑文公妾燕姞“吉梦征兰”诞下郑穆公[8](P369)的典故告知信女神灵已经收到祈愿,求子的心愿必将达成。
(二)娱神悦己功能
古时逢金花诞日,必然举行迎神赛会。清初梁佩兰《金花庙前新筑地基碑记》记载了每年四月金花夫人神诞时迎神赛会的盛况:“尔庙居河南滘口,北枕鹅潭,前临珠寺。每首夏神诞报赛者,烟花火爆,百戏骈集,歌舞之声,旬月未已。”[3](P708)每到金花诞的时候,百姓们争相庆祝,放着烟花爆竹,看着歌舞百戏表演,往往延续半个月而不停歇。
黄芝《粤小记》亦云:“四月十七日为神诞辰,画舫笙歌,祷赛称极盛云。”[9](P389)吴绮在《岭南风物记》中称,“金花夫人者,故女巫也,死而灵异,有目疾者祷之辄效。羊城特尊奉之,春时赛会,与天妃相埒”[10](P16),认为金花诞赛会的热闹程度可与妈祖诞相当,肯定了金花诞在当时信众中的份量。文人诗词中也有许多关于金花诞的描写,如清人叶廷勋《珠江竹枝词》(十二首录一)曰:“白雨黄梅四月天,金花神赛大江边。旗翻风信人归晚,几点渔灯滘口船。”史善长《珠江竹枝词》曰:“金花会起赛神忙,红疍烧猪醋浸姜。五色绣旗风荡漾,楼船沙罟尽新装。”[11](P153)
清代顺德诗人黎简《追和梁公普金花庙迎神歌》曰:“银榜临江照眼明,金花祠对广州城。城南日暖罗敷思,庙口垂杨无限情。”“袖中灯带拜神回,船尾杨花渡海来。捉得杨花裹莲子,稳抛蜜意索郎猜。”[11](P152)写女子们拜完神回来后,会扯下庙外的灯带装进衣袖带回,坐船的时候会抓一把杨花,裹着莲子。这里不像求子仪式,倒像是郎情妾意、两厢情悦的欢愉场景。说明迎神赛会的金花诞日和其他诞会一样,往往跳出娱神的窠臼,最终走向了娱人的目的,神圣的宗教庆典也充满了世俗化的人间喜乐。诞会当天,信男信女们坐着大船,往来于江面,金花庙里更是游人若织,摩肩擦踵,声声笙箫助兴,歌声响彻云霄。这幅热闹场景,与波罗诞的诞庆非常类似,民间信仰伴随着民间娱乐,参加诞会的人也不单单是求神求子的信女,而是演变成全民的狂欢节。
金花诞当天,妇女们除了为金花夫人祝寿献祭、祈祷自己早日得子、生产平安、家中孩子健康长大之外,还会以极高的热情参与各种诞会娱乐活动,毕竟金花诞会活动一年只有一次。学者赵世瑜在探讨明清时期妇女的宗教活动与闲暇生活的关系时认为,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是妇女满足外出进行娱乐性活动愿望的借口[12]。平日里良家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谨守闺门,足不出户。只有在岁时节日如春游、秋游或宗教节日如赛社、庙会、朝山进香等活动中,才能暂时抛下繁重的家务,结伴走出家门,到名胜、庙宇中游玩。金花诞自然也不例外,每年固定的这几日成为妇女们外出的少有的时刻,也是缓解平日枯燥重复生活的调剂品,还可与闺中好友相约叙旧。有钱人家的妇女们还会刻意精心打扮,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共赏雅乐,有诗云:“河南佳会竞繁华,扇影衣香鬓似鸦”[13](P192)、“金花诞会共 酬香,队 队娇鬟斗艳妆”[13](P193),正是最好的写照。
祭拜结束后,往往会有金花会的活动。金花会是由志同道合的女子们自愿结成的活动组织,“金花会举办的活动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神诞的意义和范围,但这也正是‘金花会’区别于‘金花诞’存在的意义,它依托生育女神的名义,为妇女们暂时提供了精神生活的栖息之地,在此时此景中,妇女们可以抛却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同等身份的人群进行娱乐与交流。可以说,金花夫人作为生育女神与妇女之间紧密的联系为金花会提供了合理性存在的理由,金花会以金花夫人为联结也加强了信仰关系的稳固,成为金花夫人信仰中一种重要的存在形式。”[14]
三、拜金花与金花会的影响
大多人认为拜金花的意义是为了求子保子平安,与女性生育保护有关。当代金花诞也大力挖掘金花夫人佑护生育的这个职能,以大力宣传优生优育。如广州黄埔长洲金花诞民俗文化活动,在祝礼仪式开展的前后,金花广场上都有特色文艺表演,演出节目注入优生优育宣传元素,展现被民间广泛认为是妇女和儿童的保护神——“送子娘娘”的风采。但是,对于终身不嫁娶的自梳女,拜金花的意义何在?金花会又称姐妹会,它的存在意义只是志同道合的闺蜜一起出游,互倾心事,一起拜神求子吗?是否还会有义结金兰、相互救助似的姐妹情谊?“金花夫人始终以‘生育神’的身份得到岭南地区百姓的信仰和供奉”这种说法是否要打个问号?本文认为金花诞的意义或许远不止妇女求生育平安这么简单。
金花会是由志同道合的女子们自愿结成的活动组织,除了满足妇女们休闲娱乐的功能之外,本人以为金花会作为特殊的妇女组织,也是近代广府地区妇女追求独立自主生活的表达。当我们将金花会与自梳女现象结合起来考察的时候,会发现拜金花往往可以超越育龄女子求子的局限,辐射到所有女性的精神信仰,也成为不婚嫁无子嗣女子寻求神灵庇佑的一种精神寄托。
自梳女是广府、珠三角地区特有的现象,清中叶至民国在广府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比较普遍。“自梳”是指旧时代姑娘扎辫,已婚妇女梳髻,“梳起”则是未婚姑娘梳髻以示终身不嫁。据乔玉红《明清岭南“自梳”与“不落家”风俗的再思考》一文整理,对自梳女现象的产生,学界充满争议,提出诸如宗教说、民俗说、贞节说、妥协说、经济说、文化策略说等多种解释[15]。
很多学者认为,自梳现象,反映出广府女子在较早时候就开始拥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和对包办婚姻的抵抗,从而酝酿出中国早期的女权主义思想。例如梁启超主编《清议报》转载了香港《中国日报》刊发的《男女平等之原理》一文,提到“不落家”①是对包办婚姻的抵抗。该文指出:“今居中国,男不识女,女不识男,互昧平生,强作婚姻,非其志也,迫于礼已。其或不顺,势必至男则休妻再娶,女则归宁不返。夫妇之道,不亦苦乎?压之愈甚者则激之愈高,藏之愈深者则窥之愈切。不平则鸣,不均则争。其势然也。”[16](P130)珠江三角洲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养蚕、缫丝工业地带,妇女是其中的主要劳动力,近代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机器缫丝厂的大量出现,极大增加了广东地区女性从业的机会,蚕丝业的发达为女子提供了自食其力的条件,女子可以不依靠男人和家庭解决生存问题,甚至可以凭借自己的工作赡养父母、照顾兄弟。很多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和姓名权的女子,为了摆脱成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大胆地做出终身不嫁做自梳女的抉择[17]。
也有研究者认为自梳现象并非是出于女子平权思想,也包含着一种无奈,徐靖捷通过对西樵自梳女的研究,认为“她们生活的时代是劳动力至上的时代,无论是种桑养蚕、缫丝织布、种田养鱼,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公社化之后,工分也是按人头算。所以,女儿留在家里,成为娘家重要的劳动力。在把她们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的家人之后,有很多婆婆晚年都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所谓‘家无自梳不富’,可是这种富裕是自梳女牺牲了自己为人妻、为人母的权利,牺牲了自己的幸福换来的”[18](P210)。
日本学者可儿弘明也认为金兰会的独身主义中包含的妇女解放的意识是有限的、微弱的。他在研究被贩卖到海外的中国妇女时指出,清末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出现金兰会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或是出于女子对分娩的恐惧,或是对封建社会秩序下的婚姻具有厌恶感。在当时渗透于民众之中的民间信仰潜意识里,未婚女子对结婚所带来的怀孕、分娩都存在着恐怖心理。血池地狱、胎神、血刃夫人、流霞等是够可怕的。但是,起主要作用的则是这一地区的女子有经济独立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兰会这种否定结婚的做法,在重男轻女的半封建社会里,破坏了原有制度的内部结构,可以说这是反叛妇德的萌芽。然而,其结局最终依旧是萌芽,只限于由结伙组织要求父母、社会对她们有所妥协,减轻名目繁多的妇德压迫。如此而已。例如,拒绝结婚,可以免受做妻妾的不幸。尽管其中凝聚着她们真心希望实现解放的意识,然而在金兰会的独身主义里,社会变革的意识和妇女解放的观念却相当微弱,因此难以将它视为近代妇女运动的先驱。”[19](P214)
这些自梳女们往往结成姐妹(金兰契),终身不嫁,除了租借附近房屋一起生活,或聚居在各村庄的姑娘住处之外,还有的合资建立“姑婆屋”一起居住,也有的住在斋堂里。自梳女在“梳起”的时候大多都要拜神,有的拜观音、有的拜天后、有的拜龙母、有的拜北帝,金花夫人作为女子的保护神也成为很多自梳女的精神支柱。笔者在广州番禺大岭古村的姑婆庙里即发现供奉有金花夫人神像。在广州黄埔长洲岛道光九年(1829)《重建金花古庙各家乐助碑记》[20](P21)的捐助名单中,亦发现有“花女曾桂香、曾悦好、曾金凤、曾瑞好、曾并仙、曾瑞珍……”连续18个未婚女子姓名,排在“信妇曾门黄氏、曾门梁氏……”等已婚女子之前。碑文中的“花女”与“信妇”分列,而且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收入,应该大概率指的是不愿意结婚的自梳女。由此可知,金花夫人信仰在自梳女中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清末民初,大批“梳起唔嫁”的顺德“妈姐”②流向广州、港澳或南洋打住家工。这些妈姐自小受到家务训练,心灵手巧,善烹饪,以刻苦耐劳著称,多独身(自梳女),是新马华人家庭最受欢迎的雇佣对象。华人妇女赴东南亚,绝大多数都是经由香港而去。据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可儿弘明教授统计,1920年,从香港出发的华人移民妇女中,除去与丈夫、亲属同行或去丈夫、亲属处探亲的,做妈姐的最多(2833人),做性工作者的其次(1198人),再次是裁缝(732人),做厨师的也不少(633人),其他如矿山和农业劳动者等则少些(366人),而这些“妈姐”的主体便是顺德县的金兰姐妹[19](P215)。据丘正欧教授《华侨问题研究》统计,1947年,妈姐占到新加坡妇女总人口的5.12%,在整个马来联合邦中也占到2.57%。[21](P163)人数之多,可以想见。再从顺德的300多个女归侨看,93.4%的人是做妈姐的,适成佐证[22]。而这些去往海外讨生活的女子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只有靠自己的自力更生和同族的互相扶助,才能渡过漫长的一生,这期间宗教信仰和金兰姐妹间的扶持也是其生存的重要精神支柱。例如新加坡金花庙的“金花互助会”就是海外姐妹们的救助会。
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花夫人信仰或许应该跳出“送子娘娘”的狭隘寄托。实际上,在数位奶娘中特意安排大姑婆和小姑婆两座不嫁娶的尊神,除了预示暂不能怀孕之外,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正是人们为奉行不嫁的女子们特意安置祭拜的尊神呢?这样的话,拜金花的活动对自梳女、不落家、一辈子不结婚生子的女子也同样是充满吸引力的。而金花诞后的金花会活动,不仅可以成为已婚姐妹的聚会和休闲活动,而且也可成为不婚成年女子共诉衷肠、相互扶持的精神交流的方式与途径。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来自民间信俗的金花夫人逐渐褪去女巫的鄙俗身份,不断被儒家正统规训纯化,成为粤人女子和孩子的“天南大母”保护神,也被道教收编为极为尊贵的道教女仙。逢其诞日,更是热闹非凡,成为民间颇为隆重的节庆,满足人们求子祈福、休闲娱乐、聚会欢宴、安身立命的各种需求。
[注释]
①所谓“不落家”,即女子结婚后仍长住娘家,只在重要节日或翁姑生日时在夫家住宿一两天.
②19世纪30年代,顺德丝绸业式微,当地一些本来以缫丝为业的自梳女为了维持生计,就到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香港、澳门等地当女佣,这些女佣称为“妈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