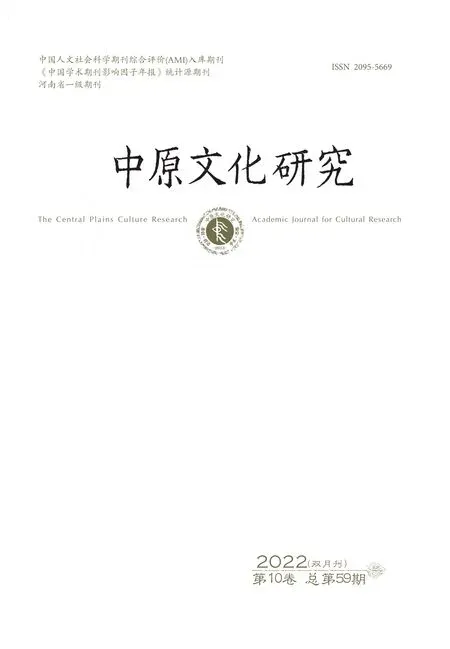夏代有无之争的背后:历史观古今之变的考察*
2022-02-08陈立柱
陈立柱
夏史有无问题,或者说存在与否、是否神话、是否为杜撰等问题,争论了百余年,不仅困扰着学术界,也对社会各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问题的研究陷于困顿,说明可能落入了某种理论误区。要走出困境,笔者认为厘清以下三个问题是关键:
第一,从西周到清代,近三千年来,中国没有人怀疑作为“三代”之首夏的历史存在,为什么?
第二,怀疑夏朝的历史性是从晚清开始的,并且始于外国学者,考古发掘尽管提供了大量关于夏时期的文物资料,甚至发现了具备王都规模的遗址,但直到今天怀疑夏朝曾经存在过的仍大有人在,尤其是一些国外学者甚至认为“殷商有一个关于夏人的神话”,“他们属于阴间和水”[1],夏就是这个阴间神话演绎的结果,或者夏是周人杜撰的①,为什么?
第三,不少学者提出,证明夏的存在关键在于出土夏时代的有关文字资料,即“字证”或“文字的自我证明”。此即所谓“确证”说②。字证或确证说体现了什么样的历史观或何以提出?
以上三个问题,涉及古代中国何以相信夏的历史存在,近人怀疑夏的历史性道理何在,以及证明夏之历史性的方式方法即历史问题用何种证据证明的问题。搞清楚这三个问题至少可以知道学者们对于夏朝认识产生分歧的根源何在,进而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从而揭开笼罩在夏史研究上的层层迷雾。本文拟通过对夏史研究来龙去脉的考察与存在问题的分析,主要对上面第二个问题即晚清以降学人何以怀疑夏代历史性的问题追根溯源,进而对第三个问题即“确证”论的逻辑前提是否可靠进行讨论。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夏史研究:古今之变的考察
夏史讨论,目前所知西周前期已经开始,当时周公等人为了训诫成王进行历史比较,主要是夏、商、周之间的对照,通过三个朝代人事兴亡与天命的关系,指出人谋重于天命,历史经验更值得重视。这是最早把夏作为比商更早的一个朝代提出来加以讨论的,记载于《尚书·周书》“八诰”中。《尚书》中还有《虞夏书》部分,也是早期传承下来的文献,只是经过很多史官转述,文字面貌可能已不是最初的样子了。《史记·夏本纪》就是根据这些早期传流下来的文献,汇总编写而成,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也相信夏代的历史性存在,夏、商、周作为“三代”也成为中国人划分历史时代的界标,三代之前是“大道之行也”的天下“大同”之时,三代开始“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2]。春秋战国以来经常有所谓“五帝、三王”之说,也是将其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这种观念秦汉以后流行两千多年,或发挥,或传承,一直到清代。
晚清以降形势大变,大家对夏代前后历史的看法在各种各样的古史著述中开始以“传说”“传疑”时期即不完全可信之时代的面貌呈现出来。1904年出版的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明确提出“太古三代”为“传疑时期”,“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故谓之传疑期”。又说“言中国信史者,必自炎黄之际始”。夏曾佑的意思是,“传疑时期”因为实事、寓言混而不分,作为研究者对此可以多闻阙疑,择善而从,但自黄帝之后的历史存在则是没有问题的。是以,关于黄帝时期他罗列了很多史事③。之前发表的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已就古史可信与否的问题提出:“所谓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者。其确实与否,万难信也。故中国史若起笔於夏禹,最为征信。”[3]1904年前后,严复在读《法意》的按语中言:“以春秋战国人心风俗之程度而推之,向所谓三代,向所谓唐虞,只儒者百家其意界中之制造物而已,又乌足以为事实乎?”[4]至于康有为认为六经是孔子所作等说法,则是为了政治变革的需要,更是影响很大。可以看出20世纪之初,如何看待古史的可信问题,或何处是信史的开始,从而关于信史、真史、传疑、证明等问题都已提出来,而且怀疑的程度不断加深,虽然不如20世纪20年代以后那么明确,但唐虞、三代是否是事实的问题已被明确提出来,说明历史观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随后的新文化运动、“古史辨”潮流把这一趋势进一步向前推动,顾颉刚虽然不否认夏的历史性,但是认为禹乃天神,以后变为人王,考古发掘见到的才是“真实的证据”[5]。其他如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则提出“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展转演述而成”[6],陈梦家也有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之说④,如此等等。从此,夏的历史性存在开始成为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大家逐渐接受了李玄伯的说法,这就是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7],即通过考古发现夏代的文物来证明其历史性存在,包括钱穆这些较传统的学者都接受了这样的认识⑤。这个思路促成徐中舒撰写《再论小屯与仰韶》⑥,认为仰韶文化即夏文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黑陶文化是夏文化,努力从考古学上证明夏的存在,但却遭到另一些人的批评[8]。
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进行考古调查研究,在洛阳地区发现二里头遗址,从此揭开了以考古学方法进行夏史研究的新篇章。最初,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商都遗迹[9]。持续不断的发掘获得了大量的文物遗存,尤其是二里岗文化之前的遗存,是以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的意见渐成主流,特别是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一些学者都认为夏的历史性因为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而得以证实⑦。与中国学者逐渐认可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不同,国外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并不以为然,这在1990年于洛杉矶召开的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充分体现出来。会上西方学者大都认为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不能等同,夏的历史存在还需要发现夏代文字才能证明,美国学者艾兰甚至认为夏只是一个神话。会议讨论环节中国学者的据理力争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民族主义的表现⑧。1999年,西方汉学家合作编写出版了《中国上古史》一书,其中第四章的题目为“商:中国第一个历史王朝”,显示西方主流学界并不认可夏为商之前的历史朝代。夏的问题只在华裔学者张光直所写的“历史时期前夜的中国”一章中有一些简短的讨论,不过一千余字⑨。大约同时,郑杰祥整理选编《夏文化论集》,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讨论夏文化的各种情况,归类为十种意见,其中多数为考古学者对二里头遗址分期的研究,即通过考古也结合文献提出对夏文化的新认识⑩。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夏的历史性是可以相信的,不过需要考古学提供进一步的证明。其中一部分学者甚至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已经可以证明夏的历史存在,因此开始将二里头文化等同于夏文化。一些日本学者的认识也开始与中国学者的思考相接近,如冈村秀典就撰写有《夏王朝》一书,明确用“夏王朝”来指称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⑪。唯欧美大部分学者依然坚持二里头文化不能等同于夏文化⑫。
进入21世纪,国内考古学界对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与夏史关系的认知有了一些新变化,主要是一部分学者质疑传统的“夏王朝可知论”,提倡“有条件的不可知论”。这部分学者主要是“接受20世纪上半叶以‘古史辨’为核心的反思传统,以及海外学界相对保守严谨的态度和观点,‘超脱’出原有的话语系统”[10]32。从这些措辞可以看出他们认可古史辨派的主要看法,并视国外一些否认夏史存在的学者意见为保守谨慎的意见。持这些意见的主要是一部分中青年学者,他们坚持认为必须有夏代文字的考古发现才足以证明夏史存在,否则不能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假说不等于实证。另有考古学者也引述国外学者的意见,提出甲骨文“未见有关夏的只言片语”,从而相信外国学者提出的夏有周人杜撰之嫌疑的意见[11]。对于此,之前已有学者指出,甲骨文证实商代为信史,但甲骨文字是占卜用的,夏人未必也用龟甲占卜,而夏代的竹木简是难以保存至今的⑬。如李学勤早就指出:“我们知道商代是有竹木简的,但简的实物迄今未能发现。夏代的情形也许正是这样,尽管有文字,却没有多少能传留至今。我们不能把希望单纯寄托在文字的发现上。”[12]2008年在郑州召开的早期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李伯谦总结几代学者对夏文化研究的成果,提出当前的夏文化研究在六个方面较为薄弱,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是:“无文字发现时能否用考古学研究夏文化?”[13]李先生的提议讨论者少,大部分学者的期待还是通过考古发现来实现新的突破。朱凤瀚最近在《夏文化考古学探索六十年的启示》中总结说:“考古学已成为最终解决若干笼罩于夏史上层层疑团的唯一手段。”[14]这样的思路又推动了近些年关于龙山文化向商文化过渡阶段的发掘与研究,仅是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及其前后时期考古与历史的研究论著,我们见到的就不下数百篇(部)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集中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一时段的考古研究,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是从考古上对文献记载的夏代及其之前一段历史的集中研讨。
考古学促进夏史、夏文化研究不断深入,也带来总结与反思的不断增多,笔者所见最近30年来有关反思性的文献比较重要的就有数十篇。对于能否发现夏人的文字问题,不少人已经表示怀疑,一部分学者开始从方法上总结有关研究的得与失。较早的时候邹衡提出:“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15]他所说的方法就是从考古遗存中去辨认出哪些属于夏文化,哪些属于商文化,他自己的研究是文献与考古相结合,涉及确定夏文化范围(包括外围)、夏商分界等⑮。另一些学者则大力提倡要与国际接轨,学习外国先进的研究方法。其他学者从各个视角进行反思的还有很多。继承并发展邹衡观点的孙庆伟,在多次反思过去的相关研究后提出“在历史语境”中研究夏,努力从考古学上解决夏的存在问题,甚至批评“刻意追求文字一类证据,实际上是对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不了解和不信任”⑯。其著作《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不久前问世,自言不怕被人讥为“证经补史”之作,但确实引起了进一步的讨论。这个讨论还带来很多非考古甚至非历史专业人士的参与,他们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其言论充斥于各种媒体。这种现象提示人们,更深入的讨论也成为学术界与社会其他各界的共同期盼。
二、晚清以降相关研究存在诸争议之分析
检视以上夏史有无研究的种种观点,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可以提出来深入思考:
第一,几乎所有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特别是一些反思性研究论述,大都说到近世以来的研究情况,不管是将有关研究分为几个阶段讨论,还是综合各方面进行分类评述,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古人对夏史的态度,个别注意到此问题的学人也没有深入分析,大多数人的反思都是从“古史辨”运动开始的,认为“夏朝的存在被怀疑,是疑古思潮的产物”⑰,也就是说缺乏古今对比的深入研究。而不进行古今对比,只拿近代以来接受了的西方历史观念并在这种历史观之内继续讨论夏之存在与否,这种反思的意义到底有多少?一些人解说“信史”[16]概念,参考《辞源》《现代汉语词典》之类的辞书,也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这些都让人想起学术界很多人使用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方式反对西方中心主义⑱,结果是越反对越迷糊。不能贯通古今中西,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历史已一而再地证明了这一点。无视古人的意见无异于全盘接受西方的历史观,而在没有任何比较反省中西历史观的情况下反思夏史研究,与过去批判的“言必称希腊”又有什么区别?不能从外界影响中解脱出来,人就不可能理解内在精神的根本意义,不能认识真正的中国文化精神,我们就只能固着于深刻习染的西方近代思想之中。
不注意夏史研究的古今之变,与讨论者很少关注晚清社会思潮的变化也相关,即忽视了夏史真实与否的讨论并不是中国学者最先开始的,西方学者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已经提出,比如法国学者沙畹1895年出版他所翻译的《史记》第一卷,在绪论中已经指出尧、舜、禹等是后人伪造的。1905年在中国出版的《迈尔通史》,其中论及中国古书所讲上古史事多不可相信,认为只有公元前七八世纪以来中国才渐有信史。1908年夏德在美国出版《中国古代史》,其书怀疑中国古史,认为周以前的古史都属于半神话,不可凭信⑲。夏德是胡适在美国学习中国史方面的老师,夏德的书无疑是胡适学习的教材。胡适1917年回国到北大教书,20世纪20年代才有其弟子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辨运动,其间要说没有联系那是不可能的。还有,1907年前后日本学者的尧、舜、禹抹杀论已经很有声势,无疑也是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学理上,西方史学强调通过文本的年代证明其记载历史的真实与否,以及“以物证真”历史的取向,必然会对中国上古传承而来的历史旧事提出怀疑与否认,这是最关键的。而古人没有怀疑夏及其以前的“五帝”历史,是因为这是按照中国自己的历史观来看的。懂得这些才能真正明白何以晚清中国才会出现对上古史的怀疑,这是因为接受了西方传来的历史观,夏史研究的古今之变隐含着中西史观之异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找到夏史有无之争的症结所在。
第二,大部分相信夏史存在没有问题的学者,很多都回避西方以及部分中国学者提出的“字证”即确证说,以至于被认为是很不严肃的学术讨论。还有一些人如刘绪等,相信夏的历史存在不会有问题,也在此基础上讨论夏文化问题,但同时又认可西方学者提出的字证说也有道理:
应该承认,这种认识有其合理之处。因缺少当时自证属性的文字材料,即使证据再多,也不能得出百分之百准确的结论。但得不出百分之百准确的结论,并不等于所有证据都不可靠,连百分之一可能都没有,因而彻底否定夏与早商王朝的存在,这显然有点极端,也是不合适的。⑳
这种认识比较具有代表性。但是,这种认识忽视了近代史学“历史客观性”之基本要求也是很明显的。西方近代史学认为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也是一个整体,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伪)的,历史之真是不可以用百分比来衡量与断定的。与此相关的还有“近真”说,即经过人们不断探索与研究会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仅就一百多年来夏史研究的变化来看就不能自圆其说。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形成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的主流意见,但是21世纪以来一部分中青年学者又回到了古史辨时代的思考,并且争议更趋激烈,怎么能说是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夏代既不可见,又如何证明相关研究是越来越接近真实呢?史学上类似的争议性研究数千年中反复其说的情况甚多见,都是对于近真说的有力驳斥。
第三,一些学者提出文字并非确认夏朝历史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又没有针对“字证说”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分析与辩驳,只是认为“字证”之要求“混淆了历史和历史叙述,贬低了历史文献的应有价值,也失去了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应有尊重”,“以不知为不有”[17],即没有从道理上说清楚何以字证说并非必要条件。古史辨派认为古史大都为神话传说的观念经过数十年的渲染早已深入人心。因此,古史记载要获得真正的尊重是需要重新确立其可信性地位的。可惜这个工作至今没有深入讨论,尽管有李学勤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18]。
此外,字证说者认为早期历史“‘真相’是无从验证的,所以‘正确’与‘错误’之类的断语并不合适”㉑。既然知道真相无从验证,可是面对夏的有无问题又提出“文字的自我证明”之“确证”“实证”要求,也让人感到其内在逻辑有问题,即真相不可知,但看到当时的文字记录就可以自我证明,这不就是“眼见为实”历史观的翻版吗?其研究结果走向“不可知论”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四,如何看待“科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问题也是需要反思的。以二里头遗址碳十四测年为例:最早的测算是在1974年,夏鼐指出当时的测年限于条件而不准确;接着1980年—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碳十四实验室进行测年,推测其年代在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前后延续三四百年,正在文献记载之夏时代的范围内,成为二里头遗址文化为夏文化的有力证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又用新的材料与方法测年,新的数据改为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20年,也在夏的年代框架内;1999年—2000年学者们利用多种数据再测年,确定其二期在公元前1680年前后,又根据每期(考古遗存分期)50年向上推,一期年代上限就到了公元前1750年,是拟合数据,更可信㉒。四次碳十四测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因为多种因素以及测算方法的不同,数据不断地在改变,几乎可以肯定,过一段时间随着新的测试标准的提出,再测试还会有不同。这也印证了爱因斯坦的名言:“我们的理论决定了观测的结果。”因为测年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拟合数据就是被当时学者认为最为可取的一种研究方式。科学测试二里头遗址年代给我们的启示已表明它的相对性,即科学数据的获得也会受外在条件的影响,不是绝对不变的。然而,“字证”说者常以“科学”态度批评和否认一切,如认为夏朝“在传世文献上当然是存在的,但见仁见智……在科学理性观念进入中国之前,这些是毋庸置疑的”[19]。其他一些否认夏朝历史性存在的学者以“科学”名义言说的也不在少数㉓。当今世界科学哲学一再强调相对论、历史主义、“范式”转移、不确定性、模糊性,甚者如科学史家费耶阿本德都提出了“怎么都行”的口号,说明正宗的自然科学研究思维都走上了相对性与历史主义的道路,知识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即由从前认为的具有确定性之“真知识”转变为不确定的“假说”或“主体间性”论,等等。而人文学科特别是关于历史文化的研究还在“唯科学主义”㉔的道路上阔步高谈,与今天世界的思想潮流相差何其之远,给人以返回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西方的感觉。在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开始承认传统中国史学有其独特之处的时候,国内一些学者却在基本方面否认或忽视,如同当年梁启超为了引介“新史学”而过度批评传统认为“中国无史”一样㉕。“科学曾经是一些人手中的棍子”[20],希望它今天只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而已。
三、何以争论不休:两种史学观的混同与矛盾
与以上相类似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仅就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在夏史、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或夏代有无问题的研究中,不少人陷入了自相矛盾或理论不能自洽的认知当中。那么,这些问题甚或自相矛盾为什么会产生?学者自己何以不自知?这个问题当然十分复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近世以来中西史学观念的混同,即不少研究所依托的史学观念时而在传统中国思想的认知中,更多的时候则是建立在学习外来的西方历史观的基础上,而这两种历史观原本存在巨大的差异,很多人并未觉察到这一点,因而造成了混乱与矛盾。如认可“证经补史”又提倡“用考古学重建古史”的学人,稍加分析就可以知道是“脚踏两只船”。因为“证经补史”乃中国古代历史观,它的前提是认为历史即是已经发生的人事活动,即已发生就是不可改变的,因而也是命定的,或者有记述,或者没有,后来的研究者可以补充、补正,甚至重写,王国维谓之“补正”,所以会有《二十五史补编》《中国通史》以及各种断代史、专门史、考证等继作。历史可以补正、重写,但不可以重建,已经发生就是确定的了,可以不断有新资料的发现与新认识的出现,但不存在什么重建问题。这是中国传统的历史观。而“用考古重建古史”则是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产物,实证主义认为有一个外在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Ⅰ),还有一个史家研究获得的主观认知(历史Ⅱ),两者符合即是历史真相的揭示。这种史学观念近世传入中国,傅斯年等人是强有力的鼓吹者,他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倡“动手动脚找东西”,就是不相信古文献记载,要按照西方重视的方法,搜集文物、档案与语言资料来重建古史,虽然他本人研究古史的方式还很传统。显然,“考古学重建古史”与“证经补史”是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两者都认可无疑即“脚踏两只船”。可是,人们的主观认知即历史Ⅱ与设定的历史Ⅰ即客观存在(于某个地方)的历史如何相对证、相符合呢?这就是实证主义史学观存在的问题,它遭到后现代史学猛烈攻击的关键也在这里。
另一些完全按照近世学来的西方历史认知方式来看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与夏史问题的人,必然提出文字的自我证明之要求。因为古希腊到近代西方的基本观念就是存在即被感知,不能感知到的就是不存在的,英国学者贝克莱的名言“任何物体,只要不被感知,就是不存在的”[21]是最简明的概括。希腊哲学独尊视觉,所谓“idea”和“theory”皆源自“看”。受这种大背景影响,希腊人只写当时发生的事即当代史,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记载没有人看见过它是如何发生的,因而是不能证实的,当然就是不真实的,不能相信的。德国史家兰克倡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书写历史”,也是强调需要当世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即通过所谓真实的资料达到对历史真相的揭示。这就是近代史家把古希腊史家强调的“目击者的证词”转换为“以物证真”,从而可以讨论过去了的历史,改变了希腊人只写当代史的情况。这即是近代西方史家何以提倡要用碑铭与出土资料研究上古历史的缘由。在他们看来,铭文与出土物才是古人留下的,是真实的,因而谓之“第一手资料”或“原始资料”,而传世文献只有“原物”才可以相信,其他用后世物质手段写下的文字难以为据,不能证明历史的真实。是以能够呈现在当前即被感知到的如正在发生的事、档案文献、出土文物、碑铭资料等,才可以证真。这就是希腊直至近代西方基本的历史真实观,它以柏拉图等人“在场”的或“看”逻辑为支撑点。坚持用考古发现夏代文字来证明夏之历史性者,坚持的就是这个逻辑。一般人受到这一思维逻辑的影响,经常会有“夏代到底存在不存在?”的疑问。其实比较恰当的提问应该是“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夏朝?”前一个提问即以“存在就是被感觉”为前提。
至于相信夏的历史性没有问题,又认为西方学者说的也有道理,即需要进一步加以证实,明显是自己基本的历史观混乱或不能自洽造成的。
可以看出,基于不同的历史观产生的历史认知方式与指向是不同的,这就需要从历史学研究的实际看哪一种历史观是更可取的,值得坚持的。史学研究工作者都知道,史学研究中不是什么揭示真相的研究才是可以相信的,而是做得比较好的才是会被取信的。所谓比较好的,就是搜罗的资料比较而言更丰富,史料的考证更严谨,得出的结论不仅与史料所示相一致,而且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表述更贴切,也更能自圆其说。几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又出现了比较而言更好的论述,人们又会认同新的观点,或以之为新权威。所以“考信”是为了更好地叙述过去的历史,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与西方把追求历史真相作为研究史学的目的,即认为历史是探究,由探究而获得的知识㉖根本不同。史学研究的实际告诉我们,没有什么真相可以揭示或对证,只有史料与史观可以进行勘覆与批判。所谓历史事实,即是在史料基础上推度出的一种最大之可能性而已。所以历史的可信性是动态的与择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即是历史学研究的实际,也是中国古人建立的取其可以信而信之的“考信”史观的基础[22]。置中国这些从历史学研究实际总结出来的历史观念而不顾,径直以西方某些预设的历史观为真理,这样做显然不可取。即便是西方,对于传统史学存在的问题之反思也没有停止过。20世纪早期,法国学者马克·布洛克等人已认识到历史知识没有可能成为一成不变的(真)知识,提出史学是关于人在时间过程中的科学[23],这和中国古人强调历史变易的观念,已经有了相通的方面。与布洛克大体同时期的美国学者比尔德批评追求历史真相的旧史学,认为那是一个不可实现的“高贵的梦想”㉗。之后,法国学者保罗·韦纳、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荷兰学者安克施密特等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者,进一步指出史学本质上乃叙述过去发生的“故事”之学或叙事学㉘。这些与司马迁提倡的史学乃“述故事,整齐其世传”[24]也有相近之处,虽然还不完全一样。最近美国学者林·亨特正式提出“暂时的真相”,认为历史研究并非追求一成不变的真相[25],也是根据历史学研究的实际得出的结论,已经趋近传统中国史学精神,虽然表述上还是西方的特点。而夏之存在与否或是否得到实证、确证的问题,明显是追求绝对真相之西方过时了的史学观念才有的问题,也是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持续学习西方,长期接受西方近代学科式教育的结果,并非古代以来就是如此,差不多在20 世纪20年代才确立下来[26],以后形成共识。大家信之既久,自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是古人考信、取信史观让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以至于与西方的史学求真观念混为一谈。可以说史学求真是向西方学来的,直到今天还很少有人进行认真的反思。
简单地说,求真史学的基本逻辑是:真的才是可以相信的,信史即真史首先必须建立在真材料的基础之上;而真材料要么被写者亲眼看到,要么是当时留下的,需要进行批判性证明;夏的可信性要得到确证就需要找到夏人自我说明的文字即可以看到的“字证”。是以,“传说”“故事”与“史实”不同,所谓史实就是被确证了的真相,而传说、故事则是神话学的或文学性的。这种求真史观说白了就是“眼见为实”,眼睛看不到的就不是真的,接续的正是古希腊史家反复强调的“目击者的证词”。它在西方持续了两千多年,20世纪中后期开始遭到猛烈抨击,形成一些人所谓的后现代潮流。仅以法国学者的研究为例,如历史学家保罗·韦纳说:“在历史学家,在这些地球之子中间,存在着一种天真的笨拙的迷恋真相的态度;他们的座右铭是‘唯实论第一’。”[27]文化学者罗兰·巴特说:“历史话语的唯实论是文化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是改头换面的‘真实崇拜。’”[28]解构主义的代表德里达说:“一句话,真实性,只是文本性的假设。仅此而已。”㉙他们的话可以理解为求真史学是西方20世纪以前思想的产物,是古希腊以来追求真理(相)思想在史学上的表现,其所依据的前提是有问题的柏拉图哲学。不过,在世界其他地方,或者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不大的地方,追求历史真相依然是史学研究遵从的基本原则,如同百年以来的我们一样。伊格尔斯曾经指出:兰克式的职业史学先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以及明治早期的日本被接受,再晚一点在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去殖民化以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被逐渐接受。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是在帝国主义扩张时代西方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的㉚。这种情况在当时被视为追求真理以拯救民族、国家。是以,很多人不避艰难奔赴国外学习坚船利炮技术,后来则是学习其政治制度与文化,以至于对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加以崇拜。
学习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成就自己而不是学习本身,永远做学生。中国史家为什么在学会了西方的史学研究方式很长时间后却未能区分中国史学的考信与西方求真之不同呢?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先从中国方面讲,中国较长时期救亡图存的任务使得学习西方一直不断地进行着,结果中国学术思考完全从“四部之学”变为建立在分科基础上的“七科之学”[29],中国学术思考方式被西方化了。中国向西方学习还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我们学科化的学习途径很多是通过日本的再转化,也就是说主要学科思想和术语是日本人使用与理解的汉字对译之西方名词,不是中国汉字与西方思想的直接对接。这个先日本化再中国化的学习截断或间隔了现代中国学术思考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如经邦济国之“经济”,变成国民生产经营与商贸之“经济”,从客人角度认真看问题之“客观”,变成曾经发生之历史实在之“客观”“客体”,如此等等。反而是严复翻译西方著作使用的一些语词,如“ 群学”(sociology)、“计学”(economics)等后来不用了。二是趋新过于承旧的风潮使得比较反思中西之别只在一些表面认知上有成果,缺少深入内在精神的研究,甚至批评否认传统史学一些主要方面而不是在中国思想的基础上吸收有用的外来思想,如前言梁启超早年对中国传统史学基本方面的否认㉛,傅斯年对中国家庭与思想在“根子”上腐坏之批评㉜等。三是相似即同一(或同源)之简单的逻辑主义运思进一步掩盖了中西之异,这从胡适当年把古人的“求实”“求是”和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相混同,到近年古史与考古学等研究都有很多具体表现[30]。这几个方面归为一点就是,当初的学习不是用中国本有的思想直接去“格义”所学对象外国思想文化,如同当年翻译佛教经典一样。“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学习方式被颠覆了,变成了“反向格义”,中国仅仅成为西方方法解释的对象而不是自我的主体[31]。
再从学习对象的西方学术思想文化来看,这是一个以逻辑主义运思为主导的认知文化,与中国以历史主义为主导的认知文化差异极大。逻辑主义思考方式中的学术研究需要先在哲学或形而上学上有突破,其他学科才会有跟进。而中国人学会了这个方式的学术思考就开始“反向格义”地研究中国,即传统中国历史文化开始以西方学术思想认可的方式呈现出来,除非在哲学上有重大突破,否则如此方式的史学研究一时间不会有根本性变革。也就是说,新史学研究自身没有多少可以从根本上自我反省的能力,除非将中西思想文化完全融会贯通了,如梁启超晚年,但融通中西又是何其之难。事实上新方式的思考还限制了人们对传统思想的接通、反省与再创造,如章太炎关于经史为“客观之学”[32];钱穆关于中国学术“主通”,西方学术“主专”[33];陈寅恪关于“通性之真实”[34],“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㉝;钱锺书“打通文史”“史蕴诗心”[35]等站在传统文化视角上的反思,也是古今中外的打通,多被掩蔽、忽视而未能成为主流。简单地说,科学主义思潮引领一百多年来中国史学思考之潮流,而唯科学主义取向掩蔽了中国史学本来之面目,从而混淆了中国传统之“信史”与现今史学“追求真相”之区别,形成马克垚所指出的“我们还只有一种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是来源于西方的,我们亚、非、拉国家,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可是并没有发展出来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36]21的局面。马先生还说:“西方的理论有其真理性,可是只是从西方出发来看世界的。所以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有不少就是我们所一再想超越的欧洲中心论,可是因为我们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理论,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实现不了这个超越。”[36]21
所谓没有自己的历史理论,就是说没有在近世以来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出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阐释历史演进变化之方式方法,如同西方的一样。自身传统被否认被忘却被遮蔽,新的具有自己特点的史学观念未能成形,只能把接受来的西方理论视为当然。
结 语
传统中国史学十分发达,史学遗产丰富多样,其对历史考据与叙述的方式方法自有完整的体系,简单地说就是众多学者一再指出的“不离事而言理”的传统,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史学观念,史道贯通的精神㉞。此与西方历史与理论分而为二的情况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巨大的史学宝库,终将会为中国史学新生带来新机遇。把西方思想与史学研究方式学好学透,或者是为了更好地融通,以成就其新的伟大。兼容并蓄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深入学习西方再融会贯通,从而在古今中外大融合中完成自己的使命。在西方,古希腊以来的历史观及其所依托的真理观20世纪以来发生了深刻危机,尤其是20世纪后期以来学界对之提出了猛烈的批判与变革要求,说明“求真”史学正在失去其现实与学理基础。在中国,古今中西史学交汇融合也有一百多年了,也到了需要系统反思与全面清理的时候了。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大家全都沉浸在“史学求真”的理念中甚至认为史学求真“天经地义”,不断追问这个文献真否、那个故事是否为神话㉟的背景下,传统史学精神的发掘与发扬是一件艰难困苦的工作。要充分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难度,迎难而上才有可能真正开拓中国史学自己的话语权。
注释
①参见杜朴著,张良仁译:《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探索》,收入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 期。②许宏的相关论述较多,近期的研究可参考《“夏”遗存认知推定的学史综理》,《南方文物》2021年第5 期。③参见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年初版,1933年以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12 页。④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25年第20 期,其节录内容以《夏世即商世说》为题发表于《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332 页。⑤如钱穆就认为:“中国古代史,直到夏王朝之存在,现在尚无地下发现的直接史料可资证明,但我们不妨相信古代确有一个夏王朝。”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7页;由该书“弁言”知,其写于抗日战争时期。⑥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原载《安阳发掘报告》1931年第3 期,后收入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顾颉刚也有类似的看法,参见顾颉刚:《春秋战国史讲义》第一编,《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0 页。⑦这方面,当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北大考古学家邹衡的意见最具代表性,参见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原载《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 期,后收入多种论著之中,本文参考的是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所收文本。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⑧关于这次会议内容国内学者的介绍甚多见,英文内容介绍可参见闫敏:《洛杉矶“夏文化国际研讨会”英文本论文译述》,《人文杂志》1991年第4 期。⑨LOEWE M,SHAUGUGHNESSY 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232,71-73.⑩参见郑杰祥:《夏文化论集》“前言”,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⑪参见冈村秀典:《夏王朝:王权诞生の考古学》,东京讲谈社2003年版;许宏《推荐序》,载宫本一夫著,吴菲译:《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实则,宫本一夫书名、书中第十章内容也都体现出日本学者对于夏史的态度。这是21世纪初的情况。据介绍,日本的通史、教科书大部分还是从殷王朝讲起,但是在学术界,个别学者如和田清很早就相信历史上有夏王朝了,从考古学上承认夏王朝的实际存在,比较早的还有1999年出版的林巳奈夫《中国文明的源流》一书,参见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9 页。⑫如德国学者罗曼·赫尔佐克说:“总的说来,夏朝被认为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的杜撰,它开始的时间,可能比那些史家所说的几乎要晚两千年。”参见赫尔佐克著,赵蓉恒译:《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 页;又,杜朴著,张良仁译《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探索》(收入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也有相近的意见,都比较具有代表性。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学者说王国维用甲骨文资料“确证”了商代为信史即真史。这个说法不符合王国维的本义,王将文献记载与甲骨文资料等相结合讨论商代的先公先王,指出文献记载可信,他自己认为出土文字资料只是“补正”文献记载,即通常所说的“证经补史”,没有说是“确证”商代为信史,考古学者所谓的“确证”或“实证”概念乃是建立于追求历史真相之史观基础上对于王之“补正”说的重新立言,参见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 页。⑭结合考古学对于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研究的论著目录,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许宏、袁靖主编《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附录”都有收录,总数超过一千余篇(部)。⑮邹衡先后有《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再续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出版。⑯参见孙庆伟:《前言: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16 页。其他反思夏或二里头文化研究方法的论著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介绍。⑰相近说法较常见,参见杜勇:《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夏朝的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 期;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 页。⑱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讨论西方中心主义,在国际国内都常见,比较深入的分析可参考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0,428-448 页;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年第3 期;陈立柱:《西方中心主义的初步反省》,《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 期。⑲以上情况详情可参考李长银:《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 期。⑳刘绪:《夏文化探讨的现状与任务》,《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 期。类似的情况很多,如沈长云先生言:“我们认为,夏确实是传说中的朝代,但并非人们杜撰的朝代,有关夏的传说在相当程度上应视为历史事实。”参见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㉑参见许宏:《“夏王朝”考古:学术史·新动向·新思考——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演讲提要》。㉒有关二里头遗址测年的情况,主要参考张雪莲、李琴:《二里头断代:我国碳十四测年的一个缩影》,《世界遗产》2015年第8 期。㉓这方面的近期研究可参看陈淳:《科学地探寻夏朝与最早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6月10日;易建平:《扩大视野,科学探索“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29日。㉔“唯科学主义”在中国曾经流行的情况,参见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㉕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8年版。梁启超晚年对于西方史学思想有很多反思,较集中的认识可以参考其《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年3月3日。㉖历史即通过探究而获得的知识,乃古希腊“历史”一词的本义,参见利科著,姜志辉译:《历史与真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7 页;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 页。㉗BEARD C.That Noble Dream[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35(1):74-87.㉘参见韦纳著,韩一宇译:《人如何书写历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 页;怀特著,陈新译:《导论:历史的诗学》,《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 页;安克施密特著,韩震译:《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㉙路西编:《德里达词典》“文本”条,伦敦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145 页,本文引自王立秋译网络版。㉚伊格尔斯著,林曼译,张旭鹏校译:《从21世纪的视角反思20世纪的史学》,澎湃新闻2018年3月27日。㉛梁启超:《新史学》,《新民丛报》第三号(1902年3月10日),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㉜参见傅斯年:《万恶之源》《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等文章,见傅斯年著、吕文浩选编:《出入史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㉝参见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1928年1月5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㉞笔者曾经讨论学界一些人认为中国史学理论不发达问题,参见陈立柱:《“中国史学理论不发达”刍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 期。㉟“神话”一词乃“myth”之译文,讲的是西方自然神灵化的问题。中国的上古神灵主要是祖先神,是人死后灵魂升天,祭拜吟诵其神灵等于讲述祖先故事即历史,这是中西神话之根本差异。西方意义的创世神在中国是战国以后才有的,主要是受到南方民族神话的影响。用西方神话理论研究中国上古史,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