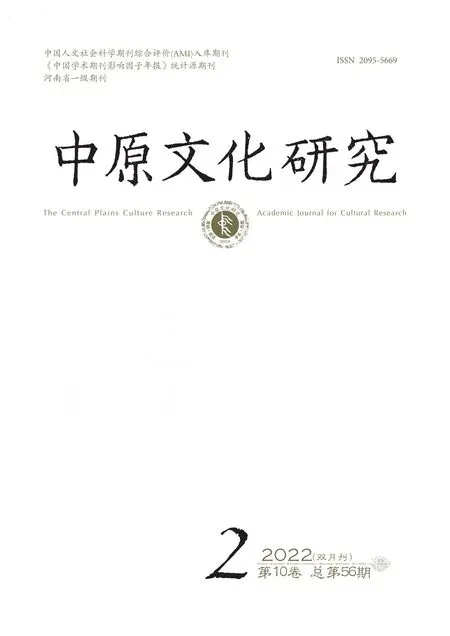含德与风教:萧统推崇陶渊明之文化因由探析*
2022-02-08王伟倪超
王 伟 倪 超
众所周知,陶渊明及其诗文作品在南朝文坛与批评界颇受冷遇。颜延之《陶徵士诔》述陶渊明平生而简概其作品为“文取指达”[1]1,刘义庆《世说新语》记东晋文人雅士却无陶渊明,刘勰《文心雕龙》文理巨制对陶渊明只字未提,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记》评述五言诗人也未及陶渊明,沈约作《宋书·隐逸传》虽有陶渊明但未评论其诗文,钟嵘《诗品》把陶渊明诗列为中品已属拔高。纵观南朝文坛,独萧统对陶渊明尤为推崇,先后为他编集写传作序,在唐前陶渊明接受史上殊为突出,其间原因值得追索。
一、萧统尊陶之原因
在陶渊明的接受研究中,学界对萧统推崇陶渊明之原因上投注了相当的关注,经归纳梳理,可大致别为如下几类。
有学者认为:“萧统生存在‘隐风’如此浓郁的时代,社会风气的熏染,佛教思想的陶冶,钟情山水的个性,使他对隐逸有着浓厚的兴趣。”[2]然而,《昭明文选》(下称《文选》)中隐逸诗有左思、陆机各一首,却未有陶渊明之作。萧统本人“性爱山水”[3]440,但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各方面正合萧统兴趣爱好,事实上萧统在《文选》中录谢之诗文是陶的三倍有余,也可以说明谢灵运比陶渊明在萧统眼中位置更高。退一步讲,即便不是谢灵运,魏晋时期隐逸诗人颇多,如嵇康、阮籍、向秀等,名气才学和隐居之志皆不在陶渊明之下,萧统想要寻找归隐之道,大可不必以陶渊明为尊。何况,“我们看到另一个陶渊明,不见得那么自然、任真与平淡”[4]203,归隐是文人仕途受阻的无奈选择,陶渊明亦是如此。萧统“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3]440,断狱公正,天下称仁,时常上书奏议国是,亦未见得有归隐之心。
有学者认为萧统与陶渊明在诗文上趣味相投,“《文选》选文定篇‘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陶渊明作品看似不符,实际上却非常符合”[5]。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6]155可以看出,萧统虽崇尚文质温厚风格,但丽典雍容是必不可少的,刘孝绰的《昭明太子集序》:“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6]245也可佐证萧统的文学观依然和梁朝文坛追求的文采繁富基本一致,这与朴素见长的陶诗风格大为不同。钱钟书先生曾在《谈艺录》中说萧统诗文“无丝毫胎息渊明处”[7]238。除此之外,萧统否定陶渊明的《闲情赋》,曰:“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6]200而萧统《文选》中却有《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等“卒无讽谏”之作。李剑锋先生认为《闲情赋》是“因为主体情感表现过于热烈浓艳而被否定”[8],然既然《文选》中有“情”赋一类,说明萧统对文学中的情欲是肯定的,至少不是否定的。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曰:“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3]447更表明“情性”之文为萧统所认同。那么从萧统的文学理论看,陶渊明朴直的诗文是与当时文风相悖的,也不符合《文选》的审美,萧统评判陶渊明诗文更多是从政治道德的角度出发。
有学者认为萧统作《陶渊明集序》与蜡鹅事件有关:“此文为陶渊明文集之序,而全篇重点却在申说韬光晦迹、遁世隐居可以全身避祸。此种思想之产生,盖与昭明晚年因埋蜡鹅事发,遭遇梁武猜忌有关。”[6]201此说似乎也站不住脚。其一,《南史》所记蜡鹅事件存疑。“《南史》较诸史,雅多逸闻,然但一二碎事本史失载而《南史》发之,若厌伏果真,父子间许大猜衅,姚察作传,岂容全不照管?恐姚无此缺漏也。”[9]840其二,萧统作《陶渊明集序》和遭梁武帝猜忌在时间上不符。据桥川时雄所说:“余所见之旧钞《陶集》,昭明《陶集序》末记云:‘梁大通丁未年(527年)夏季六月昭明太子萧统撰。’”[10]4也就是说,《陶渊明集序》所作时间为大通丁未年,而萧统遭忌的时间,俞绍初先生据《梁书》关于大通三年(529年)太子太傅之位突然重置和萧统对弈扰道之梦等记载,加之《文选》仓促杀青,推断云:“昭明之失宠当在是年十一月以前,南康王绩薨后未久。”[5]318作序在前,遭忌在后,两者相差两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三,《陶渊明集序》韬光养晦之旨与国势渐隆的背景不相衬。当年正值梁魏混战之际,梁朝兵锋日盛,大通元年(527年)春“司州刺史夏侯夔帅壮武将军裴之礼等出义阳道,攻魏平静、穆陵、阴山三关,皆克之”[11]4722,“五月,丙寅,成景俊攻魏临潼、竹邑,拔之。东宫直合将军兰钦攻魏萧城、厥固,拔之”[11]4724。如此攻城拔寨势力扩张之时,萧统以东宫太子之名作韬晦之态,不合乎朝野上下所盼。
以陶渊明的隐遁标签去判断萧统的所思所想,未免有些思维固化,那么能否换个思路,从萧统出发去思考其在众多诗人中选中陶渊明的实际用意。
二、《文选》择陶诗文之文化因由
《文选》由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其中录陶渊明诗文七题八首,较前人寥寥数语可谓相当可观,自此也开启了唐宋尊陶的接受史。《文选》中选录陶渊明诗文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挽歌》《杂诗(二首)》《咏贫士诗》《读山海经诗》《拟古诗》及《归去来》。这些诗文自然体现了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12]3的文学价值观,而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出发,也有规律可循。
《归去来》或与沈约有关。沈约《宋书·隐逸·陶潜》载:“赋归去来,其词曰……”[13]2287将《归去来》的原文引用。而且,《归去来》较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和言志辞朴的《与子俨等疏》《命子诗》,更符合《文选》的选择标准。沈约与萧统亦师亦友,萧统结撰《文选》,从陶渊明三篇赋辞中取《归去来》或受其影响。
《读山海经诗》《拟古诗》或与钟嵘有关。钟嵘《诗品·中》:“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14]337“欢言”之句出自《读〈山海经〉诗》,“日暮”之句出自《拟古诗》,钟嵘对陶渊明人品及诗文的评价是开山之作,奠定了陶渊明成为隐逸诗人的根基。钟嵘曾任晋安王萧纲的部下,“选西中郎晋安王记室”[3]1802,负责撰写参军章表,而萧纲乃萧统之弟,两人时有书信往来谈文论诗,如《答晋安王书》。所以,萧统对钟嵘应有耳闻,对《诗品》亦当有所接触,《读〈山海经〉诗》《拟古诗》之选或受其影响。
《咏贫士诗》或与云鸟意象有关。陶渊明《咏贫士诗》七首皆为五言佳品,《诗品·下·序》:“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14]459然而七篇为何单选其一?纵观七篇,唯其一者有云鸟意象,“孤云独无依”“众鸟相与飞”[15]472。萧统从其父梁武帝信佛,常游寺庙,作诗以记,诗中云鸟意象尤为突出,如梁武帝名作《游钟山大爱敬寺诗》:“飞鸟发差池,出云去连绵。”[6]22萧统《和上游钟山大爱敬寺诗》:“舒华匝长阪,好鸟鸣乔枝。霏霏庆云动,靡靡祥风吹。”[6]18另外,鸟鸣似乐声,常被视为佛法之音。云鸟意象高阔飘逸,恰合佛义之象,又显游赏之情,“这一切使得客观之景、之物完全获得了审美独立性”[16]159。萧统选陶渊明《咏贫士诗》之其一,或与云鸟意象分不开。
《杂诗(二首)》或与菊花香气有关。此二首诗乃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其五、其七,“萧统将诗歌的标题从《饮酒》改到《杂诗》,轻描淡写陶渊明和酒的亲密关系”[17]242,不与酒相关与何相关?总览《饮酒二十首》,唯其五、其七者有菊花之气。时萧统精理佛法,参与讲席,诗云:“惠义比琼瑶,薰染等兰菊。”[6]9智慧的佛义好比美玉,听之犹如被兰菊香气熏陶。萧统之母丁贵嫔也奉佛,“尤精《净名经》”[3]423,《净名经》即《维摩诘经》,经中有闻香一说:“菩萨各各坐香树下,闻斯妙香,即获一切德藏三昧。”[18]188中土未有佛国香树,萧统以菊花之香喻菩萨妙香,使之本土化文学化,在选陶渊明饮酒诗时,菊花香气或成为其优选之理由。
《挽歌》或与陆机有关。陆机被刘勰欣赏,“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19]243;刘勰被萧统爱接,“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3]983。因此,陆机诗文非常受萧统的赏识,《文选》“选录陆机诗歌52 首,居入选作家之冠,显示了对陆机的重视”[20]。陶渊明《挽歌》排于三国魏缪袭、西晋陆机诗歌之后,三人三题五首陆机占其三,皆为挽歌。“挽歌辞者,或云古者虞殡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客,皆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陆平原多为死人自叹之言,诗格既无此例,又乖制作本意。”[21]345陆机挽歌以死者自叹创诗歌新例,《文选》所录挽歌也都有这一共同特点,以死者的视角描写送葬悲哀人逝无着。可以说,萧统是以陆机挽歌特征选陶渊明之挽歌诗。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或与刘孝绰有关。《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于隆安五年(401年),陶渊明37 岁入荆州刺史桓玄幕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于元兴三年(404年),陶渊明40 岁任徐州刺史刘裕参军,这三年是陶渊明自出仕以来官职最为显要的时期,此后义熙元年(405年)解印归田,不再出山。《文选》择这两首诗颇有代表意义,而且两者皆表达了陶渊明身在官途但心系田园,在出仕与归隐之间矛盾的状态。这与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有异曲同工之妙,倦于官场,远害避祸。而谢朓是刘孝绰最为拜服之人,“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简文爱陶渊明文,亦复如此”[21]362。《颜氏家训》以谢朓关联陶渊明,那作为《文选》编者的刘孝绰以谢朓诗韵择陶渊明类似诗文,也未尝不可。
总而言之,《文选》择陶之诗文一是受人指引,二是意象贴合,凸显了萧统“独擅众美”[6]245的慧眼。如此看来,萧统在接受陶渊明的过程中,与时代背景、太子身份、周边人事都密不可分,他能选取陶渊明历久弥新之作,原因正在于他的政治眼光和文人群体的帮助,这对他的《陶渊明传》《陶渊明集序》都有影响。
三、萧统《陶渊明传》增补的儒家思想背景
论萧统的《陶渊明传》,不得不言及在萧统接受陶渊明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沈约。天监五年(506年),“以右光禄大夫沈约领太子詹事”[6]277,沈约负责教育领习太子,从萧统6 岁直到13 岁,可以说萧统对前人世事最基础的认知来自于沈约,对陶渊明最早的接受也于此时完成。
沈约在《宋书》中记载了陶渊明生平主要事迹,较颜延之《陶征士诔》更加详细丰富,增补事迹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性嗜酒”[13]2286,如种秫酿酒、王宏送酒、延之共醉、葛巾漉酒;二是“耻复屈身后代”[13]2288,如著文皆题晋氏年号。萧统评价陶渊明“篇篇有酒”以及“贞志不休”皆可源于此。沈约还记载了反映儒家思想和宗族观念的《与子俨等疏》《命子诗》,使萧统形成陶渊明“安道苦节”的儒家卫士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沈约虽将陶渊明置于《宋书》隐逸篇,但沈约说的“隐”是“贤人之隐,义深于自晦”[13]2275,是以儒家入世思想为基础的德修之道,而非远害避地的纯粹隐逸,这对萧统接受陶渊明的隐士内涵定位有非常大的作用。如果只有颜延之诔文而无沈约传文,如果没有沈约对幼年萧统的影响,也许萧统不会对陶渊明有如此直观的认识和思想的认同。
萧统《陶渊明传》在继承了沈约书写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删,从中可以看出萧统所要表达的重点所在。萧统故意不提沈约所记“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13]2288,可见萧统有意维护陶渊明的贤德之名,而增补部分更有指向性: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
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6]191-193
萧统增补部分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可归纳为两部分:一是“危行言孙”。论语:“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22]164当朝廷昏庸无德时,文人应当行为正直,但言语要谦逊谨慎,这是儒家思想在论隐士之道时最为深刻的要义之一,陶渊明就践行了这一理念。时东晋已亡,刘宋当道,陶渊明自居东晋之臣,视宋为无道,面对刺史之邀,托病不出,言语上却很谦卑,不敢以圣人自比。在看到同侪经不起劝诱出山讲礼且高谈阔论时,陶渊明加以讽刺,可见其儒家隐士自处之道。二是“父慈子孝夫义妇听”。《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23]268父母以慈爱待子女,子女则以孝顺报父母,丈夫以道义待妻子,妻子则以顺服侍丈夫。陶渊明体谅儿子生活艰辛,送劳力助其养家,并叮嘱善待下人,是为慈也。陶渊明妻子亦能勤俭持家,不畏贫苦,志同道合,可见陶渊明作为丈夫必守其义。萧统对于父子之情特别在意,“太子性仁孝,自出宫,恒思恋不乐。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还宫”[3]434。不仅如此,萧统对他人的父子之情也很在意,“徐勉子悱卒,昭明遣使吊慰之”[6]308。各方面看,萧统确实是一个非常孝谨的人,对其父其母,以至于他人父母,他都力行孝道。所以,萧统在《陶渊明传》中增补父子夫妻之家事,也就事出有因了。
从篇幅上看,萧统《陶渊明传》共近九百字,增补处近三百字,占三分之一。从内容上看,萧统分别展现了陶渊明于上、于下、于朋、于妻的相处之道,于上不卑不亢,于下爱护善待,于朋和而不同,于妻勤苦同当。从思想上看,萧统意在突出陶渊明的儒家形象,安贫乐道,自力耕耘,子孝妻贤。通览全篇不难发现,萧统较颜延之、沈约强调的是陶渊明的躬行儒道和修己齐家,前人所述陶渊明的归隐和嗜酒已然成为人物背景,贤德已占主要位置。隐和酒都不是单纯的存在,而是为了通过隐居的自处和饮酒的沉浸达到藏德于胸、守道于行的内圣之境。外表自由恬淡,内在道德之至,可谓儒家之隐。
四、萧统《陶渊明集序》的“含德”主旨
陶渊明诗文确有道家思想倾向,但说“萧统在《陶序》中则主要以道家思想为准的推崇陶”[24]96,从其所在的政治环境而言是说不过去的。天监三年(504年),梁武帝舍弃道家归入佛门,且笃定佛法为唯一正道,下诏曰:“弟子比经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散善,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25]242梁武帝舍道入佛,斥道家为邪道,“孝谨天至”[3]443的太子萧统岂敢以道家思想著书立说。
细绎萧统《陶渊明集序》可知,序文前部虽大谈隐晦之理,但意在突出先德后隐。沈约依《论语》孔子之言将隐逸之人分为隐者和贤人,“身隐故称隐者,道隐故曰贤人”[13]2276,萧统列举事例正合这两类:一类道家圣贤,庄周、安期生、老莱子,庄子曾为漆园吏、安期生献策项羽、老莱子为孝着彩服,皆为“贤人”;另一类帝王之君,伯成、唐尧、子晋,伯成曾列诸侯、唐尧一统华夏、子晋吹笙凤鸣,皆为“隐者”。而所提到的反面典型,苏秦、卫鞅、主父偃、楚庄王、霍光,与之相反,皆为纵横无德之人。萧统的隐晦之例举只是论据,论点已在章首标明:
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6]199
圣人心中有德,品德修身已达至高境界,言行随性但不逾矩,才能至大却不显露,于自然中养气,于道理中治学;自我提高的关键在于身体力行,亲自投入到生活之中,身心的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在萧统看来,隐逸之道,不是选择隐居去博得虚名,而是德道至高后必然选择韬光养晦。天监十四年(515年),萧统行冠礼赦天下,开始处理日常政务,梁武帝下诏招隐求贤曰:“若有确然乡党,独行州门闾,肥遁丘园……并即腾奏,具以名上……庶百司咸事,兆民无隐。”[3]161萧统为此仿效曹植《七启》撰文《七契》招揽隐贤,通过君子和逸士的对话劝说贤者应出仕效力,而非藏器待时,文末曰:“岂有闻若斯之化,而藏其皮冠哉?”[6]84可见作为储君的萧统站在国家立场对贤才隐居是持反对态度的。因此,萧统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不是因为其隐士身份而是其修己含德,重在彰显其德,而非向往其隐。陶渊明亲自躬耕忍受贫苦,他的归隐是因德高道悟而需遁世,他的嗜酒亦是如此,酒为表象德为根基,所以萧统曰: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6]200
圣人将世事政务寄于情趣之中,陶渊明将德道修行寄于饮酒之中,这应该是萧统对陶渊明嗜酒的理解。其实萧统对饮酒不感兴趣,因为他是佛教徒,“太子自立二谛、法身义,并有新意”[3]435,这可能也是《文选》改陶渊明饮酒诗为杂诗的原因。所以,萧统所美陶渊明之酒,并不是赞扬嗜酒,酒只不过是寄托物,或者只是一种表现方式,内核是对仁德的坚守,对道义的秉持。萧统看见的陶渊明,本意不在饮酒作乐,不在醉生梦死,而在于托醉酒之象避开凡俗之扰,保守真德。
至于陶渊明的诗文,萧统更是直接了当地将“文”与“德”联系在一起,曰:
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6]200
陶渊明的含德在于“贞”,不事二主,重乎节操;在于“耕”,自耕自种,自给自足;在于“笃”,忠于信仰,不偏不移。这在耕读时代的文人世界里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陶渊明的德行在当时已经广为传播了。萧统叔父萧秀于天监六年(507年)出任江州剌史,“及至州,闻前剌史取徵士陶潜曾孙为里司。秀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3]899。当时萧统出居东宫,正式建牙开府,此事对萧统接受陶渊明之德应有启发。萧统增一“含”字曰“含德”,更符合陶渊明外表“隐”“酒”而藏玉于山的儒家形象。
五、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风教”重点
萧统在接受陶渊明的过程中,欣赏其品格,推崇其含德,在前人标榜隐士的基础上又更加深化了儒家的内涵力量,使陶渊明更为文人所重,更为教化所用,《陶渊明集序》最后清楚地点明:
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6]200-201
“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一句出自《孟子》:“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26]256萧统以陶渊明比伯夷,取其不屈二姓之志,舍其隐世不出之行。首先,孟子论伯夷曰“治则进,乱则退”[26]256,萧统《陶渊明传》中檀道济访陶时已说过此理,被陶渊明一口拒绝,说明萧统接受的陶渊明之隐与伯夷之隐不相同,否则前后矛盾。其次,假如萧统是以伯夷之隐赞美陶渊明,编集作序行于世,那意思就是当朝横政、所事非君、贤者须隐,梁武帝岂不深究,显然不可能。最后,正如陶渊明所说“何敢望贤”,伯夷乃帝王之后古之圣贤,两者不可相提并论。“不必傍游太华”也正符合梁武帝舍道行为和萧统《七契》中招隐之旨。因此,萧统以《孟子》之语评陶渊明,非伯夷之隐评陶渊明,更拉近了陶渊明与儒家的关系。
细品概括,萧统认为,读陶渊明诗文就会变得“勿竞”“勿鄙”“勿贪”“勿懦”“蹈仁”。然而,“陶诗在题材的选择上,具有确定性和一惯性,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27]4,内容基本是田园躬耕、歌颂隐者、咏怀古人、寄酒消遣,这与萧统所说的不争名逐利、不鄙弃吝啬、不贪婪吞没、不懦弱胆小、不求爵禄并不能完全对得上号,可见萧统在有意制造陶渊明诗文“风教”的作用,品格要求的五个方面想必不是随意而写,反映出萧统作为执政者对文人百姓的教化思路。若据桥川时雄所说,《陶渊明集序》作于“梁大通丁未年夏季六月”,那么作序之时正是在南朝梁于是年三月改普通年号为大通后不久。要知改元对于国家而言并非小事,标志着推陈出新别是一体,萧统身为太子作此序文,又强调品德风教,应有政治宣扬之意。查史料所载,萧统在此年经历的朝局人事恰与“风教”重点相契合,试论之:
“勿竞”之言或与徐勉有关。徐勉在萧统七岁时领太子中庶子,“太子礼之甚重,每事询谋”[3]983,在萧统29 岁时的蜡鹅事件中固谏梁武帝才保太子之位无虞,可见徐勉在萧统一生中何等重要。不图虚名不重财利是徐勉此人的一大品格,他与同岁的王融有着鲜明的对比。“琅邪王元长才名甚盛,当欲与勉相识,每托人召之。勉谓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难可轻弊衣裾。’”[3]979王融乃东晋宰相之后,徐勉自幼孤贫却不接王融伸过来的橄榄枝,难能可贵。后来,“融躁于名利”[28]576,陷于帝位之争被赐死,时年27 岁。而观徐勉,梁武帝非常器赏,授予高位,但徐勉总是谦让解辞,如“求换侍讲,诏不许”“频表解宫职,优诏不许”[3]983“勉以疾自陈,求解内任,诏不许”[3]996,此外他还散财救济贫苦,“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3]997。正是这种不争名利之德,使徐勉及居重任,善始善终,享年70 岁。《陶渊明集序》所作时大通元年,“以尚书左仆射徐勉为尚书仆射、中卫将军”[3]189,徐勉的高位就职对太子有直接影响,萧统敬重徐勉为人,所言“驰竞之情遣”或受其感召。
“勿鄙”之言或与刘孝绰有关。刘孝绰与萧统的关系非同一般,天监元年(502年),萧统两岁,刘孝绰即为太子舍人,陪伴其左右。刘孝绰文采卓群,深受萧统敬重,“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3]1258。不过,刘孝绰恃才傲物不能容人,对到洽、何逊等人不屑鄙之,“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3]1260,“又撰诗苑,止取何两篇,时人讥其不广”[21]345。终于,刘孝绰鄙夷他人招来了祸端,普通六年(525年),到洽任御史中丞,弹纠百官,抓住刘孝绰带美女入豪宅而弃老母于陋室的失德行径,参劾致其免官。值得注意的是,刘孝绰诸弟为兄出气,奏文历数到洽之过,“又写别本封呈东宫,昭明太子命焚之,不开视也”[3]1260,萧统与刘孝绰关系密切却连看都不看,还命人烧毁,可见萧统深恶刘孝绰不孝之失和文人间“鄙吝”之举。大通元年,刘孝绰重被启用,“起为西中郎湘东王咨议”[6]313,刘孝绰除启谢武帝外,“又启谢东宫”[3]1268,说明萧统在他复起之事上有所帮助,谢辞中满是贤者见妒、必待明察的道理,《陶渊明集序》作于此时,萧统忽言“鄙吝之意”或是有感而发。
“勿贪”之言或与周舍有关。周舍先为太子洗马,后为太子詹事,总理东宫庶务,政务与萧统息息相关,责任颇重,然而出现了贪墨丑闻:“普通五年(524年),南津获武陵太守白涡书,许遗舍面钱百万,津司以闻。虽书自外入,犹为有司所奏,舍坐免。”[3]977周舍生性俭素,衣食住行皆为简朴,没想到晚节不保,于是年抑郁而卒。此事萧统印象深刻,不仅与周舍任太子詹事有关,还与时局有关。“普通中,大军北讨,京师谷贵,太子女因命菲衣减膳,改常馔为小食。”[3]441普通五年,梁朝大将悉数尽出,成景俊、裴邃、元树、彭宝等率军攻魏,导致后方吃紧,萧统以上率下,紧衣缩食,而在此时周舍贪墨事发,反差明显,难辞其咎。其实,周舍当时以清廉自居,梁武帝诏曰:“终亡之日,内无妻妾,外无田宅,两儿单贫,有过古烈。”[3]978周舍之父乃前朝中书侍郎,家境殷实,至此廉洁于斯,贪廉只在一念之差。萧统于《陶渊明集序》中云“贪夫可以廉”之语,陶渊明未有纠贪之事,何来贪廉之论,此语或起于周舍贪廉之变故。
“勿懦”之言或与萧渊藻有关。萧渊藻乃萧统堂兄,同氏宗亲又兼太子中庶子,其英雄事迹为萧统所钦佩。早年边境作乱,聚众数万,“渊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议,欲自击之。或陈不可,渊藻大怒,斩于阶侧。乃乘平肩舆,巡行贼垒。贼弓乱射,矢下如雨,从者举楯御箭,又命除之,由是人心大安”[3]944,萧渊藻最终平叛。萧渊藻不怯不懦,奋勇向前,以弱胜强,而后没有恃功自大,保持谦退,不求闻达,可谓国之良将。大通元年三月,“以左卫将军萧渊藻为中护军”[3]190,统领宫廷禁卫军,对太子之位非常重要,萧统时作《陶渊明集序》言“懦夫可以立”,或期臣民有萧渊藻之勇,保家卫国。
“蹈仁”之言或与萧纶有关。萧纶乃梁武帝第六子,萧统之弟,封邵陵郡王,但在普通五年被罢黜官职削夺爵位,《梁书》记载:“五年,以西中郎将权摄南兖州,坐事免官夺爵。”[3]1123可想事态严重,至于细节,《梁书》却未有说明。不过《南史》对此详解,萧纶“在州轻险躁虐,喜怒不恒,车服僭拟,肆行非法”[28]1322,梁武帝对他严厉责问,他也不思悔改,更加骄纵悖逆。梁武帝遂欲将萧纶下狱并赐死,幸亏“昭明太子流涕固谏,得免,免官削爵土还第”[28]1323。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帝王家里,萧统能为残暴的萧纶说情,保其性命,可见仁义之心。在萧统的感化下,萧纶有所收敛,重归正途,于是“大通元年,复封爵,寻加信威将军,置佐史”[3]1124。萧统所言“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或有对萧纶恢复爵位的劝勉之意。
综上所述,萧统总结陶渊明诗文有使人“勿竞”“勿鄙”“勿贪”“勿懦”“蹈仁”之功,而陶渊明的生平诗文与此并无直接联系,萧统作序结语非一时兴起,而是政治经历和深刻思考使然,借陶渊明之德行“风教”之举,若萧统继承帝位,其育民之术和教化重点也正在这五个方面。
余论
在《作者作为生产者》一文中,班杰明(Walter Benjamin)认为:“作品对于生产关系说出些什么是次要的,主要要强调的是该作品在成产关系中有何种功能。”[29]473历史上修文撰书大都为了产生某种社会功用,抑或服务于王朝的正统建构,生产并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30],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唐武则天编纂佛经、宋王安石撰《三经新义》,概莫例外。所以,抛开萧统个人定位,他作为一国储君,其言行必定考虑于国于民的影响,爱嗜陶文并亲自立传、编集、写序,如此大动作,需有一定的政治需求和功能指向。由于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刻板印象过深,学者常以陶渊明之性推萧统之心,不顾萧统太子身份和朝局背景,不考虑萧统接受差别和行文论点,仅以文字表意为由,指其有退隐之迹和道家思想,实有偏颇。萧统深受儒家与佛教的双重影响,虽有解脱心态,但“事实上这根本做不到,像萧正德之流绝不会因为他仰慕隐逸,笃信佛教而减轻对他的仇恨;梁武帝也不可能让自己的太子真的去做隐士或和尚”[31]80。总之,萧统的《文选》择陶诗文已经显示了政治地位和文人群体对他的影响力,《陶渊明传》《陶渊明集序》隐含着一位储君对未来执政的思考,反映了萧统对陶渊明式的儒家思想的接受和再认识,这是文学创作对于政治经历和周遭人事的反映,或可言偶然,也可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