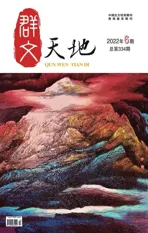“花儿”和河湟小调的区别
2022-02-06滕晓天
滕晓天

家庆有余 张成林/摄影

随着打造“花儿”品牌的不断深入,社会上一些人不自觉地将“花儿”和河湟小调混为一谈,一些媒介也人云亦云,将河湟小调贴上“花儿”的标签,错把河湟小调当“花儿”,不仅将二者混为一谈,还误导了群众。其实,它们之间有一些相似点,更有不同点,二者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花儿”?“花儿”是流行在大西北山野之间的一种以歌唱爱情为主的山野民歌。发源于河湟地区的河湟“花儿”因其历史悠久、曲令繁复、传唱地域辽阔、文化底蕴深厚而影响最广最大。河湟“花儿”,民间又叫“少年”,一歌两名。其实早在明代成化年间到清代的文献记载,一直叫“花儿”。它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流传在青、甘、宁、新四省(区)及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河湟“花儿”歌声委婉动听,高亢、嘹亮、轻漫、悠长,多种情愫俱全,多为五声徵调,曲首曲间和句间多用衬句拖腔,旋律起伏大,上行多用四度调进,高音区多用假声。欢快的曲令多为2/4 或3/8 拍,相对紧凑短小。
什么是河湟小调?河湟小调广泛流行于河湟地区,是中国民歌体裁类别的一种,流行于广大农村和城镇集市。经过历代流传,经过较多艺术加工,具有结构均衡、节奏规整、曲调细腻、抒情婉柔等特点。民间的俗称很多,如小曲、小调、曲儿、歌谣、小令、俗曲、时调、丝调、丝弦小唱等。2011 年5 月,青海省西宁市申报的青海汉族民间小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实,在河湟地区,尤其是多民族聚居区,各个民族都在传唱小调,具有多元文化的特征,区别只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小调或酒曲儿不广泛传唱外,其他和“花儿”一样,为多民族所共有,同样为多民族所培育。
河湟小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极其广泛,不受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和具体劳动环境所制约,不仅是农耕文化的反映,也是市井文化的反映,为城乡各阶层、各类别、各民族所喜爱,广泛反映各阶层各色人等的爱情婚姻、离别相思、风土人情、娱乐游戏、自然常识、民间故事等,几乎无所不含。研究表明,河湟小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诗经》中的某些叙事性篇章,已经蕴含了这一体裁的某些元素。汉代的相和歌就是用丝竹伴奏的歌唱形式,可说是河湟小调的源头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出现了《子夜四时歌》《从军五更传》《月节折杨柳歌》等时序体的乐府民歌,从中可以看到如四季、五更、十二月等时序体式传播较广的传统河湟小调。至隋唐,有更多的民歌称为曲子,成为说唱、歌舞演出的一部分。宋元之后,伴随着中国城镇经济的日益繁荣,河湟小调也走向了较成熟的阶段。明清时期,河湟小调发展而繁荣,趋于成熟。民国时期,河湟小调唱词、种类和调式等都有了很大发展,一些内容今天仍在传唱。
一、“花儿”和河湟小调的相似点
从根本上说,河湟地区的“花儿”和小调,都有着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相衔接的地域特征,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属性,有着浓厚农耕文化的根脉和印痕,又有着民间千丝万缕的百姓情结,多元文化特征鲜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可说是同根同祖。
一是都属于民间文学范畴。它们产生于青、甘一部分地区,被世居民族所认同和热爱,广泛流传于民间。
二是难以割舍的亲情渊源。它们从音乐旋律到通俗化、口语化的唱词,皆有一些相同点、相似点和关联点。
三是相同的传唱地域。河湟地区是它们传唱的广阔空间,简言之,凡是“花儿”传唱的地区,也是民间河湟小调繁衍之地,几乎没有不同。
四是广泛的民族认同度。青海省境内的汉、藏、回、土、撒拉、蒙古、东乡、保安、裕固等9 个民族都唱“花儿”,他们是“花儿”文化共同的传播者和传承者,“花儿”文化是各民族心血共同浇灌的花朵。河湟小调,凡是“花儿”的传唱空间,同样成为它们的生存空间,几乎没有例外。只不过一些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不传唱某些河湟小调而已。和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也和汉族一样,热爱和传唱河湟小调。
五是“花儿”和河湟小调互有渗透。一方面在音乐和旋律上,互有借鉴;另一方面或将“花儿”歌词与社火小调相糅和,或将河湟小调唱词引入“花儿”歌词相融合,或用“花儿”格律将小调唱词稍作规整后套入曲令传唱,因之一度出现某种混同,让人难以区分。
六是“花儿”不包括民间酒曲儿,但河湟小调却能容纳酒曲儿。有些人把《尕老汉》错当为“花儿”,可能是因20 世纪50 年代朱仲禄先生所发行的我国第一张“花儿”光盘中,同时收进了酒曲儿《尕老汉》的缘故吧。
二、“花儿”和河湟小调的不同点
“花儿”和河湟小调虽属同族同宗,但从微观上说,它们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主要的。
一是文学类属不同。“花儿”是山野民歌,其源头和关联也可溯至《诗经》,从起源到成熟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是明代成化年间,公元1465 年),它属于山乡农家以传唱爱情为主的山野民歌,无拘无束的山野是它主要的生存环境,逐渐形成不能在庄子里传唱,更不能登堂入室的一大民间禁忌。河湟小调则是大众文化,不受“花儿”的这些约束,它的传唱不受时空限制,不仅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传唱,而且可以登堂入室,甚至家庭共享,受众广泛。河湟小调更多地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和加工、贩夫走卒的传唱和改编、大家闺秀的偏爱和吟哦,因而内容更加广泛,形式多样,受众颇多。值得关注的是,河湟小调除了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之外,还深受市井文化的熏陶,可说是这两种文化的产物。
二是内容着力点不同。“花儿”开宗明义地以爱情为主要内容,叙事次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毫无遮拦的这些随性不仅迎合了相当一些群众的欣赏品味,加速了其传播,也反映了它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河湟小调也反映爱情,但比重和分量相对较轻,而且显得低调、内敛、含蓄、温和,更能被不同受众所接受。因而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地方的民间社火也将一些“花儿”情爱的唱词,大胆引进河湟小调传唱,受到群众青睐。
三是传唱受众不同。“花儿”的传唱过去只能在山野之间进行,村庄及家庭没有它的位置,而且要受家庭、大小、班辈、男女等各方面的约束和限制,尽管民族认同度很高,但规矩较多。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网络的发达,“花儿”不仅登上大雅之堂,而且进入家庭,其中传唱的情爱也逐渐失去了过去特指的内涵,而成为了人们能够普遍接受与欣赏的艺术和文化。这是后话。河湟小调则是大众的传唱宠儿,可以说是普世价值很高,很少受“花儿”传唱所受的约束,民间的社火,群众的集会,山野之间,村庄田家等皆可歌唱,约束较少,没有场合、大小、班辈、男女、老少的禁忌,显示了极大的自由性,成为群众文化的首选。

青海民间小调演唱 党海秀/摄影
四是格律要求不同。“花儿”虽然是山野民歌,是劳动人民口传心授的口头文学,且有着口语和方言的特点,但同时有着极讲究的歌词格律。简言之,就是每一句歌词是三顿或四顿的诗歌节奏,四句或六句或八句的句数,奇句三字尾,偶句两字尾,句尾既押韵又要同调,即同声同韵(调)。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花儿”,得不到老百姓认可。“花儿”就是诗歌,是高档次、高标准、高品位的诗歌,这也是“花儿”在中外众多民歌中独树一帜,经久不衰,值得骄傲的地方。河湟小调则没有这些规矩,它通常以七八字句为主干,根据调式要求,构成形式或两句或四句,只要通俗易懂,大致押韵,朗朗上口,适应需要即可,没有严格的格律要求。流传范围不广的一些酒曲儿或河湟小调,其唱词更加随意,没有韵律讲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间的一些酒曲儿,并不是“花儿”,如酒曲儿《尕老汉》等,它们归属于河湟小调。酒曲儿唱词以口语为主,无论其歌词格律和音乐曲调,都和“花儿”是有很大区别的。
五是音乐表现不同。“花儿”音乐的程式化要求较高,通常叫做曲令,河湟地区流行不同名称的曲令就达100 多种,加上同一种曲令的不同风格,可达240 多种,如“直令”“水红花令”等多达20 余种,就是“互助令”也多达10 余种。不少曲令还有音乐语言的延伸,配有程式化的衬词、衬句(如“白牡丹令”中的“阿哥的白牡丹”,“三花嫂令”中的“美尼格三花嫂明白人”等),甚至衬段(如“尕马儿令”中的尾歌“尕马儿你拉着来呀,拉回了缓来呀连手”,还有“老爷山令”中的“尕罐罐儿,煤疙瘩儿,一挂捡着来呀我的黄花姐呀,阿哥把你想着”等),实际形成了与歌词本意关联不甚紧密的副歌。它们虽和主题若即若离,却起着陪衬、烘托作用,成为一首“花儿”完整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河湟小调之中,也有衬词或衬句,但多为语气词(如“哪哈咿儿吆”“蹬吆瞪”“杨柳叶儿轻哪”等),没有衬句现象。“花儿”中所有这些衬词衬句,甚至副歌,都是洋溢着“花儿”风格的音乐旋律,重要的是,它们的音乐表现不同,熟悉的人一听即懂,这些音乐表现成为二者之间区别的重要标志。
六是情感表达不同。“花儿”唱词的情感表达,一方面,过去往往是特指的,大多是个体之间的内心倾诉,如表达“我就是爱你,爱到五脏六腑,疼到心肝肠肚,感到死去活来,今生来世不弃不离,阿哥尕妹至死不渝。”到了现在,所唱的爱情,才慢慢由个体转移到群体了。河湟小调的爱情则多为泛指,歌颂的是老百姓普遍的爱恋观和情爱观,很少有个体之间特指的感受,较少“疼烂肝花想烂心”的切肤之痛,表现也比较含蓄,但这种宽泛的爱恋也能引起大众的普遍感受,为各色人群所接受,为各种场合所容纳。另一方面,为了增加不同的感情表达,“花儿”的音乐表现五彩缤纷:或在开唱时高亢起始,力图引起对方注意,再放低音高,舒缓表述;或在结束时旋律上扬,与起始音段相呼应,以使感情圆满表达;或高亢嘹亮,声振云天,尤其是藏族拉伊旋律的引进,赋予了很强的穿透力;或轻声漫语,准确表达内在的感情,或如泣如诉,感人肺腑等等。但是,河湟小调的音乐,始终如一,沿着固有的旋律,不慌不忙,表现稳定,没有较大幅度的起伏跳动,也没有起始与结尾时的高音互对,可以说,以既定的音量音高与舒缓的感情表述相得益彰地进行相对固化的节奏推进。情感表达的不同,是区分“花儿”与河湟小调的一个显著标志。
七是歌唱动作不同。“花儿”的传唱,由于最初受众是不熟悉或不认识的人,且是山野之间的远距离,没有跳跃或其他动作,只需要借助手势以图扩音或传声,真切地表情达意,不是特别讲究节奏感,关键词语呈重音或用华腔,为加重语气,引起重视,开声或尾声拖腔较长;因是有感而发,需要思考空间,加之唱者文化水平所限,故在唱词中添加了不少与本意无关的一些“词外话”,如“我们、你们、那就、这个、那个、咿呀”等衬词,隔断了主题的连续,也显得语言的累赘和喧宾夺主。河湟小调,因为歌词几乎是固化的或是约定俗成的,没有累赘语言,也较少无关的衬词,显得明朗、干净、轻快,民众易懂易记,一些河湟小调并配有载歌载舞的舞蹈动作,更加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华丽而丰满。简言之,现实生活中的“花儿”无需渲染的动作,但河湟小调辅以动作是必需的。
随着新时代的文化发展,以及各级政府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挖掘和保护,使得“花儿”有了新境界和新世界,民间才有了“花儿”文化的新天地,同时也带来了河湟小调的大进步和大繁荣。“花儿”和河湟小调的完美结合继而合理改编和创作,被誉为东方音乐经典的“花儿”歌舞《花儿与少年》就是一个典范。严格意义上说,它既不是单纯的“花儿”,也不是单纯的河湟小调,它把青海民间小调《四季歌》《蓝玉莲》《五更鼓》等通过“花儿”旋律有机联系起来,并把原来小调的歌词按“花儿”格律进行了局部改动,也创作了相应的一些新歌词,使之串联为个体基本独立,整体有机连贯的一个音乐整体,它洋溢着河湟小调热情,飘荡着“花儿”旋律,使之耳目一新,一直为人们所热捧。作品开启了“花儿”和河湟小调有机结合的新纪元,彰显了多方面的灿烂前景,人们也记住了为创作 《花儿与少年》倾注心血的歌唱家朱仲禄、音乐家吕冰、编舞者章民新,也使这些艺术家名留史册。我们期待新世纪再创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