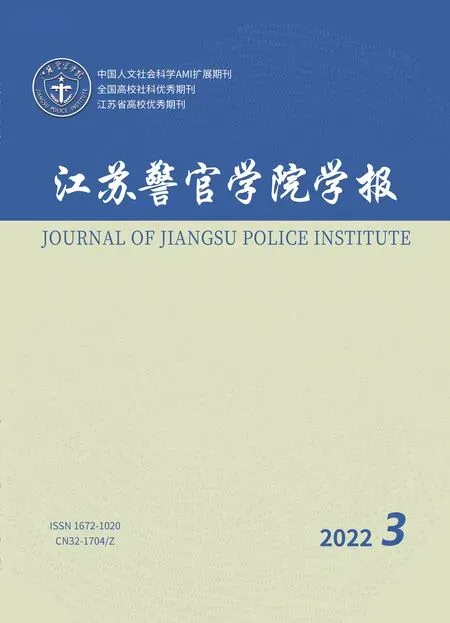行民混合侵权的责任形态及救济
2022-02-05肖月锐
肖月锐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中,多数人侵权是指侵权责任人为数人的侵权行为;①李中原:《多数人侵权责任制度的历史与现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 期。若多数人侵权的责任人之一是行政机关,则为行民混合侵权。②当前学界缺乏一个固定概念用以描述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与民事主体行为结合致人损害的情形。有的学者将此称为“有第三人过错的行政侵权”,也有学者称其为“国家机关与第三人共同侵权”,还有观点认为应将此类情形称为“行民混合侵权”。因第三种称谓在字面上体现了侵权主体的特征,揭示了不同主体侵权行为之间的交互关系,且相对更加简洁,故本文采第三种称谓。较之传统民法中的多数人侵权,无论是民法典还是国家赔偿法,均缺乏对行民混合侵权责任的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亦是零星且不成体系,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较为突出的有两个:其一是行民混合侵权中责任承担形态的确定问题,虽然部分司法解释和批复对此问题有所回应,但覆盖范围窄、在理解上存在争议。对此,是否可以参照民法规则确定责任形态?如果可以,又该如何确定?现存规定和民事规则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取舍?其二是行民混合侵权诉讼的程序设计问题,当前没有解决混合侵权的特殊程序,实践中各地做法迥异,分案处理模式存在大量缺陷,合并处理模式又缺乏规则支撑。如何设计程序方可高效化解此类冲突?欲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回归且立足于行民混合侵权中行政机关赔偿责任的性质认定。本文以对行民混合侵权中行政机关赔偿责任性质的理解为基础,继而由此对行民主体的责任形态与救济程序的设计展开进一步探讨,以期为司法实践中的冲突解决提供有效路径。
二、理解:责任性质之厘清
在混合侵权中,行政机关赔偿责任的性质决定了其法律适用上的选择。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王敬波:《国家赔偿法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 页。而国家赔偿责任的性质素有争议。现有的观点往往将视角聚焦于国家机关单独侵权的情形,从规范主义的进路去证成国家赔偿责任的属性。②王磊:《论国家侵权责任的私法属性——基于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的进路》,《西部法学评论》2018年第4 期。但少有学者将国家赔偿置于混合侵权语境下,通过功能主义的进路去对国家赔偿的性质进行分析。
(一)单独侵权视角下行政赔偿责任性质之争议
行政机关因单独侵权所致赔偿责任的性质本被民法通则第121 条认定为民事责任,但1994年颁布的国家赔偿法却更倾向于将国家赔偿责任认定为一种公法责任。之后,民法总则与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也未采纳民法通则的规定,导致学者们对国家赔偿责任性质的争议从未停止。总结而言,目前学界对该问题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公法责任说。该说认为国家赔偿责任均属公法责任范畴,其特点是:(1)在实体上,国家赔偿责任不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国家赔偿责任需具有独立的归责原则、有特定的赔偿范围以及限定的赔偿数额;(2)在程序上,民事法庭不能处理国家赔偿案件,受害人请求救济的程序设计也应与民事诉讼程序相分离。法国、瑞士的立法明确采用此观点,我国大多数行政法学者也主张此说。③江必新:《国家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关系之再认识——兼论国家赔偿中侵权责任法的适用》,《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1 期。
二是私法责任说。该说认为国家赔偿责任的性质当属一种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④《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1 页。国家赔偿法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没有特别规定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⑤杨立新:《侵权赔偿责任与国家赔偿责任的交叉与分野》,《中国审判》2013年第12 期。英美法系国家多采此观点,我国大部分民法学者是此说的支持者。
三是折衷说。该说认为国家赔偿的性质具有公法和私法两种属性,⑥刘静仑:《比较国家赔偿法》,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 页。如江必新教授指出,2008年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赔偿法修正草案”⑦2008年6月30日我国台湾地区“国家赔偿法修正草案(初稿) ”第2 条第1 款规定:“国家损害赔偿,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者,适用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未规定者,准用民法之规定。”即是此观点的具体体现。该学说的中心思想在于国家赔偿法未有规定时,就不同的事项决定适用不同的规则。
(二)混合侵权视角下行政赔偿责任性质之认定
1.规范主义理论在混合侵权中的困境。传统的公法责任说和私法责任说的观点均采规范主义之途径,从法的支配原理、理论构架出发探究国家赔偿责任之性质,且将视野局限在侵权主体仅由行政机关构成的情形。这导致其在解决行民混合侵权情形下的责任问题时难以提供帮助。
若采公法责任说,会导致该类问题解决上的混乱。首先,性质的完全分立使得责任承担形态设计受到局限,连带责任或者不真正连带责任等设计失去了理论的土壤。其次,由于国家赔偿和民事侵权赔偿范围的差异,依此观点还将导致认定赔偿数额的混乱。再次,公法责任说的观点意味着解决该问题时将采取适用不同程序救济的分案处理模式,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且易因裁判主体的不同而导致结果的冲突。最后,我国国家赔偿法本身仍处于发展阶段,⑧陈东果:《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责任竞合关系梳理——兼论我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修正》,《人民论坛》2010年第11 期。体系尚不完备,此说切断了在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时适用民事规则的路径,从而导致部分情况下法官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将私法责任说一以贯之,以国家赔偿法缺乏对行民混合侵权行为的特殊规定为由,完全适用民法规则加以处理亦存在缺陷。从实体层面看,此情形下,将行政机关责任完全视为民事责任忽略了国家赔偿中特有的举证责任分配、公平责任适用等制度设计的意义,会导致当前国情下国家赔偿制度“实质公平”的破坏。①杜仪方:《行政不作为中行政与民事赔偿的责任分担》,《社会科学》2009年第10 期。从程序层面看,全盘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问题,虽是简单明了,但缺乏现行相应规则的支持,同时也忽略了国家赔偿“双重救济途径”的制度意义。
2.功能主义理论在混合侵权中的进路。功能主义法学认为,法律的合理性在于其适用的社会效果。②朱淑丽:《比较法学中的反法条主义进路》,《社会科学》2014年第4 期。在规范主义下的学说均止步于解决实际问题时,我们应当“降低对孤立规范的关注,强调法律制度的社会功能”。③Jaakko Husa,“Metamorphosis of Functionalism-Or Back to Basics”,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2011,Vol.18,Issue 4,pp.548-553.在混合侵权责任分配和救济这一实际问题面前,拘泥于行政赔偿责任性质的公私划分,将如前文所述的那样难以达到理想的社会效果。以折衷说观点为基础,将混合侵权中行政赔偿责任定义为一种“准民事责任”最为适宜。换言之,行政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不以公私法为边界进行分立,而应就不同事项决定其适用的法律。具体而言,对于仅与行政赔偿责任相关的事项,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例如,行政机关赔偿责任的成立、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责任范围等内容可适用国家赔偿法,以保留法律为了弥补当事人实体和诉讼地位不平等而提供的制度设计。对于与民事赔偿责任相关联的事项则适用民事规则,如责任形态和赔偿范围的适用等,可依民法之规定。由此,一方面可为责任形态多样化的设计提供理论基础,一方面也契合行政法赔偿范围向民事赔偿范围接近的呼声。④台运启、杨小君:《关于国家赔偿标准的问题与建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3年第5 期。在程序方面,在分析当前观点和实际做法之利弊后,还需要设计一种特殊的程序以解决混合侵权的救济问题,回应高效、公正的程序价值追求。
三、内容:责任形态之确定
在将行民混合侵权中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认定为一种“准民事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需要明晰的便是民事规则在混合侵权中应以何种路径来适用以及如何展开等问题。
(一)民事规则在行民混合侵权中的适用路径
在民事规则之于混合侵权中适用时,存在解释论和立法论两条路径。前者旨在援引适用现行有效之规定解决问题,而后者则以行为形态与责任形态的对应理论为基础指导完善立法。
1.解释论路径。解释论方法要求在明了现行有效的民事规范之后,判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有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可以援引适用。⑤韩世远:《民法的解释论与立法论》,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 页。此思维模式下的问题解决逻辑为:首先,行民混合侵权在民法典中并无直接对应的特殊侵权行为规范;其次,因为行民混合侵权主体和行为的特殊性,故难以通过解释现存的特殊侵权规范来解决其责任形态问题;最后,根据法无特别规定即应适用侵权责任一般规定的原则,得出应适用民法典第1168 条到第1172 条的一般规定进行处理的结论。⑥张新宝:《多因一果行政赔偿案件中的多因形态与责任分担》,《中国审判》2013年第12 期。
以此路径认定混合侵权的责任形态存在两个缺陷:第一,此路径将混合侵权的责任形态限定在了按份责任和连带责任之中,切断了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等责任形态的适用;没有考虑到混合侵权中主体的特殊性,也难以平衡责任人与被侵权人之间利益。第二,从现实角度看,该路径与司法解释及批复在逻辑上存在冲突,⑦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如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答复》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财产损失系第三人行为造成的,应当由第三人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第三人民事赔偿不足、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下落不明的,应当根据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其对责任形态的认定采补充责任的观点,而非按份责任或者连带责任。适用该路径难以达到立法上的和谐。由此,该观点过于粗糙,难为治本之方。
2.立法论路径。国家侵权责任的定性只是为调整国家侵权行为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但责任的具体构成仍然离不开主体特殊性的考量,故混合侵权之责任形态设计不应徘徊于一般多数人侵权的视野;加入行为形态和主体特殊性的考量,站在立法论的立场构建一个行民混合侵权的责任形态体系,方为正道。侵权责任形态的设计“并非偶然与激情畅想的结果,而是理性与逻辑深思的结晶”①徐银波:《侵权补充责任之理性审思与解释适用》,《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 期。,民事责任形态在罗马法时期就已被认识到,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不断扩充,逐步形成一个具有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等内容的繁杂的体系。经过学者们的不断研究,多数人侵权中行为形态和责任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得以确定。杨立新教授提出了多数人侵权中行为形态和责任形态的对应框架理论,将多数人民事侵权行为类型划分为共同侵权行为、竞合侵权行为、分别侵权行为和第三人侵权行为,并分别对应承担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和第三人单独责任。②杨立新:《多数人侵权行为与责任》,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3 页。
下文便以此理论为基础,对行民混合侵权的责任形态进行探讨。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首先,如前所述,混合侵权责任承担形态应当适用民事规则加以设计,而侵权行为形态与责任形态的对应理论可谓该领域的集大成者,系统地揭示了责任形态设计的本质原因;其次,民事行为形态与责任形态的对应理论构建了一个周延的体系,可以涵盖所有的混合侵权情形,可解决当前法律规范覆盖面不足的问题;最后,多数人侵权的行为形态和责任形态的对应关系理论得到了民法学界的充分讨论,这种对应关系的确定虽然更多地是出于对于逻辑和体系的完善,但是同时也揭示了不同侵权行为形态背后所附带的价值衡量。相对于直接适用一般规则,其更加丰富了责任形态的类型,更加契合社会的价值需求。
(二)民事规则在行民混合侵权责任形态中的具体展开
将多数人侵权行为形态和责任形态的对应理论在行民混合侵权中具体展开时,需要考虑这一理论在混合侵权中应如何体现?如此适用是否合理?
本文参照杨立新教授对多数人侵权行为形态的分类,将行民混合侵权类型划分为共同的行民混合侵权行为、分别的行民混合侵权行为、竞合的行民混合侵权行为以及构成“第三人”侵权的行民混合侵权行为。
1.共同的行民混合侵权——连带责任。按照民法理论,侵权人构成共同侵权并造成了受害人的损失,应当对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共同侵权对应连带责任的本质原因在于加害人在主观上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而混合侵权中行为和主体的特殊性并不会对其本质产生影响,所以该对应关系在行民混合侵权中的适用是合理的。
在具体适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机关和民事主体“共同”的认定。民法对于“共同”的理解素有共同故意说、共同过错说和共同行为说的争议。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却采纳共同故意说的观点,并将其限定为“恶意串通”。
这样的规定让连带责任在混合侵权中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首先,在共同故意说的视角下,民法理论认为一方对另一方侵权行为的放任亦属于共同故意的范畴,③张平华:《侵权连带责任的现实类型》,《法学论坛》2012年第2 期。实践中亦有案例持此观点。④(2014)泉行初字第0017 号行政判决书与(2012)冀行终字第70 号行政判决书便采此观点。两起案件中,虽然行民主体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但是法院认为行政机关明知民事主体的违法行为而没有采取措施,同样认定其行为为共同侵权。故本文认为,行政机关明知民事主体侵害他人权益却依然实施相应具体行政行为导致他人损失的,也应承担连带责任。其次,在共同过错说的视角下,有的学者认为民事主体依靠行政机关未尽到审查义务的过失导致他人侵权的,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连带责任。①于博:《论行政民事侵权连带责任及其司法认定》,《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2 期。该观点过于激进,会导致连带责任适用范围过于宽泛,造成行政机关责任不合理增大。同样是一方主体具有一定的管理地位,我们可类比民法典第1197条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规定进行思考,但要注意该规定的立法前提在于大多数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实质性的审查义务,这是让网络服务提供者仅因过错就承担连带责任的现实前提。本文认为,可以是否具有实质审查义务为标准对行政行为进行划分,对不具有实质审查义务的行政机关适用共同过错说的观点来认定“共同”更加合理。
2.分别的行民混合侵权——按份责任。分别的行民混合侵权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和民事主体分别实施各自独立的侵权行为,但造成了同一损害结果。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对于将民法规则适用于行民混合侵权之中都不存在争议。例如,在惠彩芳与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榆横工业区交警大队行政确认案中,交警违法拦车的行为与加害人撞到行人便属于两个独立的侵权行为由于偶然因素而结合在一起的情形,法院也因此判决行政机关与民事主体各自承担20%和80%的责任②参见 (2018)陕08 行终79 号行政判决书。。
3.竞合的行民混合侵权——不真正连带责任或补充责任。竞合侵权行为中的侵权人有的实施直接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有的实施间接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仅具有间接因果关系。因此,这类侵权行为可对应不真正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两种责任形态。③杨立新:《论竞合侵权行为》,《清华法学》2013年第1 期。
(1)必要条件的竞合的行民混合侵权——不真正连带责任。竞合侵权中,从行为为主行为提供必要条件,无从行为之实施、主行为不能造成损害结果的行为形态被称为必要条件的竞合的多数人侵权。主从侵权人于此情形下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其中主侵权行为人为终局责任人。④杨立新:《中国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法律适用指引——中国侵权责任法重述之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 期。必要条件的行民混合侵权行为以“行政机关过失作为行为+民事主体侵权”形态存在。实践中常见的民事主体虚假申请与登记机关错误登记相结合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情形即属于此类。
根据民事理论要求混合侵权的行民主体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具有合理性。首先,必要的竞合的行民混合侵权中,侵权之债和行政赔偿之债的关系满足不真正连带责任发生的构成要件。⑤通说认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一是数个债务的发生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债权人对于债务人分别享有独立的请求权;二是数个债权由于偶然的原因结合在一起的;三是各个债务人对债权人承担同一给付;四是各个债务人之间没有内部分担关系,基于终局责任分担损失。其次,在此情形下,让所有侵权人对外与直接侵权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是对受害人的一种倾斜性的保护,符合侵权责任法和国家赔偿的价值取向;让提供必要条件的侵权人一方对直接侵权人一方造成的损害承担对外连带责任,也与其在侵权行为中的地位和所起到的作用相适应。
当前的司法解释和批复尚未采用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均更倾向于要求侵权人承担按份责任。但无论是现有规定中的行政许可还是行政登记,都需要和民事主体的行为紧密结合才能构成损害;其相互之间甚至存在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难与按份责任“数个行为人各自进行,自己实施自己的侵权行为,客观上没有关联共同”的要件相契合。同时,此种规定实质上是减轻了行政机关的责任,这与行政机关的管理义务和社会地位的优势性质也是不相适应的。
(2)提供机会的竞合的行民混合侵权——补充责任。竞合侵权中,间接侵权人为直接侵权人的侵权提供发生机会的形态被称为提供机会的竞合侵权行为。其中,间接侵权人在直接侵权人无法完全赔偿被侵权人损失时承担与自己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提供机会的行民混合侵权行为以“行政机关的过失不作为+民事主体侵权”的形态存在。谭某等与广东省仁化县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案①参见(2006)韶中法行终字第30 号行政判决书。中狱警没有履行好自己监管义务导致被监管人员人身损害和阆中市公安局拒不履行法定职责案②陈勇、冬妮:《轰动全国的“状告公安不作为”胜诉》,《法制日报》2001年9月19日。中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怠于处理群众的举报均属此类。当前,司法解释和批复对此情形下的责任形态认定仍有分歧,有的采纳补充责任的观点,也有的采纳按份责任的观点。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如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答复》指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财产损失系第三人行为造成的,应当由第三人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第三人民事赔偿不足、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下落不明的,应当根据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但是,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98 条却认为“因行政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该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针对后者,有学者认为其采取的观点是在此情形下,行政机关与第三人(即民事侵权方)应当承担按份责任。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不能通过本条的表述而得出主体之间责任承担的形态。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日本在静冈判决中确定了此情形下行政机关与民事主体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④[日]植木哲:《医疗法律学》,冷罗生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 页。美国的国家赔偿法则认为在公共场合打架斗殴的,警察不参加阻止的,以受害人无法向加害人求偿为前提承担责任。⑤廖海:《中外国家赔偿制度之比较》,《法学评论》1996年第1 期。我国学理上的讨论大都集中在按份责任和补充责任的取舍上,支持前者的学者认为行政机关的补充责任可能使行政机关的责任完全落空,同时会剥夺受害人自由选择诉讼对象的权利。⑥王霖华:《与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混合的行政不作为损害赔偿规则探微》,《法律适用》2008年第9 期。
本文认为,在此情形下让行政机关承担补充责任是最合理的选择。首先,从责任原理上看,与上文的理由相一致,按份责任的适用场合应当是“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中原因力可分的侵权行为”,提供机会的竞合的混合侵权中,行政行为与民事侵权行为的关联性并不允许其适用按份责任。其次,补充责任并不会让行政机关的责任完全落空,这也回应了部分学者的担忧。从国家赔偿法第1 条规定可知,国家赔偿法的价值有二:一是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赔偿;二是对国家机关进行监督和惩戒,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如果民事主体已然将损害全部填补,那么国家赔偿法的第一个目的价值就已经达到了;至于督促和惩戒的目的,可以其他方式去实现,例如批评、建议、处分和处罚等行政内部监督的形式。⑦石佑启主编:《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0 页。
4.构成“第三人侵权”的行民混合侵权行为——补充补偿责任。杨立新教授最早提出“第三人侵权行为”的形态,经过讨论和完善,学者们将其定义为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全部原因,关联人对损害的发生不具备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但与损害之间存在行为、客体或主体上关联的侵权行为。此类行为形态所对应的责任形态有三种,即第三人责任、第三人责任+补充补偿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⑧张力、郑志峰:《侵权责任法中的第三人侵权行为——与杨立新教授商榷》,《现代法学》2015年第1 期。
构成“第三人侵权”的行民混合侵权行为以“行政机关的非过失关联行为+民事主体侵权”的形态存在,通常可见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民事主体提供虚假材料,登记机关已经完全尽到审查义务,依然没能够避免受害人的损失;民事主体提供虚假信息请求行政机关采取紧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机关履行形式审查义务后实施的行为造成受害人损害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 条规定“被告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履行审慎合理的审査职责,因他人行为导致行政许可决定违法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可见,人民法院倾向于采“第三人责任”之观点,即要求民事主体单独承担损害。然而,让行政机关在民事主体无力赔偿时承担补充补偿责任更加符合当前的观念。首先,民法中现有关于第三人补偿责任的设计均以保护被害人利益为出发点,根据行政补偿的结果责任理论可知,行政补偿亦以保护受损害人的权益为基础。①姜明安:《行政补偿制度研究》,《法学杂志》2001年第5 期。在构成“第三人侵权”的行民混合侵权中,让行政机关承担补偿责任符合其价值追求。其次,让行政机关承担补偿责任契合其社会地位。行政机关的社会功能与作用也决定了其在此情况下承担补充补偿责任的合理性。行政机关因为其行政属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将其视为一种权威,对其给予足够的信任。人民因信赖公权力措施而有所行动时,如因该措施的事后变动而受到损失者,国家即应给予补偿。②王锴:《我国国家公法责任体系的构建》,《清华法学》2015年第3 期。再次,行政机关在此情形下承担补偿责任的设计,符合国家补偿的发展方向。联合国《从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认为在行政机关与损害结果毫无关系时,国家依然应给予处于困境的受害者以救济性补偿。③该宣言第12 条规定“当无法从罪犯或者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当设法提供金钱上的补偿。”当然,此类规定往往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和福利国家的“专利”;不过,我国虽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但结合本国国情不断改良国家补偿的适用范围也亦应成为一种共识。由此,让行使非过失关联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符合我国国家补偿的发展方向。
四、救济:诉讼程序之设计
混合侵权案件涉及国家赔偿和民事赔偿两类诉讼程序,由于现有立法未对此类案件的救济程序做出及时回应,导致此类案件在处理程序上存在混乱现象。
(一)当前的审理模式
在行民混合侵权案件的诉讼程序方面,实践中各地的做法并不统一,整体上有分案审理和合并审理两种模式。
1.分案审理模式。分案审理模式要求在审理混合侵权案件时有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两种程序的参与,分别处理国家赔偿和民事赔偿的问题。
(1)两种不同的分案审理模式。未规定顺序的分案审理模式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模式,其特征在于并不强行规定被侵权人请求损害赔偿的顺序。基于原告之选择,两种诉讼程序有三种启动模式: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同时提起、先行政诉讼后民事诉讼、先民事诉讼后行政诉讼。
有学者认为国家赔偿金来源于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将国家赔偿责任先于普通公民承担的做法难言合理,故设计出“民事赔偿先行,行政赔偿有条件并列”的程序,要求受损害人只能先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在审理时也仅仅关注民事侵权部分。在民事裁判之后,若认为行政机关有责任的,则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的结果受到民事诉讼结果的影响。实践中,已有案件在审理中采用了该做法。④参见(2018)皖行赔终98 号行政判决书。
(2)分案审理模式之评析。规定顺序的分案模式较之于未规定顺序的分案审理模式而言,虽以牺牲当事人处分诉权的自由来获取程序衔接上的稳定,却依然难谓一种合理的处理方式。首先,分案审理的设计让两个不同的审判组织对同一个案件进行事实和法律的审理,难免造成审判结果的冲突。在北京世纪环宇文化发展中心等与兴隆县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赔偿纠纷案⑤参见(2012)冀行终字第70 号行政判决书。中,发生在前的民事诉讼判决民事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但其后进行的行政诉讼中法院却发现登记机关亦有违法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这种由于程序分立导致的事实认定混乱,极大地损害了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其次,分案审理的设计还会造成案件处理的冗杂。在上文所举的案例中,一审判决本身已经对行民侵权人的责任进行了认定,二审却又以行政诉讼不该处理民事纠纷为由撤销了一审判决,当事人不得不再次重新进行民事诉讼然后再寻求国家赔偿。此举既徒增了当事人的诉累,又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①参见(2018)皖行赔终98 号行政判决书。最后,所谓“分别审判”在本质上其实是不存在的。行民主体侵权行为的紧密结合是混合侵权行为最大的特征,根本无法在因果关系认定中做到完全分立。例如,在王艳世与长春房地有限责任公司等房屋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案中,法官在判决中虽只让行政主体承担了责任,却在说理部分明确提及了民事主体的责任份额。②参见(2018)吉01 行再1 号行政判决书。多数案件均是如此,表面上在判决阶段实现了分别审理,但实际审理过程却依然未逃过合并审理的思维。由此,所谓“民事诉讼过程中只关注民事事实和因果关系的认定”的审判方式本身并不符合实际。
2.合并审理模式。合并审理模式主张适用单一的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民事诉讼程序对混合侵权案件进行一次性审理。例如,在北京市楼道起火导致居民死亡索赔案中,法院在审理行政赔偿案件时依职权添加民事侵权人为被告,并在同一判决中认定二者各自承担责任的份额。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典型案例(第二辑)之五》,http://gfggi66f6a8ad06ba47d9sco q66oqx0wk56f6n.fbch.oca.swupl.edu.cn/pfnl/a6bdb3332ec0adc458f3a240602b13e1b9f3976d2b069eadbdfb.html?keyword=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经营管理中心等与马某等其他行政管理赔偿纠纷案,访问日期:2022年5月24日。在另一起案件的审理中,法院依职权添加相关民事主体为第三人,判决民事主体和行政主体之间承担连带责任。④参见(2015)延行初字第150 号行政判决书。合并审理模式由同一审判机关对案件进行审理,保证了事实和法律认定的统一,且毕其功于一役,在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的同时节约了司法资源。
但是,混合侵权的合并审理虽有各种裨益,却苦于没有现实程序规则的支撑。行政诉讼法第61条虽有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但当前的做法通常要求当事人须主动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且封闭式地将适用范围限定于特定的行政作为行为,⑤张光宏、毕洪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 页。难以为合并审理提供充足的合规性。
(二)混合侵权案件合并审理制度的设计
笔者认为,应当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为基础,设计混合侵权案件的诉讼程序。
1.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适用范围的扩张。传统的行政附带民事赔偿制度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审判机关有权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⑥李战、蒋文玉:《论我国民事行政关联案件诉讼程序之重构——确立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的一体化模式》,《河北法学》2014年第2 期。该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其合理性来源于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之间的关联性,本质上是行政审判庭跨越法院对于审判权的划分,涉足于民事案件。混合侵权中的赔偿纠纷以行政主体为当事人之一,意味着其与行政诉讼之间更具关联性;相较于传统的仅以效率为目的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明晰事实方面,混合侵权案件也更有利用该制度的必要。2013年发布的行政法诉讼法修正案指出“因具体行政行为影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引起的民事争议”均可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同时,也存在应当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留有更大的适用余地的观点。故此,将混合侵权案件所涉赔偿纠纷置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范围内,由行政审判组织进行合并审理,符合制度的目的价值,具有合理性。
2.合并审理制度的具体展开。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为基础意味着在审理过程中案件由行政审判机关一并处理,而对于当事人寻求救济的整个过程来说,还应当考虑行政赔偿特殊的“双重救济制度”。
国家赔偿法第9 条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9 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确定了“双重救济制度”,即在请求行政赔偿时,当事人可以选择单独式和一并式的救济模式。其中,单独式救济模式中的司法救济要以当事人向行政机关提出赔偿作为前提。该制度的目的在于加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有利于受害人行使赔偿请求权。⑧肖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 页。作为行政赔偿程序的特征,该制度设计应当保留。
根据当事人做出选择的不同,混合侵权的双重救济制度可按以下情形展开:一是当事人选择先向行政机关提起赔偿。如果当事人选择向行政机关或以行政复议的方式请求赔偿,则采取国家先行赔偿的观点可以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防止行政机关和民事主体逃避赔偿责任。①张红:《行政赔偿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之关系及其处理》,《政法论坛》2009年第2 期。具体而言,若行政机关同意赔偿且当事人损失因此得以填补的,当事人无权再向民事侵权主体请求赔偿;若行政机关没有同意赔偿或者是赔偿数额无法弥补当事人损失的,当事人有权转向民事诉讼程序解决问题。在行政机关赔偿之后,应当赋予当事人向其他民事侵权人追偿的权利。行民主体之间承担按份责任和连带责任时,行政机关得在自己责任份额的范围内向民事主体追偿;如二者之间承担补充责任或不真正连带责任,行政机关则可向民事主体追偿全部赔偿。
二是当事人选择通过诉讼形式请求赔偿。如果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行政审判庭在处理赔偿问题时发现属于混合侵权案件的,可依职权追加民事侵权人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对二者的责任进行一并认定与判决。如果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民事赔偿,民事审判庭在审判过程中发现属于行民混合侵权情形的,则应当将案件移交至行政庭审理。法院有权依职权追加相应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