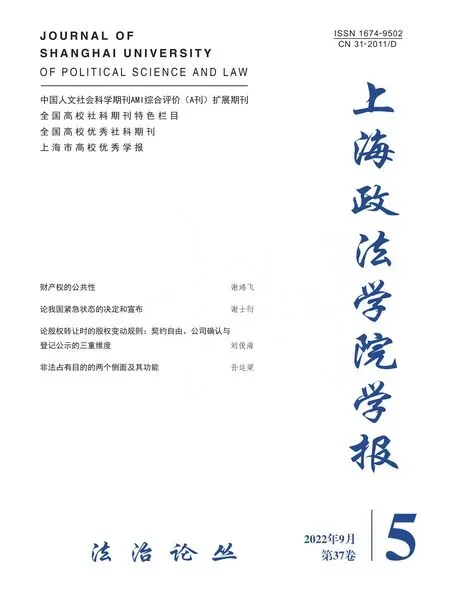非法占有目的的两个侧面及其功能
2022-02-05孙运梁
孙运梁
一、引 言
不同于民法中的占有概念,刑法学中使用的占有概念是多义的,刑法学者起码在三种意义上使用占有概念:第一种是作为财产罪保护法益的占有;第二种是非法占有目的中的占有;第三种是用来解释盗窃、诈骗、侵占等财产罪客观构成要件的占有。①参见车浩:《占有概念的二重性:事实与规范》,《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
虽然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盗窃罪、诈骗罪、抢劫罪等取得型财产罪需要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刑法学界与实务界一般认为,这些取得型财产罪都需要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且,非法占有目的不属于这些财产罪的故意内容,而是一种独立的主观要素,理论上称之为非法定目的犯的目的(超过的主观要素)。②参见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I》,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页。
日本刑法与我国刑法一样,没有对取得型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予以明文规定。几十年来,日本刑法学者对财产罪的主观目的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教义学研究,产生了丰富、细致的理论成果,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有意义的研究素材和借鉴对象。本文试图在梳理日本刑法理论中有关非法占有目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非法占有目的两个侧面的具体内涵及其功能,期望为我国在司法实务中判断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提供可以参考的理论工具。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两个侧面)
在日本刑法中,占有与领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领得更接近于取得、获取、据为己有的意思①参见[日]西田典之、桥爪隆:《日本刑法各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55页。,占有具有持有、支配的意思。“非法占有目的”在日文原文中是“不法领得的意思”,为了讨论交流的方便,也基于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上的表达习惯,我国学者一般将其翻译为“非法占有的目的”。由于盗窃罪是最为常见、典型的取得型财产罪,也由于盗窃罪规定在日本刑法财产罪之首,所以,日本学者主要在盗窃罪中讨论非法占有目的。当然,非法占有目的是财产罪的共同问题,在研究其他财产罪的过程中,这些理论成果都是适用的。
即使行为人转移了他人所占有的财物,也不是说就能马上成立盗窃罪,还要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概括地讲,非法占有目的就是指把他人所有(合法占有)的财物任意地据为己有的意思。从根本上说,盗窃罪侵犯了他人的所有权或者其他本权(如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这也决定了非法占有目的是该罪的必要要素。盗窃罪的主观要件:首先要有对该客观构成要件事实即窃取他人的财物具有认识,这是盗窃的故意;其次还要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日本判例、理论通说所支持的观点。换言之,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要成立盗窃罪,不但要有主观故意,还要有非法占有目的这种特殊的主观要素。有关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日本大审院1915年5月21日的判决(大判1915年5月21日刑录21辑663页教育敕语案)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代表性判例。该判决指出:“为成立本罪所必要的故意,仅仅对法定构成要件的事实具有认识还不够,还必须具有将该物非法据为己有的意思。因此,所谓非法占有的意思,无非就是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物作为自己所有的物,按照其经济用途进行利用或者处分的意思。”②参见[日]大谷实:《刑法各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在该案中,行为人为了陷害校长而将教育敕语隐藏起来,法院根据上述观点认为行为人欠缺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否定了盗窃罪的成立。这种判决观点也得到了日本最高裁判所的继受。
这样,通过上述判例,非法占有目的就有了明确的定义,即“排除权利人,将他人之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并按照该物的经济用途加以利用、处分的意思”。该定义有前后两段:前段是排除权利人,将他人之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的意思,即像自己的所有物那样处置他人的物,这被概括为排除意思;根据侵害占有的意思达到何种程度,若擅自暂时使用行为侵害程度轻微,则会被排除在盗窃罪成立范围之外,即排除意思存在区分不具有可罚性的使用盗窃与具有可罚性的盗窃之机能,这被称为可罚性限定机能。后段是按照该物的经济用途进行利用或者处分的意思,即利用意思;盗窃罪的成立以取得财物的利用可能性为占有侵害的目的,而毁坏财物罪以妨害财物的利用为目的,利用意思具有区分二者的机能,这被称为犯罪个别化机能。①参见[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206页。可以说,之所以要求盗窃罪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其意义正在于能将盗窃罪与不可罚的暂时使用相区分、将盗窃罪与毁坏财物罪相区分。
关于非法占有目的,存在必要说与不要说二者之间的对立。前者认为,在盗窃罪等取得型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素是不可缺少的;后者认为,就取得犯罪的主观要素而言,具有故意就够了,不必再要求非法占有目的。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日本刑法学界有以下四种观点②参见[日]西田典之、桥爪隆:《日本刑法各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80-181页。:学说1,要求同时具有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即排除权利人如同合法占有者那样支配他人财物的意思,以及遵循财物的经济用途(本来用途)加以利用、处分的意思;学说2,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只需有排除意思即可,即将自己作为所有者来支配他人财物的意思,据此,暂时使用他人财物行为不存在可罚性,但在具有毁坏他人财物目的时,便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学说3,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只需有利用意思即可,即通过利用、处分他人财物而获取某种经济性利益的意思,据此,一般情况下使用盗窃是有可罚性的,盗窃罪之所以区别于毁坏财物罪,是因为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学说4,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认为在盗窃罪的主观要件上,不必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只要对占有侵害(转移)具有认识就足够了。在不要说内部存在两种观点:一是立足于本权说的立场,认为存在占有侵害的毁弃、隐匿行为成立盗窃罪;同时使用盗窃与盗窃罪的区别在于可罚的违法性问题,即在于侵害占有的程度等所决定的排除权利人的可罚性问题。二是从取得危险犯的角度来理解盗窃罪,要重点考察的是窃取行为所存在的取得的客观危险和行为人对此的认识(犯罪故意),这样非法占有目的就被消解了。③参见[日]松宫孝明:《刑法各论讲义》,王昭武、张小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页。不要说主张的主要理由④参见[日]山口厚:《问题探求 刑法各论》,有斐阁1999年版,第110页。是:首先,从理论上来说,非法占有目的与盗窃罪的保护法益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即使在盗窃罪的保护法益上采纳本权说,也不一定就会主张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其次,非法占有目的在内容上并非很明确,比如,如果认为盗窃罪、侵占罪均需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其在内容方面便有所不同;最后,即使要求盗窃罪的成立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也不一定就能明确而且适当地界定盗窃罪的处罪范围。
按照学说1的观点,在将他人财物转移到自己占有之下而加以暂时使用的场合,行为人主观上不存在排除权利人而像合法占有者那样予以支配的意思,因此不成立盗窃罪;在出于毁坏的意图而夺取他人占有的财物的情形中,行为人不存在对财物予以利用、处分的意思,因此也不成立盗窃罪。按照学说2的观点,在暂时使用的场合,由于行为人不存在排除权利人而像合法占有者那样予以支配的意思,因此不受处罚。按照学说3的观点,在出于毁坏的意图而取得他人占有的财物的时候,因为行为人不具有利用或者处分的意思,所以否定盗窃罪的成立。总体来说,在盗窃罪与毁坏财物罪的区分上,学说1、学说3与学说2、学说4之间存在对立;在使用盗窃的不可罚性问题上,学说1、学说2与学说3、学说4之间存在对立。(与德国刑法不同,日本刑法未对非法占有目的作出明文规定。所以,在解释论上无论采取哪一种学说都是可能的。对于财产罪,我国刑法也未明文要求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所以评析日本刑法理论上的各种观点和审判实务的做法,对于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审判实务来说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
虽然上述学说3认为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仅包括利用意思,学说4主张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但是它们也承认有些使用盗窃没有可罚性,它们并不认为只要行为人取得财物占有就能成立盗窃罪。这里发挥作用的是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即盗窃罪的处罚范围不包括轻微地侵犯占有、所有权的行为。上述学说1要求非法占有目的同时具备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学说2只要求存在排除意思,在划定盗窃罪的成立范围上二者试图以非法占有目的这个要件来实现。与之不同,后两种观点试图通过客观的妨害利用程度这一视角来实现这个目的。然而,在盗窃的场合,只要行为人取得占有便构成盗窃罪的既遂,试图在盗窃罪的成立与否这个环节,让既遂之后的妨害利用程度起决定性作用,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认为只要妨害利用未达到可罚性程度,盗窃罪便不能构成既遂,则会导致既遂时点处于不确定状态。所以,我们不赞同学说3、学说4的观点。
为了克服后两种学说的缺陷,就应当从以下方面来思考:一方面,从可罚的违法性角度出发,要求具有达到可罚性程度的妨害利用;另一方面,基于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在行为当时便考虑这种利用妨害,将这种指向妨害利用的意思作为犯罪的成立要件之一。这样,达到可罚性程度的妨害利用的意思,即排除权利人利用的意思(排除意思),就成为区分不具有可罚性的暂时使用行为与盗窃罪的必要要件。从本质上来说,排除意思就是试图造成可罚的法益侵害(妨害利用)的意思,它成为判断法益侵害之危险的基础素材,所以被视为主观违法要素。①参见[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233页。当然,依靠学说2不能区别盗窃罪与毁坏财物罪,因为毁坏财物的人也存在着排除意思,也就是排除权利人利用财物、将他人的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随意进行支配,因此也是有缺陷的观点。日本判例与学界支持学说1的力量占主流地位,我们亦从之。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因为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包含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两个侧面,因此,在认定具体案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存有疑问的场合,不要笼统地、概括地判断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而要分清楚在这个案件中是排除意思存有疑问,还是利用意思存有疑问。②参见张明楷:《侵犯人身罪与侵犯财产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6页。当然,一般来说,既在排除意思的认定上有分歧又在利用意思的认定上有分歧的情形是很少的。
三、非法占有目的与财产罪保护法益之间的关系
许多观点认为,如何理解非法占有目的在学说上的争论,正是盗窃罪等取得型犯罪的保护法益在理论上争论的反映,也就是说,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必要,与盗窃罪的保护法益论之间存在着理论逻辑上的关联。具体来说,基于本权说的立场,取得型财产罪的主观要件,不但要求认识到侵害占有的故意,而且还必须具备认识到侵害本权的非法占有目的;除了由于恶意情形下的取得时效问题,作为观念性权利,所有权是持续存在的,单纯的侵害占有并不会危及到所有权的存在本身,如此一来,排除意思即指向所有权侵害的意思就有存在的价值,所有权侵害的要素便通过排除意思进入构成要件之中。与之不同,基于占有说的立场,在取得型财产罪的主观要件上,只要对转移他人财物的占有即对占有侵害存在认识就够了,所以其采取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是理所当然的。①参见[日]西田典之、桥爪隆:《日本刑法各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81页。从逻辑上来说,学说1(排除意思+利用意思)、学说2(排除意思)的主张与本权说的立场是一致的,学说4(不要说)的主张与占有说的立场是一致的,学说3(利用意思)的主张则与本权说、占有说的争论无直接关联②参见[日]大谷实:《刑法各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原因在于,学说3与取得财产罪和毁坏财物罪的区别密切相关,其目的在于为贪利型财产罪的较重处罚提供根据。
日本有学者认为:倘若在盗窃罪、诈骗罪的保护法益上采纳本权说,则会支持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倘若采纳占有说,则会赞同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从实际情况来看,虽说所有权及其他本权才是盗窃罪最终的保护法益,但是盗窃罪的保护法益也包括相应合理的占有,倘若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会侵犯他人对财物的合理占有却仍然实施窃取行为,则会肯定盗窃罪的成立,所以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必要。③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然而,虽然判例从支持本权说转而支持占有说,但始终赞同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虽然有学者在保护法益上主张本权说,但在非法占有目的问题上却支持不要说。综上可见,有关非法占有目的的学说对立与盗窃罪的保护法益理论分歧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④同注①。原因在于:首先,保护法益与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不同层面、不同范畴的问题,前者是关涉盗窃罪的客体范围问题,后者是关涉侵害客体的行为之属性问题。⑤参见[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页。其次,即使是采纳本权说的立场,一旦行为侵害了他人对财物的占有,则对该财物的使用、收益、处分等本权机能也会受到损害,所以再额外地要求存在侵害所有权的意思就无必要。再次,即使支持占有说的见解,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占有侵害行为应在何种范围内以盗窃罪进行评价,在这个意义上,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必要、其内容为何就值得考察。
虽然是否需要非法占有目的与盗窃罪的保护法益论之间并没有理论逻辑上的必然关联,但是,非法占有目的中“非法”的判断却与保护法益有关联。从理论定位上来说,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要素,但是在判断是否非法的时候,却不是根据行为人的内在想法,而是要根据客观标准进行判断。具体而言,应结合财产罪的保护法益来认识和判断非法占有目的中的“非法”,也就是说,一旦侵犯了盗窃罪的保护法益,就可以说行为意图具备非法性质,即行为人的占有目的存在非法性。我国学者认为,通常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存在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但客观上欠缺占有他人财产的合法根据,或者欠缺使他人转移财产于行为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根据,那么就可以说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此处的合法根据,一般是指在财产法上存在某种依据,当然也要兼顾刑法上的一些特别规定。①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250页。例如,没有民事权利或者民法上的其他根据,却转移他人财产的,就能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占有目的具有非法性。又如,行为人在民法上对某财物拥有所有权,他人基于某种民事权利合法占有该财物,行为人将该财物窃回的,也侵害了盗窃罪的保护法益,行为人的占有目的也是非法的。不同的是,行为人所有的特定物被他人非法占有,行为人秘密取回的,由于盗窃罪的保护法益未受到侵犯,所以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
四、非法占有目的侧面I:排除意思(盗窃罪与不可罚的使用盗窃的区别)
在剥夺(排除)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意义上,盗窃罪具有实害犯性质。同时,盗窃行为侵犯了被害人对财物的利用可能性,这是一种实质性法益侵害,盗窃罪的处罚根据也包含法益遭受侵害的危险性,在此意义上,盗窃罪又具备危险犯的性质,而且,在判断危险性有无的时候,必须考虑排除意思,因此包含排除意思的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违法要素。正如行为人的犯罪计划在判断未遂犯的具体危险性时能够发挥作用,在判断盗窃罪的危险性时,行为人转移占有时伴有的目的或者计划也是判断材料,必须予以考量。在为侵害财物的利用可能性之危险性奠定基础的意义上,排除意思是必备要素,易言之,排除意思是作为主观违法要素在施展功能。②参见[日]桥爪隆:《论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的目的》,王昭武译,《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2期。从本质上来说,盗窃罪侵犯了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在其主观要件上,不只要求有侵害占有的意思,还要有排除权利人、像所有权人那样支配财物的意思。在暂时使用的场合,虽存在占有侵害,但却没有内含上述意思的非法占有目的,所以不构成盗窃罪。上述支配意思作为主观要件,正是为侵害、威胁所有权及其他本权的行为奠定了违法性基础,所以它是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也是主观的违法要素。暂时的、轻微的侵害占有行为不具备这种支配意思,不会产生侵害本权的危险,所以不成立具有可罚性的盗窃罪。
擅自暂时使用他人财物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他人对财物的占有,但一般只是出于短暂使用之后即返还的意图。学界和实务上一般认为这种行为不可罚,不以盗窃罪加以处罚,这里适用的是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也就是对于损害法益程度轻微的行为,不必使用刑罚进行处理。例如,未经允许使用他人自行车去超市买烟后立即归还的,擅自借用他人书籍写作论文之后返还的,等等。上述行为均仅为短暂借用而不是据为己有,并不是无视他人所有权的行为。因为缺少非法占有目的,所以不被认定为盗窃罪。主流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内含排除权利人、将他人之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来加以利用的意思,在短暂使用的场合,行为人的利用意思没有达到排除权利人的程度,或者说不具备达到了排除权利人程度的利用意思③参见[日]西田典之、桥爪隆:《日本刑法各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85页。,由此否定了盗窃罪的成立。可见,非法占有目的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即从主观方面否决了擅自短暂使用成立盗窃罪。在教义学上,使用盗窃是否成立盗窃罪存在理论争议,同样,在诈骗罪、抢劫罪中也存在短暂使用行为是否成立财产罪的问题。
从非法占有目的的定义表述来说,如果行为人的想法是使用他人财物之后再予以归还,则其并没有取得他人财物据为己有的意思。但是,现代社会中汽车等交通工具具有很大的使用价值,经常发生擅自使用他人汽车去实施违法犯罪的案件,往往导致汽车车体或功能受损,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妨害车主的使用、处分。与对其他财物的擅自使用行为相比,对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擅自使用行为的可罚性较高。对于擅自使用汽车等重要财物的行为如何处理,德国、瑞士等国是通过立法论来解决的①参见[日]松宫孝明:《刑法各论讲义》,王昭武、张小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页。,即擅自使用行为不成立盗窃罪,而是在立法上设置了另外的法定刑比盗窃罪轻的罪名。(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322条规定,未经占有人的同意,暂时使用他人的汽车、航空器以及其他装备有机械动力的交通工具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10万日元以下罚金或者拘留。这样,对于非法使用汽车等的行为,草案以轻于盗窃罪的刑罚予以处罚。草案的本意是对盗用汽车等的行为加以广泛处罚。)
与立法论路径不同,日本审判机关试图以解释论路径来解决问题。如何评价暂时使用他人的交通工具的行为,判例起初的态度是,暂时使用但有事后返还意思的,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这种所谓的使用盗窃不具有可罚性,从而排除了盗窃罪的成立。相反,擅自使用且存在事后毁坏或抛弃的意思的,能够认定具有排除意思,因为行为人存在持续侵犯财物的利用可能性的意思,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该种行为成立盗窃罪。例如,针对擅自骑走他人自行车的行为,大审院认为(大判1920年2月4日刑录26辑26页),行为人占有他人的自行车时,倘若只是基于暂时使用的意思,则不成立盗窃罪。也有下级裁判所的判例持相同态度,行为人带有2至3小时归还的想法,擅自骑走了他人的自行车,判例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京都地判1976年12月17日判时847号112页)。该案中行为人实际上未归还,深夜,该行为人出于奸淫某女的目的,擅自使用他人的自行车,后因被抓获而没有归还,能够查明,行为人原本打算使用2到3小时之后即归还。上述判例表明了这样的立场,即在暂时使用他人财物并且存在归还意思的情况下,只是暂时地妨害他人使用,没有否定他人的所有权,所以不能成立盗窃罪。②参见[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付立庆、刘隽、陈少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4页。与之不同,在使用时不具有返还的意思而是有用后随意丢弃的意思,那就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例如,大审院在1920年2月4日的判决中认为,擅自使用自行车的行为,出于短暂使用的意图,但有用后损坏、丢弃的意思,这已经是持续地妨害他人使用,而不再是暂时地妨害使用,应被认定为盗窃罪。类似的判例,行为人实施了抢劫伤害行为,基于用后扔掉的意思,擅自使用他人船只到河对岸,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行为人就使用船只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成立盗窃罪(最判1951年7月13日刑集5卷8号1437页)。
事实上,对于短时间内擅自使用他人财物的行为,判例的主流做法是,并不特别强调有无返还意思,即使具有返还意思,也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样的判例是很多的,举例如下:(1)未经车主同意,从上午7时至次日下午1时,有18个小时驾驶该汽车,之后归还原处(东京高判1958年3月4日高刑11卷2号67页)。(2)夜间擅自使用他人汽车,早上即归还原处,反复多次实施这样的行为,判例认为,擅自动用他人车辆来搬运赃物,或者出于该种目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四处行驶,即使用后将车归还原处,也能认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高裁1968年9月17日判时534号85页)。(3)为了去兜风,擅自驾驶他人的汽车,大约4小时之后发生交通事故(札幌高判1976年10月12日判时861号129页)。(4)深夜,未经车主同意,从停车场将汽车开走,在市内道路上驾车闲逛,大约4小时之后因无证驾驶被逮捕,被告人开走汽车时,原本计划几小时后即开回原处(最决1980年10月30日刑集34卷5号357页)。在考察上述案件时,犯罪对象是汽车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驾驶车辆是有较高风险的活动,更何况是擅自动用他人车辆,容易发生因操作失误而损坏车辆的情况,再加上汽油等损耗,即使是短时间驾驶,也会使车辆价值受损。①参见[日]桥爪隆:《论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的目的》,王昭武译,《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2期。所以,即使行为人原本打算在短时间内驾驶他人车辆,也会产生车辆价值或者效用受到侵害的高度风险,也能肯定行为人具有排除意思。对于上述案件,判例都认为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目的。②有学者认为,结论就会因是否属于价值较高的物品、所消费的价值大小(汽油的消费等)而有所改变。其结果是,与汽车相比,自行车更容易被认定为使用盗窃(不可罚)。但是,与完全打算据为己有的盗窃汽车情形相比,对于盗用汽车行为适用相同的法定刑,这并非一种妥当均衡的做法。因此,该问题最终仍应通过立法论来解决。参见[日]松宫孝明:《刑法各论讲义》,王昭武、张小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页。(5)利用磁铁从他人的游戏机中吸取“弹子”,目的是用来兑换奖品(最决1956年8月22日刑集10卷8号1260页)。(6)出于复印的目的将秘密资料拿出,复印后大约2小时,又将该资料放回原处。秘密资料的经济价值体现在其所记载的内容(信息),行为人意图复印资料之后提供给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公司。复印秘密资料的内容并获取该信息的意思,就可以说是非法占有目的(东京地判1980年2月14日刑月12卷1=2号47页)。③也有学者认为,为了不当获取秘密信息,出于短时间内拿走秘密资料,用于复印然后返还的意思的,会因为信息的泄露而消耗或侵害其价值。如果具有泄露信息的意思,虽然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消耗其价值的危险,然而,连这种物被返还之后所发生的间接侵害,也要纳入盗窃罪的保护对象之列,这究竟是否妥当,应该说,这原本就具有值得怀疑的余地。参见[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对于这类案件,对有关信息的利益侵害受到重视和强调,而妨害使用的程度则并非重要,判例认定盗窃罪的根据在于,资料所记载的信息受到了侵害。秘密信息的价值在于其未公开性,信息的泄露会造成其价值降低乃至消失,所以,复印秘密资料并泄露其信息的行为,就不仅仅是一时使用,而是存在排除意思。(7)供公众查阅的居民基本情况微缩胶卷放置在区政府,行为人借出后复制,然后返还(札幌地判1994年6月28日判夕838号268页)。(8)从超市将商品私自拿出,然后假装退货,目的是获得等额退款(大阪地判1988年12月22 日判夕707号267页)。对于上述案件,判例认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肯定成立盗窃罪。
可见,对于不可罚的使用盗窃的范围,上述判例持限制态度。即使行为人具有返还的意思,也不一定能否定非法占有目的。排除权利人对财物的使用、处分的意图,达到了与盗窃罪的可罚的违法性程度相适应的程度,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且,不要求存在永远保持该物的经济利益的意图。④参见[日]大谷实:《刑法各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如果有消耗体现在物上的价值利用意思,即便有事后返还的想法,也能认定存在排除意思,成立盗窃罪,因为已经造成对构成所有权内容的利益的重大侵害。⑤参见[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例如,擅自使用他人的一次性剃须刀,用后即返还;出于超额投票的意图,盗走选票;出于在剧场使用看戏的目的,窃取该剧场仅限当日出售、使用的戏票。
虽然在占有他人财物时只有暂时使用的意思,但是在同时侵害了所有权及其他合法权利的时候,便不是暂时使用而已,即使支持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的见解,也会肯定取得型犯罪的成立。原因在于,如果暂时使用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则行为人就具有了排除权利人、将他人之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加以支配的意思,从而具有了非法占有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对某财物没有所有权或其他合法权利,就不能加以使用,但行为人却产生了支配意思,当成自己的物进行利用。根据一般社会观念,在使用他人的某些财物时,需要办理借用手续,征得他人同意,否则不能随意使用,但行为人仍然擅自使用,就有可能认定其存在非法占有目的。①参见[日]大谷实:《刑法各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即使在那些暂时使用他人财物之后予以返还的案件中,我们也要认识到,行为人已经打破了被害人的占有,而将财物转移到自己占有之下。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可罚的权利人排除意思,在判断这种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时,不能将有无返还意思作为标准。在现代社会中,财物的使用价值具有重要性,在暂时使用的场合理解排除意思时,要注意考察行为人是否存在实施在通常情况下不被权利人所容许程度或者形式的利用行为的意思。②参见[日]西田典之、桥爪隆:《日本刑法各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88页。在具体判断时要坚持综合考量,不仅要看使用时间的长短,有无归还的意思,还要评估擅自使用行为对权利人产生的损害以及损害的可能性。
如果行为人具有侵犯相当程度的利用可能性的意思,即使有事后返还的想法,也能认定法益侵害的危险达到了可罚程度,这时能认定排除意思的存在,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在判断可罚性时,下述因素均值得考虑:权利人利用财物的可能性或者必要性的程度③例如,研究生考试之前的教材,对于考生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利用的必要性;深夜停放在家门口的电动自行车,对于车主来说利用的必要性明显要低。可以说虽然都是暂时性使用,但前者行为的侵害程度要高。、行为人计划使用或者妨害利用的时间、财物的价值大小等等。财产权是国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实现其经济目的、社会目的都离不开财产,可以说,财产、财物是被权利人利用来达到其某种目的的手段、工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经常说财产保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对权利人利用财产进行保护。对财产的利用,不仅指对物质本身的利用,更重要的是,对物质价值的利用。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现在评判短时间使用他人财物行为之可罚性的时候,就不再那么重视使用时间长短、有没有归还意愿,而是要特别注意财物是否有重大使用价值、对权利人的利用可能性的妨害达到了什么程度。④参见张明楷:《诈骗犯罪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07页。对于那些使用权受到特别重视和保护的财物,即使只有短时间使用的意愿,也可能被认定为盗窃罪。例如,出于驾车兜风的意思,擅自开走他人的汽车,由于汽油的消耗、轮胎的磨损等损耗,可以肯定盗窃罪的成立。
考察日本判例对于使用盗窃的态度,会发现后期的判例倾向于认定使用盗窃成立盗窃罪。与之相应,学说上认为原则上使用盗窃有可罚性、不必要求非法占有目的的见解,也发展为一种有力观点。在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看来,像擅自骑行他人放在广场上的自行车绕广场一圈的行为,并非值得处罚的侵害占有行为,质言之,应依据在客观上多大程度妨害了财物的利用来判断暂时使用行为是否可罚。⑤同注①。支持不要说的学者也不是主张所有的暂时使用行为都因可罚而成立盗窃罪,对于客观上妨害利用程度轻微的情形,认为不存在占有侵害,或者不存在可罚的违法性,从而否定了盗窃罪的成立。从理论逻辑上说,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以及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只包含利用意思的观点,会主张只要占有了他人财物加以使用就能成立盗窃罪,擅自暂时使用行为都应当成立盗窃罪。但实际上,它们也会将不可罚的暂时使用行为排除在盗窃罪之外,也会重视妨害利用的客观程度问题。
但是,它们的主张存在一些疑问:(1)擅自使用他人财物时,占有已经发生了转移,所以不能否定存在着占有侵害。(2)要强调取得占有之后妨害利用的客观程度,在理论上有难以自洽之处。原因在于,盗窃罪属于状态犯,判断擅自使用行为是否成立盗窃罪,只能根据占有取得当时的事实;对于事后的妨害利用客观程度(对权利人的排除程度)是否达到可罚的违法性,也要根据取得占有当时的主观意思来判断,这样才不违背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质言之,由于盗窃罪的状态犯属性,在确定暂时使用行为可罚性的时候,必须结合转移占有时的事实来考察,必须结合该时点的意思内容来做判断。只有在转移财物的时点具有排除权利人对财物的使用的意思,且达到了与盗窃罪的可罚的违法性相适应的程度,才能成立盗窃罪。可见,要将不可罚的暂时使用区别于盗窃罪,最终的判断标准还是要看有无排除意思,这是与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利用意思说所不同的。在控制使用盗窃的处罚范围上,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违法要素发挥作用,是不可缺少的。①参见[日]西田典之、桥爪隆:《日本刑法各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87页。(3)对于盗窃罪来说,转移财物、取得占有就构成既遂,在既遂以后再来考虑妨害利用的程度,试图以此来“反制”盗窃罪成立与否的判断,这是不可行的。而且,认为只要妨害利用未达到可罚性程度便不成立盗窃既遂,也会使得既遂时点游移不定,所以不能赞同这种观点。要让既遂之后的事态在犯罪成立与否的阶段发挥作用,就只能在行为当时指向这种事态的意思内容中来考虑。可以说,包含排除意思这种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是不可缺少的。②参见[日]山口厚:《问题探求 刑法各论》,有斐阁1999年,第117页。那种使用时间很短、财物价值不大的情形,行为产生的法益侵害非常轻微,通常不会被作为犯罪来处理。具体来说,在占有转移的时点,如果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只是轻微地妨害权利人使用财物,那么行为人就没有排除意思,这种行为只是轻微的暂时使用,并不可罚,因此排除意思起到了限制入罪的机能。③参见[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付立庆、刘隽、陈少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0页。(4)倘若认为,只有侵害了组成所有权内容的所有利益才成立盗窃罪,则另当别论。④按照这种理解,在将赃物返还的情形中,就没有侵犯返还请求权,所以凭借返还意思就能否定非法占有目的。在毕竟没有否定所有权这一意义上,这似乎有道理。但是,这样一来,只要在窃取他人财物的时候做好了损害赔偿的准备,就很容易否定盗窃罪的成立。而且,不论多长时间侵犯了利用可能性,只要有返还的打算,就不构成盗窃罪,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同注①。倘若认为,只要侵害了属于所有权重要内容的利用可能性,就产生了成立盗窃罪所要求的法益侵害,那么就要采纳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将取得占有之后对利用可能性的侵害程度(妨害利用程度)纳入可罚性评价的对象,正是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盗窃罪成立要件的意义所在。⑤同注②,第117页以下。具体来说,这里是排除意思在起作用,也就是将对利用可能性的侵害程度提前到行为当时来考虑,指向这种侵害的意思即排除意思。这样取得占有之后的妨害利用程度问题就得到了理论安置,排除意思正提供了容纳的场所。
在排除意思的教义学理解上,德国的理论学说对我们的借鉴意义很有限,原因在于,德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明显不同于我国刑法。例如,德国刑法第248条b规定了未经许可使用交通工具罪,即违背权利人的意愿,擅自使用其汽车或自行车的,不成立盗窃罪,但成立法定刑较轻的未经许可使用交通工具罪。我国刑法未做类似规定,但如果认为擅自使用他人交通工具的行为只能无罪,则亦为不妥。①参见张明楷:《侵犯人身罪与侵犯财产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5页。例如,张某、李某计划假期到西藏自驾游,但没有车辆可用,偶然发现马路上停放的一辆汽车未拔车钥匙,遂开走出行,打算自驾游结束后返还原处。在这个案件中,应认定张某、李某具有排除意思,从而成立盗窃罪。
五、非法占有目的侧面II:利用意思(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别)
取得型财产罪是获取财物的利用可能性的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利用、处分财物的意思。关于利用、处分意思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学说上存在各种见解,如:(1)是指享受财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意思,即按照财物的经济用途加以利用、处分的意思;(2)是指按照财物的本来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3)是指毁坏、藏匿之外的意思;(4)是指享受财物所具有的某种效用的意思。大谷实认为,为将盗窃罪等取得型犯罪与毁弃、隐匿犯罪区别开来,才要求利用、处分意思这种主观要素,为此,只要是毁坏、隐匿财物之外的意思就可以了,不必只能是享用经济方面利益的意思,也就是说,只要存在享受财物的某种功用的意思就可以了。②参见[日]大谷实:《刑法各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西田典之也认为,在理解利用意思的时候,不是必须有按照财物的经济用途或本来用途进行利用的意图,而应是享受财物本身所具有的某种效用或者利益的意图。③参见[日]西田典之、桥爪隆:《日本刑法各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84页。因此,为了劈柴取暖而窃走邻居家具、为了卖废品而窃取钢厂新产钢材等,均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理论上要求具有利用处分意思的根据之一是,之所以取得财产罪比其他财产罪受到更重的责任非难,是因为取得罪行为人具有贪利动机,即图谋通过利用他人的财物而享受其价值。因而,利用财物时没有必要局限于经济的用途。倘若认为,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看,利用行为很容易被一般人所模仿,因而对具有利用处分意思的情形要予以较重处罚,那么,要求按照财物的本来用途进行利用还有一定道理。但是,对具有利用意思的行为予以较重非难的原因在于行为人的贪利动机,从这一角度来说,要求按照财物的本来用途进行利用就毫无意义。④参见[日]佐伯仁志:《不法领得的意思》,《法学教室》第366号2011年,第81页。从实质上来说,利用处分意思就是享受财物本身的效用的意思,在考察利用意思的时候,这才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至于是按照经济用途来利用还是按照本来用途来利用,则无关紧要。可以说,上述(3)和(4)的见解具有合理性。
日本司法判例一直以来坚持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对于利用意思的理解,判例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解释的过程。起初,判例认为,利用意思是指按照财物的经济用途加以利用、处分的意思;后来出现了很多难以说是经济用途的情形,所以认为利用意思可以是按照财物的本来用途加以利用、处分的意思;再后来出现了打算拴住木材而窃取电线的案件,判例进一步认为,利用意思还可以是享受财物所产生的某种效用的意思。具体来说,最初在教育敕语案、妨害拍卖案中,法院判决认为,行为人不存在遵从财物的经济用途进行使用的目的,从而未认定成立盗窃罪。教育敕语案的案情是,某小学的教员,出于让校长下台的目的,取走校长保管下的敕语誊本,然后藏匿在学校教室的天花板上(大判1915年5月21日刑录21辑663页)。妨害拍卖案的案情是,被告人曾得到某律师的帮助,该律师正苦于怎样才能使竞拍延期,出于让拍卖延期的目的,被告人擅自从裁判所取走拍卖记录,然后藏匿起来(大判1934年12月22日刑集13卷1789页)。后来在丢弃电锯案中,判例认为,行为人不具有依物本来的用途使用的目的,否定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仙台高判1971年6月21日高刑集24卷2 号418页)。在该案中,出于报复的目的,行为人将他人电锯窃走,并丢弃于大海中。再后来,在手表戒指案中,判例认为,行为人不存在享受财物本身所具有的效用的目的,并据此否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东京地判1987年10月6日判时1259号137页)。在该案中,行为人杀害他人之后,为了避免罪行败露,出于与尸体分开扔掉的目的,从死者身上取走了手表、戒指等财物。①参见[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付立庆、刘隽、陈少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6页。
与毁坏财物罪相比,取得财产罪的本质在于,其具有利欲犯的动机,即随意地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从利欲犯的动机这一角度所理解的利用意思,是认定盗窃罪等取得罪所必要的要素。同时,利用意思也是区分取得财物罪与毁坏财物罪所必要的。而且,除非是出于毁坏的意思而侵害占有,其他情形下的侵害占有一般都具有利用意思。例如,出于低级趣味而窃取他人内衣,可以认定行为人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相反,为了防止本人受到毒品犯罪的牵连,打算取走对方持有的毒品予以销毁,对对方施行暴力,致其受伤,判决认为,行为人为了销毁毒品而实施行为,不是为了取走之后本人使用或者转让给他人,其主观意思不包括在非法占有目的之内,所以不成立抢劫罪(福冈地小仓支判1987年8月26日判时1251号143页)。由此可见,即使在侵害财物的所有和占有的时候存在其他动机,但具有取得占有后毁坏财物意图的,不能认定存在非法占有目的。②参见[日]大谷实:《刑法各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指出:“惟在外观上虽系对于他人之物的毁损或丢弃的处分行为,但在实质上却系实现其经济目的的行为,则又为窃盗罪,而非毁损罪。实例如下:A取走与自己珍藏的高价邮票相同而属于B所有的邮票,并加以毁弃,而使自己所有的邮票成为世界上现存独一无二的邮票,以提高其交易价格。”③参见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上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29页。又如,甲向乙借钱,写了欠条给乙,后来甲为了达到不偿还债务的目的,窃出欠条之后撕毁。日本有学者认为,甲对窃走欠条有利用意思,因为撕毁欠条与免除债务有直接关联。④参见[日]佐伯仁志:《不法领得的意思》,《法学教室》第366号2011年,第82页。我国有学者对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提出质疑。A获取利益的方式不是利用B之邮票的存在,甲获利的方式也不是利用欠条的存在,相反,A与甲是通过邮票与欠条的不存在(消灭)来获取某种利益。在理解取得财产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时,我们要认识到,行为人是通过取得对他人财物的占有从而享受其效用。①参见张明楷:《诈骗犯罪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13页。根据这种观点,A与甲并非通过取得占有来获利,而是通过毁坏财物来获利。实际上,A与甲窃取邮票、欠条后再撕毁,与现场直接撕毁,在获利效果上是一样的。这样看来,很难说A对邮票、甲对欠条存在利用意思。稍微改动一下案情也许问题会更清楚,丙出于将欠条卖给甲的意图,从乙处窃取了甲所写的欠条,则能肯定丙对欠条存在利用意思。可以说,行为人妨害他人利用财物的意思属于排除意思的内容,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存在利用意思。如果认为妨害他人利用财物的意思意味着行为人具有利用意思,那么,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人就全部具备利用意思。这样一来,要求取得罪具有利用意思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根据利用意思无法区分取得罪与毁坏罪。
因此,对于利用意思的理解和认定来说,划定一个界限(底线)是完全有必要的。②参见[日]佐伯仁志:《围绕盗窃罪的三个问题——财物的消费、占有的承继、不法领得的目的》,《研修》645号2002年,第10页。当然,利用财物也意味着消耗财物,大多数财物的消耗需要一个过程,但有些财物如食品、药品,食用、服用(消耗)之后即意味着利用,并不必予以保留。利用意思的本义是对财物本身进行利用。虽然对利用意思的解释存在扩大的趋向,但在最低限度上,将物保留下来是有必要的,只有取得占有、保留财物,才有利用的可能性。
在主张不需利用意思的观点、不需非法占有目的的观点看来,在盗窃罪与毁坏财物罪二者的关系上,即使出于毁坏的意思转移了财物,也成立盗窃罪;毁弃财物也是所有权人才能实施的行为;成立盗窃罪,只要取得占有而具有了对财物的利用可能性即可。然而,上述观点存在疑问。首先,按照上述观点会得出不合理的结论:成立毁坏财物罪的情形只能是没有转移财物的占有而予以毁坏;转移占有并毁弃的行为都要成立盗窃罪。如此一来,相较于没有占有转移的毁弃,存在占有转移的毁弃会受到更重的处罚,可是根据是什么呢?而且,区分盗窃罪与毁坏财物罪的实质性依据也不清楚。其次,上述观点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在法定刑的轻重上,盗窃罪与毁坏财物罪之间有这么重大的差异。单从法益侵害来看,毁坏财物罪是将财物破坏、毁灭,或者使其功能丧失,往往失去了恢复可能性,所以危害要严重得多,但是与毁坏财物罪相比,对盗窃罪的处罚要严厉得多。其实,原因正在于主观方面,意图利用他人财物这种动机、目的更值得谴责。只有将利用意思纳入盗窃罪的主观要素,才能正确区分盗窃罪和毁坏财物罪。利用意思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获得物之利用可能性的意思,而是享受由财物所产生的某种效用的意思,因而更有实质性意义。转移占有时带有利用意思的,是出于更为强烈的动机而实施法益侵害行为,所以其具有更重的责任。③参见[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页。而且,带有利用意思的夺取占有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更经常发生,在一般预防的意义上,以更严厉的态度加以抑制也是有必要的。在区分盗窃罪和侵害占有的毁坏财物罪时,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意图取得财物的利用可能性并享受其效用,则是盗窃罪;如果只是意图妨害他人利用,则是毁坏财物罪。由此可见,利用意思不仅是主观的违法要素,还带有主观责任要素的性质。
对于利用意思的上述理解和定位,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提出了批判意见:(1)如果出于毁坏的目的取得了财物,但是后来没有毁坏而是予以抛弃或者之后又产生了据为己有(享受其效用)的意图,则对此就只能不进行刑罚处罚,如此会导致处罚漏洞,不利于对被害人财产的保护。(2)侵占(脱离占有物)罪也属于取得财物罪,但与毁坏财物罪相比,其法定刑要轻,对此,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不能作出合理说明。但是,对于上述两点批评意见是可以反驳的。首先,针对前一批评意见,出于毁坏的意图转移财物占有,之后抛弃该财物的,能够成立毁坏财物罪,因为被害人失去了该财物的使用价值,这也是一种毁坏,所以这种行为不会不被处罚;如果之后产生据为己有加以利用意思的,相当于在没有受委托而占有他人财物的基础上又产生了非法占为己有的意思,所以,能够成立侵占罪,也不会产生处罚漏洞。其次,针对后一种批评意见,利用意思是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之一,支持非法占有目的包含利用意思的观点认为利用意思是一种加重责任的要素;对存在占有侵害的行为,刑法往往用严重的犯罪来评价,而在侵占(脱离占有物)罪中,并不存在占有侵害,所以侵占行为的违法性比较轻;侵占行为存在诱惑性,侵占(脱离占有物)罪属于更容易诱惑人实行的犯罪,所以其非难性低一些,其有责性也比较轻。①参见[日]西田典之、桥爪隆:《日本刑法各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83页。因此,对侵占罪的处罚要轻于毁坏财物罪,是可以作出解释的。
根据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理,要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成立盗窃罪,只能根据转移占有阶段的主客观事实来作终局性判断。因此,行为人取得财物占有之后是否实际毁坏了财物,对于盗窃罪成立与否的判断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在区分盗窃罪与毁坏财物罪的时候,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毁损行为不是决定性因素,真正重要的是转移占有阶段的主观意思,即行为人是出于毁坏财物的目的而取得财物,还是出于非法占有目的而取得财物。当然,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取得占有之后如何对待、使用财物,对于认定盗窃罪来说也是要加以考虑的。②参见[日]伊藤雅人:《诈骗罪中的不法领得意思》,池田修、金山薰编:《新实例刑法(各论)》,青林书院2011年版,第99页以下。具体来说,在判断转移占有时点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时,将行为人取得占有后对财物的使用情况作为判断材料纳入进来,并不是以转移占有后对财物的客观使用情况来反制、决定是否成立盗窃罪。③参见[日]桥爪隆:《论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的目的》,王昭武译,《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2期。
例如鲸鱼肉案,被告人属于某环保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从事反捕鲸活动。有一艘打着科研调查旗号的捕鲸船出海归来,其船员打算擅自将鲸鱼肉送回家。被告人获知这一消息后,为了核实信息真伪,推动反捕鲸调查活动,在船员把鲸鱼肉装进纸箱交给快递之后,私自占有了这个纸箱。法院认为:“出于收集证据资料的目的,排除权利人,连箱子带肉,取得了对本案鲸鱼肉的支配,在开箱确认之后,对本案鲸鱼肉采取拍照、取样保全等只有所有权人才能实施的行为,出于连同纸箱一起利用鲸鱼肉的意思,取得了对装入鲸鱼肉的纸箱的占有。”(仙台高判2011年7月12日LEX/DB25472600)根据上述理由,法院认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有学者认为:“这是存在疑问的。即便行为人实际上是出于开箱确认后丢弃鲸鱼肉这种损坏器物的意思,但该案也是以‘丢弃是只有所有权人才得以实施的行为’这种错误的理由,而认定行为人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④[日]松宫孝明:《刑法各论讲义》,王昭武、张小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5页。本案被告人在转移占有阶段具有排除意思,但是没有保留鲸鱼肉以获取其效用的意思,即便出于其他动机、目的(反捕鲸)侵害了他人对财物的占有,但是以毁弃的意思来作处置,所以不存在利用意思,从而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成立盗窃罪。
又如支付督促正本案,即通过欺骗手段取得裁判所发出的催缴通知正本之后马上予以毁弃的案件(最决2004年11月30日刑集58卷8号1005页)。在该案中,被告人打算恶意利用支付督促制度,即通过法院查封自己叔父的财产,经由强制执行方式获取钱财。被告人虚构了自己对叔父拥有债权的事实,以此向裁判所提交了支付督促申请。被告人预想到裁判所会以其叔父为收件人发出附带预先执行宣告的支付督促正本,就让同伙在叔父家附近等候,在邮政投递员送达上述文件的时候,同伙上前谎报被害人的名字,领取了文件,这样就造成了文件已经送达这种假象,导致被害人失去了对支付督促申请异议的机会。被告人一开始就有将支付督促正本销毁的意图,而没有用于其他用途的打算,而且在领取支付督促正本的当天就销毁了。最高裁判所认为,通过欺骗邮政投递员而领取支付督促正本,只是打算销毁而没有在其他用途上加以使用或处分的意思,在此情形下,针对支付督促正本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即使是在作为用于获取财产性利益的手段之一而对投递员实施领取行为之时,上述结论也没有什么不同。可见,判例表明了骗取支付督促正本的诈骗行为不成立诈骗罪这种立场。①参见[日]西田典之、桥爪隆:《日本刑法各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84页。
在上述案件中是否成立诈骗罪存在争议。虽然行为人存在恶意利用支付督促制度获取金钱的目的,但对其骗取支付督促正本这一行为,不能认定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因为行为人的目的只是毁弃该文件,而没有为了某种用途而进行利用、处分的目的。对于实务上宽泛理解利用意思的倾向,该判例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抑制作用,所以具有重要意义。②参见[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付立庆、刘隽、陈少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7页。
六、结 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不能笼统地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将非法占有目的细分为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两个侧面,以此思路来分析具体案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在有些案件中行为人的排除意思很明显、清楚,需要探讨的是利用意思,而在有些案件中行为人的利用意思很清晰,需要分析的是排除意思。
从本质上来说,排除意思就是试图造成可罚的法益侵害(妨害利用)的意思,它成为判断法益侵害之危险的基础素材,所以被视为主观违法要素。在控制使用盗窃的处罚范围上,排除意思作为主观违法要素发挥作用,是不可缺少的。达到可罚性程度的妨害利用的意思,即排除权利人利用的意思(排除意思),就成为区分不具有可罚性的暂时使用行为与盗窃罪的必要要件。在占有转移的时点,如果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只是轻微地妨害权利人使用财物,那么行为人就没有排除意思,这种行为只是轻微的暂时使用,并不可罚,因此排除意思起到了限制入罪的机能。
从实质上来说,利用处分意思就是享受财物本身的效用的意思,在考察利用意思的时候,这才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至于是按照经济用途来利用还是按照本来用途来利用,则无关紧要。虽然对利用意思的解释存在扩大的趋向,但在最低限度上,将物保留下来是有必要的,只有取得占有、保留财物,才有利用的可能性。在出于毁坏的意图而夺取他人占有的财物的情形中,行为人不存在对财物予以利用、处分的意思,因此也不成立盗窃罪。转移占有时带有利用意思的,是出于更为强烈的动机而实施法益侵害行为,所以其具有更重的责任。利用意思不仅是为取得罪奠定违法性的主观违法要素,还带有主观责任要素的性质。
虽然是否需要非法占有目的与盗窃罪的保护法益论之间并没有理论逻辑上的必然关联,但是,非法占有目的中“非法”的判断却与保护法益有关联。与德国刑法不同,日本刑法未对非法占有目的作出明文规定。所以,在解释论上无论采取哪一种学说都是可能的。对于财产罪,我国刑法也未明文要求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所以评析日本刑法理论上的各种观点和审判实务的做法,对于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审判实务来说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