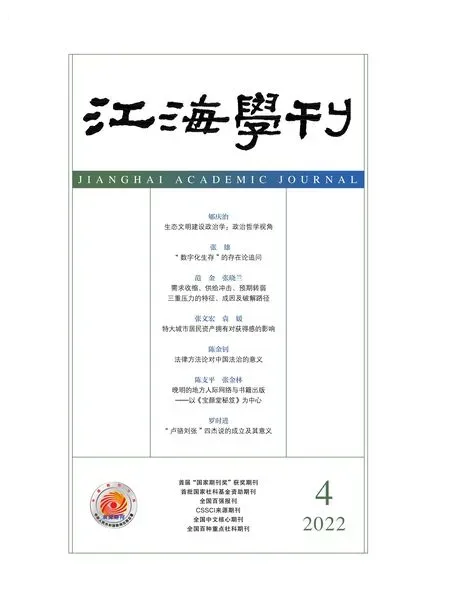“善”的自觉、“知”的建构与“行”的养成*
——《论语》之理想道德人格的逻辑进路探析
2022-02-05肖雅月
肖雅月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以“止于至善”的理想道德人格之圆成作为人文目标和价值归宿,这一点在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伦理思想中表现得尤为凸显。纵观《论语》20篇,孔子所孜孜以求的,即为融智、仁、勇于一身的理想道德人格。此一理想人格的“成人之境”何以可能?其理论内涵何在?如何在“修身为本”的实践中养成?本文拟以实践理性之省思,来客观展示其逻辑进路。
出发点:在“天人合一”中揭示人性之善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对于这句话,几千年来一个最常见的误解即谓孔子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善恶纯由人后天的居处异域、经历不同、风习所染而成。此解实则大谬。事实上,孔子讲“性相近”,意谓“至善”之道心人人本具,而生时所秉“气质之性”虽有“上智”与“下愚”的不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并无天壤之别,而表现为“相近”的特质。既然如此,人的后天品德何以有尧舜与桀纣、颜回与盗跖的巨大差别?孔子认为,这主要是由人日愈“相远”的后天习俗所造成。这就在以“性善”前提的确立来确保道德人格之“成善”可能性的同时,赋予人“向善”的后天修养以“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基本建设意义。
为什么说孔子的“性相近”内涵了对人性善的主体性确认?一旦突破了只言片句的“句读”之学而达致对《论语》通篇文意的了解,这个问题就不言自明了。在孔子看来,人先天的“性善”是后天成贤成圣之道德修养的前提,仁义礼智非由外铄,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人的后天修养不过是复归其“至善”本性之艰辛漫长的过程。反之,若设定“人性恶”,则把人混同于禽兽,所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论语·公冶长》),后天“成人”的道德修养便丧失了内在的可能性依据。同时,人性善又不只是道德上的可能性假设,而是随着人后天修养的逐步提升而渐次显露出来的“本真的呈现”。人后天不积善成德而积恶为非,绝非不具此一“至善”本性,却是因积恶所染而遮蔽、尘封了其“至善”本性而已。
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正是对人的“至善”本性之明确的主体性确认。“仁”本属心体之全德,内在于吾之一身而“皆备于我”;吾欲成就“仁者”人格,当从“明明德”的切身功夫做起,辅之以“亲民”的实践,以“内圣外王”的终身修养来实现“成人”的目标,这集中体现了孔子伦理思想之“为仁由己”的道德主体性特质,构成其沛然洋溢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源头活水。这与西方文化占主导的“性恶论”、特别是基督教文明“原罪救赎”之非人化神本主义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对“性善”的理论指认依具体情境的不同而有多方面的表现。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意谓亲近仁者以启吾内在之“仁”进而达致以“仁”为“里”的“居仁由义”之效,这是善风相习、由外而内的熏染之功,而熏染之功要发挥作用,必须启发内在的道德自觉,以成就主体的内在之“仁”。在探讨仁德与富贵之间关系时,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体现了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的超然态度,而以“仁”作为终身皈依的精神家园,强调“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而人能做到颠沛造次之际均“不违于仁”,实出于对自身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这一“至善”本性的发现和坚守。故而孔子感慨道:“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全体之大“仁”本内在于我,一旦“用力”而终身求之则不假外铄而自至,所谓“力不足者”,不过“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托词尔。
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所谓“中庸”,实乃“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的有机统一,而“发而皆中节”的“和”之大用,实出于对“未发之中”之“至善”本性的本体性把握。在这里,“体”和“用”是辩证结合的,明体方能达用,达用更须明体,“中庸”之德内涵了对本体之善的确认。而此一本体之善的发明和落实,则必须诉诸终身修养的实践。有鉴于此,孔子特别赞赏颜回“不迁怒,不贰过”之一以贯之的自觉修养精神,称道其“回也不改其乐”之超然物外、唯道是求的“乐道”精神,并判定其修养已至“其心三月不违仁”的贤者之境。所谓“三月不违仁”,意谓尚未达到“居仁由义”的完全“复性”之境,但相距已不过一线之间。其中,既内涵了对“至善”本性的确认,又强调了后天修养之必须。
孔子在畏于匡、伐树于宋的危难之际,曾说过两句著名的话,其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其二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孔子对“其如予何”的坚定自信,实出于对“至善”之性内在于吾身的确信无疑。此一“至善”本性,不仅要求个体道德之完善,也表现为存续文明礼乐的天下情怀。因此,《论语》中的理想人格自始便兼具胸怀天下的强烈使命感,所谓“天命”在我,既是要通过终身的修养实践来不断发明本心,也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而在“平天下”的使命追求中实现个体道德的圆成。故而“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此“勇”乃是“知止而后有定”,即确立“至善”为人生目标之后的义无反顾,同时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使命在身的一往无前。
“至善”本性从何而来?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极少言“性与天道”,因为人生而秉承“天命之性”,“天道”自在吾身又何须多言?孔子也不愿多言,因为“天道”之参悟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说尽,而是要下一番持之以恒的真功夫。所谓“道不远人”,人在一呼一吸之间皆是修道,在此意义上,人生实乃一场对“至善”本性体悟、省察与坚守的“复性”之旅。不过,天地之道虽无处不在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虽处处有迹可循却始终无声无形,故而《中庸》有云:“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人的“复性”之旅也是自身不断通达天地的过程,一经发明了本心,复归了“至善”之本性,便“下学而上达”即与天地合德,天、地、人合而为一,抵至“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境。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地周行四时、孕育万物,却纯任自然、悄然无息,正所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道德经》),此乃天地无私无我之“至善”大德,其为人生而所秉,便构成了人性本善的根本源头。既然人性本源出自“天道”,人性又怎么会无善无恶?将天地之道指认为人性之源,实是对人性善的再次确证。圣人之德当如是,“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中庸》),故而孔子曾感慨:“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天人合一”不仅在本体论上给出了人“成善”可能的内在依据,更使儒家伦理甫一确立便内涵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象》),如果不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出发,便难以理解“天行健”“地势坤”如何引申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品格。认为“至善”大德存乎天地之中,并确认人作为“天地之心”而与生俱来“至善”本性,构成了中华传统一经诞生就始终高扬的人文关怀。这与西方文明惯以“天人二分”的角度来考察世界的知性理智截然不同,而成为华夏文明历经千百年仍生生不息的内在生命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天地之道是人性善之“源头活水”,然而人的后天习俗却千差万别,这就使原本清澈的“至善”本性可能被光怪陆离之万象诱惑所蒙蔽,有如一汪清泉日愈变得污秽浑浊。所以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意谓“道”即“至善”本性,人皆生而有之,但若不能扩充之、弘发之,本心便会逐渐迷失。因此,“天人合一”固然给出了人“成善”的可能性前提,能否达致理想人格的“成人之境”,却必须藉由人“向善”之主体性自觉和一以贯之的终身实践才能完成。届时,涤荡去了污秽之物,清泉便得以复见清澈,此一清泉有如光辉人性之复现,可以照天、照地、照心。
“成人之境”:“智”“仁”“勇”三位一体
道德修养明所从来亦须知所趋赴,即在理论上解决往何处去的目标和归宿的问题。只有建构正确的人文理性之“知”,并在“行”中不断践行“知”,才可能成为圣贤。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知”亦为“智”,理想道德人格在人文理性之“知”的建构上表现为“智”“仁”“勇”三者的有机统一,并以此为“止于至善”的“成人之境”。
“知者不惑”,“智”构成理想道德人格的理性要素,它是理想道德人格生成的理论先导。“知者不惑”并非穷尽了世间数理规律之知识而“不惑”,人之一生也不可能穷尽对自然万物的探索,此一“不惑”实是义理上的“不惑”,是把握了宇宙人生真谛后所形成的智之明觉。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命”,天、地、人“三才之道”是也。“知命”既是知“天命”也是知“己命”,“天命”即天地之道,而“己命”为天地之道在自己身上的具体体现。所谓“知命”,就是要以义理的“智”之明觉引领自己的人生,让“天命”与“己命”在吾之一身得到有机统一。人若穷其一生追求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不知“天命”也不知“己命”,不属于自己的财富或地位却偏要强求,逆“命”而行终将出大问题。只有将复归“至善”之本性确立为人生目标,按照“天命”的指引让“己命”与其同向而行,才能日愈精进,在“向善”“成善”的人生历程中不断弘发生命的本真,此乃大智也。因此,孔子所谓“智”不同于西方文明惯以强调的知性理智,而表现为对“至善”之本体发明的人文义理之“智”。人要达至“成人之境”必须藉由“智”的指引,否则就如同盲人一般容易迷失前进的方向。
“不惑”之“智”的本体明觉在现实中有很多具体表现,孔子曾在各种情境下对其作出不同角度的理论指认。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强调求知之诚,“智”来不得半点含糊或作伪,必须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端正态度,在反复的琢磨与体悟中参透宇宙人生的真谛。樊迟曾两次问“知”,孔子第一次回答:“知人”(《论语·颜渊》),第二次回答:“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这两次回答体现了孔子的人本思想。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智”的立足点在人,人是万灵之长,把握了“人伦”即“人道”才是真正意义上把握了天地之道。所以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要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同时做到生民教化,实现“制民之产”与“恒民之心”的有机统一。而道体尽在把握后,就必然表现出灵动与欢快的特质,故“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水在山间便顺势而下,入江海则尽情奔涌,如同“智”不拘泥、不刻板一般,只因所面对象、所处境遇不同而有不同的具体表现;而山岿然不动,有如“仁”心既发便始终如一绝不偏离半毫。这一“动”一“静”之间看似矛盾,实则皆出于“至善”之本心,一为行之一为守之而已。于纷繁万象中发明本心需要“智”,处乱世而能行守本心亦需要“智”。此一人文理性之“智”既明,便如一盏不灭明灯照破黑暗,引领人向着“仁”之心体全德不断修进。
“仁者不忧”,“仁”侧重于兼善天下的大爱情怀,它构成理想道德人格的情感性、动力性要素。孔子讲“仁”有两种不同意义,一种是广义上的“仁”。所谓“麻木不仁”,最初是一种医学术语,意谓四肢血气不通、麻痹没有知觉,故而仁者通也,儒家由此引申出伦理意义上的人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息息相通之“仁”,而人之所以能与他者、与万物一体,正因为人秉承了天地的“至善”本性,虽然在现实的肉体存在上彼此分离,但在“天命之性”的精神源头上彼此汇通。在此意义上,“仁”便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价值。孔子曰:“仁者人也”(《中庸》),仁义礼智实则皆内含于此一广义之“仁”。而将智、仁、勇三者并列为三种“达德”,则重点强调广义之“仁”的一个方面,即狭义的情感之“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意谓情感之“仁”表现为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的同情,因为同情,所以能够对他人的处境遭遇感同身受,能够忧他人之所忧、乐他人之所乐,这便构成了仁爱之情感的基础。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此种广泛的同情以及由此生发而来的对众生的博大深沉之爱,实则为本体之大“仁”的一种情感的表现,它是建构理想道德人格重要的情感动力。人活于世,必须要有温暖的情感,如果一个人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十分冷漠,对旁人的境遇无动于衷,那么这个人就难以做出“仁”的行为,更难生发出道德修养的主体自觉。故而子贡说夫子“温、良、恭、俭、让”,“温”是人文意义上的温度,意谓夫子的人生处处体现出一种兼善天下的温暖的人文情怀。没有此种温暖的兼善之爱,人的道德修养就会失去情感的动力,人的一生就会变得冰冷无比而丧失作为人的本质意义。
《论语》通篇未见孔子给“仁”下过任何定义,而总是结合具体情况给出不同的阐释。所谓“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孔子已经把握了大“仁”之本体,其“仁”之用必不会脱离“仁”之实质,而其他人由于成长经历、处境遭遇、道德层次之不同,对“仁”难免有各自的理解,故而孔子在不同语境下对“仁”的解读各有侧重。在与子贡对话时,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从广义上说,是指“仁”要与他人情感互通,将他人和自己等一看待。若单从情感的方面讲,是指做人的基本要求便是具备同情心,要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意谓“仁”虽然强调“爱人”,但绝非一味宽容、忍让,而是在建构正确是非观的基础上进行公正的价值评判,对符合道德原则的行为要自觉褒扬,遇到丑陋的东西时也要坚决予以斥责。樊迟问“仁”时,孔子第一次回答:“爱人”(《论语·颜渊》);第二次回答:“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第三次回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如果说“爱人”和“先难而后获”侧重强调“仁”的基本要求,那么“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则侧重说明“仁”的实践功夫,“仁”不仅要时刻怀有同情之心,更要使自己的行为处处符合“礼”的规范,如此便是本体发明而“仁”心外化了。在论及“礼”与“仁”之间关系时,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意谓“仁”是内在之精神根本,而“礼”“乐”皆为承载“仁”的外在之表现形式。人可以通过礼乐教化来不断接近“仁”,但要想发挥此种移风易俗的功效,就不能片面追求“礼”“乐”的外在表象而脱离“仁”的实质内涵。故而孔子感慨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乐”难道只是玉帛、钟鼓吗?其所内涵的仁爱之情感才是根本。
“勇者不惧”,“勇”强调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它构成理想道德人格的过程性要素。理想道德人格之目标一经确立,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意志力量。意志,即意之所志,是人的精神所要前往的方向。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立志于“仁”,便生发出一往无前、不为任何苦难所屈服的坚定的意志品质,纵然为之牺牲也在所不辞。故而孔子言“勇”绝非血性之勇,而是指意志品质上所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它贯穿于理想道德人格之修养过程的始终。如果没有此一意志力量的支撑,人就会一曝十寒、三心二意,遇到点挑战就畏缩不前;反之,若能不断克己修身、改过向善,便能在日复一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点滴积累中,完成“至善”本性的复归。
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义”是应当,明白一件事应当做却不去做是“无勇”,可见没有“勇”的理想道德人格是不完备的,也绝无可能实现。不过,“勇”不是遇事冲动鲁莽、作无谓的牺牲。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暴虎冯河”一类莽夫之勇,孔子“不与也”,真正的“勇”是以“仁”为己任而表现出的一种“弘毅”的坚定意志,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锲而不舍,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所向无前。故而孔子曾感慨:“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仁者必有勇”的“勇”是义理之大勇,而“勇者不必有仁”的“勇”是血气、忤逆之小勇,小勇者徒有“勇”而无“仁”,孔子并不推崇。孔子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勇”如果失去了理性先导和仁爱情感的约束就要出问题,大则为乱,小则为盗,唯有“仁者之勇”才是真正的大勇。有了此种勇气,便有了任处境再艰险也绝不退缩、任前景再渺茫也绝不放弃的巨大精神力量。孔子曰:“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君子以“成人之境”为人生目标,便不再为任何外界纷扰所困惑,亦不惧怕任何可能面对的艰难险阻。因此,“仁者之勇”赋予人百折不回、奋勇向前的坚强意志,推动着人日愈完善自身,最终实现“至善”之理想道德人格的圆成。
拥有智、仁、勇“三德”可以“成人”,(1)钱穆:《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337页。即成就“至善”之理想道德人格,而“至善”之理想道德人格又内涵了智、仁、勇三者的有机统一。确立“止于至善”的人生目标是智,它必然由朴素的爱的情感生发而来,并产生为之坚持不懈、努力奋进的强大勇气;而人一旦具备了人文理性之智,藉由它的引领在人生的“复性”之旅中,必然表现出由己及人、兼善天下的大爱情怀;同时,若没有坚韧不拔的勇气作为支撑,向吾之“至善”本性的复归绝无可能完成,所以要达到大智与大仁的高度,就必然要具备大勇的品质。因此,“不惑”之“智”、“不忧”之“仁”、“不惧”之“勇”实则彼此涵摄、互动统一,如鼎之三足共同拱立于“止于至善”的“成人之境”中。
实践路径:“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实践者,实际践行的功夫与行动也。真“知”需要真“行”,空有表面文章而无实践内涵的不“行”之“知”,终将沦为假“知”。
真“行”必须勤学遵礼。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志于学”即是将“止于至善”确立为人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志于学”后才可“知天命”,“天命”虽然为人生时所秉,但“生而知之者”属少数,大多数人都需要“学而知之”,因而学习是人生第一要务。《论语》开篇有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学”偏重诵读研学,“习”偏重温故复习,常“学”常“习”才能学业日精。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可见学习要举一反三,擅于由此及彼、归纳总结,才算学扎实、学通透了。孔子也强调“学”“思”必须相辅相成,否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学习不只是个体的磨砺,还要注重借鉴他人之长,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在学习的同时也要以“礼”规约,“礼”实为“仁”在生活中的具体落实,是日常行为的规范准绳,时时遵“礼”方可渐近于“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要做到“视、听、言、动”皆符合“礼”之规范绝非易事,一个人若能无时无刻都无违于“礼”,那么己心必然已充实“仁”道,“复礼”不过是其心中“仁”道的外化,这便是达致“仁者”之境了。到了此时,人与“仁”道已经完全合一,通体发明而言行不过是其内心道体的外在表达,自然无时无刻都能“复礼”。故而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既能博学汇通又能遵“礼”行“仁”,便已然走在正道上,何时“修成正果”只是时间早晚罢了。
真“行”亦须持之以恒。所谓“知道易,行道难”,立志于“仁”并不难,难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践行。孔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笃信”与“守死”都旨在强调道德修养贵在持之以恒,“善道”不可须臾偏离之,“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中庸》),从而在日常磨砺与点滴积累中不断完善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可惜,能做到持之以恒的人少之又少,故而孔子曾感慨:“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善人”难觅,但若能见到以“至善”为人生目标并为之勇毅前行的人,又何尝不是人之何以为人的本质价值的流动与体现?事实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是内在于天地之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天地周行四时、孕育万物从不曾有过半刻停歇,人又怎么能懈怠一丝一毫?是故“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兢兢业业、勉励“诚之”,才不枉费人的一生。道德修养绝非一蹴而就,“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是继续前进还是半道废止,皆在于人的主体性选择而无关乎其他,这在强调持之以恒精神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对人之道德主体性做了再次确证。虽然成就理想道德人格之路漫长艰辛,但若能坚持到底,其精神上的富足远胜一切。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所谓“仁者与万物为一体”,天地万物都在己心之中,己心亦沛然充盈于天地之间,俯仰天地、明察人伦,此般自在而自得,任何世俗之物恐怕都难以比拟。故而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意谓一旦复归于“至善”之道心,生无所惧、死亦无憾。
真“行”还须心系天下。儒家传统一向追求“修齐治平”,要以“修己”为基础继而达致“齐家、治国、平天下”。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尤病诸!”(《论语·宪问》)意谓成就“仁者”人格,心中必须始终系挂百姓,这一点恐怕连尧、舜都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故而君子修养必须时刻怀有“安百姓”的使命之自觉,纵然“道阻且长”(《诗经》),行则将至。理想道德人格之圆成不仅是“成己”,更是“成人”乃至“成物”。所谓“天命”在我既是生而秉承“天命之性”并努力复归之,也是自觉肩负起上天赋予的使命,做到“修己以安人”进而“安百姓”。由此,孔子自然引发出“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意谓在上位者若能德行兼修,便有如众星自然以北极星为中心运行一般不怒自威、天下归心。“成己”不易,“成人”“成物”更是难上加难,故而孔子感慨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倘若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之“圣”了!“圣人”是理想道德人格的完美体现,是人之内在德性与外在社会作用的完美统一,尽管此一境界常人几乎难以企及,但“圣人”之完美人格的设定,揭示了对理想道德人格的追求是贯穿于每个人生命始终的历练过程。孔子对此一“圣人”境界的明确指认,也成为内刻于儒家与中华传统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它既表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也表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担当,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气节。它滋养中华儿女形成最真挚、最朴素的爱国情感,也是历代志士仁人为民族、为国家不惜牺牲一切而奋斗的内在精神动力。
《诗经》有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一方面,君子之道皆可察于寻常之处,而终与天地万物一体;另一方面,“仁”之理想道德人格虽看似广大至极,但因“天命之性”人人生而秉之,只待从小处近处、从一点一滴做起而苦下一番终身修养的实践功夫,便能复归吾身之“至善”本性。因此,儒家伦理给予人“万物皆备于我”而“不假外求”之明确的主体性确认,人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并在“成己”的基础上达致“与天地参”,可谓真正的、彻底的人道主义。同时,其所内涵的“天人合一”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系以及始终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格局,亦可为当代道德人格培育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