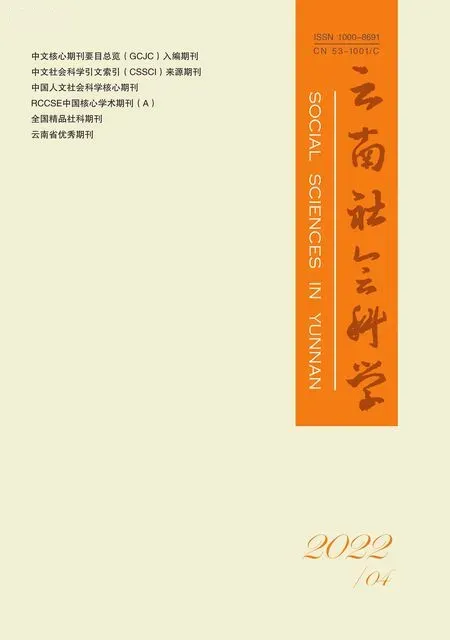丝路与博物:唐前小说殊方异物的文学书写与美学特质
2022-02-04王婧璇
王婧璇
“殊方异物”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汉书》卷66《西域传》载:“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部,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①(汉)班固:《汉书》(第12 册),(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3928 页。由《汉书·西域传》引文可知,殊方异物最早指代的是来自于域外,尤其是西域诸国的珍贵方物。在唐前小说中,与“殊方异物”相似的概念也常为小说著述者所提起。如郭宪《洞冥记》序曰:“或言浮诞,非政教所同经文、史官记事,故略而不取。盖偏国殊方,并不在录。……武帝以欲穷神仙之事,故绝域遐方,贡其珍异奇物及道术之人,故于汉世,盛于群主也。故编次之云尔。”②王国良:《汉武洞冥记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第40 页。由郭宪《序文》政教认为其浮诞,史官略而不取等种种限定能够看出,唐前小说的殊方异物概念,在正史定义的来自绝域远国珍奇异物的基础上,还明显加入了想象与虚构成分。
在《洞冥记》《十洲记》《博物志》《拾遗记》等诸多唐前小说中,殊方异物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并且对中国小说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殊方异物类小说的出现与丝绸之路的开拓有着密切联系,殊方异物的文学书写还与博物小说的发展关系紧密。而在域外色彩与博物传统背后,小说中的殊方异物还展现出丰富的审美特质与叙事程式。王国良先生较早地关注到了唐前小说殊方异物物象群体,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内容分析篇明确提出了殊方异物概念。①王国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 年,第239—252 页。他将殊方异物与神话传说、五行数术、民间信仰、鬼神世界等内容并列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重点主题。在“殊方异物”章节中,王国良列举动物、植物、矿物、杂物等具代表性的殊方异物小说条目若干,以实例的方式展现了殊方异物的内涵与重要性。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虽然没有将殊方异物纳入篇章主题进行讨论,但《西域文化的输入与想象力的拓展》《西域世界与中古小说题材内容的拓展》等篇章仍对本文所讨论的殊方异物书写问题有所涉猎。②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68—72 页、240—249 页。近来,与殊方异物相关的各类研究,大多专注于对某一具体物象的探讨。例如,罗欣《返魂香考》③罗欣:《返魂香考》,《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第1 期。、王子今《汉代“天马”追求与草原战争的交通动力》④王子今:《汉代“天马”追求与草原战争的交通动力》,《文史知识》2018 年第4 期。、王子今《玉门枣:丝路“远方”“名果”象征》⑤王子今:《玉门枣:丝路“远方”“名果”象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1 年第1 期。等,都是对唐前小说中的单一殊方异物进行物象原型方面的分辨,尤其遗憾的是,当今小说研究领域还未对殊方异物的文学书写的发生、发展及文学与美学特质等核心问题给予足够重视。如丝绸之路对唐前小说殊方异物出现究竟有何直接影响,唐前小说殊方异物书写继承了怎样的思想传统,对博物小说的发展有怎样的促进作用,殊方异物主题又有怎样的文学与美学特质。鉴于如上问题还未得到充分关注,本文立足于殊方异物书写的内涵与外延,对如上重要问题,进行讨论。
一、丝绸之路与殊方异物书写的产生
由上文《汉书·西域传》引文亦可知,殊方异物概念的出现与西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的开凿密切相关。丝绸之路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外物质文明的交流。朝贡往来与跨国贸易,除了带来陌生的域外物产以外,还带来了新鲜的域外传闻,而这些物产与传闻直接促进了唐前殊方异物类小说内容的产生。王国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在“殊方异物”一章指出:“汉、魏以下,与西域及海外邻邦之交通贸易,更形发达,奇花异果、珍禽异兽、珠玉宝石等,源源输入不绝。复有方术之士,援引荒茫之境,刻意编造渲染,新鲜物品,乃琳琅满目,不可计数矣。”⑥王国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第239 页。汉魏以降,中原与西域、海外更加频繁的互动,所指向的主要还是丝绸交往。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域外方物直接影响了小说殊方异物类物象、情节乃至故事母题的产生。丝路来物是许多小说殊方异物的现实原型。本文暂举与丝绸来物明确相关的几则小说条目,就丝绸之路对小说殊方异物物象产生的影响作具体分析。
(一)丝路来物对殊方异物物象的丰富
在丝路朝贡与贸易往来中,与中国丝绸大宗输出相对的,是来自于西域的良马、香料、植物、器物等输入品。马匹作为古代非常重要的骑乘与战备之具,历来多受古人重视。中原周边的游牧民族,不但善于骑射,其繁育的良马也较中原所产马种更加高大强健。基于军事需要,西汉以后,中原王朝通过丝绸之路开展更频繁的边境互市与朝贡往来,获得了更多的域外良马。武帝时期,崇尚域外良马之风十分盛行,尤其是对大宛汗血马的追捧更为炽热。石云涛《汉代外来文明研究》称汗血马就是从汉武帝时开始传入中原地区得,⑦石云涛:《汉代外来文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5 页。汉武帝就曾作《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西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⑧(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6 页。域外良马的输入,带给中原人在交通速度上的革命以及从高大骏马所得来的审美体验,也为小说塑造殊方异马形象带来了充沛的灵感。《洞冥记》“修弥马”是唐前小说中较明确以汗血马为现实原型的殊方异物。《太平御览》卷897 引《洞冥记》佚文曰:“修弥国有马,如龙,腾虚逐日,两足倚行;或藏行于空中,唯闻声耳。时得天马汗血,是其类也。”①王国良:《洞冥记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第105 页。
“修弥国”复见《洞冥记》卷2“驳骡”一则,称修弥国曾于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献驳骡,后文又藉东方朔之口,称修弥国献驳骡是“戎翟献其鄙兽”②王国良:《洞冥记研究》,第67 页。。戎翟,又作戎狄,是先秦时期古人对居于华夏民族西方与北方异族的统称,可见小说虚构的修弥国所指向的正是西域游牧民族。“修弥马”与汗血马类似,其形貌如龙,两足并行,奔腾迅猛,有腾空之能。小说赋予“修弥马”的异能,实际上是对汗血马奔驰速度的极致想象。首先,史书对于大宛汗血马的描述就常与龙相关,《汉书》卷49《冯奉世传》载:“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它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唐颜师古注曰:“言马形似龙者。”③(汉)班固:《汉书补注》(第10 册),(清)王先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5047 页。其次,“修弥马”的两足倚行之状也与汉代绘画中的域外良马形象相关。《洞冥记》有意强调“修弥马”的奔腾之状,《洞冥记》称其“腾虚逐日,两足倚行”④王国良:《洞冥记研究》,第105 页。。王国良先生注曰:“倚行,犹并排而行也”⑤王国良:《洞冥记研究》,第105 页。。汉代刻绘中的奔马多呈侧面,马的四肢多并行,呈申展腾空之态。⑥赵新平:《汉马图像程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安美术学院,2010 年。如出土于河北定县的西汉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其上所刻奔马就呈四肢并行腾空之势。这种自西汉中期开始大量出现的奔马图像,很可能与丝绸之路开通所引发的对域外良马的狂热现象相关。缪哲《汉代艺术中外来母题举例——以画像石为中心》认为汉代刻绘中两足倚行飞腾(Flying gallop)马形象的出现主要受到了伊朗与中亚绘画的影响。⑦参见缪哲:《汉代艺术中外来母题举例——以画像石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7 年。归根结底,无论是“修弥马”,还是图画上的飞腾马图案,它们都来自于域外良马奔跑所带来的刺激与想象。除“修弥马”以外,《洞冥记》中的“修弥驳骡”“步景马”“毕勒小马”等物象均与域外良马相关。“修弥驳骡”与“步景马”的共同点是异常高大且光彩夺目,这些特征明显仍是对以汗血马为代表的域外良马为现实原型的想象。而“毕勒小马” 虽日行千里,却身小如驹,⑧王国良:《洞冥记研究》,第105 页。其现实原型应为另一种域外小型马——果下马。《汉官旧仪》载:“中黄门驸马,大宛马、汗血马、干河马、天马、果下马。”⑨(清)孙星衍辑:《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76 页。《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载 “有果下马”。唐李贤注曰:“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⑩(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10 册),(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2818 页。。“果下马”不仅仅是“毕勒小马”的现实原型,在《博物志》中,“果下马”本身也是来自于秽貘国的异马。⑪(晋)张华:《博物志校证》,范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132 页。
丝绸之路的开通,还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域外脂类香料。西汉中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大量域外香料涌入中国。这不但改变了中国的用香习俗,在医药、宗教以及文学等诸多领域,域外香料都曾极大地影响过古人的思想与生活。《十洲记》所载“返魂香”就是一种以域外香料为现实原型的殊方异物。“返魂香”首见于《十洲记》,《汉武故事》《博物志》等唐前小说亦可见与之类似的故事情节。《十洲记》中的“返魂香”原产于聚窟洲人鸟山,月支国将之作为贡物献给汉武帝。武帝因排斥外来事物而轻视此香,后通过焚香驱疫、焚香起死回生等情节,武帝对“返魂香”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但最终异香失于封函之内,武帝也因此痛失长生机会。⑫王国良:《海内十洲记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第72—75 页。小说所描述的制香过程与域外脂类香料十分类似,所以有学者认为原产于域外的苏合香或安息香是“返魂香”的现实原型。⑬罗欣:《返魂香考》;温翠芳:《返魂香再考——兼与罗欣博士商榷》,《经济与社会发展》2012 年第2 期。“返魂香”这一文学物象的出现,无疑是域外脂类香料的神异化展现,所表现的是汉人对域外香料的理解与想象。如果没有丝绸之路的开通,域外香料的传入,小说实难空凭想象就塑造出“返魂香”这样的文学物象。
(二)丝绸之路对殊方异物情节与主题的丰富
《十洲记》汉武帝取“返魂香”祛疾除疫的情节,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有关焚香驱疫的记述。焚香驱疫是唐前小说殊方异香类物象非常核心且常见的一种异能。《洞冥记》“熏木”“精祇香”、《汉武故事》“兜末香”、《博物志》“常香”、《述异记》“反生香”等殊方异香也都具备驱除疾疫的异能。史书中虽未见有关汉代中原人焚香以除疾疫的记录,但小说中的焚香驱疫情节也许并非完全出于小说著述者的想象。在许多西方早期文献中,便有相似的用香情节。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的《俄狄浦斯王》就将场景设置在正在发生瘟疫的忒拜城,开场时的城邦,“城里弥漫着香烟,到处是求生的歌声与苦痛的呻吟”。到了第三场,《俄狄浦斯王》又明确将香料称作是祈求瘟疫消失的象征之物。①[古希腊] 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悲剧集:俄狄浦斯王》,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7 页、第48 页。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域外脂类香料的传入与流行,脂类香料的使用方式、效用以及相关驱疫传闻也可能会经由商贾或使者之口传入中国。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自然史》就曾指出,一些有关香料的奇异传闻完全是为了抬高香料价格而刻意编造出来的。②[古罗马]普林尼:《自然史》,李铁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年,第182—183 页。这也许正是汉代文献并未见焚烧域外香料驱除疾疫,而类似“返魂香”这样的殊方异香类小说物象却多具驱疫异能的原因。
丝绸之路的开通除了为小说提供物象与情节灵感外,还为小说开拓了供殊方异物展示的故事母题。唐前小说中的汉武帝故事,大多数兼具域外使臣献物情节,此类情节中的所献之物大多数又可归属为殊方异物。自《史记》设《大宛列传》以后,正史多设置专述域外事宜的《西域传》,这些正史《西域传》中的国家以及与丝路来物相关的记述也为小说提供了可作改写的原材料。西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始通,又恰逢国力强盛,朝贡制度逐渐确立,西域方物自此得以大量涌入中国。又加之汉武帝本人热衷搜求珍异,亲近神仙方士,可作改写的史料与传闻都十分丰富,故后世小说多将使者贡献、神仙馈赠这类故事托于武帝时期。又《史记·大宛列传》所述中外交往始自张骞,该篇基本记述的是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汉王朝对西域的认识与互动,两《汉书》专述域外的列传也基本承袭了《大宛列传》的内容与程式,所以多数出现于汉末以后的唐前小说,其中的殊方异物类故事多数都托于汉武帝时期,由此甚至产生了新的母题:汉武帝故事母题。上文讨论过的《十洲记》“返魂香”一则,就将西胡月支国献香托于西汉征和三年(前90),汉武帝幸安定时。安定郡始设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治在高平县(今宁夏固原附近),其下辖管二十一县。安定郡是在丝绸之路中国起始端,连接关中与河西地区的重要通道。如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8 即曰:“(安定)郡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铺,关中安定,系于此也。”③(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6 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第2774 页。由安定郡在丝路交通中的重要性就可理解,《十洲记》在择取故事发生时间与地点时是有一定细致考虑的。除《十洲记》外,《洞冥记》《汉武帝内传》《拾遗记》《西京杂记》亦多涉汉武故事,小说所托时间也常与丝路相关史料有一定呼应关系,由此亦可见丝绸之路的开通对殊方异物类小说产生影响之广泛深入。此外,专注于殊方异物主题的小说,大量出现于东汉末期以后。东汉建立以后,因国力远逊西汉,曾数次失去对西域的管理,丝绸之路也因此数度中断。经过班超、班勇、甘英等人的经营与出使,丝绸之路得到了恢复与开拓,更多的域外来物再次涌入,很可能也是激发汉末魏晋小说开始热衷殊方异物写作的核心动力之一。
二、殊方异物书写与博物小说的形成与发展
博物小说是中国文言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多数殊方异物类小说条目都可归入博物小说范畴之内。“博物”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左传·昭公元年》载:“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释“博物君子”为通晓各种事物,知识广博的人。④杨伯峻、徐提编:《春秋左传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670 页。这里的通晓与广博,说明“博物君子”对事物的见识不仅限于常人易掌握的俗常知识,是否能解说殊方异物类陌生物象,自然成为检验“博物君子”的手段之一。中国自古即有博物传统,而在这一传统中,已包含了对远方来物的辨别意识。
(一)殊方异物书写对博物传统的继承
早在先秦时期,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就已经开始了频繁的物质文化交流,西周时期出现的贡、税、赋制度,加强了中外物质文化的规律性往来,而远方异物在此时就已激起了古人的关注。《尚书·旅獒》篇载周武王时,西戎远国献獒犬,召公奭因远国所献獒犬殊异,而向周武王进警戒之言:“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①(汉)孔安国:《尚书注疏汇校》(第6 册),(唐)孔颖达等疏,杜泽逊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1843—1854 页。召公奭将物分为异物与用物两类,异物自然是指獒犬一类外来方物,而用物则可看作是常见日用之物的代称。《山海经》与《穆天子传》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母体源泉,同时也是博物小说的源头,而应引起注意的是,这两部先秦文献,尤其是《山海经》又恰好将叙述、辨别异物作为全书的核心内容。西汉以后,由于儒家的提倡以及物质文明的进一步丰富,博物之风日益兴盛,更多具有博物倾向的地理、小学书籍开始大量出现。汉代的地理书大多已亡逸,但由一些佚文来看,此时的地理书还是承袭了《山海经》记述渺茫远方的风格,其博物性更多还是在山川道里方面,当然此类地理书也有一定异物描述,这部分还是为小说殊方异物书写提供了许多营养。而以《尔雅》为代表的小学书籍专注对已知的真实俗常用物进行辨别名实工作,而并不以异物作为主要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似乎承担起了博物传统中的异物方向,尤其是接续起《山海经》异物关注的重任。
殊方异物书写的丰富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博物小说从《山海经》所开创的博物传统中成熟起来,并逐渐成为较独立的一种小说类型。《中国小说通史》指出:“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是以《山海经》为开端的专门记载山川动植、远国异民传说的志怪,如《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等等。……它主要是状物,描述奇境异物的非常表征”②李剑国、孟昭连:《中国小说通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56—57 页。。虽然在上文的定义中没有明确提及殊方异物,但就物象限定中的“远国异民传说”以及所列举的小说作品即可知殊方异物于博物小说的重要性。以《博物志》为例,其中殊方异物的占比已十分可观,如火浣布、切玉刀、续弦胶、常香、猛兽、乘黄、灭蒙鸟、鸾鸟、不死草、自然谷等物象都是非常典型的殊方异物。
《博物志》是一部抄撮故书、留存异闻的博物类小说作品,作者张华在《博物志》序中明言:
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诸国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后,并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详,其山川地泽,略而言之,正国十二。博物之士,览而鉴焉。③(晋)张华:《博物志校证》,第7 页。
张华自述著《博物志》的目的在于补《山海经》等书“各有不载者”,而由上文所罗列的物象来看,张华搜罗的大量“不载者”正来源于前代小说作品。当然除了小说中的殊方异物,《博物志》还搜集了正史、小学、地理、医药、异物志等诸多前代故书中的新奇名物,但与其他书籍中的这些物象相较,前代小说中汇集的殊方异物明显多具情节性与叙事性。虽然张华著书以物为核心,并称“作略说”,但阅读者还是能够体会到《博物志》中的殊方异物物象在状物、叙事侧重以及内涵上,较《山海经》已有了一定发展。
(二)殊方异物书写对博物小说的促进
《山海经》是小说之祖。博物小说的状物程式与《山海经》颇具承袭关系,在唐前小说殊方异物条目中也可以发觉《山海经》的浓重影响。《山海经》对陌生物象的形貌描摹方式几乎奠定了中国小说描摹陌生物象形貌的写作程式。《山海经》异物类内容最具开创性的部分还是在于状物,如专用于描摹陌生物象的“状如……(而)……”句式,就是由《山海经》开创并大量使用的特定句式。该句式采取模拟的方式,以现实中可知可见又与异物具备共同点的事物作为异物的模拟物,借助模拟物的形貌特征,对异物的轮廓进行初步的确认。在明确模拟物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异物与其模拟物的差异进行辨别,形式上则是对模拟物的某些特征进行改易增减,从而完成对异物外观形象的描摹。在之后的小说作品中,殊方异物的形貌描述大多承袭了《山海经》这一状物句式。如《神异经》载:“西南荒中出讹兽,其状若羗,人面能言,常欺人”①王国良:《神异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6 年,第79 页。;又如《十洲记》载:“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万里,……山中有火光兽,大如鼠,毛长三四寸,或赤或白”②王国良:《海内十洲记研究》,第63 页。;再如《洞冥记》载:“汉元封五年,勒毕国贡细鸟,以方尺玉笼盛数百头。大如蝇,其状大如鹦鹉,声闻数里,如黄鹄之音也。”③王国良:《洞冥记研究》,第70 页。借助于羗、鼠、蝇、鹦鹉等模拟物的形貌轮廓,异物描摹不必根眉毕述,而只需将描述更多地集中在声明差异的细节上,这正是《山海经》所开创的一种十分有效且简约的状貌方式。
然而唐前小说对殊方异物的描述不仅停留于《山海经》的状貌程式,其重心已经由辨别陌生物象,走向了更具文学性的内涵与情节叙述。还是以上文所举小说条目为例,《神异经》“讹兽”形象有明显的象征意义,《神异经》载:“言东而西,言可而否,言恶而善,言疏而密,言远而近,言皆反也。名曰诞,一名欺,一名戏。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④王国良:《神异经》,第79 页。《神异经》以数句并列来突出“讹兽”善于欺骗的特性,后文的异名也在强调“讹兽”是对欺骗行为的具象化象征,而人面能言以及人食其肉也会撒谎这样的表述,就更展现了以物讽刺的意味。《十洲记》“火光兽”一则的核心不是物象本身的光亮异能,《十洲记》载:“山可三百里许,晦夜即见此山林,乃是此兽光照,状如火光相似。取其兽毛,缉以为布,时人号为火浣布也。国人衣服,若有垢污,以灰汁浣之,终无洁净;唯火烧此衣服,两盘饭间,振摆,其垢自落,洁白如雪。”⑤王国良:《海内十洲记研究》,第63—64 页。“火光兽”的毛发是另一种异物“火浣布”的纺织材料,小说的重心在描述“火浣布”的火烧自洁异能,特别是对烧衣时间与处理方式的细节表述,更凸显了此类小说有意追求丰富叙事的潜藏倾向。《洞冥记》“细鸟”状貌后文引入了更具故事性的帝王宫廷传闻。小说将“勒毕国”贡献“细鸟”的时间托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细鸟”由此增添了一层域外贡物的身份。而后文引入汉武帝、妃嫔、王莽等人物及其与“细鸟”所发生的关联,又使小说的故事性更加丰富。而这种经由故事情节表达出的物象异能,是此类书写区别于《山海经》的又一进步之处。殊方异物书写虽然偏向于物象,但相较于其他博物小说,殊方异物类小说更多地引入了故事人物,张乡里《唐前博物类小说研究》就指出:“在博物小说中,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远国异民,也多是与国家、君王联系在一起。……博物类小说与君王有着密切的关系。”⑥张乡里:《唐前博物类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271 页。将渺茫物象的出现托于具体的时地,并引入帝王、使臣、方士、名士、神仙等人物,从而生发出与正史不同的帝王故事。《博物志》中的续弦胶、常香、猛兽等条目均属汉武帝故事之列。另一类涉及殊方异物的辨物故事,亦可归入为博物小说的讨论范畴。如《博物志》卷2 载:“西域使王畅说石流黄出足弥山,去高昌八百里。”⑦(晋)张华:《博物志》,第26 页。从《山海经》对陌生物象的程式化陈述,到通过西域王使的解说来转述物象来源或异能,这体现了小说在物象描摹上趋于复杂化的倾向。在《洞冥记》《十洲记》中,辨别异物的能人是武帝名臣东方朔,而自《博物志》以后,张华也成为了解说殊方异物的箭垛式人物。殊方异物是博物小说中十分重要的物象群体,殊方异物一类小说条目的出现,从物象、状物程式、情节、人物等多方面充实了博物小说,博物小说也因此能够与其他志怪、志人小说区别开来,并能够有更加独立的发展道路。
三、殊方异物书写的文学与美学特质
丝路来物开阔了古人的眼界,博物小说的兴起也彰显着古人对陌生世界的好奇与想象。唐前小说的殊方异物大多是基于现实的一种想象,而想象能力是人类较为原始且重要的特性之一。在人类的幼年,想象甚至是人类认识周遭世界的一种方式。想象也许使人远离真实世界,但却可以距文学与美学更近。李剑国先生《唐前志怪小说史》指出:“志怪小说的基础正是幻想,没有幻想就没有志怪。于是我们可以解释,何以这些简陋窘促的琐语卮言,竟能俘虏一代又一代的人们。”①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第18 页。殊方异物的审美特征主要以奇异为主,唐前小说殊方异物物象的珍异性,大多是通过突破固有认识、秩序的方式完成的。这里的突破,大多来源于对已有秩序边界的扭曲与跨越。这种以珍异为美的审美倾向,一定程度上治愈了人类长期处于现实生活樊网的压抑与焦虑。唐前小说殊方异物所激发的好奇与思纷,使中国文学较早地能够进入“物”与“我”的互动中来,从而获得思想自由驰骋的审美体验。与同期的诗赋等其他文学作品相较,小说中的殊方异物,不仅仅是被注视的审美对象。殊方异物的能力与存亡,常常直接影响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走向,殊方异物的变化,在小说中还是改变人物观念的契机。与正史偏重强调人的行动得失的决定性作用相较,唐前小说殊方异物主题偏重物象对故事发展的影响力,有时人物行动的作用还要暂居其后。
(一)殊方异物书写的文学特质
唐前小说以丰富的写作手段来凸显奇异之美。奇异包含了凸显奇特与鼓吹珍贵两种偏向。彰显殊方异物与现实俗物的差异,就是将珍异、矛盾乃至极端化作为塑造物象时的审美导向。通过对物象这些方面的提升与展示,唐前小说中的殊方异物类跳脱出俗世常规的束缚,获得一种徜徉于远方想象中的自由。而所谓俗世常规,一方面是自然规则,另一方面则是以儒家典籍和史书所编织的观念秩序之网。
小说对自然规律与生活经验的打破,主要是通过翻转现实与颠覆现实,还有颠覆俗常物象来实现。殊方异物类小说条目主要是通过物象的形貌与异能来彰显奇异的审美追求。在形貌方面,唐前小说创造出了灿烂缤纷而又奇异非常的殊方异物众象。那些自身光明的异草木、双瞳禽鸟、迅猛骏马、割肉返生的野兽、能言善卜的灵龟、弥小微虫、醉人美酒、冬季瓜果、火浣自洁的织物、复原弓弦的续弦胶,无一不是通过打破人对自然与生活经验的固有认识,从而获得出乎意料、新鲜有趣的文学感受。
同一殊方异物身上有时还会兼存矛盾对立的属性,如《十洲记》中的猛兽虽然是极小极弱的身形,但却拥有极强的攻击力。而这种极端化与二元对立集于一身的物象,就是有意将殊方异物与俗常物质世界区别开来。通过极端与对比,唐前小说中殊方异物在不断追求奇异的道路上,不断重迭与超越。如“养神芝”对疫病不但有治愈力,而且这种治愈力可以超越生死。“修弥国马”的奔跑能力不但超越常马,而且由于迅猛非常,其腾空之力被异化为飞翔之能。续弦胶不但能粘合金属与丝弦,其粘合力甚至超越了粘合本身,而变成一种复原与强化的能力。归根结底,这种超越是基于现实世界的极限夸大,是通过夸张的方式,使小说中的物象挣脱了现实生活经验的局限,从而获得了一种由想象力所驾驭的自由之感。现实所不能抵达的安乐与便捷、修复与长生,借由小说中的殊方异物,得以在文学领域内短暂地获得与实现。
极端化是唐前小说殊方异物物象凸显奇异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这些极远之地所产的难得之物,往往在小说中充当世间极限之物的角色。《神异经》有“豫章”“扶桑”“楂梨”等十余种通天巨树,也有可在蚊蝇羽翼下产卵生活的极小之虫“细蠛”。《玄中记》也多记述天下极端之物,如:“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举一螯能加于山,身故在水中。”②鲁迅校录:《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第235 页。再如:“东南之大者,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周回千里”③鲁迅校录:《古小说钩沉》,第235 页。。好珍尚奇激发极端化趣味,而极端化进一步激发唐前小说的创新性,唐前小说著述者不得不一再超越已知的边界,一次次以新的殊方异物形象来冲破旧有固识,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著述者掌握着异物知识的丰富性与权威性。极端化的审美追求也进一步促进了唐前小说的可读性,更多超出阅读者预期的殊方异物就在这样的审美意识之下被创造出来。唐前小说殊方异物书写对于极端化的审美追求体现在众多方面,可以说唐前小说殊方异物书写是一个充斥极端化物象、空间、环境、事件的奇异世界。
如上文所述,唐前小说中的殊方异物大多属于美好珍异之物,而它们有时象征着美好的易逝。极端化叙事昭示着变化,而变化带给人得失无常之感。唐前小说中那些美好的殊方异物物象,常常不能为凡人长期拥有。而由于故事中人物的短视、偏见、错误,导致殊方异物“得而复失”的故事,常常给读者带来喜悦与失落交织的阅读体验,这种故事情节的存在,以及“殊方异物”类条目对懊恨情绪较早的关注与叙述,都为唐前小说增添了一重以遗憾为美的情感深度。小说中“失而复得”的经历,极易使阅读者产生共情,这种与梦想擦肩而过所带来的遗憾,代表着一种悲剧意识的萌芽。可以说,唐前小说殊方异物书写所带来的遗憾之情,是中国小说早期发展过程中较富情感深度的重要部分。
《洞冥记》卷3 载:
有梦草似蒲,色红,尽缩入地,夜则出,亦名怀莫;怀其叶,则知梦之吉凶,立验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献一枝。帝怀之,夜果梦夫人,因改曰怀梦草。①王国良:《洞冥记研究》,第85 页。
《洞冥记》中的汉武帝思念已故的李夫人,故东方朔献“梦草”以暂解武帝相思之情。“梦草”的特性之一是“尽缩入地,夜则出”,其原名又为“怀莫”。“梦草”是对夜间思念之情更炽的一种隐喻。“梦草”所弥补的正是生人与逝者绝无相见机会的怅恨与遗憾。汉武帝通过怀抱“梦草”,在睡梦中短暂与李夫人相见。又如《西京杂记》“身毒国宝镜”一则。“身毒国宝镜”是一枚具有辟邪异能的宝镜。汉宣帝祖母史良娣将之系在尚在襁褓中的汉宣帝臂上。汉征和二年(前91)汉宣帝刘病已尚在襁褓中时,其祖母史良娣及其父母因巫蛊之祸而遇害,所以小说中的宝镜并不仅仅是辟邪异宝,它还承载着汉宣帝的思亲悲情,故《西京杂记》曰:“(汉宣帝)每持此镜,感咽移辰。”②(晋)葛洪:《西京杂记校注》,周天游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28 页。唐前小说中的殊方异物,虽然不着力于描写死亡,但在以殊方异物弥补生命遗憾的故事情节背后,所隐藏的正是严肃的生死议题。《十洲记》中汉武帝因失去“返魂香”而丧失长生机会,《洞冥记》汉武帝以“梦草”再见离世的李夫人,《西京杂记》汉宣帝对着“身毒国宝镜”思念早已去世的亲人,《汉武故事》中在西王母“仙桃”宴的戏谑、物象铺展、炫耀华丽宴席之外,所隐藏的也是生死话题。故事中“仙桃”曾三次出现,而每一次出现所带来的情绪是不同的,其中有憧憬、有失望,也有死亡焦虑。朱光潜《悲剧心理学》转引加尔文·托马斯《悲剧和悲剧欣赏》的观点:“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死亡是最大的不幸,是最可怕的事情,也因此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想象力的事情。”③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257 页。以物象来对时间长度进行夸张与扭曲,是生死话题的另一种表现。在千年一实的“仙桃”这类超越凡人生命的殊方异物对比之下,人类更显渺小,而这种对人生渺小短暂的遗憾之感,使小说更具艺术光彩。那些以失去为结局的殊方异物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使人解脱、净化的阅读体验。通过对小说人物的怜悯与同情,读者也经历了对重大失误的接受与历练,从而在较短的阅读时间内,收获了丰富多样而深刻的情感体验。
(二)殊方异物书写的美学特质
唐前小说中有一类“殊方异物”常在凡人世界中得而复失。这类小说中的人物一开始十分轻视异物,而当这些看似平常的物象展现出神奇能力以后,就会消失无踪,而故事的结尾大多以主人公表白悔恨,甚至是死亡作为结局。这种得而复失的情节所产生的波动,在引发读者共情的同时,能够给予读者伤感与遗憾交织的阅读感受。“懊恨”一词首见于《汉武帝内传》,书中记载汉武帝在初会西王母后,没有听从西王母与上元夫人的告诫,他“强悍气力,不修至诫。兴起台馆,劳弊百姓,坑杀降卒,远征夷狄,路盈怨叹,流血皋城”④钱熙祚校:《汉武帝内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20 页。。而在连续失去王母信任与东方朔之后,汉武帝终于体会到“懊恨”之情。《十洲记》“返魂香”一则,述西胡月支国献“返魂香”,武帝不信神香,而后在“返魂香”辟除疾疫的验证之后,武帝才“愈懊恨,恨不礼待于使者”①王国良:《海内十洲记研究》,第74 页。。《神仙传》卷6“淮南王”一则中的八公向淮南王转述武帝失信王母前后经过时,也提到了“懊恨”一词,查其内容基本源自《汉武帝内传》,故《神仙传》出现的“懊恨”一词是《汉武帝内传》的复现。懊恨所表达的是一种极度悔恨之情,而小说正是通过对故事人物情绪的渲染,进一步增强故事结局带给人的遗憾感受。《汉武内传》中的汉武帝在体会过“懊恨”以后,进行了一系列弥补行动,他遵从西王母与上元夫人的训诫,痛改前非,多次进行祭祀封禅活动,最终还是痛失羽化升仙的机会。如果将对情感的审美当作一种天性,那么就完全忽略了文学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扬·普兰佩尔《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就指出:“情感是社会所构建的,正如格里玛所说的那样,‘情感就是文化’。”②[德]扬·普兰佩尔:《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马百亮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389 页。小说率先使用“懊恨”一词来形容对过失的遗憾,对失去美好事物的懊恼,以及对死亡结局的恐惧与悲伤,这是小说著述者给予文学情感表达的一种贡献,其意义重大且深远。正是珍异之物的毁灭与消失,推动故事中的人物产生懊恼、悔恨种种情绪转变,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传达了小说写作者的观念,甚至对阅读者施加了一种教化的作用。可以设想,如果剔除掉小说中的这些殊方异物物象与故事,那么唐前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就缺失了对遗憾这种深刻情感的表达。尤其是在中国小说发展的早期,大多数小说篇目并不以表达情绪、传达感情为主要任务的情况下,殊方异物书写所展现出此类遗憾情绪的审美倾向是如此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