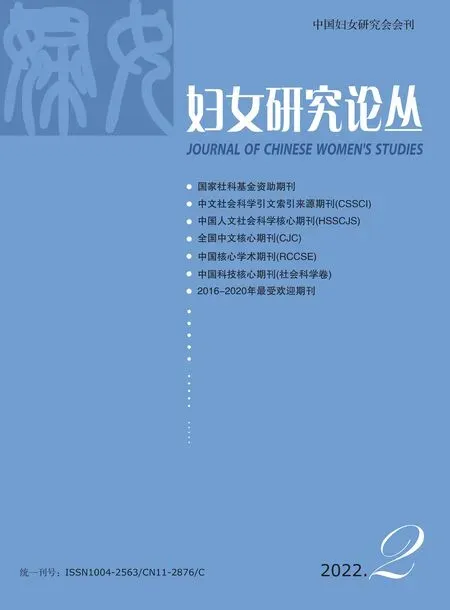交叉性理论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困境*
2022-02-04常佩瑶
常佩瑶
(贵州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境,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第三波女性主义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二元论的批判,使得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首次结合被称为“不幸的婚姻”。这个婚姻是否能继续以及如何继续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所面临的严峻考验。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是否能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当代女性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更复杂的境况。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差异”问题。当今女性所面临的不仅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所要解决的性别和阶级的差异导致的不平等、压迫和剥削等问题,还包括种族(race)、性(sexuality)、年龄(age)、能力(ability)、地域(location)、民族(nation)和宗教(religion)等一系列“差异”所带来的问题。与此相应,在政治实践方面则是如何在“差异”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广泛的激进运动联盟。理论与实践必须相统一,否则女性主义运动会面临在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走向分离和解体的危险。
第三波女性主义理论思潮中不可忽视的一派就是交叉性理论。这一理论思潮从产生到发展,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共鸣同时也保持着一定距离。交叉性理论的当前发展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交叉性理论所持的态度可谓大相径庭。但不论是否定和批判,抑或是接受和利用,在交叉性理论正在对当代西方左派激进运动和学术研究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现实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对交叉性理论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做出回应和解答。就像凯文·安德森(Kevin B.Anderson)指出的:“在二十世纪晚期,交叉性的理论话语在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生活领域几乎成为霸权……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称为一个当代的思想家,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不能掩盖交叉性理论的问题。”[1](PP 2-3)
一、交叉性理论的起源与当前发展
交叉性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女性主义,他们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发展起来,同时又批判其本质主义倾向,认为由白人女性主导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只关注白人女性所遭受的压迫,而忽视不同的种族、性、阶级和年龄所造成的压迫的差异性,导致了白人女性主义话语的霸权[2](PP 56-91)。
较早表达出这种观点的最具影响力的文献是1978年的《康巴黑河集体:黑人女性主义声明》(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3](PP 362-372)。这一声明强调黑人女性所遭受压迫的多重性和共时性,并提出独立的政治运动纲领:“我们将积极致力于反对种族、性、异性恋和阶级压迫的斗争,并将发展基于对以下事实的综合的分析与实践视为我们的特殊任务:这些主要的压迫体系是相互联系的。这些压迫综合造就了我们的生活状况。作为黑人女性,我们将黑人女性主义视为一个合理的政治运动,反对所有有色人种女性受到的多重的和共时的压迫。”[3](P362)
最先用“交叉口”(intersection)和“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表达黑人女性所面临的多重性和共时性压迫困境的是黑人法律学者金伯勒·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她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中将黑人女性在法律诉讼中遭受的困难形象地类比为发生在交叉路口的交通事故:
黑人女性所经历的歧视是以多种方式存在的……好比在一个四个方向都有来往车辆的交叉口发生的交通事故。歧视,就像通过交叉口的车辆,可以从一个方向上通过,也可从另一个方向上通过。如果交叉口发生交通事故,可能因为车辆从任何一个方向通过,并且有时候是从所有方向通过。与之相似,如果一个黑人女性因为她在交叉口受伤,她的伤害可能是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只有当黑人女性表明她们的诉求是基于种族或性别歧视,才为她们提供救助,这好比只有在确定是哪个司机应该为伤害负责时,才能为受害者叫救护车。但是认定一个交通事故并不容易:有时刹车痕迹和伤害仅仅表明它们同时发生,很难确定是哪个司机造成的伤害。在这些状况下,没有一个司机愿意负责,也没有救助实施,肇事者仅仅是回到车里然后迅速离开。[4](PP 140-149)
金伯勒·克伦肖认为,原有的关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概念以及相关的政治和法律分析框架,仅仅解决的是面临性别歧视女性群体中的特权群体“白人女性”和面临种族歧视的群体中的特权群体“黑人男性”所面临的问题。不论是女性主义的话语还是反种族主义的话语以及基于这些话语的理论分析框架,都来自于白人女性的经验和黑人男性的经验,而非黑人女性的特殊经验,导致这些理论无法解决黑人女性所面临的多重和共时的歧视和压迫[4](PP 139-140)。
此后,“交叉性”概念被广泛运用在黑人女性所面对的多重性和共时性压迫的分析中。1990年著名黑人女性主义学者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在其专著《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知识、觉悟与赋权政治》(BlackFeministThought:Knowledge,Consciousness,andthePoliticsofEmpowerment)中进一步发展了对交叉性问题的分析并提出“统治矩阵”(matrix of domination)的概念,用于阐明这些多重和共时的压迫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交叉性指的是交叉着的压迫的一些特殊形式,例如,种族与性别的交叉,或者性与国家的交叉。交叉性范式提醒我们,压迫不能被还原为一种基本类型,并且压迫共同作用从而制造了不公正。而统治矩阵则指的是这些交叉着的压迫是如何现实地被组织的。不论涉及哪种特定的交叉,结构的、规训的、霸权的和人际的权力领域都重复出现在完全不同的一些压迫形式中。”[5](P18)柯林斯“统治矩阵”的理论构想,将交叉性理论的建构提升到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克伦肖、柯林斯、莱斯利·麦考尔(Leslie McCall)、安吉·汉考克(Ange Marie Hancock)、薇薇安·梅(Vivian May)等一些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交叉性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交叉性”这一概念不但在左派激进主义的学术领域和激进政治的实践中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运用,还扩展到很多其他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和公共政治领域。例如近些年来的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伦理学、文化研究、传媒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传统学科的课程、专著和论文中,都能找到关于交叉性问题的讨论,以及交叉性视角的运用。一些人权倡导者和政府官员也将交叉性纳入全球公共政治讨论中。它不仅成为草根阶层的组织者在争取一些关于再生产、反暴力、劳工权利等方面的有力武器,还参与到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的热点话题讨论之中。
柯林斯在其与西尔玛·比尔盖(Sirma Bilge)合著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部专著中指出,如今如果追问“什么是交叉性”,或者如何定义“交叉性”这个概念,可能会得到一些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答案,但是她们也给出了关于“交叉性”的一般性的描述:“交叉性是一种理解和分析世界、人和人类经验的复杂性的方法。事件、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环境以及自我很难理解为由一种因素形成。它们通常由多种因素以不同且相互影响的方式形成。当谈到社会不平等问题,在一个既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和权力的组织更容易理解为并非由单一的社会分割的轴线形成,而是许多条轴线共同作用并相互影响的结果。交叉性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为人们理解世界和他们自身的复杂性提供了更好的途径。”[6](P1)
不同的交叉性理论家对“交叉性”的定义虽然大相径庭,很难将之称为一种统一的理论,但他们都将交叉性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即交叉性理论不仅是一种关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理论,还以此发展出关于如何将世界变得更好的政治目标和实践策略。艾希莉·博雷尔(Ashley J.Bohrer)将交叉性理论称为一种理论传统,它们之所以可以形成联盟,是因为它们之间达成了六个基本共识或核心原则[7](PP 91-95)。
第一,交叉性理论的关键和核心在于它批判对压迫的单一维度的表述,强调不同类型压迫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建构的特征。交叉性分析面对多种压迫形式和身份(例如种族、性别、阶级、性、残疾(disability)、公民地位(citizenship status)等)以及与之相关的霸权性的社会实践(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优越论、恐同症等),但是并不将它们视为不同压迫的叠加或者身份的叠加,也不是一些有序的和相互独立的因素,而是认为这些压迫以一种具体的方式相互构建、相互嵌入彼此,因此它们之间也不能还原成彼此或归因为彼此。举例来说,我们不能分别思考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而是应该思考“性别化的种族主义”或者“性别是如何被种族化的”,因此不能讨论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两种制度的作用,而用资本主义的父权制可能更好地对压迫如何产生进行说明。
第二,交叉性理论认为不同类型或不同维度的压迫是不能分等级的。其中包含了两个具体主张:不论是在理论上、经验上还是政治上,没有一种压迫比另一种压迫更重要;没有一种压迫单方面导致其他类型的压迫。因为在经验层面,压迫是不可分割的;而在本体论层面,压迫是在相互联系中共同被构建的。
第三,交叉性理论要求对压迫进行多层面和多领域的分析。压迫不仅发生在个体层面,同时也在结构性的、家庭的、政治的和社群的等层面和领域发生,并且在不同层面和领域相互构成并相互作用。
第四,交叉性将“身份”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理论的重要方面。交叉性将身份理解为多重的、以群体为基础的、历史构成的和异质的。它提出的“身份政治”是针对群体利益的复杂的、协商的政治,而非针对个人。
第五,交叉性理论虽然是一种理论目标,但是它是对社会运动和激进领域中的权力问题展开的思考,也是通过激进主义和激进组织实施的。
第六,交叉性理论既是对权力的描述,也是对权力的批判。它并非站在中立的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对权力进行描述。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它要求通过社会变革运动反抗权力造成的各种压迫,如阶级剥削、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性暴力等。因此它既是描述性理论,同时也是规范性理论。
基于交叉性理论传统中的上述几点共识和当前发展的研究可以发现,交叉性理论当前在西方学术领域的蓬勃发展甚至在社会其他领域的风靡和影响力的扩大,主要是基于它的包容性、批判性和实践性等特征或优势。
交叉性理论所使用的“交叉路口”“统治矩阵”或“多重危险”(multiple jeopardy)[8](PP 42-72)等生动形象却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的表述方式虽然备受指责,但这种模糊性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作交叉性理论一个极大的优势,因为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交叉性理论的发展可以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方法论或某个特定研究领域。交叉性理论的包容性首先表现在它在发展过程中与不同的方法论相结合的趋势。当前,不论利用哪种理论解释交叉性问题,即使这些理论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但只要不违背上述六种理论共识,就可以被纳入交叉性理论的“家族”。由于交叉性理论与后现代理论基于认识论上的基本共识——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并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交叉性理论当前发展的重要趋势是寻求与后现代理论在某种基础上的联合。例如,一些学者寻求将“集群理论”或“酷儿理论”融入交叉性理论中[9]。同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也试图寻求历史唯物主义与交叉性理论的结合。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使得交叉性理论具有内在异质性与非统一性[7](PP 81-85)。大部分交叉性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正是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才使得交叉性理论保持了“分析的敏感性”,能不断倾听不同的声音,并思考这些结构、经验、身份和压迫的观点之间的差异和相似性,关注这些理论想去命名和分析什么。交叉性理论的包容性其次表现在它的跨学科性。当前,交叉性理论已经开始逐渐渗透到哲学、文化研究、政治学、法学、心理学、教育学、地理学、文学、大众传媒等多个学科的学术研究中[10]。虽然当前交叉性分析在各个学科中还远算不上是“主流”,但至少可以称得上是“时髦”。交叉性理论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它关于身份维度的建构中。关于“身份”的讨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最初的性别、种族和阶级,越来越多的维度(包括但不限于性、宗教、国家、残疾、年龄)都被纳入交叉性范畴的讨论中,而这些范畴也是历史的、流动的和地域性的,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交叉性理论运用的时空范围,也是交叉性理论当前逐渐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原因。
不难发现,当前的所谓“交叉性理论”与其说是在为学术研究贡献一种“理论”,还不如说是贡献了一种新的理论研究的“视角”或“立场”。正是因为这种新的视角或立场,使得交叉性理论的批判性得到了充分展现,它不但挑战了原有的知识,还对一些学科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层面提出质疑。例如,玛丽·梅卡-布伦斯(Marie Mercat-Bruns)认为交叉性理论揭示出歧视问题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并引发对美国和欧洲当前司法程序中反歧视模式是否能对歧视问题真正产生效果的反思[11]。然而,交叉性理论的目标绝不仅仅限于学术研究和理论批判,柯林斯认为“批判性质询”和“批判性实践”构成交叉性理论组织和建构的核心,而实践主体不仅仅是地方性的和草根的,而且是面向国际的[6](PP 42-57)。在美国,交叉性理论主要是依托于西方政治体制中特有的“身份政治”发挥效用。相对于很多晦涩难懂的学院中的理论,交叉性理论显得异常贴近大众,使得人们能在共同的经验和身份认同基础上形成政治团体,通过政治手段干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如此,很多交叉性理论学者同时也是优秀的社会活动家,他们非常懂得如何借助大众传媒和互联网传播他们的思想,并积极参与到联合国等一些国际性组织的活动中。一些交叉性理论者还出版了针对儿童的普及性的绘本[12],登上了亚马逊儿童畅销书的榜单,真正做到了“从娃娃抓起”。
二、对交叉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交叉性理论最初是从第二波女性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阵营中产生的,但是随着交叉性理论在21世纪的蓬勃发展,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微妙变化。
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时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中明确包含了反种族主义,交叉性理论的先驱黑人女性主义者从属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阵营。她们在《康巴黑河集体:黑人女性主义声明》中申明黑人女性主义者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者,其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扩展:“尽管我们与马克思的理论在运用于其对特定经济关系的分析方面总体上保持一致,但我们认为为了使我们了解作为黑人妇女的具体经济状况,必须进一步扩展其分析。”[3](P366)
然而,随着第三波女性主义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取代,交叉性理论的话语影响力逐渐扩大,并发展成为第三波女性主义思潮中与后现代思潮并列的一支。1995年,交叉性理论创立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刊物《种族、性别和阶级》(Race,Gender&Class),一些交叉性理论逐渐不再将阶级纳入交叉性分析的核心,“阶级”范畴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取消掉。这立刻引起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警惕。《种族、性别和阶级》发刊的第2期中,特里·坎达尔(Terry R.Kandal)就提出要重视交叉性理论发展的“去阶级化”的危险倾向。之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苏珊·曼(Susan Archer Mann)、道格拉斯·霍夫曼(Douglas J.Huffman)、玛莎·吉梅内兹(Martha Gimenez)等也开始关注交叉性理论中的政治倾向以及其方法论层面与后现代理论的亲缘关系,并针对其政治策略和方法论展开批判。当前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很多学者都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行话语整合或创新的思路,年轻一代的学者艾希莉·博雷尔更是主张探索一条将两者有机结合的理论路径[7]。
在关于阶级的看法上,交叉性理论明确反对所谓“阶级还原论”,而仅仅是将阶级作为交叉性的一个维度或矢量,认为其他压迫形式不能被归因或还原为阶级问题,仅仅反抗阶级压迫也不能解决其他类型的压迫。大多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视的问题是,交叉性理论中对阶级还原论的恐惧和批判有着矫枉过正的危险。他们不否认交叉性理论强调压迫的多重性,但是对于阶级在多重压迫中的位置则与交叉性理论存在根本分歧。特里·坎达尔认为这与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新左派发起的激进民主政治中的“去阶级化”倾向有关。并且,这种淡化阶级斗争和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倾向,使得交叉性理论有走向主流政治和大众媒体宣扬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危险。他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在斗争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在当前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中,阶级问题要作为一种“宏观背景”和“宏观考虑”[13](PP 139-162)。
立场最为鲜明的是玛莎·吉梅内兹,她认为阶级压迫与交叉性理论提出的其他类型的压迫有着本质区别。交叉性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它模糊了阶级与其他类型压迫之间的本质区别,使阶级在交叉性理论中“被放错了位置”。她同意柯林斯的看法,认为女性所经历的不同类型的压迫,不论是种族的、性别的还是阶级的,都不能将其还原为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关于差异的分析,因为这种分析遗漏了构成压迫的权力关系和物质层面的不平等。但是,这不意味着阶级可以被视为一种压迫的矢量或身份,阶级压迫也不取决于某种“共同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建立的基础和核心。阶级不仅仅是一种压迫体系,它不能完全被视作像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一样的“恶”。阶级是一个已经客观形成的潜在的变革主体,它的作用不全是负面的。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导致社会变革,而种族和性别不行。但玛莎·吉姆内兹同时强调,这不意味着工人阶级是变革的唯一主体,反抗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斗争都可以帮助点燃阶级斗争,因为这些斗争都与阶级和剥削有关[14](PP 23-33)。
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玛莎·吉梅内兹深化了关于阶级的重要性的论述,认为“不能将阶级与收入或者社会经济地位混淆,将其降低为一种意识形态或阶级出身论,或者将阶级与压迫合并,例如阶级是性别的或者种族的。阶级和压迫属于两种不同层面的分析: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久结构,它的因果关系的影响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被感受到,然而压迫的身份和压迫关系更多是随历史变化的,它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被塑造,以适应变化着的经济和政治的需要”[15]。当前很多应该归因于阶级问题的对女性的伤害可能透过身份的透镜被经验和理解。例如,如果从单纯的女性主义视角来考虑,当前美国共和党想办法干预妇女通过合法手段和必要途径避孕和堕胎的做法被称为共和党“对妇女发动的战争”。然而,这种解释忽视了生物学再生产的限制性政策在不同阶级和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重要差异。不论种族、族裔和其他差异如何,资产阶级妇女和社会等级体系的上层可以规避这种政策的影响,因为即使医疗保险不覆盖避孕和堕胎费用或者堕胎在居住地被禁止,他们依然有能力寻求其他办法并支付得起相关费用,而这种政策对于处在没有足够的工资、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充足住房、缺少医疗保险等状况下的工人阶级才是有效的。因此,关于反堕胎的法案最好理解为一场针对工人阶级的战争[15](PP 23-34)。
霍利·路易斯(Holly Lewis)认为强调阶级的目的不仅在于阶级压迫在经验层面被感受到,更重要的是它在生产领域中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剥削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如果女性由于其生物性特征,真心喜爱社会分配给她们的角色,那么她们就没有在经验上感受到压迫。而阶级不同,即使经济持续繁荣,所有工人都感到很开心,在事实的剩余价值生产角度,他们也是被剥削的,这种压迫也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的核心是策略的,不是道德的。”[16](P274)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交叉性理论的另一个主要分歧体现在政治主张和政治策略方面。如果说“阶级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那么“身份政治”则是交叉性理论的政治主张的核心。交叉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于它对“身份”这个概念的话语建构上。在交叉性理论中,“身份”指的是一种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每个人都处于多重和共时的身份的“交叉点”上,例如种族、阶级、性别、性和民族。早在康巴黑河集体的声明中,黑人女性主义者就将身份政治确立为其激进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核心。不同交叉性理论家关于“身份政治”有不同主张,但是基本都赞同《康巴黑河集体:黑人女性主义声明》中提出的关于身份政治的四个核心原则:第一,身份是一种社会位置,这种社会位置是由一些不同的压迫体系相互叠加形成的;第二,身份也作为一种政治目标的概念,达到这种政治目标是通过意识的提升,即意识到在权力结构中共同的生活处境实现的;第三,身份政治将黑人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合理的政治运动,反抗黑人女性面对的多重和共时性的压迫;第四,身份政治认为有色人种妇女与其他像她们一样被剥夺权利的群体之间建立联盟的政治目标是重要的。宣言中明确的身份政治观点是反抗压迫和建立联盟的重要工具,它将身份理解为一种政治位置,而非一种本质[6](P115)。
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身份政治采取批判态度,认为它是危险和有害的。例如,玛莎·吉梅内兹和伊芙·米切尔(Eve Mitchell)都将身份政治视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认为它掩盖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玛莎·吉梅内兹指出,交叉性理论对身份的强调事实上模糊和削弱了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对身份的强调掩盖了事实存在的阶级矛盾和利益之争,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要给予阶级以优先权[15](PP 23-34)。伊芙·米切尔认为身份政治是时代的产物。1968年以后,美国的革命已经停止,黑人权力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已经被资本收编,其本身的进步性也被消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成为理论发展阵地。在实践上,阶级斗争的消失也使得理论生产成为真空,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们除了转向身份政治别无选择[17]。
苏珊·曼和道格拉斯·霍夫曼在讨论第三波女性主义的发展时指出,身份政治依赖群体认同和社会位置建立身份认同,在不同压迫群体间培养并建立以差异为基础的激进政治联盟。然而,被压迫群体是多种多样的,身份实际上为群体成员设置了排他的界线,存在着使政治实践走向“碎片化”和“部落化”的潜在危险。身份政治不仅影响着政治实践,也影响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定义和阐释方式,而这种基于身份的定义方式本身就是本质主义的和误导性的。例如,使用非洲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或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女性主义等概念,与其他的一些政治观点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等相区分。这种区分将共同肤色和种族的妇女绑在一起,忽视了其内部不同的政治立场[2](PP 56-91)。
很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阶级和身份政治方面的问题仅仅是交叉性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根本缺陷的外在表现形式。交叉性理论过多使用充满着一些数学和空间性的暗喻和假设,如交叉点、轴线、矢量、位置、多重共时性等词汇,其唯物主义立场的缺失会使得这种理论最终走向纯粹的话语建构。例如,霍利·路易斯认为,交叉性理论可以被看作第二波女性主义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双重压迫理论的扩展,它无非是将二元论扩展为三元论乃至多元论。其实质是将“女人”的不同经验移入,假设了一种多重矢量的压迫模式与个体主体相交,通过种族、性别、阶级、性、外貌(appearance)、能力等,在各个角度塑造主体,具体化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等。这使得压迫的来源似乎成为与物质生活无关的邪恶意志和坏思想[16](PP 273-274)。玛莎·吉梅内兹认为交叉性理论不能帮我们找到多重压迫的物质基础,它假定存在着根植于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特权之下的更基础性的结构,但没有提供一个宏观层面的理论观点用于区分这种结构。将种族、性别和阶级作为既定的东西并将知识的源泉诉诸经验,必然会导致理论的减弱。在构建知识时,对经验的强调应该作为对理论的修正,而交叉性理论中的这些假定反映的仅仅是部分人的经验,而非实质的共同利益。因此,交叉性理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根基是薄弱的[14]。
一些学者并非完全否定交叉性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但依然担忧其薄弱的理论基础最终会与后现代话语合流。莎伦·史密斯(Sharon Smith)认为,身份政治概念有两个不同的政治基础,一个来自于黑人女性主义,另一个是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她不反对黑人女性主义的身份政治,但是批判那些具有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特征的交叉性概念。交叉性理论最初起源于黑人女性主义,其身份政治是以群体之间的差异和群体身份为基础的。然而,交叉性概念自身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导致它越来越远离黑人女性主义传统,并逐渐被纳入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话语体系,走向个人主义的“差异”和“身份”概念,瓦解了女性主义运动共同的政治基础[18]。苏珊·曼和道格拉斯·霍夫曼持类似的观点,她们认为柯林斯等人发展的这种新的认识论采纳了与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相似的一些关键假设,例如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并关注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虽然交叉性理论和后现代理论都试图运用差异去解构本质主义、消解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但是它与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立场也有着一些明显的分歧,即它的“身份”概念是建立在集体之上而非个体,强调群体的共同经验。然而,这种理论的问题主要在于过于强调压迫的经验和话语建构而缺失了唯物主义立场[2]。
三、对交叉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尽管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对交叉性理论提出尖锐批评,但是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交叉性理论想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解释和应对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多重和共时性压迫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不能发展出关于交叉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那么再多的批判也无济于事。关于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他们的观点可以大致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主张“回到马克思”。这些学者持总体论立场,否定交叉性理论的多元论倾向,认为交叉性理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他们主张应该对马克思文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重新解读,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释交叉性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肃清交叉性理论可能带来的危害。
例如凯文·安德森认为,马克思的著作中关于性别和种族问题的分析非常多,但是没有引起交叉性理论家的足够重视。他将马克思的文本中关于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的理论和观点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摘录[1](PP 2-3)。但是,有交叉性理论学者回应道,他们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种族和性别问题的深入洞察,但认为马克思没能提供关于这些压迫之间关系的解释,而这才是交叉性理论关注的核心[7](PP 119-120)。
当前,玛莎·吉梅内兹、希曼尼·班纳吉(Himani Bannerji)和沙赫扎德·莫贾布(Shahrzad Mojab)等一些学者尝试通过重新解读文本以及话语转换解释交叉性问题。她们将交叉性解释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社会关系”,将交叉性理论提出的压迫背后的权力运作体制机制的根源转换为“生产方式”,即将当前资本主义理解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它包含很多社会关系,例如种族、性别和阶级等特定关系,这些关系相互作用导致交叉性问题的产生。
玛莎·吉梅内兹运用其一贯主张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交叉性问题理解为社会中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生活都受到阶级、性别和种族结构的影响(也包括年龄和其他不平等来源)。以马克思的术语来说,我们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我们就处于一系列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中心,而这些关系形成的基础是一些内在相互联系的等级制结构,这些结构共同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并作为那些可见表象的基础。我们需要注意某些广泛实践中的一些有问题的内在假设,即这些实践往往假设基于共同的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并且这些实践假设经验是基于性别、种族和族裔形成的。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的原因是,阶级位置(class location)以及在阶级中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将所有人区分为阶级(class)和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status),而这些阶层之间的利益往往是矛盾和冲突的。”[14](PP 23-33)沙赫扎德·莫贾布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描绘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是由处于既具有本土性和特殊性,同时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性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的辩证运动构成。这种运动依靠两种动力:一个是这些关系的内在冲突,另一个是社会现象的外在条件。这些关系决定了我们每天的日常经验,因此我们应该用这些关系的动态网理解日常经验。构成这些关系的“生产方式”是特定社会形态的组织方式,这些组织方式是为了保证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它是复杂的且历史变化着的[19]。希曼尼·班纳吉认为可以用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去理解种族、性别与阶级等交叉性问题。她以“种族”概念为例,“社会化种族概念”(socializing “race”)在理论层面将“种族”视为根植于特定物质生产方式中的社会关系的反映[20](PP 102-121)。
第二类主张发展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框架取代交叉性理论,将交叉性问题纳入一个更优的女性主义理论框架中,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和统一当前女性主义激进理论和实践。当前,学术界提出的新的理论框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再生产理论”,另一个是“酷儿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源于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一些学者对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的讨论。例如,莉丝·沃格尔(Lise Vogel)将妇女受压迫问题归结为妇女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21](PP 150-173)。这得到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阵营中很多学者的响应,例如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和苏·弗格森(Sue Ferguson)认为,可以将交叉性问题的分析纳入社会再生产理论框架中,因为父权制与种族主义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22]。
当前,最为激进的一波女性主义者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酷儿理论相结合,形成一个新的理论思潮,他们将这种理论立场称为“酷儿马克思主义”(Queer Marxism)。虽然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批判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唯心主义特征,酷儿理论也显然建立在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但是很多酷儿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酷儿理论必然走向唯心主义。例如,辛齐亚·阿鲁扎(Cinzia Arruzza)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从第二波以来相互作用以及交叉性理论的发展,认为虽然女性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产生的很大进展,但是还是没有更好地解决父权制及其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问题。而酷儿理论想要分析和阐明的正是妇女压迫的心理构成,以及作为再生产和性别角色分工的家庭和家庭关系对于性别建构和异性恋机制的维持和巩固的作用。探讨父权制等权力机制如何内化并作用于非经济领域以及如何对男性和女性共同产生作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交叉性问题。她认为,酷儿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唯心主义,并且这种理论发展对于激进政治实践的变革有着重要作用,也对一种超越文化与经济对立、物质与意识形态范畴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提出了新的要求[23](PP 124-128)。
第三类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交叉性理论有机结合,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交叉性理论。例如,莎伦·史密斯认为交叉性理论丰富了对压迫的解释,可以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压迫的理解进行一些补充和深化[18]。乔安娜·布伦纳(Johanna Brenner)虽然也认为交叉性理论中将阶级解释成一种“社会位置”模糊了阶级的本质,但是她认为应该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交叉性理论,并希望能通过身份政治建立激进群体的联合[24](PP 293-324)。
最新也是最深入探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交叉性理论相结合的学术专著是艾希莉·博雷尔的《马克思主义与交叉性:当代资本主义的种族、性别、阶级与性》(MarxismandIntersectionality:Race,Gender,ClassandSexualityunderContemporaryCapitalism)。她详细分析了交叉性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现状,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些理论争论,试图肃清相互之间的偏见和误解,并寻求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交叉性理论。她认为,大多数持批判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交叉性理论的发展没有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因此建立的只是一种“稻草人”式的批判,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存在的种族偏见。她深入分析了两个理论阵营之间的主要争论,认为两者的关键分歧在于对压迫与剥削关系的分析,并认为交叉性理论内部的一个流派,即关于压迫与剥削的“同等原生说”(equiprimordiality)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交叉性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并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可以运用到关于交叉性问题的分析中[7]。
她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压迫理论争论的根源在于如何看待压迫与剥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压迫的物质根源在于剩余价值剥削。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试图探寻的是性别压迫背后的物质根源。而当前交叉性理论提出的问题则是更多维度的压迫产生和相互作用背后的权力和制度根源。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攻击交叉性理论没有找到其他压迫形式的物质基础,或者认为其他形式的压迫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不是必需品,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才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和根本驱动力。即使对于莎伦·史密斯和乔安娜·布伦纳这些没有全盘否定交叉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不支持交叉性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例如阶级压迫与其他类型的压迫的同等重要性。他们对于交叉性理论的支持仅仅是策略上的,认为应该把其他形式的激进斗争纳入一个统一战线之中。而艾希莉·博雷尔则尝试的是建立一种符合交叉性理论基本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的交叉性理论。首先,她认同交叉性理论的一些基本立场和基本假设,没有将阶级看作更根本性的框架,并分析各种形式的关于压迫与剥削问题的“阶级还原论”和“经济还原论”中的问题,认为压迫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不同压迫类型没有一种比另一种更重要或者危害更大,不同压迫不能相互还原或者认为一种是其他类型压迫的根源,不同压迫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交叉性与马克思主义能够结合的共同立场在于,它们都认为资本主义是各种压迫的来源以及任何类型的压迫都具有其物质基础,压迫并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纯粹的经验或感受[7]。
艾希莉·博雷尔关于压迫与剥削的同等原生说将压迫与剥削的关系阐释为两者在根基性、平等的内在根源方面根植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并寻求一种对于压迫与剥削之间的深层的、复杂的和多重方向的关系,以非还原论的路径解释压迫与剥削的关系。例如,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当然有其经济根源,但是不能将其看作根本性的或唯一的根源。不过,她提出的同等原生说当前还仅仅是纲要性质的,它必须坚持如下四个立场:第一,资本主义不能仅仅还原为剥削;第二,资本主义不能仅仅还原为阶级;第三,阶级不能仅仅被还原为剥削;第四,种族、性别、性不能仅仅被还原为压迫。基于这四个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可以为交叉性问题的分析提供很多帮助[7](PP 185-206)。
四、结论
交叉性理论在当代的蓬勃发展反映出当前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透过交叉性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和调和矛盾的困难性不断增加。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压迫和剥削已经不仅仅体现在阶级方面,还体现在性别、性、种族、族裔、年龄、宗教和能力等其他很多方面。而资产阶级媒体和意识形态有意识地淡化阶级问题,反而使得其他形式的压迫从边缘走向中心。交叉性理论反映和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在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现实存在的和不容忽视的,这些问题和矛盾不但对女性主义,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挑战。在这个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在当前的发展中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考察交叉性理论,很明显地看到了其理论建构层面的种种问题和缺陷;另一方面,他们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策略去很好地应对这些交叉性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直接给出答案,而致力于将马克思与交叉性理论结合的艾希莉·博雷尔的同等原生说也还仅仅只是一个有待完善的设想和框架。从第二波女性主义开始,一些女性主义者正是出于对阶级还原论的不满而从西方的左派激进斗争中分离出来,之后是同性恋和有色人种女性主义,交叉性理论则走得更远。虽然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斗争,但是如何发展一种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建立政治上的联盟,也是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难题。
事实证明,仅仅强调阶级斗争是不够的,如果不关注其他理论的发展和其他政治势力的利益诉求,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自身走向衰落。交叉性理论在当前的蓬勃发展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相当大的重视和警惕。正如迪莉娅·阿吉拉尔(Delia D.Aguilar)指出的:“交叉性是妇女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迄今为止,该概念已被证明是相当经久耐用(durable)的。女权主义者的杂志充斥着它,女权主义者几乎不用解释它们的含义,该术语与女权主义的亲和力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不加质疑地被引入。参加任何妇女研究会议,迟早会听到这个口头禅。”[25]然而随着社会运动的衰落和资本对知识分子的蓄意利用,“当前被学术问题束缚的女性主义者早已放弃了之前分析的清晰性和目的的明确性,有意让交叉性理论变得摇摆不定(ambivalence)、模糊(obscurity)和故弄玄虚(mystification)”[25](P1)。当前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交叉性理论的批判或者改造,都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的这种担忧。如果不肃清交叉性理论的问题,或者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交叉性理论,马克思主义很可能会丧失西方左派激进斗争中女性主义的阵地。
近些年来,交叉性理论逐渐进入中国学术研究领域中。有些学者将交叉性理论作为一些学科的理论发展前沿问题进行了翻译和引介,并探索交叉性理论在中国本土问题中的运用。周培勤介绍了交叉性理论在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中的进展,认为将这种新的视角带入正在经历变迁的中国社会,对女性与空间的关系的研究方面会产生很多启发[26]。苏熠慧认为,交叉性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运用有助于我们审视中国女性内部社会分化、寻回底层和边缘的声音[27]。张也认为,交叉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面对现实中不正义形式的多样性并更好地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28]。杜平认为,交叉性理论有助于社会学中男性特质理论的拓展[29]。除了翻译和引介以外,一些学者还对交叉性理论在学术研究层面进行了运用。我国学者总体来说对交叉性理论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它有助于我们打开视角、拓展学术研究的领域。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从阶级立场、政治策略以及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对交叉性理论展开的批判,无疑触及了交叉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一些根本分歧,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与反思。在学术研究中,对于国外新的理论和思潮,我们当然要报以包容、学习、研究和借鉴的态度,但同时也不能亦步亦趋,而是要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探索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