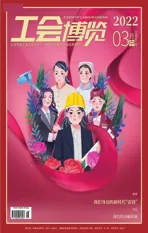《逸周书》衍生出的一些观点刍议
2022-02-04艾君
□艾君
提起《逸周书》,当今学术界一般又叫它为《周书》 《周史记》 《书》 《周志》等,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逸周书》是《汲冢周书》。无论冠以何种名字,这本残缺不全、记录“周时诰、誓、命”记言的史书,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史书之一。
《逸周书》,相传是孔子删定《尚书》后所剩,是《尚书·周书》的逸篇。汉代司马迁、郑玄、马融、蔡邕等人著作中曾有提起《周书》相关文字。而到了晋代,随着《汲冢周书》 的发现,社会民间开始流行《逸周书》的说法,有关学者在编著古书中也涉猎到《逸周书》之说。直到今日,关于《周书》 《逸周书》《汲冢周书》间的关系等在考古界、史学界和民俗界存在不同看法,出现了大量的有关学术文章和专著……
那么,《逸周书》 之说怎么来的?《周书》 与《逸周书》是不是一本书?《逸周书》与《汲冢周书》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刍议一:《逸周书》书名来源之论
对于《逸周书》之说的来源问题,近代以来,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汉代以来有关史料中提及的《周书》 《周史记》 《书》《周志》等就是《逸周书》;二是《逸周书》之名来自晋代《汲冢周书》。
一个书名的来历,为何会出现长期争论不休呢?分析看来,一个因为历史久远,又缺少相关史料明确记载;另一个则因为学者们所引述的史料会有歧义。阅读一些著作或文章后发现,古代一些图书中出现的《周书》 《周史记》 《书》 《周志》等文字与《逸周书》混淆不清。一些学者引述史料基本是出自清朝以后校勘的文献资料中,这里面或存有校勘者观点,出现歧义也是必然。
《逸周书》 里的“逸”应是散失、失传之意,“逸”在修饰《周书》而成《逸周书》,那么,之前的《周书》在哪里?如果说《逸周书》之名是来自晋代发现魏王古墓开始的,而《周书》的历史应更久远,起码在晋代之前,就是说有本《周书》在数千年历史的长河里已经失传。于是,也就有了种观点,《周书》与《尚书》相类,是部“周时诰、誓、命”记言的史书。我们知道,《尚书》最早书名为《书》,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分为《虞书》 《夏书》 《商书》 《周书》。所以,有学者便把《逸周书》断定为孔子删定《周书》篇后所剩,故为《逸周书》,这种说法似乎感觉与“逸”有些牵强附会。
而对于孔子删定所剩篇之说,应出自隋唐时历史学家颜师古(公元581 年~公元645 年)。在清朝乾隆武英殿刻本的《汉书·艺文志(卷三十)》记载颜师古注引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刘向说的话,“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这里也没有提过“逸”之字,但一些史学家由此推论在汉代《周书》是《逸周书》的本名。但疑惑的是颜师古所讲《周书》是不是指与其同时代其同乡的唐朝学者令狐德棻等人编写的《周书》?笔者并没有资料去深入考究,不过从唐代开始到现在,不少学者存在对流行版本不是《逸周书》原本存有许多质疑,认为《周书》是战国人所编。清朝乾隆武英殿刻本的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编写的《汉书·艺文志》中载有《周书》七十一篇,但其注说,“《周书》即《周史记》。”这里的《周书》没有明确指向是何本《周书》。有研究者发现,今存冠名为《逸周书》各篇其写成时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战国或西汉,另有个别篇章可能还经汉代人改易或增附。譬如,在《时训》提起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与汉以前历法相左。如此说来,原《周书》应在汉代已散佚不全。所以,在刘向校书时估计也就存有四十五篇,而今却传六十篇或七十篇本,应是后人编写。
对于《逸周书》之名是怎么来的,一些学者考究认为,《逸周书》 称呼初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即公元100 年~121 年间,不过许慎的《说文解字》提的是《周书》,也并无散失之意的“逸”字,可见,学者们还是把失传的《周书》 《周史记》 《书》《周志》等书与今存的《逸周书》相提并论。关于《逸周书》之名是从晋代开始之说,主要与晋代在汲县(今河南卫辉市)发现战国魏王古墓里发现有记载周朝史的竹书有关。此后,唐宋时编修的《隋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太平御览》等,在著录《周书》时,都认为它出自汲冢魏墓,是“汲冢竹书”的一种,加“汲冢”字样,并没见到“逸”字。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有如下记载,“旧本题曰《汲冢周书》。考《隋经籍志》 《唐艺文志》,俱称此书以晋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蒙中。则汲冢之说,其来已久。”同时,又记载道,“近代所行之本,皆阙《程寤》 《秦阴》 《九政》 《九开》 《刘法》 《文开》 《保开》 《八繁》 《箕子》 《耆德》 《月令》十一篇。馀亦文多佚脱。”可见,乾隆年间修史官员对《汲冢周书》 《周书》与流行的《逸周书》进行了比较考究,便把社会上散失的《周书》而题名为《逸周书》,这样书名才正式确定。
至今为止,笔者发现,学者们所引证的资料以及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大都是清后学者们修订或重编、注释版本,对于《逸周书》之名来源说法必然各异。而目前在一些文章或著作里,存在有《周书》 《周史记》《汲冢周书》 《周志》 《尚书义问》等与《逸周书》之间混用的现象,尽管内容有交叉或者相近,但《逸周书》书名真正确定还是在清代修《四库全书》期间。
刍议二:《逸周书》涉猎内容之争
近现代以来,针对《逸周书》涉猎的内容来历,史学界争论激烈,主要集中在《逸周书》涉猎的内容来自“汲冢书”和古已有之两种观点。以张心澄、金毓黻、李宗侗、朱杰勤等史学家为代表的著书立论,认为汉魏时已有《周书》,说明此书历史更早,并非出自汲冢。而以朱希祖、周予同、徐北文等史学家为代表的则主张,战国时期魏王古墓竹简书,经整理传世。
我们先看看《逸周书》是本怎样的书籍。今存传世本据说有十几种,以元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嘉兴路学宫刊本为最古老,但是很难见到。而现代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张元济费时七年,于1922 年初编出版的《四部丛刊初编》中所收录的是明嘉靖间四明章檗刊本。到清代对《逸周书》的研究校勘学者很多,让这部传世奇书引起足够重视。清乾隆间翰林院侍读学士、校勘学家卢文弨校勘的版本汇在《抱经堂丛书》,被称为“抱经堂本”,被后人认为是“最善的”。在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 年)间,戊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流传最广,他乃采各家之说,考定正文,正其训诂,存是删违,申以己意,成《周书集训校释》十卷。道光年间的诸生陈逢衡以卢文弨“抱经校本”为主,借鉴其它版本又参订《周书补注》二十四卷,还撰有《汲冢纪年存真》二卷,注其所出,考其异同。现在能看到的,还有史学者丁宗洛《逸周书管笺》、潘振《周书解义》、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以及王念孙《读逸周书杂志》、俞樾《周书平议》、孙诒让《周书补》、刘师培《周书补正》等,由此可见,在清代《周书》 《汲冢周书》与《逸周书》都是混用的。
隋唐之后,有关《周书》的记载出现变化,表现在对《周书》与《汲冢书》 《汲冢周书》相提并论上。这就是《隋书·经籍志》所讲,“《周书》十卷,汲冢书,盖仲尼删《书》之余。”《新唐书·艺文志》所言,“《汲冢周书》 十卷。”以及《宋史·艺文志》 所称,“《汲冢周书》十卷,晋太康中于汲冢得之。孔晁注。”有学者考究,现存版本的《左传》 《国语》以及《尚书》 《墨子》 《战国策》也有引《周书》文字,似与今存《逸周书》 相同,这也成为有些史学家们认为《逸周书》 是“先秦时期出现的一部记载周朝时诰、誓、辞命的记言体史书”的主要佐证。
从现今流行的朱右曾的《逸周书》版本看,全书有十卷,共计正文七十篇、序一篇。这与《汉书·艺文志·书类》所记“《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相一致。其中十一篇有目无文,现存只有六十篇(包括序文一篇),有四十二篇是孔晁注,十七篇无注者,各篇篇名均赘“解”字。其叙事上起周文、武王,下至春秋后期的周灵、景王,正文大体上按史事之年代早晚编次,记载许多重要史事,保存不少上古时期的历史传说,这与刘向认为的“周时诰、誓、号令也”相一致,大体反映了该书记言体史书的性质。其内容庞杂,体例不一,性质各异,与《尚书》的形式和内容比较相似。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出现一个广受欢迎的版本,这个全译本,以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十卷作底本,以当代史学家黄怀信的《校补注译》观点为基础,由黄怀信主持完成。
刍议三:《逸周书》与《汲冢周书》的关系
阅读一些史学家的相关著作或研究文章后,产生一些疑惑:在史料中提到的先秦时最原始的《周书》《周志》 《周史记》 《书》等是否同一本书并出自同一作者,其内容或包括《周书》与现存《逸周书》内容。晋代出土的记载周朝史的竹书《汲冢周书》是否就是后人讲的《逸周书》,只因时代变迁原来的《汲冢周书》散逸,故被冠以此名?笔者非专门研究史学或考古,对心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暂时无法解开。
我们先看看《汲冢竹书》。以上提过《汲冢竹书》,其是指晋代在汲郡战国魏王墓(一说魏安王墓)出土的一批竹简文献的总称。其具体出土时间众说不一,有咸宁五年(公元279 年)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说、太康二年(公元281 年)说和太康八年(公元287 年)说。现在一般认为,应以太康元年说较为可靠。根据《晋书·束皙传》等文献介绍,出土的《汲冢竹书》文献共有十几种,约七十五篇,现存编年体史书十三卷,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这些竹书中,对记载先秦诸国卜相妖怪的竹书被定名为《琐语》,共十一篇;对记载周穆王事迹的竹书定名为《穆天子传》,共六篇;对记载周朝史的竹书定名为《汲冢周书》,共十篇。其余竹书分别定名为《周易》 《国语》《名》 《师春》 《公孙段》等。不少记载与当时社会存在的传统观点大相违悖,譬如,禹子启遂即位,公天下首次变为家天下。《汲冢竹书》是我国古代的一批重要文化典籍,史学界把它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夹壁墙中发现的古文《尚书》 《礼记》 《论语》 《孝经》等,以及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同誉为我国文化史上古代的“四大发现”。
那么,其中的《汲冢周书》十卷今在何处呢?可惜,晋代当时汲冢所出土的竹书,多已亡佚,而今流传下来的《纪年》 《穆天子传》等,或为辑本,或残缺不全。从出土到今天历史走过了近两千年,就《汲冢周书》其当时内容到底如何,后来研究者都不得而知,只能从流传下来的一些两晋时期一些学者关于《汲冢竹书》的著录及描述中去推论《汲冢周书》大体情况。不过,在现存拓本《齐太公吕望表》碑文中可以发现《汲冢周书》残简中的部分内容。《齐太公吕望表》碑文,据说是当时汲县县令卢无忌在晋太康十年(公元289 年)所作。该碑原存河南汲县,抗战爆发后,下落不明。现存拓本有明拓本、清拓本、民国拓本等。
从现存拓本《齐太公吕望表》碑文可知《汲冢周书》的大概情况。碑文写道:“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得竹策之书。书藏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其《周志》曰:‘文王梦天帝,服玄禳,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赐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后亦再拜稽首。文王梦之之夜,太公梦之亦然。其后文王见太公而训之曰:‘而名为望乎?’答曰:‘唯,名望。’文王曰:‘吾如有所于见汝。’太公言其年月与其日,且尽道其言;‘臣此以得见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与之归,以为卿士。”其纪年说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数,盖寿百一十余岁。有学者从这段称引内容分析后发现,此《周志》的篇章结构上,虽以周文王与吕望问答对话为主,但实际上以推崇齐太公吕望为主旨。可见,原始的《周书》或《周志》,语言荒诞、推崇吕望。这与现在见到的《逸周书》的语言有些不符,或现存《逸周书》是经过多次校勘整合的。
从现存的古人关于《周书》观点看,刘向论定的《周书》其性质为“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著录的《周书》在“六艺略”《尚书》之后;而《汲冢周书》为晋代战国魏墓所出。原始竹本都已散失,以现有资料和个别文章所涉猎语言或者结构中,也很难判断出,《汲冢周书》与刘向、班固所言《周书》是否是同一本《周书》?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述所提到的《周书》或《周志》是战国人所编,则是无疑的。据史料记载,晋代“汲冢竹书”出土后残泐严重,其中仅《周易》《纪年》 《琐语》 《周王游行》四书可理清篇章,其余则“折简碎杂不可名题”。这说明《汲冢周书》则属于这些“折简碎杂不可名题”的部分,自然属于残缺不齐的散逸《周书》,所以,之后有学者们也常常会把《汲冢周书》加上一个“逸”字,即《汲冢逸周书》,这就有了《逸周书》之名来自晋代发现的战国魏王古墓的《汲冢周书》之说,直到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确定《逸周书》之名。再者,关于现存《逸周书》中,其中十一篇有目无文,而存在六十篇中四十二篇是西晋五经学者代表人物孔晁注,这是否与晋朝出土的《汲冢周书》有着必然联系,孔晁是否应出生在汲冢竹书出土之后,或其本人参与过竹书校勘……
以上疑惑笔者暂时无法考证确定。为此,笔者提出以下看法:其一,古代所称的《周书》 《周史记》《书》 《周志》等书名或并非《逸周书》或《汲冢周书》,应是在孔子修编《尚书》之前,西周之后,在历史中存在的一部记载周朝时诰、誓、辞命的记言体史书。其二,隋唐以后一些古书中所提起的《汲冢周书》或是《汲冢逸周书》,清乾隆以后定名为《逸周书》。因为历史信息沟通的局限性,历朝历代留下对涉猎古籍或概念以及作者混为一谈。
当代史学家刘重来教授有个折中观点认为:《周书》内容往往与儒家学说不合,孟子曾力斥该书,故汉代以后不受重视,散失颇多;《汲冢周书》则为盗墓者破坏,残损严重,加之西晋灭亡后的长期混战,此书一直搁在秘府,未能流传。所以,有可能今本《逸周书》是传世本和汲冢本互为补充的合本,由于两种版本都有残缺,故仍非完本。此说虽属新解,但究竟什么时代、什么人把残缺的传世本和残缺的汲冢本合编为一本的呢?仍无定论。
刍议四:《逸周书》的历史和社会价值
《周书》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现存版的《逸周书》虽有缺失,但经清朝诸家整理后,其价值逐渐彰显。特别近几十年来,《逸周书》相关研究的著作和文章不断涌现,使其逐渐成为史学界研究一个热点,其保存了许多西周及春秋时期的篇章,记载了许多重要史事,对研究先秦历史文化很有价值。
一是《逸周书》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其中《克殷》 《世俘》 《作雒》等篇记武王伐纣经过,是后人研究商周之际史事的重要依据之一。譬如,《克殷》文中载,“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又叙及了周王朝建立时的仪式,“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商纣之子武庚被封为商后,治理殷商移民,并“命管叔相”。这些史实可与《尚书·牧誓》 《史记·周本记》所载史实互相参照,是研究西周初年的重要史料。再譬如,《作雒》篇,记载了周武王死后周公东征平服三叔叛乱的史实。
二是《逸周书》 对先秦人类学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书中不仅记载了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有些篇还记载了人类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譬如,《职方》就记述了古代九州的人口、山川地理、物产、风土民情等史料,极为重要。而《周月解》和《时训解》列举了二十四节气之名,在古史记载中有独到之处。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吾侪读《尚书》 《史记》,但觉周武王吊民之师,其文明程度,殆为超人的。倘非有《逸周书》中《克殷》 《世俘》诸篇,谁能复识‘血流漂杵’四字作何解?”而现代史学家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也指出,《世俘》“所记社会情形与习尚,多与卜辞及吉金中所载者相合。”
三是《逸周书》为今人阐释性“语”体文献提供了材料。《逸周书》中的《王佩》 《铨法》和《周祝》等有非常多的“语”体文。“语”类文献通常以“明德”为目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有言类之语、事类之语,也有兼记言叙事之语,有散见之语等。“语”是先秦时普遍使用的一种文体,《论语》 《国语》《文子》 《管子》等书中都有成篇的语类文献,其作为古人生存经验、知识积累的结晶和为人处世的指南,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知识和共有的思想、话语资源,也是后人常常借用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