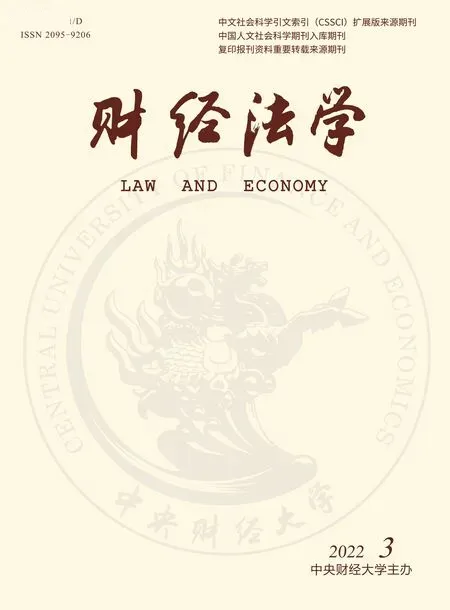论数字时代的美术作品原件
——基于展览权的视角
2022-02-04李强
李 强
内容提要:美术作品原件是我国著作权法上展览权的核心概念,然而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面对新技术、新业态提出的新挑战,无论是传统美术作品还是数字化美术作品,都存在着如何理解和认定美术作品原件的困惑。对此,有必要突破著作权法上关于美术作品必有原件、美术作品原件唯一和美术作品原件必为实体等传统认识,顺应技术发展的要求,紧紧抓住可展览性和不可替代性两个关键特征来构建美术作品原件的概念,并创建认定美术作品原件的一般规则。对于数字化美术作品,在满足“间接”可展览性的前提下,可以借助NFT技术将数字化美术作品完成时所形成的电子文档认定为作品原件。
一、问题的提出
在众多著作财产权当中,展览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大应用。近几年来,我国文博事业取得了大发展、大繁荣,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其兴旺发达最重要的权利基础就是展览权。我国著作权法上的展览权正是基于美术、摄影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以下或简称为“作品原件或复制件”)而定义的,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与展览权相关的第20条则几乎是作品原件的定制条款,(1)《著作权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作品原件所有权转移后原件展览权的归属,第2款解决原件受让人展览未发表的作品原件与作者发表权之间的冲突。可见作品原件在展览权中的重要性。
文化生活中,展示原件是举办文博类展览的基本要求和行业惯例,特别对美术作品而言更是艺术家展现创作才能、提高艺术声誉的主要途径,亦是美术作品实现艺术价值的主要方式。司法实践中,早年的“蔡迪安等与湖北晴川饭店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上诉案”(即《赤壁之战》壁画案)(2)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鄂民三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曾引发大量的学术讨论,案件起因即为绘制于饭店墙壁上的唯一壁画原件遭到毁损灭失。近年来,再次引发诸多学术兴趣的“钱钟书书信拍卖案”(3)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保字第9727号民事裁定书。和“茅盾手稿拍卖案”(4)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1 民终8048 号民事判决书。也聚焦于两位先生的手稿原件及其展览权,引来法院判决和学者观点的分歧甚至对立。(5)参见金海军:《论书信上的物权、著作权与隐私权及其相互关系——从“钱钟书书信拍卖案”谈起》,载《法学》2013年第10期;李翔、曹雅晶:《失落的展览权——从“钱钟书书信拍卖案”谈起,兼论〈著作权法〉第十八条之理解》,载《中国版权》2014年第4期;石超:《手稿著作权客体类型探究——基于“茅盾手稿案”的分析与思考》,载《中国出版》2019年第1期;陈瑞雪:《论文字作品的亲笔手稿著作权保护问题——以茅盾先生手稿著作权纠纷案为例》,载《福建法学》2019年第1期。还有判例将“音乐喷泉喷射效果的呈现”认定为美术作品,(6)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1404号民事判决书。那么音乐喷泉的喷射就是在公开展示美术作品,学者对此也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7)参见王迁:《论作品类型法定——兼评“音乐喷泉案”》,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李扬:《著作权法基本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第72页。作为展览权的主要客体,如果充分认识到美术作品原件的展示并不限于美术馆、博物馆、会展中心等专门场馆,还包括商场(含任何借助展示美术作品而进行营销的现场)、酒店、宾馆甚至街道等数量庞大的公众场所,(8)相关案例可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民终字第5951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7)东民初字第03991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武知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津01民终6756号民事判决书。那么,讨论美术作品原件既有重要理论价值又有重大实践意义,也充分展现了本文研究的问题导向。
然而,从法学角度对美术、摄影作品原件展开的研究非常少见。目前有限的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行《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展览权的定义)和第20条第1款(9)该款规定:“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改变作品著作权的归属,但美术、摄影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人享有。”的理解与适用上。比如, 作品原件转移后原件展览权的归属,(10)参见李明德、管育鹰、唐广良:《〈著作权法〉专家建议稿说明》,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97-98页;郑成思:《版权法》(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21页。作品原件转移后由原件所有人享有原件展览权则引出了作品原件所有权和作品著作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11)参见王福珍:《作品原件所有权与作品著作权的冲突及解决方案》,载《法学》1993年第9期;郭玉军、向在胜:《论美术作品著作权与原件所有权》,载《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唐昭红:《论美术作品著作权对美术作品原件所有权的限制》,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4期。。英文领域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在公共场所展示宗教物品的政教分离条款(the establishment clause)或展示艺术品的言论自由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12)See Christina A.Mathes,Bery v.New York:Do Artists Havea First Amendment Right to Sell and Display Art in Public Place?5 Villanova Sports & Ent.Law Journal,103(1998);Susan L.Trevarthen,Johanna Lundgren,Merry Litigation and Happy Attorney’s Fees:Holiday Display on Downtown Public Property,85 Florida Bar Journal,19(2011).以及数字图书馆、Twitter等社交平台的网上展示,(13)See David R.Hansen,The Public Display of Digital Library Collections,14 N.C.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145(2012);Jie Lian,Twitters Beware:The Display and Performance Rights,21 Yale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227(2019).极少提及作品原件或复制件。
笔者在梳理这些研究时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即围绕展览权或美术作品原件展开的探讨似乎将美术作品原件本身当成一个不用言说、不言而喻的概念。但是,越来越多的艺术创新对这种“想当然”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比如,用无人机编队或烟花燃放形成的艺术造型,用蘸水的笔在地面上写出的书法,还有将发型认定为立体美术作品的判例。(14)参见“何吉与杭州天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知终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在这些美术创作中,什么是美术作品的原件,美术作品是不是必有原件?人类已经进入数字社会,元宇宙也开始占据大众的视野,数字财产的价值和重要性渐次攀升。传统时代,美术作品的原件是有体物;数字时代,作为一种数字财产形式,数字美术作品的原件又是什么?近两三年来,越炒越热的NFT(non-fungible token,不可互替通证或非同质化代币)艺术作品逐渐成为数字时代收藏界的新宠和吸引流量的焦点,时不时报道出来的巨额拍卖令人咋舌。NFT艺术作品即为经由NFT技术加持的数字美术作品,那么,使用画图软件在电子屏幕上绘制一幅美术作品,呈现在屏幕上的画面,由该作品形成的电子文档,存储电子文档的内存模块或硬盘、光盘,还有制作出来的第一份纸版作品,哪一个是原件?
为此,本文在辨析作品原件和作品载体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基于展览权的角度纳入适当的考量因素,构建了可以兼顾传统美术作品和数字美术作品的美术作品原件概念,并创建了认定美术作品原件特别是数字美术作品原件的若干规则。
二、作品原件和作品载体的关系辨析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展览权的客体是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客体的载体是作品原件或复制件(以下或简称为“作品制件”),其本身也是物权的客体。
(一)作品载体学理分类的局限性
通说认为,作品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才能被他人感知;采取一定的形式固定,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不仅是作品创作的本质属性和实际需要,也是国际条约(《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2款)和相关立法例为作品提供法律保护的基本要求。这种固定的形式就是作品载体。
根据物理特性不同作品载体可以分为固定载体和瞬间载体,前者指有形的物质实体,后者指无形的物质,如口头作品之声波、表演作品之动作,数字作品的无形载体是电子脉冲。根据是否为首次依附分为原始载体和复制载体,前者又称原件,“是作品最初所附的载体”,后者又称复制件,“是承载原始载体上之作品的载体”(15)杨述兴:《论作品与载体的关系》,载《知识产权》2012年第6期,第42页。。
然而,与实践对比不难发现,除了通过最传统的纸笔或刻刀等方法创作的如著作手写稿、绘画、雕塑等作品外,上述原始载体和复制载体的分类不能直接用于确认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比如,用计算机撰写的著作,其原始载体是电子脉冲,复制载体是硬盘、优盘等存储器,但什么是该作品的原件却颇费思量。再如,口述作品的原始载体是无形的声波,复制载体是固定声波的磁带;而在大众认知中,录音棚或现场录制的母带是原件,从母带翻录的都是复制件。
所以,作品载体的上述分类主要是一种学理认识,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作品载体是固定载体或称为实体载体,如《著作权法》及实施条例多次提到的作品原件或复制件。具体到美术作品原件亦是如此,比如,“美术作品的‘原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原稿’,或者是‘原本’、‘底本’”(16)李建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美术作品必须被固定在物质载体上,不能像口述作品那样脱离物质载体而存在,否则也不可能有‘原件’和‘复制件’的区分了”(17)前引〔7〕,王迁文,第24页。。
(二)其他作品原件和美术作品原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重要差异
从司法实践来看,对于美术、摄影作品以外的其他作品,作品原件的法律意义主要体现在由于没有备份而毁损丢失时会导致整个作品的灭失。比如,在被称为国内首例教案纠纷的“高丽娅诉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著作权纠纷案”中,(18)原告原为被告所属教师,每学期按照被告的安排编写和上交教案,自1990年至2002年先后交给被告教案本48册。在原告要求返还教案本后,被告只返还了4册,其余44册被被告以销毁或者变卖等方式处理,下落不明。原告起诉被告要求其返还教案本并赔偿经济损失。原告在以物权纠纷起诉、上诉和申诉均败诉后,转以著作权纠纷为由起诉,最终胜诉。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渝一中民初字第603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渝一中民再终字第35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弄丢了原告12年间历次上交的大部分教案本(无备份)。其实,即便原告诉称被告遗失其作品原件系侵犯了其著作权,法院仍倾向于将之认定为侵犯了原告对作品原件的所有权,如“沈金钊诉上海远东出版社图书出版合同案”(19)原告按照出版合同约定将其唯一的手稿原件交由被告出版社出版,后被告将手稿的前两千页遗失。原告诉求之一即为被告侵犯了其对手稿原件的著作权。一审法院支持了原告请求,但二审法院认为被告侵犯了原告对书稿原件享有的所有权而非作品著作权。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7)沪一中民终(知)字第1469号民事判决书。和“邱传海与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等返还作品赔偿纠纷案”(20)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原告在先后三次参加被告组织的职称评审过程中,提交了包括文学剧本、电视剧分镜头剧本和著作手稿在内的大量作品手稿,绝大多数没有备份。评审结束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手稿材料无果,遂诉至法院。虽然湖北省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找到了部分手稿(约150万字)并发还作者,但仍有70余万字的手稿材料没有找回。该案历经区、市、省三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审理,原告虽然胜诉,但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没有认可原告提出的著作权侵权主张,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也没有认可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著作权侵权的抗诉意见,而是认定该案为“主张返还作品手稿原物及赔偿损失的物权纠纷”,维持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鄂民监二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抗字第5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邱传海案”)。在这两个案例中,原告的诉求都包括追究被告遗失其作品原件的著作权侵权责任,但是终审法院都没有支持原告的诉求,而是认定为涉及作品原件的财产权纠纷进行判决。
就美术、摄影作品以外的其他作品原件而言,从上述及类似案例可以得出三个重要推论。一是如果存有复制件,作品原件是否丢失无关紧要。二是如果缺乏复制件,作品原件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是作品的唯一载体,一旦灭失即意味着整件作品的灭失,至于是什么形式的载体并不重要。三是作品原件彰显的主要是使用作品的财产价值,而不是其本身的价值。比如,在邱传海案中,原告就诉称由于被告遗失其唯一的相关手稿原件,导致有关合作方取消了原告书籍的出版和电视剧的拍摄,造成了财产损失。
但是,如果涉案作品原件有可能构成美术作品原件,则不仅会关联展览权,而且侵权认定的性质也完全不同。比如,在“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案”和“茅盾手稿拍卖案”中,法院判决和学理研究均认为,在著作权法上,钱钟书先生和茅盾先生的手稿既是文字作品又是书法类美术作品,后者即为展览权的客体。(21)参见前引〔5〕,金海军文;前引〔5〕,陈瑞雪文。在这一类案例中,被告的涉案行为在侵犯原告物权的同时也可能侵犯了著作权,法院还需要判定被告公开展示美术作品原件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展览权。换言之,在涉及美术作品原件的案例中,即使存有海量复制件,作品原件本体的毁损或丢失即属于重大损失;作品原件本体不存,与其不可分离的原件展览权也归于消灭。
所以,上述针对其他作品原件的三点重要推论不能类推适用于美术作品的原件。主要原因在于美术作品与美术作品原件不可分离,以及美术作品原件所具有的可展览性。应该说,这两点都是美术作品原件的本质属性,且可展览性既是现行立法赋予美术作品原件的法律属性,又是其区别于其他作品原件的关键特征。《美国版权法》第101条定义的“公开展示权”不仅包括直接展示,还包括通过胶片、幻灯片、电视图像或任何其他设备或程序展示作品的载体;换言之,既包括直接展示和间接展示,也包括现场展示和网上展示。与之相比,一方面,我国的展览权定义没有使用诸如“借助其他任何设备或方法”的用语,应当是“直接展示”作品的载体即原件或复制件,不包括“间接展示”。另一方面,在我国著作权法的架构中,现场播放视频的展示行为适用放映权,现场网上展示作品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只有现场直接展示作品原件或复制件本身才适用展览权。所以,在我国著作权法的语境下,美术作品原件的可展览性就是指不需要借助任何设备或方法在现场直接展示原件本身亦即作品载体。
对于传统美术作品如绘画、书法、雕塑等,不论原件还是复制件都具有可展览性,展示作品载体就是展示作品本身,作品原件就是作品的原始载体,复制件就是复制载体。对于数字化美术作品,展示储存作品电子文档的内存模块或硬盘、光盘等载体不能得到展示作品的效果,即这些载体不具有可展览性,不能认定为展览权意义上的原件或复制件,尽管可以作为作品的原始载体或复制载体。所以,有学者指出,“‘原件’这一概念仅于传统创作形式的美术作品之上才有意义,才能体现出原件与复制件之差异”(22)杨明:《文字作品v.美术作品:对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反思》,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2期,第261页。。摄影作品存在同样的问题,传统的胶卷可以作为原始载体,但不能作为原件;数码相机里的存储卡可以作为原始载体,也不能作为原件。正是因为数字化美术作品的原件和载体之间的关系迥异于传统美术作品,才导致不易判定数字化美术作品的原件,这也是技术的发展对著作权立法提出的具体挑战。所以,在构建美术作品原件的概念和创建美术作品原件的认定规则时,必须将数字化美术作品的特殊性纳入考量。
三、构建美术作品原件的概念
(一)两个重要区别
1.美术作品原件与复制件的区别
无论对创作者、观赏者还是所有者而言,美术作品的原件和复制件在价值上相差悬殊,本身存在着质的不同。尤其是作品原件与作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人身联系,在精神和经济上均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蕴藏着作者最原初的艺术才情、创作技巧和身心投入,不能为复制件或任何同主题的再创作所替代,与美术作品不可分离。在文博行业,不论是文物还是艺术品,以展览真品和原件为基本原则和最低要求,观众也以欣赏到原物和真迹为最大期盼;如果展出的是复制件或所谓的高仿件,则必须特别标明,尽管这必然会贬损展览的档次。在最能体现美术作品经济价值的拍卖行业,也是以“原件为王”,拍品一般都要附上权威鉴定机构的“验真”证明,否则根本上不了拍卖目录或拍不出高价。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作品原件都是展览权架构中的核心概念和主要保护对象,因此也突显出准确建构美术作品原件的概念和创建美术作品原件认定规则的极端重要性。
2.作品原件的唯一性和作为原件载体的物的唯一性的区别
在严格意义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个物,每个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承载作品的原件亦是如此。在数字化技术出现之前,对于美术作品而言可以将作品原件的唯一性和作品载体物的唯一性等同起来,对于摄影作品原件则需要另外讨论。数字化技术出现之后,只能笼统地说,作品原件的唯一性不是其载体物的唯一性,载体物的唯一性也不能决定作品原件的唯一性。对于数字化美术作品,如果使用同样的方法和材质,得到在普通人视觉上一般无二的两份及以上作品,如果均认定为作品原件,那么即可认为其唯一性被打破了;而作为承载作品的物,其相互之间仍然保持了各自的唯一性。
(二)几点重要考虑
从展览权的角度构建美术作品原件的概念,应当将以下几个方面纳入考量。
1.美术作品的范围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8项规定:“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包括纯美术作品和实用美术作品。其中纯美术作品,是指仅能够供人们观赏的独立的艺术作品,比如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画等。实用美术作品,是指将美术作品的内容与具有使用价值的物体相结合,物体借助于美术作品的艺术品位而兼具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比如陶瓷艺术等。(23)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注解与配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无需(美术)专业审视就可知道,我们通常认知的美术作品显然比上述规定要宽泛得多,各国立法例中美术作品的范围多数也比较宽泛。对于美术作品的法律界定和范围,既有国际公约的规定(《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又有学者的细致分析,(24)参见郭玉军、陈云:《美术作品概念、成立要件及其范围的法律探讨》,载《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王迁:《论平面美术作品著作权的保护范围——从“形象”与“图形”的区分视角》,载《法学》2020年第4期;赵书波:《美术作品作者财产权益保护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20页。均可借鉴。
实践中,符合大众认知和法律明确规定的美术作品较好判断,困难的是那些非典型的美术作品,比如名家的书信和手稿,还有音乐喷泉喷射效果的呈现和那些具有审美意义的建筑设计图、视觉效果图、手绘地图和模型等,也可以视为美术作品。随着《著作权法》的最新修订确立了“作品类型开放”的立法模式,还会出现更多不常见的美术作品类型,在事实上也增加了认定美术作品原件的难度。
2.兼顾通过传统方法和通过数字化技术得到的美术作品原件
考察法律释义和学理研究,我国著作权法上美术作品原件的概念是建立在有体物基础之上的。比如,“美术作品原件,是指美术作品首次固定之有形载体”(25)前引〔7〕,李扬书,第136页。;“作品原件,即作品的原始载体,是指作品在创作完成之时被固定其上的有形物质载体”(26)曹新明:《作品原件所有人的告知义务研究——兼论〈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11期,第42页。。《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2款也规定,未以某种物质形式固定下来的作品不受保护。对于用传统方法创作的美术作品,如此理解并无疑义。有疑义的是,如何确定通过数字化技术得到的美术作品的原件。比如,通过画图软件得到一幅美术作品,当作品完成时呈现在显示器上的画面是不是原件,这种呈现是否属于“固定”在载体上。(27)有学者认为,数字作品的物质载体是无形的电子脉冲。参见前引〔15〕,杨述兴文,第41页。《美国版权法》第101条规定,用于固定作品的载体,应当具有“足够的长期性与稳定性”,以使作品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可以被感知、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传播。考虑到显示画面的暂时性和该美术作品形成的电子文档在计算机内存上存储的暂时性,显示画面和内存模块似乎不能成为作品原件。由美术作品所形成的电子文档和存储该文档的计算机硬盘或光盘由于不具有我国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直接”可展览性,也不能当然地认定为原件。
版画作品和3D打印作品的原件也存在类似问题。版画的制作具有特殊性,先制版再印刷。先行制成的模版不是完整的版画作品,(28)当然,具有审美意义的模版本身也是一种模型类的美术作品。不能视为版画作品的原件。如果套色印刷一张或若干张版画后,作者为了保证作品的稀缺性而毁掉模版,则印出来的版画作品(不论几张)即为原件似无疑义。如果保留模版,随时都可以印制出同样的版画作品,那么什么才是原件?或者说,在留存模版的情况下,版画作品是不是没有原件、只有复制件,或者印制出来的都是原件?
3.突破美术作品原件必为物质实体的传统认识
目前理论和实务上均以物质实体为基础来认识美术作品原件,如“美术作品原件,是指美术作品首次固定之有形载体”(29)前引〔7〕,李扬书,第136页。。然而,随着2020年11月《著作权法》的最新修订,这种传统认识正在发生变化。作为修订的一项重要内容,《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的作品定义被修改、提升为《著作权法》第3条,(30)该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定义中的关键要素“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改成“能以一定形式表现”。对前者的重要理解之一就是作品可以以某种有形形式固定,而改为“能以一定形式表现”即放弃强调形式的有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作品的固定性要求。
换言之,作品是不是必须固定下来,是不是必须以实体的方式存在,已经不是作品的构成要件了。那么,这种改变必然会影响到对美术作品原件的认识。早在二十多年前,日本著名学者就曾预言:“数字技术正在逐步的切断以往传统的著作物商业交易中所见到的无体物对有体物的寄生关系……著作物不再借用有体物的外衣而独立存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31)〔日〕北川善太郎:《网上信息、著作权与契约》,渠涛译,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3期,第42页。《巴西著作权法》第7条也规定:“受保护的智力作品是指智力创作成果,而无论其表达形式如何,也无论其以任何有形的或无形的、现在已知的或将来可能开发的载体固定。”(32)《十二国著作权法》,《十二国著作权法》翻译组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所以,为了适应数字经济,有必要前瞻性地改造美术作品原件的传统认识。
4.突破美术作品原件唯一的传统认识
在学理研究和审判实践中,普遍认为作品原件具有唯一性。前者如,“对于具体的作品而言,每个作品对应的原件具有唯一性”(33)袁博:《著作权法解读与应用》,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123页。;美术作品原件“有着复制件无可取代的价值和唯一性”(34)前引〔22〕,杨明文,第261页。。后者如“成都市黑蚁设计有限公司与东宏实业(重庆)有限公司等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法院认为:“作品原件一旦形成,就具有唯一性,创作者永远也不可能再创作出一件与原件完全一样的美术作品。”(35)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渝高法民终字第76号民事判决书。在用传统手法创作的年代,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颠覆了这种认识。比如,将电脑绘制的美术作品使用同样的打印机和纸张制作若干纸版,有可能都会被认为是原件。版画作品和3D打印作品的原件也是如此。版画的制作一般是先制版再印刷,制好的模版不是完整的版画作品,不能视为版画作品的原件。如果套色印刷一张或若干张版画后,作者为了保证作品的稀缺性而毁掉模版,则印出来的版画作品不论几张都是原件。对此,《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22—8条第2款也规定,作品原件是指由艺术家亲自创作的作品,以及由艺术家亲自或在其指导下完成的限量版作品。所以,对于某些特定的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作品原件有可能不唯一。
必须指出,突破美术作品原件唯一的传统认识并非认为所有美术作品原件已经不再具备唯一性特征,而是表明唯一性已经不能作为一个能够涵盖所有美术作品原件的绝对特征,但不妨碍其仍可作为绝大多数传统美术作品甚至数字化美术作品的特征。比如近年来火爆全球的NFT数字艺术作品,在NFT技术的加持下也具备了唯一性。NFT是在区块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加密技术,通过区块链来记载上一个区块数字美术作品计算机文档的哈希值,其中就包括该作品每次流转的所有数据,并形成链接关系。任意一个区块发生人为的删改,后面相连的所有区块哈希值都会发生变化,于是链接上的每个环节都能发现数据被篡改,这样可以有效防止NFT数据被随意或恶意篡改。(36)参见王功明:《NFT艺术品的价值分析和问题探讨》,载《中国美术》2021年第4期。同时,根据哈希算法,对数字艺术作品的任何修改都会产生不同的哈希值。因此,他人无法改变数字艺术作品以及链上哈希值而不被发现,也就保证了附有NFT数据的美术作品原件的唯一性。当然,这种唯一性并非通常意义上物理实体的唯一,也不是指在数字世界里只有一件数字美术作品,而是在无法篡改的技术保障下通过权属证明表现出来的“唯一”。
5.坚守美术作品原件的不可替代性
美术作品原件的唯一性与其不可替代性紧密联系,著作权法强调保护美术作品原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作品原件可以被替代,变成对创作者、收藏者和观赏者可以旧去新来的物件,法律也就没有必要加强保护了。对于多数传统美术作品,作品原件唯一就意味着不可替代;而对于某些特定的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突破作品原件唯一的传统认识并非否认其不可替代性。实际上,不可替代性是确认美术、摄影作品原件的关键要素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将根据底片(胶卷拍照)或数码照片文档(数码拍照)洗印出来的照片均认定为摄影作品原件,(37)参见前引〔7〕,李扬书,第137页。实际上是否定了原件的不可替代性。必须认识到,正是不可替代才使得美术作品原件稀缺而珍贵。
对于数字化美术作品,NFT作品的每一个TokenID(token identity document,代币唯一编码)都是独一无二、无法替代的。(38)参见江哲丰、彭祝斌:《加密数字艺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监管逻辑——基于NFT艺术的快速传播与行业影响研究》,载《法学论坛》2021年第4期;王铼、曹莹:《NFT的境外法律监管》,载:http://glo.com.cn/Content/2021/05-24/141001340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2日。即通过NFT技术,防止篡改和无法消除的权属凭证伴随并记录着该“唯一”美术作品的每一次流转,与其不可分离,在观念上、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得到公认,保证了NFT美术作品的不可替代、不可互换。也许存在跟某件特定NFT美术作品数字化质量完全一样的其他NFT美术作品或非NFT美术作品,但是在NFT技术的规则之下,不存在相互替代的可能性。
6.充实展览权的定义
现行著作权法赋予美术作品原件以“直接”可展览性,即现场直接展示作品原件本身。这对于展示作品载体即是展示作品的传统美术作品没有问题,但是却不能适用于以优盘、光盘为载体的数字化美术作品。当然,也可以将其打印出来展示,然而数字化美术作品的美感和价值更多的时候难以通过打印版展现出来。比如,三维美术作品的最佳展示方式是数字化的多角度展示,像素高度压缩的美术作品需要通过逐渐放大像素的方式来展现细微之美,还有动态的数字化美术作品也无法通过静置的方式展示。而且,同技术发展与时俱进的展览模式经常求新求变,那些比实物静置方式更活泼、效果更好的展览行为其实不受展览权的调整,比如常见的播放视频适用放映权,网上展示作品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以,有必要充实展览权的定义,参照《美国版权法》的“公开展示权”,明确规定既可以直接展示作品,也可以借助其他设备或方法间接展示作品。换言之,即赋予数字化美术作品以“间接”可展览性。
(三)构建美术作品原件的概念
虽然“作品原件”在我国著作权法中频频出现,却无相应定义。笔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应当明确“美术作品原件”的法律含义。美术作品原件与复制件相对应,其概念必然要反映出二者的区别性,关键在于如何阐释“原”或“原件”的含义。笔者认为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阐释为在时间上作品“首次”附着于载体或数字化作品的“首次”完成。前者是对传统上作品原件必为实体的理解,作者在载体物上完成作品之时,该载体物即成为原件;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3条第1款第14项规定“原件指著作首次附着之物”,也是强调时间上的“首次”。后者是突破作品原件必为实体的认识,一幅数字化美术作品完成之时,即首次达到“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法定要求,具备了成为作品原件的可能性。
第二个方面是阐释为作为复制件来源的原始件。原件先于复制件,复制件源于原件。复制可能是“二手”或“三手”,复制的维度也可能经历了二维和三维之间的转换,但是只有最原初的那件作品才是原件。
如果原件已经遗失,作为原件的“一手”复制件,虽然是所有后续复制的来源,但显然不能认定为原件。此时就需要引入第三个方面,即“作者亲自创作完成”,这也正是作品创作的“原初”状态。其实,第一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只不过是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表述而已,作者亲自创作作品过程的结束之时也就是作品“首次”固定或完成之时。参考《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22—8条第2款,对于某些特定的作品,在作者指导下完成的限量版作品亦可认定为原件。比如,作者完成了模版的制作,然后亲自或指导他人印制出限量版画。
综上所述,可以将美术作品原件定义为:作者亲自创作且具有可展览性和不可替代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美术作品。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属+种差”的逻辑定义,(39)这是一种常用的逻辑定义方法,被定义项由其属概念和其区别于其他种概念的种差组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是淡化了传统上强调美术作品在时间上的“首次”,将之隐含于“作者亲自创作”之中。凡是作者亲自创作的必然都是“首次”完成的作品,即便是作者反复创作主题、内容、布局、色彩等完全相同的作品,每一次创作都是单独创作,得到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原件,而不是第一件作品或前一件作品的复制件。作者也许还会亲自复制,但既然不是创作,就只能是复制件。“作者亲自创作”实际上是所有作品原件的根本来源和本质属性。所以,如此定义表明了作品原件的本源,既强调了其在创作主体上的特定性,也涵摄了其在时间上的“首次”。
二是突出了美术作品原件相对于其他作品原件和美术作品复制件的差异性即“种差”。我国《著作权法》上的美术作品原件应当具有可展览性,这既是与其审美属性相辅相成的另一种本质属性,也是区别于其他作品原件的“种差”。在前文所述案例中,其他作品原件和美术作品原件的判决要旨截然不同,后者总是考虑是否侵犯了展览权。美术作品原件的不可替代性则是其区别于复制件的“种差”。作品复制件的可替代性决定了其不能像原件那样彰显作品与作者之间的人身联系,也无法达到作品原件的财产价值、收藏价值和观赏价值。如果说可展览性还可能会因为法律规定的不周延而产生不同理解(即“直接”和“间接”之分),那么不可替代性则是美术作品原件坚定不移的本质属性之一。
三是淡化了传统上认为作品原件必为实体的认识,既符合《著作权法》对作品定义的最新修订,也极大地扩展了作品原件的表现形式。《著作权法》的最新修订以“能以一定形式表现”替换作品定义中的“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顺应了技术发展的时代趋势。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数字化美术作品(包括将传统美术作品数字化)将放弃实体化的展示,而采用形式更加多样的数字展示方式。在美术作品原件的概念中使用“一定形式”的表述,既包括物质载体的形式,也囊括了现在及将来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所能带来的一切展示形式,大大提升了立法的前瞻性和应变性。
四、创建美术作品原件的认定规则
(一)美术作品原件的一般认定
以前述对美术作品原件概念的理解为基础,笔者认为,现实中美术作品原件已经具备了以下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是作品原件唯一,绝大多数通过纸笔或刻刀等传统手法创作的美术作品如是。作品原件就是美术作品首次固定于其上的物质载体,其与复制件在载体性质、大小比例甚至平面还是立体上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比如将画作、书法编印成集,将雕塑作品按比例缩小或印成图册。
第二种可能是存在若干份作品原件。比如,已经毁掉模版且印制质量、尺寸完全一样的若干张版画作品,均为原件。如果作者反复创作相同的作品,每一次都是独立的创作,得到的作品是相互独立的作品原件,而不是同一作品的若干份原件,更不是第一件作品的复制件。在这种情形下,原件的认定需要辅之以作者在原件上的签名、编号、盖章、水印等客观性证明。
第三种可能是一些特殊类型的作品原件附有存续期限。比如,为了举办大型活动用灯具或花盆摆设的艺术造型。在“自贡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诉自贡市五星广告灯饰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中,法院就认定原告设计、制作的“希望之光”大型灯组属于《著作权法》所称的美术作品。(40)参见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自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活动结束后拆除艺术装置,则美术作品原件灭失,其存续期限即为活动期间。再如雪雕作品、沙画作品也有一定的存续期限。还有判例将发型认定为立体美术作品,亦为附有存续期间的作品原件。
第四种可能是并非所有美术作品都有原件。比如,曾有判例将音乐喷泉喷射效果的呈现认定为美术作品。音乐喷泉喷射出来的艺术造型转瞬即逝,无法固定,但是满足了作品“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法定要求。再如,烟花燃放和无人机编队形成的艺术造型也是类似的“瞬间载体”。《著作权法》的最新修订确立了“作品类型开放”的立法模式,未来也许会出现更多没有原件的美术作品类型。
(二)数字化美术作品原件的认定
首先,前文已述,存有电子文档的硬盘、光盘或优盘等存储器不具有“直接”可展览性和不可替代性,且该电子文档可以随时被删除,也不符合大众对作品原件的通常认知,不能作为作品原件。
其次,如同在画板上作画一样,数字化美术作品完成时呈现在显示器上的图片代表作品“首次”附着在物质载体上。但是,美术作品看似“固定”在屏幕上,其实只是暂存于计算机的内存中。而且,根据《美国版权法》第101条,用于固定作品的载体应当具有“足够的长期性与稳定性”,以使作品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可以被感知、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传播。所以,这种短暂呈现的画面没有被真正固定下来,不具有稳定性,不能作为作品原件。
再次,如果坚持作品原件必为实体的传统认识,那么只能将打印出来的实体作品认定为原件。对照前述美术作品原件的概念,虽然其具备可展览性,但却不具备不可替代性,同样品质的作品制件可以反复制作。当然,作者可以通过签名、题词、盖章或印制时加入水印等技术手段将一张或若干张打印版特定化为不可替代的作品原件。但是,那些多维的、动态的或像素高度压缩的数字化美术作品只有通过数字化方式才能全方位展示出创作精髓。比如,2021年3月,佳士得公司以6934万美元拍卖了一幅NFT数字化美术作品《Everydays-The First 5000 Days》,由作者从2007年5月以来5000个日夜所创作的数字化作品压缩而成,(41)参见司林威:《NFT玩家,谁都不曾拥有,我们只是过客》,载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901624768440859&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3月31日。其艺术价值不只是体现在由这些作品拼凑而成的整幅图片上,还包括可以被放大的每幅被压缩的作品。换言之,不能真正展现数字化美术作品美感的打印版“作品原件”颠覆了其原本应当具有的观赏性,有可能还贬低了作品的艺术价值。艺术家们肯定不愿看到自己精心制作的多维或动态数字化美术作品,只能展示其中静止不动甚至索然无味的一面。
最后,笔者认为,如果突破作品原件必为实体的认识,可以将数字化美术作品完成时的原始图片或其形成的电子文档(通常带有“.gif”或“.jpeg”等专用扩展名)认定为作品原件。此处的图片或电子文档指的是作者亲自创作完成的同一件作品的不同表现形式,均为同一事物,借助于看图软件即可将电子文档打开为图片。图片需要借助电子屏幕展示,电子文档需要借助看图软件和电子屏幕展示,均能间接地满足可展览性的要求,即具备“间接”可展览性。电子文档本身附有权利管理信息,(42)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6条,“权利管理信息”是指说明作品及其作者、表演及其表演者、录音录像制品及其制作者的信息,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权利人的信息和使用条件的信息,以及表示上述信息的数字或者代码。可以被特定化为不可替代物,作者还可以通过技术措施防止他人未经许可浏览、欣赏和复制作品。《著作权法》的最新修订不仅将原来规定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权利管理信息和技术措施提档升级,还正式纳入作品登记制度,亦可为数字化美术作品原件的认定提供公信力极强的证明。
现实中的主要问题在于权利管理信息或技术措施极易被他人攻破,安全性比较低,特别是价值越高的作品越容易遭到攻击;一旦权利管理信息被篡改或删除,数字化美术作品原件就失去不可替代性,和其他拷贝文档混同为彼此没有差别的复制件。
然而,NFT技术的出现提出了一个有希望的解决途径,在数字化美术作品的真伪鉴定、确认所有权、打击盗版和保护、管理版权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3)参见刘双舟、郭志伟:《论非同质化代币对数字艺术版权管理与保护的影响》,载《中国美术》2021年第4期。2021年3月有两则消息引人注目:一是推特(Twitter)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Jack Dorsey),以291万美元拍卖了其2006年3月在Twitter上发表的第一条推文;(44)参见揭书宜:《卖出290万美元!推特CEO首条推文以NFT资产卖了》,载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836514,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3月23日。二是佳士得公司以6934万美元拍卖NFT作品《Everydays-The First 5000 Days》(45)参见前引〔41〕。。两件数字化作品都采用NFT技术予以特定化,保证了买家与拍品之间唯一的对应关系。在NFT作品拍卖中,买卖的其实是一种所有权凭证。NFT通过一种技术方法来证明对数字艺术作品享有相应权利,并由区块链技术确保无法篡改,成为牢不可破的权利管理信息。当作者将其数字化美术作品的哈希值上传区块链并经由NFT技术特定化后就成为作品原件,其后该原件的每一次流转都被记录下来并不可篡改,满足了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要求,亦可借助电子屏幕进行展示,具备了可以作为作品原件的基本特征。因此,通过NFT技术认定数字化美术作品原件在技术上可行,并已投入应用,国内外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创作和买卖、收藏NFT作品的新业态。
(三)美术作品的复制件
与作品原件相比,美术作品复制件的特殊问题在于,与原件不同维度的复制件是否仍是展览权意义上的作品复制件。复制行为本身有广狭之分,狭义的复制仅指同一维度的平面到平面、立体到立体,广义的复制还包括从平面到立体、立体到平面的维度改变。
对此,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见解。否定见解采狭义复制论,认为改变了作品原件维度的复制件不是展览权意义上的作品复制件。在“范英海、李先飞诉北京市京沪不锈钢制品厂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对于包括雕塑作品在内的美术作品,其复制件应指由对该作品的复制行为所产生的与该作品完全相同或者相近似的作品。由于被告展览的涉案不锈钢雕塑作品构成了对原告雕塑作品《韵》的剽窃,该剽窃作品应属原告雕塑作品《韵》的复制件。”(46)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二中民初字第8042号民事判决书。肯定见解采广义复制论,认为与作品原件维度不同的复制件仍是展览权意义上的作品复制件。比如,在“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创公司’)诉群光实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光公司’)著作权纠纷案”中,群光公司购买了与原创公司美术作品美羊羊、喜羊羊、灰太狼在视觉上无明显差异的服装道具,派员工穿戴该卡通服装道具装扮成卡通角色在其周年庆活动上宣传造势,并与现场人群交流互动。其中,涉案侵权物品即为源于平面美术作品的立体卡通服装道具。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使原告美术作品美羊羊、喜羊羊、灰太狼的立体复制件向不特定公众展示,虽属于非典型的公开陈列美术作品的行为,但仍侵犯了原告对以上美术作品享有的展览权。”(47)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武知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
我国《著作权法》采用狭义复制的概念即否定见解,然而从著作权法鼓励和保护作品及其创作的目的出发,采肯定见解即广义复制的概念更为合理。盖因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而非作品载体,如果将改变作品原件维度的复制件放任于法律调整之外,显然不利于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也是一种纵容侵权的做法。
根据上述认定规则,经由NFT证明或其他类似证明的数字化美术作品的图片或电子文档是原件,没有相应证明和已经实体化的作品都是复制件;进而言之,对于数字化美术作品,其复制件具有数字化和实体化两种可能的属性。将实体化的美术作品原件进行数字化复制,得到的数字化作品也可称为复制件。这样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创作作品,均突破了作品复制件必为实体的传统认识,和确定作品原件的规则保持了一致。《著作权法》的最新修订修改了第10条关于复制权的定义,专门将“数字化”的复制加入其中。有学者认为:“这一修改只是对理论和实务中的共识以立法形式加以体现,是对已有做法的确认,而不是创设新的规则。”(48)王迁:《〈著作权法〉修改:关键条款的解读与分析》(上),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1期,第24页。所以,改变美术作品原件和复制件必为实体的认识,在理论、实务和法律依据上都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五、结 语
展览权虽然在著作财产权中并不起眼,但却是文博事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石。作为展览权的核心概念和拍卖场的竞逐对象,美术作品原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们应当从实践出发,回应新技术、新业态提出的新挑战,正确理解和认识美术作品原件的概念,突破作品必有原件、作品原件唯一和作品原件必为实体的传统认识,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趋势,构建出认定美术作品原件特别是数字化美术作品原件的新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