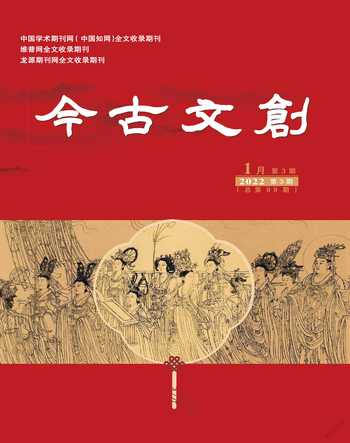《饥饿的女儿》和《鸟的礼物》中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对比研究
2022-02-03杨晓蕾
杨晓蕾
【摘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韩文坛都涌现出大批女性作家,她们解构男性作家群体的宏大叙事方式,主张进行私人化写作,注重描写个体在私人空间的私人生活与体验。许多女作家通过私人化写作,获得自我性别认同,完成成长蜕变。私人化写作在成长小说中的运用最为普遍,本文选取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成长小说——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与殷熙耕的《鸟的礼物》,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比较这两部作品中私人化写作的异同点。
【关键词】女性成长小说;私人化写作;《饥饿的女儿》;《鸟的礼物》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3-0023-03
一、引言
《饥饿的女儿》是英籍华裔女作家虹影于1997年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了主人公“六六”坎坷的身世及艰难的成长过程。六六从小就感受到自己在家庭里的微妙地位,母亲从不与她示好,父亲始终待她冷漠。六六从历史老师身上找寻爱情,抑或是缺失的父爱,但他却在和六六发生关系不久后自杀身亡。十八岁那年母亲告诉六六,她是自己和另一个男人所生的“私生女”,六六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一切,选择离家出走,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写作与自己的私生女身份达成和解,摆脱身份危机,完成自我拯救。
《鸟的礼物》是韩国女作家殷熙耕于1995年发表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这是一部讲述38岁的主人公江珍熙回想小学五年级时发生的人和事的框型结构小说。母亲早逝,父亲虽然健在但未曾谋面,珍熙从小和姥姥、小姨、舅舅生活在一起。在无父无母的家庭中,珍熙用自己独特的方法保护自己—— “我”用表演的方式蒙骗身边所有的人,用旁观的视角观察周围的人和事,用冷漠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我”有着不同于同齡人的成熟与理智。珍熙认为,十二岁之后,我已经没有必要再长大了。
这两部作品是20世纪90年代中韩两国女性成长小说的代表作,在叙述内容和叙述方式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可以看到由于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等差异带来的种种不同。本文主要从两篇小说中的私人化写作进行对比研究。
二、私人化写作——女性美学的建构
纵观两部小说,主人公的成长都从家庭视域中展开,却因在家庭中缺乏关爱而将目光投向两性关系,在见识过爱情的虚无与伪善后,开始关注自身,走向主体性成长的道路。女性作家群体通过私人化写作,使得真正的女性美学得以浮出历史地表,虽然私人化写作贯穿两部作品始终,然而叙述的展开却不尽相同。
(一)家庭视域中的女性成长历程
海明威曾说过:不愉快的童年是一个作家最好的训练。对于虹影和殷熙耕等20世纪90年代的女作家来说更是亦然,她们的前半生或许都是不愉快的、缺少爱的,但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赋予了成长后的她们以思考的时间和写作的空间。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是最主要的成长环境,父母则是个人成长的引路人,不仅母亲对于子女的成长至关重要,父亲这一角色同样举足轻重,尤其是对于女孩而言,父亲不仅是家庭里的绝对权威,也是她们出生以来接触到的第一个异性,与父亲的交流往往含有一定的性别对抗意味。
在《饥饿的女儿》中,六六虽然从小和父母、哥姐们生活在一起,但生活却是暗淡、缺少爱的。
“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的孩子。她怀过八个孩子,死了二个,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我是幺女,第六。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里很特殊,不是因为我最小,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紧,关照却特别周到,好像我是个别人的孩子来串门,出了差错不好交代。”
六六从小就感受到自己在家庭里的特殊地位,只是对其原因不甚明了。她感受不到来自家庭的丝毫温暖,也尝试去讨好母亲,可结果总是不尽人意,六六与母亲无法微笑面对彼此,更不用说向母亲袒露心声,甚至“妈妈”一词也变得难以启齿。
“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但方式完全不同。他平时沉默寡言,对我就更难得说话。沉默是威胁: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帖的皮肉。哥姐们,母亲一味迁就纵容,父亲一味发威。对我,父亲却不动怒,也不指责。”
六六和父亲之间始终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父亲虽然也会关心她,但父亲对她的态度总是让她感到无比的冷漠与疏远,六六十分渴望父爱,却从未在父亲身上获得过丝毫。
“至今唯一耐心听我说的人,是历史老师,他立即获得了我的信赖。他看着我说话的眼神,就足以让我倾倒出从小关闭在心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在六六18岁那年,历史老师的出现给她暗淡无光的生活带来些许光亮,在那个无处言说、无人在意的年纪,是历史老师听她讲述自己枯燥无聊的琐事。但就是这个对六六而言如“情人般的父亲”的存在,却在和她冲破世俗的禁忌,享受鱼水之欢后,不辞而别,选择了自杀。
同样是18岁那年,母亲告诉六六:她是自己和别的男人生的私生女。母亲安排六六和生父见面,生父向她频献殷勤,想弥补这些年无法见面的遗憾,但六六对这个未曾正式见面,却一直暗自跟踪自己的生父十分抵触,不愿接受他。
养父、历史老师、生父在六六生活中扮演着现实中、情感上、伦理上的父亲的角色,但六六却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父爱,父亲这个角色在她的生命中一直是处于缺席的状态,这也是其成长缺憾的一个重要部分。三个父亲,都负了我:生父为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只给我带来了耻辱;养父忍下耻辱,细心照料我长大,但从未亲近过我的心;历史老师,我情人般的父亲,只顾自己离去,把我当作一桩应该忘掉的艳遇。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父亲。在意识到这一现实后,六六开始对家庭产生厌倦,渴望出走。
《鸟的礼物》中,主人公珍熙从小和姥姥、小姨以及舅舅生活在一起,母亲在她六岁时便去世了,她对妈妈没有什么记忆,姥姥也对妈妈的事情闭口不谈,但在她九岁、十岁左右时,姥姥的两个侄女来到家里,在屋里旁若无人似的聊起了妈妈,那时珍熙才第一次知道了关于妈妈自杀的些许真相,感到前所未有的悲伤。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厌恶别人的视线。只要有眼睛看着我嘀嘀咕咕,我就会觉得他在谈妈妈的事。我不希望别人察觉这一点,所以总是故意低下头。父亲早年离家出走,珍熙身边也没有与父亲这一概念相匹配的男性,舅舅离家服兵役,家里只有姥姥、小姨和她三个女人,即使放眼整个“有柿子树的人家”,这个大家庭里也没有堪当父亲的角色,崔老师整天只会色眯眯地盯着在井边洗漱的小姨和Miss李;一提起李老师,珍熙就会想到他被痔疮折磨到扭曲的面部表情;逃脱兵役的广进西服大叔虽已为人夫、人父,却全然没有男子汉的气质,只会拈花惹草,打骂妻子。因此珍熙对父亲这个角色没有任何概念,音乐课上合唱《在花田里》时,才第一次发出“爸爸”这个音,且也只有在合唱那首歌时“爸爸”一词才能说出口。
从小珍熙便懂得察言观色,家人、周围的人情世故都是她观察的对象,她知晓很多人的很多秘密,开始明白大人世界充满着谎言与伪善,也开始学会伪善地对待生活中的人和事。她为了让“将军妈”出糗,设计让“将军”掉进粪坑后,自己却泰然自若地坐在门前的廊子上观看这出闹剧,事后,珍熙还借来“将军”他们班同学的笔记帮他补习落下的功课。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城府很深,而这次事件却为大家创造了一个赞扬我心地善良的好机会。这让我明白谎言和伪善原来就是同伙。珍熙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能得到大人的“疼爱”,把自己分裂成“被注视的我”与“观望的我”两部分以使自己与生活保持距离。我时刻注视着自己,我让“被注视的我”主导着我的生活,而“观望的我”注视这一切。珍熙认为,12岁之后,我已经没有必要再长大了。虽然“我”的心智很成熟,但“我”会用面具包装自己,努力使自己的气质行为符合自己的年龄。对珍熙而言,这是她保护自己的方式,让“观望的我”从身体里分裂出来,这样就可以在面对别人的指点或侮辱时少受伤害。
《饥饿的女儿》和《鸟的礼物》的文本中都对主人公“我”的成长过程有着大篇幅的描写,其主要成长环境都处于家庭这一氛围中,在家庭里,六六和珍熙都是“边缘人”,六六因身份之谜在家庭里备受冷漠,珍熙则为了保护自己,自发地与身边的一切保持距离。由于个体成长的差异性,作者对主人公成长过程的叙述虽各有侧重,但描写的都是“我”在家庭这个环境中的私人经验以及个人感受。
(二)两性关系间的私人经验叙说
在女性私人化写作中,性与爱情是女作家们写作的重点,私人化写作摆脱了以往世俗对女性“性禁忌”的种种桎梏,女作家们得以运用女性的视角描写女性对性与爱情的私人感受、个人经历等。
“我是在寻找我生命中缺失的父亲,一个情人般的父亲,年龄大到足以安慰我,睿智到能启示我,又亲密得能与我平等交流感情,珍爱我,怜惜我,还敢为我受辱挺身而出。”
在《饥饿的女儿》中,主人公六六是一个饱受身体、情感、性三重饥饿折磨的存在。六六一生都在找寻可以给予她如父亲般关爱的男人,而历史老师便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她认为自己深爱着历史老师。
“男人的裸体,正面背面;女人的裸体,正面背面,都插了长针似的标明名称,乳房、阴部等等,全是些我从说不出口的字眼。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赶紧把臉埋在书页里。”
通过翻阅历史老师拿来的《人体解剖学》,六六第一次直观地了解了男性与女性身体的奥秘,在六六看来,书中的裸体与器官是美丽的,是危险而诱惑的,这可以视为六六自我体认的契机,也使得六六与历史老师的结合水到渠成。
事实上,女性成长中的第一次性经历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的影响会贯穿女性的一生。由于这一体验“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不愉快的,始终带有一种与过去决裂的性质”。当少女实际经历这些体验时,她的所有问题,均以尖锐而急迫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性经历带给六六的是自我性别认同的开始,那一整个下午六六都沉浸在快乐中,第二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拿起镜子端详自己,感觉自己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六六开始迷恋上了镜子,觉得镜子里的世界满是愉悦。在女性私人化写作的文本中,镜像书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镜像书写指的是镜像作为一种场景出现在小说中,出现主人公对镜自照的场景,且这一镜像承载着主人公的情感投射。透过镜子,女性可以观察自己,观察自己的表情、容貌和身体等。对镜中自己的观察与欣赏实际上预示着女性对自身的认识与认可。
不同于大胆示爱,直接描述性经历的《饥饿的女儿》,在《鸟的礼物》中,珍熙对爱情的虚无、性的缥缈的感受大多是通过读书或观察周围人物的经历得出的。对于“性”的初识,便是通过阅读那些给读者留下强烈性印象的纪实小说完成的。“我开始一部接一部地读纪实小说,把历史小说中厚颜无耻、居心叵测的性爱场面反复读两遍更是家常便饭。”
周围人物的爱情与婚姻也使珍熙对“爱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中对她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小姨的爱情和广进西服大婶的婚姻。小姨的两段感情她都是见证者,甚至第二段感情中她们还是情敌。和李亨烈的感情纠葛是小姨的第一段恋情,因京子阿姨开始,又因京子阿姨破灭。从他们恋爱伊始,珍熙便对这段感情持怀疑态度,看着小姨因爱情或开心、或焦虑、或难过,看着小姨为争取爱情每天练习表情,在与爱人交往的过程中,竭力表现出“贤妻良母”的姿态,认定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李亨烈的,为了爱情割双眼皮,却也因此给了他一个离开自己的借口,珍熙感受到女性在爱情中的被动地位,认识到爱情与欺骗和背叛同行。珍熙爱许硕,许硕却爱小姨,在小姨被爱人与朋友背叛时,是许硕带小姨走出悲伤,小姨怀了许硕的孩子,但许硕走后音信全无,珍熙陪小姨去堕了胎,经历了两段失败的爱情,小姨成长了,而珍熙也切实地感受到爱情的虚无,以及爱情所带来的欺骗和背叛。
珍熙对广进西服大婶始终怀有深深的怜爱之情,她的婚姻也让珍熙思考万千。广进西服大叔强奸了大婶,大婶认为自己失去了贞洁,这一辈子就这样被决定了,便稀里糊涂地和大叔结婚生子,结婚后更将丈夫视为自己的全世界,处处维护大叔,尽心尽力操持家里家外,但大婶从未幸福过。大叔天天往外跑,处处拈花惹草,晚上回到家隔三岔五殴打大婶。大婶也想过离开家,离开大叔,从这样的命运里逃脱出去,但她总是觉得第一次性经历就决定了自己往后余生就要非此人不可。但在珍熙看来,第一次对女人来说并没有过多的意义,第一次亲吻或第一次性经历多发生于偶然,她也的确是这样奉行的,她把自己的第一次亲吻以分担悲伤的动机给了许硕哥哥。
成长小说中的私人化写作,爱情与性的描写必不可少,《饥饿的女儿》和《鸟的礼物》中主人公都通过自己的视角讲述了两性关系中的爱情与性,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描写更为大胆露骨,书中对我和历史老师的爱情与性爱经历进行了直接描写;而后者对于爱情与性的探知主要来自书籍与身边人的经历,虽然“我”爱过许硕,但这始终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三)性别写作下的主体性成长
在《饥饿的女儿》中,六六从小便纳闷为什么自己像是一个多余的人,在家庭里缺乏关爱,在学校里无人关注,在邻里间饱受指点。18岁那年,在经历了历史老师自杀、私生女身份被揭露这些事情后,六六选择了出走逃避。流浪途中,远离了“私生女”这一身份困境,六六得以在一片新的天地重新找寻自我,寻觅渴望已久的爱情,探寻自我生命的意义,她开始写诗写小说,在写作的过程中,与克服身份危机,与过去的自己和解,完成主体性成长。
但《鸟的礼物》中的珍熙认为,12岁之后,我已经没有必要再长大了。不同于大多数的成长小说,她的成长表现出一种“反成长”的意味。这里的反成长主要是指主人公基本没有按照个人或社会的理性预设模式成长、蜕变,始终与世界处于分裂而非融合的状态,更多的时候他们徘徊于自我主观世界而拒绝长大。无论是12岁的少年时代,还是38岁的现在,无论是在“有柿子树的人家”,还是在爸爸回归后的新家庭,珍熙对生活从未抱有任何期待,她总是通过自我分裂的方式刻意与生活保持距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拒绝成长。因此,对于珍熙来说,12岁时,当她在看尽成人世界的谎言与伪善,感受了爱情与婚姻的虚无缥缈后,她便完成了成长。
三、结语
《饥饿的女儿》和《鸟的礼物》是中韩两国女性成长小说的代表作。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都选择了私人化写作的方法,通过私人化写作,作者在内容上都书写了主人公的成长经历、爱情体验以及主体性成长的获得,表现了女性的私人体验与个人感受;在主旨上都再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的艰难成长过程,解构男性的宏大叙事方式,建构女性私人化写作方式。
参考文献:
[1]郑春凤.对青春的残酷回望——金仁顺反成长小说探析[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5
(06):81-85.
[2]高小弘.成长如蜕[D].河南大学,2006.
[3]张政君.镜像阶段理论与中国90年代女性镜像书写[D].上海社会科学院,2020.
[4]崔铃.世纪之交韩中女性小说比较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