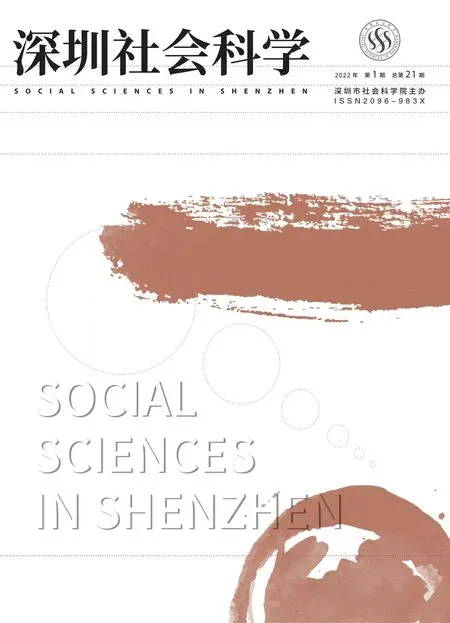论汉字传承与中国文明延续的辩证发展关系*
2022-02-03黄亚平
黄亚平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已经为史学界所公认。在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发展进程中,汉字传承与中国文明的延续始终相互伴随,形影不离。从早期中国的“汉字萌芽”“汉字先行形态”,到汉字体系在夏商之际最终完成,虽历经不同发展阶段,虽有形体演变,却始终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
在历史的长河中,汉字传承与中国文明的延续始终保持着相互成就、共同成长,不断变化创新的辩证发展关系,这一辩证发展关系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它不但出现在中国文明内部,而且在东亚汉字文明圈内的许多国家都有所体现。提出“汉字传承与中国文明延续存在高度一致性”,不但对中国文字史研究有重大价值,而且对中国文明史研究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只有立足于汉字传承与中国文明延续辩证发展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从东亚文明史甚至世界文明史的高度看待汉字与中国文明的关系,才能更加清醒地认识汉字起源和汉字体系形成对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和奠基定型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深刻认识汉字传承活动与中国文明的发展壮大过程始终相互伴随的重要事实,进一步明确汉字传承对当下进行的中国文明复兴伟业,对中国文明再度复兴的重大现实意义。
一、中国文明大格局的酝酿成形与“汉字萌芽”发生发展的辩证关系
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约距今6000年左右)首先开启了“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的大格局和大框架的先声。[1]在中原仰韶文化分布区域内,出现了一系列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的中心聚落,如西安半坡、陕县庙底沟、河南郑州大河村、山西夏县西阴村、甘肃秦安大地湾,等等。仰韶文化彩陶非常发达,许多彩陶图案和纹饰都已经初具原始宗教与审美趣味,如半坡类型的人面鱼纹、蛙纹,庙底沟类型的变异鸟纹,等等。在半坡、姜寨和北首岭等地还发现了50多种标明个人所有权的刻画符号,这些刻画符号不仅流行区域较广,而且符号的形状也更加齐整,抽象程度更高,其中部分符号已经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近似。郭沫若列举了“”等半坡陶符,并指出其与殷周铜器铭文中的几何形族徽文字“”基本一致。[2]李孝定、郭沫若、于省吾、王志俊等人都认为半坡陶符已经是“文字”,甚至是与商周甲骨文、金文同属象形文字的系统。裘锡圭、汪宁生、巩启明等人则不赞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刻画符号就是文字的观点。陈昭容认为:仰韶文化陶器记号中的记数符号和氏族标志符号或许与商周金文中的数字和族名金文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但若“将某一遗址出土的陶文全部视为文字,或全部视为偶然的刻划,都是片面的。”[3]
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文化(约距今5500年左右)空前强大,表现出强烈地向四周扩张的态势,其黑彩和花瓣纹彩陶图案一路向东进入山东,然后转向东北进入红山文化;另一路向南渗透到湖北、四川的大溪文化。河南汝州阎村陶缸上发现的“鹳鱼石斧图”,严文明认为乃是一幅白鹳氏族战胜鲢鱼氏族的图画。[4]韩建业认为“也可能是崇鸟的庙底沟类型人群战胜崇鱼的半坡类型人群的‘纪念碑’性图画,‘斧’或‘钺’应当已有象征军权的属性。”[5]庙底沟期文化在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中也有表现,“不少陶器形制和花纹都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相似或接近,显然是从庙底沟类型脱胎发展起来的。”[6](P302)约距今4900—4800年左右的庙底沟类型二期文化虽然承袭仰韶文化,但已经出现了较多外来因素,如彩陶罕见而灰陶居多,出现双耳盆、陶斝等新器型,以及半月形石刀和石镰等,表明“它是一种过渡阶段的遗存”。[6](P330)
中原庙底沟期文化前后,在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江南的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中,都发现了数量不等的陶器刻划符号。大汶口文化晚期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出现了家庭-家族-宗族的社会层级结构,并由若干个宗族构成聚落共同体,出现了较大的中心聚落。大汶口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严重,大型墓随葬品多达180余件,众多小型墓陪葬品只有数件,甚至连一件也没有。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前寨等遗址出土和采集的大型陶缸和陶瓮腹部发现了10余种约距今4800—4600年左右的象形符号,此类大汶口晚期陶符与商周文字一脉相承,既有象形文字,又有意符文字,还有繁简之分,已经脱离了草创阶段,通常被认为是比较进步的文字。李学勤、裘锡圭、高广仁、栾丰实等人都认为大汶口晚期陶符已经是“原始文字”,而且是其后的古汉字的基础。
良渚文化已经发展到地域性王国阶段,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宫城、墓葬和水利设施、专门的祭坛、制玉作坊和玉礼器、丰富繁缛的神人纹与陶器纹饰,以及多达632个刻画符号及其部分符号组合形式。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可分为象形符号、抽象记号和其它符号三类。[7](P27)其中一部分组合记号和组合象形符号被文字学家释读为文字,如在吴县澄湖古井群遗址黑陶鱼篓形罐腹部发现的四个成排分布的符号,李学勤释读为“巫戉五俞”,意思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饶宗颐释读为“冓戉五个”;董楚平释读为“方钺会矢”。在良渚文化中,不仅单个符号的数量众多,而且许多单个符号有“组词成句”的能力,此类符号组合形式甚至多达数十例。这一现象充分说明良渚文化中的符号组合形式,已经初步具备了原始记事与表意功能,其性质已经是“汉字先行形态”。[8](P8-9)
约距今4600—4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有许多重大发明和成就,使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面貌亦随之有很大改变。”[9]龙山时代的重大发明包括铜器制作、轮制陶器、骨卜、养蚕和打井以及大型城防设施建筑,等等。在一些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还出现了地域性方国,如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东部的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北部的老虎山文化石峁遗址、晋南龙山文化陶寺遗址,等等。在这些史前文化向中原汇拢的发展过程中,各史前地域文化的器物及其符号都得以充分交流与借鉴,为汉字体系在夏商之际在中原腹地最终定型打下了字符构形与构意的坚实基础。
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出土了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陶制小动物偶和人偶陶像。其中人像大概是巫师,小动物像则可能是巫师通神的工具。在肖家屋脊和邓家湾两地遗址中发现陶器刻符55个,绝大多数符号发现在泥质灰陶大口尊腹部,表示容器、农具、纺织工具、自然现象等。[10]这些刻画符号是具有一定通神功能的地域性原始文字。其中的一些符号和符号载具还与大汶口-龙山、崧泽-良渚文化符号的情况有所牵连,如符号“”就与良渚文化玉器和陶器上出现的同类符号近似,符号“” “”“”“ ”“符号,同样可能是与古汉字有所关联的汉字萌芽之一。
河南龙山文化既保持着本地仰韶文化的底色,又带有龙山时代史前文化大交流的鲜明特征。如河南淮滨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钵形鼎、高柄壶形罐、圈足壶形器等就与屈家岭晚期同类器形相似,高柄镂孔杯、三角镂孔装饰等就可以从山东大汶口文化、江苏青莲岗文化中找到根源。河南禹州瓦房店遗址发现的两个符号“”则与大汶口文化陶缸上的同类符号近似,充分说明龙山时代各地域文化加速融合的发展趋势。
山东龙山文化社会经济活跃。黑陶制作工艺达到古代制陶史的高峰,制玉工艺和冶铜技术比较发达。城子崖等遗址的城防设施,尹家城大墓表现的贫富悬殊与贵贱对立程度,说明山东龙山文化社会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的前夜。虽然山东龙山文化考古发现的陶符数量少,但成组的“丁公陶文”的发现仍独具特色。众多学者都充分肯定该陶文与古汉字的关系。[11]从地望、社会发展程度、骨卜传统、史前符号的多种形态以及与岳石文化桓台史家遗址等地发现的文字卜骨等因素来综合判断,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该地出土的陶器和玉器上的图案和、
”[12]与本地中原龙山文化陶符有别,但却在石家河文化中发现了与其形状近似者。河北永年台口发现的符号“”,[13]更是普遍出现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许多考古学文化之中。虽然目前发现的河南龙山文化陶器刻划符号的数量还比较少,且限于单个符号,少见记号组合形式出现,但在河南龙山文化中,陶器刻划符号来源于不同史前文化的特色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其中还有少数符号的形状与甲骨文、金文近似。如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的“”,被考古报告认为形似“共”字。[14](P56-59)因此,从地望和社会发展程度等因素判断,河南龙山文化发现的陶符同样有可能是与古汉字有所关联的汉字萌芽之一。
约距今4300—3900年左右的中原龙山文化陶寺遗址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殿,王者等级的大墓等文化遗迹。陶寺贵族大墓中的陪葬品异常丰富且等级分明,如以玉钺、玉圭、玉璧、玉琮为代表的玉礼器及其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等礼器群。在其中5座大墓中还发现了鼍鼓、特磬等礼乐重器。充分表明当时的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社会矛盾持续激化,战争频仍不断的状态。在陶寺遗址出土的1件残破扁壶上发现的三个朱书陶文,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最早的汉字原始初文。李建民、罗琨、高炜、冯时、何弩等人都认为右侧的1个朱书符号为“文”字,且与“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个系统”。罗琨认为左侧的两个朱书陶文应为“昜文”二字,记述尧的功绩;何弩认为应是“文尧”二字,“文”应当是尧的尊号;冯时认为朱书陶文应为“文命”二字,正好与文献记载里所说的夏禹的名字“文命”相应。2017年,何弩发表了在陶寺遗址ⅠM26墓底北侧壁龛中新发现的1件骨耜,其上刻有“辰”字。该字的发现“不仅丰富了陶寺文化文字的数量,而且将汉字体系的出现年代再次提前,进一步证明陶寺文化文字是甲骨文、金文文字系统的先河。”[15]
综上可知,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尤其是庙底沟二期及其后继的“龙山时代”是“早期中国”及“汉字萌芽”的孕育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境内各地域性史前文化出现了汇聚中原的趋势,带有“汉字先行形态”性质的史前刻画符号在较广地域范围内普遍流行。尤其在“龙山时代”,中国境内南、东、西、北各大史前文化在中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各大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但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基础底色,对最终定型于中原腹地的中国文明发展态势起到了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在符号形态上从一开始就已经初步具备广收兼备,结构互补的汉字底色。可以说,汉字符号的孕育及其符号构意起源于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之后及其龙山时代众多史前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相互作用,从符号源头上就具有“多元”性质,并与早期中国文明的“多元”态势基本保持一致。
二、中国文明与汉字体系在连续性的夏、商文化中最终定型
虽然早在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及其后的龙山时代,早期中国“多元一体”的文明大格局和总框架就已经初步显现,但这一文明大格局和总框架的最终定型,却是以连续性崛起在中原腹地的夏、商文化及其使用的汉字体系为其根本标志的。
约距今3900—3600年左右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被公认为夏代(含商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之前,来自中原周边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就与中原王湾三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融合。西北部老虎山文化南下将陶鬲等带入陶寺文化晚期的晋南临汾盆地,并将陶鬲、卜骨、石镞扩散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南方江汉平原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受到中原王湾三期文化南下的影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城垣被毁,红陶杯、人物、动物小雕塑迅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出现的瓮棺葬。[16]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受到中原造律台类型文化大规模南下的影响,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被同化乃至于最终湮没。江汉平原、江浙地区区域文明中心急剧衰落,“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得以加强,并最终促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17](P42)
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了宏伟的宫殿建筑、青铜器及其各类手工艺作坊、普遍共存和成群出现的陶器,以及墓葬中成组陶制酒器陪葬的现象,还在宫殿区及其附近集中发现了“龙文物”,尤其是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文物,均说明二里头遗址已经完全具备王国形态和礼文化的特征,很可能就是夏代的王都。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较多的“龙文物”与文献记载的夏禹、夏启、孔甲御龙的传说遥相呼应,绝非空穴来风。在二里头遗址3-4期(约当夏代至商代早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46种刻划符号,这些符号“主要出自大口尊的口沿内侧和其他器类的口部,有粗细不同的竖线、十字形、交叉型、簇形、树枝形等,有的近似象形文字。”[18](P202)二里头遗址3-4期刻划符号不但形状和风格如出一辙,且有重复出现的情况,曹定云认为:二里头文化陶器刻符中的一部分是原始的数字,如等;另有部分符号,如等已经是夏代晚期的文字。[19]高明、李先登、裘锡圭等人也都认为夏代已经有汉字出现。
中原腹地考古发现的商代早、中期王都遗址主要是约距今3550—3300年左右的洛阳偃师商城遗址,约距今3500年左右的郑州商城遗址群等。前者被认为是商早期的都城“西亳”,后者被认为是商中期“仲丁迁隞”的“隞都”。除了中原腹地殷商王畿范围内发现的商代遗址外,另在河北藁城台西,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发现了部分商王畿之外的商代遗址。在以上所说的几处商代遗址中还发现了约50个左右的早于殷墟的陶器刻划符号。另在商代二里岗期遗址中还发现了两块刀法与殷墟甲骨文相似的字骨,以及一些无字卜骨。[20](P17)
虽然目前发现的商代前期的陶文材料的总量还比较少,但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些符号性质的基本判断:无论从符号产生的社会条件,还是从符号形态观察,商代前期的50余个陶符都已然是“陶文”,它们上承二里头陶文,下接殷墟陶文,并可与甲骨文、金文联系起来。因此,商代前期的50余个陶文应当是商代通行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商代通行文字体系中较早出现的那一部分。[21](P11-12)
考古发现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主要是约距今3300—3000年左右的殷墟。殷墟遗址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部分铜器铭文以及数十例陶文。与商前期陶文相比,殷墟陶文中新增陶文单字的数量约在40例左右,另有数例多字陶文。李济将这些陶文区分为数码符号与文字、位置符号与文字、象形符号与文字、人名及其他符号与文字、符号与文字杂例、待问等六种情况。[22](P177-183)考古发现的殷墟陶文虽然在书写风格、文字规范等方面与同地发现的甲骨文、金文略有差别,其中还夹杂了部分陶符,但已经能够按照甲骨文、金文的释读方法进行确切的考释,是殷商文字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殷墟考古发现的甲骨文、金文和陶文,不但证实商代晚期汉字系统已经完全成熟,而且充分说明殷商文字在整体上是一个广泛通行的文字系统,该文字系统由许多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以及大量的竹简书,等等。
综上可知,汉字体系的形成与中国文明在中原腹地的最终定型存在一致性。汉字体系的形成在距今约4900—4800年左右的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及其龙山时代各史前地域文化向中原聚拢的过程中就已经展开,在约距今4000—3600年左右的夏、商之际最终完成,又与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体”状态高度一致。
三、中国文明与汉字体系在中原定型之后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制度性建设
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种先进文明在初兴之后,都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制度性建设,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并且具备适时改进与自我完善的能力,绝非一蹴而就。中国文明与汉字体系在中原腹地定型之后,同样需要其后继者付出艰辛的劳动,制定出完善的文教政策,在“书同文”、“儒学经典化”与“汉字规范化”、“科举取士”等一系列文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逐步得以完善,最终完成制度化建设的任务。
(一)秦汉时期的“书同文”政策与童蒙识字教育相向而行
早在东周时期,就有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作为“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23](P1721)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书同文”政策,丞相李斯受命统一文字。李斯删繁就简,创造出形态优美、笔画齐整的“小篆”,作为通行全国的标准字体。李斯等人还亲自编订童蒙识字课本《三仓》,将秦王朝使用标准字体的文教政策落实到儿童教育领域,在中国历史上,首开政府颁布童蒙识字课本之先例,在确保童蒙识字教育的质量,切实起到了推行汉字标准字体的作用。
汉代沿用李斯编订的“三仓”(《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童蒙识字课本,另由官方学者模仿《三仓》体例,新编《训纂篇》《滂喜篇》《急就篇》《元尚篇》等作为新识字课本。以上童蒙识字课本均由官方授意,由一时著名学者编纂和参订,蒙学教材于是成为集识字与书写范本于一体的启蒙教育的基石。
汉代国家层面对童蒙识字教育和书写规范的重视,还表现在朝廷先后举行过多次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高规格的文字会议。朝廷征召各地著名文字学者,论定文字是非优劣,统一认识,强化文字规范。《汉书·宣帝纪》:“《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汉书·平帝纪》:“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数百,各令记字于庭中。”此外,汉代对汉字书写规范的要求还被写入国家的法律条文之中,作为“正字”之法予以严格贯彻执行。如若书写不规范,书写者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汉官仪》:“丞相辟召,刺史,两千石察举,有非其人,书疏不端正,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在汉武帝时期,甚至还出现了郎中令石建因误写“馬”字,而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被治罪的事件。[24](P2766)
从东汉时期开始,朝廷还征召著名学者蔡邕专门书写《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儒家文献作为官定经书范本,将其刻碑立于太庙之前,即著名的“熹平石经”,供太学生模仿学习,以此确保士子们阅读和传抄的儒学文献和汉字书写的规范性。“熹平石经”开启了后世以碑刻方式建立典范文本和汉字书写规范的做法。曹魏时期的“正始石经”、唐代的“开成石经”皆步其后尘。雕刻石经之法甚至还被佛、道两家采用,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二)汉代“儒学经典化”与“汉字规范化”相辅相成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纳道、名、法、阴阳于儒学之中,儒学从此独大,成为官学,一跃而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流思想。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学文献的确立和传承经历了一个历时百余年的“经典化”过程,其中,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儒学专经博士的建立。[23](P3620)从汉武帝建立儒家“五经博士”,至汉宣帝、元帝时期,汉朝先后设立了14个儒学专经博士:《诗》有齐、鲁、韩三家,《书》有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家,《礼》有大戴、小戴二家,《春秋公羊传》有严、颜二家。14个儒学专经博士的确立,标志着“儒学经典化”历程的基本完成,儒家经书的排他性地位和今文隶书的“正字”地位也被同时确立起来,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汉宣帝时期,为了评议儒家五经传承中出现的分歧,还在未央宫石渠阁举行了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会议,召集著名儒者考订五经传承中出现的歧义,并由皇帝亲自订正是非,史称“石渠阁议”。王莽之后延至东汉时期,古文经学派的《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官》《尔雅》等才陆续列入学官,[25](P1-39)起到了进一步扩大和补充儒学文献的积极作用。
儒学文献的经典化历程完成之后,在汉代官方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就出现了儒学正典文本、权威注释、规范文字三位一体的“权力话语三角”。这一权力话语三角的出现,不但起到了确立“正典”,垄断经典解释权的作用,而且为广大士人“通经致仕”铺平了道路。
(三)隋唐以来推行“科举取士”,真正完成了儒学教育的制度化建设
隋唐以来开始的“科举取士”制度真正完成了儒学教育制度化建设的重任。
隋唐时期开始推行的“科举取士”制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科举考试为朝廷统治人才的选拔提供了公正的平台,极大地拓展了封建时代人才选拔的社会覆盖面,为大量社会下层人士提供了进入仕途的门径,许多寒门士子通过科举走上政坛,发挥政治才干,成为安邦治世之能臣。
虽然科举考试的内容非常广泛,而且随时代而有所变化,但常设的科目主要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杂文、帖经、策问)等,这些考试科目除了部分应用型专业人才的考试如“明法、明算、武举”外,主要考察学生对儒家经书和经过儒家学者注释整理的文学文献的掌握程度,以及士子们的品行才能,还有他们对时事政治的看法和应对处理问题的能力,始终以儒学教育的内容为主。
“科举取士”制度在为广大社会人士进入仕途铺平道路的同时,为儒学经典和汉字传承活动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础。经此一制度化建设,形成一个运转自如的围绕着儒学教育运转的闭环。在此一闭环中,汉字文言习得因儒学经典的学习与应用而生,儒学经典的内容符合统治者对统治思想的需求,确保人才选拔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在汉字文言习得—儒学经典学习—行政管理需求三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具有高度向心力的内循环系统,而且每隔几年举行一次,从隋唐一直延续到清末,两千年以来始终如一,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
“科举取士”制度的创立和完善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儒学教育的制度化,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一先进的儒学教育模式和人才选拔制度。
(四)汉字文言习得活动与科举取士制度在少数民族执掌政权时期发挥了巨大影响
汉字文言习得与“科举取士”制度不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还被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自觉接受与模仿学习。
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建立的鲜卑族政权,其历代君主都重视汉文化。孝文帝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对汉文化高度认同并心向往之。在孝文帝的亲自主持下,北魏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化改革,迁都洛阳,改族性,禁胡服,断北语,兴学校、与汉人通婚。[26](P536)迁都洛阳之后,北魏迅速确立儒学为统治思想,修建孔庙,又给予孔子后裔土地与银钱,让他们继续祭祀孔子。同时废除了鲜卑族原有的“西郊祀天”礼仪,改为汉族帝王式的祭祀天地仪式,圜丘祭天,方泽祭地,以祖宗配天。鲜卑族从此大踏步地融入于中原汉文化之中。
元世祖忽必烈“尊用汉法”,重视文教,设立儒户,保护文人儒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九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以祭祀社稷的太牢之礼祭祀曲阜孔庙。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各朝都重视兴办学校。[27](P315-319)元代学校的教育内容,无论国子学还是官化的书院制学校,均以“宋代理学”为宗,科举考试以《四书》及“程朱理学”经注为主,注重品德和实际能力的考察。[28](P32)虽然元代的文教政策并不完善,如对汉人和南人的歧视,科举考试时断时续,等等,但在整体上还是对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对维护民族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清顺治二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29](P73)。清顺治十二年,清王朝确立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于大成殿行三跪九叩之礼拜谒孔子,书“万世师表”四字悬挂大成殿,免去曲阜县康熙二十四年的地丁钱粮。雍正元年,又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为王爵。清朝还在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均设立孔子牌位,并在每年春秋仲月行释奠先师礼。清代尊崇程朱理学,[30](P465-477)顺治、康熙年间下诏朱熹子孙袭《五经》博士职。康熙五十一年,下诏朱熹配享孔庙,列为“十哲之次”。此年,又命熊赐履、李光地等理学名臣编辑《朱子全书》,亲为之序。五十六年,他又为新编《性理精义》一书撰序,“程朱理学”遂成为清朝推行儒学教育的指导思想,其经学注释也是清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四、儒学文献和汉字文言的输出与受容相向而行
中国文明和汉字体系在中原腹地定型并完成制度化建设的同时就迈开了向四周输出的步伐,并且受到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的热忱欢迎与真诚期待。汉字文明圈内国家和周边少数民族对集中体现中原文明礼仪典章制度的儒学文献和汉字文言始终抱着虚心学习、积极受容的态度,这一点与字母文字文明向世界各地输出过程中对当地土著文化实行灭绝的历史截然不同。
儒学文献与汉字文言向四周输出的路线大致可分为向南方、西南方向的输出,向东输出到朝鲜和日本,以及向北和西北方向的输出。
(一)向南、向西南方传入岭南地区
早在秦汉时期,汉字文言就随着行政管理的需要进入岭南地区,输入到广西和越南,并在当地使用1000年以上。其后出现的“方块壮字”大致创始于唐朝(618—907),其性质属于“汉字式词符文字”。[31](P101)
公元939年,交趾人吴权建立起第一个独立的越南王朝,但每一代越南王朝都把汉字文言当作自己的正式文字来使用,并称其为“儒字”,以示正统之意。《大越史记》《越南史略》《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等越南史书,不但书名、体例仿自中国史书,而且都用“儒字”书写。大约在公元960—1279(中国宋朝)之间,越南人才仿制汉字创造了本土文字,称之为“字喃”或“喃字”,“喃字”表示土俗之意,与正统的“儒字”相对,其性质属于“汉字式词符文字”,被用来书写民族诗歌等通俗文学作品,如著名的《金云翘传》等。中国明朝时期,安南黎朝尤重儒学经典,设立“五经博士”,专治一经。从童蒙识字教育至科举考试,皆以儒学文献“四书五经”为教材,旁及子、史部文献。在长期的文化交往和人员交流过程中,中原文化和汉字文言已经融入越南民族的血液之中,被当成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正统对待。
在中国境内的西南地区,仿照汉字造成的“汉字式词符文字”还有苗文、瑶文、布依文、侗文、白文和哈尼文,等等,他们都出现较晚。其创制过程或借鉴汉字,或受到汉族学者和中央政府的帮助。
(二)向东传入朝鲜、日本
西汉末年建立的高句丽国把汉字文言视为本族文字普遍使用,新发现的《好太王碑》《冉牟墓志》以及在忠清北道中原郡发现的《中原高句丽碑》等早期高句丽国历史文献都是用汉字文言书写的。公元372年,高句丽模仿中原王朝建立“太学”,以儒家经典传授贵族子弟。唐贞观年间,高句丽派出“遣唐生”进入长安,广泛搜求中原典籍,尤重儒学经典、文学文献以及规范化字书。[32](P5320)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朝鲜都使用汉字文言记载本国历史,并引入中原科举考试制度,以儒学文献和汉字文言作为考试内容。公元7世纪,朝鲜人才发明了“吏读(Ido)”,15世纪发明了“谚文(Hangul)”,但同时也使用汉字文言。直至20世纪,朝鲜才彻底废除汉字。
约公元3—4世纪的中国晋朝时期,汉字传入日本。日报应神天皇十五年(公元284年),百济王遣熟悉中国经典的阿直崎赴日本。285年,百济博士王仁受阿直崎之邀,携《论语》和《千字文》赴日,向太子菟道稚郎子传授汉字与汉文化。公元8世纪,日本才创造出舍去汉字字意,单用读音作音符拼写日语,按汉字意思训释日语的“万叶假名”,标志着在日本大约持续了500年左右的与汉字文言“同文时代”的结束。日本在历史上虽然不像朝鲜和越南那样与中国有着极强的政治纽带关系,但长期受容并积极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三)向北、东北、西北传入辽、金、西夏
辽太祖实行文、武并重的治国策略,大量起用南人,实行耕、稼合治。神册五年(公元920年)“始制契丹大字”,[33](P16)但创制者“多用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其后又命其弟迭刺另“制契丹小字”[33](P969)契丹文字的创制,既起到了传承契丹族固有的尚武骑射习俗的作用,又极大地方便了儒学经典与汉字文言的输入与受容活动,为契丹社会养成诵经习儒的社会风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辽国在各地建立孔子庙,在上京、中京、西京等地仿中原汉人制度设立“国子监”和“五京学”,[33](P807)专门教授儒家经学,沿用唐、五代科举考试制度,以诗赋、法律和经义取士。经过契丹统治者大力提倡,诵读儒经、尊奉孔子、提倡中原儒家文化成为辽朝社会风尚,儒学教育对辽朝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34](P494)
金朝继承辽代文教政策,既发展女真文化,又尊孔崇儒。金初,太祖命完颜希尹和叶鲁“乃依汉人楷字,因契丹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35](P16)熙宗天眷元年(1138),又另创“女真小字”。同时仿中原制度,开办女真学校,开设女真科举。并使用女真文翻译汉文儒学经典,作为贵族学校的教材。从金熙宗、海陵时期开始,金朝推行儒学教育,各地公私女真、汉人学校皆以儒学经书为主要内容,同时兼含史部、子部。清人赵翼评价说:“金初未有文字,而开国以后,典章诰命皆彬彬可观。……惟帝王宗亲,性皆与文事相浃,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会。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36](P388-389)
北宋仁宗宝元1年(1038),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建立大夏国,与宋、辽、金形成对峙之势。党项族本无文字,其创始者“(李)元昊自制藩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37](P13995)号称“国字”,后世称“西夏文”。西夏建国初期就开始广泛搜求汉籍,并用新创立的西夏字翻译了许多儒家经典。西夏在州、县各地设立蕃、汉学校,实行科举考试,尊崇孔子,同样推行儒学教育。[38](P9-30)
通过周秦乃至隋唐宋明以来中原历代王朝前赴后继的持续努力,中国文明最终成为古代东亚地区先进文化的代表,成为周边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倾心仰慕和心仪的文明典范。中国文明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域外国家的文化输出和以上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受容活动也是自然发生的,文化输出和文化受容活动始终在相互学习、和睦相处的背景中顺利进行,其间并没有经过太过激烈的文化碰撞。而在这一文明输出与受容的过程中,汉字文言和儒学文献的输出与受容活动始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例如越南就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创造了“喃字”。无论政体发生什么变化,各民族、各国都能自觉维护儒学文献和汉字文言的正统地位。
五、儒学文献和汉字传承对东亚汉字文明圈内全体人民精神品性和审美能力的涵养
绵延近两千年的儒学经典化、汉字规范化活动,以及儒学教育的制度化建设,极大地培育、滋养和润泽了东亚汉字文明圈内各民族的文化品性,并由此催生出唯其独有的“读书至上”观念与热爱“书法艺术”的优良传统。东亚汉字文明圈内人民对知识和读书人的普遍尊敬,对汉字书法艺术的共同热爱,不但培育了全体人民喜爱学习的风气、等差有别而又和谐共生的文化理念,珍视生命与热爱生活的良好习惯,博大的家国情怀与人文理想,而且渗入古典艺术的方方面面,涵养了人民的品性,提升了全民的审美能力,提高了他们的艺术修养,从根本上引导了诗、书、画、艺审美趣味殊途同归,文、史、哲合治,而归于“经世致用”的治学模式,为特色鲜明的汉字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做出了独特贡献。
(一)重视学习,喜好读书,重视文献传承和法帖模仿,自觉向先贤学习的社会风气
长期的儒学文献和汉字文言传承活动,以及汉字书法艺术的推波助澜,在中国乃至东亚汉字文明圈全社会中养成了重视学习,喜好读书,重视文献传承与法帖模仿,向先贤和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的社会风气。
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在中国历史上首开私人教育,孔子对学习的目的、学习态度、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等一系列问题,都做出了极为精辟的论述。[39](P1-78)孔子的教学实践及其理性思考为中国社会重视学习、喜好读书的风气建立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孔门教育始终强调德行培养的重要性,强调通过不断学习与实际培养君子品格,实行仁政。这一教育模式被孔门后学概括为“修齐治平”,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一生追求的远大理想。孔门教育的内容虽然包容广泛,但始终以礼乐、典章、法度、纲纪等为主,其学习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学文献。“反复温习”与“温故知新”则是其所推崇的最为有效的学习方法。
荀子撰写了专门论述学习的重要文献——《劝学》,并将其置于卷首,以凸显“为学”在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荀子本人又是儒学文献传承的一代宗师,儒家“五经之学”大都经其传承,秦汉经学大师多出其门下。与孟子提倡“性善”说,主张一切知识皆从“心性”所出不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因此,他提出“圣人化性而起伪”,主张“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40](P434-449)荀子尤其重视外部知识的学习对修身的重要作用,并具体论述了不同类型经典在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的不同作用。
荀子之后,孔门后学撰成《礼记·学记》一文,集中讨论了教育活动中教学的宗旨和目的、尊师重道、教与学的关系、学习的规程和次第,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如何为人师表以及怎样才能有志于学等一系列教学问题,将孔门教育倡导的学习理论进一步落实于具体的教学活动。在教学宗旨与教学目的方面,《学记》强调教学为治国理政之根本,强调教学活动的社会作用是“化民成俗”,提出“尊师重道”与“师道尊严”,赋予教师以崇高地位。在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学记》提出了著名的“教学相长”理论,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广泛影响。《学记》还首次明确了学校教育的规程和次第,主张从地方到中央皆设立教学场所和机构,分阶段教学并按期考核,其具体的教学环节应为正式课程与课后复习结合,循序渐进学习并反复练习,并且提出了预防、时宜、循序、观摩等四种教学方法。《学记》还对如何为人师表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指出一位好的老师应该是能够引导、勉励、启发、温和而平易地对待学生,了解学生学习资质的优劣,知道学习的深浅难易的教育者。并且提出老师一定要对自己所教的内容比较熟悉而且有自己的心得,不能马虎应付。关于学习者如何做到有志于学的问题,《学记》也提出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从大处着眼,从细处入手的具体方法。
经过先秦以来以孔子和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的反复重申,中国古代社会全民重视学习的观念遍地生根,绵延乃至汉字文明圈内各国,并在中国文明影响所到之处结出累累硕果,为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雅士乃至全体民众普遍接受与传承,不断发扬光大,成为至今影响东亚社会,促进中国乃至东亚文明不断延续与进步的根本观念。
(二)儒学文献宣扬的政治理想与汉字书法的审美追求相互契合
儒学文献内容丰富,虽各有所长与偏重,但其根本宗旨不外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既认识到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永恒性,又追求一种人与自然的结构平衡关系,谋求和谐发展。
汉字书法的审美趣味之一是对“动态平衡”关系的艺术追求,既要体现层次分明,变化万千的灵动,又要表现出对立互补、结构稳定的思想。早在古文字阶段,古汉字就有“独体字”和“合体字”之分。独体字主要是象形字,如“ 、、、”等;合体字是指形声字和会意字,如“、、、”等。独体字和合体字的区分,表现出古汉字组合形式的多样性与层级性,其“本质上体现的是建立群体合作机制的思想。”[41](P12)进入隶楷阶段之后,汉字在单字构造方面更加追求动态平衡效果。历代都有人专门研究汉字的结构平衡问题,九宫格、田字格、米字格、“永字八法”等汉字书写的方法被先后发明出来。这其中尤以“永字八法”最具特点,其要点在于追求汉字书写用笔的动态平衡而非机械构成。若以汉字横、竖笔画的构成为例,汉字书写中虽然要求“横平竖直”,但实际书写出的横画往往表现为平稳而非水平,直画表现为挺拔而非机械垂直。
汉字书法的艺术追求不限于书法本身,而是对中国古典艺术,如绘画、雕塑、园林建筑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42](P253-283)传统中国画的“皴法”即以书法中的笔法入画,来表现山石﹑峰峦和树身表皮的脉络纹理。书法中的“布白”(又称“留白”),本是书家处理篇章空间的技术,但在文人画中也同样受到重视,以至于我们很少见到将整幅画面全部占满而不留空白的中国画作品,如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等等。中国书、画艺术家对“墨色”和“笔意”“笔势”的运用,大都来自古汉字的“意象”与上古文学诗歌作品渲染的文学“意境”,并非全然出自于艺术家对自然的观察和再现。汉字书法的“间架结构”原理还被引入中国古建筑之中,尤其体现在建筑屋面和梁柱之间的配合,以及古建筑对梁柱和屋面的装饰和美化方面。如甘肃秦安元代建筑兴国寺般若殿内部的屋顶与梁柱之间的设计,就颇能代表古建筑既重视屋顶坡面,又刻意保留多级梁柱的骨架式设计理念。
(三)意象、意境、理想,共同酿造出中国文明浓厚的人文倾向
汉字从一开始就是从人的视角进行符号构意,表现出强烈的“人化意象”。[43](P149-178)文学家余光中曾经举出了一个非常生动汉字文学意象的例子,“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地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①余光中:《听听那冷雨》,载《余光中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汉字书写中表现出的“人化意象”与中国古典诗歌、中国画的意象表达手法存在天然的联系,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借景生情、因情立象的作品比比皆是,如李白的《静夜思》,字面上描写的是“明月、霜雪、故乡”,但实际上却隐含着中国古典文学中源远流长的“明月”“霜雪”“思乡”等等意象,诗人将“明月”与冰冷的“霜雪”联系起来,一下子就触动了人们的“思乡”情绪,在读者的内心引发了连锁反应,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诗人心目中丰富的文学意象,同时也为“文人画”所青睐,经过历代画家反复揣摩和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发现这些文学意象,竟创作出不胜枚举的中国画,成为长盛不衰的文人画范式与文化母题。
中国古代的“经学”非常发达,内涵也非常丰富。其中蕴涵着先王的政教典章与治国理政思想,在中国文明史上始终拥有“垂范后世,纲维天下”的巨大作用。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学与现代学科分类范畴的文、史、哲、政治、伦理、教育等学科皆有所关联,不但“六经皆史”,而且文、史、哲等领域皆囊括其中,融为一炉、合而治之。经过两千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六经”宣扬的政治理想,不但酿造出中国文明浓厚的“人文倾向”,成就了文人士子们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并将他们的个体发展价值与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文人士子的宣扬与推介,经学思想又演化出全社会共同遵守和奉行的价值观念,渗透到全体人民的审美观念之中,成为中国古典艺术表现的根本内容。
综上可知,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就具有多元一体、求同存异,相互依存的特质。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文化立国,以文化多姿多彩而著称于世,众多民族和谐相处,团结和睦,欣欣向荣,共同谱写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明。而在中国文明定型于中原腹地之后向四周扩散的过程中,儒学文献和汉字文言传承活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汉字跨越方言和语言的鸿沟,成为东亚文明圈内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儒学文献塑造了东亚文化圈内各民族、各国共同的价值观念,表达了“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德国学者弗罗利安·库尔马斯(Florian Coulmas)指出:“从历史上来说,作为一种帝国语言,汉语书面文字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自古以来,它就作为一种纽带联系着中央政府及它的附属国和中国宗主权力下的保护国。中国的书面文字是中国在东亚统治地位的最明显的表现方式。事实上,文字与中华民族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以至于只要汉民族文化与尚未使用文字的文化发生联系,书面语言就会连同文字书写体系一同被借鉴,而并非只有后者。”①[德]弗罗利安·库尔马斯(Florian Coulmas)著,董静译:《东亚书面语言的功能和地位》,载黄亚平、白瑞斯、王霄冰主编:《广义文字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393-394页。
近现代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压迫之下,中国社会被迫从事全盘“西化”的激进式改革,各种现代思潮从西方传入,如戊戌变法、洋务运动、五四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奋斗实践业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现代中国制胜的根本思想保证。虽然儒家学说和儒学文献宣扬的许多思想观念和言论已经时过境迁,不能完全契合当前的现实,但儒家学说中对家国情怀的倡导,对和谐发展理念的推崇等等并未过时,而且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新时期全体人民文化自信的提升,仍需要建立在对中国古老文化和悠久历史认同的基础之上,并以汉字和儒学文献传承作为根基。当然,同时也要主动吸收世界范围内的一切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密切跟踪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前沿动态,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与时俱进。或许我们今天应再次明确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问题,让代表西方先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握手。让马克思拥抱孔夫子,或许是一条继往开来实现中国文明的再度复兴、切实提升全体人民文化自信的不二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