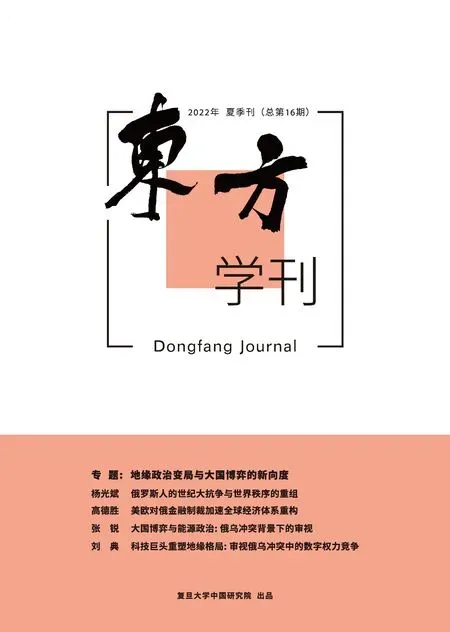英帝国殖民战略如何影响晚清当权士人:以郭嵩焘的见闻和洋务实践为例
2022-02-03周天宇
周天宇
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了长时间的斗争。中国从此被卷入列强所支配的世界体系之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列强对中国的支配是全方位的,除了血腥的战争手段,外交和文化手段同样也是它们推进殖民策略的一部分。在中国近代史的语境下,国族危如累卵之时,中西交流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朝贡体系崩溃后,中国与西方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而是在殖民体系中分属被殖民者和殖民列强,居于世界体系的不同圈层。中西之间的交流更是被冠以有积极色彩的“开眼看世界”这一名头。因此,“‘落后’的中国要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成为不言自明的惯例,不平等的往来成为晚清乃至民国时期中西交往的底色。
在这种不平等的底色中,清政府开展了洋务运动。无论是同文馆的翻译运动还是江南制造局,近代早期中西之间的交流以中国间接地获取外国的科技文化等信息为特点。除了通过译介的方式学习,派出驻外使节和西方打交道的方式则更直接。总理衙门设立后,清政府也采取选派官员出使西洋诸国的做法。其中,郭嵩焘是清政府派出驻外公使群体中最早出使的一位名臣。他动身赴欧,首先驻在英国伦敦,后又辗转法国和欧陆其他多个国家游历考察。他在欧洲获得的经验和认识成为其日后指导洋务运动实践的理论基础。
在近几十年间,郭嵩焘长期因为其洋务观点而得到高度赞赏,被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但是其局限性和受到列强蒙骗的一面却被忽视了。因此,在今天,更需要对以郭嵩焘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默默塑造这份世界观的列强殖民战略和意识形态因素进行梳理和反思。
一、研究回顾
关于郭嵩焘的独特思想和历史地位,学界对其已有丰富的研究,且出现了自1980 年代开始的郭嵩焘研究热潮。这一热潮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80 年代初,郭嵩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学界开始关注这位晚清的外交和洋务名臣。在这一时期,研究重心被放在对郭嵩焘本人的研究上。熊月之的《论郭嵩焘》(1)熊月之:《论郭嵩焘》,《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4 期。和《郭嵩焘出使述略》(2)熊月之:《郭嵩焘出使述略》,《求索》1983 年第4 期。以及钟叔河的《论郭嵩焘》(3)钟叔河:《论郭嵩焘》,《历史研究》1984 年第1 期。都系统地介绍了郭嵩焘的生平。另外王维江的研究还兼顾了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4)王维江:《郭嵩焘与刘锡鸿》,《学术月刊》1995 年第4 期。丰富了郭嵩焘使团的细节。这些研究侧重人物生平等细节的客观记述,少有直接的评价。
到了世纪之交,对郭嵩焘的评价逐渐增多,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拓展到政治学等领域。这一时期的成果有鲜明的价值判断,大多肯定其先知先觉的“进步士人”形象。夏泉分析了郭嵩焘出使时的矛盾心态,将矛盾归因于其进步的思想与中国守旧的氛围之间的冲突。(5)夏泉:《郭嵩焘出使英国时的矛盾心态》,《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3 期。吴祖鲲重点关注他的西学,赞其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6)吴祖鲲:《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西学东渐”中的郭嵩焘》,《社会科学战线》1995 年第2 期。田永秀等同样从文化角度肯定他以西方文化反思中国文化的进步意义。(7)田永秀、鲜于浩:《试论郭嵩焘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3 期。田海林等则盛赞其为洋务派里的智者、维新派的先驱、对内谋改革对外谋开放的先驱。(8)田海林、宋淑玉:《郭嵩焘评议》,《史学月刊》2001 年第3 期。除了论文,相关的论著中对郭嵩焘的高度评价也可见一斑。从高波的研究中可以观察到,王兴国、蒋廷黻、汪荣祖、范继忠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强调了郭嵩焘的先觉者形象。(9)高波:《晚清理学视野下的英国殖民秩序——以〈礼记质疑〉与〈伦敦与巴黎日记〉为中心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 期。高波文章中涉及的几位研究者的文献,可参见王兴国:《郭嵩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99 年版;[美]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0 年版;范继忠:《孤独前驱:郭嵩焘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年版。
在21 世纪的最初十年,对郭嵩焘的价值判断稍有弱化,但是研究领域的广度大大提升。除了历史学界,法学、外交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更深入地参与对郭嵩焘的研究。(10)法学领域关于郭嵩焘的研究可参见张建华:《郭嵩焘与万国公法会》,《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1 期。外交学领域的研究可参见蔡永明:《论晚清洋务思想家的近代外交观》,《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4 期。文学领域的研究可参见尹德翔:《郭嵩焘使西日记中的西方形象及其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第1 期。来自各学科不同面向的研究不仅丰富了郭嵩焘的形象,更对相关的史料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考辨。
而在最近十年,学界开始对郭嵩焘的“先知先觉”形象进行批判和再思考,特别关注时代背景和外部因素对于其形象的“建构”性作用。高波从郭嵩焘的理学角度出发考察其如何认识世界局势。(11)高波:《晚清理学视野下的英国殖民秩序——以〈礼记质疑〉与〈伦敦与巴黎日记〉为中心的探讨》。王锐指出,晚清士人的世界观受到有限信息的制约,不免受到域外知识和意识形态浸染。(12)王锐:《重新审视晚清士人的“开眼看世界”》,《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3 期。李欣然和方炯升同样注意到特殊时局对郭嵩焘的影响,并对其文明观进行了重新阐释。(1)李欣然:《道器与文明:郭嵩焘和晚清“趋西”风潮的形成》,《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8 期;方炯升:《外交思想史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驻外使节郭嵩焘、薛福成思想对观》,《山东社会科学》2021 年第12 期。而在国外,类似的从宏观出发的研究则出现得更早。(2)Man-Shing Tsui,An Advocate of Conciliation:Kuo Sung Tao's Attitude Towards Sino-western Relations,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Toronto,1973.
从上述四个阶段可以看出,对于郭嵩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领域越来越广阔,对于旧有研究的批判性思考也在次第展开。本文尝试从郭嵩焘使西以来的见闻出发,考察其获得感性认识的途径,他的见闻对其世界观的影响以及最终如何作用于他的洋务实践中。
二、郭嵩焘出使西方
光绪元年(1875 年)春,英国翻译马嘉理(A.R.Margary)前去迎接自缅甸来华的英国探路队,在云南被当地人杀死,其探路队也被逐回。为平息这一事件,英国以武力威胁要求清政府派人亲赴英国赔礼道歉。这一使命落到了郭嵩焘身上。(3)熊月之:《郭嵩焘出使述略》。虽身为一国公使,但是郭嵩焘的出访行动却受到了英国方面的支配和安排。清政府最终决定设立驻英使馆就是由英国方面,具体来说是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和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等人主动操办的。(4)张志勇:《赫徳与晚清外交》,中华书局2021 年版,第17 页。从总理衙门认可驻外公使的必要性,到选定郭嵩焘后为他挑选在伦敦的寓所,(5)《赫徳致金登干第40 号电》,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八卷(电报·1874—1895),中华书局1995 年版,第98 页。都由他们从中运作。
在英方的极力建议和推动下,郭嵩焘出使英国最终成行。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七日,郭嵩焘从上海乘英国邮轮,携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翻译张德彝、凤仪、马格里及随员、跟役共三十来人出发赴英。(6)熊月之:《郭嵩焘出使述略》。
远赴西洋向英人赔礼道歉这样的使命是耻辱的,朝臣避之不及。郭嵩焘接下担子后也遭到同僚们的百般嘲弄。(7)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234—235 页。郭嵩焘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但是这份愤懑很快化成了其参观并记录所见所闻的动力。使团途经舟山、厦门、汕头,于十月二十日抵达当时已是英国属地的香港附近,此处可以算得上是游历西方的第一站。未到香港时,郭嵩焘遇见英国船只从其座船边上掠过,互行军礼、升桅、奏乐,发出了“(英国人)彬彬焉见礼之行焉。中国之不能及,远矣”的感叹。(8)郭嵩焘:《使西纪程》,陆玉林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46 页。到达香港后,香港总督遣武官、提督来迎。使团上岸后,英国人列队欢迎。后来广东领事等人带郭嵩焘一行人参观了总督署、同时教授儒经和洋文两个学科的学馆等地。次日早晨,在香港总督的带领下参观了监牢。郭嵩焘仔细记录下了参观的厅室、犯人、刑罚等,以及附近停泊的英国、法国、美国战船的样貌和名称。十月二十三日,使团离开香港。(9)郭嵩焘:《使西纪程》,第46—49 页。后又经过暹罗、新加坡等地,记录下了在新加坡花园看到的珍奇鸟兽、名贵器物等。
除了器物,郭嵩焘看到英国海船之间的礼节,深以为彬彬有礼,因而赞赏有加。他听闻西洋船只都以古人名字命名,英国船更有用意大利(罗马)皇帝名字命名的,就认为西洋人都尊重年长的人。在座船上,郭嵩焘结识了一个意大利商人,其因开设洋行有功,而被授予世爵,便认为洋人以营商为重的特点可见一斑。他在报纸上看到英国赴北极探险的将军的惊险经历,也是啧啧称奇。从锡兰向亚丁的路上,郭嵩焘询问起荷兰和英国殖民的不同,获悉荷兰人在殖民地的课税多用于荷兰本土的建设,而英国人的课税则用在当地。无论印度还是澳洲,都是用英国人在当地征收的税款开河、修路、建设学馆等,因此“民无怨者”。他甚至听闻苏门答腊小国乐意献上土地给英国人而拒斥荷兰人。又听说英国人看重文凭,在交战中不杀有文凭的俘虏;非洲和阿拉伯各殖民地内市集繁忙,欧洲的名人如拿破仑的雕像在广场林立,雄伟壮观。何其“文明”哉!(1)郭嵩焘:《使西纪程》,第2、7、11、15、20 页。郭嵩焘虽人还未到英国,却已经在船上通过耳闻,大致建立起了英国的形象,对英国“文明”的殖民、“文明”的战争有所了解,并大加赞赏。在郭嵩焘日后看来,英国代表着一种良善的殖民主义。(2)高波:《晚清理学视野下的英国殖民秩序——以〈礼记质疑〉与〈伦敦与巴黎日记〉为中心的探讨》,第96 页。
一路经过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亚丁、阿拉伯等英国殖民地区,郭嵩焘的记录更为详细了。他记下了殖民地中的西洋人之间的礼节、身上携带的用于证明身份的凭证,英国人比荷兰人更优越的殖民地管理制度。这些在当时的郭嵩焘眼中都是先进的制度。中西并行的学馆、宗教宽容的政策等都令他赞叹不已。而新加坡某个花园内收集的大量珍奇花草、动物更是让他见识到英帝国国力之强盛和其殖民之广阔,搜罗物产的能力之强大。这些都帮助郭嵩焘在未到英国之前就知悉了这个世界上头等的强国是何等面貌。
概括来说,英国的武器、兵舰等军事装备,文书、学校、习俗等文化现象,植物园、博物馆等物质成果得到了郭嵩焘的重视。此外,他也注意到英国的对外扩张是受其殖民政策指导的。虽然殖民政策的“文明”外衣仍然蒙蔽着他,让他看不清英帝国的本来面目。
虽然看过并感受过英帝国的物质文明成就,但是对于这个头等强国称霸世界的方式,郭嵩焘显然是不了解的。几个世纪以来的殖民掠夺和领土扩张才是英帝国的本色,而非“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英国人主动向郭嵩焘炫耀的正是帝国殖民扩张政策产生的“文明的结果”,而非“野蛮的过程”。鸦片战争爆发时,郭嵩焘正在浙江担任浙江学政的幕僚。他目睹了英国船舰如何用炮火轰开中国的大门,对“野蛮的过程”深有体会。但是赴西后,他此时又对英国的船舰连连称羡,他可能并没有认识到:“英国人凭借他们在欧洲国家斗争中取得的优势,以贸易公司、武力征服和金融霸权的方式,对全球范围内的土地进行征服,以获取市场和资源。”(3)[英]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12 年版,第16—20 页。虽然这里的表述是以东印度公司和南亚的印度为例,但是在中国,两次鸦片战争和数个不平等条约已经足以证明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这个东亚的古老国家。
三、郭嵩焘在英国
郭嵩焘眼中的英国既是其所目见的英国,也是英国人想要在他面前展示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成果,两种因素叠加形成了郭嵩焘的英国观。
刚刚踏上英国的土地,郭嵩焘就受到了英方的“礼遇”。光绪二年(1876 年)十二月初八,郭嵩焘一行人抵达南安普敦(Southampton),金登干按照赫德的指示将郭嵩焘接往伦敦寓所。这座寓所是金登干严格按照赫德的要求准备的,赫德之前要求将他们安排在城里,并明确指示:“要舒适,一所乡村住宅可能是最好的;但为了观光和学习,城里的房子较好;所以,努力安顿他住在城里。他到伦敦之后,带他和一名译员乘马车转一下……”(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一卷(1874—1877),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461 页。
当郭嵩焘在安排下走上伦敦街道,看到明星万点的街灯和滔滔不绝的往来车马,楼宇间烟雾一般的蒸汽,他感叹道:“阛阓之盛,宫室之美,至是殆无复加矣”。(2)郭嵩焘:《使西纪程》,第80 页。同样是首都,郭嵩焘久居的京师和伦敦之间有着两种文明形态的巨大鸿沟。前者是一个古老农业国的京城,而后者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灯火通明。因此,当他看到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伦敦的街景,郭嵩焘激动的心情和被震撼的观念是可以想见的,溢美之词也在情理之中。但他却不知道这些都是赫徳和金登干等人安排好的。
但是郭嵩焘毕竟不是来旅游的,他的公使职务要求其不仅要与英国的官员打交道,更要多走多看,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进物质文化,并尽量带回中国,为洋务运动服务。不过,他对于英国的认识除了目见之外,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在伦敦的英国政要对他的引导。
这些政要里,英国的国会议员居其首。光绪三年(1877 年)正月初一,中国的新年元旦,郭嵩焘与在英的中国人互相拜贺之后,英国议员怀德、谛克斯专程前来带郭嵩焘一行去参观英国的蜡像展览。这些蜡像有坐有立,以国主为多,最著名者如华盛顿,还有林则徐、贞德等人的塑像。郭嵩焘看完之后评价道:“奇玮夺目。”(3)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42 页。
何为展览?现代展览本就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由于蒸汽轮船、火车的出现,世界各国和各大城市间的交通距离被大大缩短。原本难以携带转运的全球动植物可以通过蒸汽轮船和火车运往大都市。大都市也由于这些交通条件的改善,成为展览举办的地点。因此,工业化的基础设施是现代展览的物质前提。在郭嵩焘到达英国不久前的1851 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简称“世博会”)在伦敦召开。这次博览会是为了彰显英国强大的工业文明而召开的。展览会的主场馆是英国政府在海德公园建设的“水晶宫”,它是一座由玻璃和钢骨制成的恢宏建筑,通体透明,与欧洲传统的古典砖石建筑格格不入。可以说,英国正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工业实力才建设了这样一座特别的“工业风”建筑。
世界博览会吸引了西洋诸国参与,各国列强纷纷将自己最先进的工业机器、制造设备和成品送到展览会上展示。一方面,这种“展示”符合工业文明中市民阶层、中产阶级的审美需要和休闲需求,另一方面,世博会也是各国展示自己实力和国家面貌的绝佳机会。具体来说,就是各国送什么样的展品直接反映了该国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早在第一届世博会,就已有中国人参与,而中国送展的多是湖丝、绍酒、茶叶等手工制品。在世博会上,中国馆的建筑也是亭台楼阁、戏台园林的样式,多采用飞檐斗拱的木质结构,在众多钢铁巨物之间显得格格不入。中国的这些展品虽然是小农经济中的精品,但是与西方展出的蒸汽锤等工业设备和工业产品显然不属于同一范畴,两者泾渭分明。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在当时世界的经济秩序中,中国是原料产地,而西方几乎掌握全部的工业产能。甚至中国展馆的建设也几乎都是由英国人来掌握的,建设什么样的宝塔、安排什么样的展品、吸引什么样的游客均在赫德和金登干的往来书信中敲定。(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一卷(1874—1877),第338 页。
在这一背景下,“展览”这种文化活动形式具有强烈的展示文明、炫耀国力的色彩。而这次展览以西方列强诸国以及罗马、希腊这些西方文明母国的名人政要蜡像为展品,再带有少量与这些列强打过交道的、处于世界边缘地带的人(如林则徐)的蜡像,共同组成了一个以西洋列强为核心的文明展。虽然那场展品的选择、排布今不能考,但是反映了当时英国人对世界的基本看法:西方牢牢占据世界的中心,其他地区的价值是锚定在与西方关系的远近亲疏上。英国议员选择带来自中国的公使去参观这次展览,多多少少也带有展示西方文明,让郭嵩焘长长见识的意味。
除了蜡像展,正月初二,郭嵩焘在英国人带领下参观了“万生园”(Zoological gardens),即官办的动植物园,为国家驯养鸟兽的地方。郭嵩焘的夫人还在金登干的安排下,特地看了动物喂食。(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一卷(1874—1877),第498 页。园子里的鸟兽来自全球各地,其中也有中国四川的锦鸡、云南的孔雀、浙江的画眉鸟、江南的唐鹅、奉天的鹿等。其余主要来自印度、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3)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142 页。
同世博会、蜡像展一样,动物园、植物园也具有展览的属性,扮演着信息传递者的角色。在“万生园”中,可以看到中国的锦鸡、老虎,又可以看到印度地区的大象、阿拉伯地区的骆驼,各地的稀奇植物和动物一应俱全。这种展览即是一个遍布全球的、拥有独一无二广阔殖民地和丰富物产的英帝国的缩影。更重要的是,能够将这些物产——活的动物、活的植物带回首都伦敦,建起一个园子,专供伦敦的绅士淑女参观游玩。这种行为背后彰显的强盛国力让来自被掠夺物产的国家,处于展品被动提供者地位的郭嵩焘感到非常惊羡。
此外,英国官员还带他参观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大英博物馆里保存的汉文古籍,古籍中甚至还包括了许多内廷善本,这些都让郭嵩焘惊羡连连。(4)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161、228 页。
除了较温和的文明展示,郭嵩焘还参加了军事方面的展示活动。郭嵩焘一到英国就对战舰颇感兴趣,但最终没有成行。(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一卷(1874—1877),第494 页。正月初五,在金登干的安排下,(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一卷(1874—1877),第498 页。郭嵩焘如愿来到朴次茅斯(Portsmouth)眺望了英国建造的两艘铁甲小船,并观看了其演练炮击,甚至亲手开了一炮。据日记描述:“炮重三十八吨,炮子三百五十磅,火药一百三十磅,皆用机器运转……又设电气线于机器墙内,引手按之,而声发子出,可及七千五百余步。但得一人,运机器有余,可云神妙……船旁小炮及连环子炮皆历试之。亦生平之创见矣。”(1)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146 页。郭嵩焘在感叹英国铁甲战舰电气化的火控系统之先进外,也注意到英国在朴次茅斯海军基地的布置,仍然是连连称奇。用金登干的话说,他安排的参观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没有出一点差错,一切安排都十分完美”(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一卷(1874—1877),第508 页。。
按照现在的外交礼节和惯例,邀请不久前曾与自己交战过的国家的最高使节参观自己的兵工厂和战舰,并且在其面前演练实弹炮击,毫无疑问是一种带有羞辱意味的行为,是炫耀武力、警告该国的挑衅举动。但是当英国人获知公使郭嵩焘对战舰很感兴趣,于是邀请他去参观自己的战船和炮击演练的时候,郭嵩焘并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虽然这一次不是温和的艺术展、生物展,而是仅十余年前曾攻击过中国水师、杀伤军民无数的英国海军战船和火炮的展示。英国官方这样炫耀武力的举动不但没有引起郭嵩焘的怒火,反而由于英国人准备了精美的酒食,彬彬有礼,迎来送往,而被他视为又一次愉快的参观体验。
除了“物质文明”,英国人在对自身“制度文明”的展示过程中也对郭嵩焘的英国观有所引导。
光绪三年(1877 年)二月三十日,郭嵩焘来到英国议会下议院旁听会议。这次参观是应英国官员阿什百里之邀请,公使、副使、翻译三位官员对英国议会讨论事务的情景进行了生动的还原。议事进程由斯毕格(3)斯毕格即Speaker,议院议长。主持,两派议员分属两党,坐于两侧,在辩论中唇枪舌剑,而议会人数众多,但并不是毫无秩序,而是先挂号,然后依序发言、问诘、辩论,虽各执一词却秩序井然。后来,翻译张德彝感慨道:“利弊之当兴除者,曲直之当申辩者,随时布闻下院而上陈之……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因其处事力争上游,不使稍有偏曲,故举办一切,上下同心。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而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惮也。”(4)汪强:《形象塑造与知识生产:晚清域外日记中的英国议会(1866—1885)》,《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 年第3 期。
可以看出,张德彝对于英国议会已经有了一定认识——意识到这是一个代议制下,各议事代表互相争辩,一方取得优势后方能推行其政见的制度。但是他也夸大了这一制度的优越性,认为在议会争辩中取得上游后被通过的议案就一定是上下同心、合众论而顺众志的善政,用意至美。他不能看到的是:英国议会的实质是统治阶级的投票游戏,是他们瓜分利益的场所。他似乎也忘了正是在这座下议院通过了对华开战的法案,引发了鸦片战争,给自己的祖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过要求郭嵩焘、张德彝等生长于儒家农业文明的古人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下的各社会阶层激烈的斗争、博弈与尖锐的利益冲突,未免强人所难。
郭嵩焘出使时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展了起来,但过程困难重重,又遇到难以调停的马嘉理案,他是带着屈辱的使命动身赴英的。由于一心想要发展洋务,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从一开始,郭嵩焘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从香港到伦敦,他在日记中记录一路的见闻,多是称羡的溢美之词。无论是英国人的礼仪、轮船、武器、园林,凡是属于洋务中“西用”范畴的,他都一一记录下来。而在器物之外,他和他的使团在“中体”方面也有所突破,对于英国的议会制度、学仕分离的制度表示肯定,认为其有利于国家的施政和人才的培养。
虽然郭嵩焘对于英国的制度极尽赞美之能事,但是郭嵩焘所目见的英国就是这个“头等强国”的本来面貌吗?小说家狄更斯在他的名作《雾都孤儿》里如此描绘伦敦的警察局:“尽管像这类地方的当值的守护神对女王陛下的臣民的,特别是贫穷阶级的臣民的名声、信誉,甚至生命行使着随意的独断专行的权力;也尽管在这里的四墙之内每天都有人在玩弄着使天使哭瞎双眼的离奇的花招;除了通过日报有所透露之外,一般人却全都一无所知。”(1)[英]狄更斯:《雾都孤儿》,黄雨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155 页。因为父亲负债累累,狄更斯小时候需要在泰晤士河畔每天做12 个小时的童工,其所看到的伦敦与郭嵩焘所看到的大相径庭。在狄更斯笔下,英国的制度对底层的贫苦大众显然不够“文明”。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象的。”(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306—307 页。这些在现在看来完全不宜居的地方确是英国工人阶级生存的环境,郭嵩焘似乎对此并无考察。
另外,作为大清的使节,郭嵩焘本应拥有自由的行动权,能够独立考察英国的国情和面貌。但是在日记中,可以发现郭嵩焘往往是受到英国士绅的邀请才进行考察,十分被动。如果想要主动考察,也往往要询问金登干等人的意见才能成行。事实上,使团一举一动均在英国人的监控和掌握之中。在考察的成果方面,他们也多以白描的形式记录所见所闻,一心想将这些先进的文明成果带回国去,却很少思考自己的母国在当时的世界上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种攀附和模仿能否取得成效?
反观英国,英国非常清楚这个世界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他们带郭嵩焘去参观艺术展览、生物展览、铁甲兵船、议会大厦、学馆大学等,都是在向世界边缘的国家展示自己的先进性和文明的等级差异,进一步巩固和宣示其牢牢把握的世界体系,并赤裸裸地告诉中国人这个体系是被何种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力量所保护着。19 世纪的欧洲以国际法准则来推行有利于其霸权的国际关系结构,发展其贸易、殖民和外交,并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之间维持表面上平等的关系,而这种平等的、互相承认主权的国际关系的目的在于完成欧洲国家之间合法的利益转让。(3)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版,第703 页。
郭嵩焘对此没有清楚的认识,反而为殖民者论述其合法性。他认为英国殖民有天道合法性,殖民地人民天然属于下层,这种以天理等级制为基础的中华主义,与19 世纪殖民主义无意识中形成了联盟。(4)高波:《晚清理学视野下的英国殖民秩序——以〈礼记质疑〉与〈伦敦与巴黎日记〉为中心的探讨》。他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是“有道之国”对“无道之邦”的兼并——“印度无道,英人以道御之,而土地民人被其泽多矣,此亦天地自然之理也。”(5)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390 页。关于被殖民者反而对英国制度产生钦慕和认可,强世功在《中国香港》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英国保守党的政治策略一面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一面是维护帝国体制的民族主义思想。”(1)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版,第78 页。他们一边用法理上的对未开化之地的支配维护英国人的民族主义自豪感,一边利用这种自豪感为英国的资产阶级生产枪炮,继续进行殖民战略。这种政治上的精明甚至为他们培养出了一批在心性和道德观念上与英国资产阶级相通的殖民地官僚,并借由文化和社会的纽带加强了这种联系。
四、郭嵩焘论财税
关于郭嵩焘的洋务观,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本节从财税和教育两方面论述:郭嵩焘出洋的经历和见闻改变了其旧有的洋务观。
首先是财税。洋务派官员最急切的诉求是使国家富强,而只有有了财帛才能推行对国家有利的政策,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洋务运动的核心之一是财政改革。到了同治年间,大清的财政收入可以分为田赋、关税、厘金三个主要来源。郭嵩焘想要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的在于后两者。
就关税而言,同治五年(1866 年),郭嵩焘上奏《密陈粤海关情形疏》,指出粤海关官制僵化,且“近年内江通商,湖丝一项全赴上海,茶叶一项分赴汉口、九江。粤东利源全窒,商旅萧条,日甚一日,征税犹及百万。以今准昔,情事昭然”(2)郭嵩焘:《郭嵩焘奏稿》,杨坚校补,岳麓书社1983 年版,第312 页。。除了外部因素外,粤海关的萧条还在于书吏在海关事务中处处掣肘地方官施政,花销惊人,为弊滋甚;粤东民气浮动,绅商把持,远甚他省。(3)郭嵩焘:《郭嵩焘奏稿》,第312 页。所以,当时署理广东巡抚的郭嵩焘认为,虽然粤海关年征税尚能及百万,但官吏贪腐低效、绅商把持商务的积弊已久。虽然他也看出粤海关的缺陷,却没有提出相应的改革举措,仅说自己勉强维持住了关税的数额,对于腐败则无可奈何。
而到了光绪三年(1877 年),即郭嵩焘出使的第二年,他又上了一折《请纂成通商则例折》(4)郭嵩焘:《郭嵩焘奏稿》,第381 页。。在这一折中,郭嵩焘奏请设立中国与西洋通商的则例,也就是规则。他认为,中国已开放与西洋的通商,但遇到冲突,往往需要使用西洋的律法来解决,因此“观望周章,动为所持”(5)郭嵩焘:《郭嵩焘奏稿》,第382 页。,处处受到洋人牵制。
而如何落实《南京条约》中的“秉公议定则例”(6)中国海关编:《中外约章》第一卷,海关总税务司统计处1908 年版,第163 页。,郭嵩焘完全受到了总税务司赫德的影响。赫德在之前分析过中国的商情、交际、词讼,郭嵩焘认为他有关交际和词讼的见解可以加以利用,参考各国所定的通商律法,纂辑通商则例一书。而赫德则是在1861 年首次进京之后就一直力主中国应该往各个签约国派遣公使。(7)张志勇:《赫德与晚清中国驻英使馆》,会议论文,第三届“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2010 年,中国·广州。赫德与郭嵩焘私交甚密。郭嵩焘认为赫德为中国办事非常出力;而赫德则对人夸赞郭嵩焘有学问、有能力、性格温和、头脑清醒。(1)贾熟村:《赫德与郭嵩焘》,《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0 年第1 期。
郭嵩焘吸取了马嘉理案的教训,出使英国之后,他认为中国应当与通商国家订立规则,这样在解决贸易争端、教案之时不至于受制于人,而且关税的税额是一国保护本国工商业的最重要手段,是发展本国经济的护商政策。(2)李新士:《郭嵩焘洋务观研究》,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51 页。就这一点来说,郭嵩焘是进步的,他愿意实行新政缓解中西通商交流下不可避免的冲突和矛盾。但他提出的方案则是完全的英国式的,在《万国公法》间寻求中国商法模仿的对象。但是,中国和列强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于《万国公法》中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边缘位置决定了“秉公议定则例”只能是英国操控下的商业规则。
关于“规则”,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在其《大地的法》一书中借用一位西班牙传道士从道德和神学角度为所谓“正义战争”辩护的例子,阐述了国际法对于殖民战略的推动作用。(3)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72—115 页。在英国与中国对垒的前线,这种国际公法体系向中国的渗透和中国主权被外国人来建构可能也是为了合法地完成利益的转让。
至于厘金,最早是在咸丰年间设立、用于筹措清剿太平军的军费的一种商业税。到了同治五年(1866 年),郭嵩焘上奏《筹议各海口添设行厘片》一折,主要诉求是广东的坐厘制度成为绅商把持、获利无穷的地方。厘金制度中的坐厘是与行厘相对的,前者在产地或销地征收,而后者在转运过程中征收。商队通过官办的关卡,需要验货收行厘税,这一点广东绅商不能操作,而在产地和销地征收的坐厘则大有文章可做。税率多少,货物多少,价值如何判断都是绅商内部定好的规矩,贵的货品说成是便宜的,税率也是能减就减,互通方便,税额越来越难以征收。(4)郭嵩焘:《郭嵩焘奏稿》,第315 页。因此,郭嵩焘主张渐次裁汰坐厘,目的在于“稍除绅商专利之弊,于事局实有裨益”(5)郭嵩焘:《郭嵩焘奏稿》,第315 页。。
而郭嵩焘对待商人群体的态度在出使英国之后有所改变。经过考察,他认为西方富强之本在于“通商为制国之经”,以商业立国,确立了以工商为本的发展战略,(6)郭嵩焘:《郭嵩焘奏稿》,第384 页。建构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国家大政所为,商贾有权参与,百姓有利归于国家,国家有利让百姓受益的制度能够形成国富民强的良性循环,(7)李新士:《郭嵩焘洋务观研究》,第51 页。这一点让郭嵩焘非常羡慕,称为“事举而力常有继,费烦而用常有余”(8)郭嵩焘:《郭嵩焘奏稿》,第555 页。。他还从春秋战国的历史中了解到战国时期私商占优势地位;以牛犒师诓骗秦军救郑国和设计营救晋将的都是私商;齐国的渔盐之利使得其都城临淄成为商品贸易中心。(9)马伯煌主编:《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63 页。转引自李新士:《郭嵩焘洋务观研究》,第54 页,由此,郭嵩焘认为,中国古代也有商业大发展的时期,其目的仍然是为官督商办的洋务运动提供合法性。
郭嵩焘作为晚清官员中对传统抑商政策批判得最彻底、最系统的人之一,他认为,要“急通官商之情”,“《大学》平天下之道,不越用人、理财……理财有难易之分,其要不外开源节流”。(1)郭嵩焘:《郭嵩焘奏稿》,第253 页。他的财政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不仅吸取了西方财政制度的先进部分,也看到了西方列强中商人参与政治的情况。但是,郭嵩焘据此而下的判断是:英国的官商互相保护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就能够帮助中国实现国富民强。这样的一厢情愿恐怕是忽略了外因:中国事实上处于列强环伺的危险境地。
五、郭嵩焘论教育
关于洋务进展缓慢,郭嵩焘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心风俗没有改变”。出使之后,他深切感受到务实求实的风气是西方社会的根本,也是西方能够发展产业的基础。相比之下,中国“整个官场‘欺’‘瞒’盛行,举世闻名”。他又看到《泰晤士报》讥讽中国之语:“相沿制度及各衙门所办事件及官人德行,相习为欺诈已数百年。”(2)郭嵩焘:《郭嵩焘奏稿》,第703 页。所以,为发展洋务,必须改革教育。
在英国的时候,郭嵩焘在当地教师的邀请下参观了许多学校,考察了英国的教育制度。光绪三年(1877 年)十二月十九日,郭嵩焘来到一家小学考察,发现学校注重寓教于乐,讲求实在的学问,感叹道:“西洋成就人才,使之为童子时嬉戏玩弄一以礼法,又群萃而歆起之,以不至失其厌倦之心。殆尽善尽美矣!”(3)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 年版,第436—437 页。小学的课程设置包括自然课、手工课、算术课,既有提升思考能力的教学,也有锻炼动手能力的教学。(4)蔡雅红:《郭嵩焘笔下的英国形象》,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14 页。之前郭嵩焘曾见到苏格兰的一所女校中教室满墙挂图,均为地理、植物、动物、机器、工艺、数学、簿记等各科教学内容,慨叹道:“皆中国所未闻未见者也。”(5)田永秀、鲜于浩:《试论郭嵩焘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两年后,郭嵩焘在参观法国一所技工小学后,更是感叹道:“(法国6 岁到14 岁的学生)大率首识字,只习歌唱,次习加减乘除之数。”又想到这仅是一所技工小学,专习技术,“教课之方,一皆文武实用,人才安得不盛!国势安得不强”!(6)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352 页。至于大学,郭嵩焘特别注意到大学实行的导师制:学生学习天文、地理、数学、律法、诸格致之学,然后进行考试方能选择专业,导师监督其学习,期满授予其学位,实行学仕分离的制度,无论学生所学的是何专业,都有机会进入仕途或凭借其所学来谋生。(7)蔡雅红:《郭嵩焘笔下的英国形象》,第14 页。
总的来说,郭嵩焘对于西方的教育体制持肯定态度:教学的内容既是合理的,将各个年龄段的学童分为不同的年级,又有针对性,对技工教实用的技巧,对普通小学则是天文地理、数学工艺无所不教;教学方式也是寓教于乐,兼具对动手能力的培养;大学中实行的导师制也比较先进,分设多个专业,学生能够通过考试选择专业而不必考虑其他限制。
最重要的是,西方学生即使学习的是科学技术、工艺制造,仍然能够做官入仕。这一点让郭嵩焘大受震撼。中国的科举制使得对经书、文章熟悉的人可以入朝做官,而掌握算术、技艺等末技的难以为官,往往只能担任吏的职务。而在中国的官僚体制内,“官”和“吏”泾渭分明,等级有别。洋务运动进展缓慢也与官僚不懂技术,相关的技术人才难以培养等有关。郭嵩焘对这一点的关注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郭嵩焘的局限性也正在于此。他看到了英国教育重视对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和牛津、剑桥两座高等学府的优良学风,但他没看到的是英国教育的先进根植于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文明性质。因为,工业革命之后,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资本家工厂主既需要技工学校来培养训练有素的工人来做工,也需要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来培养精英人才以维持庞大的英帝国。学校的分类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不同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发达的工商业社会中已经出现了阶层,以及各阶层有各自的教育需求和供给这一现实。像郭嵩焘这样的洋务派官员看到英国的教育制度连连称羡情有可原,但想将其照搬回中国,认为仅靠这样就能培养出中国的洋务技术人才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这就有些幼稚了。
郭嵩焘对英国教育有这样一句总的评价:“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1)蔡雅红:《郭嵩焘笔下的英国形象》,第15 页。他看到的是英帝国的人才济济、教育发达,没有看到的是英帝国并非凭教育发家,而是用枪炮和钢铁征服世界,用整个帝国的资源供给本土的工商业运行、发展,它的繁荣建立在暴力的掠夺之上。
虽然郭嵩焘没能完全掌握欧洲教育体制的全貌,但是他的确抓住了重视“实学”这一特点,然后借此展开了改革。首先,他提倡恢复湘水校经堂。这是一所创立于1833 年的附属于岳麓书院的讲堂。此堂“专勉实学”,以经义、治事、辞章分科试士,较好地继承了湖湘学派重义理不废事功的学风。(2)李新士:《郭嵩焘洋务观研究》,第41 页。其次,他创办了思贤讲舍,亲任第一任主讲。他在讲学时说:“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亲师取友以求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3)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四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57 页。他强调修身和为学的各个方面,目的在于挽回颓败的世风。除此之外,他还看重自然科学。因为中国教授“实学”的学堂极少,他在湘水校经堂和思贤讲舍都开设了天文算学课程。因为他在出使英法之后,认定数学是西方一切学问的基础。(4)李新士:《郭嵩焘洋务观研究》,第42 页。同时他对创造发明、探索自然规律尤其重视,这一点与当时其他人有所不同。
诚然,西人务实的社会风气有助于其繁荣发展,值得当时的清朝官员和士人学习;重视实学的教育制度也适合当时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的中国模仿,以培养相关的人才。郭嵩焘能够跳脱一定局限,触及西方文明中较实质的部分。但是,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仍然不够深入,如上一节所说:英国的教育是为其帝国的运作而服务的。由于郭嵩焘对英国赖以发家的航海史、殖民史不够了解,只看到了先进的制度文化,便醉心于其中,想要将其带回中国,帮助开展洋务运动,以图富强,救亡图存。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在半殖民地的国家状况下,没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外部条件,仅仅通过兴办洋务就想比肩泰西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郭嵩焘在这里将西洋的教育与中国的教育作对比,看似是自发的比较,其实是接受了西方人观念中的中国印象。近代西方的知识分子对于东方的描绘伴随着西方霸权向世界扩张也传播到世界各地。更重要的是,这种东方印象也得到了东方人的认可和接受。在把话语权拱手让人的同时,类似于郭嵩焘这样的东方人已然落入西方话语的圈套之中。
虽然郭嵩焘重视教育,提倡教化和实学,但是他对整体社会的态度却是守旧的。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谈及:“微有缺者,让中国亿万小民与彼为仇立论,此正数十年来中外诸公所用以为藏身之秘术者。中国小民何知远计哉,洋人弄而玩之,夺其利而又歆之,稍厚其资,受其雇役,靡然以从。据此为言,适为洋人所笑,而中外诸公至今无能省悟,惜哉无是可也。”(1)郭嵩焘:《复曾国藩》,载《郭嵩焘全集》第十三册,岳麓书社2018 年版,第215 页。他认为,中国的小民不懂远计,在洋人愚弄下听凭外人操控而不能醒悟。他针对欧洲的工人运动,又说:“白兰茀尔得(Bradford)工匠数十年前纠众滋哄,减工加价。近年机厂以贸易日渐削落,与工匠议仍照旧价,工匠不允,遂至停机。于是工匠大汹,毁机厂而爇厂主房屋……去年美国火轮车工匠毁坏铁路,情形与此正同,盖皆以工匠把持工价,动辄称乱以劫持之,亦西洋之一敝俗也。”(2)郭嵩焘:《郭嵩焘全集》第十册,岳麓书社2018 年版,第484 页。对于欧洲的工人争取权利的运动,他形容为纠众滋哄,胁迫企业增加工资,侧面说明其对欧洲的民权运动和社会阶层的深层矛盾知之甚少。
总的来说,郭嵩焘的洋务观根植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而由于其出使英法,有游历的经验,在中体西用论上有一定突破。但是,其关于税制改革、商人治国、实学兴邦、重塑风气的主张在当时的时局下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且,即使是出使英国的使臣,他对于英国的历史和富强的根源仍然看得不够清楚。从学习者的角度来说,郭嵩焘是一个优等生,算得上出类拔萃,但他也仅仅是一个跟着英国学习的学生,在他的洋务观中可以看到他受英国影响至深,甚至有被英国人牵着走的痕迹。
六、结语
自郭嵩焘出使英国以来,其观察、体悟和思想都与英国有关。从刚刚踏足伦敦的惊讶、恍惚,到参观英国发达物质文明时的啧啧称奇,再到见识了英国的制度文明和文化后感叹自愧不如,最后在日记中记录下心得和体会。他一心要将自己学习到的先进文明带回中国,希望完成中国实现富强、现代化的历史使命。通览郭嵩焘的思想流变过程,除了其求富求强的强烈愿望外,英国人在其出使期间对他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里的英国人除了与他直接打交道的官员士绅,也包括展现在他眼前的英国发达的工商业社会各个阶层。
这些图景无不体现着英国统治之下的世界秩序是一个以西欧诸国为核心的,由已经发展起来的旧殖民地——如印度、埃及、北非等地区组成中间圈层,以及新殖民地区如中国组成外围圈层的这样一个“同心圆”式的世界体系。英国人带郭嵩焘看展览、观战舰、听议会、进学校都是在向落后地区展示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是殖民霸权在各个层面的降维打击。郭嵩焘深陷其中,对西方文明连连称羡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郭嵩焘出使西洋,观察到了西洋文明的发达和先进现象,就想要将这些搬回中国,并认为适用于西洋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中国,凡是西方来的好东西,都值得学习。他在反思中国存在的问题时,又不免落入了文明等级论的陷阱,把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归因于自己处处不如西洋,而这种一无是处,具体来说就是社会风气原始、教育体系落后、科技水平低下等,然而他却忽视了,或是被故意蒙蔽了关于帝国主义殖民者如何靠掠夺、征服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来完成早期积累,以及他们为维持这样的利益链建立了何等的世界体系。
1980 年代,郭嵩焘、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重新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在1980 年代到21世纪最初十年,郭嵩焘都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也有人认为他是受时局所限而壮志未酬的改革者。这些关于洋务派官员的重新评价构建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洋务派探索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路径。这种路径排除了自下而上的革命,而专事自上而下的改良:学习西洋的器物和制度就能够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从而形成了一套极具影响的历史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