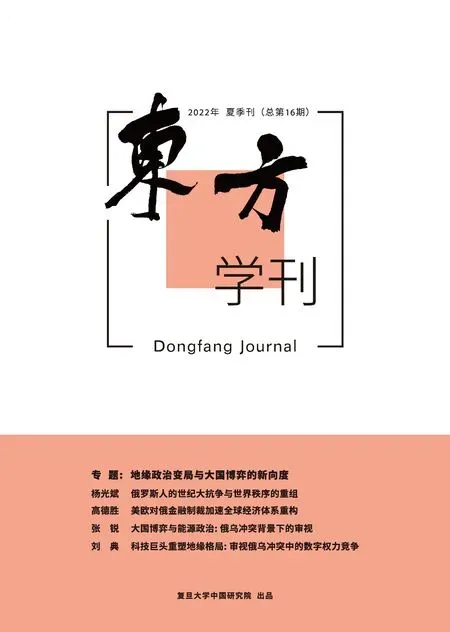《开端》的“开端”
2022-02-03冯庆
冯庆
电视剧《开端》的主要话题是“循环”。但“循环”只是剧情展开的叙事手法,而非叙事的目标。剧名暗示我们,《开端》的目标是“返回开端”。如果执着于探究“循环”,基于日常的惯性思维解释这部作品的“合理性”,很难洞穿它作为艺术作品所传达的整体意涵。更有生产性的解读应该尝试分析这样的问题:剧中人物何以进入“循环”并追问“开端”?这要求观剧者也和局中人一样,具备对“开端”的好奇心。
一、《开端》追问何种“开端”?
《开端》的英文译名为Reset,即“重新设定”。这既指剧中不断重临的“循环”,也指我们观剧者对剧中爆炸事件的重新观看。重新观看必然带来重新理解。我们不得不多次返回灾难即将发生的现场,不断观察并追问灾难得以发生的理由;也不得不跟随情节的发展,不断思考剧中人各式各样行动的理由和后果。在这个意义上,观看《开端》必然会促进一种全新观剧体验的诞生。
如果我们回忆起经典戏剧理论的开端,亦即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便不难意识到“开端”之于戏剧行动的重要性:
悲剧是对一个完整的,即一体的,且具一定分量的行动的摹仿……有起始、中段、完结,方为一体。起始是其本身并不出于必然在他者之后,而在那之后则有他者出于自然存在或生成。(1)陈明珠:《〈诗术〉译笺与通绎》,华夏出版社2020 年版,第78 页。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戏剧的谋篇布局是对现实人类行动的摹仿。这就要求剧作者首先在知识层面明确什么叫作“现实人类行动”。这样一种知识构成了艺术创作的大前提。也就是说,剧作者必须了解一个具体的人如何思考、如何下判断、如何采取具体措施,等等。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旨在探究自然事物的本原,那么可以说《诗术》要求我们首先探究人类事务的“开端”。自然事物的运动需要“原因”,人类事务则需要“理由”。具体来说,在戏剧的谋篇布局层面,人物的自然本性就是“起始”,是一切得以在戏剧中发生、发展的“开端”。优秀的剧作者通过知识探究,观察并摹仿现实中的人的性情(ethos)和品德(virtue),可以找到这个开端,他所筹划的戏剧行动也能做到“出于自然”。《开端》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在呈现剧中人物的同时,也主动邀请观剧者参与上述这种对剧中人物之性情的观察和摹仿。
让我们再回忆一下《开端》的剧情:大学生李诗情登上45 路公交车前往市区,中间睡着了,醒来后遭遇了爆炸事件,然后数次再度回到醒来的那一时刻,每次醒来的时间都提前数分钟;李诗情将这样一个反日常的事件称为“循环”,并在每次“循环”发生后,都尝试采取行动来阻止爆炸的发生;游戏设计者肖鹤云被李诗情带入“循环”,两人通过观察车上乘客、下车了解线索、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等方式,在一次次失败的行动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获得更新的认识,并最终通过言辞说服和暴力强制相结合的方式让犯罪者放弃犯罪,从而拯救了所有人的生命。
仔细观察过这部作品的人,会首先回想起,与上述主线情节相伴随的,是公交车上所有乘客和公安机关调查人员之经历、思维方式和情感结构的逐步展现。这种叙事看似新颖,却“经典”无比。习惯于《茶馆》或者《十二怒汉》的观众,乃至习惯于柏拉图对话的观众,都能清楚地认识到这类叙事和一般意义上的侦探悬疑叙事的本质性差异。任何戏剧都需要一定的悬念,但侦探剧追问的单向度的“真相”,显然并不等同于经典群像剧所要探究的多维度的“开端”。为了让我们完成编剧和导演应该完成的熟悉全部人物性情与品德的任务,李诗情和肖鹤云的探究并没有止于确认真正的作案人并加以制止,而是不断明确整个事件中全部相关人员的行动动机,这也就等同于要在我们观剧者面前明确全车人作为人赖以生存或选择毁灭的根本理由,亦即他们作为人的基本品性。《开端》进而让我们隐隐然明白:不真正认识复杂人性的“开端”,情节中的危机乃至于现实中的危机也将永远“循环”。
二、出离常态
《开端》的叙事是不断循环的,带着观者不断返回关键场景。许多人将这种设定理解为一种“游戏”:游戏可以重新开始;一次任务失败并不等于游戏彻底结束,只要玩游戏的人对完成根本任务的欲求没有终止。如果代入一种哲学人类学的视角,我们也可以说以摹仿、行动和“发现”为核心要素的戏剧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游戏。它具有净化观看者性情的“寓教于乐”功能。这种“寓教于乐”有些时候体现为对剧中人(同时也潜在地对观者)的政治实践能力的操演或训练:即便是平凡的大学生和打工人,在经历了20 多次案件循环之后,也必然会变得深谋远虑、杀伐果决。在戏剧时间里,李诗情和肖鹤云同生共死多次,不但把握了案件的整体信息,还熟悉了彼此的性情。他们之间产生爱情,也就再自然不过。
对于许多观众来说,李诗情和肖鹤云的爱情十分理想,但又稳定且自然,因为其基础“同生共死”远远超出日常生活体验。与此相反,大部分日常生活中的现代爱情并不稳定,因为,现代爱情产生于双方习惯隐藏自身性情的现代社会。人把自身塑造为人格表象,投注到浅层社交赌场。在这种社交环境里,偶然的遭遇背后携带着不可量化的风险。保持距离也就意味着保持安全。但进一步说,浅层社交恰恰反讽性地构成现代风险社会中个体之安全稳定生活的前提。公交车正是这种现代反讽特性的隐喻。当李诗情和肖鹤云为了更为严肃的拯救性目标而不得不与车上人员展开沟通时,现代社会的浅层社交机制及其承诺的安全平稳生活也就遭遇了实质性的冲击。如果两位主角也是纯粹的个体主义者,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一走了之(在某几次“循环”中他们的确也做出了这样的尝试),那么“循环”情节就不会结束。言下之意,《开端》强行要求我们放弃这种对纯粹个体主义“常态”的惯性依赖,尝试去认识、理解积极回应风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开端》用极端危机即将来临的理由,终止了日常浅层社交的个体主义。这并不是一个具有新意的设定:大凡具有一定品质的戏剧均会叫停某种“习以为常”,其主要手法则是诉诸战争、暴力冲突、疾病乃至于各种误解巧合等非常态事件。但显然,这些所谓的“非常态”并不见得就是人类历史的“非常态”,而毋宁说,和平安宁的“常态”才不过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编织的一场“大戏”。陌生化的艺术作品恰恰旨在揭示“日常”舞台布景背后人类实然生存环境的简陋与无助。《开端》在这个意义上借助“普通的阿姨拎着的普通的红色塑料袋里的普通的高压锅”这一异常现实主义的意象,暴露了现代社会俯拾即是的风险性。李诗情和肖鹤云的调查视线最后才聚焦到这一“普通”的意象上,并非没有道理。他们的探究过程也是“日常”的不稳定性逐渐暴露无遗的过程。观剧者的恐惧情感也将在这种逐渐逼近真相的过程中被推到极致,以至于在直面突如其来的暴力而感到震惊的同时,开始转而进入思考状态,尝试追问能够真正化解暴力的有效手段。《开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主角的探究行动催生了观者情感的“净化”,换句话说,激发了观者某种思索的“开端”。唯有这种挣脱“日常”之安宁惯性的思索,才能够让我们有效地免于暴死的恐惧,积极能动地与主角一同面对实在的困境。
在时空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李诗情和肖鹤云试图化解实在困境的政治实践不可能依据常态程序,也就是说,在他们拯救公交车免于爆炸的行动方案中,不会有议程、草案、投票和公示。以“权变”为首要原则的效用主义者会第一时间指出,阻止惨案发生的最有效方法是以暴制暴。在多次尝试后,两人发现,这种效用主义并没有终止“循环”的继续发生,换句话说,这个“事”没完,真正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看到这个情节,大多数人都会想:如果是我在车上,我会怎么做?这种思考的一种不成熟的反应,就是责备剧中人物的选择不尽如人意。可人类本身就不尽如人意。人类的有限性与其说体现在知性和情感上的参差不齐,不如说体现在实践判断力上的参差不齐。如果车上没有李诗情,那么惨案的发生就是必然的,这是由其他人的个体性情所决定的——他们当中没有人能够真正承担起“拯救”的使命,因为他们或多或少缺乏某种品质。那么,换了我们观剧人在车上,我们也应当首先想到:“我”具有何种品质,能够做到切切实实的“拯救”?进而,我们也就会跟随《开端》,去思考何为政治实践能力。
三、如何面对“非常态”?
在面对李诗情或肖鹤云的突发行动时,剧中大多数人采取的措施都是第一时间制止。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必然首先考虑维护公序良俗之“常态”。蹦极教练具有身体所赋予的力量,直播网红具有语言或媒介所赋予的力量,买药的阿姨具有辈分或者说阅历所赋予的力量,他们都是社会各种力量的具象化,同时也在“常态”中感到自足。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被“常态”所抛出的另一群人,他们是被剥夺政治权利、失去家庭的瓜农,是被剥夺经济自主性、失去生活空间的中年民工,是具有身体上的先天缺陷、失去精神自由的二次元爱好者。这种对位关系恰恰彰显出“常态”的吊诡和有限。两位复仇者要挑战的不公正,就来自这种“常态”:无论是涉事机关的冷漠,还是网络舆论的刻薄,都造成了他们对公序良俗的不信任。也就是说,试图通过公序良俗化解公交车上的整体性矛盾,这本身是矛盾的。李诗情多次劝说曾经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的王兴德放弃复仇,却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此。“公交车”上的爆炸本身是对“常态”的质疑。要借助常态逻辑来化解危机,也就显得力不从心。
多次诉诸“常态”却无法解决问题,李诗情逐渐认识到,必须去探究是什么导致了“非常态”的来临,进而,她必须去思考真正的“开端”,即导致危机发生的人类性情因素。这让她想到和公安机关“合作”,因为唯有公共安全的看护者具有处理非常态事件的大量经验与素材,并且能迅速掌握车上众人的过往经历信息。执法从本质上意味着超出法所规定的常态——这样一个真理逐渐为李诗情和肖鹤云所认识到。和他们一起经历各种审讯环节的观剧者,也会渐渐认识到执法者的“非常态”特质:无论是有技巧的盘问,还是看待嫌疑人时的怀疑主义态度,抑或是紧要关头的奋不顾身,都体现出公共安全的看护者恰恰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公共的“常态”。“公安”必须在“常态”中融入常人,又必须在非常态下超出常人。换句话说,“常态”的维持总是需要一定的非常态品质作为根据。李诗情和肖鹤云作为常人,通过接触公安机关,掌握的不仅仅是案件细节,还包括一种看护公共安全时必须具备的态度与视野。张成和江枫作为可供摹仿的榜样,让李诗情学习到何为“侦查”,更认识到“人民警察”应当具有的品性和勇气。通过摹仿警察,李诗情和肖鹤云让车上大多数人相信了其行动的正当性。通过摹仿警察,他们也获得了常人不具备的格局和勇气。
当然,公安干警不是《开端》的主角,而只是让主角和我们得以返回真正“开端”的“教学工具人”。任何“警察故事”都会呈现执法者在规则、实践和品质层面的例外特质,但这不足以说明他们能够取代“常态”,替换公序良俗本身。要让作为公共秩序之象征的“公交车”从“非常态”返回“常态”,更多时候必须依赖车上常人自身的努力和成长。因此,“循环”的叙事必须出现:不断延续并重复的尝试,破除了短暂时间带来的有限性焦虑,让一贯沉浸在被保护者惯性思维中的常人,也能充分完善自身的思路和方案,从而开展富有想象力的实践。
我们生活在“常态”当中,也知道公共安全的看护者会随时通过“非常态”的调整来重构常态。戏剧如果单纯呈现这些知识,会显得太过平庸;让一些先天具备超人般的决心与智识的主角替代看护者来完成一次性的拯救任务,也会落入另一种好莱坞式的俗套。《开端》则告诉我们:真正的拯救应当基于我们常人自身;而常人作为主角,必须不断成长。李诗情和肖鹤云的成长伴随着对事不关己、以暴制暴、以少换多、劝导引诱等选项的不断试错,这些失败的例证让作为观剧者的我们也逐渐认识到:也许身边常见的诸多日常事件的内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甚至深邃;对这些事件的回应也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开端》把这种深度揭示到极致:李诗情和肖鹤云的常人性情逐步获得冥冥中的某种引导和教化,观剧者如我们也随之展开了慎重且全面的思考,通过体验“常态”和“非常态”之间的逻辑转换过程,从而学会在现实中更为成熟地面对大大小小的风险与危机。
四、“知人”的难题
跟随主角的节奏,探究罪案的“开端”,观者逐步明确了什么可以作为人类政治实践的真正“开端”。如果我们聚焦于“谁是犯人”的问题,我们也就不免会思考犯罪的动机。但传统的侦探小说所揭示的动机大多停留在“原因”层面。钱财、情色、复仇……都是原因,但原因背后还有“理由”,即犯罪者自己说服自己采取犯罪实践的最重要的因素。《开端》要求我们尝试理解剧中人物各式各样的“理由”,这也就意味着,真正政治实践的“开端”或许应该是对各式各样人类性情、品德和思维的认识。
认识并不意味着“认同”。我们不会认同凶手的所作所为,但我们可以认识他,因为他或她是人类。唯有认识不仅作为种类还具有具体属性的每一个人的性情,才能真正做到与众人“打成一片”,并切实处理他们当中发生的矛盾和斗争。在审慎且周全的政治实践当中,不容许半点关于“人”的极端乐观或悲观的抽象。具体的、参差不齐的人的品性就是具体的知识,尽可能多地获取这种知识,是针对人的实践得以正确施行的准绳。
李诗情与肖鹤云经历了20 余次“循环”的试错和反省,才掌握了公交车上寥寥数人的品性,可见认识具体的“人”格外艰难。具体的人出于各种原因(比如为了安全感),或许会拒绝被了解。时间、空间、语境和信息的局限,也会让我们不免把片断化、截面化的“人格”(person)视为真实生存着的人。更进一步说,大多数人自己都不够了解自己——除非他们经历过一些全面且生死攸关的反省。李诗情和肖鹤云就在“循环”中经历了这样的反省。他们的自我认识伴随着对他人的认识,这是难能可贵的体验。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体验。艺术作品在这个意义上给予我们一种“理想状态”,让他们的自我认识得以上升到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但敏感的观剧者又会发现,剧中主角对公交车上人物的认识其实也并不全面。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和主角掌握的信息并不对称。因为公交车上大部分人的故事其实是通过补充性的单独叙事展开的,而李诗情和肖鹤云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影像叙事。而且,艺术作品直接呈现给读者、观众的人物形象,往往格外鲜活立体。这些人物形象是被精心制作的“典型”。我们可以在很短的阅读和观看时间内通过全景式视角把握一个戏剧人物的品性、智识与社会关系,但这种视角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剧情中的肖鹤云和李诗情不具备这种视角,只能普普通通地通过观察、对话和调查来认识他人。如果不通过“循环”,他们根本不可能对那么多身边的人产生认知的兴趣,更加不可能把他们当成“典型”来阅读理解。但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艺术鉴赏,需要试着确切把握每一个人物的戏剧功能和性情特征。
这其实说明,在面对一些现实事件时,作为观察者的我们,也不免会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进行观察和评价。一种是类似于读报或者读微博的视角:我们基于既有的非常有限的文本,尝试对已有的信息进行意义的完形填空,并由此协助媒介生产出更多的意见信息。这种活动非常类似于文学或戏剧批评,我们明白自己能够把握到的信息有限,但想象力会施以援手,让我们不断营造出一种圆形的、合乎自然的人物形象,并试着填补缺少叙述的事件的整体序列。这种视角显然不是面临“非常态”时负责任的人会采取的视角。危机之所以为危机,在于它不是可以任由我们冷静分析或填补意义的“文本”,而是时刻欲求解决途径的“现实”。这也就要求我们之中时或涌现出第二种身临其境的特殊视角。
《开端》在艺术上的诡诈之处就在于对这两种视角的刻意混淆。尽管面临紧迫万分的爆炸事件,但“循环”的引入让我们可以自由切换这样两种视角:当主角展开实质性的拯救行动时,我们的思绪切换到紧急应变的实践维度,和主角同情共感,在看待人和物时不再从容不迫,而是着眼于即刻回应突如其来的难题;当主角带领我们进入调查和推理活动时,我们又换上了阅读文本并进行分析的人类学眼镜,跟随全知的摄像头窥探每一个嫌疑人的生活。
仅仅具有全知式的、文本分析式的观众视角,不足以让我们融入“危机”的非常状况,进而无法理解政治实践的艰难;而若是只呈现十分有限的主角视野,我们就无法确信整个事件真正得到了解决——或者说,我们若是仅仅把自己视为身临其境的剧中实践者,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知道”自己对其他人的判断是正确无疑的。优秀的戏剧文学应当同时具有这样两种视角的设定。在这个意义上,《开端》不仅呈现了人类拯救公共生活的具体行动,还呈现了作为这些行动之“缘由”的人类性情。这个看似简单的安排有助于我们做好思想准备,以理解真正的“政治”。
五、《开端》的双重视角及其品位
分析戏剧文本的观看者视角和代入剧中人物的行动者视角,在《开端》中时刻切换。我们观剧者进而也会承担两个义务,即跟随主角不断探究解决方案的义务,以及认识剧中人物性情,从而理解整个剧情之真正“开端”的义务。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如果不转换视角,把“知人”贯彻到极致,并同时不断通过实践来试错,我们就无法找到让公共安全危机得以产生的“开端”,进而无法化解危机。但现实生活不是艺术作品,我们无法通过一种整全的读报者视角鸟瞰、评判一切人的品性,遑论洞察其中的大是大非。无论如何,《开端》也只是想说明,尽可能多追问一层“理由”而非单纯的“原因”,尽可能多一些知识性的彼此了解,人类的共同生活中至少可以规避一些麻烦。
这其实是一种温和的理性主义,其中蕴含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希望。如果把即将爆炸的“公交车”进一步类比为我们的社会和国家,这种理性主义的情感特质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不能牺牲作为具体个人的每一个公民,这也就要求我们不仅在激情的层面喊出“一个都不能少”的口号,还需要观察、反省人类情性的整全特质,并通过对现实实践能力的鲜活展示与效仿,让人明白治理和防范的艰难与重要性。《开端》始于一种拯救公共整全生活的信念,但它的真正“开端”则必然是对这一拯救信念在智识层面的可行性的确认。这一确认并非发生在剧中,而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观剧者的日常生活体验当中——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正在不断实现这种智识层面的可行性的确认,尽管它尚未完成。伴随着戏剧行动的展开,观剧者除了获得政治实践的演示性启蒙,也将逐渐回忆起追问人类本性的古老智慧遗产。对人类整全本性的回忆和探究,是在现实世界中确保共同生活实践的开端。
对于热衷于乐观想象“一切可能”的当代观众来说,《开端》其实“平平无奇”。但这种“平平无奇”却构成了它独特的品位——一种稳固且丰腴的世俗基调。比起沉浸于精巧但浮夸的叙事体验,这种世俗基调让我们明白现实生活更为重要,并且使我们愿意通过不断返回“开端”,去让世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