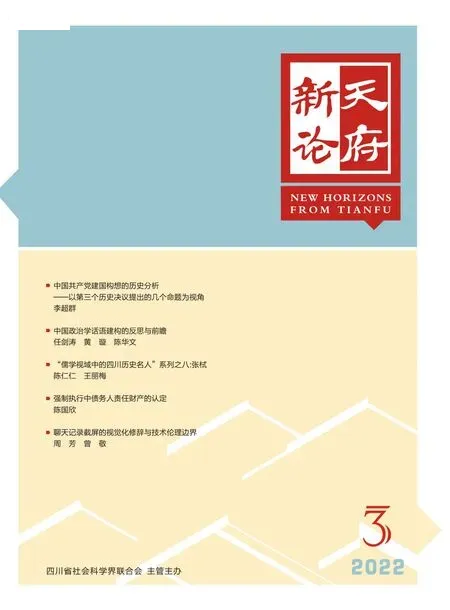“文化是平常的”
——雷蒙·威廉斯关于文化的论断及价值
2022-02-03郑莉
郑 莉
“文化是平常的”这一论断出自雷蒙·威廉斯的文章《文化是平常的》(1958),后被收入《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一书。威廉斯谈道:“无论是在一个社会里,还是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文化都是平常的。”(1)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页。这意味着文化并不是高高在上仅供瞻仰的神圣之物,它包含了普通民众整体的生活方式,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文化属于大众,普通个体也能参与文化的创造和意义的共享。威廉斯关于文化的种种认识,学界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且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透彻的探讨,但多数是在讨论威廉斯定义文化时有所提及,或是在论述威廉斯文化观时有相关阐释,并未就这一观点进行专门系统的讨论。 因此,这一问题仍然具有探讨空间。笔者认为,重温“文化是平常的”这一论断,不仅可以把握威廉斯文化观念的基调,还可以了解早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路径。这一宣言开启和奠定了英国文化主义研究的新视野和方法,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建设也具有参考价值。
一、“文化”何以成为英国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二战后的英国社会迎来了巨大的变迁,从福利国家的建立、成人教育运动的发展、现代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到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的兴起,不仅促进了人们新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形成,还带来了英国社会整体的变迁。在此语境下,理论者们开始思考社会转型带来的相关问题,“文化”成了新的介入方式。
首先,新的社会语境需要新的思考方式。工业革命推动了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发展: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发展;民主、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分化和变革加剧,如此等等。威廉斯将18世纪晚期以来英国的社会变迁喻为一次“漫长的革命”。这场革命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政治层面的民主革命、经济领域的工业革命和文化的革命。这三个方面是互相关联、不能分离的,共同构成人类生存经验的重要部分。要理解和认识这一伟大的过程,需要“新的思考方式和感受方式,以及对于各种关系的崭新构想”(2)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导言”第5页。。在威廉斯看来,以文化作为切入点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一整体进程,“文化”一词记录了人类对整体社会变迁的反应,它“不只是针对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工业’的反应……另外还关涉各种新型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事实上它同时也是对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对‘民主’所做出的反应……文化又是对社会‘阶级’新问题的一种复杂而激烈的反应”(3)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2页,第22页,第20页,第 19-20页。,其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也是思想与观念更新发展的过程。
其次,英国新左派的出场以及新的政治文化空间的开创。20世纪50年代,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危机等事件催生了英国的新左派运动。英国左翼力量逐渐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两种当前占据政治体系主导地位的阵营都有各自的弊端,于是他们开始反省并思考新的社会出路。他们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英国的社会现实状况寻求新的可替代方案,主张通过非暴力和革命的斗争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实现社会民主与公正。在他们看来,文化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向度,它显著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整体变迁,并且文化对于重述社会主义语言相当必要。(4)Stuart Hall,“The ‘First’ New Left:Life and Times,”in Robin Archer et al.,eds.,Out of Apathy:Voices of the New Left 30 Years On,London: Verso,1989,pp.25-26.由此,他们以文化为切入点,通过文化批判介入现实社会,将文化及相关问题与政治实践相结合,凸显文化的政治内涵,开启了文化政治新的路径。作为新左派核心成员之一的威廉斯,其理论思考也延续了新左派的立场与追求,文化成为理论关切和介入社会的焦点。
最后,英国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发展。 二战后,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福利国家”的举措,社会进入所谓的“丰裕”神话之中。物质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其他领域的变革。新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形成,也为新兴的文化形式和风格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借助现代媒介和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文化产业兴起,一方面促进了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文化商品化的趋势,文化逐渐被裹挟到资本的逻辑之中。传统的文化观念已经不能更好地阐释新兴的文化现象,文化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需要被重新审视,文化“正在朝着一种个体的、显然更为私密的经验领域回归”(5)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2页,第22页,第20页,第 19-20页。,文化的观念地图需要被重新绘制。
二、“文化是平常的”何以体现
“文化是平常的”是威廉斯文化观念的必然逻辑和概括。威廉斯在多篇论著中,从不同方面审视、评判和重构了关于“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文化概念的发展见证了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思维方式的变迁,“记录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这些变革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6)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2页,第22页,第20页,第 19-20页。。他首先对19世纪以降的英国文化观念史进行了总体性梳理,并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文化的内涵:第一是“心灵普遍状态或习惯”;第二是“整个社会智性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是“艺术的整体状况”;第四是“包括物质、智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整体生活方式”。(7)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2页,第22页,第20页,第 19-20页。进而,威廉斯又从两个方面总结和拓展了“文化”的含义:“表示一种完全的生活方式——这是普通含义;表示艺术和学问——这是发现和创新努力的特殊过程。”(8)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页,第4页,第4页。后来,威廉斯再次整合了他关于文化的认识,将文化概念重新梳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理想的”文化概念, “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人类根据某些绝对的或普遍的价值而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9)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第50页,第50-51页,第51页。,更多涉及文化的价值标准和理想目标,强调文化对人的本质实现的作用;第二个方面是“文献的”文化概念, “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就是思想性作品和想象性作品的实体,其中,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以各种方式被详细地记载下来”(10)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第50页,第50-51页,第51页。,更多与知性和想象作品相关;第三个方面是“社会的”文化, “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现了不仅包括在艺术和学识中而且也包含在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11)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第50页,第50-51页,第51页。,这一方面的定义包括了前两个方面的内容,还将生产组织、家庭结构、社会制度、群体成员等概括进来,涵盖了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根据第三个方面,“文化分析就是要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即一种特定的文化——中或隐或显的意义和价值”(12)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第50页,第50-51页,第51页。。这三个方面关于文化的定义,可以视为对“文化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全面铺展和再阐释。
威廉斯通过对“文化”概念变迁轨迹的梳理,将文化从传统的概念中区分出来,文化从关涉人类心灵和智识的抽象概念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进入到社会物质生活和实践之中。“‘文化’成为一个关于‘内在’过程的名词,特指那些‘精神生活’或‘艺术’方面的成就;‘文化’又成为一个关于一般过程的名词,特指那些‘整体的生活方式’方面的形貌情状。”(13)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事实上,不论是从四个方面、两个方面还是三个方面探讨文化,威廉斯的基本立场都是一致的,即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文化并不是某一特定阶层的专属,而是涉及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是所有人能够参与的实践活动。这就意味着文化高高在上的特殊地位不复存在,它成为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物质实践活动,蕴藏和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是再平常不过之事。也因此,威廉斯顺理成章提出了这一著名论断:“文化是平常的:这是个重要事实。”(14)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页,第4页,第4页。
威廉斯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阐释他关于文化的这一论断。在威廉斯看来,文化是平常的,它无时无刻存在着,存在于最普通的经验之中,在每一次变化的经历中,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各种关系的变化中,在不同的思想和语言的形成中,在每个人的行为举止和说话习惯中,在各种实践的意义和价值观念中,在人类积极健康的本性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中……“文化是平常的: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开始……文化是平常的:这是个重要事实。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形态、自身的目的及自身的意义。这些都要通过人类社会的制度、艺术和学问来进行表达。一个社会的形成过程就是寻找共同意义与方向的过程,其成长过程就是在经验、接触和发现的压力下,通过积极的辩论和修正,在自己的土地上书写自己的历史。”(15)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页,第4页,第4页。威廉斯层层递进,从多方面阐释这一观点。其一,“文化是平常的”打破了传统文化观念的藩篱,扩大了文化的论域。文化源于平常的生活经验和实践,它存在于言行举止、人际关系、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各种具体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存在于真实的体验和情感之中,从文化的形式、内容、表达方式和意义来讲,都跟平常的日常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其二,“文化是平常的”意味着文化并非某一特殊阶层的专属之物,而是平常人都能参与的实践。在社会共同体中,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都拥有参与文化创造和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其三,“文化是平常的”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价值被贬低,而是表明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蕴藏在人类社会活动的日常行为之中。文化兼具共同意义和个体的独特意义,既是整个民族和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个体经验的呈现。“文化有两个方面:已知的意义和方向,这是要引导其成员学习的;新的观察和意义,这是要提出并加以检验的。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过程,而我们则是通过它们来认识文化的本质:文化永远同时具有传统性和创新性;它永远同时具有最普通的共同意义与最优秀的个体意义……无论是在一个社会里,还是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文化都是平常的。”(16)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页,第8页。
“文化是平常的”这一论点从文化主体、文化形式与内容、文化价值等多方面得以阐释。威廉斯从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推导出“文化是平常的”,文化是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因此文化并不存在等级之分,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是平常之人的平常之事,文化是普通的。这一论断不仅显示了与精英主义文化观截然不同的文化立场,展现了平民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同时也开启了文化大众化的进程。
三、“文化是平常的”的价值
威廉斯的“文化是平常的”的论断肯定日常生活经验和物质生活方式的作用,强调文化的现实力量,文化不再是普通人瞻仰的神圣之物,也不仅是“基础”的被动附着物,而是关涉活生生的现实经验和社会物质生活实践。这一认识不仅突破了传统“文化”概念的边界,实现了对文化精英保守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简单经济决定论的超越,同时也开启了文化研究新的格局与范式。
其一,“文化是平常的”这一论断扩展了文化的边界和内涵,实现了对文化精英保守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简单经济论的超越。文化精英保守主义者认为,文化源于对智性和完美的追求,是“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17)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1页,第13页,第14页,第13页,第31页。,“最好的人类经验”(18)F.R.Leavis,“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1930),” in F.R.Leavis,For Continuity (1933),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1968,p.15.;其功能在于培养“关于美观、优雅和得体的意识”(19)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1页,第13页,第14页,第13页,第31页。并“树立完美之精神标准”(20)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1页,第13页,第14页,第13页,第31页。;文化的本质是“获得‘最好之物’的能力;‘最好之物’本身;将‘最好之物’运用于精神与灵魂;对‘最好之物’的追求”(21)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3页。。在他们看来,文化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属;大众只是“群氓”、 “乌合之众”、庸俗之人等,“文化不以粗鄙的人之品位为法则”(22)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1页,第13页,第14页,第13页,第31页。,并且“文化并不企图去教育包括社会底层阶级在内的大众,也不指望利用现成的看法和标语口号将大众争取到自己的这个那个宗派组织中去”(23)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1页,第13页,第14页,第13页,第31页。。机械唯物主义简单经济论在基础-上层建筑这一基本框架内分析文化,认为:经济作为基础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领域,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且完全由基础决定。这一认识过度强调基础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作为“基础”的复杂性、差异性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历史性和多样性以及物质生产属性,忽略了现实生活和存在的具体性,割裂了社会结构和进程的整体性及关联性,是一种僵化的、静态的决定论。威廉斯关于文化的学说正是基于对文化精英保守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反拨。威廉斯认为,文化既包含人类经验和智慧最为精妙的部分和创造性的过程,还包含人类整体的一般生活方式;文化存在于整体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心灵和思想中,关乎普通人深刻的个体意义和整体的共同意义的构建;文化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实践,跟人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人人都能参与其中,因此,文化不是少数人的文化,而是大众共建、共享的文化。此外,文化也不只是“基础”的机械反映,它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尽管“对一种文化的最终解释必须考虑到与之相关的基本生产体制”(24)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页,第8页。,但威廉斯认为文化不能仅仅被视为经济基础的附着物,二者都是构成整体社会进程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对二者的关系应该放置在总体社会领域和关系中进行考察,“需要加以研究的并不是‘基础’与‘上层建筑’,而是具体的、不可分割的现实过程”(25)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并且,文化并不仅仅是纯粹的精神产品,也具有物质属性,其本身就是具体的物质生产方式和过程的实践结构。“文化实践是物质生产形式”(26)Raymond Williams,Politics and Literature,London:Verso,1981,p.353.,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建构性力量”(27)舒开智:《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240页。。文化是物质生产实践就意味着文化获得了现实力量,文化关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参与其中的实践。如此,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被打破,文化成为普通人的平常之事,人人都能参与其中并共享文化成果。这打破了文化二元对立的格局,将文化从精英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简单经济决定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生活世界纳入文化的范畴,关注真实的、具体感性的文化实践,关注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关联,探究文化丰富的内涵和空间,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调。
其二,“文化是平常的”这一论断表明文化并不是某一特殊阶层的专属,意味着“无论是从一般意义上说,还是从艺术和信仰这个特定意义上说,创造意义和价值观的都不是某个特殊的阶级或群体”(28)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40页,第13页,第13页,第13页,第41页,第43页。,而是应该面向所有人。这承认普通民众作为文化主体的地位,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在以往的文化观念中,普通人被排斥在文化领域之外,“‘大众’变成了代替‘群氓’的新词:那些其他人、无闻之辈、平头百姓、难以接近的群氓”(29)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40页,第13页,第13页,第13页,第41页,第43页。。这样的认识在威廉斯看来是荒谬的,与民主文化的精神内核背道而驰。他认为, “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众,只有把人看成大众的方法”(30)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40页,第13页,第13页,第13页,第41页,第43页。,大众并不是无知、粗鄙、不上档次、低俗的代名词,“一般普通人实际上并不像通常对大众的描述:品位和习惯比较低俗、不上档次”(31)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40页,第13页,第13页,第13页,第41页,第43页。。相反,他们代表了社会中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立场。文化源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体验,这种经验是在具体的现实生活和日常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积淀而来的,反映了普通大众的生存状况和意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价值关切,是作为主体的人同世界发生关联的过程,是普通民众共同参与的实践。换言之,普通民众是文化活动的主体,有权利参与和创造文化并且共享文化成果。文化是平常的意味着文化的主体也是平常的,文化并不是某个特定阶层的专属,而是面向所有民众的,“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表述意义和价值观的活动中来,参与到其后对这样和那样的意义、这样和那样的价值观的决定之中来”(32)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40页,第13页,第13页,第13页,第41页,第43页。。无论他们处于什么社会阶层,是怎样的身份,从事何种职业,每位社会成员都是平等的文化实践者。总之,威廉斯将理论视线投射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和经历,肯定他们作为主体的现实存在性,重新确立他们的文化主体身份,挖掘处于下层阶级的普通民众在文化实践中的重要价值,这赋予威廉斯的文化观念一种超越性品格,推动了平民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建构。
其三,“文化是平常的”这一价值判断为威廉斯共同文化理想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前提,铺就了参与式文化民主的底色,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平民文化价值观的基础。“文化是平常的”指向一种面向全体成员的共同文化的设想,蕴含着“一种共同享有的文化,或者一种共同创建的文化”(33)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98页。。它意味着所有人都是文化实践的重要参与者,每个人都享有平等参与和自由选择的权利,全体成员在集体性的文化实践中“自由的、贡献式的、创造意义和价值观的共同参与过程”(34)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40页,第13页,第13页,第13页,第41页,第43页。。这种共同的文化旨归是参与式文化民主的构建。参与式文化民主包含和调动了社会最为广泛的民众,以大多数人的文化诉求为出发点,以平等和自由为基础,以民主的教育实践、民主的传播机制等为途径,以促成文化民主和人的解放为目标,是威廉斯在面对新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现象时所做的探讨与反思。作为早期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的文化观念也反映了早期伯明翰学派文化观念的立场和取向,延续和拓展了英国文化研究文化主义范式的方法和路径。从霍加特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社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并挖掘出文化平常性和日常化的内涵,到威廉斯关于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的主张,再到汤普森对平民文化传统的肯定并认为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的观念,等等。早期伯明翰学派理论者们将理论视野转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情感,肯定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力量,论证了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平民文化的自主性和合理性,呈现了一种平民主义立场的价值关切。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者们希望通过对文化的再阐释,打破原有的文化枷锁,发掘文化的民主力量和解放潜能,呈现民主、平等、进步的价值观念,引导文化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就超越了简单的对文化的认识,走向了更为宏大的理论视野和人文关怀。
四、“文化是平常的”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与建设的启示
“文化是平常的”这一论断宣告了与英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决裂,奠定了威廉斯文化观念的基调,并贯穿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独特的路径和新的空间,传递和契合了民主文化的内涵,推动了文化民主建设的进程,兼具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具体的现实意义。以威廉斯等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不仅因为二者在理论和逻辑层面存在一定的共通性,二者都视文化为社会整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学术话语的文化研究属于西方舶来品,融合了多种知识形态和话语思潮,从威廉斯关于文化的论断再到伯明翰学派文化观念的形塑,可以从另一个维度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因此,从“文化是平常的”这一论断出发,结合伯明翰学派关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观照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是有价值且必要的。
其一,在文化主体层面,捍卫普通民众的文化权利,为普通人的文化正名。伯明翰学派打破了文化专属少数人的观念,主张文化是平常人的平常之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民主文化价值观。他们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具有平等参与文化创造、共享文化资源与成果的权利,文化应该反映大众而非少数特权阶层的立场和价值诉求;普通民众是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群体,是文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文化实践中能够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性。注重民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为人民”的立场不谋而合,并对当代文艺创作和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实践中,尤其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3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页。,“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导向是始终如一的。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再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36)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页。的立场。在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事业中,应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肯定人民群众在文化实践中的创造性,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文化实践中来。人民群众有能力创造属于自身的文化或对现有文化资源进行有选择性和创造性地使用和再生产,从而建构符合自身体验的意义和价值系统,那种“把民众视为完全被动的外围力量,是一种根本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观点”(37)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转引自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47页。。
其次,在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中,文艺创作的内容应反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经验,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与情感,写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之事。“人民群众五彩缤纷的生活和实践蕴含了无限生动的丰富的宝藏,为文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是文艺作品的来源”,“就文化的始源性含义而言,无论是作为观念形态的价值理念、道德情操,还是作为艺术形式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都源自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人民大众不仅创造着文化,也不断传承发展着文化,并为文化所规范”(38)范玉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人民性研究》,《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最后,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和评判主体。人民群众既是文艺作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并且文艺作品中还渗透了人民的审美品位和追求。因此,人民有资格对文艺作品的价值进行评判,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是评判作品价值的原则和标准,是否经受得住人民群众的检验是文艺作品艺术价值的体现。简言之,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实践中,要重视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权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将文化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紧密联系,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一切源于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其二,文化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重要场域。建基于“文化是平常的”,伯明翰学派重构了关于文化的概念。他们拓展了文化的内涵与边界,将文化从传统的定义中解放出来,将文化放置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下、从整体的社会进程中加以探讨,文化不再拘泥于单纯的文本层面或关于“内在”精神层面的过程,也不再仅仅是“基础”的简单反映,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物质生产实践,与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相联系,是人类存在的本质维度。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是社会构成的本质性维度之一,同经济、政治、社会共同构成现代社会整体的发展进程。联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被提升到新的高度,“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41页,第41页。。文化建设被纳入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整体格局之中,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同时,文化建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共同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共同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自信”,坚定文化自信也成为“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40)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文化既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精神命脉,也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纽带,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战略任务和精神动力,文化的作用和地位不可替代。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关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有了新的要求:不仅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拓展和深化,还应该从实践中获取动力;既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体现时代精神;既坚持本国特色,同时也要具备全球视野,面向世界,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等等。简言之,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应该立足中国当下的现实,“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4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41页,第41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其三,文化研究的语境性、情境性与本土化。威廉斯结合英国文化观念史、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兴起的具体现实以及社会整体形态等多方面维度,重构了文化观念,开启了伯明翰学派新的理论范式和话语形态。可见,文化研究中注重语境性、情境性,推进本土化进程是相当有必要的。对中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大众文化逐渐兴起和繁荣,文化研究也逐步在中国显现和发展。其中,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是推动中国文化研究兴起的重要力量,中国文化研究的起步就是引入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知识和话语形态,作为观照和分析各种文化文本和现象的理论视域。伴随着文化研究在中国的逐渐拓展和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他们结合中国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实,展开了不同层面的学术思考。尽管这一过程总伴随着激烈的交锋和争论,但也正是在论争中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开启了中国文化研究逐渐“从舶来到本土化的历史转型”(42)陆扬:《伯明翰中心的遗产》,《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4期。,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而言,应该摈弃一味照搬和挪用西方模式的观念,立足于本土的社会文化现实,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出发,结合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的新特质与使命,建构中国文化研究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一方面,面对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现实,既看到大众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警惕不加批判的极端民粹主义倾向;既不能一味鼓吹大众文化对消解权威和秩序、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意义,也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完全抗拒和否定,而应以客观的立场加以理性审视。另一方面,既要有历史视野,也要有时代眼光;既要有本土意识,也要有全球观念。中国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应该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的经验和当代社会文化现实,同时也应该兼顾中国新时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与世界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简言之,新时代语境下的中国本土化文化研究同样应该坚持语境性与情境性。目前,中国的文化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定位还比较片面,特别是在消费主义盛行、文化商品化趋势加剧的语境下,对大众文化复杂性、矛盾性的认识还有所欠缺;又如,文化研究批判精神有所削弱,更多侧重于理论层面的阐释和演绎,文化的现实介入性有待加强;等等。这些都是文化研究实践中值得思考的问题。只有立足于新时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与情势,才能继续推进和保持本土化文化研究的创造性与生命力。
综上,从“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到“文化是平常的”,威廉斯的文化观念在不断深化拓展。“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侧重于强调文化的共同意义的创造和分享,“文化是平常的”在整体的基础上包含了对个体经验和意义的重视。整体的共同意义和个体的意义是不可分割的,二者联结在一起构成了文化的本质:既具有传统性,也有创新性;既关乎共同的目标和最普通的共同意义,也关涉个体经验和意义;既关乎普遍性,也彰显了特殊性;既是艺术和学问发现和创新的特殊过程,也是完全的整体的生活方式(43)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页。。文化的含义并不单一,而是包含多重话语空间,但究其本质而言,文化是平常的。威廉斯将文化视为平常的,打破了传统文化的等级之分,赋予文化更为广阔和民主的内涵,为大众文化正名,促进了文化民主化的进程,不仅改变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格局,开创了新的理论范式和思想空间,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希望的资源”,同时也为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带来一定的思考和启示,对中国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