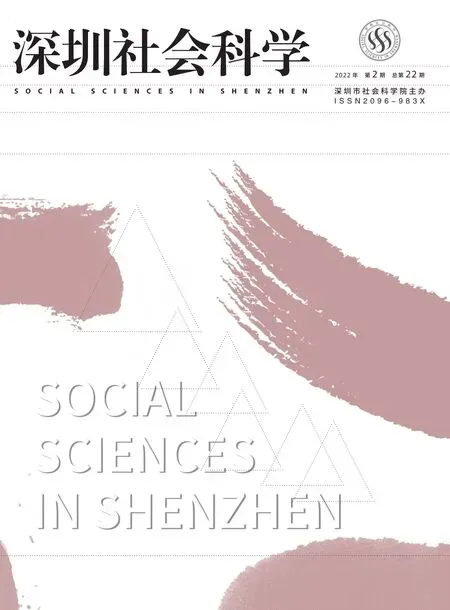阵痛与觉醒:论战时西南边疆交通建设和变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建*
2022-02-02韩继伟
韩继伟
(百色学院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百色 533099)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因抗战所需而进行的西南边疆交通建设以及相关之路线变迁,不仅凸显了国民政府于西南边疆社会凝聚力的增强,而且也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西南边疆与国家内地的紧密联系度,进一步增强了西南边民之间以及西南边民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从道路筑建和变迁实施过程中进行梳理①这常见到的诸如龚学遂的《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李占才、张劲的《超载——抗战与交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廖永东的《二战时期中国战场国际战略通道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美]约翰D.普雷廷的《驼峰航线》(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徐万民的《战争生命线——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交通》(人民交通出版社2015年版)以及笔者拙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国际援华运输线路变迁述评》(《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等。;有的则是从大后方交通建设与西部经济开发视角进行探究①持有该观点的可参见谭刚:《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建设与西部经济开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有的则完全是战时西南交通运输的资料汇编②有的研究是资料汇编,诸如交通部西南公路管理处编:《三年来之西南公路(1938-1940)》,交通部西南公路管理处印,1945年版。;而从战时西南边疆交通筑建及变迁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互动视角实施研究还不多见。本文将从战时西南边疆建设和变迁入手,运用“路学”相关理论,对战时西南边疆交通建设及变迁对西南边地各民族在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等方面进行梳理和探究,以求形成“路学”视角下的社会整合和民族认同研究,以求证于方家,并期待引起更进一步的探究和讨论。
一、战时西南边疆交通建设与变迁概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坚持旷日持久的对日作战,国民政府迁都西南重镇重庆,并发表迁都宣言。这样,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便成了中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而当时西南大后方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滞后的交通状况,显然无法适应和支撑战时军需和补给,致使当时国民政府抗战所需的各种战略物资90%以上均需自国外进口。[1]面对日军的严密封锁和后方的严峻形势,为了将国际援华抗战物资尽快运至中国,国民政府“首在求取国际线路”,[2](P9)其宗旨就是充分利用国际交通输入海外援华战略物资,并同时向海外输出土特矿产。而当时日军凭借其训练有素的陆军和占据优势的海、空,对华实施全面性、战略性的交通封锁措施,严密封锁中国出海口,阻断中国国际交通运输线路。首先,日军以凌厉攻势对中国海面迅速实施封锁,并很快占领中国当时主要出海口——天津和上海,迫使中国外贸口岸不得不南移华南英国殖民地— 香港,利用粤汉—广九铁路加以运输;同时中国还开通借道越南的印支通道,以及陆续筑建借道缅甸的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但此时对抗战发挥独特政治和军事价值的还属粤汉铁路。其次,日军又设法阻断通向沿海口岸的中国内陆铁路。1938年10月,日军发动武汉、广州战役,粤汉铁路被阻断,中国国际交通运输不得不移至以越南海防为进出口岸的印支通道上来,该通道既包括通往滇省的滇越铁路,又包括通往桂省的桂越公路,还包括紧急筑建的河岳公路、滇越公路等。这样,以南宁为中继站的公路交通和以昆明为中继站的铁路交通便成为当时中国极为重要的国际交通线。1939年10月,为确保桂越国际交通畅通,国民政府还组织了桂南会战。但鉴于种种原因,会战最终失利,桂越国际公路运输被日军切断。1940年6月,伴随着法国在欧洲战场的失败,滇越铁路亦被日军阻断。在粤汉铁路以及印支通道陆续被日军切断后,“滇缅公路便日益成为中国抗战唯一的输血管。”[3](P3)1942年春,为保卫滇缅公路畅通,中国远征军出征缅方初次作战失利,随即日军占领缅甸,切断滇缅公路,这时的中国立即丧失了90%的军需品和工业品供应,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虽然盟军及时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驼峰”航线,但由于受到恶劣气候以及日机不时袭扰等因素的影响,航线运输量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战场的军需民用。1943年初,史迪威将军多次筹划、修改并经盟军首脑会议批准的“安纳吉姆”行动方案顺利于印度利多启动实施,与1944年初中国远征军在滇西的胜利反攻遥相呼应,顺利打通了中印公路,并同时铺设了自印度加尔各答,到达利多后沿中印公路直至云南昆明的石油管道,彻底解决了中国战场燃料短缺的问题,遏制了日军于1944年春发动“一号攻势”并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战略企图,大量的海外援华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中印公路运到中国。当时一些军方人士认为“中国战场的反攻战,开始于中印公路之战,而且是胜利的开始。”[4](P1)在这些国际交通线开辟和筑建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动员了数以万计的西南边疆各族人民进行道路筑建和机场建设,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政治凝聚力延伸至偏远的边疆民族聚集地,同时亦在此过程中使广大的西南边民初次感受到强烈的国家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从战时西南边疆交通建设和变迁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
民族意识并非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后天非常的情势下与特定的背景下逐步萌发和铸造的。[5]当一个民族猛然遭受外来势力的胁迫和欺压时,其生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时,其民族意识最容易被催生和爆发。[6](P93-94)抗战时期所实施的体现国家意志并服务于战时政治、军事需求的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是民族整合和国家建构的重要支撑,不仅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层面和最终取得抗战胜利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从道路筑建过程中所体现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看,则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家认同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战时西南交通建设及变迁促进了西南边疆与内地关联度的提升
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之后,英、法列强欲将中国纳入国际经贸一体化进程,企图利用他们在缅甸和印度支那所实施的殖民地交通战略对中国西南边疆实施经济渗透和军事蚕食,但在西南边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法国多次筹划准备筑建的龙州铁路最后无疾而终,出资修建的滇越铁路仅仅勉强通车;而英国力主的滇缅铁路一线则胎死腹中。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从贵州军阀王家烈入手,对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滇、黔、桂、川等西南地区实施接管整训和政令统一,并已经意识到交通运输的重要性。所以,国民政府“一面……先谋交通运输之发展,一面更应于各省人力、物力、财力有合理之统制,以应抗战之需要。”[7](P556)例如,1933年成立于广州的西南航空公司,起初只有粤桂一条航线,未能拓展至滇、黔地区。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为服务抗战,便利西南交通,西南航空决定筹办桂滇和桂黔两线,其中一线由桂省南宁经百色、蒙自,直达滇省会之昆明;一线由桂林经柳州、独山,而至贵州省会之贵阳,以成粤桂滇黔之民航交通网。[8]在当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非常时期,为确保国家及边疆之安全,开通西南边疆与内地之交通,应是国民政府最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在国民政府交通部门的努力下,在西南边民的支持和配合下,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不断增强,主要表现为:第一,开通西南边疆与陪都重庆的陆路交通,初步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包括川黔公路、滇黔公路、湘黔公路及黔桂公路在内的西南边疆公路网络,缩短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时空距离,首次显示了西南边疆通达内地的便捷性。20世纪30年代初,黔省贵州因较早纳入南京政府的统一行政范畴,故与西南内地实施公路通联的筹建时间要早一些。1933年,为了西南地区“剿共军事”之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将西南边疆的云南纳入西南公路计划之中。因此,滇黔公路于1936年通车则成为“西南交通史上之重要一页”[9],而京滇公路于当年年底亦通车,使人感觉自边疆城市昆明至首都南京“10日可以到达”变为现实[10]。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西南重镇重庆,西南边疆的战略地位猛然凸显,由西南连接海外的国际交通建设势在必行,对滇缅公路、滇缅铁路、湘桂铁路以及西南各省际的公路建设则成为国民政府的经略重心。1940年初,川滇公路(东路)通车,从昆明到达陪都重庆的时间大大缩短,说明自西南边疆昆明到达战时政治经济中心的联系加强。第二,开通西南边疆滇黔桂与战时陪都重庆的空路交通,进一步提升西南边疆与战时中心的联系。1929年5月,粤桂滇三省实施“联航之酝酿”。1933年9月,粤、桂、闽、黔、滇等五省“筹办民用航空”。1934年8月,“交通部拨二十五万元,辟川贵滇航线”;1934年9月,中航公司“筹备滇渝航线, 与沪粤线衔接。”[11](PE81)1935年,“黔省航空运输,自二十四年四月起,为渝昆线之停航处。”[11](PE81)1936年3月,“欧亚公司试航京滇线”;4月,“欧亚航空公司首次蓉滇飞航正式班次……由蓉飞达昆明……;”1937年8月,西南航空开辟自广州经桂林至昆明的航线。此后亦开辟了西南边疆至港、越、缅等地的国际航空。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到,西南边疆航路交通建设开辟了西南边疆交通史上的革命,使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航程时间缩短为以小时计。当然,抗战非常时期航路交通未能适用于民用方面,只是利用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功效发挥积极作用。总之,不论战时西南边疆的陆路交通建设与变迁,还是空路交通建设与变迁,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
(二)战时西南交通建设及变迁促进了中国西南边疆各民族政治凝聚力的增强
早在民国初年,国父孙中山就在其《建国方略》“实业计划”部分强调:“……首言建筑十万英里铁道,并云交通为实业之母,而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必使铁路建成以后,而后可以启发内地,统一国家,以臻民族于富强之域。”[12](P272)又“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而欲巩固统一,首先非有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公路网、航路网、电信网不可,故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等各种交通事业的建设,在最短时间,应用全民众的力量,帮助政府迎头赶上,交通发达,势必产生真正的统一。”[13](P20)而国父的“尤当先以沟通极不交通之干路为重要”[14](P384)的交通忧患意识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交通状况的滞后性和交通建设的紧迫性。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后国民政府于西南边疆所展开的道路建设以及所实施的交通变迁,虽是战局所逼及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实施的战略策略,但从某种角度看,其“意义实为沟通中央各省与边疆同胞间之精神联系,……一则证明中央努力交通建设之成绩,再则表明中央重视边远同胞之德意。”[15](P164)首先,战时西南交通建设和变迁在对西南边民特种动员方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骤然上升,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性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强化,而1937年11月的国民政府自南京迁都重庆,这一悲情之壮举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西南边疆广大边民的同情与拥护,为国家和民族所实施的抗战交通建设更使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的政治凝聚力得以进一步增强,特别表现为滇、黔、桂、川等边地各族人民所体现的舍小家、为大家,自愿出工、出力,无怨无悔的牺牲精神和无私奉献。其中,战时西南边疆的道路筑建和交通建设,亦使这种政治凝聚力延伸至偏远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而使这些少数民族在民族融合、国家认同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粤汉铁路是贯通广东、湖南和湖北三省的铁路,鉴于种种原因,韶关至株洲间一直未能连接,几经周折,韶株段工程全面展开,最多时动员包括瑶族等少数民族(粤北韶关为瑶族群居区)在内的18万员工参加,并以死亡3400多人[16](P43-44)的巨大代价,完成了粤汉铁路的贯通。1937年4月,印支通道的湘桂铁路开始筑建,鉴于湘桂铁路,“十之八在桂境,当时桂省被征者,计六十二万余人,占全省壮丁百分之二十六”,[17]其中相当部分的壮丁为桂省的“特种部族”。[18]时人对广西的交通征工曾给予高度评价:“广西省自抗战以来,即毫不保留,将所有力量,全部交付给国家,此种精神,殊足令人歌泣”。[19]1938年初,滇省云南筑建滇缅公路,滇西28个县的彝、白、傣、阿昌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至少20万人,计划每天出工的人数“……加上桥涵等工程雇用的石、木等工人,共约14万人。”[20](P113)尽管他们语言不通、风俗各异,但在国家处于危急关头,为抗日救国,不分男女老少,长途跋涉几天方可到达工地。鉴于“纯系义务劳动”,所以他们都自带十天半月的干粮和简易的锄头,在工地自搭窝棚或露宿。由于劳动强度极大,安全很难保障,因而付出的代价较高。据相关资料统计,战时交通建设因死于爆破、……疟疾等事故的大约3000多人。[21](P290)1938年3月开工并由川省泸县至滇省沾益的川滇公路,在经黔境杉木箐至威宁段的抢修,黔省各族人民对于征工筑路,均“认定为应有之义务,”[22](P171)“沿线苗、彝等各族民众历尽千辛万苦,负累重重。”[23](P193)1942年对自黔省贵阳通往桂省柳州的黔桂铁路黔境段实施抢修,参与抢修的民工均为铁路沿线的独山、荔波等各县的苗族、布依族等各少数民族,尽管基本上属于“……义务劳动”,“动用人力多达120000人次”。[24](P396-397)“驼峰”空运时期,为配合盟军向中国实施战略物资运输,以及盟军与日军争夺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制空权,美国空军进驻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机场建设急不可待。据相关史料统计,仅西南边疆的滇、黔、桂、川等地区就为盟军修筑机场100多个。[25]其中云南新建陆良、沾益等31处机场[26](P669-670),共征用各族民工不下百万,仅1941年扩建昆明巫加坝机场先后征用各族民工12.7万人[26](P671);贵州扩建和新建黄平旧州、独山等14处机场,[27](P264)仅黔省黄平旧州机场就征用各族民工10万余人[28](P50);广西新建和扩建柳州、桂林二塘等10处机场,征用各族民工达195764人[29](P436-437);四川新建和扩建成都凤凰山、广汉等9处军用机场,修筑这些机场征调各族民工达150多万[30](P258-265),这些修建机场的各族民工基本上都是自带干粮和工具的义务劳动。1944年,抢修中印公路北线的保山至密支那公路,参加修路的傈僳族“因家乡被日寇弄得残破凋零”,“同仇敌忾,愤然参加修路”。[31](P177-178)对中国西南边民在抗战道路修筑和机场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美国时任驻华大使詹森回国后曾发表评论说:“……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32](P13)其次,战时交通建设和变迁对西南边疆管理事权的整合方面。这主要表现为全面抗战爆发前期国民政府“西南各省联运委员会”对滇、黔、桂等西南边疆各省公路联运业务的接管上。[33](P14-22)1937年7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军委会等部委以及滇、黔、桂等地方当局,在南京开会,成立西南公路联运委员会,其目的就是筹划战时西南公路联运事宜,改进西南公路交通运输办法,确定“长沙至贵阳,贵阳至昆明,重庆至贵阳”,以及“贵阳至柳州一线”作为联运线。[33](P1)该时期,尽管川、滇、桂等西南地方政权与国民政府中央面和心不和,但这些省份皆出于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之考量,服从国民政府全局之安排。所以,滇省方面,一是“滇缅公路即由交(通)部接管……”[34];再一就是当中央军为“保卫滇缅公路”而“源源入滇”之时,滇省政府积极配合。[35]黔省方面,国民政府交通部西南公路管理局于1938年3月正式接管黔省境内四大公路干线,合计长约一千四百余公里。[33](P14)桂省方面,桂省地方政府在接到接管办法后,曾电呈行政院提出四项意见,后行政院交通部咨复广西省政府,最终于1938年6月14日实施移交。[33](P18-20)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事务的统一接管,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民政府政治凝聚力的增强。
(三)战时西南交通建设及变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
战时道路筑建既是民族意志的象征,也是国家权利的体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西南边疆广大边民对民族和国家的认知和评判水平。一般情况下, 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是建构在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最高认同形式。[36]抗战时期实施的西南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不仅是战时国民政府设法破解日军封锁政策的一种无奈之举和策略体现,而且在西南国际交通(主权国家与西南边疆之间的媒介)筑建和变迁的过程中西南边疆各族人民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和自身实践来增进对主权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识的。
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阐释。从学理层面和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民族”、“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等若干概念基础上演化而来。
近代以降,中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和语境,对“民族”的界定和意涵实施不同的解说。一般情况下,民族概念内涵的界定,不外乎从民族学、人类学和政治学视角实施不同考量的“人群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解读。19—20世纪之交的梁启超开创“中华民族”概念之先河,它既包有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民族自强向外的一面,亦内涵国内统一、民族振兴向内的一面。[37](P126)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亦认为:“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38](P52)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主要是通过“以德怀远”的“册封”方式,吸纳周边其他民族,以至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共同体像雪球那样越滚越大。”[39]
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人们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的态度、评价和认同结果。抗战时期的国学大师顾颉刚曾大声呼吁:“中华民族是一个”,“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外我们绝不能再析出什么民族,……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40](P36-37)顾氏“俾尽书生报国之志”的爱国热情以及他的中华民族一体论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的“内在紧张”,彰显出“中华民族”逐渐成为共赴国难、凝心聚力的时代旗帜,从而为费孝通“多元一体”民族理论奠定基础。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详细地阐释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单元之间的一元多体关系,这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目标则定调于十九大报告之中。[41]
2.“路”的符号象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日军利用其坚船利炮对中国沿海实施全面封锁,中国的对外交通不得不实施新的筑建和相应变迁,这不仅仅是中国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的物理支撑和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种表征社会发展和政治认同进步的符号象征。抗战时期的交通筑建和相应变迁往往被视为一种强烈政治意愿和国家意志的结果,能够促使人民产生一种关于“路”的新表达和使用“路”的新想象。[42]战时西南边疆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改变了人们的地理认识和对空间的概念,人们开始以时间而非空间来感知距离的长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以空间换时间”。抗战时期的西南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促使西南边疆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逐渐演变为一种“接近时空”的关系,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所带来的流动性以及对时空格局的重新塑造,缩短了西南边疆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为构建国家认同和强化民族意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论述构建美国国家认同时曾说:“只有在当很大一群人能够将自己想成在过一种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行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算彼此从未谋面,但却当然是沿着一个相同的轨迹前进的,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新的、共时性的崭新事物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出现。”[42]作为一种国家意志和民族意识的象征符号,战时西南边疆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与政治因素、社会期望紧密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活网络。[42]道路建设是国家权力和意志的一种地方化表象,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必然会对生活在道路周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而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所产生的这些效应亦影响着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理解和评判。[42]如抗战时期实施筑建的“应急性”工程——滇缅公路,当时滇省地方政府因任务繁重,时间紧迫,紧急动员公路沿线20万少数民族参与了这一史无前例的建设工程。在筑路过程中,他们形成了一种具有“滇缅公路筑路人”的身份认同,一方面是受战争局势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便是基于个人使命和责任使然,有利于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构建的现代性因子不断融入西南边疆社会,直接影响着西南边地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等,“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意识便会陡然而生。
3.“路学”视角下的社会整合与民族认同。近年来,“路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外学者的视野内。所谓“路学”就是关于道路的研究,其研究范畴并不囿于某一学科的限制,而是试图跳出单独学科的限制,从跨学科的视角对道路及其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43]民族地区的“国家化”过程往往与国家道路的修筑有关,甚至有时道路的修筑具有一定的决定性作用。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化亦是如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公路建设成为当务之急。1934年初,国民政府通过《确定今后物质建设及心理建设根本方案》,规定交通建设“须首先完成西向之干路,使我国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锁之出入口。”[44](P228)南京政府充分认识到东南沿海在对外作战中的不利地理因素,在经一年多的考察之后,最终做出以西南川省为“抗战司令台”[45](P385-396)的重要决策,并在同年确定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方案。鉴于西南大后方交通滞后之状况,其首要任务就是筑建交通,“赶速修筑公路。”[46](p129)此后,在西南边疆地区陆续整修了湘川、川鄂等战略公路以及以贵阳为中心的西南公路,其中肩负战时重要使命并被列为“抗日重点工程”[47](p132)的湘川公路(湘省茶洞至川省雷神店)更是要求于一年内通车。于是,国民政府及湘、川地方政府进行广泛动员和社会整合,发动包括土家族、苗族等在内的各族民工40余万人参与施工,最终于1937年3月全线通车,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国民政府有效的宣传动员和整合能力。同时,冠之以“现代化和国族想象”标签的湘川公路给偏僻的湘西各族民众带来强烈的震撼,湘川公路川流不息地宣扬着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象,“国家的人”和“国家的物资”的强势进入亦使湘西各少数民族获得“与汉人生死一体、命运与共的历史经验”[48]。现代化与国家、中华民族如此突然地降临而又自然而然地与湘西各少数民族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
三、结语
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不仅是战时国民政府的无奈之举和策略体现,同时亦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族群、边疆事务和国族整合造成了意外而重大的影响。[48]通过一系列西南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国民政府获得了与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接触的经验,[49]并以政治承认的方式展开对少数民族的道路筑建政治动员,鉴于这些动员更加贴近西南边民少数族群自身民族化过程的节奏,所以较易与西南边地少数民族的抗日行动相衔接,并结成对抗日军事、政治攻势的共同阵线。从实施西南边疆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的战时动员规模来看,堪称中国历史上首次的“全民”动员,中国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亦真正获得与汉族族群同生死、共患难的历史经验,在族群意识之外进一步建立了中华民族意识的雏形,对近代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中国国民”化与少数民族、国族构建及国家整合有正面助益。但同时我们亦看到,国民政府在动员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实施道路筑路和机场建设时并没有将“民族因素”纳入整个工程来实施考量,也未制定出适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定方案,以至于在筑路过程之中因语言差异和民族隔阂而遭遇种种困惑和障碍,只是偶尔在非常阶段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一种灵活策略。例如,1939年后,因战局发展和形势所迫,国民政府积极建设以西昌为中心的西康宁属地区,组织兴建乐西公路(该路与西祥公路相连并入滇缅公路),为调动沿线广大彝胞参与修筑乐西公路的积极性,国民政府对广大彝族同胞舍小家顾大家的忘我牺牲精神给予正面肯定和正确的评判,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位的政治承认,然而战时政府看待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深层次思想观念并无根本性的转变,未能使民族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50](P27)但当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国家和民族形象连续不断地通过公路运输、筑路宣传、学校教育等不同方式和渠道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传播开来,这既是国民政府实施有效政治动员与资源整合的具体体现,更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演进与转变。战时所实施的西南边疆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既为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社会动员和政治整合提供了一个个丰富立体的个案,也为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重返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大家庭开凿了一条条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