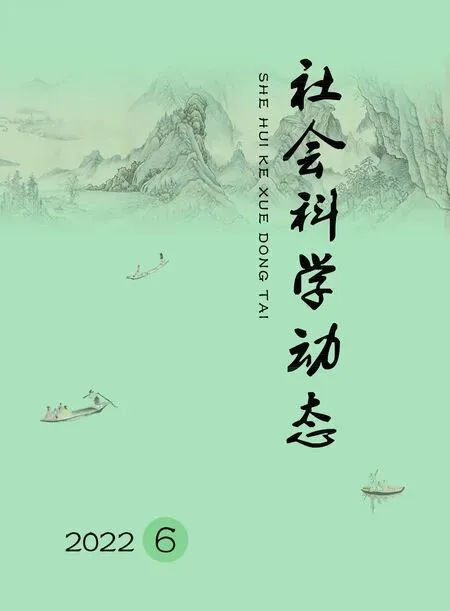屈辱与尊严:基于人际互动权利的阐述
2022-02-02王晴锋
王晴锋
本文是一项关于人的尊严、屈辱以及侵犯的研究,但它不是从宏观、制度或结构性的维度进行研究,而是从微观互动的视角加以阐述。众所周知,人际互动是微观社会学的核心议题,面对面互动既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亦是社会行为的主要形式。社会互动的主体是具有良好认知判断和移情能力的个体,他们关于自我、他人以及尊严与屈辱的感知主要源自于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互动。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关于压制、不平等以及羞辱的感受不是来自遥远的机构或抽象的制度本身,而是源于时刻都在发生的具体的面对面互动,这种切身的经验感知将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以及他对社会的理解。通常而言,至少有三个主要来源导致个体在日常互动中处于屈辱性的地位:第一种情况是由社会设置导致的,它是结构性的、自上而下的,如监狱里的囚犯面对狱警时;第二种情况是由于文化规范、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导致的,如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面对婆罗门等高种姓时;第三种情况则是在互动过程中生成的,它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本文主要通过呈现现实生活中人际互动的场景,将抽象的屈辱、尊严观念落实到具象的面对面互动进程,由此从形式化的表述进入到实质性的领域,并强调互动过程中存在的不平等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性后果。
一、 人际互动中的屈辱与侵犯
毋庸讳言,人际互动与结构性要素或场景设置密切相关,在情境性的外在压力下,有时人们不得不保持屈辱性的姿态。例如,在上下班高峰期,地铁里的人们毫无尊严地被迫挤在一起,被猛烈地推攘,尤其是年轻女性,不得不近距离地与陌生男性保持身体接触。在这种情形之下,某些人会施展各种防护性的卷入行为,甚至侵犯性地用拳头阻挡靠近他的人,使自己在密集的人群中仍保持一定的身体空间。人际互动受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影响,更频繁、明显地出现在谈话过程中。例如,当社会地位低下者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人且说话时,在场的他人可能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或表现出一脸的不屑、嫌弃或不耐烦,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便直接离场。他也可能在说话过程中不断地被打断、质疑、否定,或遭到嘲讽、讥笑、无视。当面对权威或长者说话时,地位低下者会不由自主地紧张、出汗、颤颤巍巍,甚至嗓音都发生改变,因为对方掌握着权力、资源和影响力,能决定他的前途命运。社会地位较高者也经常通过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来确立、肯定和维系自己的权威。譬如在初次见面时,地位较高者可能不愿意握手,或者仅是象征性地轻微捏一下,以此展示自己的某种高傲心态。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口头禅也体现出说话者内心的不尊重,这些所谓的“口头禅”,诸如“你懂我的意思吗?”“知道我在说什么吧?”这些话语实质上是以潜在的关系假定为基础的,它们并非不经思考地、无意识地脱口而出,因为在尊长面前不会说类似的话。又如,我们有时会见到一个人将东西扔给某个人,而不是正常地拿给或递给对方。类似的个体在日常接触中可能遭遇到的屈辱以及卑微状态不胜枚举。人们通常认为,公共场所的行为互动是平等的,因为初次接触的陌生人之间不会卷入诸如家庭背景、阶级地位和权力关系等因素,然而,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一方面,衣着打扮、面容仪态、精神面貌、性别、种族、甚至有些宗教信仰等个体特征是可见的;另一方面,言语与非言语的行为举止及其符号含义也会不自觉地渗透入互动领域,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着个体在互动过程中对待与被对待的方式。互动参与者通过这些方式确立假定的地位等级和社会关系,由此进行实质性的互动并产生相应的行为后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细枝末节的行为以无法否定的方式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态度,那些细微的怠慢、无视和鄙夷明显是有意识设计的社会性行为。
规则或规范通常以义务和期待两种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个体,但是文本性的规章制度在互动过程中往往不直接发挥作用。在某些社会中,社会不平等并非体现在抽象的法律条文里,大多数国家和社会的法律文本都堪称完美。然而,很多不同层次的法律条文被束之高阁,无法为现实的面对面互动提供实质性的约束或指导。譬如,印度独立以来的宪法规定人人生而平等,并宣布废除延续数千年的种姓制度,但是生活实践中性别、种姓以及宗教的不平等现象却比比皆是,尤其是“不可接触者”(即所谓的“贱民”) 仍被高种姓视为肮脏、不洁的人,他们具有仪式污染性。又譬如,美国的法律和制度设置也竭力避免种族不平等现象,但是,且不提施行多年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在宏观社会层面产生的效果如何——职业市场的劳动分割和社会分层可以明确表明这一点(如快递员、清洁工等体力劳动密集型的工种通常由黑人从事),与本文主旨密切相关的是,基于族裔的不平等差异仍然以微妙的方式渗入人际互动领域,即使连在图书馆借书这样的日常事件也可能反映出族群不平等。例如,当一位亚裔办理借书手续时,白人管理员可能瞟一眼之后继续跟身边的同事聊天,从他的举手投足间可以明显感受到怠慢与轻蔑。这种差异性的对待方式是在瞬间完成的,却是基于行为者大量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认知。在任何一种社会文化里,在敏锐地进行察言观色的基础上迅速做出判断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的能力几乎是一种生存之道,它是社会成员必须掌握的为人处世的基本技能。这种互动过程中的歧视和不平等对待及其运作方式极为微妙,而且不同的人社会敏感度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难以察觉到甚至不以为意。在图书馆借书这个案例中,管理员显然不是拒绝给特定的读者办理借书手续,但是在拒绝与接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之间存在大量可供自由操控的空间,这是无法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强制规定的领域,即它游离于法律与规范之外。因此,我们无法仅仅通过立法的形式消除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否则这个世界早就不会存在如此多的社会非正义现象。换言之,形式上的平等并不能确保实质性的平等。
虽然微观层面的人际互动转瞬即逝,但是它们不仅体现了人的情感以及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也展现出作为人的日常姿态与世相。嗓音、声调、着装、眼神、表情、发型以及举手投足等,都深刻地影响着个体在特定情境中被对待的方式。例如,在印度北方邦的圣城瓦拉纳西,有些职业行骗者极为善于通过衣着打扮、言谈举止和神色表情等判断外国游客的特质,然后通过各种事先准备好的行动剧本(通常与印度教信仰有关) 行骗,肆意地接近、乞求、索取甚至动手动脚。总之,当公共场所的陌生人之间产生互动时,虽然阶级、财富、声望、教育背景等先赋性与后致性因素是未知的,但是人们能通过个人呈现出来的外表进行初步判断,并迅速形成权宜性的、潜在的互动阶序。这种互动阶序将真实地影响后续的互动进程,包括个体被对待的方式、所获得信息的真实性和充分程度,以及解决问题的效率等。随着互动双方持续交换信息,参与者会不断地作出调适,从而使互动模式不断接近真实的身份。概言之,现实生活中的个体不仅是社会性的存在,更是互动性的存在,权力、尊严及其侵犯都在人际互动中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与社会情境密切相关的互动过程中,个体真切地感受到尊严、轻蔑或伤害等情感。
二、 “制度人” 与“形式人”
在曾经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有一幕场景是李达康在信访办的服务窗口前半蹲着跟里面坐在椅子上的工作人员说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可以见到类似的场景,这显然是制度设置使然。面对各种屈辱性的社会设置,普通人不得不保持低三下四的姿态,可谓斯文扫地、颜面丧尽。极端屈辱性的制度环境是监狱、收容所、精神病院之类的全控机构,例如,看守所里被收监的性工作者在与管理人员说话时,她们坐在甚至连膝盖都难以屈伸的小板凳上,这些性工作者被认为是道德败坏、没有人格和尊严的需要“改造”之人。我们这里主要从普遍意义上探讨个体被机构化对待的方式,这亦是日常生活中个体真实的存在状态,其中涉及的机构管理人员可被称作“制度人”,与之相应的被对待的个体可被称作“形式人”。
(一) “制度人”: 物化处理他者
在很多事业单位、公共机构,即使是所谓的服务型机构,我们随时会遭遇“制度人”。这类人嵌入在形形色色的制度里,他们以制度作为庇护伞和挡箭牌,以遵循制度为借口,行惰性、敷衍之实。这些人是极端制度化的,常以高傲、冷漠的态度对待工作中接触到的他人,制度成为他们唯一的圣典和服务对象。例如,在某些高校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倘若读者第一次进去,不知道要事先存包、不能带书籍进入,管理员就会以傲慢的语气说:“去看看外边门上写了些什么!”或者干脆直接让人离开,仅仅告知“这里不是自习的地方”。很多公共机构都充斥着类似这样的人,他们的工作是以物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公共图书馆每年花费大量经费订阅杂志、报纸,管理员每天认真地去取这些资料,然后将它们分门别类、仔细摆放好,但他们从来不会关心是否有人阅读这些资料,以及这些资料本身有没有价值。他们将读者当作物来对待,整天自顾高声闲谈、玩手机、煲电话粥,或者在值班时间不停地在阅览室里溜达,等下班时间一到立马拎包走人,完全不考虑是否有人需要安静地阅览、学习。对他们而言,读者甚至不如书刊报纸重要。
类似地,城市里有些公共厕所的清洁人员会很鄙夷地看着行人进入他刚打扫完的卫生间,因为被弄脏了又得重新打扫。还有高校财务处的“窗口服务”设置,也是以物化的方式对待个体。对于很多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而言,将个体物化既是磨洋工的方式,也是彰显自身存在以及优越感的工具,其背后的原因并非是简单的官僚作风使然。
(二) “形式人”: 被形式化对待
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经常会遭遇到各种被形式化对待的方式,较为典型的是乘坐地铁时,地铁安检员有一整套极为形式化、规范化的动作来搜查乘客的身体。但是,有些站点随着客流量的增大,他们每天的常规动作会逐渐简化为寥寥几个假动作。从客流量大的站点到客流量稀少的站点,乘客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不同程度的形式化对待方式。对安检员而言,乘客是毫无个性差异的“形式人”,他们是等待在流水线上需要被统一处理的客体。个体本身是无足轻重、无足挂齿的存在,他们可以被忽略不计,无需给予任何仪式性的关照。在这种物化的对待方式下,个体不再表现为温润的生命,而是被简化为某种程序,并以公共安全或人身安全的名义被剥夺尊严。由此,公共权力以这种无可质疑和辩驳的方式渗透到每一个人身上,而且每个人都能切实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及其运作。这是生物政治的日常表现形式,它通过对身体的凝视、操演以及干预人际接触来实现权力的组织化和微观管理。与米歇尔·福柯说的临床医学的凝视不同,这是一种人身安全的凝视;同时,它也是一种心灵习性上的降服。在管理者看来,个体是一具具需要经由公共力量管控的肉体。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无论是学校、工厂、医院抑或其他各种形式的全控机构,个体主义的灵魂被迫过着集体主义的形式化生活。
这里试图回答的问题是,除了剥夺政治权利、人身监禁乃至判处死刑之外,公共权力如何施展于个体身上?在人际互动的个体层面,它显然不是通过强制性和规范化的形式来实现的。例如,公共权力赋予地铁安保人员有权检查乘客及其携带的物品,并且有一整套规定动作或操作程序;不是任何人都享有如此行事的资格与权力。但是,国家机器既没有、也不可能具体规定实际发生的操作方式,包括对待乘客的姿态(语气、眼神等)、检查身体时的动作力度、对待私人物品的方式等。由于在制度规定与实际操作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不同的乘客在进站乘坐地铁时,他们遭遇的检查繁琐程度和严格程度其实是不一样的。譬如,有时安检员需要检测乘客保温杯里的开水,有时则不需要。有些地铁站人流量少,工作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此类检查;有些站点人流量多,检查变得更为形式化,仅需将私人物品放入检测仪通过即可,不会对身体进行人工检查。但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人流量集中的地方恰恰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应该从严检查才对。此外,“人物同检”在技术上完全不是问题,但现实中两者却是分离进行的。正是在这些微观的人际互动中,公共权力通过其代理人具体的行为展演体现出来,这个过程涉及公民治理术。就社会治理而言,它既可以通过机构、规范、制度等正式控制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话语、身份、互动关系等非正式控制来实现;它既可以是外在的、强制性的,也可以是内在的、习得性的自我管控。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对人际互动进行的微观管理亦可谓是一种“互动治理术”。
三、 印象管理、 身份展演与情境性弱势
社会能动者通过语言、身势以及符号标识构建他们的社会现实,在街道、公园、商店和车站等场景里,陌生人能够相对自由地进入一个人的自我领地。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以下简称戈夫曼)毕生关注公共场所的面对面互动,他进一步阐释了齐美尔关于社交性的观念。戈夫曼指出,个体在互动期间被期待拥有某些属性、能力和知识,这些要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自我,用于当下的面对面互动场合。通过行为的表意性含义和互动参与本身,个体将自我有效地投射于互动,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未被清楚地意识到。①个体确立其神圣性自我的方式是举止优雅,且得到他人的敬重。在戈夫曼看来,传统的行动者模型“使人过度理性化”②,而他更为强调身体习语,即惯例化的表意性符号。行动者以某种态度或心绪参与特定的活动,这意味着接受某种既定的身份,但身份并非某种与生俱来的内核或静态的本质,它是社会规范反复操演的结果。也就是说,对行动者而言,身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通过程式化的重复行为建立起来的。③概言之,行动者的身份建立在构成性的行为基础之上。这种身份的建构过程,对戈夫曼而言,是在他人面前进行的印象管理;而对朱迪斯·巴特勒而言,则是一种身份展演。展演性是一种阐释或意义制造过程,它发生在观众与事件、客体或活动之间的每一次交换过程中。④
行为互动模式会对即时性情境身份的塑造产生影响。正是由于互动系统中身份的含糊性、不稳定性以及权宜性,行动者需要不断地维护其情境性身份,而共同在场的他人也需要根据行动者的印象管理与身份展演进行恰当的定位。有关印度中产阶级的研究表明,阶级身份的表演“是微妙的、易碎的事物,任何一个细微的错误都可能击碎它”。⑤中产阶级身份的再生产不仅需要维持经济稳定和一定规模的消费支出,而且需要恰当的阶级行为的表演,如语言、仪式实践以及公共场所的举止和卫生问题等。在印度,高种姓的身份维持也通过仪式展演表现出来。例如,詹姆·西布林对印度北部帕哈里人的研究表明,高种姓与低种姓都遵循着当地的种姓习俗与实践。由于低种姓被视为不洁的,他们在高种姓的店里喝完茶之后,需要自己将杯子洗干净,而这种清洗存在明显的程度差异,从非常严格、彻底的清洗到象征性地清洗——店主只是倒点水,然后低种姓摇晃一下杯子将水倒掉即可。⑥在高种姓的家庭里,洗厕所、浴室之类的家务劳动被视为肮脏的、低贱的,必须交给低种姓去完成。在其他世俗性的社会文化里,实质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例如,有些人在公开场合刻意规避做细枝末节的杂务(如高校开讲座时,经常可以见到有些邀请来的外国专家“不知道”如何在电脑上使用优盘),而现场手忙脚乱的他人则迅速成为其忠实而乖巧的“秘书”。越是在众多的观众面前,这种情境性的、表演性的优越感就越强烈。
与传统的印度教社会不同,现代生活更多地受世俗(非神圣) 而理性的文化意识形态支配,个体在作出行为反应时,主要考虑的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⑦个体在采取社会行动时,将他人进行适当的分类处于行动的核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行动者以成员资格身份作为行动的基础,并以之阐释他人的行为。⑧在理想的情况下,面对面互动的参与者被视为仪式性主体,他们应待之以礼、动之以情,尊重其自主性,并且维护其自我的领地。在公共场所的日常互动中,理想状态下的行动者应该是享有尊严的,他们怡然自得、轻松愉悦。然而,由于制度设置、文化习性以及其他各种情境性因素的存在,经常导致面对面互动系统出现冒犯的现象,置社会互动的实践伦理而不顾。戈夫曼认为,当不适用于情境的仪式形式以一种滑稽的方式被使用时,它明显地是作为一种嘲弄社交的手段。⑨从行动者的角度看来,这些行为亵渎可能具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性意义,也可能是盲目冲动的结果。但是从整个社会及其仪式习语的角度来看,它们并非是随意的、冲动性的违犯行为。这些行为恰恰是有意的,它们通过象征性的含义表达彻底的不敬和蔑视。都市生活的社交性充满了各类遵从与违犯行为,包括从温和善意的提醒到粗暴蛮横的拒绝,后者违反了互动的基本伦理,暴露出互动的不平等性。
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互动都存在着特定的情境性优势与弱势。除了污名携带者、被收容者等“社会性弱势群体”之外,还存在一种更为普遍意义上的经常受到社会排斥和忽略的群体,即“情境性弱势群体”。⑩属于此类群体的个体并无明显一致的、客观的特征可供描述,他们的情境性弱势是在互动情境中即时性地生成的,并且这种弱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同在场的他人的主观原因所导致的。在公共场合,情境性弱势群体很容易成为陌生人提出各种要求、搭讪、欺骗甚至攻击的对象。他们可能被选中要求做一些通常不会对他人提出的要求,诸如借钱(通常是作为路费或买食物)、打电话、发短信甚至发邮件等,而对方不会对提出此类要求感到任何不适或愧疚,他们甚至觉得心安理得,是长辈对晚辈、高贵对卑贱、上级对下级、有资格能力者对无资格能力者的一种无须回馈的命令式要求,这是陌生人在接近情境性弱势群体时经常采取的对待方式。而在其他情况下,情境性弱势群体更多地是被无视和忽略的“非人”(non-person),他们是在场的缺席者,得不到人际互动时应有的基本尊重。而在他们面前的他人则感到轻松自在,甚至变得放肆和飞扬跋扈。在很多情形中,女性相对容易成为情境性弱势群体,事实上,很多女性自身对性别问题不甚敏感,导致对公共场所细微的性骚扰视而不见。例如,男性经常违反“礼节性忽视”的互动原则,随意侵入女性自我的领地进行搭讪。这些男性不仅破坏了“都市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毁坏了社交性的基础。1⑪此类破坏互动的行为反映出更宏大的社会结构性条件是如何形塑局部情境的。又如,在“恐同症”的社会里,一旦某人在公共场合被辨识为同性恋者,他很可能成为言语攻击、骚扰和侵袭的对象。这种日常生活里的微观政治不仅通过口头语言体现出来,而且也通过具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行为显示出来。
四、 互动公民权
公共场所不是客观、中立的自然空间,它并非平等地容纳所有实体、身份或行为。某些表达方式、身份和实体被认为是尊贵的,或至少是正常的;有些则被视为卑微的,甚至是越轨的,因而需要被监视、排斥和边缘化。换言之,现实生活中的公共空间是异质性的,人们彼此对待的方式不尽相同,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可见性、可接近性,以及被想象、感知和对待的方式也千差万别。社会不平等既通过人际互动的微妙方式体现出来,也通过它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在现代社会里,被异化的人际互动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诸如(1) 某些空间里人际距离极限压缩,这导致自我的领地受到严重侵犯。因此,在早晚高峰时间,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里经常出现争吵的场景; (2) 刻意保持人际距离,仿佛某些个体是肮脏的污染物或病毒性的传染源;(3) 当着他人的面肆无忌惮地与旁人闲聊或大声打电话,认为在场的他人不需要给予任何仪式性关切;(4) 被各种场合的陌生人/安检仪检测是否安全、能否被允许进入; (5) 以各种借口被拒绝提供公共服务,或因机构性的繁文缛节让人望而却步。在这种非人性化的互动形式中,个体虽然行走于人世间,却不是作为活生生的、充满个性和灵性的生命,而是形式化的、单调的、不会表达甚至不会作出反应的物体。戈夫曼曾经详细阐述了以精神病院为代表的全控机构对被收容者施行各种情境性剥夺的现象,而我们日常遭遇的现实也正在逐渐成为这种总体性机构的延伸和变体。在这种粗鄙、无礼、蛮横、狂妄甚至嚣张的环境下,礼节性的行为显得弥足珍贵。
个体所处的物理和精神世界充满了各种文化符号,它们被个体内化后成为认识社会及其成员的引导机制。通过这些符号手段,人们感知到从何处寻求支持并且认识到必须尊重的权力中心;同时,它也惩罚那些违反社会规范或对正常群体进行贬抑的越轨者。在情境性、关系性的互动过程中,一个人自我期待的实现不仅基于他自身的行动以及外部世界的既定结构,而且也取决于其他社会客体的行动。⑫因此,相互尊重是互动及其维系的重要前提。在某些社会中,经过充分社会化的个体是“仪式性雅致的客体”⑬,他愿意遵守社会互动的基本规范。然而,人际交往仍然可能出现大量互动违犯现象,它们体现出互动主体之间的不对等。尽管这些违犯是细微的、不足以直接影响社会结构,但它们却真实地影响个体心灵的认知与感受,并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行动者反过来又理所当然地以这种姿态对待他人。一方面,个体总是能够在由阶序等级构成的相互牵制的互动网络里找到自身的位置,并且迫不及待地使自身占据相对优势的位置,从而寻求某种心理平衡,重新树立尊严与自信;由此,行动者在不断自我延伸的互动链里制造侵犯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对权力差异、礼仪待遇的敏感度和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因此在关于互动生成的屈辱与尊严等问题上,不同个体之间往往难以达成共识,这也使日常政治变得更加个人化和碎片化。
在西方社会,订立契约是以承认个体是具有特定属性的存在为基本前提的,契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在对个体特征的广泛假定之基础上。然而,每一个契约背后有着对参与者特质的非契约性假定。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被赋予的仪式性尊重体现出一种“互动公民权”,它是“一系列模糊和分散的、却极为重要的期待与义务,这些期待与义务是表达对个人的关切、敬重和尊严的互动展示。”⑭互动公民权涉及对称性的礼仪规则,它确保面对面互动的参与者能够彼此给予大致同等的礼遇。也就是说,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相互赋予复杂的互动权利,彼此以公民身份相待,并遵守对称性的礼仪规则。保罗·柯罗米和戴维·布朗认为,与这种公民权形式对应的是托克维尔的平等原则、涂尔干的“个体崇拜”以及帕森斯的制度化的个体主义。互动公民权的权利与义务体现在不同的层面:在微观层面,它体现为表达恭敬、保持仪式性距离以及礼节性忽视等;而在宏观层面,它主要涉及社会包容与排斥。在这种意义上而言,戈夫曼关于互动秩序以及有关恭敬与风度的分析进一步扩展和修正了宏观社会学的公民权理论。⑮
互动公民权包含个体在面对面互动过程中享有平等对待的权利,它更多地涉及互动进程中的意义协商、沟通实践与身份塑造。互动公民权不是个体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也不是政体规定的固有法律地位,它是在日常生活的面对面互动实践中即时性生成的。大体而言,互动公民权至少具有四层涵义:第一,它指涉公共领域人际互动的基本权利,个体有权要求在互动过程中享有同等对待的权利,避免遭受屈辱、蔑视以及其他不礼貌的对待。第二,它强调这种权利是在互动过程中达成的,而不是先在的、高度结构化的、已编纂成文的规章制度。互动身份是在互动现场生成的一种临时身份和地位,它不是自然的、先赋的、固定的、静态的,而是文化的、后致的、弥散的、流动的关系结构,各种异质性的要素都参与到这种临时身份的塑造与建构过程之中,由此形成不同个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三,互动公民权具有交互性,它意味着互惠、互利和彼此尊重。第四,互动公民权是以“互动正义”为导向的,即个体在人际处理过程中感知到公平,它旨在创造彼此合意的、欢畅的人际互动,进而形成良好的互动秩序。互动参与者只要一旦发生面对面接触,就会涉及到这种互动公民权;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微观互动过程与宏观社会结构紧密地联系起来。
五、 总结与讨论
本文是一项关于日常生活中个体的尊严与侵犯的微观社会学研究。个体的尊严与屈辱不是停留在文本里的抽象概念,而是在实际互动中展演出来,并由行动者切身感知、体验到的。换言之,个体遭受的屈辱、歧视、排斥以及不平等更多地体现于细微的人际互动,尤其是在谈话互动中,诸如话语权的掌控、语气与口吻、身势以及面部表情等,它们都能够反映出互动进程的不对等性,与此同时也展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在说话者—听话者二元模式中,地位较高者作出的行为反应可能是皮笑肉不笑,或者别人说话时根本不听、故意将脸扭向别处。这些谈话细节表明,社会不平等不仅是互动中达成的,而且也包含着权力要素,这种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不平等是当下普通人的重要存在形态。本文从微观互动的层面探讨日常生活中的尊严与屈辱,它涉及特定的权力类型及其维持机制,从而使公共权力以极为细致和具体化的方式渗透到每一位个体身上。对此,本文提出“互动治理术”的概念,由于治理术涉及权力的再生产,与之相应的重要概念则是“互动公民权”。
人们在公共场所产生的互动不仅具有工具性意义,而且也涉及情感和仪式,互动的属性取决于参与者双方关于情境的经验判断。总之,互动参与者在关于日常表象的博弈过程中,大量具有神圣自我的个体被顶礼膜拜,同时亦面临着被肆意亵渎和羞辱的风险,个体由此遭受着灵魂与肉体的双重考验。具体而言,由于个体不断地在互动过程中遭受冷遇、屈辱、怠慢、不敬与侵犯,它们产生的累积效应导致烦躁、焦虑、狼狈和失态成为生活的常态,从而长期使个体处于沮丧、乏力、受挫的状态,进而致使其内心充满戾气、痛苦和绝望。有些个体对尊严、公平对待具有很强的敏感性,违背互动正义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各类报复行为,自尊心越强的个体越可能对感知到的不公正现象做出消极反应。⑯这些“负感经验”(negative experiences) 的长期积聚将导致集体性的社会冷漠,并无形中使社会运行的成本增大。总之,我们认为在生活实践中,个体对于现实的感知以及特定身份感的产生与维持是在日常互动中实现的。因此,礼节性尊重、给面子等对于塑造和谐有序的公共生活极为重要,创造和培育彼此尊重、平等、信任的互动关系有助于生成归属感、增强社会团结,并维系社会秩序。
注释:
①Erving Goffman, Embarrass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6, 62(3), p.268.
②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1974, p.515.
③Judith Butler, 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y and Feminist Theory,Theatre Journal, 1988, 40(4), p.519.
④ Laura Weigert, Performance, Studies in Iconography, 2012, 33, p.63.
⑤Sara Dickey, The Pleasures and Anxieties of Being in the Middle: Emerging Middle-Class Identities in Urban South India, Modern Asian Studies, 2012, 46(3), p.591.
⑥Jame Sebring, Caste Indicators and Caste Identification of Strangers, Human Organization, 1969, 28(3), p.200.
⑦Joseph Gusfield, Jerzy Michalowicz, Secular Symbolism: Studies of Ritual, Ceremony, and the Symbolic Order in Modern Lif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4, 10(1),p.418.
⑧Kevin Whitehead,“Categorizing the Categorizer”: The Management of Racial Common Sense in Interactio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9, 72(4), p.325.
⑨ Erving Goffman, The Nature of Deference and Demeano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6, 58(3), p.495.
⑩ Carol Brooks Gardner, Fine Romances: Two Arrangements Between the Sexes in Public Place, in Greg Smith (ed.), Goffma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Routledge, 1999, p.44.
1⑪ Mitchell Duneier and Harvey Molotch, Talking City Trouble: Interactional Vandalism, Social Inequality,and the“Urban Interaction Proble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9, 104(5), p.1263.
⑫Wendelin Reich, Three Problems of Intersubjectivity—And One Solu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2010, 28(1),p.51.
⑬ Erving Goffman,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New York: Pantheon, 1967, p.31.
⑭⑮Paul Colomy and J.David Brown, Goffman and Interactional Citizenship,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1996, 39(3), p.375, p.371.
⑯James P.Burton, Terence R.Mitchell, Thomas W.Lee, The Role of Self-Esteem and Social Influences in Aggressive Reactions to Interactional Injustice,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05, 20(1), p.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