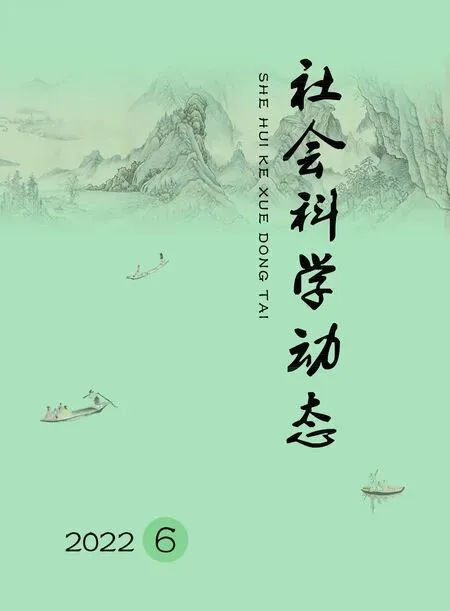邹超颖:写作是自我追赶的过程
2022-02-02陈智富
陈智富
编者按: 邹超颖, 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80 后新生代童话作家, 动画编剧。 被著名导演、 世界名人夏振亚先生誉为“80 后长篇童话第一人”。 主要作品有《再见, 蜻蜓镇》 《精灵咪萌的冒险之旅》 系列、 《十二生肖闯天下》 《目目鱼复仇记》 系列、 《魔法通天塔》 系列等; 另著有电影及电视剧作《黄帝史诗》 《东方七色花》 《班主任》 《猪猪侠之恐龙日记》 等作品。 曾荣获冰心文学奖、 第六届欧洲万象国际华语电影节最佳儿童故事片导演奖、 河南省 “五个一工程奖”、 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上海好书奖。 2022 年1 月, 新作 《再见, 蜻蜓镇》 荣获湖北省第十一届屈原文艺奖。 以儿童文学创作为话题, 本文对作家邹超颖展开深度访谈, 探讨其文学创作理念以及对文学与影视传播之现实思考。
一、 我只是中间商, 只是把宇宙的信息记录下来
陈智富 (以下简称 “陈”): 你的写作不仅仅以故事见长, 在语言的雕琢、 意境的营造方面, 亦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再见, 蜻蜓镇》 始终流淌着一种让人流连忘返的江南气韵, 让人沉浸其中, 意味悠长。 首先祝贺你的 《再见, 蜻蜓镇》 荣获湖北省第十一届屈原文艺奖。 请谈谈获奖的感受吧。
邹超颖 (以下简称 “邹”): 其实感觉比较意外的,这是我第一次申报这个奖项。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这本小说大概2019 年写完出版的。出完之后没有任何的宣传,但读者反应口碑还不错。对于江南水乡的风物人情,读者比较有兴趣。
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次转型。我此前写的更多是童话和幻想小说,这是第一次尝试写现实主义小说。题材是写少男少女的成长,也是随着写作者自己的年龄增长以及阅历的增加,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并产生新的思考,会和以前不一样。
首先,写作者在意识层面达到了自我认可的程度,在这个时候再去雕琢文本,慢慢让自己先认可作品。写作是自我追赶的过程,不断地成长,更新自己的认知,迭代知识,让作品更有深度。在当下这样一个浮躁的碎片化信息时代,人们似乎都在逐功近利,追求眼前的东西,写作者就更需要静下心来去感受世界,沉淀自己,不被干扰。
我写这本书,是真真正正地好像用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毛孔感受江南小镇。此前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去了江南的不少小镇,不是那种商业化了的小镇,而是淳朴的、有韵味的古镇。我周六周日就开着车,在百度地图搜索,开到哪里就是哪里。我看古村落,就进去,住一个两个晚上。我不像行人那样走马观花。我坐下来跟当地老人聊天,发现那里的人特别知足,他们觉得自己家乡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我在故事一开始写到阿公的一段话:“这儿的人们,从来不向往远方。”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呢?这是我跟老人们聊天后的真实感受。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一直在追逐远方,无论是想象的远方,还是脚底下踩着的远方。我们好像一直在奔跑,永远不停歇。但江南小镇的人们不一样。他们很踏实,很知足,觉得自己的小木楼很好,门后的菜地很好,屋前小河很好。他们好像梦境里走出来的一样,所有的一切好像披着一点童话的影子。虽然这是一个现实题材,但我却看到了童话的影子。
其中一个老人给我印象很深刻。那是春天,我跟他聊天。他突然站起身来说:“我去挖点野菜给你吧。”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对农村的东西都蛮陌生。他把我带到菜地里,也不是在菜地的,而是在田垄里摘一些野菜、金花菜,弄一个小袋子提给我。我说,我不会弄菜,我不会吃。他说:“那我跟你炒好了。”然后,他进屋洗菜炒菜。我全程看着他炒那盘菜。最后起锅时,他把黄酒很艺术地泼进锅,火突然“嘭”地蹿起来。那个场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那个春天的下午,我就静静地吃着这盘金花菜。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没有说自己要写作,我只是单纯地逛到这里,体验一下生活。老人非常淳朴,就是想让我体验一下江南菜。那是一个很诗意的下午,在春天,有暖阳,有老人为我做了一盘菜。
当我回到武汉后,有了强烈对比,这两年的古镇记忆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闪现。武汉是大气磅礴的城市,大江大河大武汉,和江南的婉约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我而言,写作是一种发酵的过程。当一种情绪,一些故事、情节,达到了一个程度后,就会在我的身体里发酵,发酵到一定程度,不写下来就会憋得难受。我就会开始写作。我从来不觉得写作是痛苦的。从小学到现在,我写小短文也是快乐的。写作能够带给我生命不一样的体验,这是我做其他任何事情都给不了的。任何外在的快乐永远都是短暂的,只有写作是可以持续输出的能量,我在不停地输出我的能量。但是写作又反过来向我输送能量,这种感觉非常好,反馈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滋养。有人说你看起来像个小朋友,我总是回答,可能因为我喜欢写作吧。
写作会让人的灵魂得到进化。无论我在外面遇到任何事情,只要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身体是轻盈的。我就可以放下所有事情,就可以与天地接通,我仿佛变成了一根天线。别人问我写作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说,那时候,我很怕别人打扰。我的每个毛孔,我的身体会伸出无数的天线。所有的故事和情节,都不是源于我自己。我觉得我写的每一本书都不是源于我自己,它早已存在于宇宙中,我只是信息的传递者。在写作中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即我只是中间商,只是把宇宙的信息记录下来。我不觉得写作是伟大的,我只是记录者。我可能不是记录现实世界存在的生活的经历,但是这些信息它早在宇宙中存在的,只是我们人类作为三维空间的动物无法接受到的东西。我曾经一度认为自己是一个外星人。
二、 写作是用生命影响生命
陈: 你的这种体验很独特, 可能写作的灵感是一瞬间触发出来。 有人说, 老子几千年前就有这么深邃的智慧, 是不是外星人派来滋养人类的呢。 你对科幻应该也很感兴趣吧。
邹: 我会看一些科幻作品。我最新的小说《不完美男孩》,就是偏科幻的,已经在印了,大概在明年三月上市。三四十年后,人类基因科技发展得非常先进。很多家长总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厉害的人、伟大的人、艺术家、钢琴家、作家、领导人。故事最开始的时候,当母体得知怀上孩子后,医生就会发一个表格,填写你选择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表格里有很多项选择,比如性格、特长、优异,所有一切你都可以为孩子订制。这就是未来孩子的订制计划。母体在孩子没有生下来时,就知道未来孩子是什么样子的。表格填好后交给医生,医生就可以按照要求操作。
有个孩子的妈妈是作家,爸爸是口技艺术家,崇尚自然,喜欢跟大自然接触,学鸟儿百兽的声音。只有这个孩子没有做基因调整,是纯粹自然的孩子。在这个班上所有孩子都非常优秀,各有自己的特长。只有这个主人公杨桃是纯粹的天然小孩,有孩子在这个年龄的的天性,可能喜欢玩,不想学习,打游戏,做一些小小恶作剧。但是在精英人类孩子面前,他变成了异类。这是非常讽刺的。
杨桃在班上一直受到欺负,因为他太平庸了,平庸到被人唾弃的地步。成绩差,个子也不高,形象也不好。他所有的基因看起来都不太好。班上还有个小孩是他的朋友,是基因改造失败的产品。因为这个小男孩家里的经济条件差,为了省钱,父母选择做了一个套餐便宜的计划。因此,这个小男孩的目标只有一个:希望赚钱去改造自己的基因。
杨桃经常对他的朋友说:你本身已经很好了,不要做任何改变,你要相信自己。但这个孩子不能醒悟,还是追求羡慕基因条件很好的孩子。这似乎是成为定局的事情,好像精英人类慢慢长大,就能成为更好的人。
突然有一天,学校来了一些提着银色皮箱的穿西服的男人。所有孩子们都在猜测他们的身份。穿西服的叔叔们对孩子们做了检测,最后选到了杨桃这个小男孩,告诉他即将被非常优秀的初中所录取,还为他做专门的订制的学习和生活。所有精英的孩子和家长都不服气,因为那所初中是他们挤破脑袋都想去的。怎么想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成绩不好、各方面不好的孩子被选进去。最后谜底揭开,就是因为第一批基因改造的孩子已经出现了问题,不是身体的,而是形成了低欲望的。他们只对自己熟悉擅长的领域感兴趣,对外界的任何东西不感兴趣。如果这样的群体扩大,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低欲望的社会,没有任何生气生机。这个最开始发明基因改造的人意识到问题所在,因此决定把没被基因改造的孩子保护起来,给他最好的教育,让他自由地成长。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其实是个外星人。
这个外星人来到地球,感受到了人和人之间的温度,也得到很多帮助,感觉从来没有过的温暖。这让外星人决定帮助地球人,想把他所在星球的高科技带到地球来。结果事与愿违,背道而驰,原来这些高科技才是造成那个星球低欲望的元凶。
我对于现在科技的发展、科幻、人情、社会有一些思考。特别是现在的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就感到很大的压力,在学校里面临一些困境。造成困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想寻找根源,就做了这么一个尝试。当然现在的双减政策很好,给孩子减掉一些负担。我的作品主题也很符合现在的政策导向。
我觉得,孩子的天性就应该是回归大自然,享受、感受大自然的,而不应该所有的时间花在考试、做试卷、背诵这些事情上面。当然可以有一部分时间去做这些,但不应该把所有的业余时间放在上面。这样下去,孩子成长起来后是脱离世界的。这个作品是我对于当代教育的一些思考,把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陈: 这个故事主题很有趣, 日本早就进入了低欲望社会, 国内近年也有一股躺平思潮在网上蔓延。
邹超颖: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需要我们警惕。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不愿意结婚、生小孩,甚至也不愿意出去工作,就是宅在家里。为什么会造成这些呢?我想从最根本的地方去思考,就应该是从童年开始思考。我们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是什么?我在书里都有探索。
陈: 这个主题说起来沉重, 但以儿童的视角来看的话, 小说应该有一些啼笑皆非的好玩的故事吧?
邹: 当然有。有基因改造被失败的产品,有没有被改造的小孩,就是不一样的。我确实是深入生活,跟很多小学生聊天,发现了一些好玩的细节,在故事里有这样细节。小男孩杨桃非常喜欢画画,他不知道自己画得不好,总是问爸爸“我画得怎么样”。他爸爸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能直接说不好,就说你的画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了一定境界。杨桃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夸奖,自信满满的。
他非常喜欢美术老师,觉得美术老师的画很好,人也温柔漂亮。有天上课,美术老师抱着一个金鱼缸来到教室,金鱼缸里有一尾红色的金鱼和一尾黑色的金鱼,还有一尾桔色的金鱼。美术老师说:今天我们一起来画金鱼啊。同学们开始了。杨桃盯着鱼缸,陷入了沉思,应该怎么画呢?等到同学们交上作品,他终于想到了,画了三条线:红色的、黑色的、桔色的。美术老师问,你的金鱼在哪里?杨桃说:这不就是我的金鱼吗?美术老师说:我只看到三条线,我没看到金鱼啊。杨桃说:老师,当鱼游得非常快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看到三条线啊?美术老师想想,也是的啊。
我接触孩子,发现大人的视角和孩子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问我,你怎么一直保持一颗童心。第一,我本身就是有童心的人,也是我的天性。第二,我喜欢跟小孩接触。我经常跟我们小区的孩子玩,获得孩子的语言。有一次我在小区和小孩子踢足球,有个孩子说:“树上一颗果实,害羞了,所以成熟。”这真是诗一般的语言,让人惊喜。
我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世界,看和大人眼中不一样的世界。大人只看到眼前,看不到其他。在《不完美的男孩》这本书里,有很多这样的情节。虽然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但大人的视角慢慢活成了蚂蚁的视角,只会慢慢前进、慢慢后退,或者向左向右,很久没有仰头看天空,或者俯身看小草花儿。但小孩不一样,小孩的视角是360 度的,全方位的,这个世界每个地方都可以细腻地捕捉到。作为一个儿童文学的写作者,我需要做到的,是和孩子一样同频率地呼吸,也这样全方位地看这个世界。
陈: 最后的结尾, 谁被谁改造? 能不能剧透?
邹: 故事留下了一个悬念。当杨桃去找外星人的时候,发现一切不存在了。外星人无所不能,可能之前所有的东西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幻的。我给了一个开放性的结果。就像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也是开放性的结尾。到底如何选择,我不去定义。我的小说从来不下定义。我只是说,通过我写的故事,你能感受到什么。每个人看过故事后,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感受,对于他的人生或多少地有一点影响。
三、 把我想要的情绪反复地酝酿
陈: 文学最激荡人的心灵。 你的作品也潜移默化地改变读者的人生, 塑造读者三观。 你有没有想过, 写作是如此的神圣, 反倒让你轻易不敢下笔,或者在今后写作中要注重道德力量与责任?
邹: 这跟作家本身相关的。个体经历铸就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作家在其所有的人生经历、旅途中,有什么样的感悟,最终会诞生什么样的作品。写作是神圣的事情,但我不会刻意说太神圣不敢下笔写。就像我此前说的自我追赶:当你的意识层面到达了一定程度,你怀疑自己早期的创作。这个时候,我会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加丰富深刻,不断磨练自己的写作。我电脑里还有一些练笔作品,就是平时的训练,就是自我追赶的过程。
当我的作品超越了我的自我认识,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反倒是当我觉得我的作品写得真好,这时候是需要我要警惕的。我告诉自己,当我到了这个时候,需要去看更多的作品,去增加自己的生活阅历,而不要成为局限的人。每个人都是局限的,在固定的环境、固定的阅读量,甚至在固定的朋友圈中,我们永远是有局限的。如何打破局限呢?这是我希望去做的。我要不断地突破局限,每次作品突破一个新的自己,打破一个局限的自己。
陈: 人生也是如此, 写作只是精神自我突破的最好方式, 这比物质更加具有挑战性, 而且能够乐在其中。 现实中有很多人想要突破, 苦于无法突破就会痛苦。 你在写作中想要突破自己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是不是也会感到痛苦?
邹: 当你想要呈现某种情绪,或者说想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有味道,在这时,你写下的东西可能没有达到预期,会有痛苦。结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压箱底了,不想再见了,这是失败的,因为没有突破自己;另一种是成功的时候,我会把想要的情绪反复地酝酿,无论身处何地,无论做什么,我永远有那根情绪在我的血液中,它一直存在。我有半颗心是属于这个情绪,然后把周边的人和事融到我的血液中。比如说,我要写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也要把自己酝酿到这种情绪中,就像演员演戏一样。
作家群体是一个很奇妙的群体,他可以在广阔的人世之中生存,但又会跳脱出来。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和时候,几十人、上百人的会议或活动,总是会有好几个瞬间,我是抽离出来的,抽离到一种冷眼地冷静地看这一切。这也是我们创作中大脑的反复训练,写作是理性和感性的交织。我会有我的故事逻辑在,但我需要丰沛的情感输出,书中的人物和我是共情的。里面人物遭遇不幸,我也会落泪。这种共情的时候,人的体温是升高的、热的。但这种程度在写作中是需要控制的,不能持续太长时间。我们需要清醒地知道故事的逻辑、情绪和走向,不能被情绪带偏带走。作家的大脑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强的,感性和理性两者可以分配得很好。
陈: 你刚才谈论很好, 既有方法论, 也注入了个人体验。 作家创作, 既要抽离出来有热情, 但又不能过分地热, 这是一门平衡的艺术。 写出一个丰富的人物的内心的波澜, 是很微妙的, 不应该是线性的。 王又平老师曾提出一个观点: 作家在写人物的时候, 人物本身有设定的, 一个小人物可能是无关紧要的, 或者另一个大人物可能是傲慢的高人一等的, 作家在写这样人物的时候需要自我反省, 在创作的某个瞬间能够意识到自己作为笔下人物的主宰, 不应该被笔下人物所带走带偏, 而变得傲慢、高人一等, 那么笔下人物形象就升华了丰富了。
邹: 人是综合体,很丰富的。在设定人物时,可能想好了所有的性格和喜好及一切,但当他被放到故事中就变得不一样了。他的本质是一样的,但他会摇摆,会胆怯,再坚强的人物也会胆怯。所以,人也是矛盾的,是最复杂的,要写好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陈: 严肃文学作家非常喜欢写出人性的复杂,崇高或者卑鄙到极致。 涉及到儿童文学, 大多数作家实在不太愿意写得过于深刻、 过于冷峻。 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你写儿童文学作品时, 是否要想过避免写得特别复杂呢?
邹: 这是因为年龄层有不同。孩子由于对于世界的认识、阅读量等原因,对于太复杂的东西不太能够理解。但这也不妨碍一个作家的追求。就像美国好莱坞的动画电影一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孩子看着欢乐,比如《疯狂动画城》 《功夫熊猫》这些片子,可能会让孩子表面上看到了欢乐,看到了搞笑的商业化元素。但却有一些深意在这些搞笑的背后,这个第二个层次是给大人看的。
《儿童文学》杂志定位的读者是0—99 岁的公民。我觉得,儿童文学之前是没有单独分出门类的。之所以分呢?一是因为家长不好选择,做了区分。但儿童文学仍然是在文学的大文体范围之内。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更加深刻丰富。至于人物,儿童文学作家在写人物时,会有独特的一面,有吸引孩子的一面,或者特异功能,或能博得孩子兴趣的点。在这之外,如我刚才说的《不完美男孩》,表面上有很多符合孩子天性的内容,但后面是饱含深意的。不仅是人物,包括作品主题也是这样子。
儿童文学分为类型化小说和偏纯文学的小说。类型化小说,指文学性上没有更高的追求,只是单纯追求快餐的文化,让孩子愉悦。但有追求的写作者,文学度高的文本,在主题上、在人物上都有自己思考,它不会是扁平化的,一定是作家在写人物时,对人物小传就已了然于胸。我写作时首先会写一个人物小传。这个孩子的家庭背景、爸爸妈妈职业、从小的经历,所有这一切都影响着他现在的性格,影响着他未来会做的每件事情。可能读者在看的时候只看到这件事情或者角色的反应,但作家早已思考他为什么做这个动作,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早已经熟知。
四、 借助梦境来虚构故事
陈: 如你刚才说的, 创作前会写一个人物小传。 写人物当然是有预想的, 但在写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常发生意外, 好像不是作家自己在写, 而是笔下人物在拽着你的手在写作。 这种写作的意外, 你觉得是美好的事情, 还是打破了计划、 让你郁闷的事情?
邹: 我从19 岁出第一本小说到现在,这种意外经常发生。我写作一般是集中时间,比如说这两个月,我每天写很多,然后再休整几个月。这是我的写作习惯。在集中写作的两个月里,我就会经常做梦。在梦里,我觉得,我的小说所有的人物都出来,处于同一个天地,跟我热热闹闹地共鸣。从我写第一本书《十二生肖闯天下》开始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源于一个梦。
这本书是我在高三时候,做梦而起的。我做梦,在远古时代,洪水滔天,有一艘船似乎是诺亚方舟,上面有十二只动物和猫。奇怪的是,这个梦,我连续做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什么意思,觉得是某种召唤、启示。当时马上就要高考,我没有时间写下。到了大学一开始军训时,我有大块的空余时间。冥冥之中,我想写下这个故事。当时看到新闻说,中国的传统生肖文化,竟然被韩国、日本说成是自己的。我意气风发地萌发出一种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与念头——我要为十二生肖正名!那么怎么正名呢?我觉得时机到了。华夏民族的人们,可能改变了国籍,但唯一不变的的文化就有生肖文化。一个孩子生下来,父母会想到孩子属什么?这个生肖文化也是我们的根、中华民族的根。
这种文化源于哪里呢?我就想借助梦境来虚构故事。水是人类生命延续的重要的元素。在华夏大地,有两条母亲河长江和黄河,灌溉了这片大地。我想,这两条河可能是十二生肖寻来的。上古传说曾有十日当空、后羿射日,那时是干旱的,大地到处起火,动物无法生存,根本就没有农田,人类是无法生活的。人类需要水,去昆仑山寻到了水源,让长江黄河水脉流淌滋养我们生生不息。因此,人类为了感激这些动物,每当生下一个新生命,告诉他们属什么。不然,人类为什么要把孩子的属相安在动物身上呢?
循着这种思考,我一气呵成地写完了整个故事,25 万字。故事线索类似《西游记》,十二生肖历经各种磨难,最后达到终点。这也可教育孩子如何应对挫折,只要目标明确,不畏惧艰难险阻,总可以到达终点的。
陈: 你年少成名, 起步很高, 有没有遇到过写作瓶颈期?
邹: 肯定有。我的办法是:第一,我当时写了一系列小说,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某些小说。我却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似乎不差我这一部。我自问,是否有必要再去写?在那段时间停下笔来,完全没有写。第二,想让自己多一些人生阅历。父母对我的要求是自由的状态,但我的生活实在太单纯。一直上学,毕业又到学校,没有太多的阅历看世界,接触社会的人物。我以前喜欢邮件文字交流,特别不擅长人际。要更好地写作,我就要突破自己生活的舒适圈,走出去,到人世间去体验,跟更多的人交流、谈事情,磨炼自己。比如,我跟投资商、导演、动画片制作人员、电视台,甚至政府官员,了解形形色色的人,了解当时不太明白的事情,就当做体验丰富的生活。当然,写作是纯洁的,我不喜欢沾染其他气息。有了更多的生活体验,写作的源泉才能不断流。
五、 完全没准备, 说完下一秒钟开始编故事
陈: 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于价值观的塑造很有裨益。 你什么时候爱上写作的?
邹: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写作,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写日记。有些字不会写,就用拼音,有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初中,就开始写小说、散文,就开始发表,觉得挺光荣的。我的数学成绩不太好,数学老师又是班主任。他每周会拿一个稿费单,走到班里来说,邹超颖,你的稿费单到了。我知道,哦,我又有作品发表了。初中二三年的期间,每周都有,这对于十多岁的孩子来说是很大的鼓励。这是最开始的文学萌芽吧。
小孩子年纪越小,想象力越多彩。我可以看到任何一样东西,会产生不同的灵感。看到墙上的水渍,就会想象各种画面,在我的脑海里编织一个故事出来。看到云,看到风吹落叶,看到草的形态,看到泥土的颜色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会成为一个个好故事。回想起童年是很幸福的,我生活在这样一个个的梦幻中童话中。在现实中,我会设计游戏跟小朋友玩的,然后在几个分钟内现编一个故事出来,让小孩子去扮演去参与我的游戏。小学六年,我都反复在编故事,当然很感谢配合我的小伙伴。这应该是最初阶段的对故事创作的能力的磨炼吧。
陈: 讲故事是孩子的天性, 特别是爱幻想的女孩子。
邹: 小学春游的时候,我们要去某个地方,路途很长,很无聊。我会站起来,把某几个同学的名字合在一起,编故事,非常搞笑,充满悬念,全车的人哈哈大笑。最初的幽默,悬念的设置,这就是锻炼讲故事的能力。现在我在大学课堂上,经常会在黑板上写几个关键词,然后点五六个学生现场编织故事,即兴训练。出乎意料的灵感被激发出来的故事,大学生也都非常兴奋。
陈: 美国作家莱曼·弗兰克·鲍姆以前从来没有写过作品, 只是为孩子临时讲起了一个晚安故事,讲起了一个寻找勇气的故事, 影响了几代儿童, 这就是被誉为西方版 《西游记》 的 《绿野仙踪》。 儿童文学创作的对象很重要。 在环境中, 感受到对象对故事的渴求, 会激发你创作的热情与表达的欲望。
邹: 面对的对象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在写作时,面对电脑,在心中其实有一个大概年龄层的定位的,大概面对什么样孩子的。从叙述上来说,儿童文学以讲故事的方式,比较贴近孩子的接受方式,更加温和。
陈: 彭绪洛老师在送给我的作品上, 写了一句话: “隐居是我的梦想。” 一般作家创作可能酝酿的时间很长, 但真正写起来应该很快吧? 特别是现在电脑写作很方便。 以前用纸笔写作, 会觉得手的速度跟不上脑子的意识流。 作家都希望有一种安静的环境。
邹: 沉浸在安静的环境中,心无旁骛的状态,然后才能更加细腻地跟书中的每一草一木和每一个角色,真实地体验,但是一旦抽离,再进入,需要时间,而且反反复复,会影响书的流畅度。我喜欢集中时间写,真正写起来也就一两个月。
六、 阅读: 对卡尔维诺故事的套路了如指掌
陈: 写作过程中, 你喜欢读哪些书? 哪些作家对你产生了重要影响?
邹: 小学二三年级时,我开始读卡尔维诺,他是对我的影响很大的作家。1956 年,他花费两年的心血,搜集了近200 篇意大利各地的传统民间故事和童话,也有自己加工创作的,形成了《意大利童话故事》。这套书分上中下三册,很厚,字很小,可能七八十万字。他把民间童话和作家创作融在一起再创作,有点学者型作家特点。
我在家里书柜无意中读到卡尔维诺,就被吸引了,小学阶段每年重读。我对他故事的套路了如指掌,几乎倒背如流。后来,我又找到了他的《树上男爵》 《看不见的城市》 《被分成两半的子爵》。后面的作品有一些诡异,像毕加索的画,似乎都是意象。他永远不具体地写某一个东西,而是用某种意象去表达对社会的观点,让人捉摸不透。但他有扎实的功力,把寓言、童话、科幻元素都融入其中,用想象力去描绘世界。我觉得他最终还是关注到人物的内心的变化和成长。这是文学最本质的东西,也是我的追求。小学阶段,我还看了《格林童话》 《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童话》从故事到人物、场景、描绘,用童话的笔触去写,给予孩子一个童话和现实世界的碰撞,反映的却是现实问题。
我大学里读《小王子》,惊叹原来有这样的儿童文学,自问我能不能写?《小王子》不仅仅是人间的东西,更有对宇宙的思考、对全人类的思考,是那样的广大、广阔、灵动。像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故事层面的东西,而是饱含了太多丰富的内涵,需要博学的阅历、高深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需要生活的积淀,才可能写出来。
一个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关键在于深度到底在哪里?深度在于,孩子在最开始看的时候,是奇妙的故事,但当成年以后,领悟力更高一些,就会发现这个故事饱含深意。我经常想写某一类作品,尝试了一段,发现味道不对,就放弃了,然后寻找自己会写的,未来有机会再写。
从该语言上来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洛瑞·李的《罗西与苹果酒》对我影响也很大。不同的读者去阅读,从书上找到不一样的点。特别是《罗西与苹果酒》,散文化的语言,捕捉色彩、光影、气味都特别细腻,让人惊叹竟然可以用文字呈现。《再见,蜻蜓镇》能把江南的气味写出来,就受到《罗西与苹果酒》的启发。
我看有些书,是可以闻到一些气味的,或者辛辣的,或者下过雨后草丛清新的、潮湿的、带着花香的。好书是有气味的。我看《罗西与苹果酒》,觉得就像下过了一场雨后,山峦散发的气味。走到山中,味道是清新的,带着一点忧伤,与带着泥土的厚重气味融在一起,始终是轻盈的。我不喜欢把沉重的东西写得更沉重,喜欢化繁为简,化沉重为轻盈。再沉重的东西,它可能看起来轻盈的。当你沉淀在心中的,而不是纸面上显露的。我对保罗·柯艾略的《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印象也很深刻。写的是一种朝圣的心灵旅程,牧羊少年包含了基督教的元素,就是想追求炼金术,找到金子,但整个旅程饱含了很多哲思的东西,是需要慢慢品味的。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创作出这样作品,但还需要沉淀。
至于国内的作家,阿来的藏族风情的小说,那个气息到位。莫言、余华、贾平凹、苏童、迟子建的小说和李修文散文,我都很喜欢。
陈: 您的 《再见, 蜻蜓镇》 自带的江南气韵特别吸引人, 也让我想起日本女作家的作品 《魔女宅急便》, 虽然故事类型与风格有所不同, 但其中蕴藏着温婉俏皮成长的少女心是相通的。 我想, 你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是很深厚的。
邹: 我们跟蜻蜓,相关的体悟。你所说少女心,我是认同的。李清照也是少女心,我和她是相通的。我从小阅读唐诗宋词,《再见,蜻蜓镇》是有古典诗词的体悟。西方文学对我影响更多的是小说,而古典诗词对我的影响是综合的。我阅读古典诗词所汲取到的营养,是潜移默化,就像当年游历江南,见到某个环境,置身于此,就会发现这好像是哪几句诗词曾经写过,我只不过是重逢。
古典文学有这样的魅力,会让人感到非常静。《浮生六记》 对我影响很大,不仅是语言的清新,更有一种无言的感觉:不那么在乎世事,有助于净化自己。《小窗幽记》所表达的诗意生活,也是我的生活追求。“带雨有时种竹,关门无事锄花,拈笔闲删旧句,汲泉几试新茶。”我只要闲下来,泡点茶,画画,种花种草,非常闲适的生活。
七、 优秀的作品是连接天地宇宙
陈: 现在你在大学教书, 从事文学研究与教育工作, 你喜欢这样的状态吗? 你希望自己成为学者型的作家?
邹: 我2009 年本科毕业,曾有出版社、杂志社、电视台的工作要约,我最终选择了大学老师。我喜欢有更多的时间创作,大学是最好的选择。
我教授儿童文学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我把自己的理论知识重新梳理一遍,会有新的感受,特别是重读某个作家的作品,会有不同的感受。我跟同学们分享这些感受,他们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每个人看书的角度不一样,不再是单线的阅读,而是四五十个人的思考碰撞。最后每个人不一样的想法,不仅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而是跟自己人生阅历相关的思考角度。
至于学者型作家,我还算年轻。过早地定义自己是一种禁锢,会有焦虑,我喜欢很多种可能性。写作核心的东西是不变的,我只好好写作了,就好了。
陈: 你所期待的优秀儿童文学应该是怎样的?
邹超颖:孩子喜欢的,有很多的大人也认可的。故事迷人的。迷人这个词,就是故事的境界。语言有魅力的,风格上更加宽泛一点。每个作家都会找到自己讲述故事的风格,那时讲故事就是享受。语言风格没有对自己的限制,无法定义,只有不断尝试。我用不同的方式、语气来写同一个故事,可能是温和的、冷峻的、客观的,但是经过不断的尝试会发现,只有一种口吻是最适合的。
陈: 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是否有这样一种矛盾心态——为孩子们创造童话王国体验真善美, 同时又不能完全隔绝现实世界的真实性? 你的故事中少不了要写出现实世界的残酷, 又是如何做到哀而不伤的呢?
邹: 我的文本,残酷的东西或多或少有一些体现,会有不得不面临的残酷现实问题,但不是主基调。我的主基调是能够滋养心灵抚慰心灵,而不是产生不好的情绪的。这很重要。
比如,在我书中作为弱者的孩子,可能会害怕校园霸凌,可能默不作声。但是孩子遇到问题,都具备迎难而上的品质,用智慧化解危机的品质。处理问题不是硬碰硬,而是用智慧。用暴力尖锐的方式解决问题,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脑袋的东西是最伟大的,思想层面上的睿智是很重要的。
我通过故事告诉孩子们,孩子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比如面临父母的离异,比如喜欢的老师换掉了,总有一种解决办法。要有好的心态去面对,应是抚慰心灵的。我喜欢把这些沉重的东西化解掉。第一,针对孩子,我们需要适合他们的方式去讲述,让他们喜闻乐见。第二,让他们不那么地恐惧死亡,理解生命。作家应该具有化解的本事,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同样的故事,一个普通人讲和一个作家讲,其精彩程度不一样的。作家讲故事就是要绘声绘色,情景交融,跌宕起伏,充满着魅力。这也是作家应该具备的基本功力。
我的小说《坐彩虹滑梯的外公》就是探索生命的主题,源于我自己家庭的,引发我对于生命的思考和梦境。人失去生命后去哪儿,存在于哪里?我讲述另一个世界的内容,竟然有一些场景跟我在梦中所见的是一样的。我相信,优秀的作品是连接天地宇宙,带有这种神奇的色彩。我写完后,我看到了《天蓝色的彼岸》这本书,惊异于里面的那个世界竟然与我梦中一样。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怯懦的小女孩。她曾经跟外公约定过,如果能够成功交到三个朋友,外公给她一份礼物。但是她还没有做到,外公就去世了。她不愿意相信。这个外公去世了,是如何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在反复的揣摩。
有一天,当她拧开水管,在花园浇花的时候,出现一道彩虹,外公来到身边。她爬到树上,发现树叶上滚动的露珠,散发出七彩光,外公来到身边。我希望让孩子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生命。这种相遇,相当于小女孩与外公的另一种形式的告别吧。其实,也涉及到孩子成长与父母的和解问题。
其实,她的父母是不理解这个孩子的,因为太繁忙,根本没有时间静下心听她讲奇怪的感受。当她回到房里,打开妈妈的电脑,发现妈妈正在创作漫画,标题——坐彩虹滑滑梯的外公,正是是她之前在花园的奇特经历。问题是,到底是她看到漫画之后所想象的,还是她真实所遇到的呢?她真的跟外公见面了吗?她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也不相信是受到妈妈漫画的影响。
最后,是否外公真的存在?我不愿意也没有揭开谜底,希望引导孩子发散的联想。面临生命离别是一个很残忍的过程,我希望留下更多的思考空间,思考一个短短的几十年生命,在时间河流所必经的过程,才会更懂得珍惜。我觉得,这样的思考对孩子成长是有帮助的。
八、 小说的创作空间更大一些, 可以上天入地
陈: 这些年, 你也有不少影视作品呈现, 比如《黄帝史诗》 《东方七色花》 《班主任》 《猪猪侠之恐龙日记》 《秦天龙王子》 等, 在全球院线及中央少儿频道等各大电视台都有播出。 你在创作中,觉得编剧和小说有怎样的异同?
邹: 编剧是多人的劳动,从策划开始,不是作家一个人完成的。在选题阶段,有制片人、投资商、导演、作家等共同参与的讨论会,最后定下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作家根据导演的意思再次创作和修改,最终作品是多人思考碰撞结合的产物。
剧本是视听语言,不仅仅是文本能够感受到的故事。剧本所特有的叙述方式,有自身规律在,与小说创作有很大的不同。剧本对白的叙述语言,没有小说要求那么高。小说的创作空间其实更大一些,可以上天入地。但是剧本有荧幕的限制。于我而言,写小说更自由,小说只是一个人的产物,就是自己的小孩。最后完成成形,都是一个人的所思所想。
另外,两种创作受到纸背之外的东西的影响因素也不同。编剧的剧本最终要在影院呈现,一个电影作品在90 分内完成对观众大脑皮层的刺激,观众在哪个地方哭或笑,需要在90 分钟内完成,也需要对于受众的大数据的把握进行创作。但是,小说不需要,小说故事不需要90 分钟看完,可以是长线的,每个年龄段看有不同的感悟。
陈: 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被商业化传播?
邹: 我没有想过迎合读者市场,不想这个问题,也无法控制的。当然文学作品被运作商业化后,影响力是比较大的。其实,扩大点来说,传播多元化无伤大雅都可以接受。毕竟生活在这个时代,文本有各种各样的呈现方式,影视、广播、语音等。至于网络文学的创作与阅读,也是另外形式载体的呈现。我们一直在提倡全民阅读。无论那种形式的阅读,都是美好的事情,值得更多的人做。
陈: 你怎么看待中国的影视市场? 特别是如何看待动画影视作品?
邹: 有些类型化的小说,充满孩子喜欢的故事元素,让孩子如痴如醉,不过是对孩子大脑的一种刺激,但文学价值不大,无法说有多大价值留存于世。
同样,国内有些电影烂片让观众不满意,说到底是因为创作者在迎合市场。有人批评观众水平就是这样的,我不太赞同这种观点。作为一个文学或者影视作品,首先是能够启迪引领人的作用。作为受众,当我不懂不会时,看了这个作品,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从你的电影故事收获到新东西。作为创作者,我不是站到这个低姿态去迎合市场,而是贴近你,产生共鸣,讲出你的生活。我有更深刻的东西,你不曾了解的东西,我想对未知的东西有探索,而不是对已知的简单重温,自然能够吸引你。
看看国外的好片子,比如宫崎骏的动画片,你刚刚提到的《魔女宅急便》,都是我喜欢的。还有好莱坞的《飞屋环游记》 《玩具总动员》 《疯狂动物城》,细节处理得很好,属于合家欢类型的电影。在细节处置上,外国编剧的思维模式跟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很容易跳脱出来,很多细节是观众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你都看得懂。几个场景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串在一起,故事是连贯的完整的。细节可以让你啼笑皆非,也可以让你泪流满面。这是非常高明的地方。影视作品来源于生活,也要有对生活的深度理解,才能产出笑料。那些笑料或笑话不是浮于表面,而是有深度理解的。
近几年, 《哪吒》 《大鱼海棠》 《大圣归来》等中国影视作品是国风国漫崛起的产物,都运用了我们熟悉的ip,特别是古典的耳熟能详的角色进行了一些创新,符合当代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的审美趣味。我觉得有一定价值。这些电影票房大卖,商业化的成功,可以去振奋士气,扬眉吐气。中国的动漫暂不说超越国外,但能得到一定的认可,其实是所有的动画制作人的期待。每个行业都这样。动画制作人是很苦的,如果不热爱,是很难坚持的。很多动画人几年都在亏损,好不容易完成一个好作品,值得我们关注。每个能够坚守岗位上做这项事业的动画制作人,值得赞美。我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中国的动画的成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