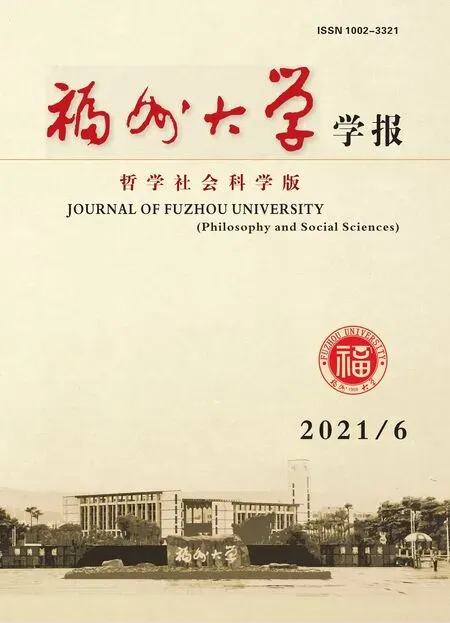晚清《新小说》追求“新国”与“新民”之研究
2022-01-27林娟
林 娟
(闽江学院人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近代中国的建立,经历了从古代“天下”“生民”转型成现代“国家”“国民”的过程。而在此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是大量传播媒介的产生,例如报刊杂志、新式学校与学会。其中报刊杂志方面的影响,特别重要——自1895年之后,报刊杂志创刊的数量一直快速增长,短短3年之间,就有60家报刊杂志诞生。[1]这些报刊杂志并非以谋利为目的,它的读者对象设定是中上阶层的智识阶级,其内容关注中国的国家大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亡国危机,并传播民族主义的信念,成为传播新思潮与新知识的重要媒介,推动着国家发展的新契机。也正是在办报救国的热潮之下,《新小说》应运而生。
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创刊于日本横滨,杂志中载明的编辑兼发行者虽为赵毓林,但实际的创办人与精神领袖却是梁启超。[2]《新小说》预定每月发行1回,1年 12号,第1卷(共12期)由新小说社发行,印刷所是“新民丛报活版部”。1905年1月之后,《新小说》迁移到上海,改由广智书局发行第2卷(共12期),第3卷以后往往无法如期发行,一直到最后一号发行之时,并无出版日号,一般估算为1906年1月。因此,《新小说》从1902年创刊到1906年1月停刊为止,发行期为4年,共发行2卷 24号。[3]本文即以此为研究对象,探讨《新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与对近代中国“国家”与“国民”性格的构建。
一、《新小说》的重要性
(一)有别于传统的“新”小说
《新小说》在创办之初便明确地揭橥其目的——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揭橥“小说界革命”的大旗,主张以小说作为传播新内容与新思想的工具,介绍西方政治与社会等各种改革思想来开启民智,并期待培养出拥有新德性,可与世界各国竞争的国民。[4]因此新小说之“新”,事实上包含了以下三层涵义。
首先,《新小说》之“新”作为动词,意指“革新”。“新小说”即指革新小说自身,亦即进行“小说界之革命”,以成为新的小说。其次,代表社会对于小说观念的普遍转变与“更新”。小说在传统中往往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如今却要成为“文学之最上乘”,成为启发民智的重要工具;[5]最后,指的是“创新”。《新小说》中的内容包含了政治小说、科学小说、法律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等(见表1),其对新知识新思潮的追求正是其与传统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而《新小说》所追求的新知识新思潮的具体内容为何呢?大抵来说,是由小说提供典范性的人物,让读者瞻仰模仿他们的性格与作为,并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读者学习与认识各种与国家兴亡相关联的政治思潮、社会现况,乃至国民在新时代中所应具备的新道德,从而建立一个有别于传统的“新”的中国。

表1 《新小说》载文及门类
(二)《新小说》在晚清文学史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研究晚清小说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新小说》是中国小说从传统到现代的重要分水岭,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6]其重要的价值与影响展现在:1.由于《新小说》的社会启蒙意义,使小说在晚清时期成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不但提高了小说在文学界的位置,成为最当时最受读者重视的文类,也使得小说家的地位有所提升;[7]2.其小说功用论,《新小说》所宣扬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以及对小说功用的讨论,成为晚清至民初小说理论的主流论述,开启讨论小说理论的先河;[8]3.《新小说》创刊后,影响了小说杂志的繁荣发展。根据陈平原的统计,自1902 年至1917年为止,新成立的文艺期刊有57种,以“小说”为名的杂志有29种,著名的期刊如《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都在其中。[9]而随着《新小说》创刊,小说地位逐渐提高,文学杂志蓬勃发展,使得《新小说》被誉为晚清四大小说期刊之首。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新小说》以小说引进西方新思想以培养“新民”的各种德性,所开创出来的“新的小说传统”。虽然“文以载道”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主张,《新小说》对“新国”与“新民”的强调看似并不稀奇。但梁启超的《小说宣言》却将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提升至中心地位,并成为承载西方新知识与思潮的载体,这却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10]至此,《新小说》在传统文学中转型至现代文学的过程中,占据了枢纽的位置。
二、《新小说》对“新民”的追求
“新民”这个词语,最早出自儒家经典《大学》,其代表着道德修养与对人的革新。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因受到了福泽谕吉(1835-1901)、中村正直(1832-1891)等人的影响,使得梁启超的“新民”已经超越传统的“新民”概念——他提出的是一套新的人民理想道德,以及与之相呼应的社会价值观;而这套道德是围绕着以“群”为核心来开展。[11]据此,梁启超所说的“新民”不仅仅具备的传统“新民”中所具备的“人的革新”之义,更重要的是还具备了“新的公民”此现代“国民”之义。而如何从传统的“生民”转变成现代之“新民”——国民呢?梁启超在《新小说》中标举了几项新民必须具备的新观念,现将其阐释如下。
(一)新的科学观念
为了推广新科学观念,《新小说》杂志中安排了科学小说这一门类。梁启超对于科学小说的构想,便是希望藉由各种机器事物的介绍,以教育读者科学新知。在《水底渡节》中,就有许多新科技名词的解释,如汽油引擎、四轮汽车、电瓶、拖驳船等,例如译者在原注中写着:
按引擎(Engine)乃机器之主动者也。其所以能运动,则端赖蒸汽之力尔。惟向之蒸汽,一皆取于煤,故锅炉愈大,蒸汽愈足,马力愈巨,而……近今上海等处,道路往来之自行四轮车,亦用汽油运动,俗呼电气车者盖误。至其详细功用,余别有译篇以明之。[12]
由上文可知,译者不但对汽油引擎与蒸汽引擎做了详细的说明,还对其功用、效果的差异做了详细的批注,为的就是带给读者科学常识。
除此之外,还通过小说主角彼此问答,来传递西方的新科学知识。例如,在《海底旅行》中,最主要的科学发明是一部超越当时科技的潜水艇“内支士”,它在海面上具有飞快的速度,可以快速沉到太平洋的底部,船身内部还有图书馆、起居室、收藏室,可以透过机身玻璃看见海底的惊奇世界,这在当时是最高科技。潜艇内部有许多航海仪器,即便是当时欧洲最有学问的法国博物院长欧露世到访,也令他眼花缭乱,船长李梦便向他解释:
这是在海底用的罗盘,那是测量海水深浅表,这又是寒暑表,还有测空气压力表、风雨针、经纬仪、测量海平线昼夜镜……[13]
而关于人们在潜水艇封闭的空间中,是如何取得氧气呢?主角法国博物院长欧露世又代读者提问:
但凡一个人会生活的原故,全仗着空气中的养气呼入,吐出炭气,内外流通,息息不已……但这船换气之法,不知怎样或用化学排炭气制成养气,还是像那海里大鱼浮上海面吸满仍复沉下呢?……起来满房一看,见房门铁板上,通着一条铁管,空气正从管中灌入……[14]
正是藉由欧露世的疑问,告知读者更多的科学知识:原来人可以活着,就是因为吸入养气(氧气)排放炭气(二氧化碳)的关系。
最后,最重要的是,若将《新小说》中的科学小说与道光时期的小说《荡寇志》相比较,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在《荡寇志》中,不管在书中发明的事物有多么新奇刺激,读者都会惊讶地发现,这些新发明都会在中国古籍中找到根据,原来那些都是旧有的东西的改变。[15]而在《新小说》的科学小说中,这些器物的发明是完全与中国传统无关的。这表明《新小说》是有意识地否定道光以来“西学中源说”,而采取一种西方横向移植的新的科学观念,希望以此建立新的科学观。
(二)新的法律观念
除了新科学观念外,《新小说》还利用了法律小说对中西司法进行对比,藉此突显晚清司法的弊端,充满了强调阶级的差别与重法酷刑,地方县官的判案具有刑讯的权力与贪污的弊病。例如《新小说》刊载的《九命奇冤》中,主要描写的就是当时中国司法制度的黑暗以及审判的不公。在贿赂官员方面,《九命奇冤》便对凶嫌简勒贿赂肇庆府上下做了深刻的描写:
勒先取了十二万出来……次日早晨,便明目张胆的,把那雪白的银子,抬到知府衙门里去。连太守的黑眼珠子,看见了那堆积如山的白银子,哪还顾得什么厉害……到得肇庆时,连太守含含糊糊问了两堂,贵兴等众人,尽翻前供,连太守便把一干人犯进行释放,倒把天来收押起来,要办他诬告。[16]
在衙役私设规费、狐假虎威,以及刑求、严刑逼供方面则分别有:
……随手取了二百两银子,拿了出来,交与陈德。陈德双手接过,连忙道谢,心中暗想:“原来是个雏儿,倒是个好主顾。将来这案,一堂不结,未免再翻些花样,赚他几个用用。如果这案子迁延下去,好处还多呢!此刻乐得作个人情。”[17]
焦臬司喝道:“看你这鹰头鼠眼,必非善类,不动大刑,你如何肯供。”……只夹得张凤眼中火光迸裂,耳内雷鼓乱鸣,从脚篐拐上,一直痛上心脾……可怜张凤回答的一句话,那没有说得完,便大叫一声,大小便一齐迸出,死在夹棍之下。[18]
而为了与当时中国司法的黑暗面进行对照,《新小说》中的《宜春苑》则以法国为背景,提出“新民”所应具备的新法律观念。
首先,新民应该熟悉法律条文,或者通过律师,从刑法的规则中找到有利自己的法律。万万不能做出行贿之事。通过《宜春苑》柯万宜律师之口,《新小说》向读者警告行贿的严重后果:
法国刑法第百七十九条,注明受贿的官吏,与行贿的人,不分首从,一律治罪,你就犯了这条法律了。[19]
其次,是对证据的看重。在《宜春苑》中,一再地强调证据是判案的最重要的依据,只有根据证据来推理案情,才是符合科学的方法。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年轻气盛的预审法官阿宾根据疯子黄升的证言,疑心杀人放火的就是年轻贵族何士兰。但是根据一个心智不健全的傻子的话,终究不是有力的凭证。因此只能通过物证,进行案情的推理:
这件东西原来就是弹筒,筒上刻着克列公司专卖六个字……巴尔逊村邻近十里,除何士兰以外,却没有别人能用的……这个弹筒,无疑是何士兰打伯爵的枪,二发中之一了。阿宾心中,暗喜有了头绪。[20]
而要是证据可以证明这个人有罪,即便他的表面德行是圣人、身份是贵族,那他还是有罪。这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
何君是个正直的人,我向来晓得,也很敬重他。总是空说他是正直,做不得证据。若判事查出真实的证据,就令正直的人,也要定案。[21]
综上所述,《新小说》通过小说进行中西司法的对比,进而指出“熟悉法律条文与自身权益”“强调证据”“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应该是每位新民都必须具备的法律常识。
(三)新的女权观念
在《新小说》中探讨女权思想的小说主要有《东欧女侠传》《黄绣球》两部,另外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有部分谈到。这几部小说所展现的女权思想大致上有以下几点。
第一,废缠足思想。颐琐在《黄绣球》中认为,女人要与男人同样会做事,第一件事即是放足。她说:
想道要做事,先要能走路,要走路,先要放了这双臭脚。如今这脚底下缠了几十层的布条,垫了两三吋的木头,慢说要与男子一同做事,就是走路,也不能同男子大摇大摆,这便如何使得,所以就急忙忙关起房门,要去放那双脚。[22]
第二,兴办女学。设女学不但因为妇女本身要有知识,也要利用这些女学生将课堂所学的知识,教给别人,以负起启蒙群众的工作。颐琐在《黄绣球》中提及:
名为教女小孩子,实则连男孩子,并不论男女老少,都看了有益。算得见个普通社会的教科书。外面地方,闻风继起,或是照样编起来,或是来借刷我的稿子,就从我这五十名女小孩子,教出五百名、五千名,乃至四万万同胞,多得了影响。[23]
第三,面对过去压制妇女的传统观念时,采取重新诠释的态度。例如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对于古训“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作出了新诠释:
向来读书人都解错,怪不得伯母那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并不是泛指一句话。他说的是治家之道,政分内外。阃以内之政,女子主之;阃以外之政,男子主之。所以女子指挥家人做事,不过是阃以内之事,至于阃以外之事,就有男子主政,用不着女子说话了。这就叫内言不出于阃。[24]
第四,女权必须打倒父权与君权的双重压制。《新小说》强调打倒君权,以救国为己任,却刻意减少了对男女平等权问题的讨论。例如岭南羽衣便在《东欧女侠传》提及:
强权盛行,平等权自然是没有了。所以君主便压制百姓,贵族便压制平民,男子便压制妇女,压制久了,便作奴隶也彀不上,哪里就会变出个英雄来……我们女儿现在是受两重压制的,先要把第一重大敌打退,才能讲到第二重。[25]
换句话说,《新小说》中所提倡的妇女觉醒,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新国”,而并非为了女子自身——这种方式觉醒的妇女,她们时兴谈论西学,较少谈及中国古典。她们争着作英雄,以男性英雄为楷模,将无数的小我投注进制造未来新中国的大火炉燃烧,而这些其实都是男性维新志士的想法。
三、《新小说》对“新国”的追求
国家思想的灌输,是《新小说》的宗旨,也是“新民”的核心道德,在新小说创作内容中,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对专制制度的批判
在20世纪初,相较于清朝衰弱的国势,同时代的英、法、俄皆是世界强国。因此《新小说》希望当时的国人能借鉴这些国家的历史,以批判君主专制制度,进而谋求新的建设中国的方案。例如《回天绮谈》主要是在叙述英国人订立《大宪章》(Magna Carta, 1215年)的历史过程,通过英雄卡尔利巴的主张:“政府的政权是由人民委托与他的。政府办不妥当,我等人民拿回自己办去,本是天公地道。”[26]给读者一个很强烈的暗示:英国早在六百年前率先实行立宪,所以才会在20世纪称霸,而这个改革是人民以武力强迫国王实行的。
《洪水祸》以“洪水”为名,主要就是以洪水为喻,说明民主浪潮犹如洪水,无法阻挡,君主专制最终将被推翻。[27]《东欧女豪杰》则通过女配角莪弥之口指出:“俄国是个金字招牌天下闻名的野蛮专制国。”[28]最后,梁启超则在《新中国未来记》中,通过主角李去病赤裸裸地批评中国的专制制度,他说:
那十九世纪欧洲民政的风潮,现在已经吹到中国,但是稍稍识得时务的人,都知道专制制体是一件悖逆的罪恶。[29]
(二)新中国的建设蓝图
如何使中国从传统的“天下”走入现代的“国家”一直是梁启超最关心的议题之一,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所提出的建设蓝图,便是藉由一个可以控制国家各种政治资源的政党来领导,以建立一个具有高度集中政治权力的新中国。他通过孔博士之口,倡议必须建立“立宪期成同盟党”以做为建设未来新中国的基础。孔博士说:
我们新中国的基础,在哪一件事呢?……前六十年所创的“立宪期成同盟党”,算是一桩最重大的了……诸君当知,一国的政治改革,非藉党会之力不能。这宪政党为前此一切民会之结束,又为后此一切政党之先河。若没有这党,恐怕中国万不能成分治统一之大业。[30]
而立宪期成同盟党的建国策略则具体落实为“治事条略”,其共分为八大事项,其总纲要求其党员必须尽力完成,并至少需承担一项以上的义务。第一个目标是,要“扩张党势”,而且需列为“第一重要任务”;第二项目标则是 “教育国民”,通过撰写新式教科书将“臣民”改造成“国民”,让这些“黎首”具有国家意识,并愿意为国家牺牲;第三是“振兴工商”,主张发展商业以利与外国竞争,同时在发展隶属于政党之下的“商会”,以求蓬勃发展各种资源与各类型商务活动;第四,充分“调查国情”,宪政党还是一手包揽,调查全国资源,使得国民有所了解,方便利用;第五,国民必须“练习政务”,党员们应该回到其家乡,参与地方自治的活动,通过两党相互竞争的国会形态,讨论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问题;第六是“养成义勇”,以党领校,通过实施军国民教育改造国民,让人民明白保卫国家是国民的责任;第七是“博备外交”,宪政党必须派遣党员进驻各国,结交权贵,以获取将来取得政权之外交势力;第八是“编纂法典”,中国缺乏现代国家的法律,例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31]等。因此必须编纂一套必须符合宪政党意志的法典。
综上所述,《新小说》所追求的“新国”,首先必须经过一个高度集中权力的政党来管理几乎所有的国家大事,亦即“以党领国”。直到人民皆成为了“新民”,同时宪政党也成功治理中国后,便可开始走向两党制的政党政治,这时也就意味着“新国”建设完成。而从这样的论述中明显可以发现,“新民”的意义主要还是为了构建“新国”,其开民智其实还是第二位的。据此,可以说《新小说》虽然想通过对西方的仿效来改造中国,但其真正追求的,其实还是“国家至上”而并非“人民为主”。因此《新小说》追求“新民”与“新国”的努力,最终却仍然是非西方的。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研究得出结论。首先,《新小说》所具备的社会启蒙意义,不但使小说摆脱了传统“不入流”之地位,成为了晚清时期的“文学最上乘”,更成为了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分水岭。其次,《新小说》所追求的新思想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新小说”,一是“新民”,一是“新国”;而前者是后两者的手段,后两者则是前者的目的。换句话说,《新小说》认为要有强大的新中国之前,必先要有新国民,而新国民的产生又要有新道德——也就是改造国民性的工程。因此《新小说》对“新民”的追求,诸如其对“新科学观念”“新法律观”以及“新女权观”等新观念的倡导与推广,基本上还是为了服膺梁启超心中理想的建国方略而设。据此,可以说《新小说》真正追求的,还是以“国家至上”而并非以“人民为主”的中国。故而《新小说》虽然想通过仿效西方,构建具备现代意义“新民”与“新国”,但其所做的努力,最终却仍然是非西方的。
注释:
[1] 张 灏:《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见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台北:南天书局,1987年,第370页。
[2][15] 孙文光:《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1840-1919)》,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935,726页。
[3] 林明德:《梁启超与〈新小说〉》,见《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5年,第78页。
[4] 陈俊启:《重估梁启超小说观及其在小说史上的意义》,《汉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1期。
[5] 黄 霖:《二十世纪起步的是与非——以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为中心》,《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台湾)》2000年第3期。
[6][9]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卷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0页。
[7] 阿 英:《晚清小说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页。
[8] 黄锦珠:《“小说界革命”与小说观念之转变》,《晚清时期小说观念之转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第65-145页。
[10]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11]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第73-82页。
[12] 上海新庵译述:《水底渡节》,见赵毓林:《新小说》2卷6号,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0年,第67页。
[13][14] [英]萧鲁士:《海底旅行》,南海卢藉东意译,见赵毓林:《新小说》1卷2号,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0年,第106,86-87页。
[16][17][18] 岭南将叟(吴趼人)重编:《九命奇冤》,见赵毓林:《新小说》2卷8号,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0年,第89,77-79,99-100页。
[19][20][21] 无歆羡斋译:《宜春苑》,见赵毓林:《新小说》1卷8号,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0年,第81,16-17,58页。
[22][23] 颐 琐:《黄绣球》,见赵毓林:《新小说》2卷3号,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0年,第113-114,111-112页。
[24] 我佛山人(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见赵毓林:《新小说》2卷5号,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0年,第25页。
[25][28] 岭南羽衣女士:《东欧女豪杰》,赵毓林:《新小说》1卷1号,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0年,第33,41页。
[26] 玉瑟斋主人:《回天绮谈》,见赵毓林:《新小说》1卷4号,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0年,第53页。
[27] 雨尘子:《洪水祸》,见赵毓林:《新小说》1卷1号,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0年,第13页。
[29][30][31] 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见赵毓林:《新小说》1卷2号,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0年,第40,60,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