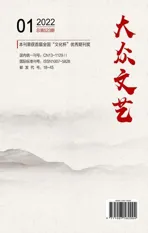刀锋下的追诉
——解放区木刻*
2022-01-24姜建勋
姜建勋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300)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解放区木刻给了我们鲜明的回答与印证。
解放区木刻兴发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成长于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的战场,是中国版画家在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的领导下,心怀救国济世的崇高理想,以艺术的刀锋积极参与到社会变革的艺术活动,真实记录了解放区军民不畏生死浴血奋战的战斗场景和边区人民翻身做主的生活新貌,书写出解放区不朽的历史画卷。
研究解放区木刻,通过对图像学的解读,真实还原出解放区军民抗战、生活的场景,是了解解放区历史、解放区文艺的窗口,是研究抗战文艺的真实史料。
研究解放区木刻,挖掘出内蕴其中的人性精神,是对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际,为拯救垂危的民族同人们一道敢于抗争、不畏牺牲的由衷赞叹;是对版画家心系天下之危而艺术救国、文艺济世的由衷敬佩;是对中华民族人性精神的深度追诉和高度褒扬。
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新社会主义文化是新时代赋予文艺创作的时代命题,版画如何符合时代之需,广大版画工作者如何紧贴时代之脉,创作出弘扬民族精神、符合时代特质的文艺精品?解放区木刻无疑是一种鲜活的参照。
一、民族呼声与木刻的革命
20世纪初,中国从坎坷多难中走来,跌宕起伏的政坛风云,交织杂糅的社会矛盾,使中国进入一个千般纠结、万般无奈的年代。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让“旧体”与“新政”走到了历史终点,但久病成疾的中国并没有走出内忧外患的危机,中华大地依然在阴霾的笼罩下悲锵泣语,民众则陷于水火。此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心怀救国济世的崇高理想,以“天下兴亡”的责任担当,举目向外,寻找解天下之忧的济世良方,从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对外学习的文化启蒙,让民主与科学的光芒照亮了封建主义的沼泽,指引出中国前进的道路。
美术从来都是人类精神的书写者,在社会形态中或直言或隐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美术在内外形式上发生了深刻变革,沉迷自我意趣的旧画被精神狂热富有现实主义关怀的新画所取代,绘画西学在知识分子的呐喊下登然入世。1931年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的倡导下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新芽”,在坎坷多艰的旅途中成长壮大。“它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武器而存在”
解放区木刻作为新兴木刻的延续,其画家一部分是新兴木刻的代表人物,体现着左翼文化的进步精神和艺术思潮,他们积极响应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以延安鲁艺为阵地进行版画创作,创作出《延安群众大会》(胡一川)、《延安各界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大会》(江丰)、《走向自由之一:简直不能留下一粒谷种》(古元)、《延安鲁艺校景》(力群)、《彭德怀将军在前线》(彦涵)等木刻作品,体现出解放区木刻直面社会创作理念和以文艺代武器的文艺宗旨和革命旗帜。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路线,回答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问题。明确指出文艺工作的政治高度和政治规约,把党的文艺工作作为整个革命工作的有机体,成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进一步深化了解放区木刻的价值导向,成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开展文艺创作的政治标准和实践方向,在美术方面创作出《减租会》(古元)、《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彦涵)、《给老百姓修纺车》(力群)、《夺回我们的牛羊》(沃渣)等木刻作品,形成了木刻创作的高潮,使解放区木刻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文化阵地,为民族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新中国美术发展的源头。
二、解放区木刻所形成的历史意义
解放区木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文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和社会意义。
(一)民族救亡与爱国主义的高扬
是什么让知识青年忘记自身的安危,义无反顾地奔向心中的圣地——延安?是什么让左翼木刻家在战争的欲火中重塑木刻精神,同抗战军民一道并肩战斗,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干部?一幅幅记录军民抗战的木刻图画给予了响亮的回答:是伟大而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解放区木刻是版画家秉承美术救国的文艺思潮,心怀投身革命以身报国的革命信念,以高尚的品格和人生信仰,用艺术的刀锋展开抗战救亡的斗争;是版画家从国运出发、以文化对社会的高度自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行为;是版画家站在民族救亡的制高点,以百姓的福祉为关切、以直击心地的力量,发出为人类自由而战的呐喊,向世界宣言中国民众抗争的决心和意志。
解放区木刻体现了版画家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高尚的爱国情怀,大义担当的使命精神;体现了版画家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在外敌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以民族大义为上,空前团结,万众一心,不畏牺牲、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体现了版画家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并肩抗战,自觉服从于党的文艺方针的使命意识。他们无不胸怀国家、兼济天下、心系苍生,甚至是为了家国理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我们矗立起了一道道广为传颂的精神丰碑。
解放区木刻抒发出中华民族人性不屈的精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幅幅生动鲜活的木刻画面,真实记录了中国军民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革命意志,以抗战到底的精神彰显出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革命气概,谱写出一部波澜壮阔抗战画卷,其意义之重,堪比泰山。
(二)现实主义创作观和民族话语的确立
解放区木刻为中国主题性绘画创作提供了学习典范。解放区木刻在主体价值追诉的同时,一场由内而外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针对文艺创作出现的问题,解放区木刻从实际出发,以革命的客观需求和现实情况来决定创作的动因和内容,从意识形态上扭转了画家以自我兴趣为主导的创作思路。解放区广大美术工作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入生活、扎根边区、以广大群众为基础展开木刻创作,用生动翔实的画面表现出解放区军民真实的抗战斗争和生活状态,用真切朴实的图像拉近了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确立起现实主义的创作观。
解放区木刻以人民群众为创作源泉,将边区军民的抗战、生活和美术创作有机结合,创作出《重建》(李少言)、《学习文化》(戚单)、《抢粮斗争》(彦涵)等版画作品,体现了一代版画人的责任意识、群体意识、服务意识,其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不容忽视。
让木刻艺术融入民间生活,转变解放区木刻孤芳自赏的局面,成为人民的艺术。解放区木刻受西方版画的影响,对西方造型语言的模仿从1931年一直发展到解放区木刻时期,自然有着表现主义的影子,如胡一川1932年创作的《到前线去》,该作品在整体风格的搭建上如人物造型语言、画面结构形式、色调关系搭配、刀法语言运用上都明显呈现西方表现主义绘画的图式风格。再者,古元1939年创作的《走向自由之一(简直不能留下一粒谷种)》,与珂勒惠支1919年创作的《纪念逝者-悼念卡尔•李卜克内西之死》,两张作品的图式语言的类比中可以得出明晰的答案。这种建立于外来文化基因的版画语言,在当时的中国有小众的受众群,颇受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喜爱,但落脚到黄土地,却遇到了“水土不适”。在解放区木刻初期,版画因群众审美意识和文化水平的差异而不被欣赏,感觉这种黑白语言的穿插置换和人物造型毫无美感,即使画面内容是身边之景,也因画面语言而变得无端揣摩。解放区木刻成了“自说自话”的艺术。
“如何让文艺更好地为人们服务”成为现实的问题。“木刻工作者既然以人们的意志为意志,那么今天的工作方向,自然也应以人民的需求为方向。”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展开文艺座谈会,本着研究文艺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关系,讲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针,指出了文艺工作的普及性和现实工作中存在的偏颇。会后解放区木刻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走向“人民语言”的探索,在作品的表现语言、审美风格上以民间绘画的借鉴、吸收来排除外来样式及“表现主义”的影子。《离婚诉》是古元表现同一主题的两张作品,分别完成于1940年和1942年,在两张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木刻表现语言的变化,如1942年创作的《离婚诉》画面中的黑白分布清晰明朗、以白为主,在人物关系的塑造上抛弃了西方造型中惯用的光线,由阳刻语言取代阴刻语言,引入中国画中的线性表达,并把烦琐的细节刻画归纳为一种简洁洗练的整体关系,截然有别于1940年创作的《离婚诉》。夏风,1947年创作的《夏锄》则是完全取法民间剪纸,画面以线为主,人物造型整体简洁,局部夸张,抛除了光影、体面的造型因素,呈现出装饰色彩。再者解放区木刻在画面构图上的处理,以平叙语言的方式展开情节化、故事化的描绘,似同连环画的形式,如古元1943年创作的《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彦涵1944年创作的《移民到陕北》等都在画面形式、画面语言、画面风格上作出了积极的民族化风格的尝试。在风格演化的过程中,解放区木刻并不是对西方造型语言的完全割舍,而是洋为中用、中西语言的杂糅与结合,亦如江丰所说:“版画民族化、并不是把外来技法排除于木刻之外”以保持艺术风格的多元化和丰富性。解放区木刻风格民族化的转向,是个人审美自由服从于集体意志的规约,在这个过程中走向民间,在历史的规约下取得了成功,并影响了新中国美术的走向。
解放区木刻以平实的绘画语言,成功践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斗争服务的要求,为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提供了典范,其富有时代内涵的作品,开创了中国美术工作的新纪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时代意义为近现代艺术史所罕见。
三、版画的超越和时代传承
(一)版画的超越
中国版画总是在时代中不断发展、不断超越。新中国成立前版画以激进的姿态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版画拓宽了版种门类,走上了正规化的学科之建,时代的抒情性改变了过去战风猎猎的画面气息;改革开放后,版画走向了多维发展,探索画面语言、强调画面图式和个体审美观的表达成为版画创作的重要议题,版画进入以学院为主导的创作阶段,突出表现在版画家对画面本体语言的探索,如个性化图式的表达、对形式语言的推崇,平凹凸漏物性原理加之肌理表现,使版画语言愈加新锐、风格更趋多样,打破了以往阐说事理的叙事表达和图式结构,图像的叙事性、风情性转变为一种观念性表达为主导的图式重构,创作出《生命之树》(苏新平)、《惊弓之鸟》(杨宏伟)、《平原上的舞蹈》(张敏杰)、《山水清梦》(方利敏)、《灰坑—文化第一层》(杨锋)等版画精品。
版画现代语权的探索与确立,增强了版画的创作活力,如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东方学与西方流派的交融、地域美学与国际性话语的混构,使版画呈现出当代多元的画面语言和文化语境,丰富了版画的画面形态,突破了以说敎、唯美为主导的文化纬度,使人性的精神之光渗入自然主义的创作法则,版画作品呈现出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状态。
(二)时代传承
当下,版画迎来了新的机遇期,在众多纷杂的版画作品中,从当代版画多元的文化格局中,我们能够以清晰的思维辨析出版画以时代性、社会性为基础的创作导向,版画现实主义的主题性架构依然融汇于作品的形式之内,使版画作品的灵魂得到有声的“呐喊”和褒扬。这是版画自新兴木刻以来,一贯保持“为人生而艺术”的底色,是解放区木刻现实主义创作观的时代传承,是版画即民族救亡、民族解放后,其创作走向民族复兴的时代选择。
新时代,当代版画家紧随时代发展,以人民群众为创作之基,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塑造人民文艺的价值导向。人民文艺的创作导向是版画家以人民为主体,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并以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和深沉体察为基础,进行个体美学的精神阐述和艺术再造。它紧贴时代之脉,洞察当今社会生活的现状,即有对人类生存现状的批评(比如环境问题)又有对人性光辉的发掘和赞美,并形成“大众化”为主体的创作美学,实现了作品的本体超越,塑造出具有时代品格的版画之作。
新时代,当代版画家坚定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从民族遗产中学习融合,从传统到民间,以民族复活,艺术复活,为生机,使它不断的茁壮、蕃息使中国版画成长为具有民族话语和民族气派的文艺精品,让东方美学熔铸东方精神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新时代,当代版画家把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体现了版画家从新兴木刻以来始终如一的家国情怀。一副副描绘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画面,一幅幅展现人民幸福生活的木刻图像,从心底折射出版画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伟大成就的由衷赞美和高度褒扬。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创作导向,体现了版画家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后幸福生活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向往,由此焕发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是自解放区木刻以来高扬至今的爱国主义旗帜。在时代的当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版画家的使命之责;在时代的当下,吹响文艺的号角,敢立时代先声是版画家的文艺之责;在时代的当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的版画精品,是版画家给人民群众最好的文艺奉献和最好的时代答卷。
结语
解放区木刻作为抗战文艺的典型代表,所彰显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内蕴其中的时代价值,永远值得后人去追诉、去学习,这不仅是后人对解放区木刻的态度,更是研究解放区木刻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