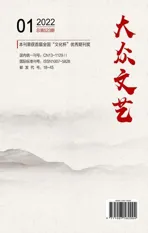脂砚斋“至情论”辨析
2022-01-24张沈琦
张沈琦
(吉林大学文学院暨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一般认为,脂砚斋是继汤显祖之后的“至情论”者。在脂砚斋批语中我们发现大量关于“情”的批点例如“自是个多情的种子”(甲戌本第五回)、“情理”“怀情不忘”(甲戌本第六回)等等。汤显祖则认为文学作品“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将“情”提升到了很高的地位甚至可以超越生死,而作为承载着至情的文学文本就成为“至情”存在的重要见证,也使实现“至情”成为可能。脂砚斋继承了汤显祖的“至情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将“淫”与“情”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本文将对脂砚斋的至情观进行分析,以期对日后对脂砚斋评点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一、“情”的界定及特点
脂砚斋“至情论”的观点主要体现第六十六回回前总评,并以柳湘莲为例阐释了脂砚斋本人的至情观。仔细阅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首先,脂砚斋将“情”与“淫”相区别,认为“情里无淫,淫里有情”,但“淫必伤情”。其次,“情”可以超越生死。在生的方面以柳湘莲为典型,他为了“情”宁可“万根皆消”,看似无情,实为至情;在死的方面以尤三姐为典型,面对威胁她为了追求属于自己的“情”敢于舍弃生命,看似绝情实际上是真正之情。最后,脂砚斋认为“情”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根本存在,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维度,甚至生死轮回也无法摆脱的向度。因此,脂砚斋将《红楼梦》归结为“至情文字”,是对情本论的见证。
那么,脂砚斋认为的“情”是什么呢?首先是“儿女之真情”。这种真情早已不同于以往的“情”,而是具有了当时的时代特征的“情”。尽管在第一回,曹雪芹借石兄之口抨击“风月笔墨”“才子佳人”等书,但整部作品却又保持了才子佳人小说中追求自由平等的“情”的观念,摒弃了这些小说在内容上将“情”与“淫”混为一谈,将“情”形式化,目的化的弊端。谭邦和《明清小说史》中指出,“才子佳人小说”在追求“情”的理想中,主要体现在容貌美、才智美、情爱美三个方面。在《红楼梦》第七十七回,王夫人要赶走晴雯,搜捡宝玉房内之物时,脂砚斋指出:“况此亦此[是]余旧日目睹亲问[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非搜造而成者。故迥不与小说之离合悲欢窠旧[臼]相对。”这样,脂砚斋的“情”首先表达的是男女之间的真情,这种真情,多了一份发自内心的真情真意,这种真情真意是曹雪芹与脂砚斋所亲身经历的,将文本中“情”注入了真实性。
其次是具有审美境界的“情”。《红楼梦》第五十二回,脂砚斋在问黛玉咳嗽的事情时,脂砚斋的批点指出了“情”的“沥血滴髓”的特点。沥血滴髓写出情与神的交合,生命体验的交融和对伦理的超越,具有了审美特征。首先,“情”既是人的情感体验又是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具有某些神圣性与普遍性。从横的角度来说,脂砚斋借此表达出,写情要从人物的心理、思想、情绪、精神境界等多方面来深入,并通过不同人情感变化,从他们的交流碰撞来传达。从纵的角度来说,这种“情”具有抽象性与普遍性,无论个体的人的情有多少种变化,终究来自并复归于至情;“情”还具有某种共通的特征,可以感人感物,达到人事间万物的和谐。这与我国古代所崇尚的天人合一精神形成了呼应。其次,这种“情”基于生命的体验,其中含有苦与乐,痛与悲的相互交织,但本质上来说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悲剧美。正是脂砚斋的“旧日目睹亲闻”,融入了生命体验,使得文字成了生命体验的见证,将“情”与活生生的人联系在一起,避免了重蹈“风月笔墨”“才子佳人等书”的窠臼。最后,这种“情”超越了传统的“发乎情止乎礼”的框架,成了一种自由的存在。这种“情”不是受到外在归训所生发的情,而是从人的内在精神生发出来的,是基于人的生命体验,人的天性本心所形成的。在这个层面上,脂砚斋既继承又超越了汤显祖对“情”的看法。
最后是一种“痴情”,是一种对人对万物的慈悲怜悯之情。这种“情”基于并超越了审美境界,其中包含了“情”与“幻”的双重维度。在词典的解释中,幻有“假象、虚无”之意,有“变换、诈惑、神奇”之意,曹雪芹在用字上,注重“情”即是“幻”,“幻”即是“情”的意味,是“情”与“幻”两者的和谐统一。“情”与“幻”交织在一起,既有一种拆解的意味,又有了一种拯救意味。拆解指的是“幻”本身会对“情”造成破坏性影响,会使“情”面临消失的风险;拯救则指的是经历了“幻”的层面,“情”就会转化更加具有超越性的“情”,也就是因“情”而超越生死,进入化境,本质上来说是“情”的更高阶段。在第五回,警幻仙子嘱托宝玉回归经济之道,脂砚斋写道:“说出此二句,警幻亦腐矣。”在脂砚斋看来,经济之道无法拯救人的存在,反而会使人丧失“情”,即丧失人的生命活力,归于腐朽。值得注意的是,在《红楼梦》中,宝玉早已神游“太虚幻境”,对于家族之事他至少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正是在整个家族充满悲剧性的命运中,正是“情”的存在,使宝玉认识到了世界的某种本质。脂砚斋的“情”,是以“情”为本,在经历世事变迁之后逐渐深化的过程。“情”无法改变人的处境,时代的潮流,但“情”可以使人精神升华,思考人存在的意义,经历劫难,才能认识到“幻”的层面,继而最终达到悟的层面,也就是参透生死幻灭,面向死亡,以死为真,以生为幻。“情”即是“幻”,“幻”也是“情”,“情”中生“情”,“幻”中有“幻”,也就达到了“至情”的境界。这颇有海德格尔“向死存在”的意味。可以说,在这方面脂砚斋不仅与《红楼梦》所蕴藉的观点一致,还呈现出别具一格甚至超越的特征。
二、“淫”的界定及特点
许慎《说文解字》中对“淫”的界定为:“侵淫随理也。日久雨为淫”。指依据事物的纹理逐渐浸入,引申为贪多,无节制。“淫”在脂砚斋这里是一个中性词,除了继承原有意义之外,更是与云雨之事相关且是与“情”息息相关的存在。《红楼梦》第五回,曹雪芹借警幻仙子之口指出,无论当下还是历史,负心浪子们都借口“好色而不淫”,以“情而不淫”来作案。在这种情况下,“情”与“淫”都难逃污名化的宿命,成了掩盖肮脏丑事的借口。事实上,“情”与“淫”本身的界限就十分模糊,想要完全将二者完全区别开来并戒除“淫”的成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脂砚斋指出,“好色而不淫,今翻案,奇甚。”否定了传统经学中将“情”与“淫”二分的看法,并同意曹雪芹对“意淫”的阐释。曹雪芹指出了“淫”的两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世俗之人的“淫”,他们将声色容貌放在首位,追求感官刺激,以自我为中心,避少求多,因此成为“皮肤淫滥之蠢物”。这种“淫”在世俗之中的存在最为多见,在那个封建时代早已见惯不怪,反而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第二条路径是以宝玉为代表的少数有“真情”“至情”的“淫”,他们将人类最真挚最美好的“情”放在首位,以“情”出发,以达到某种审美境界为要旨,以他人为中心,即脂砚斋所指出的“不过是体贴二字,故曰:意淫。”但这种“淫”多为世俗世界所不容,仅能存留于闺阁之中,“见弃于世道”。是一种人类最为本真的思想情感。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淫”不排除人的正常欲望,反而在“淫”的主导之下包含了“情”,这种“淫”也就转化为了“至情”。可见,“淫”与“情”之间不是完全对立性的反而是生成性的,这种路径的诞生与发展是脂砚斋愿意看到的。
但脂砚斋对曹雪芹的阐释并不完全满意。在脂砚斋看来“淫”与“情”不能完全等同。尽管“意淫”有其积极意义,但终究还是要回到“情”上面来的。因此,脂砚斋站在第二条路径的立场之上,对以往关于“情”的观点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脂砚斋看来,虽然“淫里有情”,但“淫必伤情”。因此,想要达到“情”的境界,就必须要对“淫”进行戒断。这样,在追求“至情”的语境之下,“情”与“淫”就变成了具有类似辩证法的相互转化:在“情”消失断裂处“淫”也就随之产生,戒断了“淫”,认识到“淫”的诸种局限,“情”也随之而产生。这样一来,脂砚斋的“至情论”体系中,“淫”成了追求“至情”道路上的一个契机——如果主体认识不到“淫”的本质与诸种局限,是无法达到“至情”的;同样,认识不到“情”的超越性与“情”对人生的诸种意义,也无法达到“至情”的境界。因此,“淫”与“情”是脂砚斋“至情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可以说,脂砚斋在这里将在以汤显祖为代表的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淫”与“情”的关系,解决了“至情论”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情”与“淫”是无法完全分开的。将“情”提升到至高地位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忽视人的正常欲望。所谓“淫里有情,情里无淫”,脂砚斋不仅将“情”提升到了根本位置,更是将“淫”纳入“情”的范畴之中,深化了《红楼梦》“大旨谈情”的主题,并使之成为“情痴之至文”。一些研究者显然忽略了脂砚斋在此处的深意,仅仅将从“情”与“淫”对立来理解,显然违背了脂砚斋的原笔原意。
脂砚斋的“至情论”的内容具体表现为“友”与“专”的双重维度。脂砚斋在第五回指出贾宝玉“不过是体贴二字,故曰:意淫。”意淫(体贴)是脂砚斋“至情论”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没有意淫(体贴),“至情论”也难以成立。宝玉对所有闺中女子都抱有一份体贴之“情”,但这种体贴之“情”早已脱离了肉欲的成分,是不包含任何性意向的体贴与怜悯。可以说,这是“友”的维度。同时宝玉对黛玉的钟情期以成配的心思是无可动摇的,可以说,这是“专”的维度。脂砚斋在第三回指出:“可见惜其石必惜其人(指宝玉),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计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宝玉“不自惜”,黛玉“为之惜”。因此在情榜中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宝玉与黛玉之间也存在着“友”与“专”的双重维度。这显示了脂砚斋的“至情论”具有的普遍性质。此外,宝玉的“情”并不是一味付出、不求回报的,而是有所期待的。脂砚斋从人的普遍情感出发,将“淫”纳入“情”之中,并赋予“淫”超越的可能性,并将“情”作为“淫”超越的依托。相比《金瓶梅》,这种期待与行为早已脱离“皮肤滥淫”的格调,具有了审美意义。此外,如果认为脂砚斋将“情”本身变成了类似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般的存在,却也违背了脂砚斋意图。“情”在脂砚斋这里是自由的代名词,显示了脂砚斋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超越性的重视。
结论
脂砚斋通过“淫”与“情”的双重变奏构建了一个以“情”为本体的“至情论”体系。在“情”的烛照之下,“淫”与“情”达到了和谐统一:至情即至性,至情即至理,开拓了至情的新境界。在这一方面,脂砚斋的评点实现了对古典小说评点的突破。脂砚斋认为,《红楼梦》是“情痴之至文也。”脂砚斋从他所主张的“至情论”出发,将“情”区别于日常生活。按照生活的常理,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情绪的产物。从“情”的角度来说,事物之所以能够发生,必有其中的道理。在脂砚斋看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成了一个伪命题,人不可能完全脱离情感,事件也永远会存在。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脂砚斋道出了《红楼梦》作为“情痴之至文”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将“情”的真正含义书写了出来,用这些文字作为“情”的见证,同时也启发他人与后世对至“情”的思考。这样不仅凸显了其中的审美的意义具有了哲学的高度。可以这样说,《红楼梦》是中国小说的高峰,脂砚斋的评点则是高峰之上的高峰。脂砚斋的评点最为深刻的文化价值,是其中蕴含的文论与审美价值。这种价值表面上似乎与某种中国传统的宗教价值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却阐发出一种人文主义的价值观。
注释:
①关于脂砚斋的“至情论”(或者“情本论”)可参见:高明月.《脂砚斋小说批评“至情”说意蕴解析》[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9(01):1-6;高明月.《因情捉笔:脂砚斋小说批评“情本论”研究》[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01):56-62;吴明东.《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谈脂砚斋对<红楼梦>“情”主题的揭示》[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55-58等文章.
②参见:脂砚斋.《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2,87页.
③关于汤显祖的“至情论”(或者“才情说”),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可参见:储著炎.《汤显祖“才情说”的理论内涵及其思想渊源》[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3(04):37-40;唐卫萍.《汤显祖“至情观”辨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2,31(01):105-109等文章.
④汤显祖“至情论”主要体现在《牡丹亭•题词》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于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
⑤这里取蒙古王府本的评点语句.戚序本作“淫里无情,情里无淫”,笔者认为不符合脂砚斋的原笔原意.本文主要以蒙古王府本为准.此处参考:周汝昌.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853),曹雪芹.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2549).
⑥这里的“生命”指的是本原性的,不需要外部事实认可的生命,具有超越性可能性的生命.可参考: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北京:三联书店,2001:324.
⑦这里的审美特征采用康德的理论.康德归纳了审美的四个契机:从质来看,审美判断与一切利害关系无关;从量来看,美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使人愉快;从关系来看,美是一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从情状来看,美不凭借概念而使人愉快.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39-83).
⑧第十九回批语.可参考:周汝昌.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