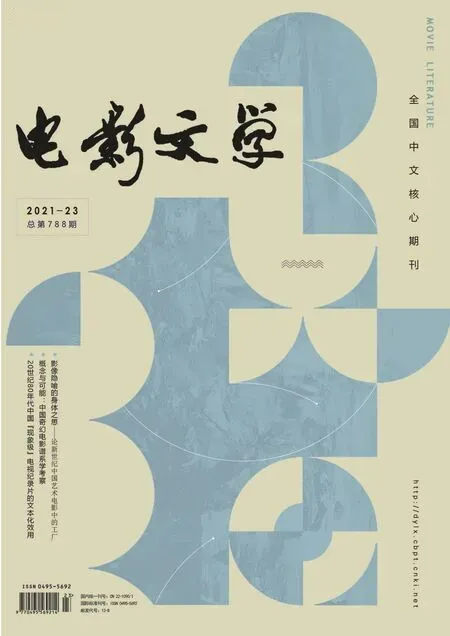从记忆重现到凝聚结构:“百年党史”题材纪录片建构党史记忆研究
2022-01-22徐丹丹杨郑一
徐丹丹 杨郑一
(1.扬州大学党委宣传部,江苏 扬州 225000;2.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江苏 扬州 225000)
记忆的概念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一般指人们对所经历事情的认识和回忆。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将涂尔干的社会分析理论引入记忆研究后,创造性地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将其视为每一个“具有一定时空边界的群体”所拥有的记忆。在与一定的社会情境连接后,集体记忆就超越日常性的社会交往范畴,可以长时段地参与到媒介叙事和文化实践中,成为扬·阿斯曼所说的文化记忆。掌握和运用文化记忆传递机制对国家或政党而言意义非凡,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都面临无形的以说服和信仰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设、传播和认同。事实上,任何历史话语和历史叙事只有修辞性地融入当代族群的文化记忆之后,才能成为滋养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的深厚土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各级媒体单位集中推出了一批百年党史题材的纪录片作品,如《重生》《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共产党人》《复兴之路》《山河岁月》等,它们通过各种介质媒体的传播展示,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红色文化景观,呼应并续写了百年党史记忆,成为传承党史文化的重要途径。在党和国家大力传播宣扬党史文化的当下,我们有必要落脚于符号表征和媒介叙事的视角,深入探寻通过纪录影像实现百年党史记忆修辞与转义的作用路径,并借此管窥强化当代政治文化传播的方法与经验等问题。
一、百年党史记忆重现的视觉修辞模式
百年党史记忆是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贯穿现代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历程中,成为中华民族“家-国”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当前中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期,文化记忆被赋予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重功能,已经成为阐释“当下”意义的重要路径。形成文化记忆的核心是符号,是表征。由于时间与空间的无限性,人类越来越难以依靠具身经验将复杂的历史现实转化为叙事性的历史书写,而是需要借助社会交往和媒介传播来获取记忆传承,并在社会文化框架驯导下形成对文化记忆的话语表达,这个过程被称为记忆重现。作为一种文化记忆机制,百年党史的记忆重现是借助符码表征和传播活动,将百年党史所承载的文化、情感和精神信念进行“物化”和“言说”的过程,相较于传统的语言或文字,视觉表达能够通过将图像、文字、音乐等多模态语言融为一体的方式,影响和推动文化记忆的建构实践,因而成为视觉文化时代传承党史记忆的重要途径。
正因为文化记忆鲜明的“当下性”特征,百年党史记忆的影像书写必然蕴含着一个通过修辞手段组织符号话语实现“劝服”功能的过程,体现为通过视觉图像在记忆文本、受众文本和社会文化文本间建立修辞结构,传达特定文化意义和意识观念,从而实现记忆重建的实践过程,其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百年党史记忆重现的视觉修辞模式
百年党史记忆重现的视觉修辞模式包含三层内涵:第一是对记忆文本的符号生产,这是一个记忆符号存储和加工的过程,通过纪录影像的视觉加工将党史记忆形象化、具体化,建构起可以被感知和言说的形式,形成人们对百年党史记忆的基础性认知。第二是受众文本的二次加工,即受众在进行“观看”百年党史题材纪录片行为的过程中,将接收到的记忆符码与自身经验世界进行融合和重写,借助文化记忆选择、强化、遗忘等机制的作用,将个体记忆“集体化”“社会化”“文化化”的实践活动。第三是社会文化情境中的记忆再生产,由于记忆书写存在集体性、建构性、不确定性的特点,相同的记忆元素在不同个体或族群中会呈现千差万别的理解,因此必须借助社会文化文本提供一种先验性的认知,建构记忆体验的“形式”和“框架”,为记忆书写提供超越维度的他者书写。上述三种内涵分别从视觉符码、受众感知与文化实践的维度发生作用,通过其中修辞结构的建立,将百年党史记忆以视觉影像的形式进行生产和传播,并对现实的社会文化产生影响。
二、纪录影像中百年党史记忆的意象建构与修辞实现
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党史记忆不是静态的、孤立的存在物,而是在社会交流中不断更新的对话性语言。基于语义不确定的客观存在,记忆交流活动中决定记忆内涵的就不仅是“我们说了什么”,还取决于“人们记住了什么”,其中必然包含了认知维度的修辞实践。以百年党史题材纪录片为载体推动党史记忆的记忆重现,可以理解为运用意象选择和符号修辞的方法让党史记忆在当下“鲜活”起来的文化实践,其意象建构与视觉修辞逻辑可以从文本分析、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记忆重建:以视觉意象组织记忆文本
从本质上讲,记忆重现是对记忆文本的符号化处理,是约定视觉符号形象和意义的意识生产活动,基础性的产品是视觉意象。既有的研究认为:视觉意象包含原型意象、概念意象、符码意象三种样态,分别回应了视觉修辞实践中语境生成、议题建构、符码表征三个层次。利用百年党史题材纪录片开展党史记忆的建构实践,就需要分别在视觉意象的三个层次中修辞操演,实现对人们视知觉经验的组织化和文本化,最终达到形成对话和劝服的效果。
第一,纪录片利用原型意象建构了底层记忆语言。原型是一种稳定、典型可以被反复使用的形象,是经由历史、文化、社会心理等反复构造所沉淀形成的普遍共享认识。人们在观看活动中获得的直接经验是浮动的、零散的、未经雕琢的,并不能在修辞实践中形成普遍意义上的记忆叙事,因此需要借助原型意象提供记忆重现的解读语境,以此回答“图像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百年党史题材的纪录片脱胎于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中借用并显现了大量表征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原型意象,如党徽、党旗、党员身份标志、党的政治仪式等,这些视觉意象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反复接触并已经形成共享认知的符号形式,是普遍性社会文化经验在人们认知系统中的投射。在观看党史纪录片的过程中,原型意象能够源源不断地铺设文本释义的文化语境,激活人们在潜意识中存在的认知经验和情感体验,从而将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元语言系统”借用到影像释义的活动中,为人们实现记忆重现提供定位基点。
第二,纪录片利用概念意象形成隐喻关系。在意象形式确立之后,概念就成为修辞的关键。在党史题材纪录片的记忆书写过程中,需要引导人们在形式认知与概念认知之间建立桥梁,激发从图像形式到图像概念的认知转换行为,即开展“图像像什么”的论证活动。在党史记忆的图像叙事中,同样的形象在不同的时间和事件背景下可以表现不同意义,如南湖红船既象征着党的创立,也象征着红船精神,还可以指向坚持党的领导的意义内涵,甚至对画面本身的不同视觉处理也可以展现出特定的意义内涵,因此有必要借助符号修辞活动提供一种外部规定性,给人们提供一种把握现实的方法指导。在党史纪录片社会传播过程中,伴随着意象叙事的是一系列概念隐喻的出场,它们之间的相互勾连在图像表征与概念意指间建立了映射结构,展开了积极的议题设置活动,激发了受众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调动概念意象解释现实问题,从而使视觉画面超脱了视觉获取物的范畴而成为共享意义的携带者。
第三,纪录片利用符码意象形成意义系统。作为观看行为的深层次活动,图像形式与意义的接合能够产生抽象意识,引导人们建立关于党史记忆的知识体系,产生对图像内涵的认识论指导。在这个阶段,人们在观看党史题材纪录片中获得的形式与象征认知经过意识想象的加工被不断雕琢、整理并系统化,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如用开国大典、东方红的配乐以及党的第一代领袖的形象表征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的历史,用邓小平等领导人画面、《春天的故事》等配乐表征改革开放初期的党的历史等,在图像能指与所指间建立牢固的指涉结构,从而牢牢掌握了记忆文本的意义生产权,让人们进行观看行为时能够被引导到共同的意义系统中,实现对党史记忆的表征确立。
(二)记忆操演:以视觉框架规范受众文本
在视觉修辞活动中,框架总是伴随话语实践“出场”的,重在解决合法性的问题。框架理论的创始人欧文·戈夫曼认为:框架意味着一种“阐释图示”,它能够帮助人们“辨别、感知、确认和命名无穷多的事实”。在百年党史主题纪录片的影像叙事中,视觉框架实际上铺设了一套逻辑推演系统,以先验存在的形式定义了人们对纪录影像的理解方式。第一,框架提供了解释和重复。框架是一套组织信息的方式,其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稳固性并能够规范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在人们观看纪录片的过程中,百年党史的记忆叙事框架被重复征用,为各种形式的影像话语铺设意义说明,以此将党的政治意志和机制观念灌注到人们深层次的逻辑认知中,实现说服和认同的目的。
第二,框架激活了知识体系。美国学者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人类的概念系统是以隐喻的形式存在的,同样是以隐喻的形式构成和发生作用的。在党史纪录片的话语叙事中,框架积极地在历史记忆与现实概念间以隐喻的方式建立意义置换结构,形成把握理解影像内涵的知识框架,并通过对知识框架的权力操演为党史记忆提供社会认知层面的合法性说明。例如,党史中的革命精神资源能够被隐喻映射进入现实的奋斗实践,鲜活阐释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黄大年精神等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展演,从而将来自党史记忆中的概念体系转译进入“当下”的文化语境中。
第三,框架提供了间接编码的流通。人们对党史纪录片的观看行为存在多种可能,有人看过很多甚至大多数的作品,有人仅仅看过一部分或者一些片段,还有人可能看过极少数作品或者完全没有看过,但是不论哪种情况,人们的认知世界中都存在对百年党史的记忆认知,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社会记忆框架的存在。党史纪录片的传播过程,实际上也是党史记忆框架的社会传播实践,人们可以借助社会交往以“间接编码”的形式开展框架叙事,形成超脱直接观看经验之外的认知体验,形成与党史记忆更加紧密的情感和文化联系。
(三)记忆规训:以文化关系勾连社会文化文本
既有研究已经指出:记忆建构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由不同的参与者、社群、媒介和文本共同塑造。从这个角度理解,党史记忆的影像传播不仅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同时也通过社会关系的统合勾连了记忆文本和受众文本,实现对社会深层次文化心理结构的生产和调试,这是百年党史记忆的再生产实践。第一,社会文化文本形成了多模态语言的空间组合体。在党史题材纪录片的传播过程中,建构人们观看经验的既包含纪录影像的画面、声音、字幕等视听文本,也包含弹幕、评论等伴随文本,还包含进行观看的场所环境、社会语境、文化风俗等环境空间,它们共同建构了党史记忆生产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在百年党史记忆的社会文本书写中,内部记忆世界与外部记忆世界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的,而是以一种“复调式”的记忆书写形成多元化的记忆流通通道,从而再造“观看关系”,形成“记忆空间”,打通记忆传播的“视觉之维”。
第二,社会文化文本重构了社会认同关系。党史纪录影像的传播过程,既包含创作者与受众的传播和交流关系,也包含不同受众间的共享和对话关系,他们之间的意识交流活动共同塑造了作为“他者”文本的社会文化文本。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形态的构造物,社会文化文本能够通过认知关系对受众文本进行解释和规范,在社会族群中发挥对话与规范的功能。实际上,百年党史主题纪录片的社会传播建构了一种“命名关系”与“排除关系”。一方面,通过视觉框架对党史记忆事件进行命名,确认其现实合法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党史记忆的传播还建构了一种“排除关系”,即通过对记忆符码的“选择性遗忘”形成“去认同”的传播活动。通过对历史叙事进行选择性传播和选择性排除,让党史记忆更好地履行文化生产和传播功能。
第三,社会文化文本促进了文化生产实践。媒介话语是被建构的产物,同时,它也可以反向建构文化、政治与社会生活。党史纪录片的传播与认知活动中,人们在社会文化中铺设了关于党史记忆的“话语场”和“意义场”,人们在面对新的文化问题时,一方面,可以通过“编码—解码”的实践主动迎合主流党史记忆形态,使得社会族群成员成为百年党史文化的积极认同者和坚定践行者;另一方面,党史记忆的媒介叙事在社会层面形成了记忆资源的积累,促进了党史记忆在不同存储媒介间的转化,例如从视听语言到文字语言,文献记录到影像记录,从视觉画面到纪念器物等,这些转化积极推动了社会记忆的再生产实践,让党史记忆更加鲜活,更加生机勃勃。
三、纪录影像中百年党史记忆重现的视觉话语实践
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百年党史题材纪录片通过记忆重现的实践,在当代社会文化生产中发挥了批判性的作用,或者说党史记忆与当代中国现实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党史题材纪录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以此形成在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维度的反向建构力。在当下文化情境中,我们有必要深入体察纪录影像在百年党史记忆传承中的话语、凝结与空间功能,以此锚定我们深化百年党史记忆生产与修辞的方法路径。
(一)以影像话语提升党史记忆的可见性
记忆可见性意味着记忆被看见,被发现,意味着让记忆叙事走出私人领域,走向公共生活。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就指出:存在两种用于存储回忆的记忆存储器——身体和语言。在记忆重现的过程中,身体之维指向了作为认知思维的记忆生产活动,体现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间的互文关系,语言之维指向了社会沟通中形成的记忆框架和关系结构,二者共同决定了记忆重现的公共性特征。在记忆重现中提升百年党史记忆的可见性,需要充分把握实现修辞的隐喻、互文、转喻等修辞方法,实现对文化记忆的创造性生产。首先,以比喻关系展示时代精神。百年党史记忆反映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它的指向意义是在党的领导下,社会成员通过努力奋斗实现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通过记忆重现能够在社会心理层面形成积极的心理建构,将人们幸福生活的获取与党的奋斗历程“接合”起来,形成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其次,虽然党史题材纪录片展现的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但其影像书写往往要落脚于现实个体的生命书写上。通过在宏大历史与个体实践间的互文书写,党史纪录片将党史记忆刻写在社会族群的经验世界中,将集体记忆、个体风格与私人记录在记忆书写中连接起来,让记忆建构中的“整体”和“个体”,“官方”和“民间”都处在“可见”的状态下,使得党史记忆能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发挥作用机制。
(二)以影像传播开展党史记忆的框架宣认
人是依赖框架存在的动物,在视觉文化时代,人们往往依靠视觉经验来“框架世界”。在视觉叙事中,图像可以证明真实,也可以书写谎言,其体现在共时性的记忆书写中时,就形成了对框架“命名权”与“释义权”的争夺。从这个角度来说,百年党史的记忆重现中也蕴含着对记忆框架“争议”和“宣认”的斗争实践。首先,纪录片以视觉刺点激发情感反应,视觉修辞研究的先驱者罗兰·巴特将“刺点”的概念引入视觉研究中,用来指代图像中能够吸引人们关注,引发人们情感的刺激物。利用党史纪录片进行记忆操演,就需要把握和运用视觉刺点,将人们的思维活动从简单的画面识别引向深层次的情感体验,如画面中的红旗、党徽,主体人物佩戴的党徽等,这些视觉刺点的出场能够迅速将记忆操演引导到百年党史的记忆叙事框架中,从而实现对党史文化意义的召唤。其次,以意识体验开展社会动员。在党史记忆的重现中,纪录片能够通过对观看“场所”“语境”等的选择实现对语义场的铺设,也能够通过程式化的重复操演将党史记忆与人们的身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媒介扮演着象征黏合剂角色,使独立的社会个体结合成为紧密的社会整体……媒介能够在文化层面构建无形的社会组织象征模式”,可以说,党史记忆的媒介传播建构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忆叙事框架,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党史记忆的神话操演,使其发挥出米歇尔·福柯所言的装置作用,从而将记忆操演拉向生命政治之维,成为知识权利框架的表征。
(三)以空间传播建立党史记忆的凝聚结构
在百年党史题材纪录片的传播过程中,人们所经历的记忆世界,实际上是传达了经由权利操演所定义的记忆路径,形成了关于党史文化的记忆空间。在党史记忆空间中,我们运用符号回忆过去,定义现在,并面向未来形成意识想象的共同体,这就是百年党史记忆的“凝聚性结构”。扬·阿斯曼认为“凝聚性结构”是维系记忆空间的基础,他认为:“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凝聚性结构可以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其方式便是让他们构造一个‘象征意义体系’——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在党史纪录片的传播过程中,纪录片借助标签符号的细描和共享式符号架构的阐释体系,成为表述特定形象的载体,将抽象的记忆符码转化为现实的回忆行为。在体验维度上,纪录片通过对社会关系的编织,将人们的生活空间、纪念空间与党史记忆连接起来,使得党史记忆不仅表现为一种回忆行为,也体现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文化空间维度上,让百年党史记忆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关系中“活化”起来,通过记忆传承和记忆形态间的互文转化,积极地介入社会文化再生产的实践中,让百年党史记忆成为当代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资本与思想宝藏。
概况来说,纪录片作为“写在胶片上的历史”,是传播和阐释党史记忆的重要载体。通过对百年党史纪录片视觉修辞模式与路径的分析,我们能够在影像世界、现实世界、记忆世界间建立贯通关系,发现并总结“记忆何以可能”的路径与方式。在世界语图时代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在视觉生产与记忆生产间建立阐释结构,回应视觉化时代开展记忆修辞的需要,从而为当代社会文化生产提供更多的精神资源和价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