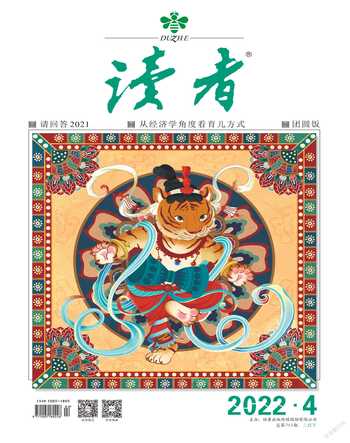发出我们的声音
2022-01-19付子洋
付子洋

一
《82年生的金智英》是韩国作家赵南柱的一部虚构文学作品,在1982年出生的韩国女性中,最常取的名字就是“金智英”。这个描述1982年生的女性如何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又如何为了育儿离开职场,却受到轻视,失去自己的故事,在全亚洲乃至欧美引发了广泛讨论。
2019年,《82年生的金智英》中文版图书出版,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当时,责任编辑任菲在正文最后一页空白处,留下一个邮箱地址,向读者征集来信。这是受日文版《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方的启发,日文版曾采用类似形式,寻找“日本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刚被引进中国时,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女性的地位比韩国女性的高得多,其中一项重要指标是,中国女性就业率显著高于同处东亚文化圈的韩国和日本。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位列全球第55位,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大型经济体相比都处于高位。
但评判女性地位,并非只有经济收入这样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何况这可能意味着更多女性需要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寻求平衡。
二
1982年,赵娜出生于河南农村,在郑州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赵娜成了二孩妈妈,停薪留职在家。
她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从这种家庭结构来看,可以确定她生活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中”。从记事起,三姐妹就下地干农活,拔草、锄地、割小麦,母亲现在常说她们小时候乖,两三岁时就会自己照顾自己。“她说得高兴,我听得心酸。”村里没有生男孩儿的女人会抬不起头来。弟弟出生后,父母再苦再累也觉得生活充满希望。
趙娜在成长中的感受更多是被忽视。但她回忆起一件小事。上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大雨天,高高瘦瘦的父亲身披雨衣,突然出现在校门口。因为生计,父亲很少出现在家中,她从学前班起就自己上下学,那是父亲第一次来接她放学。那天父亲背着她,走在雨中泥泞的路上,平日里和她一起上下学的两个女孩,蹦蹦跳跳围在两边。村里的女孩大多境遇相似,同班的一个女生,家里是5个女儿。她从父亲的肩上向下看,觉得同伴们对她充满了羡慕。
在充满爱的家庭,这是很寻常的事。但那是上学以来,赵娜唯一一次感受到,“有爸爸的肩膀可以依靠,是很幸福的事”。她快40岁了,想到当时的画面依然会哭。
1998年出生的徐媛媛原以为男女的差别只在于头发的长短,直到16岁那年,爷爷去世,她才开始感受到自己和弟弟的不同。她写道,作为长孙女,她的白色丧服上,有一点点亮眼的红色。但邻居老姨给她套上缝制的粗糙丧服后,一边强硬地转过她的身子,一边鼻子一哼:“长孙女有什么用?还不是缺个把子!”
送葬时,举引魂幡的须是家族的长子长孙,因为她是女孩,改抱了二叔家的弟弟去。弟弟因为惊恐而哭花了脸,“小小年纪的他只觉得场面大得吓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也是一件‘荣耀的事”。
徐媛媛在信里写,有一次下大雨,她和家人湿漉漉地回到家。她帮奶奶换好干净衣服,给奶奶烫完脚后,奶奶突然声音洪亮地说:“让你弟弟也洗洗脚,你把他的袜子洗了。”奶奶说这句话像在聊“今天的雨好大”一样自然。
徐媛媛不悦地说:“他长大了,洗脚、洗袜子可以自己做。”奶奶微微叹了口气,说:“你要不给洗,那就我洗吧。”“他们的苦肉计用得十分到位,我立马觉得是自己太懒惰,让奶奶再起身去做就太不孝顺了,忙应承着说,我来我来,您躺着吧。”
在中国,《82年生的金智英》受到的一大诟病是,写得很像社会新闻大乱炖,欠缺文学性。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是刻意将金智英塑造为一个女性的符号。“她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概念,我特意模糊了这个界限,就是希望有更多人在她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三
任菲发现寄来的信中,少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他们大多是普通人,生活没有戏剧性,只不过是有一些“类似金智英”的经历,但这些细节组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像是在提示社会中女性可能遭遇的形形色色的陷阱。
金智英在公交车上遭遇过猥琐男。2007年出生的阿殿说,她以前听说过猥亵少女的事,但没想到12岁那年,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天是青年节,她拿着书本,趴在图书馆二楼的窗边,看窗外一棵枝干舒展的大树。这时,一个男性将身体贴到她身后。阿殿猛地推开他,找机会悄悄告诉了图书管理员。报警之后,警察调取监控录像,因为“情节轻微”,男子被拘留了12天。阿殿说,这名男子有点儿胖,戴着眼镜,看上去憨厚老实。
让阿殿想不通的是,自己留着极短的头发,穿着黑色长袖卫衣和长裤,卫衣上面是阿童木卡通图案,“我不漂亮”,却依然成为猎物。
1994年出生的吴晓晓,海归,研究生毕业。毕业之后来到这家公司不到两个月,总裁叫她出去应酬,陪甲方吃饭。“个个都是年纪可以当我爸的中年大叔,强逼着我敬酒、喝酒,看你一口干掉后露出满意的笑容;当你拒绝时,他们紧皱眉头,露出难以置信的、不满意的神情。”
压垮她的一幕,是从洗手间出来碰到甲方领导。“哪一年的?”“1994年的。”“哦,我女儿比你大两岁,本科毕业好几年了。”他问完后,又继续回到包房,唱歌、喝酒。
“更可笑的是,后来在机缘巧合下,我认识了这个大叔的女儿。提到之前的那次酒局,她问我,从同事的角度来看,他人怎么样?我想了很久说,挺好。”吴晓晓写道。
阿雯在上海一家公司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她庆幸国家为保护女职工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但有些时候,她觉得政策在现实中成了一把双刃剑。几乎每次人力资源政策培训,她都会被无数次地提醒聘用女职工的潜在风险。
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阿雯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你刚刚录用她,她就怀孕,接着就要休产假。这意味着招进来一个人,很可能在几年内对公司没有任何贡献,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虽然有的招聘简章要求不允许向求职者询问婚育状况,但人力资源管理者培训时,对于面试提问有针对性策略。“不能直接问,但可以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想办法掌握这方面的信息。有些企业明面上不写仅限男性,但还是有权力不录用这样的女性。”阿雯说。
2002年出生的王若瑾,上初中时被男同学欺负了一年多。开始是在写作业时,被抢走文具袋,后来是眼镜。她近视600多度,像被大雾蒙了眼睛,只能慢慢走向他们。那些男生“像看小丑一样嘲笑我”。她被绊倒,挨打。谢师宴那天,一个男生送她回家,在小区门口告诉她,当年那些男生欺负她,是因为喜欢她。
她在信里引用了金智英的话:“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不是应该对她更温柔体贴吗?不论是朋友、家人,还是家里养的猫猫狗狗,都应当如此。”
四
1979年出生的段斌,是一名男性来信者。他是中部某二线城市的公务员,这本字数不算多的书,两个小时可以看完,但他翻来覆去地看了3天。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共鸣,与他初为人父有关。他说,过去对女性主义了解甚少,但陪妻子备孕、怀孕、生产这一路走来,尤其是经历指导同房、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之后,他对女性有了全新的了解。
妻子生产时,段斌在产房陪产。让他印象最深的,除了冰冷的手术钳,还有大夫冰冷的指令。“他们经常做这件事,不可能很温柔地呵护你,用的都是职业用语。”但段斌承认,虽然自诩女性主义者,但对妻子的痛苦,他不能完全感同身受。
“我所考虑的只是作為人所应当平等享有的权利、共同承担的责任,而非这是男人干的、那是女人做的,男人不能做、女人做不了这样的观念。社会存在的因素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个体组成家庭,家庭形成据点,据点形成城市,城市构成区域,区域组成整体。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独立的责任和义务,将这些形成基础的自律和意识,会让自己逐渐看到何为平等。”段斌写道。
这些信件最终被收录进一本小册子。收录的第一封信来自2000年出生的温酽,她的最后一句话写道:“就像反对按学号排队的柳娜,为女儿们争取房间的吴美淑,公开偷拍事件的姜惠秀那样,发出我们的声音吧。”
(文中阿雯、阿殿为化名)
(岩 华摘自《南方周末》2021年12月9日,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