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勾连现代精神的本土视野
2022-01-11徐梓俊
徐梓俊
“民间”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概念是陈思和先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拓宽了文学史的阐释空间,也为我们重新进入经典文学作品提供了一条宽阔的路径。王光东先生曾写了大量讨论“民间”问题的文章,并集结成《民间: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一书。此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理论阐释和批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从“民间”进入文本的具体路径,并以此为视点重新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其核心就是在对“民间”审美内涵的挖掘及现代意义的探询中,思考“民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
“民间”本身就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在讨论“民间”问题时有必要区分几种不同的“民间”内涵。首先是现实的民间空间,它丰富、复杂、多样,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启蒙者对“民间”的批判与革命者对“民间”的利用多从这一现实维度上出发。但既然是在文学范围内讨论“民间”,肯定不能将文学作品中的“民间”与“现实的民间”相等同。我们谈论“民间写作”,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以这个价值立场为中介,写作者将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转换成一个审美的、文学的“民间”,它与现实的民间相联系又相区别。在这个过程当中,“民间”最核心的内涵就是“自由—自在”,“自由”主要是指生命的自由渴望,即“民间朴素、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自在”则指民间生存的自在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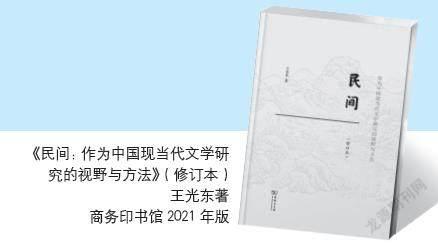
王光东在阐释“民间”问题时始终有着勾连传统与现代、本土与社会的意识,他不是将“民间”限定在传统与乡土的狭窄概念里故步自封,而是在现当代文学普遍强调的西方影响之外找到一个中国本土性的深厚传统。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初,胡适提出以鲜活的、朴实的白话文学代替雕琢的、陈腐的旧文学,实际上就是对“民间语言”中有利于文学突破因袭的因素进行了肯定,“明白清楚,有力动人”的白话语言在形式上为五四知识分子进行文学革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而且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中那种质朴、清新的表达方式和素朴的向往自由、反抗压迫的观念也与新文学“个性主义”的启蒙理想高度契合。因此刘半农在实际创作中又进一步凸显了“民间语言”的审美力量,他在对方言和口语的诗化运用中一改新诗的“欧化”倾向,于中国本土的民间歌谣中找到了个性主义诗学观的支持者。发端于五四的“启蒙—民间”的脉络一直以知识分子进入民间的不同方式在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浮沉”。现实民间不仅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更为其建设主体精神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不管是鲁迅从外部对民间的落后性进行批判,并由此获得一种“历史纵深感”;还是沈从文、老舍在“民间”的立场上呈现一个逼仄而又驳杂的民间世界。他们都是在与“民间”的对撞中找到自我观念与“民间”精神的契合点,从而建立起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使传统的、本土的“民间”迸发出现代性的精神光辉。这正是“民间”现代性价值的精髓所在。
那么民间的这种审美精神又是怎样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与之发生关联的呢?“民间原型”“民间想象”是王光东提出的“民间”多层次审美内涵中两个重要的范畴。它们主要来自于中国古代丰富的民间传說、神话故事,是小说叙事中“潜藏”的“民间印记”或者说“民间资源”,对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王光东并不是在民俗学的意义上复原当代“民间”写作中的神话、传说母题,而是强调在作家对民间原型的呈现和置换中,发展出“本土审美意识”的觉醒和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随着市场开放而来的是消费文化对国民日常生活的强烈冲击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此时来自民间的原型、想象中所承载的重要思想内涵和精神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民间原型,创作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自然生态的失衡、人的异化及生命力和道德伦理精神的萎缩——进行重新思考,并意图在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对接的过程中,构筑一种新的生命伦理和价值理念。

改革开放之初,思想刚刚解冻之时,汪曾祺就通过《受戒》塑造了一个纯净、和谐的世俗世界,表达出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对淳朴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由”人生的期盼。《受戒》的这一理想世界正脱胎于中国民间的“桃花源”传说,在“梦”与现实的反差中寄托民间内在的精神渴求。阎连科的《受活》则通过一个桃花源式的“受活庄”在各种外部力量挤压下而崩溃的故事,将读者引向对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王润滋《鲁班的子孙》,它以“太阳山”传说的善恶相报主题为想象原型,展现了社会现代化发展中民间传统美德的失落。张炜的《刺猬歌》《我的老椿树》等作品通过对民间“动物报恩故事”这一主题原型的意义置换,以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意识来反观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人性堕落等问题。在这些文本中,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强烈的改造社会愿望,通过一条“重返民间”的道路,重新呈现出强大的批判与反思能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写作中日渐盛炽的欲望化倾向,带来的是文学想象力的单薄、苍白、缺少生命的激情和活力。来自民间的想象资源为新时期小说想象世界的方式重新注入鲜活、生动的因素。莫言通过恣肆的想象力和汪洋的感受力复活了一个富有生命强力的高粱野地,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本土的又是现代的审美世界,来补足现代人的精神之钙。这是创作者从“民间”内部确立起来的反抗“现代性危机”的强硬姿态。“民间”,作为一个相对自足的审美空间,不仅为创作者提供了灵魂栖息之所,也为当代文学的颓废经脉注入鲜活血液。
由此可见,“民间”在滋养知识分子精神的同时,也以其深厚的民族根性传统关联到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主动与其形成对话。因此走向民间绝不意味着放弃启蒙;相反,随着时代语境的不断转换,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往往能通过“民间”视角而获得一种深刻的审视目光,更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以上关于“民间”审美内涵的讨论多基于对民间文学、文化中积极性因素的彰显,但知识分子在进入“民间”的过程中,必然无法忽视民间本身糟粕性的东西,因此如何理解现实民间的消极因素也是讨论“民间”问题的关键。打开这一问题的钥匙就是正确把握民间“藏污纳垢”的特质。我理解的“藏污纳垢”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它首先强调一个状态,就是现实的民间必然是善与恶、美与丑、升华与堕落的并存;其次它也强调一个“藏”和“纳”的动态过程,也就是民间对善恶美丑的包容能力,及其对外部文化、政治力量的吸收、消化能力,因而也是任何异质力量都遮蔽不了的生命活力。这使得“民间”在审美意义上呈现出丰富、驳杂的面貌,当创作主体以“诗意”的悲悯与关怀沉入民间大地,这种“藏污纳垢”催生的就是一个层次多样、内涵丰富的“民间”世界。正因为张炜在《九月寓言》里主动融入了那个纠缠着本能欲望与精神追求的“野地”,我们才能在金祥背鏊的艰苦历程中看到我们民族承继“夸父逐日”而来的那种悲壮的生命要求和本性牵引,才能从露筋、闪婆的黑夜奔突中获得久已缺失的精神野蛮生长的感动。

因此不论是以“民间”立场进行文学创作,还是以“民间”视角进行作品解读,关键是充分体认“民间”的本真面貌,深刻理解“民间”自由自在的生命观念、生存伦理和行动逻辑。只有承认“民间”是一个美丑善恶并存的真实世界,因此也是没法用简单的二元观念进行区分和阐释的丰富概念,才能真正体会到“民间”的文学性魅力與意义。
那么,在如今这个城市化不断发展、现代化不断推进的时代,重提“民间”还有没有现实意义?资本的介入、政策的扶持正在使广大农村发生新一轮深刻变革;与超大城市的建设相伴随的是城中村、“十八线”小城镇问题的日益凸显。在这一语境下,乡村民间世界有没有产生新的异质性的东西?外部力量在带来福音的同时是否进一步淹没了本土和传统的因素?那些被摩天高楼围堵、被大城市掏空的小镇空间,是否也在重演着乡村的命运?他们的命运、记忆值不值得书写?由谁来书写?怎样书写?在本书中未及讨论的“城市民间”是否值得进一步的考察?与此同时,当下一批年轻的作家也自觉地转向了与自己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民间”写作:双雪涛的东北“艳粉街”,班宇的沈阳铁西区,王占黑的嘉兴老社区,孙一圣怪诞鬼魅的山东小城,项静的傅村记忆,等等。他们的创作虽然风格各异,所表现的空间也多少溢出了乡土的范畴,但都在切身的体验与忠实的观察中展现出一个“民间”空间的兴衰记忆,以及这个空间中各色人等的欢乐与哀戚。民间原型、民间想象、民间记忆以一种更加个体的、多元的、现代的方式呈现出来,又在与时代的互动中获得一种普遍的审美价值。可见我们依然需要一个丰富驳杂的“民间”来进入文学创作,回应文学与时代的深刻关联。
正如王光东在讨论莫言小说中的“民间想象”问题时所说:“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会有多层次的存在形态,在当下文化多元、文学多样化的情境下,也不会仅仅有与消费文化共谋的文学存在,有一些作家仍然在人与外部世界、人与自身、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纠缠中思考着中国社会历史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且以独特的艺术想象构建起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世界,这种想象就是民间想象的传统。”“民间”,作为一种勾连现代精神的本土视野,同样也始终会在我们对文学的思考中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