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义还是现实意义
2022-01-11胡翌霖
胡翌霖
范内瓦·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最初是一九四五年布什给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的一份报告书,该报告奠定了美国二战后的科技政策基调,有着深远的影响。二○二一年,中信出版集团又出了最新版,在网络上推广时,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说道:“透过《科学:无尽的前沿》研究美国科学大发展的原因,培育全民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加大对于基础科学和前沿科学的投入,提升企业的科技实力和全球竞争力,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现实意义。”
就布什报告的历史地位来说,再多赞誉也不过分,但是如果说除了通过它理解历史之外,还能够直接用于指导现实,那么恐怕是有些抬举过高了。撰写新版导读的拉什·霍尔特(美国科学促进会前首席执行官),就“对布什的盲点和大胆计划提出了尖锐的反思,这也使再版的本书更加契合我们的这个时代”(安吉拉·克雷格語)。对布什报告的批评实际并不始于霍尔特,而是从布什报告发表之初就开始了,布什的理想虽然影响深远,但从未被美国人全盘接受,甚至可以说是被“阳奉阴违”的。布什为科学家实际争取到的经费并不多,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科技政策自始至终都是更加注重应用和实利的。布什的功劳或许只是在原本基础科学几乎没有政府支持的美国实用主义环境下,为科学家争取到了些许支持,但并没有让美国脱离实用主义的底色。
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科学史和技术史学科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学界对布什报告的局限性有了更多共识。至此,布什报告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已经是千疮百孔。
中译本第三部分附加的十篇“扩展评论”中,樊春良教授的长篇评论详细解读了布什报告的历史背景和相关争议,他提到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布什报告所隐含的线性模型的批评,二是与“社会契约”相关的问题。下面我用自己的思路来重述一下:第一种批评主要源自“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发展,第二种批评主要基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学科的发展。
所谓线性模型,指的是布什所构想的,形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市场效益”的线性模型。科学与技术泾渭二分,基础研究位于科学的源头,而市场效益位于技术的终端。在这条单向的河流中,扩大源头就最终能够促进最终的收益。但这种模型早已被证明是过分简单化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技术史学科开始独立发展(在欧陆,技术史发展得更早),技术史家和科学史家一道,打破了传统上认为“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发现技术的发展往往有独立的线索和动力。当然,科学与技术经常互相联动,但与其说是由基础科学单向地激发技术,不如说影响总是相互的,技术发展对理论科学的支持和激发同样显著。例如,瓦特的蒸汽机并没有受到热力学的激发,相反热力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受到了蒸汽机的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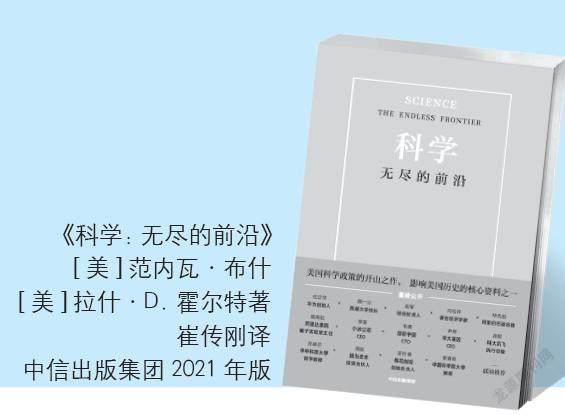
哈佛大学教授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在二○一六年出版的《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一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中指出,非但线性单向的模型是错误的,而且“基础—应用”的二分本身就是误导性的。他提议用“发明—发现”的循环模型取代旧的观点。而且发明与发现的界限并非位于两种定位不同的学科群之间,而是说在每一学科或每一研发领域中都存在发明与发现的循环激励。
所谓“社会契约”,指的是科学家“特权”的合法性问题。布什一方面强调基础研究最终会给全社会带来长远的效益,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基础研究应该由自由的好奇心驱动,因而应抵制官员和公众对科研活动的内容和方向指手画脚,主张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必须由科学家自己控制。布什鼓吹的科研自由,指的是由政府向科学家们大量拨款,但又毫不干涉款项用途,由科学家内部组织,自我管理。
但是这种科学家享受特权的观念首先是过于精英主义的,布什似乎相信科学家不止在专业知识方面远超公众,而且对其他专业领域能有更好地把握,在道德伦理和运筹管理等方面也比一般人明智。因此科学家一定能胜任政策制定者和资金统筹者的职责。但事实上,现代科学家大多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超出狭窄的专业领域时,科学家的表现和一般人并没有太大差别。科学家并不会在道德操守方面天然地占据优势地位,更不一定懂得运筹大笔资金在无数资助方向之间妥善调控。总之,布什拒绝非科学家参与科技政策的态度是一厢情愿的。
二十世纪后半叶,从农药DDT到疯牛病,在无数次公共危机中,科学家们并没有体现出崇高的道德立场,相反,许多时候科学家群体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利益,有意对公众进行欺骗和隐瞒。另外,八十年代兴起的STS学科把科学家放到实际的社会境遇中进行研究,发现科学活动并不是一种超然于社会之外的纯粹活动,科学家和企业家、政治家或任何普通人一样,都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权力关系的制约。总之,人们不再认为科学家拥有超然的社会地位,可以免于社会的约束或免于承担社会责任。到了二十世纪末,各发达国家一般都会引入某种“委员会”来制定一定的科技政策和科技伦理规则。一般来说,一个健全的“委员会”除了有科学家参与之外,还需要法律专家、伦理学家、民众代表等多元身份的参与者。

霍尔特的新导言写于新冠疫情暴发之后。霍尔特以新冠疫情为例,强调科学家不能躲在象牙塔内独善其身,而应该承担社会使命并承担更多与公众沟通的责任。他认为,科学的进步并没有在美国抵御新冠疫情方面提供足够的力量,“这是科学与公众关系上的失败,而这也正是被布什报告以及随后的辩论所严重忽略的事项。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在这方面,布什似乎有些目光短浅……他所提倡的科研体系在促进研究繁荣的同时,也促成了科学与公众的隔绝”。当前除了新冠疫情之外,气候危机也迫在眉睫,气候变化证明了现代科技的发展能够带来深远的社会影响,但这种影响未必总是积极的。布什津津乐道于科技对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因而鼓吹加大对科学家的资助。但是当负面影响增加时,科学家需要为之负责吗?难道科学家有权把好的影响归功于自己,但面对坏的影响时就事不关己了吗?
总之,科学家的社会地位被打回原形,从超然世外回归于道德主体,科学家并不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科技创新”也不能被无条件地认为是善事或中立的事情。“负责任的创新”的理念成为欧美学界的共识。

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
当然,批评不代表贬斥,如何理解布什报告,并不是一个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的抉择,我们需要指明布什报告的局限性,但并不是说布什报告并没有值得学习的意义。
就美国而言,对于自由科学的理解,似乎经历了一个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最后又回到看山是山的曲折过程。最初美国文化是完全受实用主义主导的,完全不重视不能直接看到效益的自由研究。在二战前后,一方面是由于布什报告的激励,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从欧洲(特别是德国)吸收了大量科学家移民,改变了美国科学界的风气,“自由的科学”得到了更多的提倡。到了二十世纪末,科学被打落神坛,人们又把视线转回科学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影响上面。
但这种“回归”其实是一种升华而非倒退,中间的环节并不是被单纯地放弃了,而是被有所吸收地“扬弃”了。前面说到,布什报告的缺陷主要在于,一方面对基础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划分过于简单化,另一方面在于有意无意地让科学与公众相隔绝。但是,布什报告蕴含的一些洞见并不完全依赖于上述观点。
在我看来,布什报告的一个关键洞见在于,他提示人们注意分辨科技研发中“短期目的”和“长远影响”的差异,并提倡人们更加关注研究的长远影响。
布什关于“基础—应用”的二分或许是过于简单化的,但这一区分的实质可以理解为研究与现实效益的接近程度。所谓的“基础”,指的是从短期上看并不直接产生社会效益的研究;而所谓“应用”,是在短期内就看得到实际效益的研究。不妨把“基础—应用”的二分替换为“长期—短期”的尺度,后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分割,而是一个连续谱。后者也不能简单对应于“科学—技术”的二分,在任何一门具体技术领域的研究方面,我们也可以区分出“长期—短期”的不同取向。例如,同样是研究“人工智能”,诸如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研究、对计算机算法语言的底层开发等,其目的显然是相对长远的;而为购物平台开发一个智能客服,为餐馆开发一个智能炒菜机,这也都算研究人工智能,但成果和效益是眼前可见的。
布什发现,前一类研究在长远上看能够促进后一类研究,但它的影响很难预先规划。许多长远看来意义重大的研究,在最初可能完全看不到实用的前景,或者在预期的前景之外打开出乎意料的应用空间。布什说道:“许多最重要的发现都是出自截然不同的实验本意……任何一项特定研究的结果都无法被准确预测。”
当然,“无法预测的长期影响”并不一定如布什所想的总是积极的,有些研究在短期上看影响积极,而长期的影响却是破坏性的。例如DDT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化工产物早在一八七四年就被化学家合成了,但最初看不到明显的用处,直到一九三九年科学家发现了它的杀虫作用,才展现出积极的社会效益。在广泛应用之后,其消极影响又逐渐暴露出来,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中被全面揭示,最终被禁止使用。在DDT的例子中,一八七四年到一九三九年再到一九六二年,不同的时间尺度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效益,从无用到有益到有害。

最近高速发展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也是一例。它起源于关于细菌免疫机制的研究,这一研究并没有很明显的实用效益,但科学家最终从细菌的免疫机制中掌握了能够精确编辑基因片段的基因剪刀技术,这一技术有着广泛的实用性,在医学、农业、工业等许多领域都影响深远。不过,这一技术也带来了生物恐怖主义的风险,以及促进了一些僭越伦理的行为,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危害也不能忽视。
所谓“长期—短期”的尺度,也可以对应于“不确定—确定”的尺度。一般来讲,短期效益更具确定性,更容易评估,而长期的影响更难以预料,但却更加重要。
这种对长期效益的关注—无论是有益一面还是有害一面—都是值得借鉴的。
既然我们跳出了“科学与技术”的简单二分,注意到在所谓“技术”的领域同样有“长期—短期”的不同导向,那么我们也可以扩展布什对“自由”的提倡。
布什认为,“广泛的科学进步源于学者的思想自由及研究自由,他们理应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索未知,自主选择研究的方向”。布什所谓的自由,指的是研究的驱动力应当以学者内在的“好奇心”为主导,而不是外在的效益指标为主导。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长期—短期”导向的差异,只有以短期效益为导向的研究,才容易用一些外在的标尺去衡量成效,而那些在短期看不到明显效益的研究,很难找到精确地评估其研究进展的外在尺度。
但研究终究不是胡来,总也需要有一定的评估尺度,这种尺度无法由外在的功效来衡量,那就只能从内在的尺度来衡量了。这种内在的尺度取决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很难一概而论,非要概而言之,那就是“好奇心”了。换句话说,无非就是“有趣”。托马斯·库恩把科学研究的常规活动称作“解谜题”。科学家就像玩拼图游戏那样,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但不需要诉诸外在的目的,解开谜题,拼成更完整的图景,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布什进一步指出,这种自由的研究必须由政府而非企业来主导资助,因为企业或资本总是倾向于短期利益,即便是投资领域所讨论的“长线投资”,就自由研究的潜在效益而言也过于短暂。所以,不能依赖逐利的投资者来赞助科研,那就只能由着眼长远的政府或公益机构来赞助。
在这里,布什的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把自由的研究局限于基础科学,而忽略了在各门应用科学和技术领域也存在超脱于短期利益的研究活动。其次,他忽略了同樣是着眼于“实际效益”,投资者的逐利和一般公民的公益关切并不能混为一谈。
布什警示人们,不能只以急功近利的眼光来促进研究,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与急功近利的研究相对立的,并不仅是“自由求知的纯粹科学”,还存在“好奇心驱动的应用研究”“追求公益的理论研究”“自由创造的技术研发”等复杂维度。
美国学者司托克斯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科学出版社1999年),就指出了布什的盲点。他指出,求知取向与应用取向并不是互斥的,巴斯德的工作就是同时兼具求知驱动和应用意义的研究。二○二一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奖励的大气物理学研究也是一例,这一研究领域始终是基础理论性的,但正在日益受到有关气候危机的公共关切的驱动。
科学家不应被投资者牵着鼻子走,但也不能放弃公益心。爱因斯坦教导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另外,在技术发展的领域,发明创造的驱动力也并不总是实际应用。技术史家发现,许多新兴技术在发明之初往往并不显示出明显的用处,经常是满足游戏或审美的取向。例如有学者认为,农业的发端不是为了解决食物短缺之类的问题,而是起源于园艺和祭祀活动;轮子最初可能是作为玩具被制作出来的;晚近的摄影机、留声机等最初也更像玩具,自行车最初主要被贵族用来攀比和竞速……
总之,布什倡导的“自由”是可贵的,但我们应当进一步拓展自由的含义。所谓自由,应当是允许研究者在各个研究领域中受各种研究动机的驱动,而不是只限于纯理论科学这一个领域并且只受到好奇心这一种驱动力的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