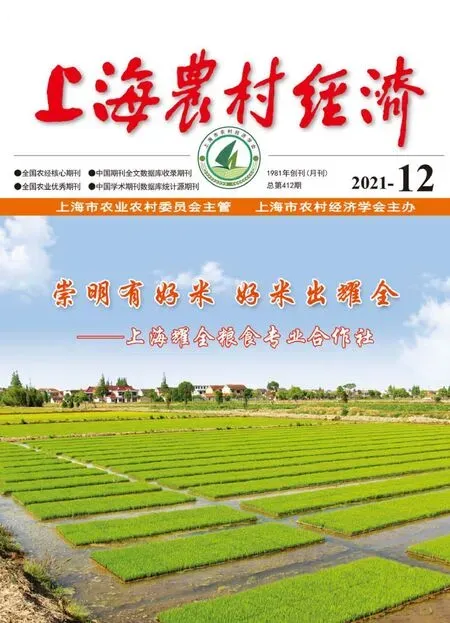“都村”:创新上海大都市乡村振兴模式刍议
2022-01-10杨贵庆
■ 杨贵庆
一、时代背景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21年6月出台了《上海市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它是依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纲要》制定的,将对上海大都市乡村振兴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规划》为上海大都市乡村振兴提出了明确定位:“强化城乡整体统筹,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战略,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当前大都市乡村的突围发展,“城乡融合”是关键。在新的城乡关系上考虑上海大都市乡村振兴,即“跳出乡村论乡村”,是创新和定位乡村发展模式的前提。
早在2018年1月4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指出要“结合上海实际抓紧抓好乡村振兴战略”。会议强调“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下决心研究提炼展现好上海农村的建筑和文化特色,在发展特色产业下功夫”。对标《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的目标,“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如何通过城乡关系的重塑来发展卓越全球城市的乡村特色产业?
作为全球城市的上海大都市乡村,需要突破原有发展路径依赖,寻找符合大都市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革、生态环境韧性和海派文化赓续的创新模式。
二、功能转型
《规划》提出上海“十四五”乡村振兴主要指标,其中第9项“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签约完成量”从2020年基期值2.7万户,到2022年要确保完成5万户目标值并“持续推进”。截至2019年底,上海市农村居民户数94.37万户,村委数1570个,那么得出上海目前以行政村计的平均户数为601户。如果以平均每个行政村管辖2-3个村庄居民点(自然村)来估计,即每个村庄以200-300户来估算,需要拆并大约200个村庄。这些要被拆除的村庄中可能不乏具有多元价值的类型,具有未来大都市多元功能承载发展的可能性。
农民相对集中上楼居住的结果之一,从居住密度上是集约了,从数量上获得了建设用地指标,这的确是一种提升土地使用效率的办法。不过,这一做法尚需要深入、精准化对待。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历史文化故事可挖掘的、村庄整体空间格局有特色、生态环境有基础的老村,虽然当前物质环境条件不尽如人意,但被物质表象掩盖下的人文精华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文化经济价值,拆并了实在可惜和不应该。因此,对于拆并村庄的做法,需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慎之又慎,亟待通过创新途径来获得综合效益最大化。
原有乡村风貌和建筑空间肌理植根于原有的河道水系和农田等空间关系,它的空间性是长期以来乡村社会关系的产物,乡村的历史人文内涵都源于既有建筑布局或街巷格局,难以复制,是一种深层次的“乡愁”。就目前规划和建筑设计水平或时间急迫状况来看,“平移”居住点统一规划设计,其结果基本上都是按照当下建筑标准或工程规范的方案,再加上建筑层数和房屋间距的一致性,很难实现原来的灵动活泼、耐人寻味的街巷空间格局。因此,如何通过功能转型发展、新的功能注入,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把原有的村庄进行产权政策处理,部分或整村加以改造、提升,以满足国际化大都市各种功能外溢的需求,将会是一种振兴模式的补充,呈现不一样的发展特色。
三、模式创新
综上分析,有必要从大都市发展的经济阶段和资本扩张的特征来认识城乡关系的重塑。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经济、文化自身需要和内生动力,强力推进了要素积聚和辐射流动,是当前上海大都市乡村突围发展的机遇。即便是受制于土地使用规模增长的严控,使得大都市空间扩张受到限制,但是其功能扩张不会受限。因此,大都市功能扩张对周边乡村发展带来辐射作用,并建立都市区内部和外部城郊(包括近郊和远郊)乡村之间的依赖互补关系。而当今便捷的轨道交通、高速公路、互联网等全覆盖支撑,使得大都市乡村与都市区内部在高水平层面建立各种要素互动具有可能性。
事实上,《规划》已经充分反映了当下城乡要素双向平等流动推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性。《规划》明确了上海大都市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基本形成城乡空间布局合理、功能多元多样、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完善、乡村风貌宜人、公共服务健全、基层治理有序、农民生活富裕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并且,要“让乡村成为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亮点和美丽上海的底色,为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现代化乡村奠定基础”。
因此,本文建议,应抓紧评估出一些有特色、有价值、有潜力的大都市乡村区域的村庄,特别是那些要被拆并但是有特色基础的村庄,作为新功能注入,实现各种可能的转型发展,同样可以达到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效益最优,从而实现乡愁保留与功能转型相结合。正如《规划》指出,“上海乡村具有城郊融合型特点,在形态上要保留乡村风貌”,“在发展方向上要强化服务城市发展、承接城市功能外,凸显乡村地区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
对此,本文提出“都村”的新概念。它来源于“大都市乡村”的村庄,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大都市乡村区域的村庄。它是对融入、植入或重构具有新的特定城市产业经济功能的大都市村庄类型的统称。其对应的英文创造一个新的名词“Metropollage”,是“Metropolis”(大都市)和“Village”(村庄)的联合。建立这个新概念,是对于像上海这样国际化大都市乡村地区、与都市功能紧密相关的特色村庄的概念和发展模式创新,并为今后这一创新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基础,为在国际上关于大都市乡村领域的研究争取中国话语、提供中国经验。“都村”模式演进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主要是大都市乡村同大都市外溢功能的单个要素进行选择性加合,特别是旅游、文创、康养、教育、研发等,简称为“农+”,传统农业开始转型,乡村产业开始多元。这一阶段基本上是市场推动的,各类社会资本自发寻求利益增长的项目和环境,“都村”的雏形显现。
第二阶段:增强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大都市要素规模化向乡村流动,通过空间规划和基础设施支撑,形成大都市乡村的增强型农业(不局限于单一种植业),传统农业快速转型为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附加值乡村产业。这一阶段的经营主体是建立在多元合作基础上,特色产业和空间布局以自上而下的统筹规划安排为支撑,“都村”快速成长。
第三阶段:成型阶段。这是“都村”发展的高目标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大都市要素和乡村产业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形成各具特色的、扎实稳固的现代化乡村产业。彼时,传统农业已经完成质的转型,实现了多元融合、功能转型,形成特色鲜明的、与大都市功能紧密关联的“都村”。这一阶段的经营主体建立在自上而下政府主导规划安排和自下而上市场主体竞争发展相结合的基础上,“都村”成为大都市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
“都村”的类型包括但不限于农旅型都村、农文型都村、农康型都村、农养型都村、农教型都村等多元形式。其中一个或若干个功能类型为主导(或主体),原有的村庄转型为机构所在的村,例如金融村、研发村、康养村等。可以设想,某些全球五百强企业在上海的总部或分支机构,不仅可以选址在大都市中心区的五星级写字楼内,也可以通过收储转化一个村庄进行整村有机更新,形成别具特色的、设在乡村的“总部村”。某些高端科研机构也可以通过整村改造形成“科技村”,研发人员在工作之余推开窗户看到的不再是高楼林立的都市景象,而是春光明媚的田园风光。某些养老机构可以通过部分或整村有机更新,加建电梯和连廊,设置系统化的无障碍设施和智能设备,成为“康养村”,老人们看到的不再是生硬的养老院围墙,囿于养老院院子或楼道内走动,而是在改造后的村内河道边、田野旁等开敞的自然环境里安度晚年。这些特色功能的“都村”虽然村庄空间环境还是原来的基本格局(“旧瓶”),但是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功能已经发生质变(“新酒”)。成型的“都村”,在大都市乡村地区成为一种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微引擎”。
四、结语
大都市乡村振兴的模式需要大胆创新突破,尤其是对于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城乡要素可以高水平流动、融合。“都村”模式,可以成为上海大都市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不过,要实施这一模式,还需要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构建适宜的“都村”类型。此外,还要充分结合乡村民意,制定实施办法,完善实施机制,把握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趋势,注重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赓续,编制具有创意的规划设计方案和具有效率的实施分期,不可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