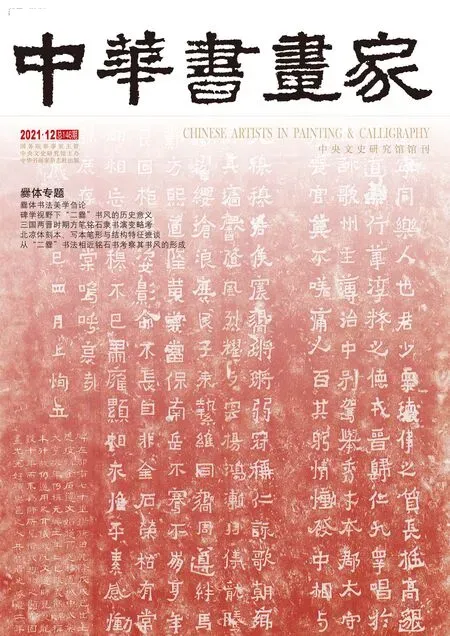《爨宝子碑》审美意趣摭析
2022-01-06聂子皓
□ 聂子皓
云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两地之间虽有地缘阻隔,但在历史的变迁中或多或少有着相关联系。
从《爨宝子碑》的形制、内容、汉字形态诸多方面均可窥见其与汉文化之间的关联。在形制上,《爨宝子碑》承于汉碑,碑首呈琬圭之形,中部刻碑额:“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志文文体也承于汉代文赋体例。东汉时期已形成了序、铭、颂、乱、诔等多形式的碑文撰写风格。其中,序多写于开头,多为碑主生平与家族、家世简介;铭,是对碑主先祖的赞美;颂多赞美之词,用于碑主本人;诔,又多累列碑主生平以及表达悲悼之情,有着述德后写哀的文本结构;乱,多为总结文章纲要;而铭、颂、诔结构多为四字韵文。《爨宝子碑》碑文内容大致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墓主爨宝子生平简介,第二部分是以四字韵文歌颂碑主爨宝子,第三部分是正文下方列故吏13人。在文本开头格式上与汉碑不尽相同:汉《张迁碑》:“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已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鲜于璜碑》:“君讳璜,字伯谦,其先祖出于殷箕子之苗裔……”
汉代察举征辟制推行使其郡守皆有幕僚,跟随着大量的故吏、门生。而其死后,碑刻多为门生故吏所立,所以在碑阴、碑侧、碑身下方有姓名刊刻。如《张迁碑》碑阴有记捐钱者,《北海相景君碑》所列故吏门生54人,《鲁峻碑》碑阴列故吏门生42人。故《爨宝子碑》的碑文与汉代碑文撰写形式相比,两者撰写风格一致。
汉代碑版艺术自身发展流变中,综以概观,整体发展宗以书体演变,由早期古篆的圆转而逐渐递变。西汉早期碑版其结字多有篆体,点画与转折间圆浑流转。至东汉时,碑版书法时有方笔表现,于《汉碑全集》中《王孝渊碑》较早具有方笔特点,此后东汉方笔碑刻逐渐增多。以东汉时期四个不同时间段的方笔特征碑刻:东汉永建三年(128)《王孝渊碑》、东汉延熹八年(165)《鲜于璜碑》、东汉熹平二年(173)《熹平石经易残石》、东汉中平三年(186)《张迁碑》,与东晋405年云南地区《爨宝子碑》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爨宝子碑》方笔特点的艺术渊源以及对汉碑的审美继承。
《王孝渊碑》中的“长”“年”二字,字形较为方整,起收笔形状已有方意但比较模糊,横画已有一定的向背关系但不明显,雁尾朦胧含蓄。《鲜于璜碑》中的“下”“新”“里”三字字形方整但稍有收放,起收笔有明显的加强方笔痕迹,横画排叠有明显的向背关系,笔画的雁尾有上扬之势,带有装饰性。《熹平石经易残石》中的“尽”“理”二字,字形更加方整、规范,横平竖直,横画起收处有明显方笔刻画并有“下弧”之势,雁尾平出,但横画起收笔有少许上扬。《张迁碑》中的“君”“长”“晋”三字,字形方整,笔画带有趣味性,横画起笔为方笔上扬,雁尾上扬,横画有下弧。《爨宝子碑》中的“君”“军”“晋”三字字形与前者相比更加方峻、张扬,其“张扬”是因笔画起收不仅加强方笔程度,且在方笔上有上扬之势,笔画下拓更加鲜明。

[清]阮元 跋吴云临《爨宝子碑》 纸本释文: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保护之。总督阮元。
从整体上看,表现出东汉方笔类型碑刻不断变化的过程。从《王孝渊碑》至《熹平石经易残石》可作为方笔类型趋于成熟的阶段。《王孝渊碑》碑主王孝渊作为朝廷官员,以记录碑主生前事迹而祭奠颂德所刊,具有名门贵族的私人属性。《熹平石经易残石》由时任议郎蔡邕正定六书文字所书上石,立于洛阳太学讲堂前供学子们传抄与校对,因此,无论从文本、意义、书写、审美等方面,此碑均与统治阶级的意志相关联。《熹平石经易残石》的方笔审美特点作为规范的符号在以后的碑版中呈现。东汉永寿二年(156)的《礼器碑》,记录修缮孔庙、增置礼器、吏民共同捐资而立石,其功能属性同于后来《熹平石经易残石》,而《礼器碑》在艺术审美表达中呈方势。故官方碑版的刊立多以方笔呈现,一方面在于碑制森严的规制亦需要相应的审美文体去迎合,同时,方笔符号的秩序性是统治阶级稳固社会审美的手段。

[东汉]张迁碑 拓本
官方方笔碑版的刊立使得后来贵族仕人所刊立的私人碑刻多带有“方”的艺术元素,使得“方势”从单一的用笔表达逐渐趋于多方位塑造。《张迁碑》已是东汉晚期,已经不再一味追求用笔的方正,而是追求体势、结字、用笔表达等方面的方正。如《张迁碑》中“君”字,不再强调主笔,笔画收紧,以打开内部空间为主,带有雁尾的横画减少向右上斜出,而是近乎直角的向上出雁尾,无疑强调了字形的方式。“君”字下部的“口”为迎合整字的方矩,缩小并向外布置,以求方势不被破坏。
因此,“方”的审美意趣在东汉隶书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强调,甚至强化追求。对于位于边陲地区的云南等地,受当时时代书风审美影响,也表现出对汉代官制碑版艺术审美的延续。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①故汉末三国至东晋,碑刻以“铭石书”书风为主要,“铭石书”在“礼乐制度”影响下带有秩序性、规范性、庄严性而被世人应用。
上述碑刻笔画中的方笔形态,从《王孝渊碑》的朦胧到《鲜于璜碑》《熹平石经易残石》《张迁碑》的规律,再到《爨宝子碑》的奇崛,审美的庄严感不断被强化。云南独特的人文地域具有较强的民族性与原始信仰。如唐宋前云南先民奉以“鬼主”制,爨氏于此时称以“大鬼主”。据《新唐书·南蛮传》载:“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②基于原始的文化信仰,该地区有浓厚的祭祀文化,并逐渐形成“巫术礼仪”,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中对“巫术礼仪”这样论述:“在巫术礼仪中,内外、主客、人神浑然一体,不可区辨。特别重要的是,它是身心一体而非灵肉两分,它重活动过程而非重客观对象。因为‘神明’只出现在这不可言说不可限定的身心并举的狂热的巫术活动本身中,而并非孤立、静止地独立存在于某处。”③可知人在巫术礼仪中是极为热诚的,在此过程中对人的精神方面有极大影响与塑造。而《爨宝子碑》地处于有“巫术礼仪”色彩的“西南夷”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其书法风格融地域特色,透露着神秘色彩。结合碑制与字形艺术,是对碑主的祭奠与怀念,书丹与刻工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将自身的情感融于作品中,其庄严生动的气韵仿佛透露出对于上天的崇敬,体现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爨宝子碑》是汉文化与云南地域先民智慧的结晶,是多民族和谐统一而铸造出的审美艺术。《爨宝子碑》继承了汉代的时代特征,从碑制体例,志文形式等方面与汉地碑制近乎一致。《爨宝子碑》既保留了前代艺术旨趣,同时结合自身多民族文化区域优势,发展出具有哲学意味审美特点。■
注释:
①《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第46页。
②[宋]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315页。
③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