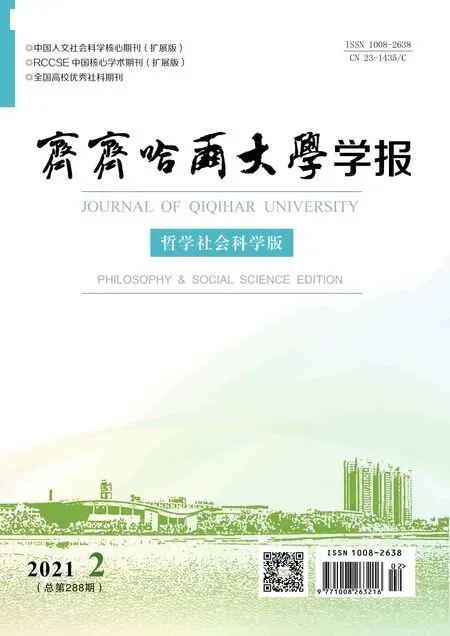身份·仪式·认同:电视文化节目《一本好书》的文化记忆
2022-01-01刘晓燕陈接峰
刘晓燕,陈接峰
(安徽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在科技兴盛,信息流变的新时代语境下,我们经历着一场文化信息革新。虽然流媒体场域、数字媒体嵌入我们现实生活,但是电视媒体依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电视节目所表现的文化记忆特质不可忽视。“文化记忆建构了一个空间,是对于意义的传承,摹仿性记忆、语言和交流:交往记忆、对物的记忆几乎都可以应用到这个空间之中。”[1]文化记忆的中国风韵,因新时代的语境,而延展出新的时代风貌和艺术风范。同时,电视媒介书写着新时代的文化篇章,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风向标。文化节目《一本好书》以“场景式”的读书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与情感、文化与记忆的盛宴。进入新时代,响应文化强国的时代号召、凝聚家国认同的精神需求,电视文化类节目《一本好书》所雕刻的中国文化记忆,呈现身份诉求、仪式想象和集体认同的三副面孔。
一、身份诉求:电视文化节目的文化机制
《一本好书》的制作团队将传统经典与传播相统一,深入到电视节目文化层面探求不忘初心的创作理念,充分展现出作为一名文化传播者的定位。着眼于中国大地上涌现出的文艺作品,正在影响我们人类文明进程和当下精神状态的,恰恰是对今天有效的传统经典,这些传统经典作品具有被大众广泛阅读的推荐价值。制作团队将传统经典作品的呈现方式重新编织,充分挖掘节目的情感表达,实现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责任感。《一本好书》的播出,获得受众广泛喜爱,成为一道独特文化景观。“这一现象后的深层原因,在于这一文化类节目体现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净化语言环境、激活真正的“文化记忆”、提升观众文化素养有一定的推动作用。”[2]电视文艺工作者不断地对电视节目进行再发现、再创作,进而丰富了电视节目呈现样态,表现中国故事的多元内涵。 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审视,《一本好书》是新时代话语创新性表达,是电视节目工作者把关人身份的着力展现。
《一本好书》将知识性的内容传授给观众,以流行元素拉动阅读增长,丰富观众认知。之所以节目《一本好书》把阅读作为着力点,是因为观众需要借助传统经典输入认知养料,进而树立终身阅读,终身学习的理念。就今天而言,大众不再以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为主要摄取知识方式,而是更倾向直观生动的图象,成为信息的“游牧者”。导演关正文认为,节目《一本好书》具有“试衣间”的功能,把书籍的选择权放置于观众手中。首先,观众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了解书籍的概况。其次,加深对感兴趣传统经典作品的接纳和认同。“借助文化记忆术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承,文化记忆术,即如何储存、激活和传达意义。[3]《一本好书》通过戏剧化呈现的方式建构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激活观众记忆,致力于打造服务大众的电视节目。电视节目《一本好书》的本质,在于对优秀作品再发现,完成电视节目制作者和观众身份构建,进而激发观众情感的认同。如在演绎《月亮与六便士》这一期节目中,充分借助图像表达的优势对多重场面进行调度,以高超的视觉交互技术,为观众呈现欧式典雅住宅、巴黎小酒馆、简陋画室,再到无人的街头。缝隙切换带领观众走出现实世界的程式化空间,置身声色俱佳的镜像世界。对12本经典书籍进行关联性创作,融入易被观众接受的娱乐元素,消除文化客体和接受主体、原著和读者间的隔阂,促进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每一本著作的故事化编排,都赋予观众新的感受角度,形成新的话语场。
二、仪式想象:电视文化节目的文化传播
《一本好书》使名著场景在戏剧舞台上真实呈现,“舞台演绎名著”的仪式激发观众阅读兴趣,对传统经典作品产生深爱之情。仪式被定义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套行为方式。它们经常被功能性的理解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过渡、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4]传统媒体时代,观众阅读名著的方式局限于纸质版书籍,而媒介技术的变迁催生了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由纸质版书籍的语言符号转化为场景符号的“仪式”媒介方式。“既有的“历史典故”与如今的舞台演绎相结合,然后以叙事的方式编织成一个观照古今的“仪式类型”文本”。[5]由此,《一本好书》为观众创造出一场经典著作的仪式展演,完成了仪式想象,强化观众对于经典著作感知,扩展其审美维度。
文化的仪式感,是通过视听符号、环境符号得以再现和表述的,在电视综艺节目中,仪式变成了文本,文本成为大众仪式想象的媒介。“我们通过对各种符号系统的建构来创造、表达、传递关于现实的知识以及对于现实的态度。”[6]《一本好书》中的视觉符号和环境符号将节目内容重新编织,深入挖掘文学经典所蕴含的情感力量。人物本身、演员、环境构成了电视文化节目《一本好书》传播的视觉符号,描绘了一幅中国传统历史形态和社会发展背景的画卷。在《万历十五年》一期中,万历皇帝人物本身具有典型的符号,在历史记载和观众感知中经典重现距今400多年的历史人物;另一方面万历皇帝扮演者王劲松,不仅完成了对于万历皇帝的诠释,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将人物的人生阅历引入到自我情感之中,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除此以外,节目《一本好书》中主持人嘉宾三人围绕在书桌前,分享与交流环境的设置,打造出一种深度阅读的环境符号。第二舞台以主持人与嘉宾蒋方舟、朱大可访谈的形式,对主舞台演员生动的演绎做出感悟性的评论,在感受跌宕情节气氛的同时,以普通大众的视角去审视这段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
观众将观看电视节目《一本好书》视为参加一场弥散仪式。在这种仪式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得到了描述和强化,在历史文化中寻找国家记忆,在文化记忆中增强文化自信。“传播的仪式观并不在于信息获取,而在于某种戏剧性的行为,在这种戏剧性的行为中,观众作为演出的旁观者加入了这一权利纷争的世界。”[7]这时,我们面对的不是信息效果或功能问题,而是观看节目中呈现和介入观众在生活与时间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一本好书》利用内容到演绎形式的创新性表达既是一种仪式化行为更是一种戏剧性的行为。《查令十字街84号》的读书推荐人潘虹,以舞台演绎式的记忆视角,介入主人公海莲在生活与时间中扮演的角色,从而使观众获得戏剧性的满足。节目描绘了海莲和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里四位店员书信往来的场景,营造了真实书信往来的读书氛围,传递出读书人对于书籍的真正情感,以及对于这段奇遇的唏嘘与珍惜。透过节目所呈现出的戏剧性行为,我们切身感受到海莲对于读书的饥饿感,把每一次新书的到来都如获至宝,跟随着海莲我们也走入“喧嚣被关在门外一阵古书陈旧气味扑鼻而来的查令十字街84号”。
三、集体认同:电视文化节目的文化价值
文化类节目《一本好书》,不仅展现出创作者身份诉求的姿态和作品的仪式想象,而且具有社会性的集体认同。以青年为代表的“粉丝”群体,通过博文评论的形式对节目内容、演员的表演,以及节目所传达的文化价值表达态度,其中正向的态度表现出受众对于节目的认同。“粉丝不仅仅是读者,更是积极挪用文本,把阅读文本的奖励转化为参与式文本(participatoryculture)的积极参与者。[8]青年文化积极地适应新媒介环境,并精准表达文化中出现的时代症候,建构了以青年为代表的“粉丝”群体。作为文本盗猎者的粉丝在“积极”参与亚文化的同时,也对主流文化产生强烈的猎奇心理和认同感。粉丝积极参与节目文化的传播,势必成为增强集体认同的重要方式。《一本好书》每一期播出后会吸引一大批粉丝入驻节目,粉丝利用微博平台发表原创性评论,积极参与到一本好书的话题讨论之中。有粉丝表达对书中角色的喜爱以及演员演技的肯定,如“海莲是一个爱书如命的女孩,有着自己的个性和对书绝对不将就的人,尤靖茹真的吧青年海莲在舞台上演绎出来了,很棒”。“……王劲松老师的表演,自然流畅,举重若轻,轻松从容,娓娓道来,和人物融为一体”。也有粉丝在挖掘节目细节和情感力量的同时,进一步解读节目文化价值。如:“偶然看到了一本好书……把书当朋友体味不同人生,给书一个体现价值的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成长的机会”,“最近看了一部特别有质感的综艺《一本好书》……我们跟随着演员的步伐发现,除了真相还有人性,既感慨人士,又反思自己,既思考未来,又活在当下,关注当下社会身边的问题”
此外,粉丝群体将节目传达的文化价值引入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通过弹幕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粉丝积极与节目制作者以及其他受众展开讨论,在参与、互动中领略经典文艺作品的独特魅力,从而完成集体文化价值的认同。“我们保存着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9]观众通过回忆方式完成对过去的重建,个体记忆的产生,只有根植特定的情景和社会语境中才能够生成记忆。一部好的作品是呈现过去、启迪当下,关照未来。在节目《一本好书》所演绎作品《红岩》中,实力派老艺术家凭借自身高超的演技将峥嵘岁月中的故事再现。故事讲述热忱的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崇高事迹。革命先烈们即使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心中依然有信仰,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而坚持。节目的最后一个片段讲述了革命先烈许云峰上刑场前的自述,这一段内容浩然正气,催人泪下。观众感受到了荡气回肠的民族精神,纷纷弹幕留言:“拍得很生动,泪崩了”、“不改变黑暗的环境,就没有和平安乐可享”。观众也被革命先烈们的无私奉献所深深打动,懂得当下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并对祖国表达最美好的祝愿。如:“勿忘前辈无私奉献,致敬前辈们,加强我们自身”、“我们现在走的路都是用你们的鲜血生命铺成的”、“一笔千秋,万代敬仰,一世芳华,护国永昌”、“盛世如英雄所愿,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节目传达的文化价值弥合了现实和历史之间的距离,成为当代个体对革命先烈精神的承续。文化类电视节目《一本好书》,是新时代下电视节目的创新表达,以全新的形式诠释文化自信,为民族记忆的传承给予更多力量。
综上,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考察,电视文化节目创作者为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精神,通过仪式和精神层面的努力,促进社会文化的形成,借助文化手段将文化得以代代传承。电视文化节目《一本好书》,除了在节目创作上流露出创作者的身份诉求,在节目内容呈现时以符号化的方式完成其仪式想象,也以集体认同的方式实现节目的文化价值。因此,电视文化节目积极主动地书写新时代文化记忆,在文化记忆传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