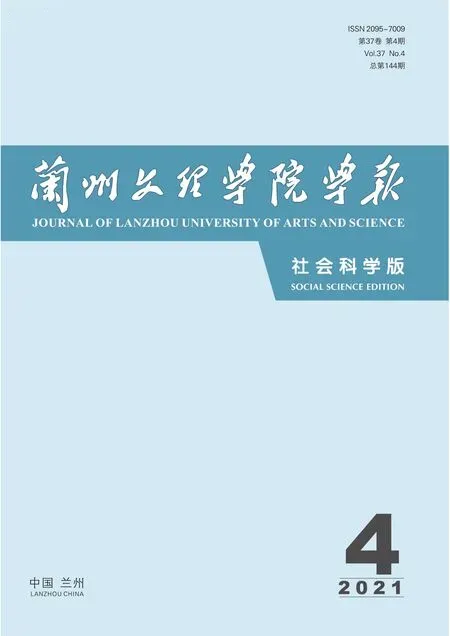中国西部儿童诗歌的文化生态价值
——以邱易东、高凯、王宜振、钟代华等诗人为中心的考察
2022-01-01陈柏彤
陈 柏 彤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西部作为被关注的文学现象,既表征着客观地理概念,也指向作家的西部身份以及由此秉持的文化自觉。本文所研究的中国西部儿童诗歌,主要指发生发展于中国西部大地上的儿童诗歌创作活动,范围限定于云南、广西、贵州、西藏、重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十二省区市。它们书写西部地缘文化风情,描摹儿童现实生活,展示多元民间艺术特点,不仅体现了独特的儿童诗歌创作风貌,还反映出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也就是说,西部儿童诗歌的主题内容形式等与文化生态之间具有内在关联。
一、诗歌主题与文化价值观培育
一般而言,儿童文学作品往往会通过儿童读者的阅读接受作用于他们的社会生活,对儿童乃至成人的思想感情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韵律自然、朗朗上口的儿童诗歌亦是如此。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欠发达、现代化进程缓慢,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西部儿童诗歌作品通常呈现出独特的主题形象。
“自然”是诸多西部儿童诗歌作品观察描写的主要对象。一是因为地理环境特殊,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季风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从西南到西北跨地分布,戈壁、盆地、草原、雪山、雨林、湖泊等多重景观成为创作者得天独厚的审美对象,这些自然资源为西部儿童诗歌创作提供了天然土壤。二是儿童天生亲近自然,他们灵动真善的本质、追求自由的天性与自然万物和谐相通,那些以儿童为本位的诗歌作品容易将自然作为表现儿童世界的主导视角。在中国古代,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书写自然的山水田园诗一度成为汉族诗歌的重要流派,但儿童诗歌与意象复杂、意境静谧、情感深刻、修辞丰富的成人诗歌不同,其自然主题更为简单鲜明和活泼。比如,诗人们擅长描述四季,王宜振的《初春(一)(二)》《春天很大又很小》《春天是一只鸟》《春天的小花朵》《春天的鸟语》《撕开春天》《夏之歌》《秋之歌》《秋风娃娃》《冬天的小雪人》、钟代华的《春天是个大舞台》《春雨》等诗将春天的露珠花草、蝴蝶虫鱼,夏天的稻田西瓜、荷花萤虫,秋天的苹果石榴、玉米高粱,冬天的童话世界、雪人冰柱等情境呈现在读者眼前。同时,不少动植物语汇也充斥于各类作品的诗里行间,既有小雏鸡、小燕子、小羊羔、布谷、黄鹂、蝈蝈这些普通动物形象,也有鹳鸟、白桦树、胡杨林、果花、红松树、沙枣花等颇具地域特色的种类,它们共同丰富着儿童诗歌所构筑的自然景观。此外,常见的天气、风景也为诗人们所关注,在钟代华《雨窗的眼睛》中,雨水与孩子的感官融为一体;《雨季的遐想》中,漫长的雨季与少年心事难以分离;《海螺沟的海螺哪儿去了》中,迷人的风景与童话的幻想交相辉映。自然是万物之源,孩子们与世界最初的接触就存在于四季天气、花草虫鱼、山河风景这些在成人看来显得微不足道的自然元素中,儿童诗歌对自然主题的特别关注,不仅代表一种来自儿童本身的认知和观察视角,更重要的是,诗歌描写能够激发儿童对词语、视觉、听觉的联想能力,引导儿童好奇自然、亲近自然、爱护自然,有助于培养儿童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
儿童自出生以后就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同时也存在于社会环境之中,他们持续不断地接受周围人事及身体的内部信息,其中,家庭结构、家庭情感的稳定在儿童情感系统和社会性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亲情”成为不少西部儿童诗歌所着力表现的主题。以甘肃诗人高凯为例,他的诗歌中包含奶奶爷爷、父亲母亲各类人物形象,有对奶奶“一串甘甜的奶汁”[1]的思念,对卷着老旱烟、唱让人“淌眼泪珠珠的信天游”[1]30的爷爷的怀恋,也有对“整日背着双手……稳当踏实”[1]39~41的父亲的崇拜。能够发现,高凯对亲人及亲情的描述并不是稚嫩天真的,而是从自身童年记忆出发,经过简洁凝练的艺术加工,阐发西北孩童的乡土体验和心灵思绪,显出生动的纯真和土意。还有一些诗人则在告白亲人的言语中传达出一种成长焦虑,譬如邱易东的《妈妈,不要送伞来》向妈妈倾诉小朋友的心事,希望妈妈不要送伞来,让自己走在小雨中、用书包顶着头、感受自由的勇敢和快乐,这是儿童自我意识的生长和表达;《关于爷爷的钓竿》则通过儿童视角表现对生态环境污染的愤慨,特别是“自从那座愚蠢的工厂/弄脏了水里的蓝天/你的钓竿/和我游泳的渴望/都被锁在了岸边”[2]等诗句,直白地反映出孩子们对现代工业污染的恐慌。也就是说,西部儿童诗歌中的亲情主题既浸润着朴实的乡土气息,也具有现代性反思意识,它们能够启发儿童从多重角度思考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对儿童的成长发展具有一定作用。
尊重儿童天性,表现儿童情感和生活只是儿童诗歌所着力反映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通过诗的朗诵,通过对祖国大地、校园生活等情境的描述,促使孩子接受诗的教育、接受正面的道德情感观念,也是儿童诗歌重要的创作主题。事实上,自《诗经》以来,“诵”的特征即与诗教传统一同发生,王宜振的《21世纪校园朗诵诗》明确将诗歌与朗诵结合起来,将大家共同关心的现实和诗歌联系起来,接续了这一优秀的诗歌文化传统。在王宜振的朗诵诗中,有献给未来的世纪之歌,《走进新世纪》等诗歌展望21世纪的科技文化、经济自然,表达了对新世纪的热情期待和对未来人生的积极展望;有献给祖国的深情之歌,《中国》《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诗歌回顾祖国曲折的历史、歌唱祖国的辽阔丰富、表白与祖国的不可分割;也有赞颂少年儿童美好品质和梦想情怀的激昂之歌,称赞少年真诚好奇、探索不凡、担当未来的精神,表达保护母亲河的热忱、缅怀革命先烈的悲痛、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愿和反对环境污染的呼声。这些诗歌从书面形态上升到语音形态,不仅呈现出情感真挚、回旋反复、韵律优美、节奏铿锵的艺术特点,而且,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价值倾向能够引导青少年发展,帮助他们成长为关怀现实、热爱祖国、拼搏奋斗的新世纪人才。邱易东在《中国的少男少女》的后记中同样也秉持“提高文学修养”“丰富想象力”[3]的教育立场,提倡现实精神和科学观念,他认为孩子的内心世界本就是丰富奇特的,儿童诗歌不一定要以不谙世事的童真童趣去迎合孩子,而应站在自身丰富的生活体验和人生高度上,以具体新颖的艺术形象引导读者积极向上,诸如《中国的少男少女:你是谁》《一个女孩的肖像》《绿叶化石:一瞬之前一瞬之后》等诗就从多重角度探讨了人的自我塑造、未来追求及生命思索等问题,与少年儿童成长的自我意识产生共鸣。
林文宝先生曾言,“诗作得好,作不好,是另一回事,作诗的心灵倾向,是人生教育所不可缺的,也是最重要的”[4]。西部儿童诗歌站在儿童立场,从个人生命体验、社会经历和人生经验出发,书写阐发自然、温情、智慧的诗歌主题,使之作用于儿童的思考和感情,对儿童树立美好道德品质和正确文化价值观念具有重要作用。
二、诗歌精神与文化内涵彰显
诗歌是人类最精粹的艺术之一,是能直面人类灵魂、纯化心灵的针剂,作为滋养人类精神的食粮,它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因素。在物欲迷离、信仰危机频发的现代社会,西部儿童诗歌能为诗坛带来什么?能为读者带来什么?这是关乎诗歌精神的追问。
西部儿童诗人通常成长生活于地形复杂、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自然精神是与他们诗歌创作发展密切联系的内在精神。一方面,它体现为一种平等意识。不少儿童的苦恼在于不被成人世界所看见,而许多非人类生命的苦恼则在于不被人类所看见,西部儿童诗歌透过未经世事过滤的、清澈纯真的儿童眼光,走进那些还未被现代化文明侵蚀的生灵并观察体会他们,以平等姿态对之进行诗化的记录。西部儿童诗歌不仅反映儿童的现实生活,更对儿童眼中的自然触以浓重笔墨,譬如在诗人笔下,小到一朵蒲公英(林染《蒲公英》)、一只小螃蟹(邱易东《小螃蟹独自度过一个冬天》),大到戈壁沙漠高原或山峰(林染《沙漠之歌》《哦!我的戈壁》《青藏高原》等),都是儿童所好奇、幻想和追求的对象,这种“发现”的眼光是儿童纯真童趣的外在折射,也是诗人从儿童本位角度书写诗歌的表征。另一方面,自然精神表现为对万物有灵的信仰和敬畏生命的意识。西部地区的生活环境总体而言并不宜人,在现代文明不发达的时期,人们往往习惯于将一些无能为力的愿望交给神秘的自然力量,这种代际相传的敬畏情怀使万物皆有灵魂的观念根驻诗人内心,因而,那些有生命的动植物或没有生命的季节风景,都是他们的书写对象,草木鸟兽、山川丛林等也成为有知觉有思想的存在。这亦是儿童诗对皮亚杰所提出的“儿童泛灵论”特点的表现。
西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遭遇到许多现实问题,这一情境下,西部儿童诗歌亦体现出鲜明的现实精神。这一精神首先表现为一种乡土情怀,例如在高凯的童诗中,有“张狗蛋”“李铁蛋”“赵狗剩”等充满乡音的人名,有“搓玉米”“打酸枣”等乡村画面,有“羊粪蛋”“鸡冠花”“苦苦菜”“黑牦牛”等富含乡味的物象,也有“没盐的年代”这样苦难的回味。中国人眷恋乡土,就像树木扎根文化的土壤,是与民族历史密切相关的客观现实。这一精神也体现为一种时代关怀。如重庆诗人刘泽安十分关注山里孩子、留守儿童的问题,其《留守儿童的诗》《孤独的少年与村庄》《留守儿童的四则运算》《留在村庄的儿童》等诗反映了留守儿童的生活现状和情感心理,还有王宜振在《母亲河,红领巾为你植树》等诗中,把当下备受关注的现实联系起来,引发读者对当前社会共同关注问题的思考。此外,有关儿童成长的书写也是现实精神的重要表现。蒲华清从心智逐渐成熟、善解人意的学生角度出发,创作了《我们老师的窗口》《浇花》《每当老师发下作业本》等诗歌,将老师的辛勤和白发描绘得细致入微,邱易东在《男孩:关于战争的抒情》《一颗被砍伐的树怎样获得生命》《高地:追寻或升华的进行曲》等诗中,给予孩子们对战争的认知、对生命的思考、对成败得失的看法等以诗意的表达和升华。
新时期以来,西部地区在经济文化上得到较为充分地开发,恰如一部诗选的前言所述,西部诗歌的精神在于“为社会主义理想所鼓舞的积极开拓与献身精神”[5],开拓精神是西部诗歌的基本底色,在儿童诗中体现在不同侧面。它首先呈现出一种少年精神。这种少年精神,是《胡杨》《珠穆朗玛》《野草莓》(林染)等诗对万物的探索,是《渴望之歌》《探索之歌》《真诚之歌》(王宜振)等诗对美好品德的追求,是《走进少年》《拥有明天》(王宜振)等诗对未来的好奇,是《留守儿童日记》(刘泽安)等诗与苦难的对抗,也是《登山少年》《旅途少年》(钟代华)等诗对冒险的尝试。同时,它呈现出一种磅礴的气概,既包含对西部辽阔疆域的书写,也有对少年儿童想象力的发掘勘探。例如,钟代华的“川西童话”和“遵义童话”系列对放牧山峰、海螺沟、红石滩、四姑娘山等宏大风景进行描述;林染的抒情诗歌对博格达峰、白杨林、疏勒河、塔里木河等地的山川地理展开形容;邱易东的诗歌将思考延伸至对“宇宙”(《绿叶化石:一瞬之前一瞬之后》)、“地球的孩子”(《地球的孩子不要黑雪》)等有关时间和空间意识的探索之中。诗人们以中国西部的自然人文地域为诗歌情感的触发点,从高视点广角度透视其文化心理与当代意识,由此呈现西部文学凝重深沉、质朴厚实的诗学生命形态。
西部是严酷的、苍凉的,同时也是充满前景诱惑的,诗人们以坚韧乐观的态度,为儿童诗歌注入一种面向未来的幻想精神、冒险精神,激发儿童发自内心的情感声音。诗歌表达了他们立足现实对未来的期盼。特别是在王宜振的校园朗诵诗中,孩子们对21世纪中国有“大地辽阔、原野漫漫”“百花盛开、阳光灿烂”[6]的企盼,有“共同为西部的开发献出光热”“走进西部,投入大开发的行列”[6]102的梦想,也有“把握机遇”“走向成功的彼岸”[6]131的奋进。诗歌也体现了孩子们对自然的幻想和思维的奔驰。它们把春雨打扮成小姑娘(钟代华《春雨》)、让阳光像一个娃娃一样活泼自在(钟代华《阳光娃娃》)、举办森林音乐会(钟代华《森林里的音乐会》);它们也通过一块化石或一片绿叶追问生命的意义、探寻人类亘古的谜思。“幻想是儿童文学精神世界的灵魂”[7],西部儿童诗歌的幻想精神以地域人文为底色,构建出现实乐观、积极浪漫、唯美理性的童年审美形态,充实丰富着儿童文学的表现维度。
在乡村、都市、民间、地域等多样文化形态浸润下的西部儿童诗歌,具有独特的精神特质,既是西部自身物质精神样态的反映,也是西部文化内涵的彰显和升华。探寻西部儿童诗歌精神现象,能够激活儿童诗歌中的“西部精神”、拓展儿童诗歌本土创作向度中的原创思维。
三、地域特点与文化多样性保护
相对于儿童诗歌这一大概念来说,中国西部儿童诗歌最明显的不同便是地域限定语——西部。中国西部地大物博,且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本文所涉及的高凯、邱易东、钟代华、林染、王宜振、刘泽安、蒲华清等诗人均来自西北或西南地区,他们的儿童诗歌创作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语言文字是地区文化的地质层,它无声地记载着一个地区物质和精神的历史,在西部儿童诗歌作品中,这样的活化石无处不在。比如,王宜振在《笑丢了》一诗中,描述一个天真烂漫的山女子失去笑容,万般寻因后发现她是因为要跟一个“很阔很阔的男人”[8]结婚而丢掉了笑,很阔很阔就是典型的陕北方言,表示身份地位较高的意思。此方言词汇的使用既交代了山女子不再欢笑的原因,同时也使诗歌更加明白易懂、具有质朴气息。再如高凯的《村小:生字课》使用方言炼词,对“蛋”释以“张狗蛋的蛋”“马铁蛋的蛋”[1]、对“花”释以“王梅花的花”“曹爱花的花”[1],这些颇具乡村气息的人名,反映了流行于陇东农村地区名贱人贵的起名心理,即人们期望通过命名来提高孩子们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本事,使之健康成长;此外,还有他的《玛曲二题》,使用藏语“玛曲”作黄河的奶名,书写黄河周围草原云朵、羊群牦牛等藏区风景,展现了西部地区多民族文化交汇的特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英语的普及、普通话的推广不同程度地对地区方言文化产生了冲击,保护地区语言文字实际上就是保护民族历史记忆,儿童诗歌以方言入诗的做法对于传承地方语言文化,增加儿童诗阅读的趣味性和本土性具有一定价值。
西部地区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诗人们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它们并赋予其一定文化内蕴,生产出适合儿童接受的自然人文知识。四川诗人邱易东曾在诗歌中介绍了多样地形地貌,比如海螺沟、红石滩和四姑娘山,它们均是四川省境内因特殊地质条件形成的著名景区。海螺沟有冰川雪谷、温泉森林,红石滩的石头遍布山谷,四姑娘山陡峭壮丽,但诗人并没有直观地描述这些特点,而选择从景观名字出发,以联想、提问等方式诠释自然谜思。诗歌以“海螺哪儿去了”[9]“谁是大姑娘/谁是二姑娘/谁是三姑娘/谁是四姑娘”[9]发问,引起读者好奇,并结合抒情与叙事,呈现活泼有趣的自然奇景,例如:“天边跑来一群阳光孩子/捧出山泉/揉出溪流”[9]是阳光和山石溪流交相辉映的海螺沟;石娃们离开了山峰妈妈,被风雪“冻红了脚/冻红了手/冻红了脸蛋”“全身呀,都长出了红斑斑”[9],讲述的是布满鲜红石头的红石滩;雪花儿“还没到冬季就早早地爬到山尖尖/去采摘朵朵白云/去迎接白色王国的冬天”[9],陈说的是终年积雪的四姑娘山。这些诗句充分考虑到儿童天真且充满想象力的心理特征,使用童话拟人的手法描绘自然风景,既可以从科学角度让孩子们了解到山川河谷最突出的地理特点,又能在人文情感方面加深他们对地区景观的认识理解,丰富儿童的艺术思维和文化记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塑就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并在诗歌创作中呈现相应特征。其中,有多样的民间艺术,如诗人通过描述安塞剪纸——“只有在她的剪刀下/沉重的生活才变得很轻”“剪了一对蝴蝶飞上天/剪了一只蟋蟀跳进草丛/剪了一只蜜蜂钻入花心/剪了一只小鸟唱在枝头”[10],既体现了剪纸艺术的高超,也反映了安塞女人赡养老人抚养孩子、操持家务的辛苦;还有让小村庄牛起来的秧歌(《陕北秧歌》),“悲也得意喜也得意/把日子吹得像鲜葱/把生活吹得像诗句”[10]的唢呐(《陕北唢呐》),使小村“枝繁叶茂/蓬蓬勃勃”[10](《陕北信天游》)的信天游等,无不彰显烘托着黄土高原粗犷高亢的地域风情。同时,王宜振、高凯等诗人对特色吃食、民俗文化的表现也十分丰富,如王宜振在《父亲从乡下来》《山村的夜》《陕北小米》等诗中描绘陕北高原农村地区常见的“烟锅袋”“苞米酒”和“小米”,向读者展示浓浓的温暖乡情,他的《寡妇门前的脚印》《她走了》等诗还涉及纳鞋底、搓麻绳等传统制作手艺;而高凯在《爷爷的河》《搓玉米的奶奶》等诗中,也将民间生活形态融入唱信天游、搓玉米等具体细节描写。这些书写是诗人自身童年经验的积累和闪现,也是推动现代儿童了解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
西部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复杂的自然条件可能限制其各方面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需要发扬,更需要传承和保护。诗歌因为其朗朗上口的韵律特点,成为最适宜启蒙和教育儿童的体式,所以,西部儿童诗歌对区域语言文字、自然人文和民俗习惯的描述,不仅能够发掘阐释当地文化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域气息浓厚的作品也能增进儿童对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对展现西部儿童诗歌文化多样性特点、扩大其传播接受范围、增强地方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结语
儿童诗歌是诗的一个分支,它既具备诗歌属性,也具备儿童属性,是关涉文学、哲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的重要文学体裁;同时,阅读鉴赏儿童诗歌可以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丰富儿童的思想情感,提高他们的审美认知,有一定教育价值。西部儿童诗歌既包含儿童诗共通的艺术性,也打上了鲜明的文化烙印,因此,探讨诗歌的主题精神、地域特点与文化价值观、文化内涵及文化多样性的培育保护问题,有多重意义。从儿童成长教育的角度看,能够引领读者阅读方向,参与塑造读者的价值理念,使少年儿童在了解地方文化生态特点的基础上萌发保护传承的观念意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诗歌阐释发掘地方文化、凸显地域风格,能启发西部地区文化发展的创新路径,增强西部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力;从当代诗歌与儿童文学创作来看,重视西部儿童诗歌的精神内容及诗教功能一定程度上能对当代诗坛出现的私语化倾向和儿童文学体裁发展不均的现状有所改善。本文的研究对发掘西部儿童诗歌的时代价值、推动西部儿童诗歌发展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