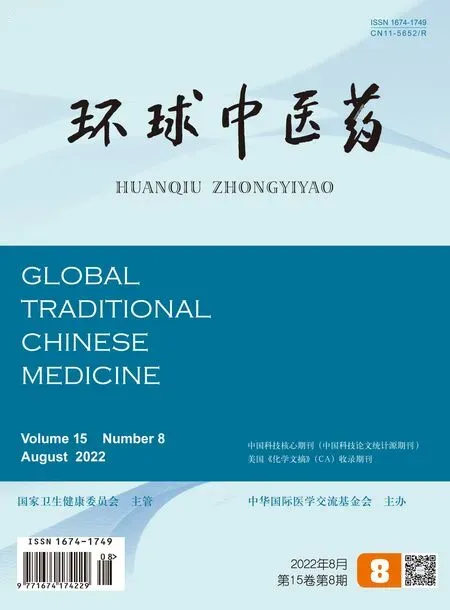中药改善心肌梗死促血管新生机制的研究进展
2022-01-01刘甜甜张彦丽何婷姚魁武曹俊岭
刘甜甜 张彦丽 何婷 姚魁武 曹俊岭
心肌梗死是世界范围内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心肌梗死属中医“胸痹”“心痛”范畴,其病机主要是脉络不通导致的瘀血阻滞心脉。由于瘀血不去,新血不生,故治疗原则为祛瘀生新,首先通过祛瘀法除去体内瘀血,其次通过生新法促进新血生[1]。祛瘀生新与治疗性血管新生相对应,血管新生是在缺血、缺氧条件下,从预先存在的血管中,形成新的毛细血管,它是机体的适应性反应,受多种环境因素的调控。新生血管可以重新供氧,改善心肌梗死后心肌重塑。临床上胸痹、心痛以血瘀证为基础,治疗则以活血化瘀药为主,兼以益气、行气、化痰等方药,祛瘀通络、推动血液运行、促进血管新生、建立侧支循环,进而改善心肌梗死后胸闷、心痛等症状。因此,通过药物干预或理化治疗手段促血管新生,加速缺血心肌的血运重建已成为临床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重要策略。本文通过查阅近十年相关文献,对中药促血管再生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为新生疗法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1 中药增强干细胞血管修复与新生能力
1.1 心肌梗死后血管新生机制
急性心肌梗死后,新血管的形成从缺血边缘区进入梗死组织,恢复对梗死组织的营养和氧供,该过程是介入术后修复的关键。心肌梗死存在3种新血管生成方式,即以出芽方式从预先存在的血管中形成毛细血管,由小侧支动脉形成血管,由内皮祖细胞生成新血管[2-3]。血管新生由缺血引起,始于血管通透性的增加,基底膜和细胞外基质进行降解,此后内皮细胞沿细胞外基质的新区域迁移,形成新的管腔,血管被周细胞覆盖并融入循环。动物模型中,血管新生可以由生长因子以及细胞治疗诱导,促进血管再生是克服持续微血管功能障碍的关键[4]。近年发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内源心脏干细胞、胚胎干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等具有组织修复和再生特性的干细胞[5-6],拥有较强的促血管新生潜力,可以增强心肌再生、修复缺血心脏,逐渐成为心肌梗死的重要治疗途径。
1.2 中药动员内皮祖细胞调控心梗后血管新生
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是具有促血管生成潜力的干细胞统称。当组织受到缺血缺氧损伤时,骨髓来源的EPCs被释放入血,启动损伤级联信号,进行迁移和归巢,促进机体组织修复[7]。研究表明,新生小鼠的心脏动脉内皮细胞对缺血损伤具有独特反应,缺血会刺激动脉细胞迁移并重新组装成侧支动脉,而激活趋化因子配体12(CXC chemokine ligand-12,CXCL12)-趋化因子受体4(CXC chemokine receptor 4,CXCR4)信号可以进一步引导动脉重组,促进心脏再生[8]。此外,已有研究证实骨髓来源的EPCs具有分化为内皮细胞的潜能,将EPCs注入心肌梗死的心脏可以促进血管新生改善心脏功能[9-11]。
补阳还五汤、血府逐瘀汤等活血化瘀类中药可通过增强EPCs的动员、增殖、分化、迁移和侵袭能力,增加细胞因子分泌,促进内皮修复和血管新生[12-13]。刘革铭等[14]发现外周血EPCs移植同时给予丹参注射液治疗能够显著改善急性心肌梗死大鼠的心功能,起到协同修复心肌组织的作用。研究显示白藜芦醇具有促进EPCs生成血管、抑制EPCs凋亡,不仅能增加循环EPCs的数量,还可以直接修复内皮细胞的完整性[15]。另外,瓜蒌皮可提高急性心肌梗死大鼠心肌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内皮型一氧化氮合成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9,MMP-9)的表达水平,显著增强EPCs的动员,发挥梗死心肌的保护作用[16]。可见中药通过促进EPCs动员及血管生成,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心肌梗死提供潜在的细胞治疗手段。
2 中药调控促血管生成因子及其受体
2.1 中药促进VEGF表达
血管新生机制较复杂,多种生长因子、蛋白酶、粘附分子和细胞因子均参与血管新生的调控过程[17]。血府逐瘀汤是治疗心肌梗死的经典名方,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可以增加血清和心肌组织NO水平,诱导EPCs分化,促使内皮细胞迁移、粘附,促进急性心肌梗死大鼠缺血区血管新生[18]。麝香保心丸是缓解急性心肌梗死和心绞痛的有效中成药,可以改善心肌缺血患者血液流变学参数,增加VEGF、NO及一氧化氮合酶水平,促使冠脉侧支循环建立,缩短梗死患者发病频率和持续时间[19]。此外,银杏内酯B能通过增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的心肌VEGF表达而促进血管新生,并且通过降低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发挥抗炎作用,减少心肌梗死面积[20]。柚皮素可通过提高心脏CD31、VEGF和成纤维生长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表达含量,促进心肌梗死大鼠血管新生[21]。一些中药配伍药对,如黄芪、丹参也能增加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和VEGF表达,调控促血管新生作用[22]。
2.2 中药增加阳性血管密度
活血温通方可以下调钙离子/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II氧化和磷酸化活性,提高心肌梗死大鼠缺血心脏CD34和α-平滑肌肌动蛋白阳性血管密度,减轻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抑制心肌凋亡和促进血管新生,从而改善梗死区内环境和增加心功能恢复[23]。中药复方可以通过升高促血管生成因子,发挥促血管新生作用。单味药及其活性成分也具有明显的促血管新生特性,鹿茸可通过上调VEGF、bFGF等促血管新生因子的表达,增加微血管密度与小动脉生成,有效促进血管新生,修复心梗大鼠心肌损伤和改善心功能[24]。彭程飞等[25]和魏英等[26]采用人参皂苷Rg1和人参总皂苷干预大鼠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肌组织CD31阳性细胞血管密度和表达水平明显升高,说明人参皂苷Rg1和总皂苷能促进心梗后心脏血管再生,进而增加血氧供应和恢复缺血心脏功能。
2.3 中药提高促血管生成因子受体表达
吴佳妮等[27]研究揭示益气活血方能降低VEGF受体2(VEGF receptor 2,VEGFR2)及上游缺氧核心调控因子HIF-1α的蛋白表达和mRNA水平,逆转心肌梗死大鼠心肌毛细血管形态病理改变。淫羊藿总黄酮能上调急性心肌梗死大鼠缺血心肌CD31与α-平滑肌肌动蛋白水平,同时增加蛋白激酶B磷酸化、bFGF、VEGF及受体VEGFR2表达,促进缺血心肌血管新生,改善梗死区附近心肌灌注不足,抑制急性心梗后心室重构和心力衰竭的进程[28]。丹参素和羟基红花黄色素A单用或配伍均可上调VEGF、基质细胞衍生因子-l(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1,SDF-1)、CXCR4表达,发挥促血管新生作用[29]。另外,枸杞多糖可以通过增加CD133、VEGFR2蛋白表达,激活内皮细胞功能,促进新生血管生成及血流灌注,从而明显改善心肌梗死后大鼠心肌缺血损伤[30]。因此,无论是中药复方、单方、配伍药对或中药活性成分均有显著的血管新生因子和下游受体蛋白的促进作用,最终增加心肌梗死后心功能恢复。
3 中药靶向调控外泌体介导血管新生
外泌体是从细胞释放到血液的纳米囊泡,具有调节血管新生的作用。近年来研究发现,外泌体可以激活心血管疾病中有益的信号通路,可能介导人类干细胞的促血管生成作用,外泌体可以通过血液传递miRNA和蛋白质,是一种潜在的细胞间通讯模式。治疗上,外泌体可能介导干细胞的许多有益特性转移到心脏[31-34]。外泌体通过传递与血管新生相关的miRNA,如miRNA-21、miRNA-132、miRNA-210等促进下游通路血管新生相关的基因表达,或间接增强促血管新生相关蛋白表达,提高内皮细胞在缺血缺氧环境下的存活、迁移、成管能力,从而促进心肌梗死区域血管新生。
研究显示活血益气方可以升高急性心肌梗死大鼠血清miR-484水平,通过调控外泌体miR-484靶向受体,参与VEGF诱导的内皮细胞增殖、分化,进而诱导心肌梗死后血管新生[35-36]。傅小媚等[37]发现脂多糖刺激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产生的外泌体注射小鼠心脏后,可明显改善小鼠心肌梗死后的心脏收缩功能、纤维化沉积和IL-6、IL-1β、转化生长因子β、趋附因子CCL2等炎症因子水平。此外,芪参益气滴丸能调控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外泌体miR-155靶向调节线粒体自噬改善心肌缺血,从而起到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后局部炎症,改善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功能的作用[38-39]。目前,利用外泌体可以找寻冠心病的诊断和预后分子标记物,揭示缺血性疾病的发病机制,还可以作为缺血性心脏病治疗的靶点和手段,以及作为药物载体实现靶向给药。此外,通过基因修饰手段增强外泌体介导的心脏修复作用,以及将外泌体与生物活性肽结合形成工程外泌体的靶向缺血心肌治疗[40],是外泌体目前在心血管领域的研究热点。
4 中药介导血管新生的相关通路
研究证实中药介导心肌梗死后血管新生有以下几个通路:(1)VEGF/eNOS信号通路。VEGF是参与内皮细胞功能的重要调节因子,VEGF通过促进eNOS丝氨酸1177位点磷酸化,产生NO促进血管再生[41]。(2)Notch信号通路。Notch信号由受体(Notch1、Notch2、Notch3、Notch4)和相应配体(GLL1、DLL3、DLL4、Jagged1、Jagged2)及胞内效应分子、相关酶组成。Notch能调控多种血管新生因子表达,介导微血管生成过程,是组织再生和修复的重要通路[42]。(3)蛋白激酶D1(protein kinase D1,PKD1)及其下游通路。PKD1能降低心肌梗死后炎症反应和抑制细胞凋亡,促进血管新生和修复梗死心肌组织。PKD1在新生血管的形成、稳定和成熟中发挥重要作用。(4)沉默信息调节因子3(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3,SIRT3)/β-连环蛋白(β-catenin)/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 γ,PPARγ)信号通路。SIRT3可调节内皮细胞能量代谢、心脏功能、血管生成和细胞凋亡过程,与心肌重构、心力衰竭、心肌梗死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43]。β-catenin促使心肌纤维化。PPARγ降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血管新生。β-catenin和PPARγ之间存在负反馈调控[44]。
4.1 中药激活VEGF/eNOS信号通路促血管新生
VEGF/eNOS信号通路参与了小鼠和人源心肌细胞增殖和心脏再生功能,可能对干细胞分化和预防心肌梗死具有重要治疗意义[45-46]。土贝母苷Ⅰ是从土贝母中提取的三萜皂苷,研究发现土贝母苷Ⅰ在体内和体外都能促进血管生成,降低eNOS活性可抑制其促血管新生作用。提示土贝母苷Ⅰ可能是一种治疗缺血性疾病的新药,它能通过激活eNOS/VEGF信号通路保护血管生成[47]。此外,VEGF和VEGFR2的激活也是诱导血管新生治疗的重要信号,丹参活性成分及其制剂可以通过上调VEGF/VEGFR信号通路,提高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分化与管腔形成能力。同时可通过激活SDF-1/CXCR4信号通路,提高EPCs的趋化与归巢能力,进一步增强缺氧诱导因子的转录活性,调节血管新生相关因子,如VEGF、SDF-1α、促血管生成素1及其受体Tie-2、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β、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和一氧化氮合酶等表达发挥体内外促血管新生作用[48-50]。
4.2 中药调控Notch信号通路促血管新生
李双娣[51]在“祛瘀生新”治法基础上,以行气化瘀扶正为治则,采用宣痹通瘀方干预心肌梗死大鼠,可以改善心肌氧化损伤和左心室功能,缩小梗死范围,促进梗死区血管新生,升高心肌VEGF表达,抑制Notch1、Dell4的表达,表明宣痹通瘀方的作用可能与调控Notch/Dell4信号通路相关。王思颖[52]发现通心络能激活Notchl/Jaggedl/VEGF通路,促进梗死边缘区微血管新生,增加新生微血管密度,减少细胞凋亡,稳定心梗大鼠心率,减少心律失常发生率,改善心肌氧供和内皮功能。此外,联合应用川芎、白芍能改善心肌梗死小鼠左室射血分数、降低梗死面积,增加心肌梗死边缘区CD31表达水平,降低梗死区CD31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水平,且增加心脏组织中FGF受体1、SDF-1、心肌营养素1、Notch1表达,降低HIF-1α表达。当加入Notchγ分泌酶的抑制剂后,川芎和白芍联合改善心功能和心脏病变的作用均被抑制,同时Notch1表达降低[53],说明川芎、白芍配伍可能通过激活Notch信号和干细胞动员促进缺血心肌血管生成。
4.3 中药激活PKD1及其下游通路促血管新生
研究证实,丹参酚酸B可以减少心肌梗死大鼠的瘢痕组织,降低心肌胶原比例,改善因缺血受损引发的心肌纹理模糊、闰盘断裂、线粒体萎缩、微血管管腔塌陷等病变,并上调心脏PKD1、HIF-1α、VEGF和Ⅷ因子表达[54],说明丹参酚酸B可能通过激活PKD1/HIF-1α/VEGF信号通路增加心肌梗死后大鼠血管新生,保护缺血心肌组织。组蛋白脱乙酰酶5(histone deacetylase 5,HDAC5)是PKD1的下游蛋白之一,它在抑制调控基因的表达和诱导染色质的修饰中起重要作用。PKD1与HDAC5结合后上调HDAC5,控制相关基因表达并调节内皮细胞的迁移和增殖[55]。研究发现,黄芪甲苷可明显升高心肌梗死大鼠心肌组织PKD1、HDAC5、VEGF的mRNA和蛋白水平,而PKD1的特异性阻断剂CID755673则会显著抑制黄芪甲苷组大鼠心肌组织的相关mRNA和蛋白水平[56],结果提示黄芪甲苷可能调控PKD1/HDAC5/VEGF信号发挥促心肌梗死后大鼠心脏血管新生作用。
4.4 中药调控SIRT3/β-catenin/PPARγ信号通路促血管新生
研究发现中药可通过SIRT3/β-catenin/PPARγ信号通路发挥抗心肌梗死后的促血管新生作用。荣霞等[44]的研究发现积雪草酸可以明显改善心脏功能,增加微血管密度,提高心肌SIRT3、β-catenin、PPARγ的mRNA水平,同时降低血清IL-6、TNF-α、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的含量,表明积雪草酸可能通过抑制心脏SIRT3/β-catenin/PPARγ信号通路,促进急性心肌梗死模型大鼠血管新生及保护梗死心肌组织。谢方方等[57]发现蒲参胶囊可以增加心脏VEGF、bFGF水平,提升SIRT3和β-catenin的表达,同时抑制PPARγ含量,提示蒲参胶囊可能通过调控SIRT3/β-catenin/PPARγ信号改善急性心肌梗死大鼠的血管新生和心室重构作用。此外,芪参益气滴丸能显著改善心梗后心脏射血分数和短轴缩短率,抑制IL-6、TNF-α、NF-κB表达,增加微血管密度和心肌组织SIRT3、β-catenin的mRNA水平,降低PPARγ的mRNA水平,说明芪参益气滴丸可能通过激活SIRT3/β-catenin/PPARγ信号通路降低急性心肌梗死大鼠炎症反应,促进血管新生,从而改善心肌功能[58]。
上述研究表明中药方剂可能通过多个不同的信号转导通路介导心肌梗死模型动物的促血管新生作用,逆转缺血心脏结构病变,增加微血管密度,改善心肌血氧供应,从而增加心功能恢复。但目前对中药干预心肌梗死的促血管新生作用及其机制的挖掘还只是冰山一角,尤其是中药配方的促血管再生机制及药效物质基础尚不完全明确。随着研究深入,将来可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中药有效成分和通路参与心肌梗死后的血管新生与修复作用。
5 结语与展望
综上,中药可能通过骨髓来源的内皮祖细胞、外泌体、促血管生成调控因子,以及多个信号通路增加缺血心脏微血管密度,建立侧支循环,促进心肌梗死后血管新生,从而增加血氧供应和恢复心功能。当前,在啮齿动物和细胞实验中观察到生长因子可以刺激血管生成。然而,旨在诱导血管新生的人体试验尚未取得明显成效。此外,心肌梗死后通过干细胞或外泌体靶向血管新生治疗尚处于临床前的研究阶段,相信随着研究技术和再生医学的发展,血管再生疗法终将使心肌梗死患者受益。由于血管新生和心肌再生的相关分子机制研究还在不断更新中,中药干预亦在深入挖掘。因此,探索中药促进心肌梗死后血管新生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完善,确保其在临床应用上的安全、有效,为患者提供最佳治疗方案改善心肌梗死预后功能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