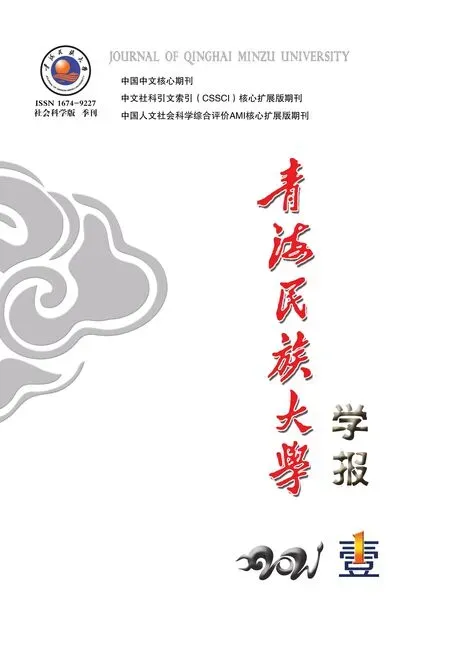关于浙藏敦114 号《肃州府主致沙州令公书状》的几个问题
2021-12-31陆离
陆离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97)
浙江省博物馆藏敦114 号《肃州府主致沙州令公书状》 是一份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的藏文文书,文书图版刊载于《浙藏敦煌文献》,[1]近年来,任小波先生对之进行了录文和译释, 并对涉及的相关史实、文书年代进行了辨析。笔者在其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中涉及的柔然、龙家部族及晚唐五代肃州的龙神信仰等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
首先将任小波对文书的译文转录如下:
“……, 思虑……, 并且前往。 遣使甘州, 乞请…… [狄]银 (jin) 及其臣僚 (blon po)、 茹茹都督 (ru ru’ Ito dog) 等, 达成和断, 新立咒誓,入于安乐。 此后, 前往上部。 据前往上部者所说,未弃恶劣……其于肃州, 亦未通报。 对于府主,忧虑……故而, 未向令公呈请。 商议不谐, 调集……扣留使者。 于是, 令公之愤, 亦受不佳……人主令公, 遣去众多劲旅, 制服门戍, 各个处死。[官]民痛心失望……苦难。
因此, 人主令公, 发菩提心, 为求利益百姓,新增咒誓。 新增咒誓有云: 此后, 肃州府主 (sug cu dbang po) 以及一切百 姓, 龙家 (lung ’bangs) ……等, 对于人主令公, 决不心生邪念。百姓民众, 决不自立为王。 沙州家安善振 (an shan shin) 等, 趋前……祈请神龙 (lha klu) 眷属、 三百六十兄弟、 北方之主毗沙门证盟, 规诫晓谕。 [若违]誓词, 诸事不佳, 众原难遂, 农牧无功。 所居之处, 各色兵器, 击刺其身, 一经起身……戟剑。 划定辖境之后, 母族在右, 子嗣在左……”[2]
以下对与该文书内容相关的几个问题分别加以论述:
一、关于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柔然部族
任小波认为,该文书反映了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文书中称为令公leng kong)925-926 年征讨甘州回鹘、 肃州及肃州地方政权效忠曹议金的史实,文书中的“[狄]银(jin)”为甘州回鹘可汗狄银。 当时甘州回鹘进攻肃州地区的龙家,归义军则派兵支援肃州,将回鹘军队击败。此时,以龙家为主的肃州地方势力对归义军保持依附关系, 这与曹议金不久前亲征甘州得胜有关。浙藏敦114 号文书记载:当时肃州地方政权遣使甘州, 与甘州回鹘可汗狄银及其臣僚(blon po)、茹茹都督(ru ru’I do dog)商议和断之事。 任小波认为,茹茹(ru ru)即柔然部族,其衙帐在河西走廊北部, 但是并未结合有关汉文史料记载对此柔然部族的来源以及与其他部族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对于文书时间的判断, 笔者同意任小波的观点——发生在曹议金征讨甘州回鹘之时,当时,甘州回鹘可汗为狄银, 肃州政权则受到甘州回鹘的某种挟制。 内容与之相关的P.t.1189 号文书《肃州长官向天大王禀帖》年代则较为靠后,在931-935年(任小波认为该文书年代是在967 年前后,笔者不能同意这一观点), 同样也反映了这一情况,虽然当时肃州政权臣属归义军, 但甘州回鹘在肃州也有相当的影响力。[3]从文书内容来看,茹茹都督(ru ru’I do dog) 与甘州回鹘可汗及其臣僚(blon po)并列,不属于甘州回鹘管辖。柔然又称为茹茹、芮芮、蠕蠕、蝚蠕,[4]属于鲜卑、敕勒、匈奴、突厥等许多部族的混合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强盛,建立起柔然汗国,牙帐设在敦煌、张掖以北的漠北地区额尔浑河流域东部,曾吞并高昌国,进攻于阗,北魏和东、西魏都曾与之和亲通使,但最终被突厥攻灭,柔然部族也大部分融入突厥,还有一部分则入居中原内地。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一记载:“芮芮国,爇锐反。亦名耎国。北狄突屈中小国名。”[5]耎国即茹茹的转讹,突屈即突厥。 表明突厥灭亡柔然后,残余的柔然部族仍然聚集于漠北,归突厥统治,此后该部族应该一直居于漠北, 历经突厥、 回鹘的统治。此外,五代胡峤的《陷虏记》记载了契丹西北有妪阙律部族, 其具体情况来自契丹人传闻:“西北至妪阙律,其人长大,髦头,酋长全其发,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黄貂鼠皮,北方诸国皆仰足。其人最勇,邻国不敢侵,又其西,辖戛,又其北,单于突厥,皆与妪阙律同。 ”[6]妪阙律当系柔然王族姓氏郁久闾的同名异译,柔然政权末期东部主铁伐曾被东边契丹所杀, 柔然亡后可能有一部分部众迁入契丹, 辗转到契丹西北定居,其生活习俗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
晚唐五代时期, 柔然在汉藏文书中出现得很少,P.3579《宋雍熙五年(988 年)十一月神沙乡百姓吴保住牒》中记载:
“□负难还,昼夜方求,都无计路□差着甘州,奉使当便去来,至□贼打破般次,驱拽直到伊州界内,□却后到十一月沙州使安都知般次□押衙曹闰成收赎,于柔软家面上还帛□疋,熟绢两疋,当下赎得保住身,与押衙曹闰成□到路上粮食乏尽,涓涓并乃不到家乡,便乃□得人主左,于达坦边卖老牛壹头,破与作粮□牛价银盌壹枚,到城应是赎人主并总各自出银□氾达坦牛价, 其它曹押衙遣交纳(□付) 银价, 又赎身价……伏望大王阿郎高悬宝镜,鉴照苍生,念见保住窘乏之流,今被押衙曹闰成横生欺负。伏乞仁恩,特赐判凭裁下□(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 雍熙五年戊子岁十一月日神沙乡百姓吴保住牒。 ”[7]
北宋初年,敦煌神沙乡百姓吴保住出使甘州,被贼人劫持到了伊州境内, 后被沙州归义军使者从“柔软家”赎出。“柔软家”应即柔然部族,《晋书》卷125《冯跋载纪》记柔然为蝚蠕,[8]《晋书》所采用的史料时间较早,蝚蠕为柔然的原始发音,而柔软与蝚蠕发音最为接近。 当时柔软家应是活动在伊州一带,[9]敦煌汉文文书中目前只见有这一处关于柔然的记载。笔者以为,浙江省博物馆藏敦114 号中的茹茹都督(ru ru’I do dog),应该与 P.3579《宋雍熙五年(988 年)十一月神沙乡百姓吴保住牒》中的柔软家都属于五代宋初活动在河西走廊北部地区的柔然部族,来自漠北地区,但是人数较少,其势力应该小于在晚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汉文文书中频繁出现的回鹘、吐蕃、达怛、龙家、退浑(吐谷浑)、党项、南山(仲云)等河西地区部族。
晚唐五代,柔然部族活动在伊州一带,与之相邻的河西走廊以北地区主要活动着达怛(旦)部族。 归义军同河西走廊以北地区的达怛部族保持着通使关系, 这在敦煌汉文文书中多有记载。 P.4525《都头吕富定状》记载归义军都头吕富定与知客赵清汉出使达怛。[10]P.4061 背有一件写于壬午(982 年)年的《都头知内库官某状》称:“伏以今月十七日支达怛大部跪拜来大绵被子叁领, 胡床壹张。未蒙判凭,伏请处分。”[11]这个达怛大部分应该是活动在河西走廊以北地区的一支达怛部族,该部族派使者前来晋见归义军节度使, 内库官员为其安排住宿事宜。
唐代达怛,源出中国以北地区。《新唐书·地理志》曾记载回鹘牙帐东南有达旦泊,其周围即达怛部族居止之处。此外,立于开元、天宝年代的突厥文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也分别载有“三十姓达怛”“九姓达怛”。 五代时期活动在阴山一带的达怛属“三十姓达怛”或“九姓达怛”的一部分南下者,而在回鹘牙帐东南(达旦泊)一带的达怛则应为九姓达怛。840 年以后,回鹘为黠戛斯所败,部众西逃,其中一支奔安西,一支奔吐蕃(即河西)。 当回鹘西迁安西或南下河西之时,其牙帐附近的属部九姓达怛也可能随之西迁或南下,敦煌文书所见河西北部地区之达怛,应是从回鹘牙帐迁来之九姓达怛。[12]
五代北宋时期, 漠北回鹘故地存在一个达怛国。 王明清《挥塵前录卷四》载有宋臣王延德《使高昌记》记载其出使高昌回鹘的沿途经历,王延德由夏州出发,渡过黄河,取道漠北,经过回鹘故地、马鬃山、格啰美源、伊州,最后到达高昌。 达怛部族在黄河至回鹘故地一带沿路皆有分布,居住于回鹘故地腹心地区的达干于越王子族为九族达怛中地位最为尊贵者,也是当时漠北地区达怛部族的核心[13],该族与其他达怛部族组成了传世史料记载的达怛国。 有学者提出汉籍记录十世纪时期以国王、天王娘子、宰相名义朝贡宋朝的鞑靼(达怛)国,乃九姓鞑靼,堪称九姓鞑靼王国,为当时的漠北游牧政权。[14]
晚唐五代于阗文书P.2741《使臣奏稿》曾经指出,达怛人骑马从北面的Buhathum 到黑山和蓼泉。Buhathum,白玉冬考证其地为漠北地区额尔浑河流域的卜古罕城,[15]又说“从蓼泉到肃州的道路已被达怛人封闭”。 黑山又名紫塞, 在肃州北一百八十里处。蓼泉在今高台县东,属张掖管辖,可知达怛部族活动在河西北部地区,他们来自漠北回鹘故地。 该文书还记载了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时期(9 世纪末期)达怛与沙州归义军、仲云在甘州地区共同采取军事行动,讨伐甘州回鹘。[16]敦煌藏文文书P.t.1189号文书《肃州长官向天大王禀帖》记载931-935 年达怛(da tar)、仲云(ji ngul)、甘州回鹘(hor)在肃州大云寺盟誓不再进犯归义军政权。[17]
茹茹都督(ru ru’I do dog)应该是活动在伊州一带的柔然部族首领, 前面提到柔然汗国灭亡后,一部分柔然部族一直聚集在漠北地区, 历经突厥、回鹘统治,晚唐五代时期,这些柔然部族应当随达怛部族南下进入伊州一带地区活动。浙藏敦114 号文书内容表明,茹茹都督(ru ru’I do dog)当时率领柔然部族和甘州回鹘可汗军队一起在肃州地区采取军事行动。S.367 光启元年(885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大庆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在“伊州”条下记该州人口时说:“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18]并未提到柔然部族的存在,说明他们进入伊州地区应在885 年之后。
P.2970《阴善雄邈真赞并序》是归义军曹议金时期的一件文书,其中记载有归义军官员阴善雄任职瓜州常乐,“达怛犯塞,拔拒交锋”,后来阴善雄又参加了归义军在甘州、肃州同甘州回鹘的战争,“张掖再复,独立殊庸,酒泉郡下,直截横冲”。[19]达怛进攻瓜州常乐,与后来归义军同甘州回鹘在酒泉作战并非同一次战争。活动在河西北部地区的达怛曾经进犯瓜州常乐,可能当时与甘州回鹘已经结盟。 活动在伊州一带的茹茹都督(ru ru’I do dog)也曾率部同甘州回鹘联合在邻近瓜州的肃州采取军事行动,与达怛情况相同。
二、关于龙家部族迁入河西的时间
浙藏114 号文书记载表明,当时活动于肃州地区的主要部族有龙家(lung’bangs)等。 龙家原居西域焉耆,《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赞普赤松德赞传记》记载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攻陷焉耆,龙王(lung gyi rgyal po)投降吐蕃,龙家部族遂迁居至河西等地,当时的吐蕃赞普是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rtsan,754-797 年在位),[20]敦煌汉文文书 P.3328 号所载武涉《上焉耆王诗》,则记录了当时龙家首领龙王还得到了吐蕃赞普的召见及常年赏赐,并率部族迁入河西地区,[21]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记载830 年前后凉州节度使(mkhar tsan khrom chen po)衙署有龙族及羌将军(lung dor gyi dmag dpon),[22]应该是吐蕃统治时期管辖、迁入河西甘、凉地区的龙家部族和羌部族(dor)的吐蕃官员,dor 即 dor po,即指党项羌人,根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t.1287XV《钦陵赞婆与王孝杰之论战》和《新唐书·吐谷浑传》等记载,唐前期甘南地区的洮州羌就是敦煌藏文文书中的dor po,此洮州羌为党项羌人。[23]任小波认为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关于龙家的记载较少,故龙家应是在840 年回鹘西迁时期进入河西,[24]实际上,这是因为当时敦煌只是吐蕃统治下瓜州节度使(khwa cu khrom chen po)管辖的一个州,并非统治中心, 故而这一时期的敦煌文书中记载有关河西、西域地区情况的文书较少。龙家部族当时则被吐蕃安置在甘、凉地区,与羌(dor po,党项羌)部族相邻而居,归属凉州节度使(mkhar tsan khrom chen po)管辖,与敦煌并不属于同一节度使管辖。 而归义军时期,敦煌为归义军政权所在地,归义军政权同河西等地政权、 部族频繁交往并与之发生多次战争,对这些政权、部族情况非常关注,龙家部众又随龙王从甘州迁入肃州,故此,归义军时期记载关于河西地区龙家等部族活动情况的文书较多。
龙家部族当时与吐蕃、 吐谷浑、 回鹘、 党项(羌)、南山等被称为河西地区的六蕃,敦煌汉文文书中龙家经常与羌(党项)并称为羌、龙,也反映了龙家部族与羌(党项)在吐蕃及归义军时期在甘州等地毗邻而居的情形。 而且在840 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glang dar ma)扶植苯教,打击佛教,于842年被杀,二子争立,引发吐蕃分裂内乱,最终导致了吐蕃灭亡,河陇地区的吐蕃边将尚思罗、尚婢婢、论恐热等展开混战,动荡四起,民不聊生,848 年敦煌汉人张议潮乘机率众起义归唐, 建立归义军政权。敦煌文书P.3328 号所载武涉《上焉耆王诗》记载了当时龙家首领龙王自西域迁入河西,得到了吐蕃赞普的召见, 而且每年都加以赏赐,“神圣赞普见相次,宝辈(贝)金帛每年赐”,在当地率领部众安居乐业,自己时常射猎宴客,出巡四境,得到各方敬重,很有威望,福禄双全,龙家部族也在河西地区过着安乐和平的生活,[26]这绝非是840 年才迁入河西的龙王及龙家部族的写照,所以,龙家应该是8 世纪末吐蕃占领焉耆后即迁入河西甘凉地区, 殆无疑议。
S.367《沙州伊州地志》云:“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其人轻锐捷斗战,皆禀皇化。”文书末尾有光启元年(885 年)十二月廿五日张大庆抄写题记,[26]则在此之前,龙家部族已经分布于甘、肃、伊各州。 S.389 号《肃州防戍都状》记载了甘州的龙家、 退浑等族在回鹘的逼迫下进入肃州,肃州逐渐成了龙家的主要活动地域,[27]时间在中和四年(884 年)十一月,此时,随着龙王带领龙家、退浑、通颊、羌等部众入居肃州,龙家已经成为肃州地区的主要部族。 晚唐五代时期,藏文文书P.t.1131《张安扎芒古禀帖》 文书提到由肃州使者(sug chu pho nya)喀特蕃(khad bon)捎去张安扎芒古(cang am ’gra mang ’gu) 给宰相同平章事刺史(chab srid blon che la tshin sre,此人应该是河西一带地区的某个地方政权首领)的礼物,张安扎芒古对宰相同平章事刺史致以问候,所以张安扎芒古应该是肃州地方政权的主要官员,[28]应该是吐蕃化的汉人。肃州地区的居民包括吐蕃化的汉人和龙家、羌(党项)部族。 肃州府主(sug cu dbang po)与龙家首领龙王是其首领。
三、肃州地区的龙神信仰
浙藏114 号文书中提到了肃州地区首领和部众、龙家部族与归义军使节对神龙(lha klu)眷属及三百六十位兄弟、毗沙门天王盟誓效忠归义军节度使,这表明了当时肃州地区也流行龙王、毗沙门天王信仰。P.T.1189《肃州府主司徒致河西节度天大王书状》就记载了达怛(da tar)、仲云(ji ngul)、甘州回鹘(hor)在肃州大云寺对毗沙门天王盟誓,肃州地区毗沙门天王信仰在晚唐五代河西等地的流行情况笔者已经加以论述,[29]这里重点论述一下龙王信仰。我国自远古就有较强的崇龙意识及其活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后, 龙作为天龙八部之一的护法神,司水、主降雨、有神通、善变化,甚至能变形为人,或常具人格化思维及行动,有眷属家族、居龙宫、拥有奇珍异宝等观念亦传入中国,佛典中的龙王龙女故事也迅速为中土广大民众所接受,与中国原有的龙崇拜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龙崇拜信仰。
海龙王信仰流行的主要表现就是祈雨, 转诵《海龙王经》,海龙王就应其所请,唐代开始就有了帝王命祭龙的仪制。 肃州、沙州等地在唐前期是唐朝辖境,唐朝境内流行的龙崇拜信仰在此流行。 安史之乱后,吐蕃逐步占领河西走廊,吐蕃以佛教为国教,779 年桑耶寺建成后,赞普赤松德赞颁布兴佛诏书,称:“对所举之盟誓,十方诸佛,一切正法……天地各级诸神、 吐蕃地区之神、 一切九尊诸神、龙(klu)、夜叉及一切非人,敬请彼等作证,以使知此盟誓不得改变。 ”[30]这说明了吐蕃同样也有龙神信仰,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后, 吐蕃的龙神信仰也传入肃州、沙州等地,敦煌藏文文书P.T.969 号据考证或为《海龙王所问经》(’Phags pa Klu’i rgyal po rgya mtshos zhus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的某个别本残页,[31]内容涉及海龙王信仰。 此外,唐朝和吐蕃都流行毗沙门天王信仰,[32]在吐蕃统治下的肃州、沙州等地也同样流行这一信仰。
归义军时期,敦煌海龙王信仰盛行,在造像、礼佛、转经、燃灯等多种佛事活动中,均向护法海龙王祈愿,希望龙王护佑敦煌国泰民安、年岁丰收。归义军节度使以龙王自居,五代宋初的莫高窟、榆林窟中多处有龙王礼佛图,敦煌地区信仰海龙王包括有四大龙王、八大龙王等,[33]浙藏114 号文书中提到的龙神眷属及诸兄弟即指四大龙王、 八大龙王等神灵。
P.3149《诸杂斋文》中有《新岁年旬上首于四城角结坛文》(五代时期)记载:
“厥今旧年将末,新岁迎初,结坛于四门四隅,课念满七晨七夜, ……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某公,先奉为龙天八部,护卫敦煌;梵释四王,镇安神境……使龙王雨主,九夏疽无伤苗;海圣风神,三秋霜无损谷,敦煌永泰,千门唱舜日之歌;”[34]
这是归义军节度使在新年辞旧迎新时向龙王祈福。
P.2854(11)《礼佛发愿文》云:“总斯功德,回奉龙天八部、护世四王:伏愿威光孔盛,神力无疆;拥护生灵,艾□安邦国。 ”[35]八部龙王是佛教重要护法神,可以护国安邦。 浙藏114 号文书的记载表明了在与瓜沙邻近的肃州及河西其他地区,海龙王信仰和毗沙门天王信仰同样盛行。敦煌汉文文书记载晚唐五代时期, 肃州政权与归义军频繁通使,P.2032背《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记载:“粟贰斗,肃州张都头用。 ”[36]这个张都头是肃州政权的使者,为汉人,与P.T.1131《张安扎芒古禀帖》中的张安扎芒古(cang am ’gra mang ’gu)、P.T.1189《肃州长官向天大王禀帖》(该文书是931-935 年间,肃州地方长官司徒向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汇报归义军辖境内人员在肃州地区偷盗被抓获, 将遣使送回,以及肃州地区达怛、仲云、回鹘部众即甘州回鹘右翼部族活动情况的一封牒状)中的肃州政权使者张安扎腊拉(cang am ’gra lta la)都是肃州张姓汉人。[37]
S.4782《寅年乾元寺文谦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状》记载:“白面五升,充肃州僧粮用。 ”[38]
S.2474《宋太平兴国五年至七年(980-982 年)油面破历》:“肃州僧三人各面七斗,各油二升,共面两石一斗,共油三升。”“肃州使面二升。”“看侍肃州家胡饼一十五枚用。 ”[39]
P.2049 背《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油壹胜,纳官供肃州僧统用”;“面捌斗贰胜, 三件纳官供肃州僧统用。 ”[40]
S.1053 背《乙巳年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残卷》:“粟三斗,僧统院内看肃州曹寺主用。 ”[41]
以上这些记载说明了肃州使者、僧官、僧人频繁访问沙州,晚唐五代时期,肃州僧统是肃州地区僧团首领,具有独立性,并非从属于归义军僧团领袖河西都僧统, 肃州曹寺主则是肃州地区某寺寺主,是当地基层僧官。
肃州僧人同沙州僧人的往来敦煌藏文文书同样有所记载,P.T.1211《肃州色噶致索尊文书》,具体内容是肃州(sug cu)色噶(gser dka’)问候沙州大德索尊(sha cu na sku btsun ba chen po sag bcun)等人,并敬献礼品。[42]P.T.1212《云善致大德玉善等书》,内容是肃州云善(sug cu na yon shan) 致信沙州大德(sha cu btsun )玉善(yo shan)等人,并致奉礼物]。[43P.T.1129《库公布致僧录司赉禀帖》记载肃州(sug cu)库公布(khug gong ’bug)致沙州(sha cu)赵僧录(co sing lyog )司赉(zhi legs),请求赐予护身符及项链,保护其免于被敌人伤害。[44]这些汉藏文书说明敦煌、肃州两地佛教界往来频繁,敦煌佛教对肃州佛教具有重要影响,两地包括海龙王信仰、毗沙门天王信仰等在内的佛教信仰具有一致性,这些信仰源自唐朝境内流行的龙崇拜信仰和吐蕃的龙神信仰,以及唐朝吐蕃同样流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 另外,英藏黑水城西夏文书中发现有西夏文《海龙王经》,年代在西夏时期,[45]1176 年立碑于甘州的汉藏文合璧《西夏黑水桥碑》 也记载了西夏皇帝李仁孝向黑水河上下所住之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神等祈愿,保佑地方平安,[46]表明了在11 世纪前期西夏占领河西地区后, 龙神信仰仍然流行于西夏境内,西夏的龙神信仰与晚唐五代宋初敦煌、肃州等地区的龙神信仰也一脉相承。
总之,浙藏114 号藏文文书记载了五代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时期肃州政权与归义军的关系,龙家、柔然、回鹘等部族在肃州一带活动的情况以及肃州地区的宗教信仰状况, 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与P.T.1189《肃州长官向天大王禀帖》等藏汉文书都是研究晚唐五代肃州政权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