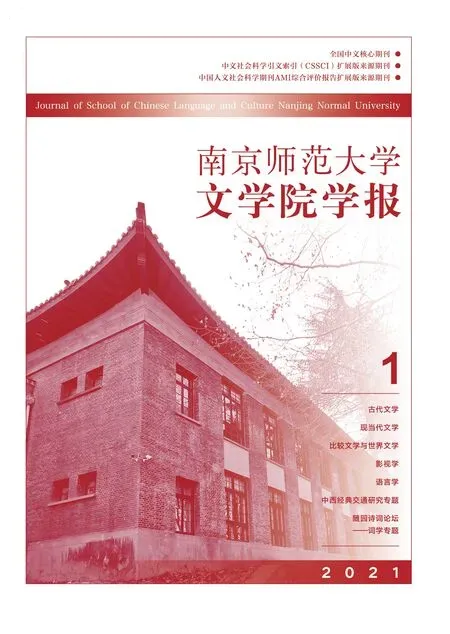论民国时期的“中国女性文学史”书写
2021-12-31王少芳陈文新
王少芳 陈文新
(武汉大学 国学院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民国时期“平等”“独立”等近代思想的流行,促进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展开,女性研究也逐渐兴盛,有关于参政、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如翻译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的《妇女问题十讲》;有关于妇女运动历史、现状的研究,如杜君慧的《中国妇女问题》;有涉及中外妇女运动的,如杨之华的《妇女运动概论》、新华日报馆的《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有关于文学的研究,如胡云翼的《中国妇女与文学》、谢晋青的《诗经之女性的研究》等。随着女性研究的深入展开,结合近代文学的构建,也有了以女性为对象的“中国女性文学史”。
民国时期的女性文学史,以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1916)、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1)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在初版时名为“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第三版(1934)更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1984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修订本时更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话”。(1930)以及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1932)最有代表性。而梁乙真的主要观点已见于1927年版的《清代妇女文学史》,谭正璧在其《中国女性文学史》初稿自序中也提到已耳闻梁乙真将有女性文学史问世,因此三者的先后次序应为谢本、梁本、谭本。
一、“文学”观的差异与叙述对象的不同选择
“中国女性文学史”尽管以“女性”为限定词,但追根究底仍是近代新兴文学史书写的一部分,同样要面对文学史书写的种种问题。而由于书写者学术立场和学术素养的不同,其文学史叙述对象的选择,也会各有偏重。
谢无量作有《中国大文学史》一书,其卷首绪论讨论了“文学之定义”(含中国古来文学之定义、外国学者论文之定义、文学研究法、文学之分类细目)、“文字之起源及变迁”、“古今文学之大势”“中国文学之特质”“古来关于文学史之著述及本编之区分”等问题。谢无量引用欧洲学者如白鲁克(Stopfors Brooke)、亚罗德(Thomas Arnold)、戴昆西(De Quincy)关于文学的定义,并对文学作了狭义与广义两种界定,而以广义的文学作为叙述对象。基于这种“文学”理念,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以诗文词赋为主,在“杂文学”的概念下收录了为数不少的书、颂、赞、铭、疏、表、序等,如顾若璞论河漕、屯田等“经济”大计的文章;如梁小玉因有思致而被收录的《女史序》;如晋代寡妇为了拒绝再嫁而写的《与兄弟书》;以及刘娥、苻坚妾张氏等人劝诫君上的疏文等,都可划归杂文学范围。
传统学术重视先秦、重视六经的观念也体现在谢无量的文学史中。谢无量对周代描述详细,尤为重视“五经”的价值。他不仅在第一编“上古妇女文学”中叙述女性在六经方面的研习,还用了一节专论《诗经》中的女性文学;在论述《诗经》时,大量引用了《毛诗序》《列女传》等以美教化、正风俗解诗的论述。其文学史中以传统注疏观点解读《诗经》之处不在少数。例如,在论述《召南·行露》时,谢无量和梁乙真都引述了《列女传·贞顺传》的内容,但梁乙真是为了指出《列女传》的附会,并指出申女的反抗精神,而谢无量则不仅全信《列女传》对《行露》写作背景的介绍,也肯定其对《传》文“正其本则万事理”[1](P14)的认同,肯定“夫妇为人伦之始”的解读导向。他论述《卫风·硕人》,赞同的也是《列女传》强调的砥砺女子高洁品行,作为人君子弟、国君夫人不可以有邪僻之行的告诫。他对《诗经》的解读大抵如此:认可《列女传》对故事背景的说明,认可《毛诗序》等对教化内容的注疏,高度赞赏“男女之别”“贞女之义”。
谢无量常将妇女文学等同于“妇学”,不仅包含妇言,也包含了妇容、妇德、妇功。所论春秋时的女性文学,多非具体作品,而是引述《列女传》等著作中的女性故事,以女性的言行来代替文学创作。“春秋之时,妇学未坠。故闺壸之彦,往往词成经纶,言为法则”[1](P26),“敬姜能推治国之达道,以立人生义务之本,其言甚有法度,亦文章之工者”[1](P29)这一类叙述随处可见。他的战国女性文学首以孟母:“战国时妇学已渐微,而犹多贤母。如孟母之善教子,尤其著者也。”[1](P38)孟母教子有道,又深通六艺,这类与文学无所关涉的内容,在谢无量的文学史中较为常见。
梁乙真的中国女性文学史书写,始于断代的《清代妇女文学史》(1927),完成于1932年出版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共七章,分别是“古代妇女文学之渊源”“汉代妇女作家之盛”“魏晋六朝平民文学之勃兴”“唐代妇女文学之转变”“五代宋辽妇女文学之中衰”“元明妇女文学之复兴”“清代妇女文学之极盛”。由章节来看,以时代为中心,体例统一,比谢无量混杂时代、文体、人物的标目方式有所进步。梁乙真往往以母女姑媳相从,或将诗脉相近、同舍同门者并在一处,或集中叙述某一地域、某一团体,表现出对文学史发展脉络的重视。
梁乙真对于影响文学发展的各方面因素都尽力做了梳理。第一,高度关注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本书于叙述中国妇女文学源流中,注重标示中国各种文学之优点劣点,及各作家之作风有无受他家(指男文学家)之影响与暗示。”[2](P1)梁乙真持客观理性态度,无论是男性、女性,只要在文学史上有较大影响,都会为其留有一席之地。例如,不论是《中国妇女文学史纲》,或是《清代妇女文学史》,都强调袁枚等人对推进女性文学的作用。第二,重视各种体裁、题材的溯源及其独特意义。例如,他在论及皇娥《清歌》时,不止于评述其诗本身,而是由其歌体为七言,对七言古体的来源作了一番阐发;论及《房中歌》时,强调其与汉代乐府的关系;还借昭君《怨诗》以论述汉代诗式的变化。他论述《紫玉歌》时强调,“此等故事,颇有文学意味,后世才子佳人一派小说传奇,颇多从此衍出”[2](P33)。第三,留意非文学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梁乙真注意到:魏晋时期胡汉杂居内地,于是胡人影响汉族文化,故北方文学全带异族色彩;五代在科学技术上的一个进步是印刷术的发明,这一发明极大地推进了文学的发展。他强调“杨妃在艺术史上地位之重要,不在其才而在其遇”[2](P204),以杨贵妃为“艺术之母”[2](P205),比之耶稣之圣母。实际上,他重视的是杨贵妃作为诗歌、戏曲、小说甚至音乐、图画、雕塑创作的共同题材,而不是杨贵妃本人的文学作品。换言之,梁乙真的文学史不仅重视优秀作品,作为后世作品底本来源的故事、传说以及人物等非文学作品也从历史的角度给予极大重视。
注重文学史整体发展脉络的梁乙真,不以“情感”作为选择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一方面,他指出文学以情感为主,诗的起源是“民生而有悲愉之情,情性所至,自然流露”[2](P1);“雕琢粉饰,无生气也”,不如“时有动人情处句也”[2](P139);他否定传统“诗教”,认为后世对《诗经》的道德教化式的解释都是穿凿附会,对一切道德教化的解诗方式都予以否定,“左芬所作,仅此两诗,尚是情性之真,而又为附会者强引到‘文以载道’之上,冤煞左芬矣”[2](P109)。另一方面,出于对“史”的注重,也不摒弃非抒情作品,例如回文诗等。他认为回文诗虽是雕虫小技,但毕竟流传中国数千百年,对中国文学不无影响。
注重文学史整体发展脉络的梁乙真,不拘泥于以文体判断作品价值的高低。在理论上,他是重视平民文学、俗文学的,他指出,“汉代文学,亦应侧重于平民之一方面。‘西京文章东京赋’,只好留为古典派之点缀品耳”[2](P44)。在具体的文学史书写中,对平民文学、俗文学这部分文学也多所涉及。例如,他以“邃古妇女文学之传说”开篇,其中西王母一节不仅包括“所传西王母之诗文”和“西王母故事之转变”两部分,援引不同著作中关于西王母的故事和论说,还厘清了西王母的三种形象的转变:虎齿豹尾的神人、外国女王、神仙美人,显示了梁乙真对传说神话的重视。他很看重始于唐代的西厢故事:“《会真记》之变迁,可考宋、金、元、明间声曲发达之沿革,换言之,即《会真记》常为中国戏曲发达之中心。”[2](P222)但是,必须注意到,出于客观理性的态度,他最终没有在女性文学史中专门叙述戏曲等较为典型的俗文学文体。无论是《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还是《清代妇女文学史》,都以辞赋诗词为主。其缘由在于,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女性的戏曲创作,实际成就不大。
完成于30年代的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深受胡适等新文化人的影响,重视“情之文学”而忽视“知之文学”,认为“文学的发生,在于有文字之前,而且肇始于风谣。人生不能无情感,既有所感于中,便不能不谋有所以抒于外”[3](P28),并据此批评了受谢无量盛赞、在梁乙真著作中也有一席之地的苏蕙回文诗:“苏蕙的《织锦回文》,也不过在艺巧上显得她的聪明,在诗的本身毫无情感与风韵,都是些枯索无味的陈言,简直不能称作文学。”[3](P69-70)他不承认先秦的作品属于文学,与谢无量与梁乙真都看重《诗经》不同,谭正璧直接以“汉晋诗赋”为正文首章。
谭正璧尤为重视小说和弹词。他以为,“中国的通俗文学,在民间最占势力的,散文当推通俗小说,韵文当推弹词”[3](P336),“能得一般人的欣赏和传颂;那东西的本身就有它不死的生命存在”[3](P254)。他批评谢无量、梁乙真说:“谢、梁二氏,其见解均未能超脱旧有藩篱,主辞赋,述诗词,不以小说戏曲弹词为文学,故其所述,殊多偏窄。”[3](P5)其《中国女性文学史》正文共六章,分别是“汉晋诗赋”“六朝乐府”“隋唐五代诗人”“两宋词人”“明清曲家”“通俗小说与弹词”。与梁乙真章节中多用“盛、衰、兴”等描述发展状况不同,谭正璧以每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标目,而“通俗小说与弹词”赫然在目。在所有俗文学中,女性最擅长的是弹词。谭正璧这样论述女性文学以弹词见长的原因:女性多是情感的,并且多有音乐的天才,因此相比散文更擅长韵文,而弹词是韵文的,所以女性作家长于弹词,并且一般女性读者也好弹词多于小说。所以,他盛赞打破一切戏曲、小说、弹词旧套的《天雨花》。谭正璧也重视通俗文学、平民文学的其他样式。例如,他之所以肯定林以宁,“并不因她有诗人之誉,也并不因她会组织社团,只因她能在和一班女诗人吟风弄月之余,曾试作戏剧《芙蓉峡》”[3](P314)。对通俗文学、平民文学的重视,也导致了对以诗赋为主体的“贵族文学”的否定,认为汉高祖宫人唐山夫人的《房中歌》“纯仿古代颂体,文辞毫无情趣”[3](P78);上官婉儿“诗属于浮艳一派,开沈(佺期)宋(之问)体之先,华而无实,非诗歌正宗,实不足取”[3](P113)。
谭正璧过分倚重通俗文学、平民文学的各种文体,导致了将“以次充好”掩饰为“瑕不掩瑜”。他所论及的俗文学作品,相当一部分水准不高,实际上,他论述“在一切女性所作的弹词中”,属于“鸡中之鹤”[3](P395)的郑澹若《梦影缘》时就已透露出对女性弹词质量的忧虑,并为《梦影缘》的冗长可能带来的读者厌烦情绪作了这样的解释:“上等的文学方法,我们读西洋长篇小说时也会起这感觉,原因是在于我们没有鉴赏这种文学的素养,因为我们看惯了那些肤浅的低级趣味的记事式的‘闲书’的缘故。”[3](P398)
比较而言,谢本的体例和对“文学”对象的把握与现代“文学”理念距离较远,梁本和谭本虽然较多遵循现代“文学”理念,体现了平民文学、通俗文学逐渐受到重视,文学核心由“知之文学”向“情之文学”过渡的趋势,但和谢本一样,依然论述了书法绘画等非文学作品。由此可见,现代“文学”理念对文学史书写的约束,不仅在20世纪早期是松弛的,即使是在30年代,也并未形成统一的尺度,文学史书写的个人主导空间依然很大。
二、“女性观”的差异与叙述对象的不同选择
“女性文学史”是文学史的一部分,也是女性史的一部分。按谭正璧的说法,女性文学史的书写对象有三,一是文学里表现的女性;二是女性所给予文学家的、艺术的情绪和环境;三是女性作家。“所谓女性文学史,实为过去女性努力于文学之总探讨,兼于此寓过去女性生活之概况,以资研究女性问题者之参考;成绩之良寙不问焉。故女性文学史者,女性生活史之一部分也。”[3](P6)因此,作者的“女性观”对叙述对象的选择以及论说重点的确定,影响甚巨。
作为首部女性文学史的作者,谢无量高度赞许欧美女子在就学、就业,甚至参与政治活动等方面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利,并对中国女性的未来做出了展望:“今世女学稍稍为教育界所注意,使益进其劝厉之方,加以岁月,自不难与欧美相媲”[1](P2)。这里的“与欧美相媲”,既指中国女性的能力、权利能追上欧美女性,也指中国最终能像欧美那样走向男女平等。他从生物学的角度揭示了男女平等的可能性:女性的体力虽逊于男性,但心智没有差别,至于现实中女性能力弱于男性乃是境遇不同导致的,“纯出于后天之人事,而非其先天之本质即有异也”[1](P1)。谢无量还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寻找到了男女平等的依据,其《绪言》指出,先秦的一阴一阳之道是中国男女平等可追溯的源头,而“夫妻”代表“匹敌”之意是中国男女平等的表现;中国上世有自然法则下的男女平等,中世则由于势力不均导致贵男贱女,到了近世应提倡顺应公理的男女平权。
文学史中优秀的女性文学,是谢无量论证女性能力不亚于男性的绝佳例子。其一,谢无量从中国的北音、南音以及部分文体都起源于女性肯定了女性的创造能力。对于上古女性文学,他认为,既然神农时有诗,那么必然也有女性作家,虽然作品不存,但可以通过常理推断女性诗作的存在,女性文学与男性文学同样历史久远。其二,他认为五言诗也应该是起源于女性。例如,虞姬和项羽歌即为五言,早于苏武、李陵;与苏、李同时代的有苏武妻、卓文君、罗敷等。女性既开辟了部分文体,又有久远的写作历史,因此女性文学从根本上可以、也应该与男性文学并驾齐驱。他强调,虽然历史上女性受到压迫,但“近来学者多持男女同性之公理,故男女终有趋于平等之一日,断可知也”[1](P2)。
尽管提倡男女平等,但由于男女平权之风初兴,尝试放开手脚的谢无量对于“女性应当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可避免地仍较为拘谨。首先,他所认同的妇德,偏于贤妻良母。从他的《妇女修养谈》一书大量引用《列女传》等的故事可以发现,谢无量对于《列女传》《女诫》等所提倡的妇德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文学史中对《女诫》“以卑顺为主”[1](P75)的训诫没有过多评论,但他确认班昭是“古今列女文学之宗”[1](P81),说明他的女性观带有前近代的痕迹,他所肯定的女性仍是“家庭中的女性”。他称述少寡而能养幼孤的陶婴拒二婚所作的诗歌,将“名妓工诗”赞许为“以男女慕悦之实,托诗人温厚之词,雅而有则,真而不秽,不能以人废”[1](P268),论述李冶等人时,虽然也肯定她们有优秀作品,但还是要指明“其行检不足称”[1](P261),都一以贯之地重视妇德。
不同于谢无量从生物学、历史平权等角度提倡男女平等,梁乙真从辨析男性偏见入手为女性文学正名。他批评《蜀志》的女性文学观点,指出“翰林之事非妇人女子之能”[2](P261)的说法只是一偏之见。在肯定整体的女性文学之外,梁乙真对具有“平等”“独立”等近代价值的作品,拥有独立人格、作为“个人”的女性更为重视。体现在他的文学史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选取本身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品作近代解读,对传统的礼教解读予以否定。他在评述《召南·行露》时,否定了刘向《列女传》的“女性之贞烈”说,指出“申女乃具有反抗性之一女子”[2](P15);认定《邶风·柏舟》是“写女子不满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式之婚姻而提严重抗议者也”[2](P21),而《毛诗序》“矢志不嫁”的寡妇节操论是去古益远。二是对历史影响重大的作品作全新解读,以期达到振聋发聩的效果。例如,对于被谢无量盛赞的班昭,他明确指出,“昭书自今观之,可谓集妇女‘奴隶道德’之大成矣”[2](P73)。班昭以《女诫》而被誉为“女中圣人”,“然而中国之妇女苦矣”[2](P65)。还摘录了《女诫》部分内容,提醒“读者自批评之”[2](P71)。他的文学史对古往今来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女仪母训”[2](P28),一概不取。对于曹丰生批判《女诫》的著作不传,他感到十分惋惜。
梁乙真对传统女性的批评,建立在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上,而非道德教化的鞭笞:“女子言行,有失之迂腐,不合现代生活;或流於迷信,不脱神权思想者,则编者依时代眼光,加以适切之批评。”[2](P2)例如,他认为娼妓文学“亦自有其价值在焉”[2](P235),“盖人之一生,为善为恶,其转移全在乎种种环境之支配;社会制度之不良,能使其日趋於恶之一途而不自觉,则女子之堕而为娼妓,岂其本意耶”[2](P241)。他对苦难生活中的女性也多有同情。但比较而言,他还是更赞赏卓有识见之作,而非“‘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一派婉媚为工”[2](P420)的书写:“清季浙中妇女能诗者虽多,然大抵清俊柔婉,情致缠绵。惟山阴秋瑾女侠诗,跌宕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绝无半点脂粉气。女侠一枝生花笔,实可横扫千人也”[2](P424)。代父从军的木兰也受到他的热烈赞赏。
谭正璧的女性观较谢、梁来得激进,他对女性生活的苦痛多有关注,对未来女性的反抗抱以极大期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激烈抨击所谓的“冒牌男性的女性”[3](P20):尽管身为女性,却对女性进行物化,对女性的戕害极为严重。他指出,唐人传奇中如聂隐娘一类的女性,是理想中的人物,而这些理想人物“反映了当时女性的柔弱,不肯用一些反抗的力量,很辜负了一般人的希望”[3](P20)。他还指出,以女性为中心的弹词抒发的畸形的理想,只以改装男子以求功业为起点,最后仍不出“雌伏”丈夫的结局,仍属于男性中心社会的因袭思想。这种骨子里仍是男性思想的女性,还不如没有的好。
中国女性作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堕落的?谭正璧的回答是:南北朝,女性作家从此开始以写作来谄媚男性。“南北朝仿佛是女性生活堕落的鸿沟”,“南北朝以前的女性作品,都是她们不幸生活的写照,像卓文君、蔡琰一流人的作品中,没有一丝谄媚男性的表示。南北朝以后就不然,就像侯夫人的许多幽怨诗,也无处不是表现她与男性交际的失败;至若李季兰、鱼玄机、薛涛一流人,她们的作诗仿佛专为了谄媚男性。至若明、清两朝女性诗人和词家,可以车载斗量,但她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为了要博得男性称赞她们为‘风雅’而作。她们在谄媚男性失败时,又把文学当做泄怨的工具。有时情不自禁,和男性没有交接的机会,于是文学又做了她们和男子交通的工具”[3](P25-26)。“幽怨诗”等作品在谢、梁的文学史中通常无毁无誉,在谭正璧那里则由于“谄媚男性”而被痛斥。
除了批判“冒牌男性的女性”外,谭正璧也对传统妇德作了清算:“班昭《女诫》,才系统的把压抑女性的思想编纂起来,使之成为铁锁一般的牢固,套上了女性的颈子。”[3](P49)“她是以女教的圣人的资格,博得在历史上的声誉的。她的作赋,不过是随众的附和,或奉命而作。因为是不欲言而言,所以作品大都没有情感,也没风趣。但是在赋发达的时代,女性的作者仅有班婕妤和她二人,究属不可多得。所以在这一节里,一面揭穿她们的谬悖的见解,一面仍叙述她们的著作。”[3](P52)
谭正璧对女性的反抗给予了热情赞美: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不仅是女性中的豪杰,也更胜于男性。他论述北魏公主复仇之事,说“有这样‘富贵不能移’的坚定的意志,也是一时难得的女英雄了”[3](P105);说吴淑姬“如其单单吟风弄月,究竟竖不起她文学的声誉的”[3](P245),这些反抗的女性“不但不是镇日长坐闺门的少妇所能比拟,也不是那‘浅斟低酌’‘风流自赏’的名士生活所能企及”[3](P220)。“在被数千年来礼教所压服的女性中间,一旦有人忽然发现了自己也是人,是和男性一般有独立人格的人”[3](P320),这样的女性是谭正璧所赞美的,而这样的女性所写的作品,即便手法平常、剧情平庸,在他看来,仍值得在文学史上留名。这种内容第一、艺术第二的取舍策略,在谭正璧的文学史中并不罕见。谭正璧寄希望于女性积极的、有计划的、大量的反抗,以造就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
谭正璧甚至认为,因历史上女性的反抗太少,不得已而求其次,女冠“玩弄男性”也是一种不无可取之处的反抗方式:“她们一方面在生活中相挣扎,一方面又发现了人类社会对待女性的不平等,于是便与之反抗。她们的反抗手段,就是玩弄男性,于是便也走入了这种半娼妓式的生活中。”[3](P133)对于女冠文学,谢无量持隐晦的批评态度,梁乙真取同情之理解,谭正璧则因将女冠视为反抗者而滔滔不绝地为之辩护:李冶“既不能作积极的反抗,也不安于过那单在理想中造成女性的伟大(像弹词家之创作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弹词)的渺茫生活,于是只有浮沉于那对男性以报复式的玩弄男性的消极生活之中,以度过那不幸的受创的生命”[3](P134);鱼玄机的多情,“正是对症发药,以怨报怨的公平手段”[3](P139);鱼玄机和李冶虽然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机会,但已经是巾帼英雄了。
谢无量、梁乙真与谭正璧对清代以袁枚、章学诚为代表的“女性之争”看法不同,也反映了他们在女性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谢无量总体是赞同章学诚的,如他通过引述章学诚的《妇学》,来论证娼妓文学是真而不秽,符合温柔敦厚之旨,因此在文学史中具有合法性。相反,梁乙真则高度肯定袁枚对女性文学的推进,而痛斥章学诚对“守贞”“死节”的支持,认为这些礼教分子是导致女性不幸的始作俑者。他也否定章学诚古代只有卿大夫家庭才有妇学,齐民妇女则未能知妇学的观点。至于谭正璧,因为他更强调的是男性对女性的戕害,以及认为袁枚对女性文学的支持主要在诗文而非通俗文学,因此并不太肯定袁枚的作用,但他更否定的,是自诩为“正人君子”的礼教者非难、攻击袁枚的论调。对于清代经典的“女性文学”之争三方的看法的不同,其实也正是他们女性观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果。
三、不同的文化姿态与不同的学术世代
“五四”以后,尽管“文学”的定义、文学史体例并未能形成统一的认定,但学术构建的总体趋势是:“文学”由关涉经、史、子等的传统杂文学概念向现代纯文学概念转换,“文以载道”向“情之文学”转化,文学主流由诗文向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过渡,贵族文学向平民文学让步。“五四”是不同学术世代的时间标志,谢本、梁本、谭本之间文化姿态的差异,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五四”在女性史上也具有标志性意义。“民国八年之五四运动,不特为学生运动,爱国运动,良亦妇女运动有关系时代。以我国妇女运动,时伏时起若断若续,如波浪式。辛亥前后盛极一时,民国元二年以还,又复沉寂,自五四运动发生,妇女运动乃随之而起。”[4](P94)五四以后的妇女运动,在要求男女平等、性别平权,以及在婚姻、教育、职业、参政等方面主张女性有自主权的基础上,强调女性作为“个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将女性从家庭中独立出来,从丈夫、父母的附属中独立出来,特别重视为女性在经济上创造独立的条件。女性被赋予了新的任务,不仅是要解放中国女性,要爱国,也要致力于救亡运动的事业。五四前的谢本仍注重传统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指出家庭事务是女性必须研究的内容,而梁本和谭本则较为注重女性的独立性,谭本更通过对传统女性苦痛的描述,号召广大女性进行反抗,这样一些不同的学术姿态正是不同文化世代的反映。
“五四”前后学术构建的一个巨大差异,在于是否刻意区分新、旧文化。“五四”前的谢无量,对传统的接受度和亲近度要比梁乙真、谭正璧高出许多,他所认可的近代学术构成,是“取旧以融新”,是能够吸取传统的营养,融旧以成新的。这其实也是学术构建早期常见的一种态度,尤其是对于本国传统学术抱有较深情感的学者。所以,谢无量虽支持女性独立,赞同男女平等是世界公理,但不妨碍他同时赞美“贤妻良母式”的传统妇德。他对班昭《女诫》多有赞誉,在《妇女修养谈》中提出“列女之模范。尤多有可矜式者”[5](P6)。他认可晋代女性的“动止有仪”,说“魏晋之际,尤重妇容。故汝南以此取妇,亦礼教之遗也”[1](P101)。也认可“男外女内”的观念,认为只有和睦家庭的女性才能说得上“克尽妇职”[5](P79),并以孝顺舅姑为女性第一品德,就算如今情势有变这一点也不会改变。他没有那种新、旧文化势不两立的意识。
新文化的冲击使得“以新解旧”成为学术构建中一个常见现象,“五四”以后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加速了这一方法的运用,对“旧文化”的否定日趋激烈。例如,梁乙真尝试运用近代外来的“心理学之方法以研究六朝时妇女之文艺”:“古情歌若据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以解剖妇女文艺之内容则可以看出有最显明的两种特殊之表现而为他时代妇女文艺之所不及者,——即麻醉的现象(Phenomena of Contretation)与性欲的想象(Sexual imagination)是也。”[2](P146)这是比较典型的“以新解旧”。谭正璧则是“以新破旧”。他确信旧文化必定灭亡,“中国旧体文学到了清末,无论文雅的,通俗的,受了欧风东渐的影响,一概都成为强弩之末”[3](P410);新时代必会产生新文化,“民国以来,中国文学逐渐走入了新的领域,完全受了西洋文化的浸染。截至今日,几乎完全脱离了中国旧有文学的关系,站入世界文学的场所”[3](P340)。谭正璧对传统最为疏离,对女性苦痛的描写最为充分,对男权的抨击也最为激烈。他在反驳“女祸”论时,甚至以夫差为西施放弃一切、吴三桂为陈圆圆引清兵入关等为例,赞美女性的力量超越一切物质。
对于新、旧文化的刻意区分,导致了对作者身份、作品文体的刻意区分。文学史叙述对象的选择,从身份来说应该是侧重于平民还是贵族,从文体来说应该是侧重于诗文还是小说戏曲,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五四”前的谢无量,虽然也重视民间文学,但并不强调“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之间的对立。“民间女子,并能自歌其劳怨,年老又能采诗。春秋时虽下邑耕桑之女,类有辨通之才,见于载记,则民间亦自有妇学可知。唯宫壸以及士夫之家,其妇女有贤德文采者,尤易为人传播耳。”[1](P7)他将妇女文学分为宫廷文学、娼妓文学、女冠文学、闺阁文学四种,所看重的是生活范围的区别,而不是社会身份的差异。他对“知之文学”、“道之文学”均予重视,理所当然地以诗文为主,小说戏曲等平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而梁乙真则明确指出,文学的核心部分在平民文学而非贵族文学:“本书叙述时侧重於平民的及无名作家之作品,对於贵族的及宫廷文学,则多从简略。”[2](P1)他强调魏晋六朝女性文学的一大变化,是作为平民文学代表的古情歌的勃兴,“《子夜歌》者,中国诗歌界最伟大之平民文学也”[2](P114),“在文学上有绝大价值”[2](P126),所录多至百首。梁乙真还从沾溉后人的角度梳理了六朝女性平民文学对唐代文学的深远影响:《子夜歌》为唯美派所本,《木兰诗》为边塞诗所由出。较之梁乙真,谭正璧更为激进:梁乙真虽以平民文学为中心,在文体上仍以诗文词赋为主;谭正璧则既以平民文学为中心,也以通俗文学为重点。当然,坚持以平民文学为主流的梁乙真和谭正璧,也并未完全抹煞贵族文学的价值,谭正璧说戏曲、小说因为名士多所以流传广;而梁乙真对《房中歌》等贵族阶层的作品多有赞誉,对上官婉儿等宫廷作家多有褒奖之词。他们从传统教养中获得的鉴赏能力有助于摆脱阶层对立观念的左右。
“五四”以后的民国学术构建,另一特点是文学史的现实功能日益增强。梁乙真说:“文学者,时代精神之反映也”。[2](P245)这句话的延伸含义是:文学是反映时代的,文学史也是反映时代的;文学是关于人的,文学史同样是关于人的。因此,文学史不仅观照历史上的社会情势,也映射出书写者面对当前社会的姿态。“五四”以后,这种理念更为明确和强烈。以胡适《白话文学史》为例,在历史研究的目的之外,更重要的是为现实服务,推进用“国语的文学”来造“文学的国语”。
文学史现实功能的增强,从谢无量、梁乙真、谭正璧的女性文学史书写,也可以找到生动的例证。以武则天为例,谢无量说武则天雄才大略,但对她的赞赏仍建立在肯定她的诗文作品的基础之上;梁乙真对武则天的才、智也极为推崇,盛赞为“女中怪杰”,不仅肯定她的诗文,也强调她对唐代政治文化的影响;至于谭正璧,他认为武则天最重要的身份是政治家而非文学家,“武则天(曌)以一代大政治家而兼为文学”[3](P112),“她对于文学上没有什么贡献可言,因为她已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活动上”[3](P124-125),“总之,她是政治史上、社会运动史上的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在女性文学史上只沾到她的光荣的余影,为五千年来女子一吐愤气”[3](P125)。谭正璧之所以对一位女性政治家而不是女性作家如此推崇,在于他不满足于对历来女性文学的梳理,而是要揭示女性的反抗与革命史,以作为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旗帜。他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一个人起来反抗是永不会成功的预兆,要多数人起来必须经相当时间的宣传。像《繁华梦》这类作品,虽不能即认为反抗男性的哀的美敦书,由于时代的关系;然无论若何,她们已是表现出她们也有一般人所共有的人格。她们既也是人,她们未尝不能似班超般的为国争光,也未尝不能似李白般的浪游豪唱。这是女权运动开始的第一声,她们的大队正在后面浩浩荡荡的奔来,我们不要轻易看为平常啊!”[3](P317)他在《中国文学进化史》中论及班昭《列女传》《女诫》时不作批评,但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则以其为女性苦难的源头之一而痛加指斥,也是这种现实使命感的表达。从谢本到梁本再到谭本,文学史反映的“如欲建设新中国,必须动员二万万多女同胞的力量,共同参与伟大的建设工作”[6](P5)的诉求越来越迫切。
四、结语
谢无量、梁乙真、谭正璧等人对于女性解放的路径选择有所不同,但他们促进女性解放,追求男女平等,启蒙民智的目的是一致的。以民国女性解放中的经典母题“娜拉”为喻,他们对于娜拉应该是怎样的娜拉有不同的观点,对于娜拉出走是否要与原本的家庭完全切割有不同看法,但在鼓励娜拉出走,在社会应该给予出走的娜拉以尊重与平等上,并没有分歧。
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出版于1916年,对平民文学、俗文学未作广泛探讨。“五四”文学论争之后,谢无量出版了《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特意说明他之前的《中国六大文豪》所论作家是贵族的、模拟的、少数的,因为有必要为平民文学补写一本。从谢无量的自觉反省,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对学术的影响。梁乙真和谭正璧的书,就是新文化运动强势影响下的产物,而谭正璧因为个性、素养等方面的原因,其文学史受影响的程度更深:梁乙真对进化论仍有迟疑,说“昧于文学进步之自然程序而未为详考”[2](P3)(2)虽然梁本出版在谭本之后,但其主要观点是其1927年出版的《清代妇女文学史》的继续,因此不妨将梁本视为谢本与谭本之间的过渡。;谭正璧则明确采用了“文学进化”的观点,更看重宋元以后的俗文学,这从其《中国文学进化史》直接用了“进化”一词即可见出。
谢无量和梁乙真、谭正璧的著作之间隔了“五四”文学论争,谭正璧对谢无量有所批评乃题中应有之义,但并不代表后者与前者没有重合之处。比如,谭正璧以刘清韵为“女性戏曲史上最光荣的一页”[3](P323),因为她是专门作家,她的戏曲不是为了消遣解闷而作。这种观点就与谢无量所持文学须“有物”的立场接近。他们文学史中这些不够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反映了文学的复杂性和学术的复杂性,也提示了对他们加以细致区分乃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