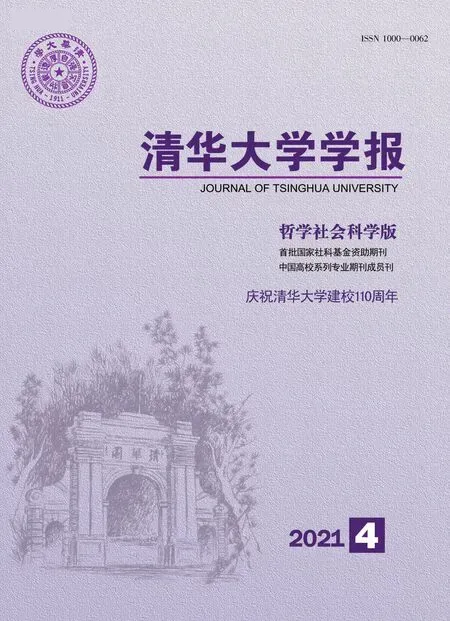现代中国哲学家哲学方法论溯源及其自觉
2021-12-31高海波
高海波
现代中国哲学是在东西方哲学交汇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受西方哲学的影响,现代中国哲学家在进行哲学史研究、从事哲学创作、思想文化改造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方法论的重要意义,很多哲学家都有明确的方法论自觉。他们的方法论,既受西方哲学方法的影响,同时也有某些中国传统哲学方法的特色。其中,某些哲学家试图融合中国与西方的哲学方法,建立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哲学方法,既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也为世界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本文拟围绕这一主题,通过历史的梳理,以揭示现代中国哲学家方法论意识的兴起过程及其自觉。
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哲学方法”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说法,在现代,陈黻宸、谢无量均认为“哲学”相当于中国古代学术中的“道术”观念,不过,他们更多将其限定在儒学经学的范围内,因此,尚未摆脱中国传统学术的限制而获得哲学的自觉。①陈卫平:《中国哲学史研究第二次学术自觉的开端》,《哲学研究》2018年第12期。梁启超也曾建议将philosophy译为“道术学”,1926年,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将中国学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道术史,即哲学史”。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第8册,《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3页。梁启超所说的“道术”出自《庄子·天下篇》,它既包括关于宇宙人生的基本理论(道),也包括如何运用这些基本理论的方法(术)的部分,其范围不限于儒学经学。梁启超是在此意义上使用“道术”观念,不过,我们认为,在中国哲学中也有很多讲如何求道、得道、修道方法的内容,这些都应该包括在广义的“道术”概念中,故我们说,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方法”(Philosophical Method)的说法,但中国哲学中却不乏“为学之方”、修养方法的讨论。如果承认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是哲学的特例,如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中的说法,“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①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页。因而如果说中国哲学也是哲学的话,则中国哲学中也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方法。不过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更加关注如何修道、得道、如何成就理想人格,故人生哲学特别发达,所以,多数的方法都系“为学之方”,冯友兰曾说:“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注重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不过因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在“为学之方”的问题上,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存在不同的主张。如先秦时期,老子强调“致虚”“守静”“为道日损”,庄子强调“心斋”“坐忘”等,都是诉诸内心体悟的神秘方法。孔子则强调“博文约礼”“多学”“一贯”,将“默识”与“博学”、“思”与“学”结合起来,既不反对经验认识,也不反对理性思考,同时也重视个人的内心体悟,应该说将体验、理性、知识结合得很好。孟子一方面强调对道德本心的自我反省,“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另一方面又强调“反身而诚”(《孟子·尽心上》)的神秘体验。总的来说,孟子更倾向于内向的反省,具有强烈的体验主义色彩。而荀子则主张通过“虚一而静”(《荀子·解蔽》)的方法,培养一种客观无蔽的认知主体,以此去认识“礼义”,并进而转化人性,“化性起伪”(《荀子·性恶》),表现出经验主义的为学路向。在宋明理学家中,程朱和陆王也有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为学之方”之争。陆王强调“发明本心”“致良知”的内向反省功夫,而相对而言,程朱则强调外向的格物穷理。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关于方法论的不同看法和论争,所以,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中也有致知方法的讨论。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他将孔子后,中国哲学家的方法,大致归为六种:
一、验行。即以实际活动或实际应用为依据的方法,这是墨子的方法。清代颜习斋的方法亦属此种。
二、体道。即直接的体会宇宙根本之道,是一种直觉法,这是老子庄子的方法。
三、析物。即对于外物加以观察辨析,这是惠子公孙龙及后期墨家的方法。清代戴东原的方法亦可归入此种。
四、体物或穷理。即由对物的考察以获得对于宇宙根本原理之直觉,兼重直觉与思辩,可以说是体道与析物两法之会综。此方法可谓导原于荀子及《易传》,后来邵子张子及小程子朱子的方法,都是此种。
五、尽心。即以发明此心为方法,亦是一种直觉法。这是孟子及陆王的方法。
六、两一或辩证。中国哲学中论反复两一的现象与规律者颇多,而将反复两一作为一种方法而加以论述的,则较少;惟庄子与《易传》论之较详。其发端在老子。后来张子程子亦言及之。在中国哲学中,这一方法不是独立的,哲学家用此方法,都是以它法为主而兼用此法。③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555—556页。
张岱年在描述这些方法的时候,主要运用了中国哲学本身的概念和词汇,称这部分方法为“探索真知的途径之理论”。另外,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中还有关于名辩方法的论述,也属于方法论,它们是“关于表达思想、论证真知的思维规律之理论”。④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588页。总的来说,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当中的方法论可以包括两部分:“一般方法论是讲求知之道,名与辩则是论立说之方。”⑤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588页。张岱年上述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概括,虽然主要是本着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及理论进行的,但仍可以看出西方哲学方法的影响。即,在张岱年看来,哲学方法是探求真理并表达真理的方法。这一对哲学的定义本身就是西方式的。这与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①冯友兰:《新理学》,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4页。的定义有相近之处。事实上,张岱年也采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解释上面列举的六种中国哲学的主要方法。张岱年说:“体道与尽心,都是直觉的方法,不过一个向外一个向内。析物是理智的方法。体物或穷理,则是直觉与理智合用的方法。验行是实验的方法。两一则与西洋哲学中的辩证法有类似之点。”②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556页。直觉、理智、实验的方法、辩证法,这些都是西方哲学的基本方法。可以看出,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方法的归纳也是以西方哲学方法为对照的。
从张岱年的例子来看,即使像张岱年这种试图从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内在地对中国哲学进行客观研究的哲学家,其方法论意识也受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影响,这是现代中国哲学家方法论的一个根本特点,实际上也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一个自然结果。
二、现代中国哲学家方法论意识溯源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家的方法论意识,是在与西学学术的对照与互鉴中逐渐上升为自觉意识的。最直观的是,以哲学的组织形式而论,先秦之后,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哲学家进行哲学创作的主要方式是经典诠释(经学)和语录。当然,即便是宋明理学家的语录,也以讨论、诠释儒家经典为主,因此,可以说,先秦之后,从汉代一直到清末,哲学表达的主要形式是经学,故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汉代董仲舒之后、清末之前这段时间称为经学时代。在此期间,很少有人对这种思想表达的形式进行非议,这种情况直到1918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才被改变。1930年代,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关于中国哲学无“形式的系统”但有“实质的系统”的说法,也是在中西哲学对比的情况下提出的。冯友兰哲学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中国哲学披上形式的外衣,以便使中国哲学从形式上显得更“哲学”。而这种对于中国哲学缺乏“形式的系统”(换言之,即不重视逻辑)的意识,也是到了晚清、民国时代,伴随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才会逐渐上升为自觉意识。
当然,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下,中国节节败退,逐渐显示出衰败的迹象,才是引起中国哲学家进行深刻反省的根本原因。1840年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强大的军事、经济冲击之下,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国人先是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坚船利炮,进而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工商实业、政治制度,五四时期又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其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自强、求富、中体西用),再到康梁的“戊戌变法”(提倡君主立宪,主张政治制度改革)、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最后到陈独秀、胡适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对西方的学习和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政治制度、再到文化思想的逐渐深入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中国哲学家开始深刻反思中西文化、中西哲学的异同问题。
早在清末,严复就意识到逻辑学(严复将其译为“名学”)的重要作用,认为逻辑是西方学术文化发达的主要原因。1900年—1902年,严复翻译了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穆勒名学》的上半部,在一段按语中,严复说:“而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③严复:《严复全集》卷五,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4页。严复借培根的话表明逻辑学作为一种根本方法、根本学问的重要。实际上,严复对西方逻辑方法的介绍,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早在1896年写的《天演论自序》中,严复就将西方逻辑学中的归纳、演绎法翻译为“内籀”“外籀”,并试图阐明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这两种方法:
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
……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①严复:《严复全集》卷一,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6页。
严复是最早认识到逻辑在学术中的重要地位,并试图用它来改造中国哲学的第一人。在《穆勒名学》的“按语”中,严复还揭示了自己为什么要将逻辑学译为“名学”的原因:“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②严复:《严复全集》卷五,第14页。这说明严复对逻辑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很熟悉。关于严复在中国传播“形式逻辑”的重要作用,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自明末李之藻译《名理探》,为论理学输入中国之始,到现在已经三百多年,不过没有什么发展,一直到了严几道先生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形式论理学始盛行于中国,各大学有论理学一课。”③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3页。郭湛波充分肯定了严复在传播形式逻辑方面的重要贡献。
除了严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也非常关注逻辑学,并用它来作为观察中国学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视角。王国维在一篇讨论西方学术语言输入中国的文章中就指出,中西学术的差异以及中国学术落后的原因在于有无“名学”或“辩论思想之法则”:
夫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雅里大德勒自哀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④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6页。
王国维认为,中国先秦时代虽然有“名学”,但是,却流为诡辩,且缺乏方法的自觉。而印度哲学很早就出现了因明学,古希腊很早就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它们很早就开始注意到“辩论思想之法则”,具备了抽象思维以及“分类”法(逻辑分类法),因此,印度、希腊学术实现了自觉,而中国学术因为缺乏“名学”,故“尚未达自觉”。也就是说,在王国维看来,有无逻辑学是中、西、印学术发达与否的标志,中国学术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发明形式逻辑的方法。
1898年,梁启超也发表了《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比较》一文,在文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中国虽有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之言,然不过播弄诡辩,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后亦无继者……推其所以缺乏之由,殆缘当时学者,务以实际应用为鹄,而理论之是非,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国语言、文字分离,向无文典语典Language Grammar之教,因此措辞设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⑤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4—45页。
梁启超此处的观点几乎完全同于王国维,或是受了王国维的影响。当然,在当时,也存在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哲学中本有“论理学”,最早持这种观点的是日本学者桑木严翼,据梅约翰的研究,章太炎、王国维等人都受其影响。桑木严翼认为荀子的“论理学具备组织……无异于亚里士多德的《理则学》[Organon]”。①梅约翰:《明治学术资源、论理学与中国哲学的雏形》,见景海峰编:《拾薪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尽管上述观点存在差异,仍可以发现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均关注中国哲学当中的“论理学”问题。无论是王国维还是梁启超,都以有无“论理学”作为评价中国哲学或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标志。
另外,清代以来,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也出现了诸子学研究的新兴趣。梁启超指出,这种诸子学的新兴趣与校勘学的发达有密切的关系,也带来了思想转变的契机。“及今而稍明达之学者,皆以子与经并重。思想蜕变之枢机,有捩于彼而辟于此者,此类是已”。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主编:《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之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0页。当然,这种诸子学研究的新兴趣,除了内部的原因外,也与西学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正如梅约翰所说:“正像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过,西潮无疑也促进了诸子学的上升……无论是刺激还是冲击,西潮对诸子学的上升起了促进作用。”③梅约翰:《明治学术资源、论理学与中国哲学的雏形》,见景海峰编:《拾薪集》,第107页。
这种诸子学研究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其中,对于名学(特别是名家、墨家的名学)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根本原因就在于名家、墨家思想中有很多可以与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方法相通之处。在对名学的研究中,胡适的《先秦名学史》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郭湛波说:“中国近代自从西洋思想方法来到中国,同时影响对于旧思想方法之注意;就研究到先秦诸子的辩学,第一部成功的作品,就算胡适先生的《先秦名学史》。”④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97页。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胡适也说:“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⑤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3页。在胡适之后,梁启超、章士钊、伍非百、冯友兰、谭戒甫等人都有关于墨家、名家的研究,掀起了一个名学、墨学研究的热潮。
可以说,自形式逻辑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学人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五四时期,很多学者反思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他们获得的比较重要的一点共识就是:中国传统中缺乏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更进一步说,即中国学术缺乏形式逻辑的方法,而形式逻辑在当时恰恰又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主要内容。在科玄论战中,丁文江、任鸿隽、胡明复、胡适等人均持类似的观点。根据王中江的总结,“近代中国强调的科学方法,从逻辑学上说主要是归纳和演绎”。⑥王中江:《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7页。任鸿隽曾经引用爱里亦脱(C.W.Eliot)的说法来表达这种看法:
关于教育之事吾西方有一物焉,是为东方人之金针者,则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是也……西方近百年之进步,既受赐于归纳的方法矣……吾人欲救东方人驰骛于空虚之病,而使其有独立不倚、格致事物、发明真理之精神,亦唯有教以自然科学,以归纳的论理、实验的方法简炼其官能,使其能得正确之智识于平昔所观察者而已。⑦转引自王中江:《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第266页。
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逻辑学的传播对中国哲学的反思起到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哲学家对哲学方法的反思。因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亦认为,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缺乏“有意识的将思想辩论之程序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从而导致逻辑也不发达:“哲学家不辩论则已,辩论必用逻辑,上文已述。然以中国哲学家多未竭全力以立言,故除一起即灭之所谓名家者外,亦少人有意识的将思想辩论之程序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故知识论之第二部,逻辑,在中国亦不发达。”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因此,冯友兰始终很关注逻辑的问题,在19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他多次提到逻辑的问题,比如,在讨论到朱子的“理”概念时,冯友兰区分了伦理之理和逻辑之理,认为朱子将二者混而为一,未能明了二者的区别。这一批评实际上是站在西方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立场上来评判朱子的理概念。冯友兰进一步指出,朱子的理概念主要是伦理的,其主要内涵是应该(ought),对伦理的特别关注也是中国哲学的整体特点。此外,冯友兰还对中国哲学中“逻辑不发达”深表惋惜。
因此,冯友兰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家受西方文化的刺激,欲在中国学术中引入逻辑方法,逐渐有了方法论的自觉。如果说中国传统哲学比较重视直觉,因而形式逻辑的方法不够发达的话,那么,在未来的中国哲学中,这一点就应该改变,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第二章中说:“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将来会变吗?这就是说,新的中国哲学将不再把自己限于‘用直觉得到的概念’吗?肯定地说,它会变的,它没有任何理由不该变。事实上,它已经在变。关于这个变化,在本书末章我将要多说一些。”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页。在《中国哲学简史》末章,冯友兰称“逻辑分析法”的运用是近代以来“时代精神的特征”,就体现了他对这一改变的期待和努力。
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西方的哲学研究虽有那么多不同的门类,而第一个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的是逻辑。
……
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③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12—313页。
所以,冯友兰1949年之前哲学史与哲学创作的重要工作就是在中国哲学中引入逻辑分析方法,以便使中国哲学更加理性一些。当然,民国前后,西方哲学界也流派纷呈,受其影响,现代中国哲学家的方法论也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除了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外,其他多种哲学方法在现代中国哲学家中也都有拥护者。
三、现代中国哲学家的主要哲学方法
现代中国哲学家方法论意识的自觉与西方哲学的传入有密切的关系。1890年之后,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逐渐进入中国,特别在五四前后更是掀起了一个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的高潮。贺麟曾说:“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实验主义、生机主义、尼采的超人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唯物论、英美新实在论、维也纳学派,等等,五花八门,皆已应有尽有。”④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4页。五四前后,杜威、罗素来华演讲,在中国传播实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以及1920年代—1930年代,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的传播,尤其对中国哲学家具有刺激作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回忆说:“1919年邀请约翰·杜威和柏特兰·罗素来北京大学和其他地方讲学……他们对中国的访问,毕竟使当时的学生大都打开了新的知识眼界。”⑤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10—311页。实验主义的主要宣传者主要是胡适,胡适企图将实验主义上升为一种“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用来诠释中国文化,并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罗素、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法对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与金岳霖一起是“逻辑分析法”的推崇者和实践者,又因他们曾经一起在清华大学共事,因此,被有些学者称为“清华学派”。清华学派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注重用逻辑分析法来分析哲学史,讨论哲学问题,建构中国哲学。另外,1920年代前后,在西方哲学中也产生了一个反理性主义的哲学潮流,主要代表有柏格森、倭伊铿、杜里舒等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等人的思想分别受其影响。尤其是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因其与中国哲学的整体主义、体认式哲学思维有着很大的契合度,得到了一些新儒家学者的深刻认同。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中心观念“直觉”就深受柏格森的影响。熊十力哲学中的“性智”概念尽管主要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与佛教唯识学,但也可以看出柏格森哲学的影响。张君劢与科学派之间的“科玄论战”的核心归根结底其实也是方法之争,即张君劢坚持直觉在人生观中的独立的重要意义,而科学派则企图用科学理性、科学方法来囊括一切,根本否定直觉方法的意义。冯友兰、张岱年都坚持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观,虽然对直觉方法有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根本否定其作为方法论的独立意义。只有贺麟对理智与直觉两种方法采取了较为平衡的观点,认为二者都是重要的哲学方法。
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1930年代,曾经在一些学者中间发生了一场“唯物辩证法论战”,在这次论战中,部分学者认为形式逻辑是唯一的科学方法,而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不相容,因此,不是科学方法。张申府、张岱年则既接受了逻辑解析法,又认同唯物辩证法,并试图将二者融合起来,认为唯物辩证法与逻辑分析法一样,都是最重要、最基础的哲学方法。贺麟一方面受宋明理学,另一方面又受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他试图将理智、直觉、黑格尔辩证法三种方法融合起来,以创造一种较为综合、均衡的哲学方法。
纵观整个现代中国哲学,主要可以分为三大思潮,即实验主义、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的哲学家都有其根本的核心方法。实验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胡适,胡适的主要哲学方法是实验主义方法;现代新儒学家学者,基本都高度肯定直觉思维方法的意义,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学都有高度认同,而按照张岱年的说法,直觉方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主要方法,因此,现代新儒家认同直觉方法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冯友兰尽管受新实在论、维也纳学派的影响,对逻辑解析法情有独钟,早期虽然不甚认同直觉方法,但是,在其新理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形而上学的“负底方法”,这种方法以“神秘主义”为顶点,归根结底又对中国哲学直觉主义的方法有了正面的评价。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但是,受“时代精神”的影响,为了改造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他们试图将逻辑解析方法与唯物辩证法结合起来,以创造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这主要是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所做的工作。关于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思想方法,郭湛波总结说:“总之:五十年来中国思想方法大有进步,因之影响于五十年中国思想也甚大,一是介绍西洋形式论理学,代表封建社会的思想方法;一是介绍美国的实验论理学,代表资本社会的思想方法;一是介绍新近的矛盾论理学——辩证法,代表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①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205页。
可以看出,现代中国哲学家的方法论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画卷,系统梳理这些方法论的内容对于研究现代中国哲学、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本文的主要目的主要是想揭示现代中国哲学史中方法论意识兴起的源头及现代中国哲学家的方法论自觉,更多有关现代中国哲学家方法论的论述只好留待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