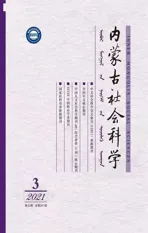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思想与生命政治批判
2021-12-31董彪
董 彪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北京 100871)
在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研究中,“资本权力”往往被忽视或误读,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政治哲学向度也因此未能得到有效凸显。生命政治理论的兴起,为我们从权力特别是操控生命诸种形式的权力角度重新审视《资本论》、深化资本批判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生命政治”(biopolitique)滥觞于近代柏格森等的生命哲学,由瑞典学者鲁道夫·科耶伦率先提出,后因法国思想家福柯的阐释,以及维尔诺、朗西埃、内格里、阿甘本、埃斯波西托等人的进一步探讨,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前沿理论。科耶伦将生命体概念引入政治领域,并指出国家的生命体优先于个体的生命体,从而使生命进入国家政权的视野。生命政治理论的执牛耳者福柯认为,18世纪,随着“把国家财富作为自己目标”的政治经济学成为国家治理的内在理由,国家开始担负起对生命的责任,并把人口的繁殖、健康、疾病、死亡等纳入治理之中,导致了生命政治的形成。阿甘本《神圣人》从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原初结构出发,研究了主权者剥夺生命质性、制造例外状态、生产赤裸生命等一系列生命政治现象,使隐藏在福柯思想“边缘”的生命政治话语被进一步激活(1)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参见郭伟峰《阿甘本与福柯生命政治理论的根本区别——基于生命概念的视角》,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1期。。
总的来看,所谓生命政治就是生命的政治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一整套与生命操控有关的知识体系、技术策略与现实效应。其核心问题是,权力(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社会权力)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具体穿透到主体们的身体中,以及穿透到生命的诸种形式中”[1](P.8),从而实现权力的自我生产、自我维持、自我扩张的意志和目的的。生命政治理论是推进政治哲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
尽管马克思没有提出“生命政治”这一概念,但其资本批判理论无疑与福柯、阿甘本等思想家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视域融合”,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权力理论包含着深刻的生命政治思想。根据《资本论》,在资本的双重逻辑(创造物质文明的财富逻辑和支配操控现代社会的权力逻辑)中,资本的权力逻辑处于主导地位。资本特有的社会关系本质和结构决定了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有意志的力量关系,即权力;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资本就意味着资本权力(2)可见,研究资本权力不是研究资本和权力的关系,也不是研究为权力服务的资本或者为资本服务的权力,更不是研究与国家相关的资本,而是要研究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具象同一性。参见Jonathan Nitzan,Shimshon Bichler,Capital as Power:a Study of Order and Creorder,Abingdon,Routledge,2009,P.3。。资本权力必须施诸活生生的生命才能彰显自身的意志和力量,才能实现价值增殖和资本积累的目标。当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和“异化了的社会权力”之时,就深刻地蕴含着资本权力对生命的支配,蕴含着对资本权力所导致的生命异化的批判。总之,《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批判与资本权力批判是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生命政治批判必须上升为基于资本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使自身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而只有进入生命政治视域,才能深入挖掘马克思资本权力理论的思想深蕴,开显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性。
一、价值增殖:资本“生命化”及其权力构式
“资本”的英文“capital”的拉丁文是“capitālis”。它的词源为拉丁词“caput”,指牲畜头部。先民时期,由于牲畜不仅可以被加工成具有较高价值的形式,而且具有生育繁衍能力,牲畜被当作具有增殖属性的财富(通过数“头”计算牲畜数量)。它的词根为拉丁词“capere”,意为抓住、攫取、掌控、占有,即捕获野兽,抑或是养殖家畜,把它们变成财富并控制他们的生命。(3)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原富》)时,就把其中的“capital”和“capital stock”翻译成“母财”,强调其生殖和增殖的内涵。所以,资本实际上是财富和权力的统一体。它既意味着财富本身,特别是某种具有生命力和繁衍力的财富;也意味着攫取财富的一种权力,特别是攫取具有增殖能力的财富的权力。
在一定意义上,资本就是“能生钱的钱”。这里的“生”表明,资本不是僵死之物,而是能够自我复制、自我繁衍的有机活物。对资本的生命和生殖属性的认识,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从城邦生活伦理出发,批判了以孳息为目的的信贷现象。他认为,人们开展经济活动只应是获取满足自然需要的使用价值,消除短缺和实现自给自足之后就应终止交易。然而,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以牟取利息为目的的信贷业发展起来,钱商把本钱作为“父”钱,企图通过借贷生出更多“子钱”,以谋求货币增殖。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做法超出了交换双方的自然需要,助长了人的过度欲望,动摇了人作为城邦动物追求良善政治生活的根基,不仅是对生命繁殖力的戏仿和嘲弄,也是对自然法则的破坏和亵渎。(4)亚里士多德指出,“为了交易的方便,人们引用了货币,而钱商竟然强使金钱[做父亲来]进行增殖。这里显示了希腊人惯用的‘子息’一字的真意,‘儿子必肖其亲’,如今本钱诞生了子钱,所谓‘利息’正是‘钱币所生的钱币’……钱贷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2页。但是,钱贷对生殖力的戏仿使货币具有了自然合理性,其中的“自然性”与“反自然性”矛盾使原本依附于政治领域的货殖理论(家政学)分离出来。并且,货殖资本的生命繁殖特性随着后来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肯定。
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关于经济活动与城邦政治之间的矛盾转化成经济活动与基督教神学的矛盾,神学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力图使自身的理论与经济发展的现实相适应。他认为私有财产是自然法则的补充,只要最终目的是用于自给自足、公益慈善或公共福利,那么,使货币增殖的盈利行为就是道德的、公正的。18世纪,随着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追逐货币增殖、追求发财致富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马克斯·韦伯将基督教的“天职”观念、禁欲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充分肯定了财富增殖的意义。他引用富兰克林的话指出,货币孳息和哺乳动物产崽一样,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毁弃货币有如伤害生命(繁殖力)。(5)富兰克林指出,“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的本性……谁若把一头下猪崽的母猪杀了,实际上就是毁了它的一千辈后代。谁若是糟蹋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就是毁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钱,甚至是许多英镑”。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孙国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6页。既然繁衍、孳息是货币的本性,那么顺应并推动这种本性发展就是理所应当了。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从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剩余价值增殖的角度来理解资本。在他看来,资本不仅是具有生殖能力的财富,而且也是对财富“生殖力”的攫取、占有和操控,是一种权力形式。一方面,资本是处于生息繁衍之中的、具有生命属性的价值形式。在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转换过程中,资本的价值形式发生着转变,剩余价值不断与原有价值形式分离,从而推动价值量不断发生变化。“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2](P.180)比如公债,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2](P.865)。另一方面,资本是一种将他者生命纳入自身的支配结构之中的权力形式。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P.877)。很显然,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性关系,更是一种政治性关系——即权力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拥有财富意味着法律上的独占权和处置权,财富所有者虽然不能以武力胁迫他人服从自己的命令,却能通过随时收回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撤销规律性的报酬等潜在惩罚方式“逼迫”物质资料的匮乏者放弃反抗、“自愿”就范。所以,物的占有的不平等性必然导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必然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有目的、有意志的力量关系,即权力。资本权力的目的就是价值增殖。
资本要实现价值增殖就离不开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生产,离不开劳动力,因而它必须通过活人及其活动来延续生命、繁衍“后代”。正是由于资本的社会关系结构,它才能把不同的人及其相应的生命活动关联起来,构成资本本身的生命运动。在其中,资本的意志和欲望通过资本家获得表达,资本生命的延续则通过劳动者的生命活动来实现。如果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主人),那么劳动者就是资本的肉身(奴隶)。资本家凭借对生产生活资料的垄断,操控和驱使工人将自身的活劳动对象化为死劳动,把外物的躯体同化为自身的躯体,以资本灵魂取代自身的灵魂。正是这种“灵与肉”统一的社会关系,资本成为自我繁衍和增殖的生命有机体,成为生命化的资本。
资本的增殖欲望反映了资本的生命属性,资本生命的存续和繁衍离不开资本家凭借“私有财产”对生命的支配。这种以物为中介的生命结构也是一种以生命为对象的权力结构,由此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微观构式。资本的生命孕育并成长于社会有机体之中,但其病毒式的扩张能力使之对社会有机体产生了一种强大的、不可控的反噬力。因此,资本按照自身的逻辑法则推进自我生命演进的同时,也把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纳入到自身的逻辑法则之中,使之成为自身生命形式的质料。福格尔指出,资本必须承担所有分裂繁衍的任务,它考虑的是如何使一切可能存在的财产汇入资本洪流之中;如何使一切可能存在的行为和生产方式变成“抽象劳动”,“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资本的自我再生产才能被理解为获得所有生产力和生产的主要机器,也才能被设定为社会和政治团体进行自我保护的新的‘准理由’和协调因素”(6)参见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Anti-ödipus. Kapitalismus und Schizophrenie I,Frankfurt/M. 1974,PP.290~293,339。转引自福格尔《资本的幽灵》,史世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所以,资本的价值增殖是资本生命化和生命资本化的统一,是资本对生命统治和支配生命的结果。当这一过程表现为资本权力对劳动者生命基质的剥夺、重塑和技术统治时,资本和生命的内在关联就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学意义,更具有生命政治意义。
二、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权力与赤裸生命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基本条件,也是资本权力形成的基本条件。离开劳动力,资本将失去生命,资本权力也将不复存在。这是因为,权力是一种不对称的力量关系,若只有实施力量的主体而没有承受力量的对象,那么权力就不复存在,“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会丧失他的权力”[2](PP.223~224)。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和形成资本关系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二是劳动者能够在市场上自由地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当货币占有者与劳动力出售者的交易一旦达成,货币就能利用其对活劳动的支配来摆脱自身“化石般”的存在形式,成为自我繁衍、自我增殖的生命有机体。历史表明,活劳动并非现成地等待着资本权力的支配。资本家的财产要以全新的形式与活劳动结合起来,就必须使活劳动从土地和劳动工具的直接束缚中摆脱出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而出卖自身劳动力的过程,不仅是旧有所有制关系被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的过程,而且也是劳动者生命持存和生命活动的直接对象物被剥夺,从而成为赤裸生命的过程。所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不是简单的政治经济学事件,而是一项生命政治事件。
“赤裸生命”是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发明的生命政治概念,意指由共同体中的至高权力所生产的一种特殊生命形式。他指出,在主权者所宣布的例外状态(如紧急状态)下,一些人被纳入性地排斥在法律的保护之外,这些人可以被主权者任意地杀戮而不必担负法律责任,这种人的生命就是赤裸生命(bare life)(7)阿甘本指出,英文中的生命,即life,在古希腊有两个对应的词。一是zoe,指生物学意义上的存活,如家庭、繁殖等;二是bios,指政治学意义上的生活,如城邦共同体中向善的美好的政治生活。在古典时代,zoe意义上的生命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属于上帝;只有bios意义的生命才属于世俗政权。但是,《权利宣言》却把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写入民族国家的司法,使赤裸生命进入国家结构,并成为政权的世俗基础。。赤裸生命能够被生产出来,就在于主权者拥有悬置法律有效性、将自身置于法律之上的至高权力,以至于它可以正当地实施超越法律的暴力。主权者的司法悖论构成的是赤裸生命的存在悖论。赤裸生命好比狼人,他既不是人也不是野兽,而是处于人与野兽、自然与约法之间的不可区分之域,任何人戕害他、杀戮他都是合法的。质言之,由于与自然的切身性关系被斩断,由于被纳入社会(法律)关系中又被抛回自然,因而赤裸生命变成了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漂浮物和任人宰割的生物体。
如果说阿甘本是从法律权利的角度分析赤裸生命,那么马克思则是从财产权利角度探讨作为赤裸生命的劳动者。这是因为,这种分离完全剥夺了活劳动赖以生存的质性,致使劳动者失去原有共同体的保护,成为任由资本权力操控的赤裸生命。可以说,一部资本原始积累史就是一部赤裸生命的生产史。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要建立吮吸他人生命、剥削他人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就要埋葬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随着资本逻辑逐渐在主权治理领域取得统治地位,在自然法权的外衣下暴力具有了合法性。在原始积累过程中,资本不惜一切手段打破封建式的共同体。它让个人摆脱土地的束缚、脱离奴隶主和封建主的人身束缚以及行会制度的束缚,成为市场上自由行动的单子化个体;它让土地等生产资料完全变成新兴地主或资产阶级新权贵的私有财产,变成可以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它让原本由君主掌握的生命支配权和财产支配权转移到资本家手里,成为资本的权力。这样,洛克所说的同属单一个体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就被分裂并对立起来,变成两个群体、两个阶级分别独立占有之物。在资产阶级社会,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被强制抛到市场上的“劳动力的出卖者”完全成为一个悖论性的存在。从其生物属性来看他是一个人,但从其社会属性来看他又不能算作一个人;从其拥有对自身身体和生命的处置权来看他是有产者,而从其生命活动没有现实对象来看他又是无产者。他们被纳入资产阶级法律体系之中,却又不受法律保护,反而被合法地奴役、戕害甚至处决。所以,他们是资产阶级社会“例外状态”中的“赤裸生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状态”中的“狼人”。马克思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就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2](P.823)的过程,它始终伴随着“‘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2](P.836)。被暴力剥夺土地的农村居民变成了贫民、盗贼、流浪者、游惰者,进入法律保护的真空地带,成为任由国家和资本宰割的对象,成为赤裸生命。自15世纪末以来,为给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英国颁布了大量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包括鞭打、烙印、酷刑、处决等等),使流浪者变成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和纪律的工人。
与生产资料分离后在资本统治下重新结合起来,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基础。然而,劳动力成为自由市场的商品,掩盖了资本权力对赤裸生命的生产。在货币向资本转换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消极自由能力,市场自由不过是一种被强迫的、形式上的“积极自由”;由于没有对等的财富权利作为物质基础,交换平等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上的“虚假平等”。一方面,劳动者表面上可以“自由地”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但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他除了将自己作为活人的生命时间交由资本家支配外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市场平等只是一种虚假的平等,由于买卖双方在财富(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占有)上的严重不对称,交换的发生不是基于平等关系,而是“物”的力量的博弈。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关系导致的却是实质上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二律背反。可见,资产阶级宣称的市场权利不过是神圣自然法与资产阶级经济主权的秘密共谋,不过是资产阶级法权关系与资本权力的有机团结。劳动力买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劳动者的赤裸生命状态,相反,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条件,推动了资本权力向生产中的生命权力过渡。
三、从身体规训到人口治理:作为生命权力的资本权力
资本运行的根本目的是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这一过程既创造了物质财富,又实施了资本权力。正是这二者的统一,资本才成为名副其实的“财富—权力”。以《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统摄,可以把资本权力区分为身体规训和生命操控这两种生命权力形式。前者表现为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对个体活劳动的吮吸,即对工人身体的规训;后者表现为资本积累过程中对劳动群体的排斥性吸纳,即对工人人口的调节。对个体身体的规训和对人口的调节按照资本的意志绞合在一起,并构成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循环,共同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后来,福柯也洞见到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包含着对身体和生命的算计和利用。他指出:“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4](P.91)资本权力内在地包含着“驯化—惩戒”和“吸纳—排斥”的二重化机制,它构成了资本实施生命权力的本质性领域。
剩余价值生产为资本权力进行身体规训提供了空间。由于劳动与资本之间不对称的力量关系和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穷贪欲,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表现为资本在其增殖理性支配下对活劳动的吮吸,即对劳动者的肌肉、神经、脑等的消费,以及对身体的利用、操控、激发和压抑。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权力对生命的操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外延式吮吸,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内涵式吮吸。就前者而言,资本对活劳动的剥削表现为工作日即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这种延长超出了工作时间的道德界限和工人身体的自然界限。就后者而言,由于延长工作日必然遭遇道德界限、自然界限和法律的限制,资本将外延式剥削转向内涵式剥削,即相对缩短劳动时间而增加劳动强度,“在一定的限度内,力的作用的持续时间上的损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来弥补”[2](P.472)。
同时,在分工、机器以及技术的“座架”下,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特别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更加隐蔽化、精细化,资本权力针对劳动者身体的规训日益加深。由于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机器快速发展,生产的计划、部署、调节逐渐成为资本的内在职能,工厂的制度、纪律、惩戒成为资本控制生产的手段,劳动者的身体时空组合形式、动作节律状况、生产效率高低以及工作意识状态都成为资本管理的对象。例如,一切在机器上的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2](P.484),即让肌肉和身体运动的姿势、强度、频度、效能必须符合机器的要求,变成机器的无意识的附庸和零件,“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2](P.483)。最终,机器成为工业的君主,而工人则成为围绕在其身旁的臣仆或奴隶。
通过对身体的规训和剥削,资本拓展了自身的生命宽度,然而它旺盛的生命力是以工人生命力衰退和生命长度缩短为代价的。工人的整个工作日甚至一生都在从事无内容、无灵魂的机械劳动,这一过程必然会破坏工人的生命基质。但是,资本对此毫不在意,“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2](P.307)。所以,为满足资本积累对鲜活劳动力嗜血般的需要,资本还必须由对生命的规训转向对生命的治理,变成针对人口的生命权力。
马克思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8)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时期的资本逻辑。参见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出发剖析资本针对人口的生命权力的。在人类学的一般生产逻辑下,人们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和种的繁衍参与生产劳动,此时生命政治表现为以自然性或神性为原则的生命操持。在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商品生产普遍化,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成为生产的目的,生产逻辑被置于资本逻辑之下,人的自我生命的生产以及人对他人的生命的生产均被纳入到资本逻辑之中,被资本权力支配。人口的繁殖、出生、死亡、健康水平和寿命等及其变化的条件均成为资本权力关注、评估、干预、规制、监管的对象。资本实施生命权力的目的,就是以最大化地吮吸剩余劳动、最大化地推动资本积累的原则操持群体生命、调节人口生产。
资本权力作为一种对生命进行治理的权力,就是要管理和调节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的比例,控制人口再生产和劳动力供应的速率与节奏,这集中表现为资本积累过程中对人口规模的调控。资本积累意味着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没有被榨干吃尽,而是投入到新一轮的价值生产中,“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这就是所谓‘资本生资本’”[2](P.672)。资本规模与人口规模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资本的有机构成,二是资本的总体规模。如果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劳动数量就随着总资本的数量增加而增加。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单位可变资本推动不变资本的能力增强,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固然也会增长,但劳动增长比例相较于总资本增长比例会逐渐降低。这意味着,为了继续雇佣和支配已经在职的工人以及新增的工人,资本的规模需要不断地以递增的速度向前发展。如此,又将进一步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减少单位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劳动量,加快资本积累的速率。其结果是,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断高于就业人口(可变资本)的增长率,从而导致剩余人口的产生。表面看来,这些剩余人口获得了自由,实质上却被资本更为严苛地统治着,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资本权力。“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膨胀力也增长了。”[2](PP.728~729)
资本的生产和积累的过程不是单调、平稳地进行,而是受市场的影响出现周期性变化,这种变化也会使剩余劳动人口周期性地“历险”。经济形势良好,剩余劳动人口则可能被资本吸纳;经济形势低迷,剩余劳动人口则可能被资本排斥。“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口具有显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相对过剩人口时而在危机时期急剧地表现出来,时而在营业呆滞时期缓慢地表现出来”。[2](P.738)剩余人口(无论是流动的、停滞的,还是潜在的)的命运也处于不确定之中,对他们而言,生命只有两种状态,即暂时做成了工业奴隶的状态和想做工业奴隶而不得的状态。如果说被迫与生产资料强制分离的劳动者是资本权力第一次生产出的赤裸生命,那么作为剩余人口,即被抛到市场上的剩余人口则是资本权力第二次生产出的赤裸生命。
福柯认为:“种族主义保证了生命权力经济学中死的职能,根据他人的死亡就是对自己的生物学巩固的原则,因为我是种族或人口的一部分,因为我是活着的多样的统一体中的一份子。”[5](PP.196~197)在人口治理的过程中,被排斥在资本吸纳机制之外的工人实际上也被执行了一种种族主义政策,因为被排斥在生产机制之外的劳动工人变成一个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新的阶级,一个弃民或贱民阶级,甚至是另一个民族或种族。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道德习俗和宗教政治形式,“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同,好像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6](P.438)。资产阶级也是按照自己异族的方式来对待工人的,他们在统治阶级内部加强保障、处理好遗传繁殖等问题,而对于无产阶级则不管死活。这虽不像国家的种族主义那样直接残忍地杀人,但却是在间接地、“温和”地杀人。由产业工人的患病种类、伤残数量以及死亡率可以勾勒出资本病理学(或工业病理学)的历史图谱。一部资本主义生产史,就是工人这一种族的生活史、健康史、疾病史,也就是资本权力对生命的支配史。
可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不断“生产着”供自身支配的剩余劳动,并通过剩余劳动加强了对现有劳动力的操控。全部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都被置于资本的霸权之下,接受其对身体活动的支配、对生命生产的控制以及对整个劳动人口的操控。资本生产过程中对人口和生命的操控既服从于资本的“财富逻辑”又服从于资本的“权力逻辑”,最终形成了资本权力的本质性领域。
四、资本权力与资本的生命政治学
权力,首先生产出真理,然后才能生产财富。正如福柯所言:“如果没有真理话语的某种经济学在权力中,从权力出发,并通过权力运行,也就不能行使权力。”[5](P.18)这里所意指的,正是政治经济学诞生所带来的“权力—知识—真理”效应。马克思实际上也发现了权力对知识和真理的生产功能,特别是剖析了资本权力对生命政治学的生产。在他看来,资本权力不是单纯地以暴力为支撑,反而更需要内在的合法性论证作为基础。这种合法性就建立在特有的知识体系和真理机制的基础之上,而由资本权力驯化而来的整套思想观念、认知体系以及经济理性,即成为资产阶级建构自身合法性、推动社会发展的认知基础。
首先,资本在支配和操纵生命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生命支配的知识体系。在社会生产的上游,资本致力于将活劳动变成可变资本,将非资本性的物品转化为不变资本;在社会生产的下游,资本则致力于整合财富生产、权力生产和生命主体生产。一方面,身体成为与经济利益密切关联的生产性对象,操控、驯化、激发、压抑身体的一整套手段构成了肉体的力学;另一方面,人口被纳入资本权力的生命治理机制,构造了人口的生物学和人类学。例如,为“探底”工人维持自身基本生存需要的最低工资,为验证工人的身体能够承受何种恶劣的劳动对象、劳动环境,资本家不惜拿工人的身体和生命做生理学实验(就像解剖学家拿青蛙做实验一样),劳动者的生命活动被当作无价值的生物体。由于工人平均寿命不断缩短,资本使“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2](P.739),并由此生产出一条仅适合于无产阶级的人口规律。根据资本主义人类学,“儿童时代到10岁,或者至多到11岁就结束了”[2](P.323)。所以,资产阶级学说并不是秉持真理性原则的科学理论,而只不过是一套为资本主义生产做合理性、合法性论证的说辞。
其次,资本权力使国家权力服膺于自身,并由此形成了有效治理生命的法律体系。资本与法律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其一,法律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特别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国家法律表现为资产阶级不可褫夺的“天赋人权”。资本主义法律及其制度就是要以野蛮的方式为资产阶级的文明开辟道路,把“资本的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贫穷化当做全部国策的极限”[2](P.826),使“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2](P.827)。其二,法律开始对生产活动进行适当限制,但资本生产具有高度的优先性和自由度。出于最基本的社会治理和人口治理职能,国家会颁布强制性法律,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最起码的清洁卫生设施。但是,一旦工厂法影响资本通过劳动力的“自由”购买和消费而实现价值增殖、破坏自由生产和资本家的利益、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资本就会阻击、反抗国家权力和法律权力。资本权力与国家权力抗争周旋的结果就是,国家的卫生机关、工业调查委员会、工厂视察员把对工厂的要求限制到资本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其三,法律被内化到资本生产的内在机制之中,促进了资本权力的理性化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进步,工厂法等法律制度纷纷出台,迫使资本改变增殖方式和权力策略。表面上法律权力外在地限制了资本权力发挥作用的空间,实际上法律权力促使资本专注于自身内部的改造、整合和革命,使价值增殖效率不受分毫损失。经验反复证明,“如果资本只是在社会范围的个别点上受到国家的监督,它就会在其他点上更加无限度地把损失捞回来”[2](P.564)。在与政治权力进行较量和周旋的过程中,资本权力将法律内化为自我约束的机制,将经济理性、技术理性作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理由,并以此使权力的实施更加微观化、精细化,并由此获得一种自我驯化的形式。
最后,资本关于生命的政治经济学,在资产阶级那里被美化为一种公正合理的经济学理论。对他们而言,没有真正的真相,只有被挑选、被扭曲的真相。资本的发展史也被美化为具有田园牧歌式的历史。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血腥暴力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2](P.821)。他们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把劳动者转变成雇佣工人的历史片面地解释为生产者获得解放的历史,而忘记了这一过程是用血与火的文字书写而成的。所以,只要是为了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亚派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2](P.836)。资本权力为劳动阶级生产了愚昧无知,却为资产阶级生产了服务于价值增殖的知识体系。
在资本权力和生命政治的双重互动中,资本将关于生命的系列知识注册在自己的财富—权力逻辑之中,产生的正是嵌入资本权力结构内部的生命政治学。当然,和西方生命政治理论不同,马克思思想视域中的生命政治学不仅批判资本权力造成的生命存在形式的异化,而且也指明了反抗和超越资本权力、建立积极健康的生命政治学的路径。在马克思看来,超越资本权力导致的生命异化,必须彻底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把资本的权力还给历史,使剥夺生命者反被剥夺。在共产主义社会,伴随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个人所有制的重建,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力将重返劳动者,由资本权力主导的社会结构将被实质正义的社会结构所取代,物化的社会关系将变成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社会将迎来自由自觉的生命存在形式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