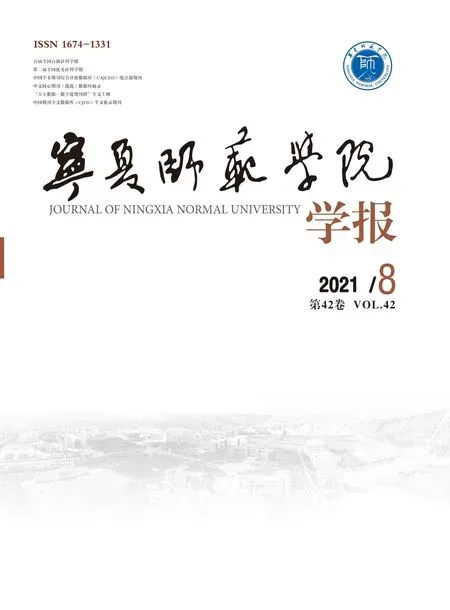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皇帝诏书研究述论
2021-12-31马维仁
马维仁
(宁夏师范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宁夏 固原 756099)
明代皇帝的诏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诏书是各种诏令文书的总称,而狭义的诏书“是在明代诏令文书中排列第一位的御用文书,不仅具有多种存在形式,而且有着极为广泛的功能与用途,形成了明代诏令文书的一个显著特点”[1]。本文所探讨的“诏书”即指后一种狭义的诏书。
诏书是中国古代帝制时期以皇帝名义颁发的政府下行公文,代表皇帝的神圣权威,一经正式公布,即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诏书不仅体现皇帝的政治意志,同时也是皇帝治国国家的重要手段之一。学界历来重视对诏书的考察和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史学界对明朝皇帝诏书的探讨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新阶段,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新成果。
一、对遗诏、即位诏的研究
明朝270余年历史,共历16位皇帝,留下完整遗诏12份,即位诏17份,其中包括1份明英宗南宫复辟后的复位诏书。这些遗诏和即位诏是明代皇位更替之际的重要政治文件,对确保皇位顺利更替、皇权顺利交接具有重要作用,与其他类诏书相比,具有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
学界关于明代皇帝遗诏、即位诏的整体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中国台湾学者张哲郎对明代皇帝即位诏、遗诏与明代政权转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明代皇帝除了太祖、惠帝、成祖之外,遗诏与即位诏全由内阁负责,“一般而言前期的遗诏及接任皇帝的即位诏皆出自同一人。即位诏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多半是应景的官样文章”。即位诏后面开列的应行条款,未被真正执行,“虽然有时新君会遵守一些诏文……但这是特殊例子”[2]。
田澍在其专著《嘉靖革新研究》一书中对明代即位诏书中所列弊政情况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将诸帝即位诏的兴利除弊内容分为“枉司法”“重民困”“纵百官”“废武备”“滋冒滥”“恤王府”“其他”七个方面。通过列表和数轴图形的方式对即位诏所列前朝弊政做了细致的分析比对,指出:“自建文至弘治年间,明朝的积弊总体上呈上扬趋势,到了正德时期,形同奔腾之势,达到了最高点。”[3]同时得出吏治腐败加重趋势与民众负担程度之间成正比关系的结论。通过对即位诏书内容的分析,从而对明代政治走向情况进行整体把握。
其《嘉靖革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以列表和图示的方式对明成祖至明熹宗诸帝的即位诏书所列前朝弊政情况进行梳理,从而为其提出的“嘉靖革新”观点找出有力的证据支持。
洪早清对明代阁臣代皇帝起草遗诏和即位诏的政治功能问题进行了探究,指出“从实际上看,永乐以来历代皇帝的遗诏和即位诏书大多是内阁阁臣起草的,特别是即位诏书”,而对于内阁阁臣代皇帝起草遗诏、即位诏的政治功能。作者认为:“明代废除宰相以后阁臣代皇帝起草遗诏或即位诏书实际上就是‘代王言’,它在明代的政治运行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皇帝的政治素质、知识阅历、能力水平等表现都很一般,个别的非常差,他们都比较的缺乏治国的才能,国家最高权力的运作又缺乏一个名正言顺的中枢机构来协调,如何使皇帝的发号施令尽可能切合国家政治的实际,并努力具备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效用,阁臣的‘代王言’在这方面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
毛佩琦研究了明代皇权嬗递之际的改元更化问题。他通过对明代诸帝遗诏、即位诏的分析,认为“皇权的嬗递,为纠正政治偏谬提供了机会,遗诏与即位诏体现一种变革精神,以使庶政不致过远偏离轨道”。但是,这种改元之际的更化效果如何?更化是否彻底呢?他指出:“明朝从建文、永乐以后可以说在每次改元后的新政都起到了或多或少的作用,也就是说改元之后有所更化。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哪一朝君臣又都没有将新政贯彻到底。这样,明朝政局就处于败坏——调整——再败坏——再调整,直到朝政败坏到无法调整的总趋势之下。”[5]
赵轶峰对明代皇帝遗诏和即位诏进行了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系列论文来探讨相关问题,影响较大。其《明代的遗诏》一文主要论述了明代皇帝遗诏的基本规制及传世情况、明代遗诏的内容及草拟背景、明代遗诏的政治功能、太后遗诏及矫拟遗诏等问题。他认为明代遗诏为皇位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正式文献,即使在已经立有储君的情况下,仍然是嗣君即位合法性的必要基础。同时认为,由于遗诏由文臣起草,士大夫有可能借草拟遗诏之机,渗透自己政策更革主张,故遗诏颁行,通常带来一定政策调整,这反映出遗诏作为士大夫群体纠正皇帝弊政的潜在途径的意义。他提出明代遗诏在皇位交替之际的三大政治功能,即最终确定皇帝继承人;特殊情况下授权后宫干预政治;为随后改革弊政张本。[6]
赵轶峰还发表三篇系列文章:《明前期皇帝的即位诏——从洪武到正统》《明中期皇帝的即位诏——从景泰到嘉靖》《明后期皇帝的即位诏——从隆庆到崇祯》,分三个阶段对明代皇帝即位诏进行了系统探讨,从整体上回顾了明代皇帝即位诏,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即位诏是明代国家政治运行至皇权转移之际的重大政策文本,肯定不只是官样文章。第二,每次皇权转移之际,皆为明朝政局、人事、政策方针调整的重大节点,因而是研究者探讨、理解明朝政事的关键点。第三,明代历朝即位诏中的大赦新政条款,都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当时国家政务与民生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当朝者当时考量的重点问题。第四,内阁为主的士大夫是所有即位诏拟写的主要人群,他们曾多次试图通过即位诏书调整前代推行或积累形成的弊政,甚至借机限制皇权或者推行改革,因而即位诏背后常常隐含着士大夫与皇权的政治博弈。第五,洪熙、嘉靖、隆庆、万历诸帝即位诏是明代历史上最具有政治文化意义的即位诏,其公布之际,也是明代庙堂政治历史具有特殊含义的时刻,从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的纠结角度看,尤其如此。[7]
赵轶峰认为即位诏“肯定不只是官样文章”这一观点,不同于中国台湾学者张哲郎先生的观点。
马维仁探讨了明代皇帝遗诏与即位诏的关系,认为“明朝的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皇帝遗诏与即位诏的作用更加凸显,尤其在皇位更替之际更是发挥着重要作用。遗诏与即位诏关系密切,共同确保皇权的顺利交接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时,两诏中有大量兴利除弊的内容,这集中体现了大行皇帝临终悔过之诚和新皇帝的图治之心。”[8]
除了对遗诏、即位诏进行整体研究之外,还有学者对明世宗即位诏进行了个案分析。明世宗即位诏在明代所有诏书中显得很特别。正德十六年,明武宗死于“豹房”,结束了其荒唐的一生,死后未留下后嗣,明世宗朱厚熜以宗室藩王入继大统,杨廷和草拟了即位诏书。关于明世宗即位诏书,李洵于1986年发表了《“大礼议”与明代政治》一文,在该文中,作者探讨了明世宗入继大统的政治环境,比较系统地剖析了明武宗遗诏和明世宗即位诏。从武宗去世到世宗即位这段皇位空缺的时间里,“是一个帝国的紧急时期,必须防止来自武宗亲信势力的突然政变”。所以,杨廷和等人做了紧急应付政变的准备,这种准备更多地是以武宗遗诏的名义进行。经过一个多月的皇位空缺,明世宗终于在四月二十二日顺利登基,即位诏书中所列兴利除弊条款多达80条。李洵先生将这些条款分成了十一大类,得出“世宗的登极诏,对武宗持一种委婉的批评态度……这一种指导思想就使即位诏书的兴革条款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是针对武宗弊政的”这一重要结论。而且,他从世宗继统当时情形推断,世宗的登极诏不是出于明世宗本人的意见,而是出于张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意见。[9]
田澍《嘉靖前期裁革冗员述论》一文也涉及明世宗即位诏书。文章就明世宗即位之前的明代冗员状况、世宗即位之初杨廷和依据即位诏书对冗员的初步裁革,以及钦定大礼之后张璁等“大礼新贵”对裁减对策的调整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察,认为明代中后期的冗员弊政的真正裁革是在嘉靖初期“大礼议”之后张璁等革新派大臣在阁时期。[10]
马静对明世宗即位诏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明世宗即位诏“是正德、嘉靖之际复杂局势的投影,是改革派复杂心情的体现,也是他们的政治革新的指导思想和改革目标”。她将明世宗即位诏除弊内容分成了冗滥、宦官、司法、经济、吏治、宗藩等六个方面,通过分析得出明世宗即位诏的落实是不够彻底的,其原因是“大礼议”的发生、腐败势力的不断产生以及办事官员贯彻不力。[11]
嘉靖、隆庆之际的皇位更替也有着重要的政治改革意义。姜德成《徐阶与嘉隆政治》对明中期首辅徐阶在嘉靖、隆庆两朝政治上的作用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其中涉及徐阶起草明世宗遗诏与明穆宗即位诏的过程与影响。[12]
也有一些介绍新出土诏书文献的论文,王咨臣《新出土的明孝宗“罪己诏”与传抄本〈明实录〉校勘记》,对1978年出土于江西新建县明墓中的明孝宗“罪己诏”作了介绍。[13]郑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征集到正德皇帝的“罪诏”》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征集到的明武宗罪己诏进行了介绍。[14]总体来看,学界对明代皇帝遗诏和即位诏的探讨是比较深入的,既有系统研究,也有个案分析。
二、对其他类别诏书的研究
除了遗诏和即位诏,其他类诏书对明史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很多学者对这些诏书也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
署名“西藏自治区管理委员会”的文章介绍了明太祖和明成祖赐给西藏楚布寺宗教首领的两道诏书。第一道诏书是洪武八年正月明太祖赐给楚布寺噶玛噶举活佛的宣谕诏书,字数不多,语言表达口语化,诏书内容主要表达的是明太祖对楚布寺噶玛噶举活佛宗教活动的赞同和支持。第二道诏书是明成祖十一年赐给楚布寺大宝法王的诏书,诏书文字内容较多,文章附录了诏书的原文,并对诏书反映的主要思想进行了分析。[15]
熊文彬《明封佑善禅师诏书》一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一件藏于民间的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敕封藏族高僧沙加的诏书。作者先后就此份珍贵文物的保存情况、材质、尺寸大小、图像、诏文等向读者进行介绍,并考述了诏书所反映的时代背景。[16]
孙宗贤、刘亮著文向读者介绍了收藏于陕西凤翔县博物馆的明代天启年间一份珍贵诏书。此份诏书系明朝后期抗清将领袁应泰牺牲后,天启皇帝为表彰袁应泰而颁发给其家属的一份诏书,具体颁诏时间是天启四年九月三十日。该文不仅介绍了诏书的制作材质、形状、大小等,而且对诏书内容加以考证。[18]
以上四篇文章都是对新文物资料的介绍,对推动明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万明对明太祖诏令进行了较系统地研究,就此问题先后发表了系列文章,如《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明代外交诏令的分类考察——以洪武朝奠基期为例》《明帝国的特性:以诏令为中心》《明初政治新探——以诏令为中心》《明代诏令文书研究——以洪武朝为中心的初步考察》《明代诏敕的类型——以明初外交诏敕为例》等等。万明以明太祖时期的诏令文书为切入点,考察明初的政治和外交,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诏令,而诏书只是诏令文书中的一部分。
在《明代外交诏令的分类考察——以洪武朝奠基期为例》一文中,作者对所见洪武时期外交诏令进行分类考察,认为:“在洪武时期对外颁发的诏令文书中,诏书是第一位的。”[19]
在《明初政治新探——以诏令为中心》一文中,万明以明太祖诏令为中心探讨了明初的政治构建和运行情况,其中诏书是作者要考察的重要方面。文中涉及的诏书有即位诏、免除税粮诏、平边诏、求言诏、劝课农桑诏、赦宥诏等,作者通过对以诏令文书为中心的明代政治的考察,指出“明代中国平民帝业的成功,产生了颇具特色的政治过程,‘以文书御天下’形成了君主专制一元多维政治体制。”[20]
在《明代诏令文书研究——以洪武朝为中心的初步考察》一文中,万明对《明太祖御制文集》所收录的41通诏书进行了分析,认为《御制文集》将“诏”列在全书最前面,“说明了诏书在明朝诏令文书中的首要地位”。她将这41通诏书分为三个用途,分别为通告全国、颁发地方、颁给个人,并认为“以上说明诏书的形式用途广泛。并不只是狭义的昭告天下之义。实际上,诏书成为明代皇帝的文书泛称,布告天下之外,有广义上的诏谕之义。”[21]
在《明代诏敕的类型——以明初外交诏敕为例》一文中万明对明初所见外交诏令进行研究,在涉及“诏书”的内容中,认为“一般而言,诏书是布告天下的,具有公告的性质,属于通行文书一类。但是在专门颁给一国的情形下,也具有专门文书的性质。”[22]
所以,办公室工作需要建立一些规范制度来规避不恰当使用同理心导致的对制度和道德的侵蚀。首先是办公室各项业务工作都要有依据、有制度、有规定,这是使用同理心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在制度规定范围内使用同理心做好各项工作是受鼓励的,但是决不允许出于同理心,为了帮助某个人而置制度于不顾。其次是加强制度学习、同理心把关。每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首先应该学习岗位工作制度,学懂弄通后才能开始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鼓励工作人员为做好工作在制度范围内使用同理心。如稍有不慎,同理心泛滥、凌驾于制度之上的时候就要给予提醒,确保办公室工作人员合理使用同理心。
李媛研究了明代皇帝的修省和罪己行为,其中涉及明代皇帝的罪己诏,指出“当皇帝认为单纯修省已经不足以达到弥灾效果时,便会颁布罪己诏”。 同时作者认为:“与以往历朝相较,明朝皇帝颁发罪己诏书的情况并不十分常见,这与频繁举行的修省活动形成鲜明对照。”作者在论文中还列举了明代曾经颁发的10份罪己诏书,并将这些罪己诏书分成了两类,一类是配合修省而颁发……修省不足以显示反思罪己之诚意,即颁布诏书,以示慎重警惧和反省之诚意。第二类是指建文、崇祯时期面临君之将易、国之将亡的局面,皇帝为稳定人心所下的罪己诏。[23]
赵中南以洪熙到成化时期的皇帝诏书为例,探讨了明前期减免宫廷财政的问题,他认为明朝前期通过诏书减免宫廷财政的手段分为两种,一种是恩蠲,另一种是因灾蠲免,“不论是哪一种减免,都存在一个减免力度大小的问题,而诏书减免的内容是定时定额的部分,还是临时额外加派的部分,是消耗量大、较为急需的部分,还是消耗量小、不甚急需的部分,则是衡量诏书减免宫廷财政收入力度的重要标志之一”。[24]
陈时龙对明代诏令的类型进行了研究,他把明代诏令分为:诏、诰、制、敕、册文、谕、书、符、令、檄等十类,并对诏书的特点和功用进行了举例分析,认为“诏令无疑是因重大事情向臣民发布的最正式的、常用的、公开的诏令格式。”[25]
另外还有杨卫东《简说明代文书中的“诏”与“敕”》对明代诏令文书的“诏”和“敕”进行了简要介绍。
李明明对明代的“矫诏”问题进行了研究。由于诏书具有神圣性,诏书的使用权具有不可僭越性,故“矫诏”实为帝制时代的政治大事。李明明在其硕士论文中依据《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明史》三种文献,对明代的“矫诏”问题进行了考察,将这些文献中的“矫诏”情况归纳为三种类型,即子虚乌有的“矫诏”、存有疑问的“矫诏”和皇帝默许的“矫诏”。[26]
周桂林对明初朱元璋诏令文书的起草文笔进行了探讨,认为朱元璋的诏、谕、令、旨多是经文人润色之笔。[27]
对明代诏书文本写作及其流传问题的考察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新问题。李新峰的《明代诏书文本差异考析》一文以洪武十三年废省分府诏书中的五府分区方案流传文本为例,考察了《明太祖实录》《皇明诏令》《皇明诏制》《明会典》所记录此方案的诸多差异,指出:“明代的制度条文,即使是最重要的内容,即使成文于明初那样严猛苛责的环境下,即使有非常接近成文时代或照录原文的版本,其传世文本的内容、文字也不一定精确。”因此,“对诏书条文的解读乃至对相关史实的深思,或可更严格地建基于文本比对,慎重对待内容突兀之处,以免过度解读。”[28]
肖虹、胡明波从文本书写的角度对明代公文写作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研究认为:“明代是一个文法理论迅速发展的时代,表现在公文领域是对奏疏、诏书、表三个典型文体投以了极大关注,并总结出了一套关于文体写作的理论诉求。”具体到诏书写作上,明人更重视“务实性和典雅性”,“更推崇从简约精练的文辞、务本求实的内容上下功夫。”[29]
三、关于诏书研究的特点及不足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明代皇帝诏书进行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探讨和研究,成果丰硕,对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此问题奠定了基础。对这些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学者们研究和关注的焦点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从横向看,相比其他类诏书,学者们对明代皇帝遗诏和即位诏书更为关注,研究也更为深入,更为系统。如张哲郎先生、赵轶峰先生、田澍先生等,都对明代皇帝遗诏、即位诏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
其二,从纵向看,相比其他诸帝诏书,学者们对明初,尤其是明太祖时期的诏书更加关注,这可能是由于明太祖时期正处于明代初期的创制时期,学者们希望通过对太祖时期诏书的研究和分析,找到明朝历史发展的初期脉络。最为典型的是万明,她的一系列研究明代诏令文书的论文,大都是以明太祖时期作为视角和切入点。
此外,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就明代诏书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如下不足之处:
其一,缺乏对除遗诏、即位诏之外的其他类诏书的专门考察。
其二,对明初朱元璋的诏书研究比较深入,但对其余诸帝诏书的研究比较薄弱,成果较少。
其三,就明代皇帝遗诏、即位诏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更多的是从宏观上对遗诏、即位诏的考察,缺乏微观的、针对某一份具体诏书的个案分析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