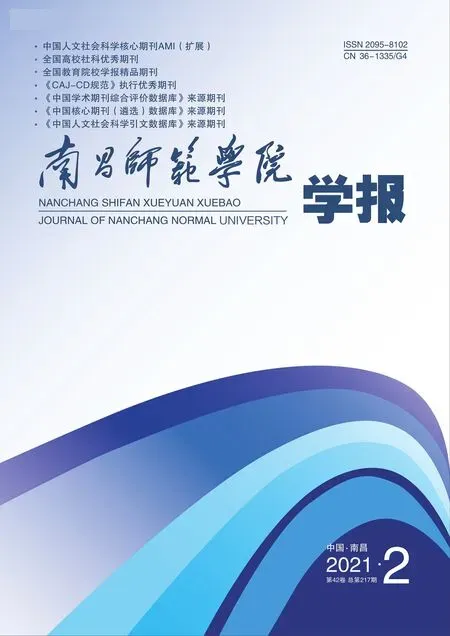当代广告的“戏仿”创作策略考察
2021-12-31姜易杰
程 军,姜易杰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安徽蚌埠 230030)
“戏仿”(parody)是一种拥有悠久历史且独具特色的文艺创作手法和文化生产方式,它常常通过对经典文本(1)这里的“文本”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可以指一切意指实践所产生的制成品,不限于指文学的、书面的文本,还可以指电影、绘画、音乐、建筑等其他艺术文本,也可以指一切具有语言—符号性质的构成物,如图像、服装、饮食、仪式乃至于历史等等。进行反讽、戏谑性的模仿和改编来创作、生产新的文本。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和通俗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兴起,戏仿逐渐成为大众文本生产的一种重要手段和策略。这一点在广告文本的生产或创作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一、戏仿在当代广告创作中的普遍运用
戏仿作为当代广告文本生产和内容创意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各种类型的广告文本中都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运用。
首先,通过对传统语言的戏仿和改造来进行广告文案(广告语)的创作。这类戏仿一般包括几个层次,一是对经典的词汇、成语、俗语或流行语的戏仿,如某服装店的店名“依衣布舍”对成语“依依不舍”的戏仿,水果店的店名“鸭梨山大”对网络流行语“压力山大”的戏仿,胆结石药物的广告语“大石化小,小石化了”对俗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戏仿,某抽油烟机的广告语“专食人间烟火”对俗语“不食人间烟火”的戏仿等等;二是对经典名言名句的戏仿,如某冰箱的广告语“众里寻他千百度,想要几度就几度”对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名句的戏仿,某望远镜的广告语“欲穷千里目,不必上高楼”对王之涣《登鹳雀楼》中诗句的戏仿,《大公报》美洲版的广告语“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阅报纸倍思亲”对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诗句的戏仿等等;三是对经典名篇的戏仿,如“娃哈哈”非常茶饮料的广告文案,“曾经有一瓶娃哈哈非常茶饮料放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我会对它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加一个数量,我希望是一万瓶……”,是对刘镇伟导演的电影《大话西游》中至尊宝经典台词的整篇戏仿。
其次,通过对经典名画、流行图像、名人影像等视觉素材的戏仿和改造来进行平面广告的创作。这类戏仿也同样包括几个层次。第一,对经典名画的戏仿。如2017年美国庄臣旗下的KIWI®鞋油广告《完整的肖像画》,打着“伟人都是脚踏实地开始的,下半身也同样重要”的旗号,为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梵高的《自画像》、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等十幅经典半身像画作增加了它们丢失的“下半身”——其中增加的部分与原作完美融为一体,并让由KIWI®鞋油呵护的锃亮的鞋子成为画作中的主角,构成了对这些名画的戏仿和改造。经典名画一直是广告戏仿的“重灾区”,有些世界名画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梵高的《自画像》、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路易·大卫的《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等作品因被太多的广告作品所戏仿和挪用,因而被网民称为“广告玩滥的世界名画”。[1]第二,对大众文化领域流行图像的戏仿和挪用。如某航空公司的优惠机票广告,就挪用了NBA篮球比赛开场时球员跳起争球一刹那的经典画面,只是将高空中的篮球置换为一张打折机票,加上“千年良机,岂容错过”的广告词,营造了一种众人争抢、一票难求的售卖热潮。第三,对名人影像的戏仿。作为一种为大众所熟悉的公共文化资源,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名人、明星影像(包括照片、肖像画、雕塑等影像形式)也常常成为广告戏仿的对象。如一则德国奥林匹克体育同盟的倡导运动减肥的公益广告,就设计了一个胖得只能瘫坐在椅子中难以站起的黑格尔的增肥版雕像,雕像底座上铭刻着“你不运动,就会变胖!”通过对名人雕像的戏仿实现了广告诉求。
再次,通过对电影电视经典情节、桥段或类型电影的核心元素进行戏仿来进行影视广告的创作。如丽珠得乐2003年制作的一则胃药广告就戏仿了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中的影像元素,包括在情节、氛围、音乐、演员、道具、服装(如女主角的旗袍)等方面都对电影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模仿,然而,当女主角感慨“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时,男主角回答:“其实受伤的不一定都是女人。我的胃就经常痛!”台词的画风突转陡然打破了经典电影制造的视听幻象,将原作中的“为情所伤”巧妙转变成广告中的被胃痛所伤,然后广告结尾点明产品的诉求“保护容易受伤的胃”。通过对经典电影情节的戏仿,该广告让平淡无奇的胃药参与到电影细腻感人的情感冲突中,借用观众熟悉的故事和场景,实现了广告的特定诉求点。另一则2015年的康师傅炒面套餐广告“吃炒面喝靓汤”则更是一次戏仿的大串联,广告以男主角“吃炒面”和女主角“喝靓汤”在经历了七生七世的患难最终走到一起的爱情故事为叙事主线,分别戏仿了董永与七仙女、大话西游、新白娘子传奇、神雕侠侣、还珠格格、泰坦尼克号、上海滩、韩国偶像剧等经典爱情电影和电视剧中的生离死别桥段,最后通过康师傅“炒面+靓汤”的二合一套餐让经历了七世惨痛分离的男女主角最终得以“有情人终成眷属”。通过不断唤醒观众熟悉的影像记忆,该广告在戏谑、搞笑而又富含文化内涵的情节叙事中巧妙突出了产品的卖点。
二、广告戏仿的常用手法
戏仿作为一种广告创作的整体策略,往往需要采用具体的手法在模仿、挪用原作(源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创新,这些具体手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一)夸张性模仿
夸张性模仿是戏仿的一种典型手法,学者华莱士·马丁(Wallace artin)曾经指出:“滑稽模仿(parody,即戏仿,笔者注)本质上是一种文体现象——对一位作者或体裁的种种形式特点的夸张性模仿……滑稽模仿夸大种种特征以使之显而易见。”[2](P183)批评家西蒙·丹提斯(Simon Dentith)也明确宣称:“戏仿运作的典型方式之一,就是抓住一种风格或文体的某一特征并对它进行夸张以达到滑稽可笑的效果。”[3](P32)同样,当广告作品采用戏仿作为其基本创作手段的时候,也常常会通过有意识地对源文本某一形式特征的强调、凸显、夸大来获得一个变形、乖谬或怪诞的形象,以此来服务于强化商品(或服务)的特定诉求点的目的。这种夸张性模仿与作为广告创意中常用的表现手法“夸张”有所不同,后者直接强化、夸大商品(或服务)的主要功能或优点,以突出其特殊诉求点,从而增强广告效果和传播效应,而前者总是通过对先已存在的文本(源文本)的夸张性模仿来间接地达到突出商品(或服务)特定诉求点的目的。夸张性模仿类似于哈哈镜的功能,可以造成源文本形式特征的变形而达到一种漫画化和怪诞化的视觉效果,因而在平面广告的戏仿作品中最为普遍,如在前面我们所举的德国体育同盟倡导运动减肥的系列公益广告中,设计者对大卫雕像进行大幅增肥——在他的肚子上加上了几个“游泳圈”,使其原本比例完美的男性体型变得十分肥胖而“油腻”,通过将臃肿、变形的体型与源文本(标准大卫雕像的完美身材)进行对比,从而突出其广告诉求点——“你不运动,就会变胖!”另一则泰国的银行广告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它将人民币、美元和英镑上的毛泽东、林肯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头像进行夸张性的增肥,创造出三个既陌生、怪诞而又略显滑稽的增肥版领袖头像,通过这种巧妙夸张的处理来告诉我们:通过该银行的兑换系统,可以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手里的货币在泰国变得更值钱、更具有购买力,从而以充满智慧而幽默的方式表达了银行服务的诉求点。
(二)模仿+倒置
戏仿本身就是对源文本的一种模仿,只不过这种模仿与普通的文本模仿(拟作、仿作)不同。普通的模仿追求对源文本整体风格、特色和细节的逼真再现,以逼似源文本为最高目的;而戏仿则是一种有意识的歪模斜仿,并不追求对源文本的原样重现,而是往往要植入戏仿者的反讽、戏谑或嘲弄的意图。在戏仿中,这些主体意图往往需要通过“倒置”(inversion,又译作颠倒、倒转)的手法才能实现。倒置是戏仿的典型手法之一,这一点为学界所公认。如著名后现代批评家哈琴(Linda Hutcheon)就把倒置看作戏仿的本质特征,认为戏仿就是“以反讽性的倒置为典型特征的模仿”。[4](P6)批评家巴赫金也指出,戏仿通常意味着一个颠倒的、“翻了个的世界”,[5](P167)是一种“内外翻面上下颠倒的配置逻辑”,它改变物体的空间位置,把下部放到上部,把后部放到前部,如男性穿女性的衣服、用上衣代替裤子穿、面朝尾巴骑马、头朝下倒立着走路等等。[6](P477-478)倒置遵循的是一种否定、颠倒和反转的逻辑,将源文本的正向的、肯定式的叙事逻辑改造为反向的、否定式的。运用“模仿+倒置”手法的戏仿广告案例非常多,在语言类、平面类和影视广告中都屡见不鲜。如某抽油烟机广告语“专食人间烟火”就是在模仿俗语“不食人间烟火”基础上的倒置,某望远镜广告语“欲穷千里目,不必上高楼”是在模仿王之涣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基础上的倒置,某冬令补品广告词“一年之际在于冬”是在模仿谚语“一年之际在于春”基础上的倒置,而六神花露水的广告词“六神有主,家人无忧”则是对成语“六神无主”的倒置,等等。另一则平面类的以保护鲨鱼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则戏仿了美国经典电影《大白鲨》的海报。它通过将原电影海报中“鲨鱼吃人”的主题倒置、颠倒为公益广告中“人吃鲨鱼”的主题,对当代人与鲨鱼(动物)的强弱关系进行了崭新的阐释。人与鲨鱼强弱关系的变化通过图像语言的设计得到了充分表达:电影海报中巨大的鲨鱼占据海报的主体和醒目位置,它正张开血盆大口,随时要吞噬位于海报画面上方仓皇逃命的渺小的人——“鲨鱼吃人”、鲨强人弱的主题昭然若揭;而公益广告的图像语言恰好是对前者的颠倒,它虽然模仿了电影海报的形式模板,但是却将一个露出獠牙的巨大人头图像置于海报的中心和醒目位置,而一只浑身血迹、奄奄一息的小鲨鱼(位于画面上方的不起眼位置)则成了被追杀的对象——鲨弱人强、保护鲨鱼(动物)的主题也是显而易见。这种“模仿+倒置”的手法在影视类戏仿广告中,则往往表现为叙事中的情节反转。如湖南新闻频道2006年播出一则啤酒的广告,叙事的开头营造了史书中“屈原投江”的情境——屈原念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准备要“投江”,然而正在此时,叙事发生了反转:从屈原身后走来一位时髦、潇洒的现代年轻人,他奉劝屈原说:“人都死了,你还能求索啥?”结果屈原笑逐颜开,拿起此品牌啤酒与年轻人开怀畅饮起来。通过叙述情节的反向突转,这则广告把历史悲剧变成了现代日常生活中的喜剧,同时将商品信息有机融入了故事情节,达到了突出广告诉求点的目的。(2)尽管该广告颇有亵渎历史名人的违规之嫌,但这里我们只从广告创意的角度来考查其叙事技巧。另一则泰国Katalyst银行制作的创业宣传广告片“如果马云选错合伙人”,也运用了“模仿+倒置”的叙事模式对马云的创业史进行了戏仿和改写。这则广告虚构的故事开始于1999年,35岁的马云当时正在谋划创立一个会永远改变零售业的平台,当他踌躇满志地向身边的街坊朋友们征询建议、寻求支持的时候,朋友们却都建议他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去办英语补习班创业赚钱,马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办了一个“阿利”英语补习班,在课堂上大讲特讲“future”(未来),可是不久补习班就人去楼空,马云的创业也完全失败,阿里巴巴和淘宝的创业神话也不复存在。这时,屏幕上打出广告语“糟糕的合伙人会毁了你的生意”,点明了广告宣传的主题。通过对马云的创业史进行颠倒、反转的叙述,这则广告让现实中功成名就的马云在虚构的故事中经历了另一种“失败的”人生,来强调创业者选择正确合伙人的极端重要性。
(三)挪用+置换
对源文本的整体风格或核心元素的挪用,也是戏仿运作的重要手法之一。法国批评家萨莫瓦约(Tiphaine Samoyault)认为,戏仿在对源文本进行转换时,或者采用漫画化的方式来再现源文本(即对源文本的夸张性模仿,笔者注),或者挪用源文本。[7](P41)一般而言,广告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其创作、创意总是会涉及到对传统文化元素或材料的挪用、吸收、借鉴和转化,但是戏仿广告的挪用与一般广告创作中的文化挪用和借鉴不同,它不是对源文本中片段、局部的元素的挪用、吸收和拼贴,而是对源文本进行全局的、整体性的挪用、再现和改造,是通过对源文本进行整体的转换来再造一个新文本。同时,戏仿广告的挪用总是跨文本、跨语境的(常常可以任意跨越古今、雅俗的文本界限),它通常把源文本整体风格或核心元素从其自身语境中抽离出来,并将它们置入另一个全新的文本语境之中,利用这个截然不同的语境造成源文本的“语义转换”,服务于当前的广告创意和特定诉求的表达。当然,戏仿类广告并不会原封不动、一丝不差地整体照搬源文本的风格或核心元素,而总是会在整体挪用中进行一定的细节改造,通过植入某些关键元素(与广告的商品或服务密切相关)来置换掉源文本中的某些元素,同时植入和增加的新元素往往能够与源文本的整体语境和背景能够和谐地融为一体,共同服务于广告诉求和传播效应的达成。“挪用+置换”手法的效果由于在视觉图像领域最为明显,因此在平面类、影视类的戏仿广告中运用得最为普遍。如上文所提到的2017年美国庄臣的KIWI®鞋油广告《完整的肖像画》中对经典名画半身肖像的挪用和“下半身”的增加,某航空公司的机票广告中对NBA篮球赛开场争球画面的挪用以及用机票置换掉篮球等等案例,都是这种手法的巧妙运用。另一则潘婷洗发水的戏仿广告,在整体挪用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基础上给蒙娜丽莎换上了一头大波浪式的卷发,使原作中忧郁和深邃的蒙娜丽莎变得时尚、青春而靓丽,原作中神秘的微笑也变成了对新发型的满意的微笑。其他的如爱普生打印机、花斑奶牛软件、高露洁牙膏、奥迪A7汽车、乐高等平面广告,都纷纷采用挪用这种戏仿手法对《蒙娜丽莎》画作进行改造,以至于由于挪用过多过滥而使蒙娜丽莎成为了“这个艺术圈最著名的女人”。[8]同样,另一则1994年由香港艺人陈浩民主演的维他奶影视广告也是运用“挪用+置换”手法的戏仿广告佳例。陈浩民主演的角色是一个来自城市的中学生,暑假期间来到乡下爷爷家里生活,由于爷爷不善言辞、不苟言笑,爷孙之间的代沟很深,相互之间缺乏交流和理解,孙子对爷爷一直持敬而远之的态度。然而,孙子一次在野外玩耍时摔伤了腿,爷爷给予了孙子悉心的照顾。在此过程中,爷孙之间加强了沟通和相互理解,使得亲情开始逐渐复苏。广告叙事的高潮是爷爷送孙子坐火车回城这一段情节,孙子看着爷爷老迈的背影迈着蹒跚的步子艰难穿过轨道,翻过月台,从对面小卖部买来自己最爱喝的维他奶时,禁不住泪如雨下。至此,爷爷对孙子无声的爱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爷孙亲情得到了升华。显然,这则广告的主体情节上整体挪用了朱自清散文《背影》中的父子相处(从隔阂到理解)情节,然后通过在人物设置(父子关系变成爷孙关系)、场景(回家奔丧的父子相处变成暑假乡村生活中的爷孙相处)、道具(红橘子变成了维他奶)、音乐(整个广告叙事的背景歌曲是林子祥演唱的《谁能明白我》)等细节上的置换和植入,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而维他奶作为爷孙之间亲情和爱的承载物,巧妙而毫无痕迹地融入在整个故事情节中,服务于整个广告故事情感氛围的营造和浓浓亲情的表达,成为整个广告创意的点睛之笔。
三、广告创作中戏仿策略的运用所造成的影响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重要的大众文化生产策略和手段,戏仿在当代广告创作中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运用,这对于丰富广告的创作手段和提升广告的创意水平具有毋庸置疑的积极意义。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如果对戏仿不加限制、不分对象、不顾场合地过度滥用,则会带来各种负面效应,需要我们全面、辩证地看待广告中的戏仿现象。
首先,从审美和传播效应角度来考察,戏仿在广告中的应用带来了陌生化和喜剧性这两种审美效应,从而大幅提升了广告的传播效应和宣传效果。如前所述,戏仿总是一种在源文本基础上所进行的改编和再创造,无论是采用夸张性模仿、模仿+倒置还是挪用+置换的手法,都创造出一个变形、颠倒、怪诞、似曾相识而又与源文本截然不同的新形象、新故事、新文本。与大众熟悉的源文本相比,经过变形和改造的戏仿作品总是以一种背离常态的、变异的、陌生化的面目出现,以一种显性文本的方式直接呈现在受众面前,给他们带来强烈的陌生感、新鲜感和新奇感。同样,戏仿也是制造幽默、引起笑声的有效手段。《牛津英语大词典》就指出:“戏仿是对一部作品或多或少接近于原作的模仿,但是又作出改变以产生一种可笑的效果。”[9](P489)无论是夸张性模仿带来的漫画化和哈哈镜的变形效果,还是“模仿+倒置”、“挪用+置换”手法的运用所带来的对受众正常接受习惯和心理期待的颠覆,都足以引发笑声、制造喜剧化审美效果的常见机制。戏仿给广告作品带来的陌生化特征和喜剧性风格,对于提升广告的传播效应是十分有利的。根据美国著名广告学家刘易斯(E.S.Lewis)提出的经典营销理论AIDMA原则,戏仿类广告的陌生化形式不仅有利于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还能通过这种新颖、奇异的形式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困难来激发受众的兴趣;同时,理解困难导致的受众注意力在广告信息上的长时间驻留又有利于受众对其形成深刻记忆,从而带来十分显著的广告效果。同样,戏仿广告的喜剧性或幽默的特质也有利于引起受众的兴趣,让受众在轻松、愉快的心境下形成对广告信息的深刻印象,从而带来良好的广告效果。
其次,从广告接受角度来考察,戏仿类广告对受众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戏仿总是在依托源文本基础上的一种再创造,因而受众必须对源文本有所了解,才能在对二者进行对比、比较的基础上准确理解和把握戏仿者的创作意图。同样,受众对戏仿类广告作品的源文本有所了解甚至十分熟悉,当然也有利于他们对此类广告创意的理解和广告信息的把握。反之,就会对广告创意和广告诉求的准确理解造成障碍。比如上文所举的维他奶广告的例子,如果观众没有读过朱自清的《背影》,尽管他们也能大致理解这则广告的基本情节和所表达的情感,但却无法唤起与《背影》相似的情感共鸣,不能在古今共通的普遍性人类情感的深度上去准确理解这则广告所蕴含的亲情表达和文化内涵,从而让这则广告的审美效应和传播效果因此而大打折扣。同样,对西方经典名画一无所知的受众,当然也无法准确地理解类似于KIWI®的《完整的肖像画》这种广告。正是由于戏仿类广告对受众的高要求,使得很多网友感慨道:“不认识几幅名画,连广告都看不懂了。”[10]而广告作为一种大众化、通俗化艺术,必须保证内容和创意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其所运用的符号、所传达的信息、所构思的创意必须以最大数量的受众能够理解为前提。因此,戏仿类广告在源文本的选择上应当更多地考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传播范围较广的经典作品或流行文本,以保证广告内容的通俗易懂和广告传播的受众面,实现广告效应的最大化。
再次,从文化传承和发展角度考察,戏仿在当代广告中的大量运用对传统文化造成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戏仿类广告的基本创作模式就是在模仿、挪用经典文本(传统文化的具体承载形式)基础上进行改造、改编来完成自己的广告创意,这种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现代化改造和转化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对于推动、促进传统文化在当代大众社会和商业文化中的传播和传承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如批评家哈琴所言,“你在戏仿某事时,虽然嘲弄了它,但也使其得以流传”,[11](序2)从而以一种看似矛盾的方式扩大了传统文化的受众范围。同时,戏仿在广告中的运用还让各种“高雅”艺术和经典文化成为广告这种通俗文化的重要创作素材,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固有界限,跨越了艺术与普通生活之间的障碍,对于推动艺术和文化从精英、小众走向民主化和大众化,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戏仿在当前广告创作中的普遍运用,使得某些经典文本和传统文化素材、符号一次次被重复模仿、复制、挪用而导致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毫无底线、毫无节制的过度滥用(如前文所述的《蒙娜丽莎》的例子)。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滥用不仅使戏仿这一广告创新手段沦为盲目的跟风模仿,还会造成经典的意义和价值丧失殆尽,导致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虚无化和空心化。正如著名媒介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所言,那些被多次反复使用的词会因此而“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当图像处处可见时,……图像的重要意义随之减少”,因为“重复耗尽了它的象征价值”,而且“符号失去意义的过程是一个因变量,如果用得越频繁,如果不问语境滥用,它们失去意义的速度就越快”。[12](P99-100)同时,戏仿的过度使用还让合理的文化借鉴变成了非理性的文化滥用,造成对经典的意义和内涵的扭曲、对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的破坏以及对传统审美规范和伦理价值的解构和颠覆,导致经典和传统文化走向媚俗化、娱乐化和肤浅化,严重妨害了青年一代对经典和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接受,因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消极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四、结 语
戏仿作为一种当代大众文化生产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它的普遍运用为广告文本的生产和创作带来了无数的灵感、丰富的素材、崭新的创意和突出的审美效应,为广告信息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良好的内容基础。同时,戏仿在广告创作中的普遍运用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挑战,从而为当前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戏仿的双重(积极和消极)功能,我们既不能完全从商业思维和功利角度出发,对其放任自流,任其泛滥过度而不加以任何管理和规制;同时也不能因噎废食,因担心戏仿的文化解构力和颠覆性而将其完全否定。当前需要我们做的,应当是激发出戏仿的正能量和积极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古为今用的文化转化力量和推陈翻新的文化创新功能,同时不断完善相关的文化法规和广告法规,将戏仿的使用限定在“合理使用(fair se)”的限度之内,避免对经典和传统文化元素的过度滥用,以降低其负面的文化影响。总之,在文化的大花园中,戏仿既非杂草,也非鲜花,而是一种介于杂草与鲜花之间的“蒲公英”,在当下适宜它的文化环境中茁壮成长,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杂草是否是杂草……而在于是否可以在控制杂草的同时又不抑制随之而产生的美丽和有价值的东西”。[13]147这或许才是我们对待广告戏仿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