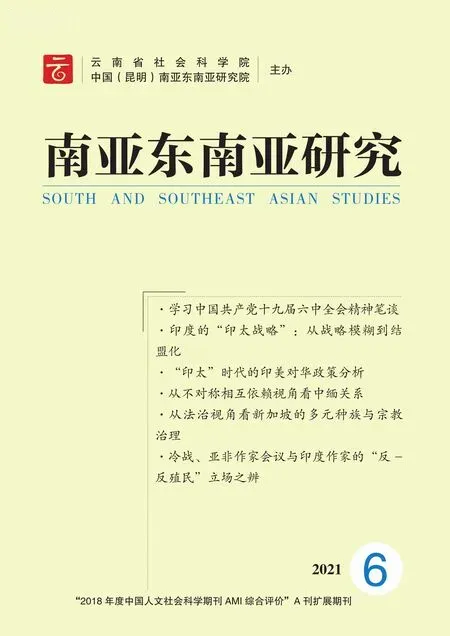从法治视角看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与宗教治理
2021-12-31马腾飞
马 平 马腾飞
1819年2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佛士爵士(Sr.Thomas S.Raffles)来到新加坡岛,通过谈判设立了自由贸易埠。自此,新加坡开始了自己的政治历史。一百多年后,新加坡逐渐发展成为繁华的殖民地转口港。1959年新加坡成为独立自治邦,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独立。在李光耀等人的领导下,新加坡逐步发展成为经贸繁荣、廉洁高效和具有良好社会秩序的现代化国家。作为典型的种族与宗教多元国家,新加坡能够实现种族与宗教的和谐共存,建国以来几乎没有因为多元文化的冲突而导致政治与社会不稳定,这是新加坡国家治理的重要成就之一。截止到2020年,新加坡人口总数569万,其中新加坡公民约352万、永久居民约50万,公民和永久居民人口中华人占74.3%、马来人占13.5%、印度族裔占9.0%,其他族裔占3.3%;15岁以上人口中,31.1%信仰佛教、8.8%信仰道教、18.9%信仰基督教、15.6%信仰伊斯兰教、5.0%信仰印度教,约20%无宗教信仰。①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Census of Population 2020 Statistical Release 1 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Education,Language and Religion,https://www.sgpc.gov.sg/media_releases/singstat/press_release/P-20210616-1.在新加坡,种族多元与宗教多元交织在一起,华族主要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基督新教)等,马来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族主要信仰印度教、伊斯兰教等,还有少数人口信仰锡克教、耆那教以及混合型宗教等。
新加坡是如何调整和处理多元种族-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这样的族群基础上维系国家认同的?目前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法治建设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借用“雅努斯”之面来指称新加坡种族与宗教治理的法治路径,以说明新加坡法治的二元性特征。雅努斯(Janus)是古希腊的两面神,一头两面,一面朝向过去、一面朝向未来。②见《韦氏辞典》“January”词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01页。新加坡法治的这种二元性至少在三个维度上有所表现:第一,新加坡被称为威权法治国家,③参见约西·拉贾著,陈林林译:《威权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话语与正当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所谓威权,一般意义上指当权者政治上集权而不遵循对政府的约束,也不认为个人权利是不容侵犯的。约西·拉贾强调,威权主义和法治并非是不兼容的。“威权”与“法治”曾被认为是分属前现代与现代的两种治国路径,新加坡实现了两者的自洽融合;④梁治平认为“威权法治”代表了法治的一种分裂特征。参见梁治平:《“法治”与“治法”之间》,《读书》,2021年第4期,第55页。第二,新加坡是名副其实的多元种族-宗教国家,一方面尊重和承认各个种族宗教之传统和现状,一方面又通过立法严厉打击煽动仇恨、破坏种族宗教和谐的行为,将所谓保守主义和促进平等与反歧视的进步主义相结合。第三,成功地整合了重视家庭与公共社群纽带之亚洲价值观与盎格鲁民主圈之殖民遗产,在从殖民地解放到独立建国进程中,没有完全抛弃历史遗产,反而吸收了其中的理性法治精神。①1950、60年代前后第三世界国家兴起了民族解放事业,很多国家在民族解放后十余年又遇到了“宗教反革命”式的宗教回归甚至宗教狂热,参见迈克尔·沃尔泽著,赵宇哲译:《解放的悖论:世俗革命与宗教反革命》,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页。新加坡国家建设中没有强化民族主义,而是强调对英式民主法治的继承以及对多元种族与宗教现状的尊重与耐心,警惕和遏制极左派与宗教政治化,没有出现大的国家动荡和宗教狂热,实现了长期平稳的发展。新加坡的上述法治路径,集中体现了该国的共同价值观和国家意识形态,它包括五项内容:(1)国家先于社群,社会高于自我;(2)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3)社群支持和尊重个人;(4)寻求共识,而非冲突;(5)种族和宗教和谐。这五项价值观由1991年1月16日新加坡国会发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所确定。②1988年10月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首次倡建国家意识形态,以促进新加坡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并塑造统一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1989年新加坡总统黄金辉在国会开幕演讲中强调了建设国家认同的重要性,提出“将社会置于自我之上、坚持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通过共识而不是争论解决重大问题、强调种族和宗教宽容与和谐”四个价值;其后政府推动了有关国家意识形态的辩论以及新加坡不同种族和社群共同身份与关键价值观的讨论,提交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草案,最终经国会辩论修订确定了五项共同价值观,正式予以公布。See National Library Board,“Shared values are Adopted”,15th January 1991,SG Resources,https://eresources.nlb.gov.sg/history/events/62f98f76-d54d-415d-93a1-4561c776ab97.
一、新加坡式法治:经贸与政治领域的不同治理方式
基辛格曾评价李光耀说:“他的智慧和判断力无人能及。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卓越的智慧、纪律性和创新性弥补了资源稀缺造成的劣势。”③亨利·基辛格的这段话出自他为格雷厄姆·艾利森、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主编,蒋宗强译的《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所作的推荐序。李光耀长期担任新加坡总理,其治国理念的核心是“现实主义”,以解决新加坡现实问题为导向,自认并非哪一种政治哲学的信徒,而是随着现实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自由主义者”。④格雷厄姆·艾利森等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这种灵活务实在新加坡法治中体现得极为明显。
关于法律的地位问题,新加坡采取了如下策略:第一,“法律”在新加坡国家观念中占有核心地位,律师出身的李光耀“恐怕是近代国家中第一个善用法律治理国家且妥善达到此任务的政治人物”;⑤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第二,“英国法”“普通法”和“法治”被宣称为新加坡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三,涉及外国投资、贸易和经济采用了西方式自由民主法律,但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法律采取了家长主义式的管制。⑥约西·拉贾著,陈林林译:《威权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话语与正当性》,第40页。李光耀认为“法治占据根本性的地位,因为法治能够确保国家的稳定性及可预测性”;①格雷厄姆·艾利森等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第96页。更重要的是,新加坡要通过法律来实现国家同质化,包括塑造公民在法律上的同质性,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的同质化。在多种族、多宗教的基本民情上,新加坡适用普通法同时有限地承认一些习惯法,如回教社群有关婚姻、家庭设有回教法庭裁决,②新加坡《施行回教法法令》(Administration of Muslim Law Act,AMLA)于1966年颁布,2009年修订,是关于回教事务立法、设立回教理事会(Majlis)与回教法庭(Syariah Court)的国家法律。根据该法,回教法庭管辖遵从回教法缔结婚姻的回教徒或一般当事人的婚姻、家庭案件,包括结婚、离婚、订婚、婚约取消、法定分居、婚后财产分割、婚姻聘金及礼品处理等。但法院又通过判例确定涉及公共事务时国家法具有最终的裁决地位。政府通过设定条件来落实法律的不明确之处,牢牢地掌握了立法和法律的解释权力。
在法律是否可以强制推行道德、推行何种道德的问题上,新加坡也有自己的选择。英国保守派学者丹尼尔·汉南认为,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地方,即英格兰及其前殖民地,共同组成了盎格鲁圈,这些国家建立在超越种族的核心观念之上:普通法、契约神圣、代议制政府、良心自由、财产安全以及个人自由。③丹尼尔·汉南著,徐爽译:《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所谓盎格鲁圈,核心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大部分人还认同爱尔兰,以及新加坡、百慕大群岛、法兰克群岛,加勒比海岸民主国家、南非,部分人认为印度也应包括在内。在李光耀看来,上述英国式民主制乃是新加坡的政治源头。新加坡从独立时就承袭了殖民地时期的一些法律,并且一直坚持声明它厉行的“法治”也属于这个盎格鲁圈。在精英治国、效率优先的框架下,合同法领域内的法治特征非常明显,借此新加坡能够吸引到各种跨国企业和人才,维系其国际金融、货运中心之地位。然而,在汉南看来,“自由”才是西方式盎格鲁圈的首要价值,而且这个自由是属于传统式自由,优先于人人平等诉求下的“民主”。④当代西方部分进步主义学者较之似乎更强调“民主”的价值,该类观点可参见叶礼庭著,成起宏译:《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做法与之存在表面上的冲突,比如限制个人自由部分,但仿佛又与之部分暗合:并非所有的人或文化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相较于汉南推崇的盎格鲁式传统自由,新加坡以亚洲价值观、家庭传统与道德来整合国家,社会利益比个人利益更为优先。在这个意义上,新加坡“似乎在这一点上同意黑格尔,即康德式的自由主义的独处的、个体主义的,或者说是‘无拘无束的自我’,对于产生出一个道德上以及政治上令人满意的共同体形式,都是一个过于薄弱的基础”。⑤史蒂芬·B.史密斯著,杨陈译:《黑格尔的自由主义批判:语境中的权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对西方式传统自由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将不同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同理心”限定在国家主导的道德解释框架下,是新加坡维系国家认同的主要路径。
综上所述,新加坡式的法治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策略,在两个领域施行两种治理模式:一部分法律承袭了西方式自由法治传统,以技术理性规则推行治理,与英语世界在贸易、金融等领域无缝接轨;另一部分法律则发展出了自己的特征,通过政府确认的“善”(家庭、社群)替代了所谓多数者之治(一人一票的绝对平等),规制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中国近代哲学家贺麟(1902~1999年)曾将法治分为申韩式法治(功利主义法治)、诸葛式法治(道德法治)和近代式法治(基于学术的法治)三种。新加坡法治模式近似于后两者的混合。“诸葛式法治”,即基于道德的法治:“父教子以严,上治下以严,严即表示执法令者对于遵法令者有一种亲属的关切,故欲施以严格的教育与训练”,这在现代被视为威权式的前现代路径。“近代式法治”,即“人民自己立法,自己遵守”,通过法律对政府施以约束,通过代议制辩论制定保障权利的法律。①贺麟:《法治的类型》,载《文化与人生》(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在新加坡,“威权”与“法治”并行,在国家牢牢掌握立法和法律解释权力的前提之下,合同法领域的英式法治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领域内的“父爱主义”法律②法律父爱主义,一般指法律基于对当事人有利的原因而对其自由意志或行为进行干预、限制或强制,对此概念之脉络梳理可参见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及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结合在一起,以“稳定”为第一要务,走出了独具特色的新加坡法治之路。
二、种族与宗教的相关法律结构
这种混杂特征在新加坡有关种族与宗教的法律制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李光耀说:“我对新加坡人的定义就是无论是谁,只要加入了我们,就是我们中的一员……改革不能操之过急……没有人愿意丧失自己的种族、文化、宗教甚至语言属性。”③格雷厄姆·艾利森等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第95页。既要尊重种族与宗教的多元传统及现实,又要将它们牢牢地统合于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和法律规制之下。新加坡自建国伊始即采取了“族群平等、不设国教、政教分离的多元族群、多元宗教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④范磊:《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实现多元族群社会的“善治”》,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建立了完整严格的维护族群和宗教和谐的法律制度。
(一)新加坡政教分离的宪法框架
新加坡共和国宪法中对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有明确的体系性规定。①本文所引新加坡共和国宪法条文,系依据官方“新加坡法律在线”版本翻译而成,访问时间2021年7月31日。下文引用的《煽动法令》《内部安全法》《公共秩序法》等也是如此。
第一,平等保护条款(第12条):(1)除了本宪法规定之例外,任何法律,包括担任公职、财产权利、贸易、商业、职业、职位或雇佣均不得基于宗教、种族、族裔或出生地歧视新加坡公民。(2)上述条款并不禁止与宗教事务有关的公职、雇佣或由宗教团体管理的机构设立特别宗教要求。
第二,宗教自由条款(第15条):(1)每个人都有权信奉和实践他的宗教,并传播他的宗教。(2)任何人不得被强迫缴纳其全部或部分收入专门用于他本人所信奉之外的宗教目的的任何税款。(3)每个宗教团体都有权利:(a)管理自己的宗教事务;(b)建立和维持宗教或慈善机构;(c)取得和拥有财产,并依法持有和管理。(4)本条规定不得被用于任何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的一般法律之行为。
第三,总统资格条款部分。新加坡总统是虚位元首,原由议会任命,在1991年修宪后改为公民选举总统,现行宪法规定总统可以否决政府预算和重要的公职任命,除了传统的仪式与社群功能外,还明确增加了角色的国家守护功能。总统参选时不得属于任何政党。为了保证各族群人士都有机会担任国家元首,宪法第19B条中特别规定了“保留机制”,为连续五届或五届以上未担任总统的族群举行保留选举,如果构成新加坡四大族群的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少数族群中(宪法第19B(6)条对族群作出了解释,某人是否属于某族群需要自己和族群的双重认可),有任何一个族群历经五个总统任期都没有代表担任总统,下一届总统选举将优先保留给该族候选人。新加坡现任总统哈莉玛·雅各布就是在宪法保留条款下于2017年顺利成为该国首位女性总统和担任最高政治职务的马来族女性。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从形式上保证族群以及与族群密切关联的宗教平等,杜绝某一特定族群长期占据国家元首位置,形成对其他族群的压制。
第四,有关种族和宗教的条款还包括:宪法第Ⅶ部分第77条设置了“少数人权利总统理事会”,该理事会的主要职能就是在国会法令或政府附属法规送交总统签署发布之前,对任何理事会认为构成或可能构成对任何种族或宗教群体直接或间接不利的差别对待进行审查,确保此类不公正被消除。第ⅩⅢ部分“一般条款”中,关于少数族群与马来人特别地位的第152条:(1)政府有责任始终关心新加坡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利益。(2)政府应以承认马来人为新加坡圭著居民这一特殊地位的方式行使其职能,有责任保护、保障、支持、培养和促进马来人之政治、教育、宗教、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以及马来语。关于穆斯林宗教事务的第153条:“立法机关应通过法律规定管理穆斯林宗教事务,并成立一个理事会,就与穆斯林宗教有关的事项向总统提供咨询意见。”
(二)维护宗教与种族和谐的法治路径
建国以来,在对新加坡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上,新加坡政府一直保持了李光耀式的立场:新加坡是一个脆弱的小国,宗教和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①约西·拉贾著,陈林林译:《威权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话语与正当性》,第202页。现任总理李显龙强调:“新加坡必须珍视它所享有的种族和宗教和谐……我们为来到这里付出了长期和艰苦的努力,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为子孙后代维护这种和平。”②此为2019年7月21日新加坡种族和谐日当天,李显龙在其Facebook页面所发推文内容。在新加坡宗教和种族有关问题的立法、白皮书、国家安全策略中,处处展现出世俗的、理性的政府强力主导维护稳定之特征。
1.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的一般性立法
(1)新加坡承继殖民当局1948年颁布的《禁止煽动条例》,于1964年修订出台《煽动法令》,该法历经多次修改适用至今,是用以维护国家秩序、族群和宗教安定最重要的法令,打击任何旨在煽动不同族群和阶层之间恶意与敌意的行为和言论,包括印刷、出版、销售、分发、复制及进口具有煽动倾向的刊物。
(2)始于1960年并于1987年修订的《内部安全法令》,主要规制针对个人及财产的有组织暴力活动及相关事项,允许政府以禁止令、预防性羁押等方式阻止可能危害新加坡内部安全的非法准军事或政治团体的形成和发展,在紧急情况下允许政府迅速宣布某个地区受到安全威胁,并通过确保公共安全的措施对其进行控制。
(3)1985年颁布的《破坏公物法》打击城市涂鸦,包含有禁止通过涂鸦方式散播非法信息之意;③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87页。1985年公布的《公共秩序维护综合法》,将一切可能造成社会秩序的轻度混乱,包括犬只攻击人、公开辱骂他人等纳入处罚范围,这两部法律是新加坡用以维护市容与社会基层秩序之“法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4)2009年通过的《公共秩序法》,立法目的是规范公共场所集会和游行等,授权警察和官员在特定活动场所维护公共秩序和个人安全所需之权力,补强与维护公共场所公共秩序有关的其他法律。因此,该法意在再次加强公共领域的规制,严格限制公共领域内的竞争性诉求或运动,以维护新加坡经济和社会稳定。
2.直接与宗教或种族有关的立场文件、立法和政策
(1)《宗教和谐白皮书》。新加坡先是于1988年发布该白皮书,为即将进行的宗教和谐立法进行立场和依据说明,阐明了宗教宽容与节制必须同时并行,宗教不得参与政治、多宗教和谐的理由和主要立法内容。
(2)《宗教和谐法令》。该法于1990年11月通过,1992年3月正式生效,立法目的是规制维护宗教和谐、建立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以及相关事宜。该法体现了两大原则:不同宗教的信徒应该对彼此及其信仰保持节制和容忍,不可煽动宗教敌意或仇恨;宗教和政治应该分开。该法的主要内容包括:(a)尊重和保持各宗教的特点,提倡各宗教的平等、互相尊重、和谐共处,使各宗教的传统文化都有自由的成长空间;(b)设立“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职能是“考虑并向内政部长报告由内政部长或议会转给理事会的那些影响到新加坡宗教和谐的事务”;(c)该法最核心的内容,是授权内政部长对在任何宗教团体或机构中处于权威地位的人发出限制令,前提是内政部长确信该人已经或正试图实施以下任何行为:“造成敌意、仇恨,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的恶意或敌意;或以宣传或实践宗教信仰为幌子,推动政治事业,进行颠覆活动,或煽动对总统或政府的不满”;还可对煽动或鼓励任何宗教领袖或任何宗教团体或机构实施上述行为的人,或非宗教领袖但在不同宗教团体之间引起或试图引起敌意、仇恨、恶意或敌意的人,发出限制令。针对宗教领袖的限制令可要求他或她在向任何宗教团体或机构的成员讲话、协助或出版宗教出版物或担任此类出版物的编辑委员会或委员会职务之前,必须获得内政部长的许可。因此,《宗教和谐法令》主要针对宗教人士的言行内容及受众对象两方面进行限制,并要求其进行自我审查和约束。该限制令不能通过法院得以救济,但可提交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以及总统审查;违反限制令属于刑事犯罪,将受到监禁及罚款。虽然该法令颁布之后很少真正发出限制令,多进行零星的警告,但是该法建立起了一种机制,起到了警示、预防的作用,①《宗教和谐法令》颁布后十余年,对破坏宗教和谐的违法行为主要还是依据《煽动法令》或《内部安全法》进行裁判或处理,因此学者约西·拉贾认为,这一法令最核心的目的在于维护政府在公共话语领域的支配地位,而事实证明新加坡民众对于宗教和谐之于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知,与政府的话语保持了一致。参见约西·拉贾著,陈林林译:《威权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话语与正当性》,第230~236页。有效地促进了新加坡的宗教和谐。
随着最近10年来宗教极端主义国际影响的扩大,新加坡领导层认为:“外国势力已透过散播宗教极端主义在世界各地造成分化,它们可能也会以我国的种族和宗教断层线为攻击目标,以分化我国人民。”②陈庆炎:《新加坡不能容忍外国或外国机构尝试操纵人民情感》,《联合早报》,2017年11月29日。2019年10月,《宗教和谐法令》进行了较大幅度修订,以更有效地应对宗教不和谐事件,并加强对威胁宗教和谐的外来影响的防范措施,其主要修订为:(a)设立防范外来影响的措施,如宗教团体的关键行政人员不得是外国人,超过1万美元的外国捐赠必须声明等;(b)推行社群补救措施,如出现了冒犯宗教情感的行为,引导进行社群关系修复与弥补;(c)更新限制令条件,将限制令扩大适用于能够迅速传播的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并且取消了政府提前14天通知的要求,即限制令可以立即签发生效;(d)对与宗教和谐相关的罪行进行整合,凡刑法中鼓动基于宗教或针对宗教团体或其成员的武力或暴力,煽动对宗教团体的敌意、仇恨、恶意或敌意,侮辱宗教或伤害他人的宗教感情的罪行,将依照《宗教和谐法令》进行处罚。
(3)《宗教和谐宣言》。2001年12月新加坡本圭破获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伊斯兰祈祷团所策划的炸弹阴谋,极大地增加了族群—宗教关系的敏感性,国内稳定和宗教和谐受到威胁。作为强化解决族裔—宗教关系恶化问题战略的一部分,新加坡政府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宗教和谐,于2003年6月公布了《宗教和谐宣言》,鼓励新加坡人在每年种族和谐日(7月21日)的一周内朗诵:“我们都是新加坡人,谨此宣誓:宗教和谐是确保我国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社会之和平、进步与繁荣的要素。我们决心通过互相容忍、信任、尊重和了解,强化宗教和谐。我们将始终如一,确认国家的世俗性,提升社会的凝聚力,尊重各人的信仰自由,既增广共同空间也尊重彼此差异,促进宗教间的沟通,从而确保在新加坡宗教不会被滥用来制造冲突与不和。”①新加坡宪法中规定公职人员任职誓词计十种,集中列于宪法附表一。而在国家层面,存在两大誓约共同促进新加坡的国家认同。第一个是1966年通过的《新加坡国家誓约》,内容为:“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关于此誓约可参见官方网页:https://www.nhb.gov.sg/what-we-do/our-work/communityengagement/education/resources/national-symbols/national-pledge。第二个即为本文所引《宗教和谐宣言》。新加坡学者认为,该宣言性质上属于“宪法性软法”,这一类文书虽然不具有正式的法律地位,但它们所包含的一系列规范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法律影响,并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塑造产生影响。新加坡是个拥有宗教性社会的世俗国家,《宗教和谐宣言》对该国人民宗教自由的范围和实践,毫无疑问是具有实际影响的。②Thio,Li-ann,“Constitutional ‘Soft’Law and the Management of Religious Liberty and Order:The 2003 Declaration on Religious Harmony”,Singapor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004,pp.414~443.
(4)新加坡宪法授权法院可以提高对破坏宗教与种族和谐罪行的惩罚力度。将破坏宗教和谐类罪行放入《宗教和谐法令》后,刑法中尚有涉种族关系类违法,包括故意伤害任何人的种族感情,基于种族或其他理由故意促进或企图促进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不和谐或敌意、仇恨或恶意,作出任何明知有损于维持不同种族群体之间和谐、扰乱或可能扰乱公众安宁的行为等,这些罪行将受到较普通犯罪更严格的处罚。
(5)用公共组屋租售“插花式”种族比例促进不同族群的社区融合。新加坡政府于1960年成立了“建屋发展局”,向新加坡居民提供出租的房屋单位。1964年,建屋局进一步推出了“居者有其屋”的计划,政府将开发的住房以99年地契售卖,它们统称为“组屋”。新加坡现在有80%的人口居住在这些具有公共性质的组屋中。居者有其屋是新加坡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各次选举都能获得民众“概括授权”的重要原因。①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33~234页。为了维护文化多元,抑制特定种族偏好居住在特定区域的势头,确保各种族的均衡混合、并防止形成种族飞地,政府于1989年引入了种族融合政策,即根据新加坡的人口构成在街区或住宅区设定人口种族比例限制,它适用于所有新建或转售的组屋以及由建屋局分配的租赁公寓的租赁和买卖。该计划旨在促进新加坡的种族融合,能够让不同种族的居民一起生活和定期互动,孩子们可以一起上学一起成长。②“HDB’s 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Why it still matters”,https://www.gov.sg/article/hdbs-ethnicintegration-policy-why-it-still-matters,Published on 13 Apr 2020.
3.21世纪后推进的反极端与反恐怖主义战略文件。如上所言,21世纪以来新加坡与其他国家一样,开始直面恐怖主义犯罪和极端主义思想的冲击。因此,新加坡于2004年公布了《反恐怖主义:新加坡的国家安全策略》,将维护宗教和谐、去极端化的社会防卫工作作为该战略全面防卫计划中的重要内容。③李捷:《东南亚地区反恐去极端化的理念与举措》,《光明日报》,2019年8月17日,第7版。李光耀曾经对极端主义发表如下观点:只有那些温和的、以现代化的观念对待生活的穆斯林才能同原教旨主义者作斗争,以赢得穆斯林灵魂的控制权。应对恐怖主义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事业,要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同盟,支持和鼓励宽容的、非极端的温和穆斯林站起来反对极端主义者,这样他们才能在同极端分子抗争的过程中逐步占据上风。④格雷厄姆·艾利森等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第90~92页。
综上所述,新加坡通过数十年的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和法治建设,较好地实现了种族和宗教的和谐共生。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件即展示了这样一种全民式的系统努力。2021年5月7日,正值德尔塔病毒在印度暴发之际,55岁的印度族女子在公园进行快走运动时未戴口罩,某华族男子上前以带有种族侮辱字眼辱骂和踢倒该女子,该男子被警方以“公共滋扰”“蓄意伤害种族情绪”以及“蓄意伤人的罪名”逮捕。⑤《涉以种族侮辱字眼攻击印族妇女 男子三罪名下被捕》,《联合早报》,2021年5月12日,https://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story20210512-1146023,访问时间2021-05-18。警方表示,任何人无论是用行为或语言挑起种族间的敌意,警方必定采取严厉行动。就在这起疑似种族主义的袭击案发生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交通部长王乙康和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等均通过脸书谴责类似行为。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新加坡国内发生了若干起类似的种族之间敌意案件,但政府和社会各界保持一致的谴责立场,呼吁加强沟通和相互了解,警方与法院也强调了对此类行为的严惩态度,维护了种族—宗教和谐。正如新加坡国家发展部所属“宜居城市中心”在其研究报告中总结,宗教间的和谐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人口稠密、文化多元的城市国家的宜居性至关重要;在种族和宗教问题日益极化的当今世界,新加坡能够成为不同宗教信仰和宗教习俗和谐共存的典范,这是通过精心地规划、治理和利益相关各方共同努力实现的。①The 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Religious Harmony in Singapore:Spaces,Practices and Communities”,https://www.clc.gov.sg/research-publications/publications/urban-systems-studies/view/religious-harmony-insingapore-spaces-practices-and-communities.新加坡严格的立法和执法,以及据此所形成的法治氛围,对于保障宗教宽容和不歧视,维护该国不同族群间的和谐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新加坡以法治促进多元族群和谐的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法治的二元性特征,就其根本而言是在惯常的西方式法治概念占据主流话语权下的一种区分,后者建立在对法治特征的垄断性解释之上,在这种解释路径之下,虽然新加坡政府坚持自己继承了英式民主法治制度的遗产,但常常被批评为“非法治的”,特别是在司法诉讼制度方面,颇受非议。②包括有损人格尊严的鞭刑、征收高额聆审费用、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审查不力等。然而,有学者同时也指出,法治存在不同模式,英美式“法治”与德式的“法治国”就不尽相同,③苏永钦:《法治、法治国和依法治国》,《中国法研究》,2016年第3期。惯常将法治与自由民主政治一体视之是一种成见,“rule by law”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但对人们的生活有实质性影响,同时也蕴藏着变化的契机”。④梁治平:《“法治”与“治法”之间》,《读书》,2021年第4期,第63页。换言之,“法治”可以是不同的实践路径,不同国家以法制建设为基础展开的“法治”实践多样化反而是一种常态。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奉行种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原则。新加坡华族占人口多数,但从宪法到下位法,都十分注意防止“华族沙文主义”,在政治、法律、经济等领域,以种族人口比例为基础而进行一定的合理调适,统筹考量不同种族的需求。环绕在不同族裔来源国包围之中的新加坡,在外交上坚持新加坡是种族多元的独立国家之主权定位,不因文化亲疏而改变国家间关系原则。立足于新加坡社会宗教多元之现实,各类立法均追求在平等、宽容和不歧视角度尊重各个宗教传统和文化,强调宗教和谐,社会与公共秩序之稳定优先。这些举措使得新加坡较好地实现了种族与宗教和谐。
第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厉行法治的路径上,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落实维护种族和宗教平等不歧视的立法和政策,另一方面严厉打击煽动族群和宗教敌意与仇恨的违法言行。如前所述,在政府主导的国内立法层面,新加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规制框架,努力在不同领域实现不同种族民众获得平等机会,弱势群体得到相应的福利与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受到法律保障的同时,与宗教有关的行为亦由法律划出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同时,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为主旨的法令得到了严格执行,全社会形成了种族与宗教和谐是国家核心价值的共识。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进行法律界分,私人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但在公共空间不容任何破坏行为发生。
第三,在反恐和去极端化中坚持维护宗教和谐、宗教宽容和不歧视。进入21世纪,宗教极端主义对和平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全球范围内宗教不宽容、宗教歧视增加,宗教与文化冲突加剧。联合国《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宽容与歧视的宣言》第2条第2项对不宽容和歧视作出了界定:“本宣言中‘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不宽容和歧视’一语系指以宗教或信仰为理由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偏袒,其目的或结果为取消或损害在平等地位上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认、享有和行使。”奉行宗教宽容和不歧视,同时也是对抗极端主义的一种工具。2003年6月,新加坡政府公布了《宗教和谐宣言》,倡导民众朗读。正如李光耀所言,面对极端主义,要坚持鼓励宗教内的温和力量掌握优势地位和话语权。在宗教会长期与人类共存的现实面前,宗教宽容和不歧视是实现宗教—族群和谐的根本途径,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立国以来持续不懈地促进族群—宗教和谐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第四,保障多元种族—宗教公民能够在宪法与法律之下平等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在历史上,宗教政治参与一般包括个体的参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参与和宗教团体的有组织参与三种类型。①金宜久、吴云贵主编:《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7~93页。在当代新加坡,要求宗教不得参与政治,严格禁止以“群众运动”这种方式参与政治。无论是为了实现宗教理想,还是为了促进世俗目的,这一禁忌都不得打破,宗教本身必须严格地与政治分立。②1989年新加坡总统黄金辉在国会开幕时的演讲内容,转引自约西·拉贾著,陈林林译:《威权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话语与正当性》,第204页。在新加坡,不同族群和宗教信众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两种途径:一种是誓言保护本国多元种族宗教和谐主流价值观,以公民身份担任公职;一种是族群和宗教团体的领袖通过“少数人权利总统理事会”“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等机构,参与到国会法令、政府法规以及部长限制令等事务的审查与咨商中;而关于马来族则特别在宪法中作出了以圭著居民身份获得各个领域权利保障的承诺。以世俗政府为主导的“种族多元之国家”定位,保障了族群—宗教的合法政治参与,有助于通过法治途径将正当合理的诉求与非法不合理的诉求区分开来,走出“压迫、暴力与极端主义”的恶性循环。
第五,鼓励宗教团体的合法社会参与。宗教具有一些基本的社会功能,包括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伦理功能和文化功能,在人类历史经验中,宗教的社会参与包括开展宗教对话、祈求和平、关注全球化、环境保护、慈善救济、医疗帮助等。①金宜久、吴云贵主编:《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第70页。在新加坡,宪法保障宗教自由,坚持宗教宽容,但也要求在宗教多元化的社会中宗教要自我节制。《宗教和谐法令》对宗教人士特别是宗教领袖的严格要求,就体现了新加坡政府预防为主,任何团体都不得利用宗教事务和操纵宗教组织煽动种族、宗教敌意的立场。同时,政府鼓励宗教组织开展教育、社会和慈善工作,认可宗教组织对社会和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②参见前引1989年黄金辉总统国会开幕演讲。宗教信仰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巨大能量,新加坡通过共同价值观培育、多元文化维系、法律规制等方式,引导其在实现社会功能过程中增加社会福祉。
四、结语
新加坡采取以解决本国问题为导向的现实主义路径,将不同的理念与基本国情相结合,不拘泥于特定的教条,虽然不否认传统“法治”所承载的价值和理想,但更多地将“法治”用以维系多元族群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本国经济与社会稳定,视“法治”为促进发展的工具。新加坡的法治路径因而呈现出多个面向的综合特质,政府主导立法和法律解释权下“威权”与“法治”自洽,尊重传统与文化多元的保守主义与促进族群—宗教平等和谐的进步主义共生,重视家庭与社群温暖纽带的亚洲价值观与经济领域内的个体自由观共存。新加坡在种族与宗教和谐领域内的治理成效,再次验证了法治建设需要与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