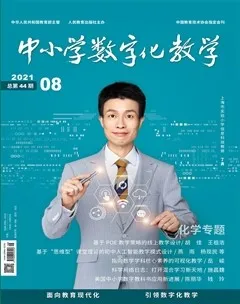跨学科视域下STEM素养模型建构
2021-12-29贺凯强

一、STEM教育与核心素养的关系
时代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发生了转变。我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依据,确立了素养导向的教育目标体系,正在以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为主线,着力建设和完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1]。STEM教育作为一种跨学科的育人方式,其在学校课程中的定位及其与核心素养的关系一直都备受人们关注。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将“跨学科主题教育教学”列为要着力改革的关键领域和主要环节之一[2]。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两份文件,则从课堂教学层面提出了跨学科教学的实践方式。《中国STEAM教育发展报告(起点篇)》指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应培养具有科技和人文素养的创新应用型人才。无论是国家未来发展战略还是个人的职业发展需求,都应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协作交流能力、批判性思考、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社会责任等置于优先地位[3]。不难看出,STEM教育所强调的运用“真实情境下的问题解决”“跨学科”培养学生创造力等综合素养,与培育学生核心素养应遵循的深入跨学科整合的要求是一致的[4],它顺应了时代发展与政策要求,成为培养未来人才的教育模式之一。随着STEM教育的发展,STEM一词演变为STEAM、STREAM等[5],但其所倡导的理念与STEM基本一致。
二、提出STEM素养的意义
尽管STEM教育与核心素养理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在开发STEM课程的过程中,一直有个困扰着教师的难题,那就是教师对STEM课程要达到的目标比较模糊,STEM课程的指向性不清晰。这个难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学生最终的学习结果。如一些STEM课程看着热闹,但是学生到底从中学到了什么,却是存疑的。凝练STEM课程目标,形成并明确STEM素养,既可以促进上述问题的解决,也对学校系统开发STEM课程具有重要意义。从课程角度分析,相对于有课标、教材的学科课程,STEM素养明晰了STEM课程作为跨学科课程、校本课程、社团活动、主题实践活动等方式的独特育人价值;对教师而言,无论是一节课或者一个主题的课,STEM素养可以帮助教师将日常的教学行为与核心素养对接,促进核心素养落实到课堂中;对学校而言,即使学生在几年间选择了不同的STEM课程,但STEM素养的连47cd8363864e20032b9949dcc50cc858续性可以保障学校对学生核心素养的持续跟踪与培养。
当前,STEM素养的概念界定尚未形成广泛共识。国内有学者将其定义进行了梳理,分为两大类[6]。一类侧重于STEM素养涵盖的学科范畴。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美国NGA(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给出的。 NGA将 STEM 素养(STEM Literacy)界定为:个人将其关于现实世界运行方式的知识运用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以及相关跨学科领域的能力。另一类则侧重于 STEM 培养的能力方向。被广泛运用的定义是著名科学教育专家罗杰·拜比提出的。他认为STEM 素养包括:在实际生活情境中发现问题、解决疑难、解释自然和人造物、形成基于证据的结论的相关知识、态度和技能;理解 STEM是关于人类探究和设计知识的学科;意识到 STEM 学科对我们的材料、智力和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作为一个富有建设性和善于思考的公民,有运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概念参与 STEM 相关事务的意愿[7]。
相比学科而言,STEM作为一种跨学科育人模式,更加注重跨学科综合素养的培养。因此,本研究倾向于能力方向的STEM素养定义,认为STEM素养是愿意关注、参与解决STEM相关问题,并运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素养。
三、STEM素养模型建构
对于STEM素养的构成,已有一些文章进行了论述。学者们主要从两种视角对STEM素养进行了分析:一是将STEM素养分解为STEM各学科素养,二是从跨学科整合的视角来整体建构[8]。《创新美国:拟定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议程》从分解的视角论述STEM素养,将STEM素养分为科学素养、技术素养、工程素养和数学素养四个方面[9]。这种分解的方式能够比较全面地概括STEM重点培养的素养,但没有很好地体现STEM各学科融合之后培养的素养[10]。北京师范大学郑葳教授在《中国STEAM教育发展报告(起点篇)》中提出整合视角下的STEM素养构成,具体包括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设计思维和合作共情能力[11]。华东师范大学祝智庭教授等提出能力为本的观点,认为 STEM 教育是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深度学习能力、适应未来的能力等[12]。由此可见,跨学科整合视角下的STEM素养不局限于学科素养,更侧重综合素养,回应了STEM跨学科育人的目标诉求。
除了以上两种视角的素养建构,还有机构和学者尝试将两者融合,体现STEM分科和整合育人的价值。《面向ATS STEM的概念框架》将243种具体的STEM技能和能力分为八类:问题解决、创新和创造、沟通、批判性思维、元认知、协作、自我调节和学科能力[13]。杨彦军等综合了国内外描述STEM素养的14个文件,分析STEM素养的共性与差异,形成了“STEM素养结构金字塔模型”。金字塔最底层是STEM各相关学科基础知识、技能和方法的综合;中间层次是建立在STEM基本知识、技能和方法之上的学科核心素养(科学素养、数学素养、工程思维等);最顶层是超越学科界限的共同核心素养(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创新能力等)[14]。这三层依据从具体到抽象、从个性到共性的顺序排列,更加明晰了STEM素养的结构。可以看出,第三种STEM素养建构视角涵盖了解决STEM问题所需要的各种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但素养构成显得过于庞大,不易操作。
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问世,它从跨学科角度呈现了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15],其中包括STEM教育所强调的理性思维、质疑批判、勇于探究、工程思维、问题解决、技术运用等。因此,一方面,STEM素养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其某一领域的具体化;另一方面,STEM素养具有特殊性,由于STEM主要是科技类课程的学科组合,科学与工程实践是STEM主要包含的领域,因此,STEM素养应突出强调在解决科学与工程实践问题过程中常用到的共同素养,这些共同素养在科学与工程相关学科也有所体现。在教育部2017年颁布2020年修订的普通高中物理、生物、化学学科课程标准中,除了各学科特有的核心素养之外,其他核心素养虽然名称有所差异,但均包括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这三个方面。在通用技术课程标准中也可以看到有关工程实践的核心素养,包括工程思维、创新设计等[16]。
在实践层面,STEM在学校多以跨学科的方式出现,其育人功能是在学科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与补充的,以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学科目标体系已经非常完善,因此,从跨学科整合角度构建STEM素养就变得尤为必要。
基于理论与实践分析,本文的STEM素养模型侧重从跨学科整合角度整体构建。以国内外STEM素养模型、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等为前提,聚焦科学与工程实践中所需要的共同核心素养,囊括认知、能力、态度、元认知等多个层面。如图1所示,研究者构建了“123+X ”STEM素养模型。该素养模型略去了STEM学科知识技能,突出STEM学习中学生解决真实复杂问题共同需要的能力、思维以及价值观念。
STEM素养有四个层次,分别是一个价值观念、两个核心思维、三个普适能力、X个专项能力。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价值认同;第二层是凸显科学与工程实践本质的理性思维和工程思维;第三层是解决STEM问题都需要具备的能力,包括展示表达、合作共情和项目管理能力;第四层是多种专项能力的集合,包括但不限于科学探究、工程设计与信息收集加工能力。
(一)一个价值观念
一个价值观念是指价值认同。价值认同是指对STEM领域及其学习活动产生兴趣,认同STEM对社会产生的价值,愿意通过STEM解决实际问题,为社会做出贡献。价值认同处在STEM素养最核心的位置,认知上的发展应起源于学生的兴趣、根植于学生对社会的责任。STEM、项目式学习课程让学生关注真实世界,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深度理解和掌握概念,或锻炼思维能力,也是为了让学生敬畏自然与生命,理解何为社会责任,最终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17]。
(二)两个核心思维
两个核心思维是指工程思维与理性思维。工程思维蕴含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同时属于通用技术学科核心素养之一。这里的工程思维在上述二者的基础上结合STEM特点进行了进一步优化,是指能认识系统与工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能够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进行要素分析、整体规划、科学决策和创新设计。理性思维则采用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的定义,是指崇尚真知,能理解和掌握基本的科学原理和方法;尊重事实和证据,有实证意识和严谨的求知态度;逻辑清晰,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解决问题、指导行为等[18]。工程思维和理性思维是在STEM学习活动中经常要用到的关键思维,体现了STEM的独特育人功能。例如,在设计制作水火箭的活动中,学生运用工程思维,权衡发射器发射角度、气压、水火箭使用材料和装水比例等各种限制条件,整体规划小组分工、实施进度,创新设计、实施、评估改进水火箭,使其飞得最远。疫情期间,教师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方式判断一个口罩可否起到防疫功能。教师发给学生口罩,让学生去判别。学生不能人云亦云,而是怀着质疑的态度,找到可以证明口罩有防疫功能的证据,进而根据口罩的透光性、防水性、是否有静电等多方面的证据进行推理,最终判断口罩是不是防疫口罩。这就是理性思维在课堂中的体现。
(三)三个普适能力
合作共情能力、展示表达能力、项目管理能力这三个普适能力对应着STEM整个学习过程或者多个学习环节。合作共情能力是指在任务或问题驱动下,小组成员分工协调、相互支持,建立与维持团队组织的能力;合理沟通、正确处理小组内冲突,建立与维持共同理解的能力。展示表达能力是指可以清晰、顺畅、有逻辑、高质量地展示内容和表达观点的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是指围绕项目目标,结合实际,对项目进行管理、监控与调整的能力。关于合作共情能力,STEM学习活动因其任务的复杂性,小组合作完成任务是必不可少的。展示表达能力主要体现在最后的成果展示和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汇报上。项目管理能力目前在STEM学习活动中被关注得较少,但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对项目进行管理、监控与调整,实际上是学生的元认知在发挥作用,体现学生对自我或对事物的认识、反思和调控。
(四)X个专项能力
X个专项能力包括工程设计能力、科学探究能力、信息收集加工能力等。这些能力对应着STEM某一种类型或者某一特定过程的学习活动,同时这些能力与科学、通用技术等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是一致的。工程设计能力是指针对现实世界生产或生活中的结构不良问题,进行问题与需求的系统分析,结合已有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艺术(人文)知识以及经验等,设计并选择最优的解决方案,通过模型建立、检验评估、多轮迭代等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科学探究能力是指基于观察和实验提出问题、形成假设、设计探究方案,通过探究获取证据,基于证据得出结论并做出解释的能力。信息收集加工能力是指借助一定的信息搜索工具,自觉并有效地搜集、评估、评价和使用相关资料的能力。专项能力会随着活动类型的增多而不断丰富。比如,有一些STEM课程会侧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调查能力,在STEM专项能力中就可以加上社会调查能力。这会使得STEM素养模型具有开放性和较强的操作性。
四、结语
STEM课程作为跨学科课程的一种形式,与学科课程形成了互补,其独特的育人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和综合能力。本文提出的STEM素养模型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除了前三个层次的素养比较稳定,第四层次的素养可以结合具体的课程类型和活动环节进一步丰富。这样的素养体系设计既考虑了科学性与操作性,又便于学校在其基础上形成校本化的表达,更科学地开发STEM课程。
注: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一般课题“基于项目化学习开发与评估STEAM教育课例”(立项编号:CDDB19243)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17]夏雪梅.项目化学习的实施:学习素养视角下的中国建构[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0.
[2][1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EB/OL].(2014-03-30)[2021-05-24].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54/201404/167226.html.
[3][11]郑葳.中国STEAM教育发展报告(起点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4] 贺凯强,王志强,刘平,王贝贝.表现性评价在STEAM课程中的设计与实施[J].中小学数字化教学,2020(9)BWo1zPBR5ja7zxH16AoTIleW/R+hqKc4jekXRmbZr8U=:24-27.
[5]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STEM教育白皮书[EB/OL].(2017-06-20)[2021-05-24].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917/8063005115002050.shtm.
[6][14]杨彦军,张佳慧,吴丹.STEM素养的内涵及结构框架模型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21(1):42-49.
[7] BYBEE R W. Advancing STEM education: a 2020 vision[J].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teacher,2010(1):30-35.
[8] 宋怡.STEM素养视域下的科学教学:审思与重构[J].现代教育科学,2018(8):96-100.
[9]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Innovation America: Building a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Agenda[R]. Washington: NGA,2007.
[10]蔡海云.STEM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践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7.
[12]祝智庭,雷云鹤.STEM教育的国策分析与实践模式[J].电化教育研究,2018(1):75-85.
[13]Dublin City University et al.. Towards the ATS STEM Conceptual Framework [EB/OL]. [2021-5-24].http://www.atsstem.eu/wp-content/uploads/2020/02/ATS-STEM-REPORT-5-1.pdf.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18]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J].中国教育学刊,2016(10):1-3.
(作者系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课程发展中心教研员)
责任编辑:牟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