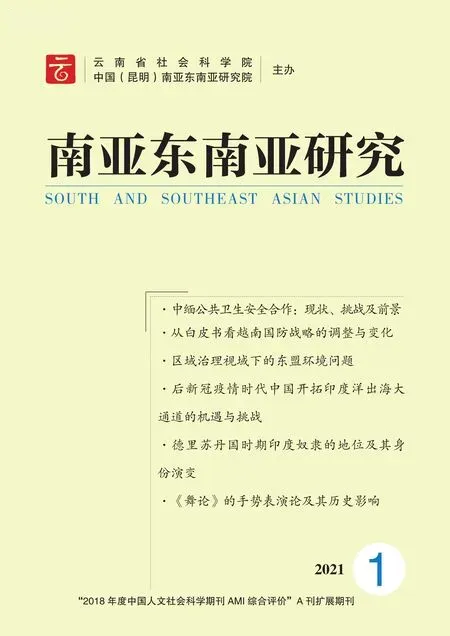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
2021-12-29高奕
高 奕
在当今国际社会,文化外交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高度重视并着力推行的对外战略手段和外交模式之一,各国政府结合本国文化软实力的特点和优势,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外交政策及活动开展方式。
一直以来,无论是从事文化外交的政府官员还是该领域的研究学者,都对“文化外交”的定义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界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米尔顿·卡明斯(Milton Cummings)认为:“(文化外交)是各国及其人民之间思想、信息、艺术和其他文化方面的交流,目的是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①Milton Cummings,“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A Survey”,Washington,DC: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e,2003,p.1.这个定义忽略了文化外交作为国家行为而应具有的政治属性,进而模糊了文化外交与一般跨国文化交流间的区别。美国文化外交史专家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A.Ninkovich)将文化外交定义为“一种在国际政治中有关管理文化知识的影响力的、专门的国家政治手段”。②Frank A.Ninkovich,The Diplomacy of Ideas:U.S.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1938~19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宁科维奇明确指出文化外交属于国家政治范畴,但该定义仍过于宽泛。曾任职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闻署(USIA)的前富布赖特协会主席、著名文化外交研究学者理查德·阿恩特(Richard T.Arndt)通过与“文化关系”(Cultural relations)的对比来阐述他对文化外交概念的理解:“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文化关系自然而逐渐地发展——跨境贸易和旅游、学生流动、通信、图书流通、移民、媒体访问、异族通婚——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跨文化接触。如果这是正确的,文化外交只能被认为是政府正式的外交人员对这种自发的(跨境的文化)流动的整理和引导,以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③Richard T.Arndt,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Dulles,Va.:Potomac Books,Inc.,2006,p.xviii.阿恩特的概念相对较为全面,但从文化外交史来看,政府往往在文化外交事业上起到“创制”和“领导”的作用,比如著名的“庚款兴学”及“富布赖特项目”等,政府在其中表现出的不仅仅是阿恩特所提出的类似因势利导的情况。在综合分析比较文化外交的各种定义后,笔者给出了自己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文化外交,是一国的政府或与政府合作的非政府行为体通过国际教育交流、国际文化体验、海外文化中心、国际展览、国际文体交流以及国际文化贸易等形式向另一国的国民投射本国文化元素中的精华和成就的行为。文化外交的直接目的是加深两国间的相互认知和理解,增加文化外交发起国对对象国的吸引力,树立和提升发起国的国家形象,创造对发起国有利的观念环境。文化外交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和实现发起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利益。
美国政府自20世纪30年代正式开展文化外交以来,“文化”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战略“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利器,被美国在包括东南亚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地推行了大半个世纪,成为美国争夺和护持霸权的重要手段之一。
近些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文化外交的关注与研究不断深入。其中,中国学者的研究相对集中在美国对华文化外交领域,而对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渗透、文化扩张涉及较少。冷战时期是奠定美国官方主导的文化外交的基本思路、立法支持以及管理架构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延续至今的“明星”项目,因此研究这段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美国文化外交。此外,对中国而言,东南亚地区具有不可估量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价值,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美国在我国周边地区开展“攻心战”的演进逻辑,为我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提供借鉴。
一、美国对东南亚开展“文化冷战”的背景与动因
经过20世纪初的实践①20 世纪30 年代前,美国政府谨慎地开展了一定程度地介入国际文化事务以服务对外政策的尝试。一是1908 年美国国会批准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庚款兴学”。利用清政府约1800 万美元的赔款安排了近2000 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深造,其意图既有加强对华渗透和影响的现实目的,也有基于“使命感”的理想主义色彩。二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7 年4 月成立“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CPI),意图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支持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该委员会的活动范围不仅仅限于美国国内,而且在欧洲、拉美和远东地区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通过广播、出版、演讲、电影等各种形式向世界宣传美国的理念、制度、决心以及强大的实力。但是在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下,该委员会于1919 年8 月被威尔逊总统裁撤。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是美国第一个带有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色彩的联邦机构。此外,美国政府还尝试打通慈善界和文化界与政府外交部门的联系,以进一步探索利用文化服务对外政策的可能性。和二战的检验,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文化手段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更加坚定了使用文化外交塑造战后国际秩序、建立美国霸权地位的决心。基于这样的思路,美国官方开始更加深入地介入公共文化事务。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单纯协调私营部门文化活动的传统角色,转而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历史上留给非政府行为体的责任和活动”。②Michael L.Krenn,The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Cultural Diplomacy:1770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7,Kindle Version.美国政府主导的文化外交项目在世界各地粉墨登场,东南亚地区则成为“文化冷战”的重要战场之一。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开展文化外交的背景与动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外交管理机构的调整与演进
为了促进文化外交,更好地服务美国对外政策,从二战后期开始,美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机构调整和改革。1944年1月,美国政府将“文化关系司”(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改名为“科学、教育与艺术司”(Division of Science,Education and Art),继而又与其他一些机构合并组成了一个新机构——“公共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OPI)。1945年8月,美国政府撤销战时信息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将其职能以及泛美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的对外信息职能一起转移到了美国国务院新成立的名为“临时国际信息服务局”(Interim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的机构。同时,美国国务院从公共信息办公室剥离出部分职能,新建了“国际信息与文化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Affairs,OIC)。不久,战时信息处和泛美事务办公室的职能都被整合进该办公室。自此以后,美国二战时负责对外信息与文化关系的三大部门被统一划归为国务院体系管理。
战后,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深入,美国政府意识到仅凭国务院的力量来领导、管理和协调日益繁重的国际信息与文化活动,已经无法满足需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和责任大大增加,加上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以及需要‘重新教育’曾经是战败国而现在是被占领国的人民,使之走上民主道路所带来的特殊挑战,使得其(美国新闻署的成立)成为必然。”①Arthur A.Bardos,“‘Public Diplomacy’:An Old Art,a New Profession”,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Summer 2001,https://www.vqronline.org/essay/public-diplomacy-old-art-new-profession.1953年8月,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下,“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USIA)成立,该机构整合了美国政府各个涉及对外信息传播的机构职能,其中包括了国务院几乎全部的对外信息与文化交流项目(只有国际教育交流项目还留在国务院,但1955年这些教育交流项目的海外运作和管理也被移交给了美国新闻署)。美国新闻署独立于美国国务院,直属美国总统管辖。
1978年,吉米·卡特总统再次改组美国文化外交相关机构,将美国新闻署与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合并,组成名为“美国国际交流署”(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gency,USICA)的机构。自此以后,美国的文化交流项目的分治局面(运行管理权归属国务院,海外行动管理权归属美国新闻署)正式结束。里根总统在1982年又将该机构的名称恢复成美国新闻署(USIA)。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新闻署是美国政府对外信息传播和推行文化冷战的主要负责机构。
(二)对文化外交的立法支持
除了对行政部门进行机构改革,为文化外交提供组织保障外,美国国会也在文化外交的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外交的法案上。
作为1944年《剩余物资法案》的修正案,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提议国会“批准使用向国外销售(战争)剩余物资所获得的账款,用于通过教育、文化、科学等领域的学生交流的方式促进国际善意”。②Michael L.Krenn, The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Cultural Diplomacy:1770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7,Kindle Version.美国历史上不乏使用政府资金支持教育交流的先例,比如著名的“庚款兴学”,但是这次富布赖特参议员的提案“与之前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有明显区别,因为其具有全球范围的潜在影响力,并且力图组织起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教育交流”。①Michael L.Krenn, The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Cultural Diplomacy:1770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7,Kindle Version.1946年8月1日,杜鲁门总统正式签署了《富布赖特法案》(Fulbright Act of 1946)。
随着冷战的逐步升级,美国政府意识到自己与苏联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展开竞争。因此,在国会表决通过后,杜鲁门总统于1948年1月正式签署了《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又称《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该法案确保了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国际信息、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②Milton Cummings,“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A Survey”,Washington,DC: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e,2003,p.7.这样,通过国会正式授权的美国政府资助的文化交流项目的活动内容不再限于教育交流,其适用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不再限于购买美国战争剩余物资的国家。
1956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国际文化交流与贸易公平参与法案》(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and Trade Fair Participation Act)。该法案授予美国总统一系列管理文化交流活动的相关权力,如可以派遣美国艺术家和运动员以个人或团队的形式出访外国,宣传美国在该文化领域取所取得的成就,派遣美国代表参加在国外举行的艺术、戏剧、音乐、体育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节、比赛以及展览会等。此外,该法案还鼓励个人、公司、协会和其他私人团体参与该法案提到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③参见美国政府出版局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官方网站提供的该法案内容全文,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STATUTE-70/pdf/STATUTE-70-Pg778.pdf.
1961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互助法案》(Mutu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又称《富布赖特—海斯法案》(Fulbright-Hays Act)。该法案带有明显的富布赖特参议员个人的理想主义色彩,通篇没有任何涉及“冷战”或“对外政策”的表述,某种程度上是对冷战开始以来美国文化外交过于侧重服务现实政策、强调冷战对抗的一种“回摆”:“新法案缺少冷战论调,它有四个目标:第一,‘增进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人民,而不是精英)之间的相互了解’;第二,加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相互依存);第三,促进国际合作以推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进步;第四,致力于建立‘友好、互谅及和平’的国际关系。”①Richard T.Arndt,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Dulles,Va.:Potomac Books,Inc.,2006,p.329.该法案给予美国政府在推行对外教育文化交流项目方面更多的授权,并且也使这些项目从立法层面具有获得更多资金支持的可能。伴随着该法案的通过,1961年底,美国国务院成立了“教育与文化事务局”(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三)“多米诺骨牌”理论与东南亚重要地缘战略地位的确立
从二战开始,美国逐渐认识到了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价值和重要地缘战略意义,但是在战后初期,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重心仍然放在东北亚,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两国。在中国,美国希望通过扶持蒋介石政府,将中国变为美国在远东的坚定盟友,但中国内战的走势让美国逐渐意识到即将“失去中国”,于是将日本作为代替中国的选项,开始着力扶持日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美国来说,东南亚既是它对付中国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的前沿阵地,又是推动日本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其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②刘莲芬:《一个半世纪的美国与泰国关系史》,科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63 页。此外,苏联借二战后东南亚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之势,开始介入东南亚事务,也让美国政府感受到了苏联的威胁,认为苏联的目的是要取代西方国家控制东南亚地区,扩大共产主义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此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加紧了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步伐。朝鲜战争的结果让美国感受到了新中国的力量,因而更加着力谋求全方位地遏制中国。通过朝鲜战争,美国也暂时稳住了东北亚的局势,于是将遏制中国影响的重点转移到东南亚方向。
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正式提出了“多米诺骨牌”理论(“falling domino”principle):“你摆了一排多米诺骨牌,你把第一张打翻了,最后一张肯定会很快翻倒下去。当我们谈到可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比如印度支那、缅甸、泰国、(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丧失,那么你在谈论的,就不仅仅是会使你们遭受物资和原材料损失这样不利因素成倍增加的地区了,而且是一个会真真正正丧失成百上千万人口的情况。”③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Volume XIII,Part 1 Indochina), Kindle Version.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1954年通过《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的签订,加上美国之前与亚太地区国家签订的一系列防卫条约,美国建立了遏制中国的封锁链条。
在思想上,美国希望自己的观念和文化能够被东南亚各国国民了解和认可,进而促使处于战后“非殖民化”转型期的东南亚各民族和国家接受美式思维,效仿美国模式,构建亲美、亲西方的现代国家,加入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在有意识地影响和塑造东南亚正在发生的变革进程的活动中,文化外交体现了美国在该地区的使命:(使该地区国家)对共产主义产生免疫,按照自由资本主义路线实现现代化,以及从殖民地和传统社会向孕育着西式民主的种子的现代社会制度转型。”①Marc Frey,“Tools of Empire:Persuas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s Modernizing Mission in Southeast Asia”,Diplomatic History,Vol.27,No.4,September 2003,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SHAFR),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Inc.,p.545.
二、美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的实施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南亚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外交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类项目,即教育交流、图书外交以及表演外交。
(一)教育交流项目在东南亚的广泛开展
1948年秋,《富布赖特法案》生效后美国开展的第一个项目就在东南亚地区的缅甸落地。1948年1月4日,缅甸正式宣布独立,美国当天便宣布承认缅甸的主权国家地位。就在两周前的1947年12月22日,美国才刚刚与英缅政府签订了《富布赖特协议》。
“富布赖特”缅甸系列项目由美国驻仰光大使馆负责具体实施,“最初的资金来源于美国在缅甸剩余军事装备的销售,预算为每年20万缅甸卢比”。②Robert L.Clifford,Helen B.Hunerwadel,“Burma Beginnings:Fulbright and Point Four”,The Fulbright Difference,1948~1992, edited by Richard T.Arndt,David Lee Rubin,Transaction Publishers,1 edition,January 1,1993,p.18.第一个项目是资助缅甸的两名女护士到美国学习,她们也因此成为最早获得“富布赖特项目”资助的外国学生。第二个项目是邀请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University of Nevada at Reno)经济学系的欧内斯特·因伍德(Ernest L.Inwood)博士担任仰光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第三个项目是邀请一对夫妻——农业专家奥斯卡·亨德瓦德尔(Oscar Hunderwadel)和家庭经济学家海伦·亨德瓦德尔(Helen Hunderwadel)——于1949年2月来到缅甸的掸邦地区提供服务。奥斯卡在当地建立了农业培训学校,为当地的农业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海伦则在当地开展了家庭罐装食品的相关培训,成为缅甸食品罐装产业的引路人。随着缅甸内战的不断升级,出于安全考虑,美国政府对“富布赖特”这样的教育交流项目在缅甸的开展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尽管如此,冷战期间双方的教育交流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规模。
由于日益担忧共产主义对东南亚的影响,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便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思想攻势”的力度。1950年6月21日,副国务卿詹姆斯·韦伯(James E.Webb)向杜鲁门总统提交备忘录,明确表露出这样的政策倾向:“国务院建议立即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加强信息和教育交流项目,使这些国家了解美国的政策,并解释美国对这些国家人民和政府的军事及经济援助方案。”①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Volume VI,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Kindle Version.韦伯将泰国作为落实这一政策的重点国家。
1950年7月1日,泰美双方签订了《泰美教育文化交流协定》(Thai-U.S.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greement,即《富布赖特协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70年代初期,是美泰教育交流最频繁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将在泰教育交流项目的重点放在培养泰国具有社会领导潜力的青年精英身上。在一份递交给负责监管美国政府秘密行动的“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1953年由艾森豪威尔总统设立)的名为《对泰国行动计划纲要》(“Outline Plan of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ailand”)的文件中,在提到美国对泰国的信息宣传工作时,特别强调优先考虑接触第二梯队潜在的领导人,并且对这类人选给出了明确的界定:“a.那些处于统治集团边缘、可以受到美国影响,而且凭借才干或环境有可能在统治结构中崛起的人。b.那些因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公民责任感而使其能够采取有利于城乡民众普遍福利的行动的人。c.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中那些政治上较活跃和有一定影响力的人。”②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Volume XXII,Southeast Asia),Kindle Version.在这样的指导思想的引领下,美国在泰国筛选出了一批符合条件的人选,通过富布莱特项目将他们送往美国学习和生活。
除了缅甸和泰国之外,富布赖特项目还在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等国家展开。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地区局势的缓和,80年代的里根政府将教育交流外交的重点转移到了西欧和苏联的年轻人身上,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教育交流外交活动逐步减少。
(二)图书外交的大力推广
美国设立海外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期。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4月成立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简称CPI),负责向世界宣传美国的思想文化和强大形象。该机构在一些国家设立了美国的海外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其中“最著名的图书馆是在墨西哥城,一个名叫罗伯特·H·默里(Robert H.Murray)的人在那里从美国侨民社区招募人员为当地人提供英语课程”。①Nicholas J.Cull,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8.二战期间,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的孙子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领导的“泛美事务协调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OCIAA)继续在南美地区建立图书馆,组织讲座和各种文化活动。1942年,在战时信息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主导下,美国在英国伦敦设立了海外图书馆。到了1945年,美国相继在斯德哥尔摩、里斯本、马德里、伊斯坦布尔、开罗、莫斯科、重庆、贝鲁特、墨尔本、悉尼和大马士革建立起海外图书馆。
二战后,作为在目标国家和地区传播美国思想文化的平台,美国的海外图书馆和信息中心(Information Centers)在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冷战中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东南亚地区在战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去殖民地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这一进程中,知识分子阶层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如果美国政府能够让这些社会精英被美国文化所吸引,影响这些人的价值倾向,让他们认可和接受美国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那么这群“意见领袖”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这将大大有利于阻挡共产主义进入该地区,同时对美国渗透和控制东南亚地区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图书馆作为知识阶层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资源,自然就成为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开展文化外交的必要手段。
美国政府从二战期间就开始布局东南亚地区的信息中心,“美国的小型信息中心要么在战争期间就投入运作(例如在曼谷),要么就是在日本占领军投降后立即建立起来(例如在仰光和新加坡)。到1949年,东南亚的所有主要城市都已经设立了信息中心的办公室。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在东南亚的)信息中心的数目已经增加到了58个”。②Marc Frey,“Tools of Empire:Persuas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s Modernizing Mission in Southeast Asia”,Diplomatic History,Vol.27,No.4,September 2003,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SHAFR),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Inc.,p.551.1951年8月,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与教育交流办公室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设立了新的信息中心。1953年美国新闻署成立后,美国的海外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全部归属该机构管理。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东南亚地区的重视也促使该地区的美国海外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得到了更加快速的发展。1954年,美国设在菲律宾的图书馆数量已经达到了8个,馆藏图书41500册,这些图书馆在当地非常受欢迎。例如,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图书馆有242个座位,平均每天要接待2000名读者。①常贝贝:《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战与海外图书项目(1945~1961)》,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年,第102 页。同年,美国新闻署在缅甸的港口城市毛淡棉市设立了新的信息中心,以加强对缅甸的少数民族克伦族的影响,同时,美国新闻署又在缅甸东枝(Taunggyi)建立了另一个信息中心以覆盖掸邦地区。此外,美国还扩大了设立在仰光大学的美国图书馆的规模,以进一步影响当地的学生群体。②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Volume II,Part 2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ndle Version.
随着海外图书馆的增设,美国政府面临着图书翻译的问题。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除了少数的社会精英或有过海外教育经历的人士之外,大多数的当地国民并不具备阅读英语书籍和资料的能力。因此,美国开始将大量反映美国和西方思想文化的著作翻译成当地语言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推广。
缅甸独立后,国家领导层与美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缅甸政府对美国文化持欢迎态度,因此缅甸自然也就成了美国译本图书发行的重点国家。被译成缅文的著作包括《艾默生精选集》《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自由的精神》《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论民主》《亚伯拉罕·林肯》《论美国的民主》等。
针对越南,美国则出版了越语版的《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托马斯·杰斐逊:民主之父》(Thomas Jefferson:Father of Democracy),以及上文提到的《本杰明·福兰克林自传》,③Congressional Record: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87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Volume 107-Part 13,August 24,1961,To September 5,1961,(Pages 16897 to 18214),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61,p.17799.该著作也被翻译成了印尼语在印度尼西亚发行。④Ibid..在印尼发行的西方文学翻译作品还有诸如吉恩·利西茨基(Gene Lisitsky)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该书首发10000册,因受到当地民众欢迎而加印了3000册。⑤Ibid.,p.17800.在马来亚联邦,诸如《杰斐逊:自由思想的捍卫者》(Jefferson:Champion of the Free Mind)这样的著作被翻译成马来语在当地发行。⑥Ibid..
(三)表演艺术外交的积极行动
一国的表演艺术(这里指作为“严肃艺术”或“高雅艺术”意义上的音乐、舞蹈、戏剧等)除了给人以美的享受外,还能映射和传递出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体现该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状态、精神品质、思维模式和价值追求,因此表演艺术也成为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冷战时期美国表演艺术外交在东南亚最广为人知也最成功的是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①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1894~1991 年),美国舞蹈家和编舞家,1999 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葛兰姆为世纪舞蹈家,并称她为20 世纪最重要的舞者之一。的案例。1955年,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下,葛兰姆开始了她的亚洲巡演之旅。从1955年9月到次年3月,葛兰姆和她的舞蹈团从日本东京开始演出,一路在东南亚地区的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巡演,随后前往南亚地区和伊朗,最后一站是以色列。美国国务院对此次巡演寄予厚望:“由于美国国务院在战后寻求修复(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并在亚洲建立联盟以推广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葛兰姆的作品具有特别的功用。葛兰姆的现代主义舞蹈展现了领先时代的独创性,将亚洲美学与美国风情的特色融合在了一起。”②Michael L.Krenn,The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Cultural Diplomacy:1770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7,Kindle Version.由于此时的东南亚地区正处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去殖民化的高潮期,葛兰姆及其团队的美国现代舞传递出的打破约束、追求自由的思想,深深打动了当地人民的心灵,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例如,印尼媒体就给出了高度的评价:“我们很难说服自己,除了廉价电影,以及美国人在政治、军事和商业等方面的霸道态度,美国还有另一面存在。我们厌烦了‘美国主义’浪潮日复一日地出现,而玛莎·葛兰姆的到来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因为她的作品让我们相信,美国也拥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东西。”③Lucy Victoria Phillips,“The Strange Commodity of Cultural Exchange:Martha Graham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on Tour,1955~1987”,doctoral 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2013,p.152.
美国政府的驻外机构在葛兰姆的文化外交之旅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葛兰姆一行每到一处,美国驻当地的机构就会开始宣传造势,在当地的媒体上展开报道,并配以引人注目的宣传照片。除了舞蹈演出外,美国政府还安排葛兰姆发表演讲,会见当地精英人物,竭尽全力地把葛兰姆打造成魅力十足的“文化大使”形象。葛兰姆的此次亚洲文化之旅,被美国政府认为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她的艺术中展现出的美国与众不同的特色,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对美国文化的深度和活力的有力证明”。④“Martha Graham in Asia”,Hope for America:Performers,Politics and Pop Culture,https://www.loc.gov/exhibits/hope-for-america/cultural-diplomacy.html.
三、美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的影响效果及制约因素
(一)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的影响效果
第一,对于泰国和菲律宾这类国家,基于历史渊源、相对悠久的文化交流史以及美国文化外交在当地较多的资源投入,美国思想文化在当地得到了相对广泛的了解和接受,两国参加过美国文化交流项目的国民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如1956年泰国的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沙努·乌纳军(Snoh Unakul),从美国学成回国后担任泰国全国立法会议成员,后来又担任泰国银行行长(1975~1979年),并于1991~1992年担任泰国政府副总理。除了担任政府职务外,沙努还是泰国影响力最大的智库“泰国发展研究所”(Thail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TDRI)的创始人,担任过该机构董事会主席以及TDRI基金会主席。菲律宾驻美国前大使小何塞·兰佩·奎西亚(Jose Lampe Cuisia Jr.)在富布赖特项目的支持下于1968年赴美留学,对于美国与菲律宾之间开展的教育交流项目对菲美双边关系的影响和作用,奎西亚给予了高度评价:“(诸如富布赖特等教育交流项目)是‘有利于发展菲律宾与美国双边关系的非常好的项目’,‘也是美国人得以了解菲律宾人的生活方式以及菲律宾文化的一个好渠道,这些项目让双方建立了非常稳固的关系’。”①Soriano,“1948 Pinay scholar honored at Fulbright 70th Anniversary”, GMA News,March 24,2018,https://www.gmanetwork.com/news/lifestyle/content/647778/1948-scholar-awarded-at-fulbright-phl-s-70th-anniversary/story/.
第二,对于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等美国介入较晚的国家,美国的文化外交同样对当地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和政府官员)接受西方思想、树立和强化亲美倾向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在1957年10月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拍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提到,印度尼西亚政府“请求(驻当地)美国新闻处(USIS)向其提供15000册反共书籍,用以在共产主义盛行的爪哇中部地区分发传播”。②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Volume XXII,Southeast Asia), Kindle Version.美国官方对这类项目的实施效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对美国新闻署的“民主经典图书项目”做出的评价:“也许没有任何项目在赢得新兴国家人民的人心方面,(比该项目)做得更加成功。”③Congressional Record: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87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Volume 107-Part 13,August 24,1961,To September 5,1961,(Pages 16897 to 18214),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61,p.17798.
第三,美国通过文化外交向东南亚各国输送美式自由民主思想的做法在某些情况下也给当地的统治阶层带来了一些麻烦,其中典型的例子是泰国社会主义党总书记、反对泰国军人独裁的富布赖特学者卜萨农·卜育他那(Boonsanong Punyodyana)。卜萨农于1962年和1967年先后两次赴美学习和工作,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回国后在泰国法政大学任教的卜萨农迅速投入到宣传和组织学生开展旨在推翻泰国军人独裁政府的政治运动中,并担任“泰国社会主义党”总书记。该党在1975年的大选中获得众议院的45个席位,位列所有参选政党的第二位。由此可见,一些在美国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东南亚精英投入到本国争取政治民主化、反对威权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对当地统治阶层的政权稳定造成了冲击。
第四,美国力图在东南亚国民心中树立“民主、自由”的国家形象,在老牌欧洲殖民者眼中,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外交具有明显的“反殖民化”倾向,这一做法引起了希望继续控制该地区、阻止或延缓其非殖民化的英、法等西方强国的反感。其中尤其以企图继续控制印度支那地区的法国反应最为激烈:“法国官员(以及反应相对没那么激烈的在西贡和河内的英国外交官)认为,美国新闻署是美国为迫使法国离开该国而发动的协同攻击的先头部队。法国殖民地官员深信美国的文化外交充满了反殖民主义的‘开放自由精神’,因此他们经常试图阻挠美国新闻署的各种项目,并且(安排)秘密警察密切监视(美国在当地的)公共事务官员。”①“M.Haussaire (Saigon) to Foreign Office”,14 March 1947,Serie B,Amérique 1944~1952,L’Etats-Unis,Box 128,Archives du Ministère Étrangères,Paris (hereafter MAE);“Activités Étrangères,Mois de Novembre 1954,”Commissariat Général de France en Indochine,Direction des Services Francais de Sécurité,Haut Commissariat d’Indochine,Cabinet,5/31,Centre Archive d’Outre-mer,Aix-en-Provence;Geoffrey A.Wallinger(British Embassy,Bangkok) to H.A.Graves (Saigon),14 February 1952,FO 371/101054,PRO.Cited in Marc Frey,“Tools of Empire:Persuas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s Modernizing Mission in Southeast Asia”,Diplomatic History,Vol.27,No.4,September 2003,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HAFR),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Inc.,p.566.
(二)美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的制约因素
首先,美国文化外交的扩张主义本质严重制约了其实际影响力的发挥。美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的本质是基于美国的“例外论”“天命论”以及国家利益基础上的针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扩张主义行径。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文化外交手段,以美国思想价值观和美式发展道路影响东南亚地区国家国民的观念偏好,为美国渗透、介入和主导东南亚地区事务以及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目标服务。美国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思想和文化元素,目的是影响和同化东南亚地区的各国国民。当这些国家的国民接受美国思想文化、认可美国社会制度和采取美式衡量标准时,美国会对其大加赞赏,反之则斥之为远离“文明世界”。这种过于强调用本国文化影响他国,而忽视了对对方文化的认知、理解和尊重的行为,不可能获得他国国民的充分认可。
其次,冷战期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严重制约了文化外交效果的发挥。例如在印度支那地区,尽管美国采取了文化投射和观念渗透等措施,但由于美国先是支持法国殖民者干涉印度支那地区国家的民族独立进程,随后又取代法国殖民者介入该地区事务,企图全面控制印度支那,并最终演变成一场持续近20年的战争,这些做法足以“对冲”美国与印支三国的文化交流带来的正面效应。当美国的炸弹落在越南土地上的那一刻,美国通过文化外交在当地建立起来的国家吸引力便随之“粉身碎骨”。
四、结语
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外交活动,是“文化”作为国家对外战略工具的重要实践。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认为文化外交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进入21世纪后,为了有效应对世界各地汹涌的“反美主义”,挽回美国日益恶化的国际形象,文化外交再次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与此同时,伴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东南亚再次成为美国外交关注的焦点。在总结冷战时期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美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再次粉墨登场,除了扩大诸如“富布赖特”这样的传统项目规模以及对海外图书馆进行信息化升级外,还创制了以“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Young Southeast Asian Leaders Initiative,YSEALI)为代表的新型文化外交项目,竭力争夺人心,为其“重返”东南亚并维护其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