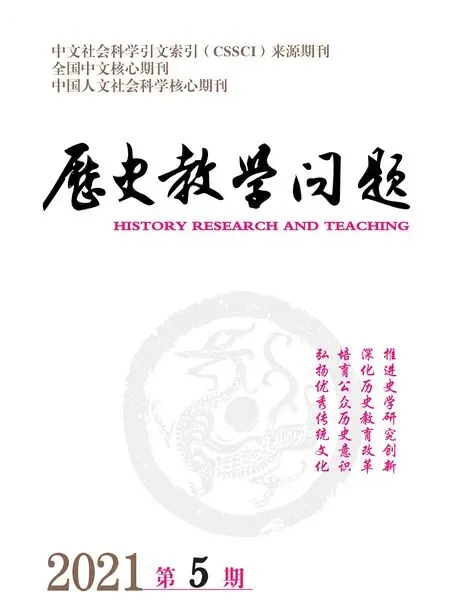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国民党关系之研究(1920—1921)
2021-12-29杨阳忻平
杨 阳 忻 平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虽然排斥其他政党的异质分子,但并不介意涵纳其中“同质的先进分子”。①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808 页。1920 年中共早期组织成立后,在政治领域形成一股具有独特政治信仰的坚定力量。面对五四时期面目繁多的政党、社团,初生的中共如何处理与在意识形态、政治诉求及阶级基础上存在较大差异的其他政党的关系,比如与国民党的关系,无疑是现实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共与国民党的早期关系已有丰富论述,其中稍有涉及中共一大以前的内容,但在观点上存在较大差异。据笔者归纳,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即“相对互斥说”“根本排斥说”“非排斥说”“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②“相对互斥说”认为中共早期组织与国民党“互相排斥”,但此种互斥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参见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 年,第3—8 页。“根本排斥说”认为在共产国际“进攻理论”的影响下,中共早期组织“存在着明显的排斥国民党的政策”。参见张喜德:《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的政策与共产国际成立伊始的“进攻理论”》,《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 期。“非排斥说”认为此一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对国民党是“抱着合作的,而非对立和排斥态度”。参见唐纯良:《论中共二大前的国共两党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6 期。此外,杨奎松提出,中共尚未正式成立以前国共双方交往仅限于主要成员间的“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2页。笔者在对比阅读中外档案文献后发现,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与国民党人之间的关系确如某些研究所称是“渊源较深”,但是细究起来又不止于此。双方在1920 年搭建起错综复杂的社会网已溢出个体交际范畴,对中共早期组织形态构建提供了客观助力。国民党在广东建立政权后提供的政治舞台,使国共关系不是“互相排斥”或“无组织间问题”所能概括,而是趋向党际合作。这种关系的转变对中共建立之初的政党政策构成实质性影响。鉴于既往研究对上述问题未能详尽展开,笔者将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类资料,系统梳理中共早期成员与国民党人由交叉合作走向组织分化的复杂过程,揭示社会网在建党中的影响与作用,进而探究国共关系演变与中共一大相关决议的关联所在。
一、早期共产主义者与国民党人的社会网
以往囿于史料限制,有流行观点认为中共与国民党“建立联系”的时间要晚于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直至1922 年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才为国共联系创造了前提条件。然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在20 世纪90 年代出版后,这一观点已不能成立。更多的新史料证明,中共早期组织与国民党的直接联系在1920 年已经展开,并不依靠共产国际作为中介。1920 年2 至12 月,中共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寓居上海,他领导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在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进行了频繁互动,两大群体的交际往来为两党转向组织合作逐步积累了主客观条件。对此,笔者试从地缘、学缘、业缘与同道关系四个方面分析其间交集及社会网的作用。
晚清以降,中国人口频繁向口岸城市流动,以同乡、邻里为代表的地缘关系是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一个标志,发挥了团结群体的作用。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都市人群中没有形成乡村社会中通过家族血缘或生产劳动维系的社区观念,居民间缺乏里弄或更宽泛地域单位的社区认同观念。①卢汉超:《霓虹灯外:20 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210 页。在此背景下,同乡身份认同成为上海自发组织更为突出的组建原则。起初,活跃在上海的共产主义者与国民党人并不以政治身份作为群体界限,而是经由同乡关系聚拢成为两股力量。其一是旅沪湖北同乡群体,以湖北善后公会为联结点,人员包括李汉俊、董必武、张国恩、詹大悲、陈潭秋等。其二是旅沪浙江同乡群体,以《星期评论》社为中心,包括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杨之华、刘大白、俞秀松、施存统等在内。同乡之间“差不多天天见面”,促使群体关系愈见亲密。②董必武:《忆友人詹大悲》(1928 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7 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第5 页。其间的交流砥砺也对厘清各人驳杂的思想头绪起到关键作用。③《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71 年8 月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369-370 页。由于上述人员主要活动在上海法租界范围内,比邻而居的邻里关系也成为地缘纽带之一。陈独秀、李达、李汉俊、詹大悲等人居住在渔阳里,位于董必武、张国恩住址的“正对过”,且与住在三益里的邵力子、陈望道距离很近。陈望道后来说,正是因为“大家住得很近”,得以“经常在一起”反复交谈。④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1956 年6 月17 日),《“一大”前后》(2),第20 页。此时,国民党总部与一些党内要人的寓所也位于法租界,地缘便利为群体联系创造了条件。陈独秀与戴季陶等人“过从颇密”,⑤张国焘:《我的回忆》(1),东方出版社,2004 年,第81 页。李汉俊是孙中山家中的“常客”,孙是李“最重要的朋友”。⑥Bolshevism in the Far East,April 7,1920,FO371/5341,Foreign Offices Files for China,1919-1929.
师生、同学交织而成的学缘关系是凝聚团体的另一条重要纽带。受“《非孝》事件”影响,浙江一师的部分师生汇集到戴季陶主持的《星期评论》编辑部。如陈望道、刘大白、沈仲九等原系该校教师,俞秀松、施存统、周伯棣等是该校学生。栖身于社内的俞秀松、施存统亦以师长礼对待戴季陶、沈玄庐。据俞秀松自述,旅居沪上时他“认识了戴季陶、沈玄庐等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获得“多方面帮助”。⑦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年,第230 页。施存统也说,他在这一时期受到戴季陶的影响较大,称后者是自己“最崇拜的人物”。戴季陶则颇为赏识施存统,支持其留学日本并帮助汇寄每月生活费用。⑧《关于驱逐处分中国人施存统之后日本人的感想》(1921 年12 月29 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147 页。留日期间,施存统仍与戴季陶、邵力子保持联络,继续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经验。
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较多人是以编辑、翻译、记者为职业。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若干宣传刊物为他们提供了工作岗位和交流平台。其中的合作典范当属1919 年6 月创办的《星期评论》。该刊原以宣传三民主义为要,后来转向宣介马克思主义。《星期评论》的思想转向是吸引陈独秀来沪的重要原因。陈独秀有意“联合他们发起组织共产党”。⑨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1927 年1 月4 日),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 年,第313 页。中共的发起者中,有五位是《星期评论》社成员。①五名成员分别是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沈定一、陈望道。编辑部内“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工作氛围与“都极彻底”的思想交流使身处其间者感受到“做人底生趣”。②《杨之华的回忆》(1956 年9 月),《“一大”前后》(2),第26 页。戴季陶离开后,由陈望道接替工作。沈雁冰、李达时常到社内活动,李大钊、陈独秀也为该刊供稿。统计该刊发行期间的文章,由中共早期组织成员撰写的稿件达164 篇,约占总篇数的39.8%。③参见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年,第56-57 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胡汉民任总编辑的《建设》和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与《建设》虽无直接关系,但“也给它写稿”;同时,还通过邵力子的关系把“《觉悟》拉过来”,藉此开展“游击性的战斗”。④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编:《觉悟渔阳里》(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1319 页。
所谓“同道”(common cause),是指近代以来中国人基于对某一共同信崇的公共目标“或对一致行动的渴望”而“自愿地结成组织”的原则之一。由同道关系构成的团体,其内部的志愿性要强于“地缘”与“业缘”。⑤卜正民:《中国社会中的自发组织》,卜正民、傅尧乐编:《国家与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第25,28 页。1920 年,国共主要成员呈现的同道关系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共同兴趣。十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较早采取了对苏俄友好的立场,⑥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年,第34 页。并于1918 年夏主动致信苏俄表达了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的愿望。⑦《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1918 年夏),《孙中山全集》第4 卷,中华书局,1985 年,第500 页。随后,孙中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对外宣称国民党的“基本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⑧《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 年4 月21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94 页。此时的国民党员陈炯明则以更为积极的态度争取苏俄并关注社会主义理论,他公开“对于共产主义予以财力上与精神上之赞助”。⑨《漳州有过激主义传播说》,《申报》,1920 年4 月29 日,第7 版。秘密来华调查的俄共(布)西伯利亚局负责人威廉斯基把陈炯明称为“苏维埃制度的追随者”,陈治下的福建漳州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⑩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党史通讯》1986 年第1 期,第40 页。国民党人主动向陈独秀提议,将“马克思主义大学”和《共产党》月刊等转移到漳州开办。⑪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99 页,第81 页,第76 页。
国民党人倾向苏俄革命的言行引发共产主义者的共鸣。陈独秀与陈炯明“经常通信研讨”社会主义。作为“南陈北李”联络人的张国焘也两次拜访孙中山,并将具体情况向李大钊作了报告。李大钊专门与张国焘讨论了能与孙中山“携手合作到甚么程度”的问题。⑫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99 页,第81 页,第76 页。自1920 年2 月起,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在“同道”基础上与国民党人协同进行实际的政治活动。据英国外交档案记录,李汉俊与孙中山的随从和支持者筹划在上海建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团体和宣传刊物。⑬Bolshevism in the Far East,April 7,1920,FO371/5341,Foreign Offices Files for China,1919-1929.4 月3 日,陈独秀、李汉俊与戴季陶、孙中山的秘书曹亚伯共同出席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⑭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 daily report,July,19,1920,上海市档案馆藏,U1-1-1127。18 日,上海七个工人团体联合筹备纪念“五一”节大会,陈独秀携手国民党人参与组织。⑮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1879—1942)》,重庆出版社,1987 年,第85 页。5 月,张国焘在沪担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理事会总干事。⑯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99 页,第81 页,第76 页。该协会具有国民党背景,由曹亚伯实际控制。⑰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 daily report,July,19,1920,上海市档案馆藏,U1-1-1127。10 月,工商友谊会正式成立,孙中山与陈独秀参加大会。⑱《工商友谊会成立纪》,《申报》,1920 年10 月11 日,第11 版。11 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孙中山带领胡汉民、戴季陶等到会支持,并发表“二小时之久”的演讲,勉励工人“以工会为武器解放自身”。⑲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 daily report,July,19,1920,上海市档案馆藏,U1-1-1127。
经由地缘、学缘、业缘和同道关系构建起的社会网,不仅密切了国共成员的交际往来,也为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依据中国国民党《规约》第三章第十条规定,党部组织设于上海。⑳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上,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第261 页。自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在上海形成一定政治影响力,且握有若干社会资源。在上海租界当局与北京国民政府严密监视共产主义活动之际,陈独秀等人需要借助国民党的关系展开秘密工作。一方面,他们以国民党要人的住宅为掩护,可以“避法帝和中国反动政府的耳目”。比如,陈独秀居住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是柏文蔚的寓所,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所在的霞飞路新渔阳里6 号原是戴季陶的住宅,中共一大则是在李书城的住宅召开。另一方面,由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活动时常遭到巡捕与流氓滋扰,为尽量减少阻碍,张继、柏文蔚等人时常运用其社会关系“出为相助”。①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袁振英研究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年,第441—442 页。陈望道回忆,每当巡捕房干扰出版事宜时,“总是推邵力子”出面解决。②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觉悟渔阳里》下,第1320 页。蔡和森在总结上述情况时说,建党前夕共产主义者与国民党人合作“是有利益的”,“因为他们都有社会地位”。③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文集》下,第815 页。
二、中共早期组织与国民党的合作趋向与思想差异
至迟于1920 年5 月,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抵达上海。在陈独秀介绍下,维经斯基结识了国民党要人戴季陶、邵力子,并多次召集座谈。复经“陈独秀之建议”,维经斯基于当年秋天首次访问孙中山。年底,维经斯基又在陈独秀陪同下南赴广州会见陈炯明。在到沪后近半年时间里,维经斯基并未与同住法租界的孙中山晤谈,直到获悉陈炯明攻粤告捷后才提出面见孙中山的愿望。维经斯基对访孙目的直言不讳:通过孙氏“就有可能认识陈炯明”,以便“就近仔细观察”其辖区建设。④《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109—111 页。维经斯基的言论表明,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未把孙中山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起初,维经斯基承继了其领导者威廉斯基的观点,后者在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的各派力量时也严重忽略了孙中山。⑤参见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党史通讯》1986 年第1 期,第37—42 页。当时,相对熟悉中国局势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在中国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合作对象并非孙氏。⑥《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 页。但在陈独秀的积极推荐下,维经斯基的看法发生改变,并通过陈的帮助与孙氏建立直接关系。正如张国焘评论,维经斯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苏俄使者,是因为他“找着了主要线索”,即会见中国革命的主要人物——陈独秀与孙中山。⑦⑩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119 页,第127 页。维经斯基的目标转向反映了陈独秀对孙中山等人的某种支持与好感。
10 月29 日粤军攻占广州,国民党重建广东根据地,为中共早期组织与国民党转向组织合作提供了政治舞台。在上海时,陈独秀领导的中共早期组织参加了关于粤军击败桂系后“如何组阁的谈判”。谈判的结果是:“陈独秀被列为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未来广州政府成员,将做同国民党的联合工作”。同时,在南方政府新制定的政策与措施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的适用于苏维埃情况的法令”。12 月,陈独秀受国民党人邀请赴广东主持全省教育事业。在12月28 日公布的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中,陈独秀列名“国民教育部长”。⑧《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 年4 月21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 卷,第59—60 页。
对于陈独秀南下任职,以往研究多视为单纯办理教育事业而一笔带过。事实上,陈独秀的南下兼负着发展共产党组织及与国民党合作的双重任务。接受国民党的邀请后,陈独秀有意利用工作便利,在广州建立“像在上海、长沙以及北京那么人数众多”的党组织,在华南创建“巩固的基地”以利共产党的发展。临行前,他向党内同志征询意见,李汉俊、陈望道提出应果断抓住机会,“刻不容缓地利用他的职位,推动广州的新统治者向前迈进”,切不可在“机会面前摇摆不定”。⑨彭述之:《彭述之回忆录: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上),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年,第202 页。陈独秀又致信各地党组织征询意见。李大钊、张国焘回信赞成陈独秀赴任,以便在广州“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⑩陈独秀最终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广州发展“共产主义核心”。①马贵凡译:《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卡拉乔夫同志在中国研究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81 辑,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180 页。随着国民党中央南迁与孙中山到粤履职,陈独秀到广州就职“办理两党联系事宜”。②张朋园,马天纲,陈三井访问:《袁同畴先生口述历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年,第14 页。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沈玄庐、袁振英、李季等也随同赴粤,共同开展“同国民党的联合工作”。
在粤军驱逐桂系军阀以前,广州既无共产党组织,也没有“能在广州做组织工作的人”。③《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22 页。但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共产主义者得以在国民党人的支持下进行公开活动。受陈独秀的影响,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也开始与国民党人合作。④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238 页,第128 页。首先,创办《广东群报》。该报是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报,由陈炯明提供津贴,在当地得以“完全公开出版”。⑤《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 年4 月21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 卷,第60 页;K·B·舍维廖夫:《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 年第2 期,第57 页。国民党员陈雁声、陈秋霖也参与编辑。陈公博称,国共双方合作办报,互不过问各自的政治行动,恰如“君子协定的模样”。⑥陈公博:《寒风集》,地方行政社,1944 年,第204 页。其次,开设广州宣传员养成所。该所由陈公博担任所长,教员多系共产主义者,为中共“吸收新党员”的重要来源。《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提到,宣传员养成所的存在取决于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中共需要“暂时利用这种关系”。第三,开展工人运动。国民党在广州的根基深厚,对工人群众“有着明显的影响”,如果中共与其直接竞争工运领导权,情况要“困难得多”。鉴于此情势,广州党组织制定的策略是“在表面上”维持与国民党人的联系,藉此扩大宣传、组织工人。比如,国民党人与广东的机械、五金工人联系较深,共产主义者便将“建立机械工人和铁路工人俱乐部”作为“组织工人方面的首要任务”,同时也“设法单独组织工会”,“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便在机械工人中形成独立的影响力。⑦《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 册,第22 页。
1921 年上半年,国共双方的合作取得一定成效。然而,陈独秀等人与国民党人之间也矛盾渐生。一方面,陈独秀在广州教育领域施行的举措“迭遭民党之忌”。李季指出,国民党邀请陈独秀南下的“用意只在藉此以资号召,并没有诚意改进教育”,而且广州政府“军用浩繁,无力兼顾教育费”。最终,陈独秀“办事数月,一筹莫展”。⑧李季:《我的生平》,亚东图书馆,1932 年,第252 页。另一方面,此时的中共尚属“草创期”,“力量还很薄弱”,“只能做团结工人的运动”而无法在广东与国民党公开竞争。⑨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1927 年1 月4 日),《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第313 页。而广州党组织试图独立发展工会和领导工人运动,难免在工人群众中与国民党构成紧张的竞争关系。此外,由于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日益尖锐化,“广东显分孙、陈两派”,共产党人依违其间,时常遭受猜疑。⑩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大同书局,1927 年,第15 页。总之,双方在粤期间的关系发展“不算圆满”。⑪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238 页,第128 页。这一不圆满的结果消解了国共进行更进一步的组织合作的可能。
从上海到广州,双方之所以从短暂合作走向矛盾分化,离不开思想立场的根本差异。由于国民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浅程度、哲学基础及所属阶级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对推动中国革命的方式方法与共产主义者存在本质区别。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以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俱有相当之成功”,唯独民生主义“初未努力”,因此,他将“贯彻民生主义”作以为推进的重点,有意借鉴五四时期颇为流行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善民生主义学说。⑫胡汉民:《胡汉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3 年,第57—58 页。国民党的理论家也藉此论证三民主义的合理性。比如,戴季陶是国民党内公认的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有较深研习者,但他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未给予特殊定位,研习与宣传该学说也并非出于信仰。戴季陶自称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去做社会思想的指导”,研究的目的仍是“使人明白三民主义”。⑬《要使人明白三民主义须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工夫》,《星期评论》第3 号,1919 年6 月22 日。于是,当他面临组织身份抉择时,便以“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由,宣布退出筹组共产党的工作,①《“一大”前后》(2),第26 页,第62 页。最终未能完成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
对于戴的退出,共产主义者同样是从思想层面加以分析。蔡和森认为,所谓“同孙中山的关系太深”、“从道德、心理都过不去”都只是表面原因,实际根源在于戴季陶的思想“已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多立足于“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戴季陶主张阶级调和,质疑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理论。②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文集》(下),第810—813 页,第801—802 页。此一思想认识在国民党人中具有普遍性。陈独秀指出,“马格斯底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取革命的行动”,“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③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1921 年1 月15 日),《陈独秀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3 页。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理论并不为国民党的政治思想所能接受。
尽管一些国民党人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学习社会主义著作和俄国革命经验,但对理论及实践的理解却存在各种各样的隔膜。比如,标榜自己是“中国共产派之提倡最先者”的谢英伯,认为“提倡社会主义之法至为简易”,仅需“一二信仰此主义之学者合群为之,当无不成功之理”。④《讲演社会主义纪》,《申报》,1916 年12 月13 日,第11 版。又如在苏俄革命影响下开始阅读《俄国革命记》及《新青年》等书刊的蒋介石,萌发自学俄文、“预备留俄”的计划。不过,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呈现两极化摇摆:有时认为中国需要实行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有时认为中国“缺乏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蒋介石的前后矛盾心理主要是个人经历变化导致的。他在被工人怠慢时,便对实现共产主义“甚抱悲观”,⑤《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 年2 月2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而在受到上海资本家欺压时,他就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忿恨,认为城市资产阶级与乡村绅耆等阶级“须先扫除廓清”。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19 年10 月12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另一方面,国民党人与共产主义者对革命依靠对象及革命方式也有不同选择。1920 至1921 年,国民党人主办的刊物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常有外地学生专程奔赴上海求见国民党的负责人。⑦《杨之华的回忆》(1956 年9 月),《“一大”前后》(2),第26 页。据美国情报人员观察,广州的青年也大都成为国民党的支持者。⑧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20,China,p.479.国民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通过宣传吸引青年学生的目的,但以学生作主要革命力量的观点并不被共产主义者认可。来华考察的苏俄使者指出,在民众“蓄意消极”的情况下,学生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国民党作为“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党”,不能准确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与方法,采取的革命策略也存在“模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在时局影响下,国民党的政策和“革命情绪”经常改变。⑨《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 年4 月21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 卷,第58—59,63 页。蔡和森也指出,国民党在寻求革命的依靠对象时具有较大局限性,它“不知有群众”,对工农力量“丝毫不相信”,采取的革命方式是联合会党、军阀以及发动青年学生实施暗杀。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国民党的政治前途是“危险的”,中国革命在客观上已经需要“无产阶级的政党来指导”。⑩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文集》(下),第810—813 页,第801—802 页。总之,两大群体间的思想与认知差异意味着组织的界限与分化已不可避免。
三、中共一大对国民党的观点争论和政党政策形成
中共创建时期,共产党员的组织身份认同是逐步形成的。党内对于是否容留其他政党或政治团体的成员,有一个态度变化的过程。一大以前,陈独秀等人并不严格限制入党者的政党背景,党内存留国民党员的现象也不鲜见。比如,“以特别方式”吸收了邵力子入党。所谓“特别方式”即跨党。据陈望道回忆,“跨党的办法”是党组织在讨论邵力子入党问题时提出的办法。⑪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觉悟渔阳里》下,第1318 页。邵氏本人也专门解释过党组织之所以批准其“跨党”,着眼点在于他的特殊政治身份。⑫《“一大”前后》(2),第26 页,第62 页。实际上,该时期以跨党方式加入中共的国民党人并不只有邵力子,其人员“规模在10 人以上”。⑬欧阳湘:《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跨党问题》,《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1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8 页。如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林伯渠于1920 年12 月经陈独秀介绍入党。
同时期,异党成员选择退出中共建党,并非出于中共的组织纪律限制。如戴季陶的退出有来自国民党的纪律约束,因为国民党有“党员不得兼入他党”的规约。①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上,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第134,261 页。研究系的张东荪由于不愿脱离原团体以及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党时机未到”,也未再参与组织活动。对于戴、张的退出,共产主义者也没有从组织纪律角度加以分析。直到1921 年共产党人在广州与国民党人的冲突加剧以后,上述情况才发生变化。双方政治思想碰撞及对工运领导权的竞争促使中共进一步增强了自身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身份认同感。作为组织形态初具规模的独立政党,中共对“他者”的排异反应愈加鲜明,最终在党的一大上明确提出拒绝党员跨党的规定。
解决党员组织身份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如何对待国民党的立场问题,成为中共一大的一项重要内容。1921 年7 月,大会在上海召开前夕,由若干代表草拟和审查“党纲政纲草案”作为会议讨论的基础。在商讨草案期间,代表们对于如何评价孙中山、国民党及南方政府问题已经“发生了歧见”。②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138页。此外,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李达等人的回忆也证明了一大文件在会前已经有了草稿。会议正式召开后,对该问题的争论仍未停止。当事人在后来回忆中,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过程有过不同的描述——“小的”、“短时间的”或“严重的争论”、“热烈的讨论”,这些程度各异的描述反映了同一种情况,即代表们对国民党的看法确曾有明显的分野。
广州代表陈公博称,由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的后一部分同时列举了“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的罪恶”,并指出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并不比北方军阀的政府好”,此类评价在会上引发一些代表的反对。他们提出,尽管“国民党的纲领”存在诸多缺陷,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新的趋势”。③陈公博著,韦慕庭编:《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101—102 页。关于如何看待国民党党魁,武汉代表董必武多次发言反对将孙中山视作军阀,他指出“孙中山是革命领袖”。④《包惠僧谈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79 年5 月阅改),西安师专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党史教研室合编:《中共一大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79 年,第118 页。上海代表李汉俊也表示“应当支持孙中山”,甚至提出中共党员可以在孙中山完成革命后参加由他组织的议会。此外,还有一些代表也认同南方政府相较于北京国民政府是“进步点”,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应当“予以支持”。⑤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139—140 页。这些代表与孙中山等人的社会网联结点较为密集,相互之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革命互助活动,因此对后者抱有好感,也属于情理之中。从现实角度出发,中国新生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建立自己的政权”的过程中需要寻求“同盟者”,孙中山显然是比较合适的对象。⑥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3),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69 页。
但另一部分代表提出了相反看法。他们认为,南、北两政府在本质上未见区别,均为“一丘之貉”,“应一律攻击”。⑦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第10 页。包惠僧根据在广州的所见所闻表达了对国民党的不满,认为国、共是“代表两个敌对的阶级”,所以“没有妥协的可能”,对待孙中山应与“对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更严厉些”,否则不能破除其在民众中的“欺骗作用”。他进而提出,中共的政治宣言不应对“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表示丝毫妥协。包惠僧后来提到,他的意见获得很多代表的同意。⑧《“一大”前后》(2),第289、321 页。陈公博也提到,有“多数代表”不赞成给予国民党较高的评价,因为有“很多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所以南方政府应当推翻”。⑨参见陈公博著,韦慕庭编:《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102 页。上海代表李达正是持反对意见者,他在会前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南北各派政党”均“免(不)了鼠窃狗偷”,没有“改造中国底诚意及能力”。⑩《李达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746—747 页。可见,包惠僧的观点在会上并不是孤立的。
关于包惠僧的意见获得多数代表赞成的说法流传较广。⑪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3),第169 页。但是,会上支持该意见的代表究竟是占多数抑或少数?此点尚存疑问。比如,李达的说法就完全相反,他指出反对批评南方政府的人是“多数”。尽管根据现存史料无法还原会上每位代表的具体意见,但仍能判断当时不赞成批判国民党的代表包括哪些人。据陈公博称,其本人正是会上“根本反对”宣言草案中相关提法的一员,他还曾向持有相同意见的李汉俊、周佛海寻求“补救办法”。①陈公博:《寒风集》,第207 页,第207 页。周佛海在1927 年的回忆也表明,他本人确曾“主张应与广东政府合作”。②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第10页。据包惠僧称,不赞同批判意见的还有董必武。③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25 页。董必武本人在多年后的访谈中也指出,“一大”制定的一些决议助长了“关门”政策。④N. Wales,Red Du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40.该材料由李丹阳老师提供。另,本文曾提交“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学术研讨会(2019 年4 月18 日,上海),在修改过程中先后获得李丹阳、田子渝、张静、贺江枫、徐光寿等学者提出宝贵意见。笔者在此一并致谢,但文责自负。侧面印证了他当时的看法。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代表的反对之下,包惠僧所代表的意见“被大会打击”。陈潭秋称,大会最终通过的原则是:中共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政治思想持“批评态度”,但对其“某些进步运动”应当“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来援助”。⑤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1936 年),《“一大”前后》(2),第289 页。该原则确立后,大会须对草案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正。包惠僧称,在会议尚未结束时,似已将宣言草案中批评孙中山及南方政府的“这一段删去了”。⑥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第25 页。李达的回忆也证明,草案中批评南方政府的相关语句最终被“修正”。⑦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 年8 月2 日),《“一大”前后》(2),第13 页。由此,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可以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赞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结论,并作为党的政治纲领要点之一留存。⑧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140 页。
如上所述,部分代表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肯定态度改变了党纲和宣言草案中的内容,受此原因影响,中共一大的宣言最终未公开发表。在部分代表反对下,大会决定将党的宣言发表问题“留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即把问题暂时后移。⑨陈公博著,韦慕庭编:《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102 页。陈公博称,暂不发表宣言是解决部分代表反对批评孙中山及国民党意见的“一个折冲方案”。他回到广州后立即向陈独秀“痛陈利害”,陈独秀经过权衡后决定不发表该宣言。⑩陈公博:《寒风集》,第207 页,第207 页。究其原因,固然有陈独秀本人“早就主张联合民主派反对军阀势力,从来不拒绝与国民党合作,且身体力行”的原因;⑪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77 页。同时,也需要考虑陈独秀、陈公博等人当时正在广州任职。为避免激化国民党人的恶感并维持两党关系,暂时不公开发表该宣言也属于考虑周全之举。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一大制定对待国民党的原则和对待与国民党联合的政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代表们认可孙中山与国民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革命性,并不等于主张与其联合。张国焘称,一大代表们“都主张不与任何政党联合”。⑫K.B.舍维廖夫:《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 年第2 期,第55 页。他们对于国民党是否有能力负担起“民族与民主的革命”任务是“颇有疑问”的。⑬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140 页。因此,最后一天的会议接受了“实际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的提案”中的观点,即“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均应当“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 册,第558 页。大会通过的决议在“对现有政党态度”一项中明确指出,中共“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在革命斗争中“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 册,第8 页。
然而,中共一大决议达成的政党政策与苏俄、共产国际在对待“与国民党联合”问题上所持有的观点并不一致,因此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反对。在讨论宣言草案之时,虽然李汉俊等人不完全同意其中观点,但仍将草案作为会上“讨论的基础”进行了充分的辨析。与此不同的是,马林的态度更见激烈,他对草案中没有明确说明中共支持民族民主革命的具体步骤和现阶段的政治纲领进行了“较严格的批评”。①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137 页。不过,马林未能改变会议已经形成的排斥与国民党联合的观点。因此会后不久,他要求陈独秀及早返沪“讨论国共合作问题”。②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1978年8月12日),《“一大”前后》(2),第377页。
在一大闭幕以前,列宁在批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拒绝议会制斗争形式时阐发的批判“左派幼稚病”的理论与策略,尚未被一大代表们知悉。共产国际二大制定的政策文件也还没有及时、完整地传达到代表们手中。代表们只是根据马林口述和零星的欧洲共产主义刊物约略获悉一些内容,因此在制定政党政策时主要是进行自主探索,最终形成对待其他政党的“关门”政策。③杨阳:《中共一大代表与共产国际代表关系之研究——以张国焘、李汉俊与马林的三者互动为对象》,《苏区研究》2020 年第1 期,第107—108 页。直至1922 年初远东会议后,列宁要求中共与国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合作进而希望国共两党直接合作的指示传入中国,方才引发中共对待国民党政策的变化。
余 论
社会网理论将社会结构视作一张人际关系网,个人或组织是其中的“节点”,人与人的关系则为交叉的“线段”。网络中的行动者既是自主的,也会因为镶嵌于网络中而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④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9—10 页。中共创建时期,发展党员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社会网开展组织动员。正如陈独秀指出,组织是依靠“个人联络感情式的介绍”吸纳党员。⑤《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联席会议记录——关于组织工作及职工运动等问题》(1926 年6 月17 日),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 年4 月—1926 年6 月)》乙2,1989 年,第258 页。一大以后,经过长期的政治教育和组织训练,社会网的凝聚作用被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功能所取代,上级组织构成垂直关系网中新的领导权威,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也逐步取代传统政治文化,树立起党员鲜明的阶级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形成一种全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组织关系。
1920 至1921 年,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与国民党人之间也是通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网进行人际交流、信息交互和思想互动。这一动态过程不仅影响到个人行动,也影响到集体行为与整体性的组织塑造。共产主义者在寻求革命同路人时,自然而然地首先带动社会关系较为密集、空间距离较为接近的国民党人。比较而言,越是处于双方联成的社会网中心、联结“线段”复杂的“节点”,要比处于社会网边缘、联结“线段”稀疏的“节点”,受到的带动和影响越大。1920年底国共之间一度呈现的组织合作倾向,便是社会网强连带作用的体现。
在中共一大上,部分代表多次发言肯定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某种进步性,反对将孙中山与军阀划等号,这一认识既基于对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判断,也离不开传统的人际情感因素,如包惠僧所说是“对孙中山有深厚的感情”的体现。⑥包惠僧著:《包惠僧回忆录》,第374 页。另一方面,大会最终制定了排斥和攻击其他政党的政策,包括排斥国民党。这是代表们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政党政治所得出的结论。综合两个方面,大会确立了辩证地对待国民党的“原则的决定”。这一原则的实践为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安下一个伏笔”,也为“发展广大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运动,种下了一种根基”。⑦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1936 年),《“一大”前后》(2),第289 页。不过,由于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与国民党人在思想观念、政治立场与革命方式上存在的显著异趋,也决定了双方关系发展的曲折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