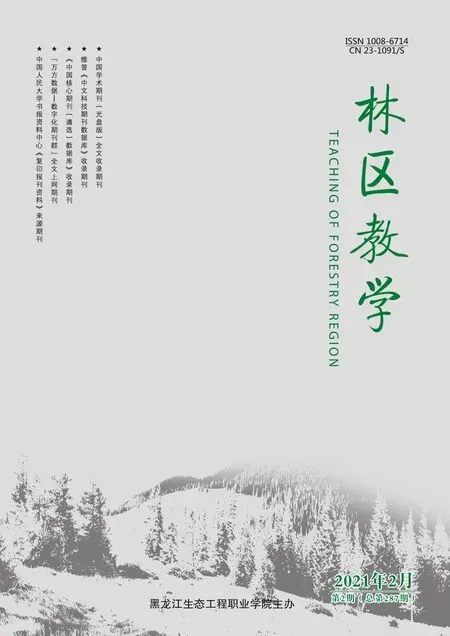《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叙事视角研究
2021-12-28程文强
程文强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引言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1943—)作为当代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而蜚声世界。1992年其短篇小说《索涅奇卡》 为她带来巨大声誉,2001年获得俄罗斯布克奖,2007年、2016年获得大书奖。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女性的命运际遇和情感体验,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坛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长篇小说《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首次被刊登在文学杂志《新世界》上,被称作“家庭小说”。小说讲述了在20世纪近百年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西诺普里家族在美狄娅的守护与引领下不断繁衍及壮大的故事。小说通过家族一员的“我”展开叙述,讲述了大家族中以女性精神象征般存在的美狄娅一代以及年轻一代的生活经历。美狄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克里米亚,她所经历的时代与苏联时期基本重合,家族的“小历史”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农业集体化、斯大林的“民族大迁移”、勃列日涅夫外松内紧“停滞”时代的影响都反映在这个大家族成员的生活中。乌利茨卡娅说:“我的长篇小说《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是一本献给老一代的书,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对家的呼唤。”书中的政权更迭与政策变化夺取了家族中多数男性的生命,美狄娅却以自身的坚强与独立、坚守与忍耐承担着家族的苦难与重任,最终成为家族的守护神。
一、小说的叙事视角
自西方现代小说理论诞生以来,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1]。叙述视角又称作聚焦。学界对视角的界定众说纷纭,20世纪初至今西方叙事理论在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流派的影响下经历了“盛—衰—盛”的发展历程,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叙事理论的兴起,叙述视角问题研究不断得到丰富。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将视角看作是“与读者交流的艺术”,俄罗斯学者乌斯宾斯基更将“视角”问题看作是“结构的核心问题”。
叙事学对叙事视角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对叙述视角的界定向来众说纷纭,戈尔什科夫在《文学修辞学》中认为叙述视角可分为作者视角和讲述人视角,而与作者视角密切相关的是概念即“全知”和“客观化”,而讲述人视角则不同于作者视角,使用第三人称讲述,一般是讲述人自己讲述,多采用第一人称形式(“我”或者“我们”)进行讲述,此外,讲述人同样也可以以第三人称方式出现。作者视角与讲述人视角都存在叙述的主观化问题,主观化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物语言的存在,作者视角或讲述人视角中人物语言(人物视角)的呈现情况导致了视角的转换,构成了不同的叙事布局特色。基于上述理论阐释,结合小说中叙述视角的转换手段分析乌利茨卡娅作品中的审美效果与主题表达。
二、全知视角下的历史演进
乌利茨卡娅小说创作极具个人“气质化的写作风格”。“乌利茨卡娅是当代俄罗斯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大多数小说都以第三人称展开叙述。从叙述者的语言和态度方面来看,作品中的叙述者常常是一个来自日常生活、善于观察又贴近主人公生活,特别是熟悉女性生存状态的讲故事的人。”[2]《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中讲故事的人“我”正是来自这个大家庭又详知家族历史的女性。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主要是一种客观的全知型叙事,以尾声部分出现的“我”增加了文章的真实感,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
作者视角的叙事一般具有全知全能的作用,全知视角“提供全方位的审美感知,注重新奇多变的情节设置。给人以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审美快感”[3]。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偏爱的全知视角,其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能够反映较为广阔复杂的社会历史生活。作家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正是运用全知视角描绘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全知视角在《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中的使用主要体现在背景铺陈以及人物介绍层面。
在小说开篇部分描写美狄娅家族的来历、现状以及美狄娅的生活背景时即采用了全知视角描述:“早在远古时代,这个希腊家族就移民到与古希腊有亲密关系的克里米亚海岸来”“现在,美狄娅是这个家族中最后一个纯血统的人”“迄今为止,美狄娅的后裔们不断来到小镇——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格鲁吉亚人、朝鲜人……”[4]作为描写家族纪事型的小说,全知视角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寥寥数语就从古代写到未来,呈现出宏大的时间维度,美狄娅老一辈与儿女新一辈的故事才能在跨越近百年的政治历史背景下缓缓展开。而乌利茨卡娅笔下的全知型叙事呈现出其独有的特色。
首先,对社会历史、政治背景“轻描淡写”。在家族近百年的生活经历中,重大历史事件仅仅一笔带过,一方面表面虽然看似美狄娅与社会变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总是对政治保持着疏离,因为在她那里“所有政权都一样”,而政权统治时期家族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实际却是个人或家族在社会历史面前的无奈选择;另一方面也使“家庭”“家族”的内涵得到丰富与延伸,家的延续与维系依靠更多的不是外在的社会影响,而是内在的道德坚守、无私的爱与家族精神,是文化传承中独立的、不依附于男性的美狄娅式的女性。
其次,叙事时间呈现非线性化特征。作者并没有采用顺序式的时间叙事,而是对时间点进行了散落式的处理。故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四月中旬”,对于年份的确定只能从美狄娅的信件落款日期寻得踪迹。而故事的发展时间也聚焦在70年代,此时正值美狄娅的晚年,通过她的视角追忆家族人物,回忆亲人过往。正如王加兴所言,“小说的整个叙述时间,自然是逐渐向前推动的。但由于作者与人物主体域的对立,作者的叙述时间就常常被属于人物意识的时间所切断。这样,时间的运动就取决于不同主体域的相互穿插。”[5]例如,文中通过美狄娅在海湾寻得以前丢失的戒指,回忆了与妹妹1946年夏天的战后重逢,进而写到了妹妹年轻时代的生活状况。可见,时间的发展以人物的视角与事件为导向,时间呈现出不断回溯的特点。
三、人物视角主观化手段
人物语言的出现使主观化得以产生,无论是作者视角还是讲述人视角,戈尔什科夫认为在转向人物视角时主要有两类手段:一是语言手段,二是结构手段。视角的转换使得文本从客观的描述转向人物的感知感受,人物视角的运用“可产生短暂的悬念,增加作品的戏剧性”[1]。
1.语言手段
乌氏在全知视角的运用中总是掌握着极强的“分寸感”,体现在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或者说即使知晓一切,却做了很多“限知”的处理。这种对读者的“限知”是从讲述人的视角转向了人物的视角,戈尔什科夫指出词汇手段是客观叙事向叙事主观化转变的重要手段,主要的语言手段有直接引语、非纯直接引语以及内部言语。乌氏在小说中对非纯直接引语的使用既营造了悬疑,又为之后的情节埋下伏笔。例如,“她丈夫是一位快活的犹太人、牙科医生,具有十分突出的小缺点和隐藏得很深的大优点”[4],作者没有继续进行描述,只通过点到为止的方式向读者“卖关子”。很显然,这里的“小缺点”与“大优点”是美狄娅的感受与认知,所谓的缺点其实是丈夫对美狄娅坚守的婚姻出轨与背叛,美狄娅仅用了几天时间就消化了背叛带来的痛苦,继续照顾身患重病不能自理的丈夫。此外,作者在对美狄娅丈夫出轨的描写继续“拖延”,仅以“那件事”“尼卡的额头像极了丈夫的额头”作出提示,这些都是美狄娅视角下的心理感受与所指,利用这种非纯直接引语的方式进行铺垫与伏笔,尽管为读者设置了理解上的“障碍”,却不断激发着读者的阅读与探索兴趣,为读者提供丰富的联想与想象空间。直到丈夫死后美狄娅才知道他的秘密,尼卡是丈夫与妹妹亚历山德拉之女,这对她来讲是一种巨大的打击,她不仅承受了来自丈夫背叛的痛楚,还要面对伦理道德难以越过的心结。通过非纯直接引语的使用将视角从全知型转向人物内心,巧设悬念,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2.结构手段
讲述人视角向人物视角转换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蒙太奇”(монтаж)式手法的使用,“蒙太奇”这一术语来源于电影艺术,但文学中早已存在类似的手法。修辞学家奥金措夫在《篇章修辞学》中指出:蒙太奇的实质在于,它不仅完全符合人物的视点,也与人物的运动相吻合。它既呈现出场景的运动变化,也反映出人物本身的运动过程。人物的视点在空间上发生了位移,由此形成了镜头的转换(如全景镜头、近镜头、特写镜头)[6]。
布托诺夫去基什尼奥夫出差路上的景物描写正是运用了蒙太奇手法。“瓦列里走到了集市。广场地方不大,却挤满了各种车辆和驴骡牛马。头戴暖皮帽,蓄着下垂小胡子的矮个子男人们来回拖着篮子、框子和箱子。”[4]此处作者借用布托诺夫的视角对广场上的人和物进行了镜头般的扫描,随后“他看见了公共汽车瘪进去的后屁股……车是空的,瓦列里坐了上去,几分钟之后司机钻进了驾驶室”[4]。人与物的呈现随着瓦列里的移动而不断发生空间上的转变。除了蒙太奇手法的运用,结构手段的另一种是展示手法,戈尔什科夫认为该手法与陌生化手法相似,都是将日常、寻常事物通过不寻常的、奇怪的方式展现出来。小说中多处使用了这种具有陌生化效果的人物视角,例如布诺托夫说“对不起,演出结束了”[4],将布托诺夫与玛莎的情爱关系隐晦地表达了出来;再如“亚历山德拉自由言谈举止便受着左脚的支配,美狄娅永远无法理解这个不可思议的‘左脚’法则”[4],左脚的支配即轻浮爱情的支配。什克洛夫斯基首次提出“陌生化”的概念,指的是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用新的词语方式表达出来,“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间长度。”[7]玛莎渴望得到灵魂与肉体完美统一契合的爱情,而布诺托夫只是一个注重触觉感知的人,无法理解玛莎的诗歌与内心。在羞耻与失落感中玛莎陷入深深的精神危机,最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小说中对玛莎病症的描写颇具浪漫色彩:“天使出现了。……她聚精会神似乎按了一个电钮——她的身体开始非常缓慢地脱离山峰。山峰也在轻轻地帮她完成这个动作。”[4]最终玛莎“做了一个飞到空中去的体内动作……”[4]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陌生化的手段使用加剧了玛莎死亡的悲剧效果,陌生化作为重要的结构手段在视角转向人物过程中起着唤醒读者新奇感、使人脱离生活麻木状态的作用。
结束语
整部小说采用倒叙的方式,具有强烈的追溯往事的色彩,作者仅在最后一部分出现讲述人“我”而将读者拉回现实,美狄娅的故事发生在过去,但在最后一部分的现实中美狄娅的精神拥有了生生不息的传递,她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象征,家族成员遍布世界各地,但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家,一个以美狄娅精神维系着的家园。乌利茨卡娅在与沙列夫的对话中指出,家庭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写作中关注的焦点,她认为,世界是一个大家庭,人越强大,个体意义越大,就能够将更多的人聚集到身边,这种聚集不一定依靠血缘关系,它可以是邻里或朋友关系。美狄娅正是这样一个强大的人,依靠自身的能量不仅将亲人后代聚集到克里米亚,还将遗产留给了曾遭驱逐的巴维尔一家,令他们重返家园。
“女性写作是多元的,乌利茨卡娅从‘细微的家庭叙事’中剥离出了女性的人生体验,看到了女人在时代巨大变迁中对民族、政治、经济、文化、重建等问题做出的历史回应,找到了女人的历史。”[8]女性自身之美的构建源自乌氏作品中叙述视角与策略的构建:乌氏在其小说中运用了各种不同的视角转换手段,她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来调动读者的鉴赏能动性,使叙事视角呈现出由全知叙事向人物叙事转换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两种视角功能各不相同,小说的主题呈现方式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