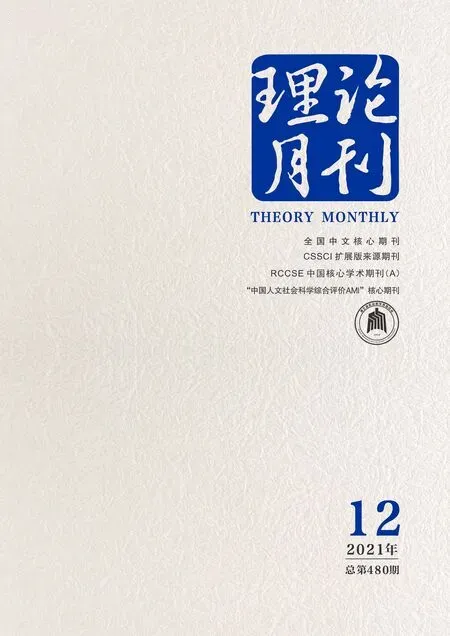新政治经济学的华盛顿学派:理论缘起、核心议题与意义评析
2021-12-28马雪松吴健青
□马雪松,吴健青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中的实证政治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愈益关注制度议题,产出了有别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系列成果。在公共选择理论、演化博弈分析、组织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实证政治理论学者与新制度经济学者形成了当代新政治经济学的身份认同,其中以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为纽带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新政治经济学者扮演关键角色。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张五常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交易费用与分成合同的论述,开启了华盛顿大学交易费用研究的端绪;华盛顿大学的约拉姆·巴泽尔(Yoram Barzel)、基斯·雷福勒(Keith Leffler)、桥本昌典(Masanori Hashimoto)与诺思等学者,对张五常的交易费用理论持续进行修订和补充。20世纪90年代,诺思从交易费用视角阐发新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时指出,他所遵循的华盛顿学派的制度研究路径不同于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组织分析模式[1](p27-28)。事实上,当代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重点命题和主要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诺思制度变迁与过程理性观点的影响,如诱致均衡分析的代表学者肯尼斯·谢普斯勒(Kenneth Shepsle)、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借鉴诺思与巴泽尔关于制度演化和国家功能的认识,权力冲突分析的代表学者杰克·奈特(Jack Knight)在华盛顿大学攻读学位时得到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谢普斯勒、诺思的指导[2](p12)。作为兼具内在凝聚力和广泛影响力的学术群体,华盛顿学派的核心成员包括诺思、张五常、巴泽尔、列维、谢普斯勒、温加斯特、奈特、乔治·米格代尔(Joel Migdal)等任教或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新政治经济学者,与他们学术交往密切的部分新政治经济学者亦可视为扩展意义上的华盛顿学派成员。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在社会科学脉络中吸收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主张与分析方法,探索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产权设置、分成合同等制度议题,推动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国家理论转化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重要内容,对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和学科视野的扩展作出实质贡献。
一、华盛顿学派的理论缘起
华盛顿学派开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与分析视角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影响下的公共选择理论,其演进动力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得益于社会科学脉络中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学理资源,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拓展并深化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分析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历史分析。
第一,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在采取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一般均衡模型方面,与其他新政治经济学者并无明显不同,他们共同受到新政治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这也是华盛顿学派对政治经济现象与制度议题保持长久兴趣的重要原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志在解释人类行为并对政治决策作出全新说明的做法不仅加剧了西方经济学阵营的分化,还促使一部分秉持科学抱负的政治学者为了应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与经济学者共同孕育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3](p8)。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期成果,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行动者视为存在既定偏好、运用可行决策以实现合理目标的策略主体,从经济学视角考察政治问题并关注公共生活中的制度现象。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对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难题的探讨,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对民主原则与民主实践张力的论述,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对个体理性与集体行动悖论的阐释,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对一致同意与宪制规则的分析,都是公共选择理论重视制度研究却没有摆脱新古典经济学影响的突出表现。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主张具有自利动机且掌握充分信息的理性个体是社会生活与市场领域的基本单元,个体行动的聚合可从根本上引发社会变迁[4](p31-32)。华盛顿学派的早期研究成果同样认为权利平等的市场主体在得到保障的约定规范之下开展交易活动,价格机制可以防止产权安排不当所引发的资产缩减与租值消散,这意味着交易活动、契约原则和价格机制的动态稳定实现了市场的均衡状态[5](p35-39)。不无悖论意味的是,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构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导范式和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内核,却由于抽象的理论预设和自负的科学取向而无法使公共选择理论得心应手地处理复杂的制度问题。华盛顿大学的新政治经济学者于是从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以及推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正式形成两个方面凝练了研究意识和身份认同。
第二,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吸取新制度经济学产权分析学派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在认识新古典经济学局限性的基础上回应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并关注现实情境中的人际互动。通过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阿门·阿尔奇安(Armen Alchian)、张五常、诺思之间学术观点的承袭和修正,新制度经济学为华盛顿学派赋予交易费用途径、产权分析意识和历史研究维度。
新制度经济学注意到现实生活中难以确定归属的产权与价格高昂的信息比比皆是,据此质疑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产权清晰与信息完全的假定有违实际,主张围绕产权结构的制度分析有利于理解资源配置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科斯认为,现代企业普遍采用科层制的组织形式的原因在于市场价格机制往往产生难以负担的交易费用,而企业的组织架构和产权的制度结构可有效降低交易费用[6](p386-405)。由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制度和社会成本分析,启发了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研究者重新审视效用、权利、组织等概念,阿尔奇安在其确立的现代产权经济学中关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的内在联系并对科斯的交易费用分析予以拓展。作为阿尔奇安的得意门生和衣钵传人,张五常向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容纳理论意蕴和现实关怀的交易费用分析路径。张五常的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和分成合同研究影响了诺思,两人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协力从事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也被认为是与威廉姆森所代表的组织分析并驾齐驱的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模式[7](p541-565)。在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张五常与诺思的影响下,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以开放包容的理论视野和敏锐独到的务实眼光考察社会科学背景下的政治制度及其经济效应,重视时间进程、文化规范、观念意识对人类选择和制度安排的影响[8](p3-4)。华盛顿学派在经济史和制度史的宏大叙事中着重阐释制度的规制作用并兼顾制度分析的逻辑性和历史性,在长程历史分析与特定情境分析中结合多种现实变量而开拓了制度分析的交叉学科途径。
第三,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广泛汲取社会科学中的演化博弈论与新国家主义研究成果,通过融汇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以及交易费用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
就演化博弈论而言,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从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等注重使用经济理论分析社会制度的研究者那里获取有益养分,采取博弈论工具考察制度生成和制度演化,并在历史情境中分析制度变迁的动因和机理[9](p4-5)。就新国家主义研究而言,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受益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研究成果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复归浪潮,诺思、列维创建的华盛顿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深耕国家理论,探讨国家作为阶级统治暴力工具以及公共政策反映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等实质性问题[10](p213-217)。华盛顿学派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充实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内涵的同时,还带动了实证政治理论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兴起。在实证政治理论方面,以实证主义的经验取向和理论建构意识为指引,华盛顿大学的新政治经济学者强调历史进程、博弈分析、案例数据对于制度研究的重要性。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列维等学者结合历史情境审视公共政策,关注非合作博弈条件下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如何影响政策后果;诺思、温加斯特、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等学者在特定历史场域中运用演化博弈与微观契约分析,为数理逻辑和抽象论证赋予历史素材及现实数据[11](p216-227)。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面,谢普斯勒、温加斯特强调理性选择理论不应忽视行动者的结构环境和组织背景,指出政治科学的新制度主义研究须具备微观基础和均衡模型;两位学者所奠定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经验解释和理论建构中坚持微观视角、演绎方法、理论检验,并在后续发展中吸纳了诺思的经济变迁理论和实证国家理论,从而成为兼容新制度经济学与实证政治理论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重要流派。
早期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为大本营的华盛顿学派主要围绕交易费用理论开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其风格集中体现新制度经济学的典型特征。随着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诺思意识到应从制度的基本原理出发,建立能够解释长期制度变迁及其差异后果的政治经济学模型。1983年,诺思离开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携带新的学术抱负前往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12](p16)。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谢普斯勒、温加斯特、奈特等学者此前不同程度地受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当时正在推动圣路易斯成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学术重镇。诺思从西雅图来到圣路易斯,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华盛顿学派学术阵地与研究重心的转移,此后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群体的政治学意识更加突出,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联结愈益密切。
二、华盛顿学派的核心议题
华盛顿学派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先后关注交易费用、制度与国家等范畴。诺思、巴泽尔、张五常、雷福勒、桥本昌典等学者在交易费用、私有产权与分成合同研究的基石之上,构建制度研究的解释模型并考察国家的经济功能、基本含义与发展特性。
第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热切地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作出释义,一致认为制度安排起到了降低交易费用的突出作用,着重探究私有产权与分成合同这两种制度形式的经济后果。
其一,以张五常、巴泽尔、诺思、雷福勒为代表的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认为科斯对交易费用的理解局限于“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这一抽象层面,既没有充分呈现交易费用的政治经济学意涵,更不利于在现实中发挥分析优势,因而主张从人际交往和产权制度的角度界定交易费用[6](p386-405)。张五常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提出广义的交易费用是“所有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此后更进一步阐释狭义的交易费用指向人际交往成本[13](p1-9)。巴泽尔认识到交易费用与产权密切关联,指出交易费用是“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14](p4)。诺思将交易费用划分为交互性和沟通性两类,并对围绕交易活动所产生的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和人际成本进行具体分析[15](p65-69)。雷福勒认为交易商品的性质和买卖主体共同决定交易费用的特性和程度,因此精准测度交易费用并将其上升至概念层面绝非易事[16](p1060-1087)。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倾向于把交易费用和人际交往联系起来,以此理解制度对行动者互动关系的规制作用。
其二,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认为产权私有化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根本途径,致力于论证产权制度在国家语境中所发挥的经济功能。诺思认为交易活动能够提供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安全环境与经济效益,确定产权的边界是保障交易活动的前提条件与国家理应承担的重要经济功能[17](p17-18)。巴泽尔认为产权处于确立、维护和停滞的动态过程,市场交易者对待产权的态度取决于与之相关的成本收益;当产权设置和长期维护的成本高于产权的预期收益时,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无法界定归属或难以有效维护的公共资产[14](p4)。张五常在其转型国家研究中指出,产权私有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应回避产权问题[18](p110-113)。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倾向于认为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前提是国家设置并维护产权,但他们还强调国家往往是产权制度的破坏者,这种重视成本收益与制度分析的研究取向为新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国家研究提供了产权视角。
其三,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从契约角度探讨分成合同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实际效用。张五常反对分成地租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传统观点,指出地主和农民的分成合同实际上分散了农业生产的风险,从而形成相对稳定且可持续的互惠型农业生产模式[19](p4)。巴泽尔赞成张五常关于分成合同促进农业生产的主张,但他认为分成合同的突出优势不在于规避风险,而是与固定工资、定额地租、独占所有权等形式相比,分成合同更有利于保持农民积极性、农地适度开垦、农业专业化之间的动态平衡。巴泽尔还关注到各类主体按照所占资源参与制定分成合同,而分成合同实际上构成了组织中收益分配的重要依据[14](p83-84)。桥本昌典主张分成合同不仅有助于企业和职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还能够从合理配置资源的角度优化人力资本[20](p475-482)。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倾向于把分成合同看作具有制度形式的契约,重视其在抵御风险与配置收益方面的作用,从而在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提出了以分成合同为核心的制度分析模式。
第二,20世纪80年代前后,制度因素在华盛顿学派的交易费用研究中更多显现身影,众多学者采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复合视角构建制度理论,考察制度的概念、制度变迁的发生机理并构建制度分析框架,还运用现实案例与历史分析对各式理论作出检验。
其一,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探讨制度的内涵与起源,将其视为构建一般性制度理论的前提[8](p242)。诺思认为制度是旨在规制人际交往而人为设计的博弈规则,涵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制度实施,这一界定也被其他新政治经济学者普遍接受[1](p3)。谢普斯勒以此质疑新古典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偏好诱致均衡模型,他主张现实生活的均衡状态更多源于制度因素,并以结构诱致均衡(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的观点强调制度对集体行动施加的结构性影响[21](p27-59)。结构诱致均衡模型认为制度源自外部的强力冲击或内部的自身演化,应当依据具体研究的理论设定和现实情境思考制度起源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即从外衍性和既定性的角度分析制度的影响,从内源性和自发性的角度分析制度的演化[22](p168-169)。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在早期交易费用研究的基础上思索制度问题,以经济学的分析立场关注更具政治学意蕴的现实对象,为此后华盛顿学派融汇新制度经济学、实证政治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综合性研究视野凝练了制度分析的旨趣。
其二,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关注影响制度变迁的诸多经济因素,在权力分析路径中形成了交易费用政治学研究模式。政治科学的制度变迁研究在一般意义上考察原有制度安排的变化和新的均衡状态的产生,新政治经济学强调制度变迁得以发生在于制度的推陈出新符合人们的成本收益预期,技术变革、法规调整、创新成本降低、市场规模扩大则是制度变迁的重要触发条件。华盛顿大学的诺思、列维、温加斯特与不在华盛顿学派之列的特里·莫伊(Terry Moe)、威廉姆森等新政治经济学者,均重视作为政治科学核心范畴的权力,并在制度变迁研究中将权力分析与交易费用、产权界定、分成合同熔为一炉,提出了交易费用政治学的解释逻辑。交易费用政治学认为制度变迁受到经济效率的影响,制度结构下的政治权力关系同样不容忽视,既得利益者的倾向性和占据要津者的抑制力尤其值得研究[23](p761-779)。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的制度变迁分析在保持经济学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容纳政治学视角,凸显了新政治经济学对两个学科的开放态度和兼收并蓄。
其三,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重视一般性的制度理论,使用多种方法对自身命题加以验证。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注重政治与经济的重合性和互动性,关注那些对国家发展施加深远影响的特定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从结构与能动的张力中审视制度的规制性和行动者的能动性。与之相比,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的制度研究更注重揭示一般规律,在实例论据和历史进程两个方面采取恰当方法对理论框架的相关命题作出检验。倚重实例论据的张五常从贩卖桔树的个人经历与个别案例中获得灵感,主张制度理论不可忽视针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力和想象力[24]((p22)。倚重历史进程的诺思等学者从制度经济史的角度将制度置于长时段、跨时空的比较视野中,提出契合制度分析的经济史研究可以提供更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对制度理论的探索,为此后的国家研究奠定了微观的分析视角和长程的历史取向。
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新政治经济学者在交易费用和制度分析的基础上,更为深入地探究国家的经济功能、基本含义和发展特性。
其一,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关注国家以设置产权和汲取赋税为中心的经济功能,从产权、税收、分成合同等方面阐释国家与市场的复杂联系。诺思与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认为遵循效率逻辑的经济组织是近代西方兴起的关键所在,国家可对经济组织的效率产生重大影响[25](p1-8)。诺思的产权理论将制度的经济分析扩展至国家领域,认为国家的产权政策旨在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或统治者收入最大化,因此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性条件,又是经济衰退的结构性根源[17](p20)。列维认为国家的经济功能集中体现为税收政策,其实质是以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与行动者进行利益博弈,在国家强制力和市场有效性的均衡中汲取赋税[26](p7-9)。温加斯特认为国家功能的实际效果与社会成员的普遍期待并不一致,政府与民众共同制定能够自我实施的分成合同有利于缩小这种落差[27](p245-263)。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对国家经济功能的研究兼及政治学与经济学相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国家研究的交易费用分析方式。
其二,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在现实议题的引导下,从国家与行动者的关联角度对国家作出界定。行为主义政治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全盛阶段的尾声见证了国家研究的复归,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则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新国家主义研究成果中寻找依据,在暴力的垄断与运用、合同的协定与实施等方面理解国家。诺思认为国家是通过垄断暴力来控制资源且具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其统治区域反映了国家权力所能到达的边界[17](p21-23)。巴泽尔认为国家是服务于合同实施并拥有终极力量的第三方主体,其管理对象包含合同关系所涉及的全体公民,其疆域即为强制权力所散布的空间范围[28](p22)。列维兼取诺思与巴泽尔的观点,认为国家在垄断暴力、维护财产权、约束社会力量的过程中,形成了集权化和制度化的复杂机构[29](p20)。这些学者虽然设定国家有其经济功能,却主张国家在政策制定方面拥有相对于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主导权;这些学者不但强调国家研究的制度维度,而且重视个体行动者在其中的能动作用[26](p186-187)。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的国家范畴突出了国家与行动者的互动性,还揭示了国家统治和国家施政的相对自主性,在凝练一般性国家理论的同时也预留了承认国家发展差异性的论述空间。
其三,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关注国家发展的共同性和分殊性问题,为国家理论建构与相关案例比较提供较为丰富的素材。新政治经济学曾在一段时期强调发达国家由于先发优势而保持经济繁荣,后发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对先行者只能亦步亦趋。巴泽尔从产权理论和合同理论的角度阐释国家起源和法治历程,尝试将历史脉络和学理逻辑予以统合。诺思在西方国家立场上“诠释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的概念性框架”,尝试概括出国家政治经济演化的普遍规律[30](p258-262)。有别于巴泽尔与诺思的是,华盛顿学派其他新政治经济学者意识到统摄性的国家理论难以容纳众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由此建议正视国别差异和历史情境。在此意义上,奈特认为政治经济制度大多是国内利益团体博弈和妥协的结果,米格代尔认为国家能力往往呈现国内环境和国际格局的实况[31](p1003-1020)。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对国家发展的务实思索以及对相关案例的深入分析,反映了经济学的抽象化、形式化、数理化风格与政治学的实例性、分析性、叙述性风格相互交织。
三、华盛顿学派的意义评析
华盛顿大学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因保留经济人假设和缺少政治学本位立场而受到部分学者批评,但是华盛顿学派对认知科学前沿领域的探索及应用,对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和现实研究成果的关注及吸纳,对经济史研究中案例叙述和因果机制的探究与阐释,能够推进新政治经济学的华盛顿学派的理论发展和方法更新。
第一,将新政治经济学置于社会科学的演进脉络,可以发现华盛顿学派的成就在于促使新制度经济学凝聚制度议题并修订研究方法,并在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织影响下设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
其一,就新制度经济学而言,华盛顿学派把蕴含政治因素的制度分析引入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其中不少学者也被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将新制度经济学定义为聚焦制度范畴、制度互动与组织结构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启发更多经济学者重视制度的生成演化及其政治经济后果[32](p1)。1993年诺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7年巴泽尔获得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终身成就奖,反映了带有华盛顿大学烙印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路径持续产生影响力。与此同时,华盛顿学派主要成员的博弈分析、经济史分析、比较制度分析扩展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诺思认为制度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和引导博弈的规则,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把博弈分析和制度分析结合起来。诺思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辨析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后发优势,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为经济史分析确立了一席之地。深受诺思影响的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指出,政治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未必若合符节,包容性与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组合方式对国家长远发展意义重大[33](p429-430)。
其二,就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而言,华盛顿学派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提供制度研究的视角和素材,不少学者融合了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分析取向。政治科学中以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较早重视制度分析,谢普斯勒、温加斯特等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所从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国家理论研究,则推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成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派别[11](p216-227)。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扮演着重要角色,诺思更被视为联结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人物[34](p50)。列维关于国家税收的研究成果作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国家理论的典型范例,揭示了微观维度、历史进程、个体行动依然是国家研究无法忽略的主题,凸显了理性个体在宏大国家研究中的主体地位[35](p104)。其他同华盛顿大学颇有渊源的新政治经济学者,如贝茨、莫伊、詹姆斯·阿尔特(James Alt)、让·恩斯明格(Jean Ensminger)、诺曼·斯科菲尔德(Norman Schofield)等人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赋予实证政治分析、理性选择分析、比较制度分析的广泛素材。
第二,在承认华盛顿学派为新政治经济学提供发展动力和学理资源的同时,还应看到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假设与交叉学科取向存在明显不足。
其一,华盛顿学派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坚持经济人假设,但其中的理性预设和微观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为相关研究设定限度。经济人假设主张个体决策行为由偏好取向和策略活动所主导,拥有理性算计能力的经济人在本质上类似于依照理性规程而采取行动的自利性傀儡[36](p234)。一方面,华盛顿学派的部分成员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主体简化为缺乏历史背景与文化底蕴的经济人,忽视个体行动者在理性认知和信息处理方面的局限,贬抑人的生活性、实践性和历史性,由此饱受政治学者和行为经济学者的诟病[37](p1577-1600)。另一方面,华盛顿学派的部分成员看待国家及其制度架构时,没有深刻认识到个体微观视角的简单叠加不会呈现社会整体视野,对国家现象和制度安排的广义尺度、复杂状况和历史细节缺少关注,在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的制度议题上难以像历史制度主义那样游刃有余[38](p10-12)。
其二,华盛顿学派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注重学科交叉,但也展示出相对偏重经济学而轻视政治学的倾向。华盛顿学派大体上将经济学解释逻辑应用于政治生活,却较少全面阐述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与经济市场的逐利性这一本质差异。虽然贝茨在热带非洲农业政策研究中发现,许多不符合经济理性的政策安排有着政治上的合理性[39](p5-6),但是大多数新政治经济学者并不重视心理动机、权力关系与经济理性共同作用于个体行为的内在机理。过于倚重经济逻辑导致华盛顿学派低估了政治因素对制度的影响,权力的非对等关系、行为主体的政治策略、关键节点的路径塑造、观念与话语的建构功能因此受到忽视[40](p1-25)。以充分性和前沿性的标准来看,华盛顿学派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石主要是经济学与政治学,尚未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更未足够重视批判经济人假设的认知科学。以独特性和纯粹性的标准来看,过度借鉴来源多样的理论视角可能消解华盛顿学派的新政治经济学特色,降低华盛顿学派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认同意识。
第三,在肯定现有成就和认识当前局限的基础上,华盛顿学派的发展潜力在于借鉴认知科学与国家研究,通过新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分析和细节描述强化解释力。
其一,华盛顿学派的发展潜力端赖于新政治经济学者吸收认知科学的前沿成果,并在现实取向与对话意识方面深化国家研究。一方面,行为经济学者与认知科学研究者主张将抽象的经济人替换为真实的行为人,倡导在个体动机与大脑意识研究中运用心理实验、脑科学实验和神经实验[41](p57-63)。华盛顿学派对经济学动态的追踪以及对人与制度互动关系的关切,使其能够获取行为经济学与认知科学研究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国家的本质和功能以及国家与经济、社会、政治的关系,仍是诺思等老一辈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长期思索而未得其解的难题。华盛顿学派对社会科学脉络中的国家理论以及对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特色的重视,使其能够自觉接受政治学取向的国家研究和制度研究的熏陶[42](p937-947)。国家理论近年来对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探索,以及对国别研究的历史情境、国家繁荣的制度根源、经济分流的制度解释等的考察,均成为华盛顿学派从事国家研究的理论指引。
其二,华盛顿学派的发展潜力蕴含在新政治经济学者对历史分析与细节描述的关注中,并表现为理论建构水平和现实解释效度的提升。一方面,华盛顿学派的新政治经济学者为呈现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和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自觉采取长程历史分析与细致案例分析。格雷夫等经济史学者的演化博弈研究和比较历史研究,通过考察制度演化的自我实施机制而深化关于内生性制度变迁的理论认识[43](p1-36)。列维、温加斯特等实证政治理论学者的分析性叙述(analytic narratives)研究,通过钩稽案例的细枝末节和隐秘环节而推导特殊事件的关键结果[44](p10-11)。另一方面,华盛顿学派的新政治经济学者注意到理论构建与现实情况的张力,相较此前更加留意理论是否得到有效验证。对于实践取向的新政治经济学者而言,不同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是凝练问题意识与酝酿理论创新的潜在资源,权力关系中的政治主体互动和公共政策制定则在供给研究议题的同时检验理论的解释效力[45](p1521-1545)。可以看到,华盛顿学派在社会科学复合脉络下对时序进程和案例细节的强调,能够支起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续航的风帆;华盛顿学派在历史与现实的丰富事例中对真实变量和因果机制的重视,能够擘画新政治经济学经验研究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