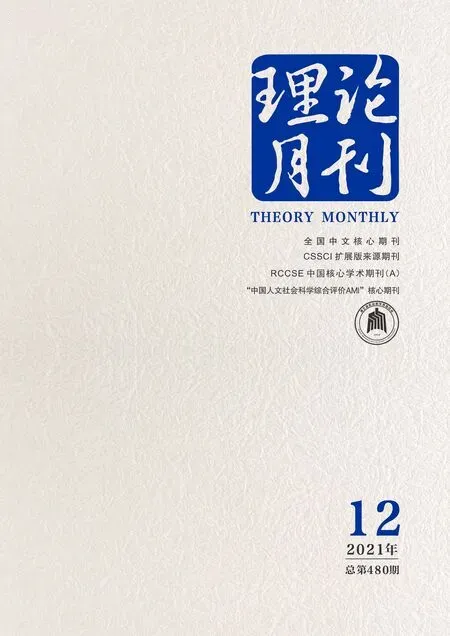隐喻式反讽的哲学思辨
——以利科的隐喻理论为视角
2021-12-28涂天煦李洪儒
□涂天煦,李洪儒
(1.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2.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隐喻式反讽是以隐喻为字面形式的特殊反讽类型,其意义生成机制中具有复杂的冲突性或对立性,其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和评价也极具深刻性和多元性。鉴于隐喻式反讽是以隐喻为形式而呈现的,且法国哲学解释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œur)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隐喻的意义问题,本文拟以利科的隐喻理论为基础,从哲学层面对隐喻式反讽进行探索。
一、相似性与对立性的辩证关系
隐喻的本质特征为事物的相似性,“反讽的本质特征为字面义与隐含义之间的对立性”[1](p239-264)[2](p19),隐喻式反讽意在通过表述事物相似性反向显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隐喻式反讽的显著特征在于其意义表达的辩证性。在哲学上,辩证是一种全面看待问题的眼光,反映的是对事物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关系的认识。莱布尼茨指出,“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意即世界上的事物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相同性。与此同时,世间事物又并非完全彼此隔绝,而是相连、相通的。同类相似的事物之间自然互连互通,不同类、表面上不相似的事物之间,甚至相互对立的事物之间其实亦可相通。世界万物皆归属于一个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就隐喻而言,隐喻中的相似性便存在于不同的事物之中,其所反映的事物相似性是在差异中的相似,“差异是构成隐喻的必要条件之一”[3](p100),与相似性同等重要。隐喻的本质是利用已知或具象的事物去理解未知或抽象的事物,其一般构型可被表述为“A是B”。其中,A为本体,即被解释的事物,B为喻体,是用作解释的事物,系词“是”则将本体与喻体相连,体现了说话人对本体与喻体之间关系的一种认同。在隐喻中,本体与喻体原属于两个完全不同或相距甚远的领域,通过系词“是”将本体与喻体相连体现了说话人对二者相似性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使隐喻具有一种直陈性特征,展示了一种带有创新性的认知思维。事物相似性是隐喻得以成立的基础或前提,这种相似性通常被认为是在客观世界中事先存在的,隐喻只是将各类事先存在的相似性表达出来而已。而在哲学家眼中,隐喻中的事物相似性是人通过观察世界,对事物进行抽象加工所形成的结果,是一种概念性映射。隐喻是认知主体对世间万物的感知,体现的是人的主观思想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一般说来,“事物的相似性可分为物理相似性和心理相似性两类”[4](p127),而当其凭借隐喻得到表现时,这种相似性最终取决于人的认知能力,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如利科所言,隐喻中的相似性不是被简单表达出来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它与说话人的想象力密切相关。正是通过说话人的想象力,两类本相距甚远的事物才可被“看作”具有某种相似性而被放在一起[5](p590)。隐喻中的相似性事实上体现了语义学与心理学的融合。
与隐喻类似,反讽也并非一种装饰性的语言技巧,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不过,不同于隐喻的“类比思维”,反讽是“逆向思维”,且在语义的表达上,反讽同样依赖于人的想象力。只是与隐喻相比,隐喻体现的是“类比联想”,反讽体现的则是“对比联想”。反讽是对客观世界的异化表达,其字面陈述与隐含意义相对立。该辞格显示的不是词语与世界之间的某种简单、直接的不匹配,它同样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反讽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来体现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对立,其最终目的是在各类的矛盾与对立之中寻求一种新的和谐与统一。就隐喻式反讽来说,此类修辞显示出的两个对立事物之间的互连互通便具备两层意义:其一,对立双方的统一和相互依存,没有对立的A方,就没有与之对立的B方;其二,同类相似意义下的相通,即它们均在同样的种属概念之中,以相通为存在的基础。倘若两个事物之间没有相通性而处于相互隔绝的孤立状态中,那么若无同类间的相似性,何来对立和矛盾?也就是说,隐喻与反讽作为两类常见的辞格在各自的表达中均体现出了辩证的特征:隐喻是在差异中建构相似,反讽是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对于隐喻式反讽来说,由于同时展现了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与对立性,其意义表达的辩证性较其他辞格而言便体现得更为深刻。而在其中,事物的相似性和对立性同样处于辩证的关系之中。在隐喻式反讽中,字面上的隐喻意义与真实的反讽意义之间并不呈现为彼此孤立的关系,二者之间通常相互比照、相互映衬,这些不同的意义具备同等作用。隐喻式反讽的魅力或突出的性质在于其因承载着意义的统一体而展现出的整体效应。当隐喻与反讽相融合时,话语意在从隐喻中体现出极度的外延意义,随后又从这种极度的外延意义延伸到反讽中极度的内涵意义,表现为一种意义的连续体。换句话说,隐喻式反讽的特色在于将相似性与对立性并置,这两种性质之间一般呈对照、补充或对立颠覆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隐喻式反讽通过描述相似来展示对立,通过提示矛盾而取得语义平衡,这使得话语获得了一种新的和谐,同时也呈现为一种含有意义、评价和阐释在内的有机结构。隐喻式反讽凸显的是矛盾的统一性,反映了矛盾在各个方面的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隐喻式反讽以不平衡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并以此来反思世界和生活。在此类话语中,意义表达具有调和的特质,它使得对立与斗争变成了次要矛盾,并最终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态势。
二、隐喻式反讽的意义生成机制
意义问题是修辞学与哲学共同关注的主题。隐喻式反讽具有较一般辞格而言更为复杂的意义生成机制。就隐喻来说,意料之外的语词组合可激发出一种惊异感与新奇感。这种惊异感与新奇感印证的是话语中语义层次的某种转移和改变,体现了语言在使用过程中的多义性或歧义性。依照利科的观点,“隐喻在字面上的解释是荒谬的东西,其意义主要源自字面解释与隐喻解释之间的张力。隐喻的解释预设了隐喻在字面上的意义要被摧毁,其目的在于将一种战胜自我的、意外的矛盾转变为有意义的矛盾”[5](p588)。在利科看来,隐喻只有在陈述中才有意义,它是一种瞬间的创造和语义上的更新。在字面上,隐喻将两个相距甚远的事物联结在一起,这构成了一种“范畴错误”。“通过‘范畴错误’,新的语义领域就从新的关系中诞生了”[5](p590),且这种语义领域的出现是和语词的多义性、歧义性以及语境紧密相关的。利科认为,隐喻应以话语为研究范围,而“话语是以句子为基本单位的,句子本身是一种不确定的和无限制的创造,这种创造的基本条件乃是语词内在的多义性”[6](p12)。此外,具有多义性的语词“只有在特定背景下的特定的上下文和听众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实际的意义”[6](p13),也就是说,“一词多义的理论为隐喻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准备,但词义还需通过特殊的语境关联动作来实现,并获得我们所说的确定意义”[6](p173-174)。因此,隐喻中的意义不是字词本身的意义,而是语境创造的意义。在陈述中,通过语境和说话人想象力的作用,字词的其他意义均被排除,在此情况下,“单义性的话语才能从多义性的字词中产生出来”[6](p13),隐喻也由此成为一种语言学的创造。换句话说,利科关注的隐喻乃是一种“活的隐喻”,在他看来,“活的隐喻”具有“事件”与“意义”两个处于辩证关系中的特征。“事件”与“意义”的辩证关系指隐喻的效果只存在于某种单独的语境之中,隐喻既是有意义的事件,也是语言中所突现的意义[6](p179)。而依照利科的观点,当隐喻本身被用以呈现反讽之意时,它同样表现为一种独立的事件以及意义上的更新。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手段也具有独特的表意方式,其要旨是通过话语的字面意义间接表达出说话人的实际用意。反讽事实上是将两类处于同一范畴下的对立意义置于同一话语之中,其意义的实现同样受制于语境。在反讽话语中,字面意义与交际语境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将引导听者跨越字面意义所处的心理空间,转而探求与字面意义相对的话语的隐含意义。这种隐含意义是仅存于此时此地的情境之中的,它代表了多义词的种种可能性的实现。如利科所言,“语词的多义性离不开语境的影响,语境的意义就是筛选适当的意义变种并用多义性的语词去形成各种话语,这些话语被看作是相对单义的,它仅仅提供一种解释,即说话者有意赋予这些语词的解释”[7](p158)。由此可知,隐喻式反讽的意义同样产生于字面意义解释与隐含意义解释之间的张力,是话语体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的有机整体。其中,说话人表达的最为深刻的反讽无损于字面隐喻的外延作用,反讽的含义也是经由对隐喻意义的解释才彰显出来的。换句话说,隐喻的一般构型为“A是B”,隐喻式反讽的一般构型则为“A是¬B”。在隐喻式反讽中,说话人作为认知主体通过字面表述逐步导引出隐喻的复杂含义,继而在物理语境和心理语境的辐射中制造话语的深层意蕴,使听话人在相似中发现对立,在对立中发现相通,最终借此达成话语意义奇妙的转换平衡。例如:某学生甲因答对了一道难度系数并不高的考题而沾沾自喜,这时学生乙对他说道:“你可真是我们班的爱因斯坦啊。”在此例中,学生乙将学生甲称作“班里的爱因斯坦”,从字面上看,前者的用意当然不是说学生甲与我们所熟知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是同一个人。将某人称作爱因斯坦,其含义是指此人与爱因斯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即头脑聪明或解决了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难题。但在此例中,学生甲所解决的考题难度系数并不高,而且该生竟还为此沾沾自喜。因此该情境表明,学生乙并不是要对学生甲表达赞叹,其话语的真实意义与字面意义是相对立的。学生乙话语的真实意义为“答对了这道题并不能证明你很聪明”,也就是说,“你并不是我们班的爱因斯坦”。在班级生活中,同学们之间进行竞争应尽量避免直接的言语冲突,因此学生乙便用隐喻式反讽的方式委婉地向学生甲道出了自身批评之意,且与一般的反讽相比,此类反讽的交际效果通常更为突出。
从此例中不难看出隐喻式陈述在语境中发生了明显的意义扭曲,反讽随之产生。从命题形式来看,隐喻式反讽的存在基础是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异性,这两者之间的距离越远,产生的张力越强。隐喻的意义具有开放性,而隐喻式反讽的意义则更加受制于语境,具有特定指向。在理解隐喻式反讽时,语境因素或隐或现,我们要思索的并非喻体对本体的说明方式,而是当两者并置、相互对照、相互映射时产生了什么样的复杂含义。隐喻式反讽使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从事物的差异中看到相似,又在相似中感受到差异和对立,其所体现的主客观互动过程更为复杂。隐喻的映射具有多点、多源的特征,其方向也并非单一地由具体域向抽象域映射,而是呈散射状。然而,在此类表达方式中,说话人对相似性的使用不能随心所欲、凭空想象,隐喻中的主客观互动要以一定的物理和心理特质为基础。隐喻是弱化差异,凸显相似;而反讽是弱化相似,凸显差异。用隐喻作为命题形式,此类反讽话语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其中的“对立”以共同的意义为前提,没有“相似”与“相同”,也就无所谓“相异”与“相反”。
三、隐喻式反讽与现实世界
隐喻式反讽以一种特殊方式揭示了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就隐喻而言,隐喻的发出者审视世界,捕捉事物表象中的相似之处,挖掘事物内在的属性,并对这些属性所凸显的多种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抽象加工,从而获得对于事物的认知。在利科看来,隐喻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隐喻所具有的指称功能。利科认为,任何陈述都能区分出意义与指称两个维度。其中,“意义是陈述所表达的内容,指称则是陈述所表达的相关对象。陈述所表达的内容是内在于陈述自身的,而它所涉及的对象则超出于语言之外”[5](p591)。受指称功能的影响,隐喻自然会在其陈述中通过语义上的更新而指向自身之外的人的世界。也就是说,隐喻是贴近于现实的,只不过它是以一种较为曲折的方式贴近于现实而已。事实上,通过建构事物间的相似性,隐喻实现了对于现实世界的重新描述。借助于隐喻,个体可形成对世界意义的全然不同的新的解释。为此,利科提出了隐喻的二级指称这一说法。在他看来,“隐喻的意义包括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隐喻的指称也相应分为字面指称和隐含指称”[7](p304)。隐喻之所以能够重新描述现实,其原因便在于隐喻悬置了字面指称而使得隐含指称发挥作用。除此之外,依照利科对话语所作的分析,话语在指向世界的同时也指向了说话人与听话人两方[8](p12-14)。利科认为,话语是对语言的使用,“语言没有主体,但话语却通过一套复杂的指示物如人称代词而反过来指示出它的说话者,且作为一种信息的交换,在话语中除说话人之外还有一个其他的人,另一个人,一个它面对的谈话者”[6](p136)。这便表明,话语体现了主体的意向,它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其中表达自身在世存在的种种经验与意义。借助话语,主体能够言说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且在话语交流中交际双方还可在面向世界的同时表达自身或进行自我理解。在此基础上,既然隐喻是以话语为研究范围的,那么隐喻所展示的便是人类可以拥有的新的生存可能性。利科指出,隐喻在悬置了字面上的指称后实际上开启了一个新的可能世界,这是一个个体可以居住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个体可将自身生存的种种可能性投射于其中,从而实现对于现实世界的种种重新理解。由此可知,在利科的哲学研究中,隐喻其实同时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两个层面上的意义。通过重新描述现实,隐喻可使个体在完成对世界认识的同时也对自身的生存或存在进行更好的理解与筹划。借助隐喻,个体在理解世界意义的同时也反向了解了自身,所谓现实世界其实应当通过观照人之自身存在的方式而被理解。以利科的观点为基础,当隐喻被用以呈现反讽之意时,此类表达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可被表述为通过对隐喻指称方向的明显调整来强调某一事实的真实性。反讽实际上是个否定性的概念,它意味着从对立的视角出发达到对某一事物的另一层面的认识。在反讽者眼中,世界万物的意义皆具有不确定性,各类对立最终都可进入相互转换的游戏之中。面对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反讽者认为人们均应当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识别其中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对世界意义的理解从来都不存在一种唯一、确定的方向,所以唯有不断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真理才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更加充分的揭示。此外,反讽体现的意义之不确定性其实反映的是不同主体对世界的不同理解,而从利科的观点看来,理解并非一种认识的方法,而是作为此在的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就各类意义的理解来说,这种理解始终是和主体自身的生存状态或方式密切相关的。因此,反讽显示出的不同主体对世界的不同理解其实源于各主体所具有的存在方式。这表明,反讽同样是对世界的一种创造性的再描述,它消除了主客体之间的矛盾与隔阂,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彰显。因此,隐喻式反讽实际上也同样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两个层面上的意义。通过建立一种似“是”实“非”的表达方式,此类反讽其实兼具对于现实世界的建构与解构,它在话语的显性层面上通过隐喻悬置了交往双方感知世界过程中的直接指称,随后又在隐性层面上调整了自身指向,并最终以他者的眼光向说话人与听话人展示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式或新理念。通过掩饰隐喻指称的真实性,隐喻式反讽扬弃了客体带给主体的种种束缚,使主体进入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自由空间。在这个自由空间中,主体可通过自我反思表达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以一种诗意化和浪漫化的眼光重新感受现实。通过隐喻式反讽,人与世界之间的指称关系可得到重新调整,人对自身的存在方式亦将拥有更深刻的理解。例如,2020年11月,《四川日报》曾刊登了一篇题为《冷空气年底“冲绩效”?四川下半年来最冷一天本周到货!》的报道。在报道中,记者指出在11月底及12月初成都已出现明显的雨雪天气,且接下来该地区的气温还将持续降低。在未来一周的时间内,成都或将迎来2020年下半年以来最冷的一天。
此例中,“冷空气”像人一样要“冲绩效”,而“到货”则将“冷空气”看作已预订的商品,作者运用隐喻的方式陈述了未来成都天气的变化趋势,即成都在未来一周的时间之内或将迎来2020年下半年以来最冷的一天。然而,“冲绩效”和“到货”等字面形式通常传递出的情感是令人振奋的,它一般意味着其陈述的事实令人期待。但在此例中,作者的实际用意即希望读者注意防寒保暖,并未被直接道出。因此,此则报道运用了隐喻式反讽这类特殊的修辞方式。从此例中,人们不难体会到隐喻式反讽包含着双重张力:一方面,隐喻表现了对于现实世界的虚构;另一方面,反讽则从新的角度出发以一种委婉的方式表明了对于现实的态度。而就该新闻标题的形成来说,“冲绩效”和“到货”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常用的言语表达,以之形容冷空气的降临是人们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并且,面对冷空气的到来应当注意防寒保暖,这是人们的基本生存经验。因此,之所以“冲绩效”和“到货”可被用以描述天气变化并同时提醒人们采取相应措施,这取决于人们所经历的生活内容或人们所具有的存在方式。由此例可看出,隐喻的指称功能使现实世界在人们的认识之中获得了一种表象之外的升华。而在此基础上,当隐喻本身被用以呈现反讽之意时,反讽又在其后修正了指称的方向,使话语指向一种独立而又有待求证的真实。也就是说,隐喻式反讽通过调整隐喻指称的方向而间接道出了世界中的真实,在此类修辞方式的影响下,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可得到全然不同的表述,人自身所具有的存在方式也将得到更为直观的诠释。
事实上,利科等哲学解释学家所要阐明的是:对世界的真实性看法其实取决于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所谓世界的真实乃是人类自身存在中的真实。此外,人对世界的把握最终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语言是连接人与世界的中介。李洪儒亦指出,“语言完全是以人为中心的”[9](p48)。所谓的现实世界其实是在语言之中的人的世界。因此,就隐喻式反讽而言,此类修辞方式便证明语言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镜像反映,由于语言与人相连,人类必定会在语言中留下自身认知或自身理解的痕迹。通过隐喻式反讽,个体可以重新调整对于世界的态度或眼光,这标志着主体性的觉醒,也印证了所谓世界的意义不过是主体间性角度下人类语言中的意义而已。而就语言与世界之间的指称关系来说,隐喻式反讽表明语言与所指称的事物之间也不存在恒定不变或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于同样一种事物,人们可以运用多种不同的指称来表述。也就是说,语言与世界之间的指称关系其实也是人类自身认知的结果,在利用语言指向世界中的万物时,人类也通过语言指向了自己,语言中的指称功能连接的是人与世界两方。隐喻式反讽通过调整其指称的方向表现出了现实中的真实,其所展现的指称灵活性是人类通过语言而认识世界的必然结果,它在描述世界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
四、结语
在隐喻式反讽中,事物的相似性与对立性呈辩证的关系,且相似性是形式上的诉求,在其背后说话人的实际用意与隐喻意义通常呈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才是隐喻式反讽的本质或最终导向。隐喻式反讽的意义生成依赖于语境的影响,在语境的作用下,其意义表达中的多重矛盾与冲突可得到一种调和与统一,说话人的实际用意是通过字面上的隐喻意义而以间接的方式透露出来的。除此之外,隐喻式反讽的哲学思辨还涉及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此类修辞方式证明,所谓世界的真实其实是通过人类自身的语言而向人类显现出来的,通过隐喻式反讽,世界的意义将得到全新的描述,人对自身的存在方式亦将拥有更为深入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