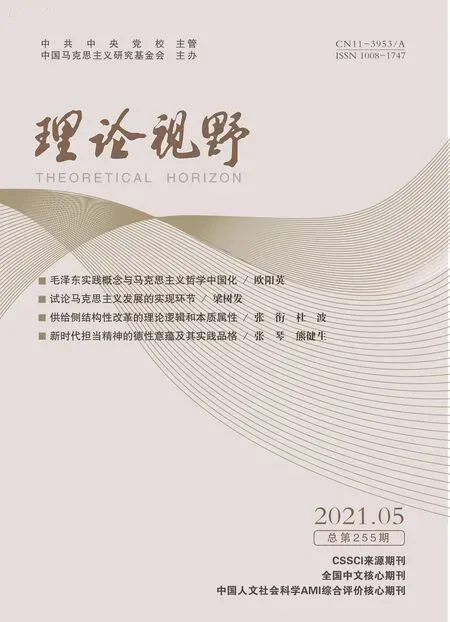国外学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2021-12-27郑国玉
■郑国玉
【提 要】许多国外学者注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次理论创新都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理论根基扎实,受民众欢迎。但也还有另外一些国外学者没能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吸纳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元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应重视认识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讲好中国的故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全世界关注,也让许多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国外学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他们试图从后者之中找到前者的力量之源,找到前者长盛不衰的原因。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代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一些国外学者所关注。有的从政治学理论角度解读;有的从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解读;还有人从苏共的理论剖析;……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也不同,甚至截然相反。[1]在这些国外学者中,有的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解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列昂季耶 维 奇·季 塔 连 科 (Михаил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认为,邓小平在将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积极采用中国传统儒家的社会伦理思想,如关于信任和上下级之间的相互责任、尊敬长者、关心人民生活的重要性、纪律性、正义性等,来充实其理论。他甚至认为,邓小平把改革的近期目标——实现中等程度的富裕——称为“小康”,也用的是儒家的术语。[2]季塔连科在谈到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相似之点时强调,毛和邓都相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不断更替,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因为这种愿望是与传统儒家的社会理想以及孙中山关于“大同社会”的设想一致的。季塔连科进而断言,邓小平理论能够凝聚和动员中国各阶层的民众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共同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贡献力量。邓小平曾说过,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标准不适用于中国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造成了人们不能接受分权原则,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是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季塔连科对此表示认同,认为这是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的明智选择。[3]
一些美国学者也注意到了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芝加哥大学教授张大卫(David W.Chang)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不易撼动,西方的价值观改变不了它,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改变它,所以邓小平才创立并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张大卫分析道:“当代中国的改革似乎也不能在本质上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是几千年来发展的结果,西方的价值观,马克思的或非马克思的则只是在20世纪才进入中国,这个事实也许是邓小平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4]张大卫看到,中国曾经试图按苏联模式创立共产主义国家没有成功,二战后台湾的西式政治体制也没能影响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的地位。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外来的思想理论体系要在中国生根发芽,被中国的老百姓所接受,都必须满足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否则,无论这一思想本身是多么精深和有价值,在中国都没有发展前途;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互相融合,彼此促进,因而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迅猛发展。张大卫由此推断说:“任何形式的现代化都必须承认一个国家的历史遗产,这份遗产是一种有价值的经验和有力的影响。”[5]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于邓小平理论的特征和属性,除了从中华民族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进行分析,更多地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在他看来,邓小平支持并在中国农村积极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大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中国农民的大力支持和响应,是因为这一政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治国策”相契合。他说:“所谓‘治国策’就是怎样组织农民,改善他们的福利并富强国家。中国统治阶级有史以来世世代代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合同在半商业化的农业中最有刺激力,因而有利于生产。魏源和其他一些早期的‘治国策’学者,毫无疑问是理解和肯定这些组织农民群众的新方法的。”[6]
也有国外学者并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契合因而为后者的提出和推行奠定了很好的群众基础,而是认为这两者之间互相冲突,前者导致后者必然失败。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苏珊·奥格登(Susan Ogden)就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她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各有一套价值观,三者之间互相矛盾,常常冲突,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很长时间力图平衡这三者的关系,希翼同时满足这三套价值观的要求,结果屡次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却始终没能制定出能够取得成功的政策。苏珊·奥格登断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与习俗,使许多社会主义的政策注定要失败。”[7]她由此认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要取得经济上的发展,必须重新界定社会主义,不强求同时践行三套不同的价值观,才能冲破藩篱,打开困局,在她看来,邓小平理论正是这一尝试的结果。
一些国外学者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邓小平理论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的事实。的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正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吸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元素,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因时因地制宜,加以了一定改造,既赋予了其契合时代要求的全新内容,又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民众的传统价值观、习俗与思想基础的新理论。这样一来,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互促进、彼此融合,前者的传承为后者的巩固筑牢防线,后者的建立为前者的弘扬提供制度保障。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民众自上而下乐见其成的事情。遗憾的是,有的国外学者没能正确地看待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却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无限放大,得出两者的矛盾不可调和这样的荒谬结论,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思想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思想时,一些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源与流的关系。前文提到的俄罗斯的季塔连科在评价十七大报告的内容时说:“十七大报告为如何把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及与国外优秀文化相结合的问题给出了部分答案,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8]应该说,季塔连科的观察是比较敏锐的。俄罗斯另一学者诺马洛夫(A.B.Помаиов)认为,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思想,同中国特有的民族传统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表达了中国亘古以来睦邻友好的祈愿以及构建繁荣昌盛的和谐社会的追求,对于论证中国的对外政策更有说服力,因而对于解决中国面临的内外问题更有利。[9]
德国埃森-杜伊斯堡大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对胡锦涛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渊源很感兴趣,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思想的联系,并试图从前者溯源后者。他认为,中国倡导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儒家“大同”理想社会的一种复归,是一种以社会平等和政治和谐为特征的社会。托马斯·海贝勒进而指出,相比抽象的遥远的“共产主义”,中共目前倡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更实际,更容易实现。[10]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罗西塔·德利斯(Rosita Dellios)也认为,和谐社会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复归,她甚至还公开表达了对儒家治理方式的接受与希翼。德利斯在她的文章中写道:“21世纪随着国际上对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政策的接纳,儒家价值观也进入国际社会。儒家治理将是目前世界四种治理方式——霸权治理、联合国体制、欧洲联盟的模式、国际化的全球治理——之外的第五种治理方式。”[11]在麦斯威尔空军基地战略中心的约翰·P.吉斯二世(John P.GeisⅡ)与布莱恩·霍尔特(Blaine Holt)眼里,复归儒家思想甚至是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思想与邓小平以及江泽民治国理念的最大区别。他俩在其合著的《和谐社会:新中国的崛起》一文中说:“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也被称为和谐社会,与邓小平、江泽民一样追求经济繁荣。然而,胡锦涛试图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控制经济增长。他的方式与儒家思想比较一致。”[12]
不过,也有一些国外学者不认同“和谐社会”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复归的观点。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爱丽丝·莱曼·米勒(Alice L.Miller)就是反对者之一。她反驳说:“尽管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共对儒家思想的复兴,但无论从价值观还是从内涵来看,二者都几乎没有共同之处。”[13]米勒的判断无疑是错误的,她不仅没能对“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做出正确解读,甚至还滑向了又一更加荒谬的错误方向,竟认为“和谐社会”思想与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关于“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规范”相似。[14]从苏联的党章中寻找“和谐社会”思想渊源的作法毫无可取之处。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哈克·何必(Heike Holbig)不同意“学习苏联说”。在他看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被具体描绘为“民主法治、公正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说明“和谐社会”思想与苏联家长式的管理模式不是一回事,前者更接近于现代工业国家“开明”的治理风格。[15]何必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从上文我们看出,一些国外学者对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评价是比较准确的,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思想吸纳了中国传统儒家追求“大同”社会,祈愿国内民众和谐相处、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他们也意识到,正是因为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契合性,或者说,前者从后者中汲取养分的事实,才使得前者的理论根基更加稳固,更为中国民众所接受。不过可惜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看出了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思想中的某些治国理念来自中国传统儒家,但却没能看出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部分养分。对此,美国银行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批评他们说:“西方很多评论家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间有矛盾,提法不一样……(他们)不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即中国已经经历了加速发展,在不同阶段上有不同需求。”[16]库恩的批评显然找准了要害。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
国外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溯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趋势,在习近平执政以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与习近平相比以往的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更多地谈及儒家文化有关。2014年3月底,习近平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柏林的科尔伯基金会发表了演讲。阿拉伯国家联盟驻中国办事处前主任阿卜杜勒·瓦哈卜·萨基特(Abdul Wahab Saket)评价说:“习近平的演讲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和谐共存的理念,……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中国实现了稳定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17]同年9月,海峡两岸首届联合祭孔大典在福州文庙隆重举行,习近平亲自致信祝贺。对此,美国《世界日报》刊文称:“习近平一再为传统文化撑腰,不仅是其个人喜好,更是在树立‘三个自信’的历史文化基础。”[18]同年12月,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撰写的书评中写道:“习近平主席对儒家思想的阐释,显示出中国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在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国,国家的凝聚力至关重要。但寄希望于民族主义会反受其累,因为这很可能引发并非本意的危机甚至战争,而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中华文明更能提振中国人的自信和自觉。”[19]这些学者的观察是比较细致的,评价也比较中肯。
在谈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国外学者最常做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溯源“中国梦”。他们认为,“中国梦”具有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特别是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大同思想”有着密切关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柯岚安(William A.Callahan)在他的《历史、传统与中国梦:世界大同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中,论述了“中国梦”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的统一关系。他认为:“中国梦的目标是团结世界上其他国家构建大同世界。”柯岚安进而指出,在“大同世界”的价值理念下,中国梦不仅与亚洲梦、欧洲梦、非洲梦等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而且是一个对中国、对亚洲、对世界都好的梦想。[20]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列奥纳德·贝列罗莫夫(ЛеонардСергеевичПереломов)认为,“中国梦”不仅体现了儒家的“大同世界”理念,并且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在了一起。他评论道:“从小康社会到世界大同,中国当代的决策者们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治国理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理论和奋斗目标——中国梦。它是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话语表达,也是‘先国后己’传统文化的现实体现,致力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把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融合在一起。”[21]
说到从儒家思想解读“中国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Yury Tavrovskiy)是一位值得重视的学者。他是俄罗斯撰写关于习近平的著作的首位学者。他在其《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一书中说:“习近平很推崇孔子及其学说。……这一点可以从习近平系列讲话中旁征博引《论语》及其他儒家经典语句得到说明。……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体系,习近平将儒学价值观一一列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充满着儒家思想的精神。”[22]在该书中,塔夫罗夫斯基还记录了他对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俄罗斯孔子基金会主席列·谢·彼列洛莫夫的采访实录。后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等理念都是源自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对历代中国人的世界观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从‘中国梦’这一概念中、从习近平经常引用的先师名言中强烈意识到,他致力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把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融合在一起。……在我看来,中国正在建设儒学的社会主义。”[23]这两个俄罗斯学者看到了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看到了“中国梦”中蕴含的一部分儒家思想,也看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他们的结论是比较中肯的。
有一些国外学者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溯源“中国梦”,而是从中国近代文化与革命传统溯源“中国梦”。俄罗斯知名政论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中国梦”的渊源不是儒家学说而是“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梦”的共同目的都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复兴。他说:“‘中国梦’思想不是来源于儒家学说,而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旨在复兴中华民族,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种民族复兴的思想在中国非常流行。”[24]美国迈阿密大学副教授斯蒂芬·哈尔西(Stephen R.Halsey)的观点与塔夫罗夫斯基非常类似。他也认为“中国梦”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理想的继承。他写道:“从1850年开始,追寻民族富强一直是中国革命家和政治人物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显然是对这一目标的时代继承。”[25]这种观点是有局限性的,这些国外学者不明白“中国梦”与“三民主义”的思想源流之一都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当然,不是所有的国外学者都认为“中国梦”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古代或近代的传统文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梦”脱离了这一根基。华东师范大学美籍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Josef Gregory Mahoney)就是这样的学者,他表达了对传统文化未与中国经济同步发展因而“中国梦”难以实现的担忧。马奥尼“杞人忧天”地指出,“中国梦”的实现要同经济增长率下降、政治腐败现象、后现代主义以及西方文明的影响等因素相抗衡,中国虽注重加强经济建设,但与传统文化道德已经凸显脱节,因此来之不易的成果易受到损失。[26]马奥尼的观点值得商榷,但他表达的担忧值得我们警醒。他在善意地提醒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重视基于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从上面这些国外学者的论述中我们看出,相比之前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解读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思想,虽然他们还是从传统文化角度,也主要还是从儒家学说中去找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但理解的偏差度却明显减少了。他们中的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多地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了新的高度,使得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事实。在看待“中国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一些学者甚至还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理想的世界意义与价值。这说明,随着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来越多的了解与研究,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理解也渐趋客观。这是一种可喜的转变。但是,一些国外学者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与中国近代文化与革命传统分割,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的“中国梦”思想是源于后者而非前者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建设繁荣昌盛的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际上是中国一代代人长久以来共同的追求与热望,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渊源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
结语
不管怎样,国外学者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讨与研究,不论观点正确与否,客观上都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有助于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
注释
[1]梁怡:《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学习出版社2014版,第439页。
[2]ЖигулёваВ.Ценоваяполитикакакинструмент переходпкрыночнойзкономикевкитае\Пробпемы дапънеговостока,2001,No4,5.
[3]【俄】М.Л.季塔连科:《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6期。
[4][5]【美】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喻晓译,法律出版社1991版,第13页;第14页。
[6]【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版,第327~328页。
[7]【美】苏珊·奥格登:《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
[8]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пика: политика,экономика,культура2007,M.,2008.
[9]Ломанов А.В. Подъём Китая-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глобалънойирегионалънойстабилъности,Москва,XXI,Рубежи,2007.С.29-30.
[10]Thomas Heberer& Gunter Schubert,"Political Reform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Asian99(April 2006).
[11]Rosita Dellios,"China's Harmonious World(Hexie Shijie)Policy Perspective:How Confucian Values are Enter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Conference Paper for 2560thAnniversary Conference and the Fourth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Association,Beijing,PRC,September 2009.
[12]John P.GeisⅡ&Blaine Holt,"Harmonious Society:Rise of the New China",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Winter,2009.
[13][14]Alice L.Miller,"Hu Jintao and the Sixth Plenum",China Leadership Monitor,No.20,Winter 2007.
[15]Heike Holbig,"Ideological Reform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China:Challenges in the Post-Jiang Era",March 2006.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909186<
[16]【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吕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版,第143页。
[17][18]柯岩:《他的文化视野甚为宽阔》,《学习时报》2015年12月31日。
[19]常雪梅、程宏毅:《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有感》,《人民日报》2014年12月4日。
[20]William A.Callahan,"History,Tradition and the China Dream: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the World of Great Harmon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4,No.96,2015,pp.1-19.
[21]【俄】列奥纳德·贝列罗莫夫《让世界理解中国梦》,《人民日报》2014年2月10日。
[22][23]【俄】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习近平:正圆中国梦》,埃克斯莫出版社2015版,第104页;第58页。
[24]【俄】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中国梦凝聚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学习时报》2016年2月18日。
[25]【美】斯蒂芬·哈尔西:《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赵莹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25页。
[26]Josef Gregory Mahoney,"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Dream:An Exercise of Political hermeneutics",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