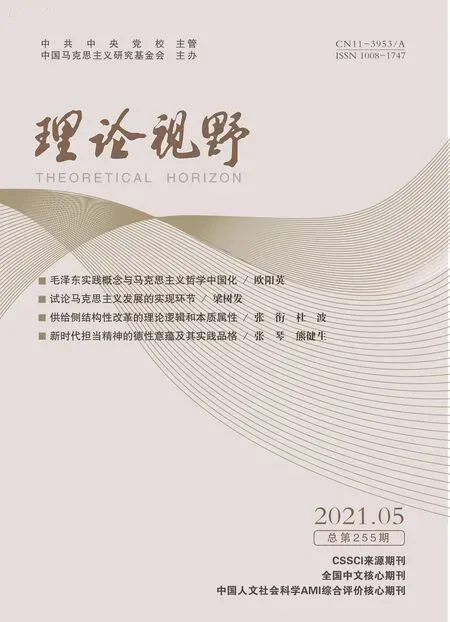毛泽东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2021-12-27欧阳英
■欧阳英
【提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创新的辉煌历程。以往,人们主要是将毛泽东实践概念放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体系中加以理解与阐释。严格说来,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的确立有其自身独立的重要意义,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毛泽东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随着中国化的实践概念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的正式问世与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坚实的发展基石。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历史进程提供了认识论保证,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推进中持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与领导者。在胜利迎来建党百年之际,深入地反思毛泽东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让我们真正以历史的视域来理解与把握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的确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由自发走向自觉的重要分水岭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创新的辉煌历程。以往,人们主要是将毛泽东的实践概念放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体系中加以理解与阐释,更多地强调的是毛泽东实践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发展、补充与完善[1]。但是严格说来,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的确立有其自身独立的重要意义,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毛泽东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随着中国化的实践概念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的正式问世与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坚实的发展基石。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历史进程提供了认识论保证,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推进中持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有关毛泽东实践概念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澄清
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但是单就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的发展来看却是较晚的,它的正式问世肇始于1938年毛泽东的《实践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不仅界定了实践概念,指出:实践就是人们“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还提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3]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由此保证了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的正式确立与系统化发展。至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翻开了新篇章,拥有了围绕毛泽东实践概念而展开的思想体系,并快速进入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阶段。但是,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韦克曼(以下简称韦克曼)曾认为:“毛在论文(指《实践论》——引者注)的开头明确区分实践与认识,从而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4]因此,关于毛泽东的实践概念,也是需要展开深入分析的,需要更加明确其科学性。围绕毛泽东实践概念,可以看到以下问题的存在:在毛泽东那里,为什么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积极主张调查研究,提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却会被讥为狭隘经验论?[5]“调查研究”与“社会实践”两个范畴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重要区别?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真的如韦克曼所认为的那样不能区分开来吗?毛泽东的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的知行观有什么样的联系?毛泽东的“社会实践”概念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对于上述问题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第一,就“调查研究”范畴来看,它是青年毛泽东的“动”范畴与成熟毛泽东的“社会实践”范畴之间的过渡环节,如此一来它既具有“动”的特点又具有“社会实践”的特点。《体育之研究》是青年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重要文章,其中着重阐述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动”。他指出:“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动必有道”[6]。这里的“动”,既包含有人类之动,也包含有宇宙天地之动。更进一步,动是有道的,有规律的,因而很明显是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中国式范畴。从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发展来看,“动”是一个重要概念,它的确立具有本体论意义。因此,从一个侧面说,“调查研究”本身具有“动”的特点,但它同时又是将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动”中的认识能动性抽离出来的结果,更多强调的是认识能动性,即如毛泽东所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7]从另一个侧面说,“调查研究”注重的是认识能动性,它又有着涵盖面上的不足,因此,它需要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实践”范畴,即成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之所以会被讥为狭隘经验论,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原因就在于调查研究主要与认识能动性相联,人们由此有可能根据其主要来自经验认识这一点,而将其归类为“狭隘经验论”。调查研究清楚地含有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提到的“亲身经历”的内涵[8],而它之所以有向“社会实践”范畴发展的必要性,就在于后者是认识的能动性与行动的能动性的统一。毛泽东社会实践范畴的提出,让人们充分看到了“调查研究”范畴在“狭隘经验论”问题上做出认识突破的可能,这是因为,如此一来人们便可将调查研究纳入社会实践的范围内加以理解,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狭隘的经验性认识。1941年3—4月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写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9]应当说,这段话正是在新的起点上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加以审视的结果,反映出毛泽东已将调查研究视为实践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与起点。
第二,从“社会实践”这个范畴中,不仅可以看到实践与人的社会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可以从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的意义上去把握实践活动。“调查研究”范畴体现了对实践问题的初步认识;毛泽东将“社会实践”范畴明确提出,反映出对实践问题的认识达到了高峰。“社会实践”范畴完整地涵盖了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全部内在规定性,无论是生产劳动还是军事活动,乃至科研活动,都包含在社会实践的外延之中。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特别提到了认识二元论的有害结果,说道:“人类思考时,不能不使用概念,这就容易使我们的认识分裂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个别的与特殊性质的事物,另一方面是一般性质的概念。特殊和一般本来是互相联系不可分裂的,分裂就脱离了客观真理”。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主观与客观并不是互相隔离的二元关系,而是能够实现统一的,而它们统一的桥梁就是社会实践,即“思维从社会实践中发生,同时又能动地指导实践”。因此,借助于“社会实践”范畴,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能够得到充分理解。
第三,就毛泽东为实践所下的定义,以及他明确指出认识的能动性和行动的能动性是主观能动性的两种形式而言,说明在他的头脑里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区别是明确的,因此进言之,毛泽东的实践观也绝不是将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等同起来的“实践主义”。人们可以在行动中实现认识,但是认识与行动却是有所区别的,行动能够成为认识的条件,却不能等同于认识。因此,毛泽东用“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来界定实践活动,也是对“干就是学习”这一思想的升华[10]。前面提到韦克曼认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实践与认识区别开来,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背离。[11]但果真如此吗?其实,如果从毛泽东关于实践的定义来看,将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之间区别明确化,不仅是可行的,并且恰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重要贡献,而不是背离。将此说成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背离,只表明韦克曼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是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12]在此实际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虽然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抽象的思维的存在;另一层是,费尔巴哈眼中的感性不是“人的感性的活动”即实践活动。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为了理解实践活动,他并没有将作为“抽象的思维”的认识活动与作为“人的感性的活动”的实践活动混为一谈,这一点与毛泽东是相一致的。正是基于对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加以区分,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13]这一著名论断。
第四,毛泽东的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之间有联系,但又有本质性的区别。实践第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14]因此,当毛泽东在《实践论》一书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作为书名突出出来,并将其作为分析中国哲学知行问题的重要工具时,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韦克曼曾写道:“任何受过中文教育的读者读到毛泽东《实践论》的最后一行文字,就会立刻联想起王阳明。毛的‘知行统一’立刻会使人想起王的‘知行合一’;两者都是指认识和行动的统一。”[15]在这里,韦克曼强调了毛泽东实践观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点之间的联系。但是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韦克曼并没有领悟到毛泽东实践观的思想精髓。毛泽东在《实践论》的末尾强调:“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6],只是旨在将中国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的理解与解决纳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关于这一点,正是冯友兰先生在1951年撰文说明的那样:“《实践论》以完全新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发展了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解决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且就中国哲学方面来说,“《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的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17]。
第五,从毛泽东实践观的历史形成来看,提出“社会实践”概念并将实践界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实践问题探究的重大飞跃,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在走向成熟。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反复使用“社会实践”“社会的实践”等概念,如,他在说明认识的真理性时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8]从语义学上看,将“社会”和“实践”统一在一起,组成一个概念,所包含的寓意是非常深刻的。这些概念的使用潜在地蕴含着毛泽东对以社会整体为基础的集体实践的一种认识与理解。毛泽东的“社会实践”概念帮助人们认清了集体实践的重大认识论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将实践视为个人的行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性事业,因此,在此可以看到对于集体实践的两层理解:一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加以认识过程中的集体实践性,另一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需要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实践基础上的。日本学者野村浩一曾评价道,“在毛泽东看来,实践的现实的过程在本质上带有集体性”,在毛泽东的“这种‘实践的思想’中的集体认识和集体实践的把握上,这种思想打开了‘认识论’=‘实践论’世界里的新地平线”[19]。在这里野村浩一提出,着力把握“集体认识”与“集体实践”是毛泽东实践观的主要特点;毛泽东提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正确看法是与他特别从集体实践角度理解实践分不开的。在野村浩一看来,正是在对“集体认识与集体实践”有所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打开了“认识论=实践论”世界里的新地平线,从而使认识论与实践论成了彼此不可分割的两大思想体系。因此,应当看到,正确把握集体实践的伟大意义,是毛泽东提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结论的重要的科学保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能够积极建立在集体实践基础上的重要保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道:“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段论述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平台,就是“千百万人民”团结起来所形成的“革命实践”即集体实践。
二、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认识论保证
由于实践的观点就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20],因此,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的确立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认识论保证。对此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解读:
第一,在毛泽东将实践明确界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的前提下,人们可以在认识论上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之间做“两张皮”的处理,而是更加强调它们之间的结合在认识论上的合理性,由此表明的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题中之义”。韦克曼曾评价说:“像毛(指毛泽东——引者注)那样的人如何成为伟大的革命家的?因为毛泽东大胆地否定那些既定的知识的实在性,并不惜‘冒风险’把他的命题交给真正的理论实践去检验,来寻求‘正确的’认识。但是,毛自己是否实际上意识到了这样一种冒险活动呢?不管他的成就在某些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多么重要,他本来也许不该进行这种存在主义的赌博?”[21]对于这种评价,我们应该充分地认清这只是一个不可知论者的认识,它的前提是在否定主观与客观能够相互沟通。严格地说,将主观的观念积极地运用于指导实践不仅不是冒险活动或赌博,反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中国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于这一点,正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22]
第二,在将实践界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的基础上,社会实践在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过程中的桥梁意义得到确立,毛泽东由此也在新的起点上确定了“实践第一”原则的科学性。这主要是因为,既然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这便意味着它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哲学家所理解的那种单纯意义上的行,即墨子的所谓的“亲身经历”,更不是王阳明的所谓的“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实践是已包含了实践主体的行本身与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东西,因此其本身就是一种综合物。当毛泽东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的目的以及检验真理的标准时,他显然确定的是“实践第一”的原则,但这种确定并不是简单地对“先行后知”原则的确定。倘若我们将此理解为对“先行后知”的确定,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评价苏格拉底的道德观和认识论时,毛泽东既肯定了苏格拉底提出知识与行为关系的辩证法的大功绩,同时又指出:“他只知知识给行为的影响,而不知知识的来源在于行为(实践),行为是决定知识的基础,又是检验知识的标准。”[23]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以实践为基本内容的行为是知识的基础与检验知识的标准。同时也正是这种实践,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基础。
第三,在毛泽东将实践界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的前提下,人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在认识论上积极防范经验主义错误的发生。所谓经验主义的错误就在于,让实践活动脱离理论指导,往往只是“想当然”地将实践放在经验之上,甚至让实践活动只是简单地停留在经验活动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必须防范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4]马克思将实践定义为“人的感性的活动”[25],深入地揭示了实践与“人的感性活动”之间紧密的内在关联。毛泽东将实践明确界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则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了经验活动与实践活动的联系与区别。尽管经验活动和实践活动都属于“人的感性的活动”,但二者之间并不是毫无差异,而是有着高低之分:经验活动主要建立在感性之上;实践活动则除了与感性相联,还具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特点。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说道:“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26]在此,由感觉获得的经验与“不能立刻理解”相联;“理解了的东西”则与“更深刻地感觉”相联。很显然,这两方面的内容之间有着高与低之别。因此,把经验与实践混为一谈,肯定是完全错误的。
第四,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体系化建设奠定了认识论基础。美籍学者弗兰西斯·苏曾说,“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从方法论上看表现在两个事实中:“一是他的综合实践是由许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组成,而且特别强调由列宁首创和运用的方法——灵活性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二是他对综合实践的解释充满了‘实践’、‘辩证法’、‘上层建筑’这类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这些都使毛泽东的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组成部分。”[27]在此,弗兰西斯·苏的分析使人们充分地看到了毛泽东实践观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性质,主要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的使用上。例如,“实践”“辩证法”“上层建筑”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而不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客观地说,毛泽东实践观积极地运用了“实践”“认识”“理论”等术语以及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因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了基本一致,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体系化建设是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认识论而展开的。
三、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的确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推进
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28]这是对在坚持实践第一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与当代推进的明确告诫,也表明了实践在这一过程中的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项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也是需要人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运用于实践才能加以大力发展的伟大事业。由此一来,充分重视毛泽东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美国学者本杰明·施瓦茨曾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到底是什么含义?”这一点是不清楚的,因为人们并不知道,“它是不是指个人的一种有意识的自由行为”,或者说,它是不是“与美国社会科学中所运用的‘行为’一词的意思相近?”[29]因此,倘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尚未对实践概念做出十分明确界定来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将实践直接界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史中也具有重要的分水岭的意义。自此之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发展,拥有了自身的思想认识基础。列宁曾经指出范畴的地位与作用:“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的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30]由此可见,面对毛泽东对于实践概念的确立以及明确界定,更应当看到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分界线性质。通过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及其相关思想的确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可以不再是一种自发的认识,而是能够成为一种主动的自觉行动。
没有“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在充分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向前推进,对此,正是毛泽东所谈的:“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31]习近平也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进一步还可以说,正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有了具体的行动保证,可以实现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飞跃。这是因为,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所谓的实践就是人们“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被积极地运用于改变中国实际的过程中实现了其中国化的发展。在正确理解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在积极运用于改变中国实际的过程中向前推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与理论要想实现中国化的发展,就必须与实践活动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同时需要明确的有两点:第一,必须深入地看清毛泽东将实践概念予以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以往人们大量谈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提出实践概念以及“实践的唯物主义”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但客观上说中国化的实践概念及其定义的确立与发展,却是与毛泽东的努力分不开的,而且是经历了一个思想发展过程的。第二,应当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地运用于改变中国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离不开实践活动,它必须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实践活动中得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因此,任何脱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难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曾尖锐批评,只懂外国不懂中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就是忘记了自己的祖宗,这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实践活动及其思想总结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具有意义的重点强调。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就是其“中国化”实践的开始。就此来看,人们既需要借助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实践活动来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又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就视为一个实践活动的过程。当前“中国道路”已成为世界焦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实践活动,正在欣欣向荣地开展起来。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完整与成熟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多方面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认识,而且从认识论根据上看,这一切的发生与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的确立与明确化是密切相联的。在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的引领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在积极地实现当代推进,展现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中国式发展。这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32]这一重要思想的现实写照。
注释
[1]参见雍涛:《毛泽东论范畴体系的改造》,《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11期。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3][10][13][16][18][22][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第181页;第296~297页;第296~297页;第272页;第292页;第286页。
[4][11][15][21]【美】费里德里克·韦克曼:《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第280页;第292页;第98页。
[5][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2页;第792页。
[6]《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7][31]《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第6页。
[8]《讲堂录》是毛泽东于1913年10月至12月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预料时作的课堂记录和读书笔记。
[12][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第501页。
[1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
[17]参见《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
[19]参见【日】野村浩一:《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张惠才、张占斌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20][30]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0页;第90页。
[23][32]《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页;第144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27]【美】弗兰西斯·苏:《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余瑞先等译,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90页。
[28]《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1页。
[29]《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页。